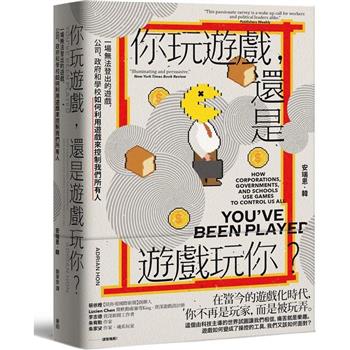每週都會傳來又有一間公司開始採用工作遊戲化的消息。亞馬遜在印度的公司採用「跑任務次數」來為送貨員計分,並且以板球為主題設計出「遞送超級聯賽」(Delivery Premier League),每三十天就會發出智慧型手機和摩托車做為獎勵。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也曾短暫推出一場實驗來幫助員工「建立興奮感和成就感」,內容是把他們的獎金換成彩券,當然了,只有全勤的績優員工拿得到。Uber、來福車(Lyft)、達美樂、克羅格(Kroger)、微軟、巴克萊銀行(Barclays)、聯合利華(Unilever)、T-Mobile、Instacart等公司全都用上遊戲化來管理旗下數以百萬計的員工。[編注]到了這種地步,列出沒有用上任何形式的遊戲化來管理員工的大型公司可能還比較簡單。
[編注]網約車Lyft是美國僅次於Uber的第二大叫車公司。Kroger為美國一家零售企業,同時也是世界第三大零售商。Instacart則是美國一家主打「超快速配送」的公司,用戶在線上訂購商品後,由該公司配合的購物者代為於指定超市採買並遞送。
一直以來,我都對工作場所的遊戲化抱持懷疑態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根本沒打算真的像是我設計遊戲時那樣,讓困難或是重複的活動變得有趣。取而代之的是在表面下工夫,這些「遊戲」通常只是在現成的業績追蹤系統上,套上一層點數、獎章、獎勵和排行榜,藉以盯著員工加快裝箱動作或是持續開車——這是最極致的通用遊戲化。
雖然如此,我還是得承認,確實可能有些工作場所中的遊戲化能讓員工感到快樂,只是不論遊戲化是好是壞,我們都沒有具體證據。大多數公司都不願意分享內部研究的成果,就算真的公開給大眾知道,也必然是粉飾得漂漂亮亮的宣傳材料。
即使存在先天上的偏差,還是有少數研究有系統地去檢視工作遊戲化是否有效,而結果好壞參半。短期而言,員工會更努力工作,也會更快樂,但是長期下來,只要花上幾個月,這個效果就會消退。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會產生反效果,導致員工表現得比原先還要差。有鑑於遊戲化的內容各不相同,很難從中汲取一個概論,不過就短期的改善效果來說,很有可能是因為「新奇效應」,也就是當你遇到環境或科技的改變時,會感到新鮮而有動力。
新奇效應背後的運作原理不難理解。如果有人改變了你的辦公室配置,像是幫你安裝一張新地毯,並且開始給每週最佳員工一張摸彩券,你會感覺受到雇主重視,進而激勵出更好的表現。可是幾週後,你習慣了新的辦公室。你可能抽到過一次獎品,但拿到的二十元美元抵用券有點雞肋,因而回到原本的工作模式。這就是為什麼新奇效應終究會消散,因為工作內容本質上並沒有改變。原本無聊的工作,還是很無聊。事實上,你還可能因此感覺比原本更無聊,因為你清楚發現老闆並不是重視你,只是想要拿你當小白兔實驗一下——於是你更不想工作。
很悶,對吧?不過,其中也有神祕之處。既然實驗證明,工作場所遊戲化並不會大幅增加員工的產值或快樂度,那為何企業仍前仆後繼地嘗試投入?
和其他未被證實的流行趨勢一樣,答案顯而易見:因為大家都這麼做。如果你在一間大公司的人資單位上班,你想要持續往上爬,你就要表現得像是你在做一些很創新而且很有用的事情。遊戲化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它很新穎,但又不會太新,它符合千禧世代與Z世代喜歡的潮流,而且還有很多現成的遊戲化平台可以套用,所以你也不用真的設法改變公司結構或流程。那如果它沒用呢?沒有人會怪你,反正大部分公司根本沒有真正評估過這些實驗的成效。這就是魅力科技的優點。
若這個說法成立,可以想見遊戲化很快就會和其他企業熱潮面臨同樣的命運:快速而靜默地消亡。或許現在仍時候未到,過去幾年來其實我一直痴痴等著工作場所遊戲化消亡。然而,現實卻是逆風高飛:它不斷成長。既然如此,一定還有別的解釋。或許遊戲化真的有助於企業提升獲利,只是不是我一開始想的那樣。除了增加員工滿意度或是生產力,企業要增加獲利還有一個辦法:降低成本。人事成本在絕大多數的公司中是沉重的負擔,因此減少人事支出相當重要,然而員工往往不樂見遭到減薪,這對雇主來說可不是好消息。這時就該遊戲化出手了,它給出一套間接減薪的策略。聯合航空在二○一八年曾嘗試將績效獎金改成抽獎的方式發放,當時他們的意圖過於明顯,很快便引發員工不滿。不過,其他公司就比較順利地利用遊戲化的方式來降低薪資和獎金,尤其是針對低薪的員工。
艾米莉.關德斯伯格(Emily Guendelsberger)在《準時打卡:低薪工作對我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令美國陷入瘋狂》(On the Clock: What Low-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一書中,描述了亞馬遜倉儲工人在一小時內完成一百次貨物揀選的獎勵:得到一兩個「積分」(vendor dollars) [編注],可用於公司內的一些(還不是全部)販賣機。二○一九年,另一位前亞馬遜倉儲工人波斯汀.史密斯(Postyn Smith)描述了更為複雜的「履行遊戲」(FC Games,取自「訂單履行中心」[Fulfillment Center],亞馬遜對其倉庫的稱呼)。他在倉庫中離職率最高的部門出入倉揀貨站工作,他的螢幕上會顯示遊戲畫面:「大部分的遊戲都會有一些競爭。象徵你的飛龍會隨著你的進度向亞馬遜的吉祥物飛去,你要一對一和附近的同事競賽,或是參加樓層對樓層的團體賽,看誰的進度最快。另一款遊戲中,你要嘗試盡可能完成任務,於是你就要愈做愈快,愈做愈久。他們也會在你提前結束用餐休息時間時給你獎勵。這些程式都被巧妙設計過,要讓你不自覺想要做得更多、更快、更久。」
[編注] 亞馬遜內部貨幣稱為「Swag Bucks」,可以用來兌換T-shirt或其他物品。
在不增加薪水的前提下增長工時,實際上就相當於減薪。更糟的是,長期高壓的工作環境會導致嚴重的人員耗損。正如關德斯伯格在書中所提到的,無數亞馬遜倉儲工人承受著身體不適與疲憊,根據新聞組織《揭露》(Reveal)的報導,其設施的嚴重工傷率超過倉儲業平均兩倍之多。
史密斯表示,「其中一位遊戲設計師向我提起,在倉儲部門採用他們的遊戲之後,他們一度很難讓該部門員工參與其中。幾個月下來,大部分的螢幕都被晾在一邊……很多人根本不會去和這些螢幕互動,它們就只是在一旁轉著待機畫面。」
史密斯告訴我們,履行遊戲最有用的地方並不是娛樂效果,甚至不是讓人從工作中分心,而是用來檢視自己當天的工作效率如何,以免被打小報告。對史密斯來說,新奇效應沒有維持多久。「這些『履行遊戲』相較於這份勞心勞力的工作本質帶來的後遺症、日復一日感覺毫無變化、無止盡的工作量,遊戲簡直連OK繃都稱不上。事實上,在一些比較困難的工作層面上,這些遊戲只是雪上加霜。」
即便如此,科技新聞媒體《The Information》指出,在二○二一年年間,亞馬遜更進一步用了像是築城大師、任務大師、飛龍對決、宇宙揀貨專家之類的名稱,分別將履行遊戲擴大至全美至少二十個州的倉庫。該公司聲稱並沒有監控遊戲結果或是依此來懲罰不參加的員工,考慮到他們先前的名聲,這至少是件好事。《The Information》訪問到的員工對此各持己見:有的人為了避免過勞,會盡可能避開這些遊戲,也有人坦言,「這些遊戲沒有做多好,雖然有些人會覺得至少讓連上十小時的無腦班不那麼無聊,所以還算喜歡。」
其他公司則是將工作遊戲化披上「工人賦權」([worker empowerment]即權力下放給員工)的羊皮。關德斯伯格討論了來自麥當勞和其他速食餐廳的電子設備供應商HME集團業務手冊的一段話:「服務速度計時器要與壁掛螢幕連結,讓員工能在時間上競速,在管理層設定的目標內完成訂單。大型計時器則要維持在員工的視線範圍內,增強完成訂單的緊迫感……在團隊成員之間提供誘因和良性競爭,就能讓他們真的享受工作,覺得有挑戰性,同時提升顧客滿意度並增加銷售。管理層和營運者可以透過計時數據評估員工績效,並做出必要的調整。」
團隊當中,確實有些成員可能會在這些無止盡的數位目標中找到工作樂趣,但真正受益者仍是管理層和加盟主,他們可以從底下的員工身上得到更多產值,還有數據可以用來管訓懲罰績效不佳的員工。給部分團隊成員帶來的樂趣只是順帶的附加價值。
這些公司還厚顏無恥地宣稱自己的遊戲化系統是給予員工更多選擇,現實根本相反。HME集團所說的「能在時間上競速」,好像這是可以選擇的機會似的。亞馬遜的倉儲工人若是遲到或是上廁所回來晚了,就會「獲得」分數。關德斯伯格引用了一段該公司主管說過的話:「你有六分的機會,若你達到滿分,你和亞馬遜的契約就會終止。盡量維持低分,這樣你才有應變緊急狀況的彈性。」
這套選擇心法聽起來有點自由論的味道,比起控制和局限,這種遊戲化給了工作者個人選擇的自由——試著證明自己的價值,你就可以升職。如果你做了對的選擇,維持低懲罰分數,超出你的績效目標,自然就會被升職。如果你失敗了,就算是為了照顧生病的孩子而睡過頭,也不能怪這套系統不公平,因為是你沒照規矩來。
可是這種選擇的概念只是假象。工人實際上只能選擇遵循亞馬遜的所有規則,否則就會被開除。這不是選擇──而是脅迫。
***
Uber在遊戲化經驗方面顯得較為老謀深算。它必須如此:因為亞馬遜是聘用員工,內聘員工給了公司工作條件的控制權,用以交換穩定的收入。相較之下,Uber駕駛大致上是獨立接案,照理說他們可以隨意地自由來去。此外,職業駕駛通常還能選擇要和哪間共乘服務公司合作,因此Uber沒辦法像亞馬遜逼得那麼緊。進而代之,Uber在遊戲化的獎勵上是真金白銀的任務和獎金,為誘使駕駛盡可能為Uber多開幾趟車。Uber經濟和政策研究主管強納生.霍爾(Jonathan Hall)在二○一七年告訴《紐約時報》,「我們設定出最佳預設值,那就是我們希望你盡可能多完成工作。當然,我們不會用任何方式逼你去做。但那是預設值。」
問題來了,若你沒有完成Uber的任務(也被稱為「機會」),像是完成連續三趟的系列任務來換得額外六美元的獎金,或是前往特定區域接案來得到獎金,你要賺到像樣的薪資就會變得更困難。根據「Ridester」網站在二○二○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美國Uber駕駛的時薪中位數(包含小費)為十八.九七美元。但Uber駕駛不是內聘員工,因此他們得自行負擔各種開銷,像是汽車貸款、燃料費,該網站估計這些成本落在每小時七.五到十五美元之間。這使得實際報酬低於每小時十美元,遠低於亞馬遜付給倉儲工人的最低薪資十五美元。
Uber不是唯一利用工作者的薪資補償來玩零工經濟的公司。來福車會提供接受所有搭車請求的駕駛「連續接案獎勵」(Streak bonuses)。Instacart、Postmates、Shipt等外送公司則是以完成每週最低任務次數的方式發放獎金。喬許.齊薩(Josh Dzieza)在「Curbed」網站的文章中指出,在紐約有些工作者稱這種遊戲化系統為「patrón fantasma」,意思是幽靈老闆。
為了以最低成本達到最高生產力,這些公司不斷調整其額外津貼的複雜條件與真義,藉此混淆工作者對整體薪酬的理解。網路論壇Reddit上一份針對Shipt新手的非官方指南,其中解釋了它以「接案率」、乘客評分、會員配對模式組合來決定哪些工作者會接到哪些工作。這篇密密麻麻兩千四百字的指南,每隔幾個月就會追加「此回覆已過期」、「請閱讀置頂更新資訊」的警語。這種混淆方式讓工作者很難發現他們的薪資變少,也無法預測未來的薪資。
當然,如果零工經濟工作者的整體薪資不是如此之低,這些任務、額外津貼和獎勵也不會有什麼影響。可惜現實如此,每天可以獲得幾次六美元額外津貼就已經占去收入一大部分,這已經稱不上是額外津貼了——只是依照指令(案件量)計算的薪資。這就是另一種強迫的方式。Uber也不覺得有必要和工作者講公平。「the Rideshare Guy」網站創辦人哈利.坎伯(Harry Campbell)就在科技新聞媒體《The Verge》的訪談中表示:「他們鼓勵駕駛在特定時間去特定地點,但是並不保證你到了那裡會載得到客人。」
倒是駕駛肯定得跟著Uber的方向盤走。
***
回到我們先前提出的問題:如果工作遊戲化長期來說並沒有帶來更高的生產力,為什麼仍有許多公司持續不懈地嘗試?答案是,因為它能用看起來吸引人又友善的方式來壓低工作者的薪資。
對於像是亞馬遜、Uber、聯合航空這種大公司來說,有一整個世代的人玩遊戲長大,將點數、任務、排行榜視為「有趣」的東西,公司又能用這些來控制和懲罰這些人,簡直是愉快的偶然。也許不久之後,你的上司會告訴你,由於你沒有完成一項「選擇性」任務,所以他扣發了你百分之十的預期薪資。
當然,躲在工作遊戲化這套系統背後的設計師也不是刻意要重現《黑鏡》(Black Mirror)中的反烏托邦。在時間和預算都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往往已經盡力讓這些系統讓人感到正面、有趣。可愛的畫面、引人注目的動畫和有趣的文案都有助於降低人們的戒心,特別是它們還套上虛擬城市建築師或是屠龍勇者的角色扮演的時候。它們也真的可以很好玩,至少在剛進去的前幾天是如此。
但我懷疑有多少人過了幾週、幾個月,還會覺得這種工作遊戲化是有趣的,儘管亞馬遜敦促倉儲工人「努力工作,樂在其中,創造歷史」。就算遊戲變得乏味,這種工作遊戲化仍可成功讓工人相信,工作績效不彰──以及相應的低工資──是他們自己的錯,而不是資方的問題。我們認為遊戲設計是公平的,每個玩家都能有贏的機會。但在大多數工作場所遊戲化的系統中,如果你輸了,那是因為它本來就要你輸。
而且,正因為遊戲化通常都是高度自動化並透過數位方式傳遞,管理層心理操縱員工的規模可以達到前所未有的層級。不久之前,若有人想扣你的薪水,他們得當面跟你談。遊戲化會把壞消息粉飾過,變成一則不帶感情的友善通知傳到你手機上:「噢,可惜你不想多做兩小時來賺取額外十美元的獎金。那就下次囉!」
那這些工作者還去參與一場被操縱的遊戲是傻了嗎?不。他們別無選擇。在某些地區,亞馬遜這種巨擘可能是主要雇主,有著壟斷地位,也就是說,他們是勞動力市場的主要買家。在就業變得愈趨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下,麥當勞或亞馬遜可以單方面支配工作者,一點都不讓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