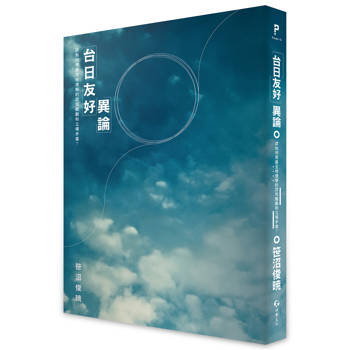序 被隱蔽在台日友好矛盾中的旅台日人
本書中的文章大多來自二〇二一年七月至二〇二四年二月在「獨立評論@天下」上發表的連載專欄「和僑鄙言」。自二〇二一年迄今,台灣、中國、日本以及世界各國發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事件,如新冠病毒蔓延、烏克蘭戰爭爆發、東京奧運、台海危機論述盛行、安倍晉三遭刺殺、日本能登大地震等等。在本書中,我藉由這些時事問題談論在約十九年的台灣生活中我時常思考的事情。
然而,我畢竟是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而非政治學、社會學的專家。書中有些內容含有為提供讀者、我自身思考材料的「假說」,不一定基於人文科學專門領域的實證研究,而有些部分則是介紹在日本社會或學術界中早已流通的論述,同時向台灣讀者們表達我自身的想法。因此,本書不能說是正統的學術專書,而是為一般讀者書寫的社會文化評論集。不過,若本書有稍微獨創的部分,那就是從一個旅台日籍人士的「跨境」處境之角度,批判地反思與評論橫跨台日間的思想矛盾,並且為台灣一般公眾直接以中文書寫。
先前我之所以取「和僑鄙言」這個專欄名稱,是因為身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我希望從「異邦人」角度發出與台灣主流思想不同的聲音。也就是說,我本來意圖讓「鄙」一字代表著思想上的「邊陲」,但沒想到竟然有幾位朋友跟我說:「你怎麼那麼謙虛。」其實我絲毫沒有「客氣」念頭,但似乎由於我的中文語感不足,而沒想到竟然令人聯想到「日本民族性」刻板印象。由於如此,本書重新取了書名,以免造成誤會。
台灣和日本之間的思想矛盾、齟齬
約五年前,我出版了《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游擊文化,二〇二〇)一書,那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以文藝評論形式談論以台日為主軸的東亞思想問題。書寫那本書時,我盡量考慮一般讀者,但畢竟是文藝評論,且我只不過是一個無名作者,能獲得的讀者數量、範圍難免受限,但後來幸好能得到在「獨立評論@天下」上發表文章且向更加廣泛的讀者層直接發言的機會。事實上,剛開始連載時,起初我沒有明確的核心理念,而只是籠統打算透過各種社會事件、文化現象、歷史背景等隨心隨意寫下我自己的想法而已。但現在回頭來看,發現那些文章的背後一貫有著一個問題意識――當代台日間有著思想分歧、扭曲、不平等等各種矛盾。
我本來在日本出生長大,專攻日本近現代文學,三十二歲時遷來台灣。在那之前,我幾乎只在日本國內的社會思想脈絡中思考各種問題,沒認真意識過日本與其他亞洲地區之間存在著,社會意識、思想脈絡、思維方式等的矛盾、分歧。但在台灣的長年生活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台日間的思想齟齬其實相當嚴重,並且深刻影響到雙方的互相認識。
關於台日間的矛盾,我從前在推特(X)上曾以日語寫下如下內容,獲得不少贊同。
①許多日本右派、保守派欣賞台灣的「親日」一面,卻不願意思考台灣政治社會的先進一面。
②不少日本左派、自由派過於稱讚台灣的先進自由一面,卻忽略其黑暗面向。
③部分日本左派、自由主義者過於小看在國際社會中台灣所處於的危機。
④不少台灣人士對日本右派的「親台」示好,但忽視其反民主主義、反自由主義一面及其危險性。
⑤不少台方人士忽略日本戰後民主主義、和平主義,也過於輕忽許多日方人士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的歷史。
不用說,不僅對日關係,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也有彼此認識上的問題。但在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特殊脈絡下,台日間形成的思想矛盾特別嚴重,就如難以解開的亂絲一般。令人頭痛的是,基於這種矛盾的互相認識,與許多人士自身的身分認同、政治立場息息相關,他們往往沒意識到那是「問題」。然而我認為,若要推行「台日友好」,首先該做的就是反思自己而認知台日間有著這些齟齬、矛盾的存在。
現今台灣社會中許多人呼籲「台日友好」,日方則掀起「台灣潮」,台日民眾的交流變得頻繁多元,雙方的互相認識有相當大的進展,但許多人卻似乎刻意忽視或沒意識到相關的矛盾問題。即使針對對方的資訊和知識增加,若忽略那些思想、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歧矛盾,在水面下雙方的意識齟齬不斷地增大,最後恐怕會「突然」導致無法挽回的破局。橫跨台日間的這些矛盾和齟齬,確實是極為難以解開的。但無論如何,至少必要的是,台日雙方民眾認識這種矛盾、齟齬的存在本身。
互相迴避「批判」的台日關係
約十九年前,我剛來台灣時,同事們給我一些關於台灣生活的建議,我還記得其中之一是「最好不要提及政治話題」。但我一直無視此勸告,時常聊聊政治、社會、歷史、思想相關話題,甚至十幾年後在台灣出書,內容都涉及「敏感」議題。讀者們必定會發現,本書含有對於台灣社會的批判意見。而我在書中到處痛批現代日本社會中的各種問題,有些讀者也可能會對此部分感到不愉快,因為部分台灣民眾似乎接觸到針對「日本」的批判,就懷有如自己遭攻擊似的情緒。
據我觀察,不少台灣民眾只關注日本社會中漂亮一面而迴避提及黑暗面向。例如,在我所任教的系所裡,不少同事時常批判地解釋日本的社會問題,但部分學生似乎將之理解為「系上老師們不喜歡日本」。「批判某個政治體制、政府、社會」與「厭惡該國家」截然不同,但部分人將這兩者混淆。此外,當我提到日本政治社會問題時,有時會遇上「此種論述讓企圖拉開台日距離的勢力得利」、「其他國家也有此問題」這種反應。我並非拒絕別人提出反駁,但那種說詞的背後,存在對於任何事情都從黨派、政治角力的角度來理解的思維方式。在這種邏輯下,實際存在著的問題本身和其受害者以及為改善它而奮鬥的人們永遠被忽略。
另一方面,由於對侵略戰爭、殖民主義的贖罪意識,二戰後許多日方人士有對於近鄰國家相當客氣的傾向。雖然近年來關注台灣的日本民眾大幅增加,許多人公然說「喜歡台灣」,但為台灣正面提出批判意見的人卻還不多。其實,我屢屢看到,在台灣旅遊或生活的日人諷刺地「評論」台灣,例如:交通安全太過惡劣;人行道無法正常行走;鐵皮屋和違章建築很多;裝在大樓外牆上的冷氣室外機看起來很可怕;店家倒閉後看板都不會撤除;到處都有錯誤的日文字;餐桌、洗手間不夠乾淨;有些食物油膩或太甜;時間觀念籠統等。那些人聊到這種無害無毒的生活相關話題時非常健談,嘴巴犀利惡毒,但一旦遇上較為「抽象」、「敏感」的政治社會議題,他們忽然就變得沉默寡言,或者直接模仿「台派」人士的口吻,只說出「台灣自由民主」、「台灣是個國家」、「台灣很可憐」等安全套語,令台方高興。
不過,我認為欠缺批判言論的「台日友好」,不能說是真正的「友好」。若台灣和日本真的要加強關係,就必須打造能互相坦承地交換意見的風氣。尊重對方是該有的態度,但永遠過於擔憂踩到對方國族情緒的地雷,始終迴避批判性對話,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賴關係。
做為一個日籍人士,我為何在台灣以中文發聲?
雖然如此,我還是無法完全否定日方人士不敢正面批判台方的情緒,因為即便殖民時代早已結束,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仍留下其後遺症,並且現在台日間仍有國家規模、國際地位等差別所帶來的不平衡關係。前提條件不平等且其原因中許多部分來自日方,在此情況下日方有什麼資格與台方「平等」地交換批判意見呢?
如本書中所述,現在台日間有語言方面的不平等關係。近來在日本,中文學習者人口大幅增加,許多日方人士在台灣積極以中文交談,但與學習日語的台灣人相比,其數量、比例仍然較低。並且許多台方人士似乎以為歐美白人和日人「較高級」,而內化「國際交流=英日語」的觀念,一看到歐、美、日人士就條件反射似地試著用英、日語交談。反之,許多日人雖然對於歐美白人懷有類似的觀念,卻認為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們以日語跟自己搭話是理所當然的。這種不平等的語言觀念和語言使用狀況,顯然是近代以後的「脫亞入歐」、殖民主義及其後遺症所留下的價值觀使然。
上面我談到台灣有迴避正面批判日方之嫌,但其實現在有不少台灣籍作家、記者、學者等,在日本媒體中以日語進行批判性言論活動。非文字工作者的民眾也在社群網站中向日方以日語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時發表相當嚴厲的批判意見,糾正日方台灣相關論述的問題。日方人士也許會以為台灣人擅長外語,對他們來說以日語說話是不怎麼樣的。但認真學習過外文的人都知道,在異國以其國家的語言發出批判意見,此行為會給予本人極大的心理壓力,哪怕你的講話或文筆聽起來或讀起來極為順暢,此問題都不可能消失。周圍都是當地人,只有你艱苦奮鬥地運用他們的語言對抗那些母語者,討論內容可能也會有你從未想過的當地社會文化脈絡,而讓你陷入出乎意料的窘境。平時向你示好的當地朋友們,一旦你講出批判意見,即使你遭攻擊且吃虧,說不定也不會幫你講話。雖然任何社會必定會有些人理解且同情這種苦難,他們可能會站在你那邊一同反擊對方,但你最後還是得自己應付落到你身上的子彈。最大的問題是,在當地社會中主導權永遠在母語者手上。
自日據時代至二戰後,許多台灣作家、學者、政治運動家等以日語從事創作、學術、言論活動,在(前)殖民地宗主國的平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的日文讀起來極為流暢,但他們卻仍不可能完全沒遭遇那種苦難,或多或少都在台日不平等關係所形成的逆境中搏鬥。反之,迄今為止,有多少日人在台灣的語言平台上進行批判性言論活動呢?現在在日本,中文學習者數量增多,對台灣的關注度也大幅提高。在台灣發表中文文章、學術論文等的日籍作家、學者、記者隨之逐漸增加,在社群網站中已有不少日籍網友以中文與台方交換意見。但總體而言,與以日語進行言論活動的台灣人相比,其數量和比例仍明顯為少,此狀況反映出台日間仍保留的不平等關係。
我之所以在台灣用中文書寫的原因,是希望對抗此情形。我認為,身為一個屬於前殖民地宗主國出身的人士,既然提出對於前殖民地社會的批判意見,至少要把自身投入到與當地人平等的平台上,在從前那些台灣日語作家們同樣的條件下進行言論活動。或許,以中文發表文章的日人增加區區一個也不可能推翻大局,但就我而言,這至少是一種如江湖人般的倫理意識,也是不願認輸的固執。我不願意在被日語防護膜圍繞的安全地帶中單方面批判台方,也不想輸給以日語跟日本主流社會堂堂正正對峙的台灣人士之勇氣。
剛遷來台灣時,我完全不會台灣的語言,日常生活都不如意,有時陷入出乎意料的困境。後來我的中文能力稍微進步,但現在還無法說是完美,當因語言障礙而陷入困難時,周圍的台灣人士幫助我。事實上,就我而言,中文書寫是對於台方的日語之「報恩」,但此「報恩」不可能是全面稱讚台方,因為「批判」就是文學家的生命線。此外,所有的批判性言論活動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才能成立的。本書中不少內容涉及針對台灣社會的批判,這是因為我現在身在台灣。但若我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社會脈絡中向不同的讀者層發表文章,我說不定會寫下擁護台灣的論述,以對抗當地的主流思想。
就我而言,「台灣」、「日本」算什麼呢?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也許會說:「做為一個日本人,你怎麼那麼關心台灣。」不過,請不要誤會,「日本人」並非我的身分認同的一切。我在日本靜岡縣東部鄉下出生長大,在茨城縣筑波市度過青春時代,而後搬遷到花蓮、台中。在各地遇到的具體人們、社會、自然風景、都市環境等,確實是現在構成「我」的重要因素,但「日本」各地的許多土地我沒親自踏上過,也不可能認識所有的「日本人」,並且在我人生中給予「我」深刻影響的人們中,有許多是外籍人士。對我而言,「日本」畢竟是個由各種媒體所打造的「想像意象、形象」,這雖然也算是構成「我」的因素之一,卻絕非一切。說到底,我畢竟是個個人主義者,我所寫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而我根本沒資格擅自代表全日本發言。
雖然如此,與外籍人士討論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時,我還是有肩負著某些歷史社會脈絡發聲的「責任」。日本和台灣之間有曾殖民/被殖民的特殊歷史,因此即使我自以為是個「世界公民」,但在台灣發表自己的意見時,仍無法逃脫做為一個日籍人士的歷史、社會責任。這種「國家自我認同」和「歷史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難以解釋,目前我無法以更明確的理論來說明,但在此我將這兩者區別開來。在本書中我有時會寫下「做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但這種句子與其說代表著我的「國家、民族認同」,不如說是「歷史社會責任」。
再者,我不敢說出「我喜歡台灣」那類句子。因為對我而言,「台灣」並非單純的遊玩、觀賞場所,也不是觀察、分析對象,而是我自己所生活的場所,它已經變成了構成「我」存在本身的核心因素之一,因此我無法以「喜歡/不喜歡」那種將事情單一化的說法談論它。我在台灣與各種人們相逢,經歷各類的事情,對此複雜多元的情緒交錯,實在難以言喻。並且我不可能認識台灣所有的地方、民眾。事實上,在日本生活時也有一樣的情形,因此我對於「日本」的感受也無法以「喜歡/不喜歡」來形容。
另一方面,我確實希望台日民眾能打造更好的社會。其實不僅台日,全世界所有的民眾本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因為某種命運的捉弄使得我「偶然地」出生於日本,而後在台灣討生活,因此我接觸且思考台日相關議題的機會較多,並且做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我確實有義務該承擔某些歷史社會責任。我較為頻繁探討台日的理由,並非認為只有台灣和日本有出眾的價值。儘管如此,既然在台灣生活十九年之久,在我自身的生命中台灣確實有特別的存在感。對我而言,台灣並非用來加強自己的既有認識、意識形態之場所,而是充滿未知的「他者」之空間,它給予我機會懷疑自己既有的自明性且不斷重新打造思想。
本書中的文章大多來自二〇二一年七月至二〇二四年二月在「獨立評論@天下」上發表的連載專欄「和僑鄙言」。自二〇二一年迄今,台灣、中國、日本以及世界各國發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事件,如新冠病毒蔓延、烏克蘭戰爭爆發、東京奧運、台海危機論述盛行、安倍晉三遭刺殺、日本能登大地震等等。在本書中,我藉由這些時事問題談論在約十九年的台灣生活中我時常思考的事情。
然而,我畢竟是個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而非政治學、社會學的專家。書中有些內容含有為提供讀者、我自身思考材料的「假說」,不一定基於人文科學專門領域的實證研究,而有些部分則是介紹在日本社會或學術界中早已流通的論述,同時向台灣讀者們表達我自身的想法。因此,本書不能說是正統的學術專書,而是為一般讀者書寫的社會文化評論集。不過,若本書有稍微獨創的部分,那就是從一個旅台日籍人士的「跨境」處境之角度,批判地反思與評論橫跨台日間的思想矛盾,並且為台灣一般公眾直接以中文書寫。
先前我之所以取「和僑鄙言」這個專欄名稱,是因為身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我希望從「異邦人」角度發出與台灣主流思想不同的聲音。也就是說,我本來意圖讓「鄙」一字代表著思想上的「邊陲」,但沒想到竟然有幾位朋友跟我說:「你怎麼那麼謙虛。」其實我絲毫沒有「客氣」念頭,但似乎由於我的中文語感不足,而沒想到竟然令人聯想到「日本民族性」刻板印象。由於如此,本書重新取了書名,以免造成誤會。
台灣和日本之間的思想矛盾、齟齬
約五年前,我出版了《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游擊文化,二〇二〇)一書,那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以文藝評論形式談論以台日為主軸的東亞思想問題。書寫那本書時,我盡量考慮一般讀者,但畢竟是文藝評論,且我只不過是一個無名作者,能獲得的讀者數量、範圍難免受限,但後來幸好能得到在「獨立評論@天下」上發表文章且向更加廣泛的讀者層直接發言的機會。事實上,剛開始連載時,起初我沒有明確的核心理念,而只是籠統打算透過各種社會事件、文化現象、歷史背景等隨心隨意寫下我自己的想法而已。但現在回頭來看,發現那些文章的背後一貫有著一個問題意識――當代台日間有著思想分歧、扭曲、不平等等各種矛盾。
我本來在日本出生長大,專攻日本近現代文學,三十二歲時遷來台灣。在那之前,我幾乎只在日本國內的社會思想脈絡中思考各種問題,沒認真意識過日本與其他亞洲地區之間存在著,社會意識、思想脈絡、思維方式等的矛盾、分歧。但在台灣的長年生活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台日間的思想齟齬其實相當嚴重,並且深刻影響到雙方的互相認識。
關於台日間的矛盾,我從前在推特(X)上曾以日語寫下如下內容,獲得不少贊同。
①許多日本右派、保守派欣賞台灣的「親日」一面,卻不願意思考台灣政治社會的先進一面。
②不少日本左派、自由派過於稱讚台灣的先進自由一面,卻忽略其黑暗面向。
③部分日本左派、自由主義者過於小看在國際社會中台灣所處於的危機。
④不少台灣人士對日本右派的「親台」示好,但忽視其反民主主義、反自由主義一面及其危險性。
⑤不少台方人士忽略日本戰後民主主義、和平主義,也過於輕忽許多日方人士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的歷史。
不用說,不僅對日關係,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也有彼此認識上的問題。但在近現代東亞歷史的特殊脈絡下,台日間形成的思想矛盾特別嚴重,就如難以解開的亂絲一般。令人頭痛的是,基於這種矛盾的互相認識,與許多人士自身的身分認同、政治立場息息相關,他們往往沒意識到那是「問題」。然而我認為,若要推行「台日友好」,首先該做的就是反思自己而認知台日間有著這些齟齬、矛盾的存在。
現今台灣社會中許多人呼籲「台日友好」,日方則掀起「台灣潮」,台日民眾的交流變得頻繁多元,雙方的互相認識有相當大的進展,但許多人卻似乎刻意忽視或沒意識到相關的矛盾問題。即使針對對方的資訊和知識增加,若忽略那些思想、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歧矛盾,在水面下雙方的意識齟齬不斷地增大,最後恐怕會「突然」導致無法挽回的破局。橫跨台日間的這些矛盾和齟齬,確實是極為難以解開的。但無論如何,至少必要的是,台日雙方民眾認識這種矛盾、齟齬的存在本身。
互相迴避「批判」的台日關係
約十九年前,我剛來台灣時,同事們給我一些關於台灣生活的建議,我還記得其中之一是「最好不要提及政治話題」。但我一直無視此勸告,時常聊聊政治、社會、歷史、思想相關話題,甚至十幾年後在台灣出書,內容都涉及「敏感」議題。讀者們必定會發現,本書含有對於台灣社會的批判意見。而我在書中到處痛批現代日本社會中的各種問題,有些讀者也可能會對此部分感到不愉快,因為部分台灣民眾似乎接觸到針對「日本」的批判,就懷有如自己遭攻擊似的情緒。
據我觀察,不少台灣民眾只關注日本社會中漂亮一面而迴避提及黑暗面向。例如,在我所任教的系所裡,不少同事時常批判地解釋日本的社會問題,但部分學生似乎將之理解為「系上老師們不喜歡日本」。「批判某個政治體制、政府、社會」與「厭惡該國家」截然不同,但部分人將這兩者混淆。此外,當我提到日本政治社會問題時,有時會遇上「此種論述讓企圖拉開台日距離的勢力得利」、「其他國家也有此問題」這種反應。我並非拒絕別人提出反駁,但那種說詞的背後,存在對於任何事情都從黨派、政治角力的角度來理解的思維方式。在這種邏輯下,實際存在著的問題本身和其受害者以及為改善它而奮鬥的人們永遠被忽略。
另一方面,由於對侵略戰爭、殖民主義的贖罪意識,二戰後許多日方人士有對於近鄰國家相當客氣的傾向。雖然近年來關注台灣的日本民眾大幅增加,許多人公然說「喜歡台灣」,但為台灣正面提出批判意見的人卻還不多。其實,我屢屢看到,在台灣旅遊或生活的日人諷刺地「評論」台灣,例如:交通安全太過惡劣;人行道無法正常行走;鐵皮屋和違章建築很多;裝在大樓外牆上的冷氣室外機看起來很可怕;店家倒閉後看板都不會撤除;到處都有錯誤的日文字;餐桌、洗手間不夠乾淨;有些食物油膩或太甜;時間觀念籠統等。那些人聊到這種無害無毒的生活相關話題時非常健談,嘴巴犀利惡毒,但一旦遇上較為「抽象」、「敏感」的政治社會議題,他們忽然就變得沉默寡言,或者直接模仿「台派」人士的口吻,只說出「台灣自由民主」、「台灣是個國家」、「台灣很可憐」等安全套語,令台方高興。
不過,我認為欠缺批判言論的「台日友好」,不能說是真正的「友好」。若台灣和日本真的要加強關係,就必須打造能互相坦承地交換意見的風氣。尊重對方是該有的態度,但永遠過於擔憂踩到對方國族情緒的地雷,始終迴避批判性對話,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賴關係。
做為一個日籍人士,我為何在台灣以中文發聲?
雖然如此,我還是無法完全否定日方人士不敢正面批判台方的情緒,因為即便殖民時代早已結束,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仍留下其後遺症,並且現在台日間仍有國家規模、國際地位等差別所帶來的不平衡關係。前提條件不平等且其原因中許多部分來自日方,在此情況下日方有什麼資格與台方「平等」地交換批判意見呢?
如本書中所述,現在台日間有語言方面的不平等關係。近來在日本,中文學習者人口大幅增加,許多日方人士在台灣積極以中文交談,但與學習日語的台灣人相比,其數量、比例仍然較低。並且許多台方人士似乎以為歐美白人和日人「較高級」,而內化「國際交流=英日語」的觀念,一看到歐、美、日人士就條件反射似地試著用英、日語交談。反之,許多日人雖然對於歐美白人懷有類似的觀念,卻認為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們以日語跟自己搭話是理所當然的。這種不平等的語言觀念和語言使用狀況,顯然是近代以後的「脫亞入歐」、殖民主義及其後遺症所留下的價值觀使然。
上面我談到台灣有迴避正面批判日方之嫌,但其實現在有不少台灣籍作家、記者、學者等,在日本媒體中以日語進行批判性言論活動。非文字工作者的民眾也在社群網站中向日方以日語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時發表相當嚴厲的批判意見,糾正日方台灣相關論述的問題。日方人士也許會以為台灣人擅長外語,對他們來說以日語說話是不怎麼樣的。但認真學習過外文的人都知道,在異國以其國家的語言發出批判意見,此行為會給予本人極大的心理壓力,哪怕你的講話或文筆聽起來或讀起來極為順暢,此問題都不可能消失。周圍都是當地人,只有你艱苦奮鬥地運用他們的語言對抗那些母語者,討論內容可能也會有你從未想過的當地社會文化脈絡,而讓你陷入出乎意料的窘境。平時向你示好的當地朋友們,一旦你講出批判意見,即使你遭攻擊且吃虧,說不定也不會幫你講話。雖然任何社會必定會有些人理解且同情這種苦難,他們可能會站在你那邊一同反擊對方,但你最後還是得自己應付落到你身上的子彈。最大的問題是,在當地社會中主導權永遠在母語者手上。
自日據時代至二戰後,許多台灣作家、學者、政治運動家等以日語從事創作、學術、言論活動,在(前)殖民地宗主國的平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的日文讀起來極為流暢,但他們卻仍不可能完全沒遭遇那種苦難,或多或少都在台日不平等關係所形成的逆境中搏鬥。反之,迄今為止,有多少日人在台灣的語言平台上進行批判性言論活動呢?現在在日本,中文學習者數量增多,對台灣的關注度也大幅提高。在台灣發表中文文章、學術論文等的日籍作家、學者、記者隨之逐漸增加,在社群網站中已有不少日籍網友以中文與台方交換意見。但總體而言,與以日語進行言論活動的台灣人相比,其數量和比例仍明顯為少,此狀況反映出台日間仍保留的不平等關係。
我之所以在台灣用中文書寫的原因,是希望對抗此情形。我認為,身為一個屬於前殖民地宗主國出身的人士,既然提出對於前殖民地社會的批判意見,至少要把自身投入到與當地人平等的平台上,在從前那些台灣日語作家們同樣的條件下進行言論活動。或許,以中文發表文章的日人增加區區一個也不可能推翻大局,但就我而言,這至少是一種如江湖人般的倫理意識,也是不願認輸的固執。我不願意在被日語防護膜圍繞的安全地帶中單方面批判台方,也不想輸給以日語跟日本主流社會堂堂正正對峙的台灣人士之勇氣。
剛遷來台灣時,我完全不會台灣的語言,日常生活都不如意,有時陷入出乎意料的困境。後來我的中文能力稍微進步,但現在還無法說是完美,當因語言障礙而陷入困難時,周圍的台灣人士幫助我。事實上,就我而言,中文書寫是對於台方的日語之「報恩」,但此「報恩」不可能是全面稱讚台方,因為「批判」就是文學家的生命線。此外,所有的批判性言論活動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才能成立的。本書中不少內容涉及針對台灣社會的批判,這是因為我現在身在台灣。但若我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社會脈絡中向不同的讀者層發表文章,我說不定會寫下擁護台灣的論述,以對抗當地的主流思想。
就我而言,「台灣」、「日本」算什麼呢?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也許會說:「做為一個日本人,你怎麼那麼關心台灣。」不過,請不要誤會,「日本人」並非我的身分認同的一切。我在日本靜岡縣東部鄉下出生長大,在茨城縣筑波市度過青春時代,而後搬遷到花蓮、台中。在各地遇到的具體人們、社會、自然風景、都市環境等,確實是現在構成「我」的重要因素,但「日本」各地的許多土地我沒親自踏上過,也不可能認識所有的「日本人」,並且在我人生中給予「我」深刻影響的人們中,有許多是外籍人士。對我而言,「日本」畢竟是個由各種媒體所打造的「想像意象、形象」,這雖然也算是構成「我」的因素之一,卻絕非一切。說到底,我畢竟是個個人主義者,我所寫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而我根本沒資格擅自代表全日本發言。
雖然如此,與外籍人士討論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時,我還是有肩負著某些歷史社會脈絡發聲的「責任」。日本和台灣之間有曾殖民/被殖民的特殊歷史,因此即使我自以為是個「世界公民」,但在台灣發表自己的意見時,仍無法逃脫做為一個日籍人士的歷史、社會責任。這種「國家自我認同」和「歷史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難以解釋,目前我無法以更明確的理論來說明,但在此我將這兩者區別開來。在本書中我有時會寫下「做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但這種句子與其說代表著我的「國家、民族認同」,不如說是「歷史社會責任」。
再者,我不敢說出「我喜歡台灣」那類句子。因為對我而言,「台灣」並非單純的遊玩、觀賞場所,也不是觀察、分析對象,而是我自己所生活的場所,它已經變成了構成「我」存在本身的核心因素之一,因此我無法以「喜歡/不喜歡」那種將事情單一化的說法談論它。我在台灣與各種人們相逢,經歷各類的事情,對此複雜多元的情緒交錯,實在難以言喻。並且我不可能認識台灣所有的地方、民眾。事實上,在日本生活時也有一樣的情形,因此我對於「日本」的感受也無法以「喜歡/不喜歡」來形容。
另一方面,我確實希望台日民眾能打造更好的社會。其實不僅台日,全世界所有的民眾本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因為某種命運的捉弄使得我「偶然地」出生於日本,而後在台灣討生活,因此我接觸且思考台日相關議題的機會較多,並且做為一個旅台日籍人士,我確實有義務該承擔某些歷史社會責任。我較為頻繁探討台日的理由,並非認為只有台灣和日本有出眾的價值。儘管如此,既然在台灣生活十九年之久,在我自身的生命中台灣確實有特別的存在感。對我而言,台灣並非用來加強自己的既有認識、意識形態之場所,而是充滿未知的「他者」之空間,它給予我機會懷疑自己既有的自明性且不斷重新打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