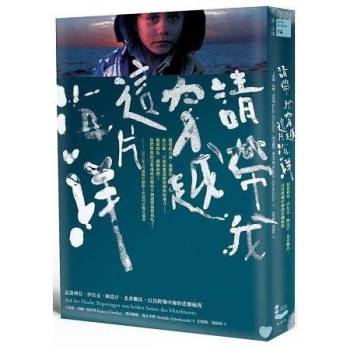完全沒有希望的一代
拜訪完貝卡谷地難民營的第二天,我坐在貝魯特聯合國難民署的一間遊戲等待間裡,觀察敘利亞難民兒童遊玩的情形。有一些兒童彼此談笑、尖叫著,合力將彩色的樂高積木套在一起;其他小朋友單獨坐在地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蓋房子。這群小孩一共有二十四個,全部都很起勁地蓋著一座慢慢變高變大的樂高城市。
難民兒童的父母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他們將過去的一切留在摧毀殆盡的敘利亞,然後跟其他幾百個人排隊站在這裡等待一個新生活。聯合國難民署職員坐在一個白色的貨櫃裡,透過辦公室的小窗口,難民可以正式登記成為敘利亞難民,同一時間,黎巴嫩已經有超過一百萬名難民。
當敘利亞戰爭結束,這群用樂高積木搭蓋夢幻房子的小孩,總有一天不是用塑膠積木,而是在現實中重建國家的人。「但是現在還沒人知道,從未受過教育的他們該如何達成這個使命?」民間救援組織「戰爭兒童」(War Child)的蜜努.黑克絲普兒(Minou Hexspoor)這麼跟我說,她是這間遊戲室的負責人,她說:「這是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一代。」並用兩個數字把眼前的災難計算出來:「在黎巴嫩有五十萬敘利亞籍的學齡難民兒童,其中三十二萬名兒童沒有學校可就讀。」現在黎巴嫩與敘利亞難民兒童的比例幾乎已高達三比一,完全超出黎巴嫩教育體系的負荷,學校無法提供足夠的位子。雖然許多公立學校也開始在下午上課,但是仍然不夠。那國際的救援組織呢?「他們的教育經費只足以支付必要款項的三分之一。」這位荷蘭籍女士很氣餒地表示。
加上很多小孩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他們有心理和社會問題,因為經歷過太多的激戰和死亡,並且失去了親友。他們行為失常,並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黑克絲普兒解釋,並把問題一一列出來。「有些十歲的小孩子又開始尿床,有些作惡夢,有許多小孩心中鬱積著暴力,經常跟人爭吵;其他的小孩完全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裡。」她娓娓地敘述著。
就算學校有足夠的位子給他們,對大部分年紀較大的孩子而言,生命對他們另有安排。「十二歲以後,許多小孩開始工作,以確保他們家庭在黎巴嫩的生活無虞。這些孩子在餐廳、工廠裡打工,去農場當助手,到街上賣東西,或是在工廠裡幫忙修車。」一位在「戰爭兒童」工作的小姐這樣描述著。
貝魯特到處可以遇到這些在工廠裡或是商店櫃台後度過童年的孩子,例如十三歲的阿馬德.哈瑪迪(Ahmad Hamadi)。當我二○一五年年初在貝魯特時,他整天在一間小麵包店裡做雜工,掃地、刷地板、清理櫃台、擦拭玻璃櫃。不過大部分的時間還是穿梭在小巷弄裡送貨給客人。「我來自阿勒坡附近的一個小村子。我們會來這裡是因為房子在戰爭中被摧毀了。」這個伶俐的小孩子這樣告訴我們。他很驕傲能找到一份工作幫助家計。「我每星期獲得的工資換算成歐元有十九塊錢,可以幫忙負擔家中的開銷。」在他父親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時,這份工資對他們來說更顯重要。「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再回到敘利亞,我的願望是能回學校上課,將來成為醫生。」小阿馬德加上這句話,可是也不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反正我把以前在敘利亞學校學到的東西通通都忘了。」他靦腆地笑了笑,接了下一位客人的訂單就上路了。他必須工作,沒有時間說話。
留在店裡的麵包師傅阿馬德.哈蘇恩(Ahmad Hassoun)是老闆,本身也是敘利亞難民,只不過比阿馬德大六歲。「這裡到處有敘利亞兒童在工作,他們比成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比較便宜。」他把黎巴嫩非正式就業市場上的經濟算盤做了一個總結,父母找不到工作並不是一個特例。「兩個童工可以抵一個成人的工資。」他計算著。
這家麵包店座落於巴勒斯坦人難民營夏提拉(Shatila),是貝魯特市內一個封閉的區域。以前的巴勒斯坦難民在這裡收留了新的流亡難民,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幾乎有三萬人湧進這塊只有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因為房租比較便宜的緣故,現在巴勒斯坦人難民營一半以上的人口來自敘利亞。
巴勒斯坦婦女后妲.阿爾—阿優茲(Hoda al-Ajouz)本身也是居留在黎巴嫩的難民,在當地領導一個小型地區性的救援組織,工作對象也有難民營中的敘利亞難童,她幾乎認識夏提拉的每個人。「還有比阿馬德年紀更小的兒童必須工作。」她在受訪時告訴我。因為父親找不到工作,所以一家人靠阿馬德的工資和他媽媽做清潔工賺來的錢維生,他媽媽還把阿馬德十四歲的姊姊帶去工作,充當清潔工助手。
后妲帶我們參觀難民營,路上經過無數的商店和工廠,后妲不斷強調,裡面的小售貨員和工人都是來自敘利亞。我們進入一條狹窄黑暗的巷子裡,唯一的光源來自一家網咖,一群男孩心無旁鶩地坐在電腦前玩著戰爭遊戲,他們跟虛擬戰士一起在準備槍擊敵人的巷子摸索前進,跟店門口前面的巷子相似得不得了。這裡也有一些來自敘利亞的孩子:從戰爭中逃出來,卻又被囚禁在戰爭遊戲裡。偏偏是這些過去飽經戰亂的孩子,逃避到現在虛擬的戰爭世界裡:他們長大後會是一個和平的世代嗎?
再過去幾公尺,我們來到一所小型非官方的學校。后妲領著我們走進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十二個小學生,坐在圍成U字形的課桌前,興味盎然地跟讀英文字母。「早上是我們巴勒斯坦的學生在這裡上課,下午則是敘利亞兒童。」后妲解釋。她說教導敘利亞的小孩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並把一些圖畫和素描從櫃子裡抽出來當作證據。那是一些讓人害怕的圖畫,上頭畫有被炸碎的人體、血和所有想得到的戰爭武器。其中一幅就是本書開頭所描述的八歲阿布達拉的畫。
「當他們剛來這裡的時候,最先畫的都是關於戰爭的圖畫,高空射下的導彈、一座座的大砲、血流成河的戰鬥。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做輔導工作,讓他們忘記過去。直到某個時間點,他們的畫又跟其他小朋友的畫一樣了。他們開始畫海洋或是山脈,有時候也畫他們未來想從事的職業。」后妲敘述著,並把小阿布達拉較新近的畫拿出來,這次他畫了一盤五顏六色水果,他還有兩三年的時間可以待在學校裡,之後,八歲的阿布達拉可能也要跟麵包店的跑腿阿馬德一樣開始工作。
人蛇集團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蛇集團涉入國家之間的內戰。然而義大利警方可以肯定,人蛇集團也具有「武裝組織」,因此二○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對義大利海岸警衛隊的攻擊可以算到他們頭上。他們趁著派遣部隊拯救上百名難民時開火,但是因為考量到難民的安全,軍官並沒有予以還擊,所以只好把用來渡海的船拱手讓給人蛇集團。
梅雷德.梅德哈內應該會喜歡這類事故,大家普遍認為他對本身的權力意識過剩、自戀,而且深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強的」。他被追隨者稱為將軍,而他的偶像就是前獨裁領袖穆安瑪爾.格達費。在電話中,他偶爾會用嘲弄的語氣抱怨「太多工作導致壓力」,難民被他當成「產品」或「數字」,而且有越來越大量的人口落入他的陷阱。他能在的黎波里過著美好的生活,這都要歸功於許多人的血淚錢。毫無疑問地:梅雷德.梅德哈內喜歡娛樂,而且愛好奢華。
身為最有影響力的主謀之一,梅雷德.梅德哈內顯然十分享受於從事此類國際「交易」。在某一次攔截到的電話中,他談到是否或是何時要在杜拜開立帳戶,但是美國和加拿大也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因為他說:「在那邊不會有人問你錢從哪裡來。」然而,西西里的調查人員在這段期間認為人蛇集團事業的「收銀台」就設置在杜拜,每月都有好幾千萬美元流入該處。
梅雷德.梅德哈內和埃爾米亞斯.戈赫瑪一同策畫跨越整個非洲的難民流亡路線,而根據拘捕令記載,「從未顧慮這將使移民暴露於風險與危險之中。」人命對人蛇集團頭目來講實在是一文不值,他們只需要盤算一件事:資金的流動絕對必要,而且最好是大量金錢,因此他們的至高目標是盡可能獲取更多難民,手段則不拘。調查人員得到結論,他們不斷從非洲其他同業手中大批購買難民,被綁架的難民之後再轉售給其他人蛇集團,以此獲得利益。流亡了好幾個月的人時常突然發現自己又返回牢籠中,他們被完全交付給人蛇集團,並隨著每次的交易而背負更多的債務。
義大利阿格里真托(Agrigento)法庭分別對一名突尼斯和一名索馬利亞人判處二十年及三十年徒刑。這些人隸屬於一個集團,他們在沙漠中竊聽難民的手機,藉此定位他們。然後人蛇集團突然憑空出現,並襲擊毫無防備的移民、洗劫難民,還要求額外的贖金來釋放他們。只要抵抗,就得面臨虐待和酷刑的威脅,無論女性或男性都經常被強暴,最後破碎的人還會再次被轉賣給其他人蛇集團以換取現金。
每當這兩名東非的頭目決定船如何、以及什麼時候要從利比亞海岸出港時,他們也總是追求利益。「大家都說我擠太多人了,」梅雷德.梅德哈內有一次在電話中輕蔑地大笑,「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要馬上出發,那我究竟又能怎樣。」而他的同伴埃爾米亞斯.戈赫瑪——義大利調查員把二○一三年十月發生在蘭佩杜薩外的難民悲劇歸咎到他身上——吹噓說他在利比亞發現了新大陸。「我們的活動是非法的,畢竟我們不是一個能幫助所有人的政府。」三十八歲的衣索比亞人現在正被國際通緝,造成三百六十六死的悲劇發生後不久,他在一段電話錄音中無動於衷地說:「依阿拉的旨意,他們現在到真主的身邊去了。」
在組織流亡路線時,人蛇集團試著盡可能不要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難民的旅程大多靠直接聯絡或藉助智慧型手機來規劃,蛇頭為了更容易躲避警方的監控,通常都交替使用WhatsApp、Skype、Volp和Viber等通訊軟體。
就連資金轉移,也是有各種不同系統供人蛇集團利用。他們最常運用的當屬中世紀在東方形成的「哈瓦拉系統」,金錢可以透過這個系統秘密轉移,能夠躲過金融及警察機構的監督,而且這種仰賴經紀人與代碼執行轉帳的方式,大部分也都比傳統銀行還迅速。不用委託人和收受人的書寫紀錄,也不需要可以辨識的文件,這種情形使警察根本無法歸納資金的流向。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義大利警方基於「格勞克二號」作戰計畫,同時於許多不同城市展開大搜捕。警察也闖進位於米內奧的收容中心,逮捕了許多來自厄利垂亞、衣索比亞、迦納和象牙海岸的人。但是他們當中最大條的魚在羅馬機場落網:阿斯格頓.戈赫瑪(Asghedom Ghermay),他是埃爾米亞斯.戈赫瑪在西西里的主事者。四十歲的阿斯格頓住在卡塔尼亞,被視為義大利區「細胞」的首領。他以「第三頭目」的身分負責接收新來的難民,並且幫助他們繼續前進歐洲中部和北部。
為了做到這一點,這名厄利垂亞公民抵達義大利後,馬上建立名為「野豬」的密集網絡,其成員於船隻靠港後在各個港口等候可能的客人,他們的任務是提供迷失方向的難民往北轉移的機會,連同所有想得到的保險。
與難民的第一次接觸多半是透過電話或當面進行。集團成員野豬們承諾會帶疲憊的難民到收容中心享用第一餐,同時建議不久之後立刻再帶他們出去,如此一來才能避免《都柏林第二公約》規定的查驗,這樣就可以前往歐洲其他國家,不會再被送回義大利。西西里的蛇頭不斷策畫讓難民逃離米內奧,顯然已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消失,彷彿被地表吞噬。事實上,他們已經踏上接下來的旅程:前往德國、瑞典、荷蘭、挪威,也有些人只是到義大利本土。多數人的目標都是在親戚或朋友那邊安頓下來。
對於人蛇集團而言,這又意味著許多財富。每階段都有它的價格,甚至義大利還產生一種價目表。在西西里一兩天的住宿和前往羅馬或米蘭的車票,集團收取高達四百歐元。而如果行程是要到另一個歐洲國家,每人還要額外負擔二千歐元的費用。許多時候,組織直接與難民家屬取得聯繫,勒索他們不等的金額作為「他們承擔高風險的補償金」,若是家人不給,就轉嫁給難民本身。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慣用的一般公車來當作運輸工具,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在購買車票時不需要出示護照或身分證,和飛機與火車不同,不用受到警察的監控;再來人蛇集團得到一個結論,公車比私人交通工具安全,因為私人交通工具在街道或公路上有被警察盤查的風險。無論如何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只有當難民支付完對方要求的金額,而且最好付現,他們的旅行才可以繼續下去。
蘭佩杜薩
出於深刻的信念,蘭佩杜薩人將他們的家鄉取名為「L’isola bella」(美麗島)。這裡只有二十平方公里的大小,彷彿一顆巨大岩石坐落於海中,被藍綠色、如玻璃般清澈的海浪從四面沖刷,是個由石灰石和白雲石構成的地塊,它險峻的一側(高岩壁)面向北方,但是朝南邊敞開它的海灣。從地質學來看,它屬於「義大利熱帶地區」,而擁有美麗海灘的部分已經算是非洲大陸板塊。
歷史演變中,它由腓尼基人、希臘人、羅馬人和阿拉伯人相繼接手,之後這個荒蕪的島嶼長期無人居住,不過由於它的戰略地位,法蘭西王國、沙皇時期的俄羅斯和馬爾他都同樣覬覦著這座小島。自一八六一年以來它歸義大利所有,凡是占有蘭佩杜薩的國家都知道:這座島是這座島是歐洲和非洲之間的橋梁。
救援者
當「安吉拉C」(Angela C)從蘭佩杜薩南部駛向外海時,天色已經昏暗。接近七點三十分,漁船又開回港口。這次夜間捕魚的成果相當令人滿意。多梅尼科.卡拉品托(Domenico Colapinto)和拉斐爾(Raffaele Colapinto)兩兄弟正準備卸載漁獲,一切都是每天例行公事,卻突然看到遠處有不尋常的騷動。他們察覺蘭佩杜薩島附近的一座小島周圍有船隻,船員正在把人拉出水面。「我們全力發動引擎。」五十八歲的多梅尼科後來向不同媒體的代表敘述。
兩名漁夫所看到的景象十分驚悚,男人、女人和小孩浮在水上喊叫,並且乞求救援。放眼望去就知道有好幾百人。「大海充滿人頭。」多梅尼科恍惚地作出反應,他丟繩子進入海中,開始把遇難者拉上船,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些人已經沒有力氣可以握住繩索。他只剩一個選擇:徒手把溺水的人抬到甲板上。兩名漁夫像著魔似地奮力搶救遇難者的生命,許多難民裸著身漂浮在海上,再加上外漏的柴油,使他們變得像肥皂一樣很難抓住。漁夫竭盡全力成功將二十個人從潮流中拉起,不過他們也馬上就確定當中有兩人打撈上來時已經死亡。
當兩兄弟先前正準備把漁獲運回港時,有另外兩個男人已經出海:柯斯坦提諾.巴拉塔(Costantino Baratta)和翁德.維奇(Onder Vecchi)。柯斯坦提諾六點剛過沒多久時起床,前一天晚上,這名受過訓練的水泥工和已經退休的朋友決定早上要去捕魚,漁獲不是用來販售,只是要自己享用而已。
翁德.維奇擁有一艘機動性強的小船,柯斯坦提諾剛好很喜歡這樣出遊,在特拉尼(Trani)長大的他最愛前往的地點就是蘭佩杜薩。一九七○年代中期,他當時的未婚妻在他阿普利亞(Apulien)的家鄉就讀師範學院,結婚後這對年輕夫婦特別常造訪這座小島,直到最後夫妻於一九八七年遷居。柯斯坦提諾十分了解蘭佩杜薩,所以知道如此多的難民悲劇對島上生活造成何等巨大的影響。但是,他也清楚小島上的居民向來有多麼樂善好施。
七點過後,當五十六歲的柯斯坦提諾和他朋友離開港口時,他們成為事件的第一發現者。和那兩名漁夫一樣,他們察覺到遠方的船。沒有再對事實多加揣測,就往那個位置靠近,接著突然明瞭自己面對的是什麼情形。「我們一下子就看到在水中呼救的人,毫無疑問:我們面臨事故現場,必須要去救援。我們的船雖然小,但是很快,這也是它的優點。」
具備外裝馬達的機動快艇試圖從危險區域的邊緣開始減少人數,但洋流在那裡增強,把溺水的人推向大海。
他們瞬間驚慌失措起來,究竟應該先救誰呢?而且如何分辨看似沒有生命跡象、浮在水面上的身體是否還活著?柯斯坦提諾知道一個不成文規定:「你必須拯救生命。這裡的漁民都說這是大海法則。」他強調道。「凡是遇到海難的人,我們都有必要搭救。我們有拯救生命的義務。」
柯斯坦提諾還清楚記得一名年輕女性,他本來已經打算放棄她。「太多人了,只要顧好活著的,死者就交給海岸警衛隊打撈。」有人從另一艘船對他喊。然後,張開手臂漂浮在海上的「小女孩」——據他表示——突然有了些微的生命跡象,她用最後的力氣舉起手,到柯斯坦提諾剛好可以發覺的程度,然後她的嘴唇微微顫抖。「救……救我,拜託。」她的呢喃小聲到幾乎聽不見。
柯斯坦提諾眼見他無法憑一己之力救援,因為女孩子實在太虛弱,抓不住他伸出的雙手,因此他呼叫他的朋友暫時關閉馬達過來幫忙,接著他們合力把年輕女性拉到船上。她全身發抖,而且吐出柴油,頭髮和眼睛完全被黏住。柯斯坦提諾唯一能給她幫助保暖的東西是一件T恤。
烏安是當天早上救起的最後一名生還者,繼她之後被撈上來的只剩屍體。受難者在水中已經浸泡好幾個小時。
拜訪完貝卡谷地難民營的第二天,我坐在貝魯特聯合國難民署的一間遊戲等待間裡,觀察敘利亞難民兒童遊玩的情形。有一些兒童彼此談笑、尖叫著,合力將彩色的樂高積木套在一起;其他小朋友單獨坐在地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蓋房子。這群小孩一共有二十四個,全部都很起勁地蓋著一座慢慢變高變大的樂高城市。
難民兒童的父母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他們將過去的一切留在摧毀殆盡的敘利亞,然後跟其他幾百個人排隊站在這裡等待一個新生活。聯合國難民署職員坐在一個白色的貨櫃裡,透過辦公室的小窗口,難民可以正式登記成為敘利亞難民,同一時間,黎巴嫩已經有超過一百萬名難民。
當敘利亞戰爭結束,這群用樂高積木搭蓋夢幻房子的小孩,總有一天不是用塑膠積木,而是在現實中重建國家的人。「但是現在還沒人知道,從未受過教育的他們該如何達成這個使命?」民間救援組織「戰爭兒童」(War Child)的蜜努.黑克絲普兒(Minou Hexspoor)這麼跟我說,她是這間遊戲室的負責人,她說:「這是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一代。」並用兩個數字把眼前的災難計算出來:「在黎巴嫩有五十萬敘利亞籍的學齡難民兒童,其中三十二萬名兒童沒有學校可就讀。」現在黎巴嫩與敘利亞難民兒童的比例幾乎已高達三比一,完全超出黎巴嫩教育體系的負荷,學校無法提供足夠的位子。雖然許多公立學校也開始在下午上課,但是仍然不夠。那國際的救援組織呢?「他們的教育經費只足以支付必要款項的三分之一。」這位荷蘭籍女士很氣餒地表示。
加上很多小孩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他們有心理和社會問題,因為經歷過太多的激戰和死亡,並且失去了親友。他們行為失常,並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黑克絲普兒解釋,並把問題一一列出來。「有些十歲的小孩子又開始尿床,有些作惡夢,有許多小孩心中鬱積著暴力,經常跟人爭吵;其他的小孩完全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裡。」她娓娓地敘述著。
就算學校有足夠的位子給他們,對大部分年紀較大的孩子而言,生命對他們另有安排。「十二歲以後,許多小孩開始工作,以確保他們家庭在黎巴嫩的生活無虞。這些孩子在餐廳、工廠裡打工,去農場當助手,到街上賣東西,或是在工廠裡幫忙修車。」一位在「戰爭兒童」工作的小姐這樣描述著。
貝魯特到處可以遇到這些在工廠裡或是商店櫃台後度過童年的孩子,例如十三歲的阿馬德.哈瑪迪(Ahmad Hamadi)。當我二○一五年年初在貝魯特時,他整天在一間小麵包店裡做雜工,掃地、刷地板、清理櫃台、擦拭玻璃櫃。不過大部分的時間還是穿梭在小巷弄裡送貨給客人。「我來自阿勒坡附近的一個小村子。我們會來這裡是因為房子在戰爭中被摧毀了。」這個伶俐的小孩子這樣告訴我們。他很驕傲能找到一份工作幫助家計。「我每星期獲得的工資換算成歐元有十九塊錢,可以幫忙負擔家中的開銷。」在他父親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時,這份工資對他們來說更顯重要。「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再回到敘利亞,我的願望是能回學校上課,將來成為醫生。」小阿馬德加上這句話,可是也不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反正我把以前在敘利亞學校學到的東西通通都忘了。」他靦腆地笑了笑,接了下一位客人的訂單就上路了。他必須工作,沒有時間說話。
留在店裡的麵包師傅阿馬德.哈蘇恩(Ahmad Hassoun)是老闆,本身也是敘利亞難民,只不過比阿馬德大六歲。「這裡到處有敘利亞兒童在工作,他們比成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比較便宜。」他把黎巴嫩非正式就業市場上的經濟算盤做了一個總結,父母找不到工作並不是一個特例。「兩個童工可以抵一個成人的工資。」他計算著。
這家麵包店座落於巴勒斯坦人難民營夏提拉(Shatila),是貝魯特市內一個封閉的區域。以前的巴勒斯坦難民在這裡收留了新的流亡難民,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幾乎有三萬人湧進這塊只有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因為房租比較便宜的緣故,現在巴勒斯坦人難民營一半以上的人口來自敘利亞。
巴勒斯坦婦女后妲.阿爾—阿優茲(Hoda al-Ajouz)本身也是居留在黎巴嫩的難民,在當地領導一個小型地區性的救援組織,工作對象也有難民營中的敘利亞難童,她幾乎認識夏提拉的每個人。「還有比阿馬德年紀更小的兒童必須工作。」她在受訪時告訴我。因為父親找不到工作,所以一家人靠阿馬德的工資和他媽媽做清潔工賺來的錢維生,他媽媽還把阿馬德十四歲的姊姊帶去工作,充當清潔工助手。
后妲帶我們參觀難民營,路上經過無數的商店和工廠,后妲不斷強調,裡面的小售貨員和工人都是來自敘利亞。我們進入一條狹窄黑暗的巷子裡,唯一的光源來自一家網咖,一群男孩心無旁鶩地坐在電腦前玩著戰爭遊戲,他們跟虛擬戰士一起在準備槍擊敵人的巷子摸索前進,跟店門口前面的巷子相似得不得了。這裡也有一些來自敘利亞的孩子:從戰爭中逃出來,卻又被囚禁在戰爭遊戲裡。偏偏是這些過去飽經戰亂的孩子,逃避到現在虛擬的戰爭世界裡:他們長大後會是一個和平的世代嗎?
再過去幾公尺,我們來到一所小型非官方的學校。后妲領著我們走進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十二個小學生,坐在圍成U字形的課桌前,興味盎然地跟讀英文字母。「早上是我們巴勒斯坦的學生在這裡上課,下午則是敘利亞兒童。」后妲解釋。她說教導敘利亞的小孩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並把一些圖畫和素描從櫃子裡抽出來當作證據。那是一些讓人害怕的圖畫,上頭畫有被炸碎的人體、血和所有想得到的戰爭武器。其中一幅就是本書開頭所描述的八歲阿布達拉的畫。
「當他們剛來這裡的時候,最先畫的都是關於戰爭的圖畫,高空射下的導彈、一座座的大砲、血流成河的戰鬥。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做輔導工作,讓他們忘記過去。直到某個時間點,他們的畫又跟其他小朋友的畫一樣了。他們開始畫海洋或是山脈,有時候也畫他們未來想從事的職業。」后妲敘述著,並把小阿布達拉較新近的畫拿出來,這次他畫了一盤五顏六色水果,他還有兩三年的時間可以待在學校裡,之後,八歲的阿布達拉可能也要跟麵包店的跑腿阿馬德一樣開始工作。
人蛇集團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蛇集團涉入國家之間的內戰。然而義大利警方可以肯定,人蛇集團也具有「武裝組織」,因此二○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對義大利海岸警衛隊的攻擊可以算到他們頭上。他們趁著派遣部隊拯救上百名難民時開火,但是因為考量到難民的安全,軍官並沒有予以還擊,所以只好把用來渡海的船拱手讓給人蛇集團。
梅雷德.梅德哈內應該會喜歡這類事故,大家普遍認為他對本身的權力意識過剩、自戀,而且深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強的」。他被追隨者稱為將軍,而他的偶像就是前獨裁領袖穆安瑪爾.格達費。在電話中,他偶爾會用嘲弄的語氣抱怨「太多工作導致壓力」,難民被他當成「產品」或「數字」,而且有越來越大量的人口落入他的陷阱。他能在的黎波里過著美好的生活,這都要歸功於許多人的血淚錢。毫無疑問地:梅雷德.梅德哈內喜歡娛樂,而且愛好奢華。
身為最有影響力的主謀之一,梅雷德.梅德哈內顯然十分享受於從事此類國際「交易」。在某一次攔截到的電話中,他談到是否或是何時要在杜拜開立帳戶,但是美國和加拿大也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因為他說:「在那邊不會有人問你錢從哪裡來。」然而,西西里的調查人員在這段期間認為人蛇集團事業的「收銀台」就設置在杜拜,每月都有好幾千萬美元流入該處。
梅雷德.梅德哈內和埃爾米亞斯.戈赫瑪一同策畫跨越整個非洲的難民流亡路線,而根據拘捕令記載,「從未顧慮這將使移民暴露於風險與危險之中。」人命對人蛇集團頭目來講實在是一文不值,他們只需要盤算一件事:資金的流動絕對必要,而且最好是大量金錢,因此他們的至高目標是盡可能獲取更多難民,手段則不拘。調查人員得到結論,他們不斷從非洲其他同業手中大批購買難民,被綁架的難民之後再轉售給其他人蛇集團,以此獲得利益。流亡了好幾個月的人時常突然發現自己又返回牢籠中,他們被完全交付給人蛇集團,並隨著每次的交易而背負更多的債務。
義大利阿格里真托(Agrigento)法庭分別對一名突尼斯和一名索馬利亞人判處二十年及三十年徒刑。這些人隸屬於一個集團,他們在沙漠中竊聽難民的手機,藉此定位他們。然後人蛇集團突然憑空出現,並襲擊毫無防備的移民、洗劫難民,還要求額外的贖金來釋放他們。只要抵抗,就得面臨虐待和酷刑的威脅,無論女性或男性都經常被強暴,最後破碎的人還會再次被轉賣給其他人蛇集團以換取現金。
每當這兩名東非的頭目決定船如何、以及什麼時候要從利比亞海岸出港時,他們也總是追求利益。「大家都說我擠太多人了,」梅雷德.梅德哈內有一次在電話中輕蔑地大笑,「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要馬上出發,那我究竟又能怎樣。」而他的同伴埃爾米亞斯.戈赫瑪——義大利調查員把二○一三年十月發生在蘭佩杜薩外的難民悲劇歸咎到他身上——吹噓說他在利比亞發現了新大陸。「我們的活動是非法的,畢竟我們不是一個能幫助所有人的政府。」三十八歲的衣索比亞人現在正被國際通緝,造成三百六十六死的悲劇發生後不久,他在一段電話錄音中無動於衷地說:「依阿拉的旨意,他們現在到真主的身邊去了。」
在組織流亡路線時,人蛇集團試著盡可能不要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難民的旅程大多靠直接聯絡或藉助智慧型手機來規劃,蛇頭為了更容易躲避警方的監控,通常都交替使用WhatsApp、Skype、Volp和Viber等通訊軟體。
就連資金轉移,也是有各種不同系統供人蛇集團利用。他們最常運用的當屬中世紀在東方形成的「哈瓦拉系統」,金錢可以透過這個系統秘密轉移,能夠躲過金融及警察機構的監督,而且這種仰賴經紀人與代碼執行轉帳的方式,大部分也都比傳統銀行還迅速。不用委託人和收受人的書寫紀錄,也不需要可以辨識的文件,這種情形使警察根本無法歸納資金的流向。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義大利警方基於「格勞克二號」作戰計畫,同時於許多不同城市展開大搜捕。警察也闖進位於米內奧的收容中心,逮捕了許多來自厄利垂亞、衣索比亞、迦納和象牙海岸的人。但是他們當中最大條的魚在羅馬機場落網:阿斯格頓.戈赫瑪(Asghedom Ghermay),他是埃爾米亞斯.戈赫瑪在西西里的主事者。四十歲的阿斯格頓住在卡塔尼亞,被視為義大利區「細胞」的首領。他以「第三頭目」的身分負責接收新來的難民,並且幫助他們繼續前進歐洲中部和北部。
為了做到這一點,這名厄利垂亞公民抵達義大利後,馬上建立名為「野豬」的密集網絡,其成員於船隻靠港後在各個港口等候可能的客人,他們的任務是提供迷失方向的難民往北轉移的機會,連同所有想得到的保險。
與難民的第一次接觸多半是透過電話或當面進行。集團成員野豬們承諾會帶疲憊的難民到收容中心享用第一餐,同時建議不久之後立刻再帶他們出去,如此一來才能避免《都柏林第二公約》規定的查驗,這樣就可以前往歐洲其他國家,不會再被送回義大利。西西里的蛇頭不斷策畫讓難民逃離米內奧,顯然已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消失,彷彿被地表吞噬。事實上,他們已經踏上接下來的旅程:前往德國、瑞典、荷蘭、挪威,也有些人只是到義大利本土。多數人的目標都是在親戚或朋友那邊安頓下來。
對於人蛇集團而言,這又意味著許多財富。每階段都有它的價格,甚至義大利還產生一種價目表。在西西里一兩天的住宿和前往羅馬或米蘭的車票,集團收取高達四百歐元。而如果行程是要到另一個歐洲國家,每人還要額外負擔二千歐元的費用。許多時候,組織直接與難民家屬取得聯繫,勒索他們不等的金額作為「他們承擔高風險的補償金」,若是家人不給,就轉嫁給難民本身。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慣用的一般公車來當作運輸工具,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在購買車票時不需要出示護照或身分證,和飛機與火車不同,不用受到警察的監控;再來人蛇集團得到一個結論,公車比私人交通工具安全,因為私人交通工具在街道或公路上有被警察盤查的風險。無論如何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只有當難民支付完對方要求的金額,而且最好付現,他們的旅行才可以繼續下去。
蘭佩杜薩
出於深刻的信念,蘭佩杜薩人將他們的家鄉取名為「L’isola bella」(美麗島)。這裡只有二十平方公里的大小,彷彿一顆巨大岩石坐落於海中,被藍綠色、如玻璃般清澈的海浪從四面沖刷,是個由石灰石和白雲石構成的地塊,它險峻的一側(高岩壁)面向北方,但是朝南邊敞開它的海灣。從地質學來看,它屬於「義大利熱帶地區」,而擁有美麗海灘的部分已經算是非洲大陸板塊。
歷史演變中,它由腓尼基人、希臘人、羅馬人和阿拉伯人相繼接手,之後這個荒蕪的島嶼長期無人居住,不過由於它的戰略地位,法蘭西王國、沙皇時期的俄羅斯和馬爾他都同樣覬覦著這座小島。自一八六一年以來它歸義大利所有,凡是占有蘭佩杜薩的國家都知道:這座島是這座島是歐洲和非洲之間的橋梁。
救援者
當「安吉拉C」(Angela C)從蘭佩杜薩南部駛向外海時,天色已經昏暗。接近七點三十分,漁船又開回港口。這次夜間捕魚的成果相當令人滿意。多梅尼科.卡拉品托(Domenico Colapinto)和拉斐爾(Raffaele Colapinto)兩兄弟正準備卸載漁獲,一切都是每天例行公事,卻突然看到遠處有不尋常的騷動。他們察覺蘭佩杜薩島附近的一座小島周圍有船隻,船員正在把人拉出水面。「我們全力發動引擎。」五十八歲的多梅尼科後來向不同媒體的代表敘述。
兩名漁夫所看到的景象十分驚悚,男人、女人和小孩浮在水上喊叫,並且乞求救援。放眼望去就知道有好幾百人。「大海充滿人頭。」多梅尼科恍惚地作出反應,他丟繩子進入海中,開始把遇難者拉上船,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些人已經沒有力氣可以握住繩索。他只剩一個選擇:徒手把溺水的人抬到甲板上。兩名漁夫像著魔似地奮力搶救遇難者的生命,許多難民裸著身漂浮在海上,再加上外漏的柴油,使他們變得像肥皂一樣很難抓住。漁夫竭盡全力成功將二十個人從潮流中拉起,不過他們也馬上就確定當中有兩人打撈上來時已經死亡。
當兩兄弟先前正準備把漁獲運回港時,有另外兩個男人已經出海:柯斯坦提諾.巴拉塔(Costantino Baratta)和翁德.維奇(Onder Vecchi)。柯斯坦提諾六點剛過沒多久時起床,前一天晚上,這名受過訓練的水泥工和已經退休的朋友決定早上要去捕魚,漁獲不是用來販售,只是要自己享用而已。
翁德.維奇擁有一艘機動性強的小船,柯斯坦提諾剛好很喜歡這樣出遊,在特拉尼(Trani)長大的他最愛前往的地點就是蘭佩杜薩。一九七○年代中期,他當時的未婚妻在他阿普利亞(Apulien)的家鄉就讀師範學院,結婚後這對年輕夫婦特別常造訪這座小島,直到最後夫妻於一九八七年遷居。柯斯坦提諾十分了解蘭佩杜薩,所以知道如此多的難民悲劇對島上生活造成何等巨大的影響。但是,他也清楚小島上的居民向來有多麼樂善好施。
七點過後,當五十六歲的柯斯坦提諾和他朋友離開港口時,他們成為事件的第一發現者。和那兩名漁夫一樣,他們察覺到遠方的船。沒有再對事實多加揣測,就往那個位置靠近,接著突然明瞭自己面對的是什麼情形。「我們一下子就看到在水中呼救的人,毫無疑問:我們面臨事故現場,必須要去救援。我們的船雖然小,但是很快,這也是它的優點。」
具備外裝馬達的機動快艇試圖從危險區域的邊緣開始減少人數,但洋流在那裡增強,把溺水的人推向大海。
他們瞬間驚慌失措起來,究竟應該先救誰呢?而且如何分辨看似沒有生命跡象、浮在水面上的身體是否還活著?柯斯坦提諾知道一個不成文規定:「你必須拯救生命。這裡的漁民都說這是大海法則。」他強調道。「凡是遇到海難的人,我們都有必要搭救。我們有拯救生命的義務。」
柯斯坦提諾還清楚記得一名年輕女性,他本來已經打算放棄她。「太多人了,只要顧好活著的,死者就交給海岸警衛隊打撈。」有人從另一艘船對他喊。然後,張開手臂漂浮在海上的「小女孩」——據他表示——突然有了些微的生命跡象,她用最後的力氣舉起手,到柯斯坦提諾剛好可以發覺的程度,然後她的嘴唇微微顫抖。「救……救我,拜託。」她的呢喃小聲到幾乎聽不見。
柯斯坦提諾眼見他無法憑一己之力救援,因為女孩子實在太虛弱,抓不住他伸出的雙手,因此他呼叫他的朋友暫時關閉馬達過來幫忙,接著他們合力把年輕女性拉到船上。她全身發抖,而且吐出柴油,頭髮和眼睛完全被黏住。柯斯坦提諾唯一能給她幫助保暖的東西是一件T恤。
烏安是當天早上救起的最後一名生還者,繼她之後被撈上來的只剩屍體。受難者在水中已經浸泡好幾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