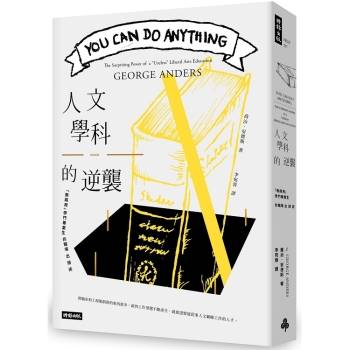第一章 探索者
二○○七年,喬書.朱赫(Josh Sucher)從紐約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畢業時,對怎樣才能找到工作毫無頭緒。他花了四年的時間(以及父母的一大筆錢)攻讀人類學專業,學會了如何以局內人或局外人的身分進行人類學研究;他能告訴你不同社會裡最叫人瞠目結舌的巫術故事。他的畢業論文主題,是分析一部價值一百美元的筆記型電腦的「建構主義基礎」,他形容這臺電腦是「一部內建政治意涵的機器」。朱赫浸淫在這所文理學院的校園中,各方面的表現都可圈可點。然而用美國一流雇主比較嚴苛的標準來看,朱赫就像暴風雪中的一株蘭花,一無是處。
朱赫的許多同學也遭遇類似的挫折。巴德學院的校園文化崇尚自由精神,學院畢業生理當找份待遇優渥的職業,但是這兩者似乎連繫不起來。朱赫的父親覺得這種情況悲慘到荒謬的地步,一度評論道:「你怎麼不去人類學工廠啊?我聽說他們在徵人。」連在畢業典禮上致詞的巴德學院畢業生,也沒辦法抹去那片陰霾,他們行禮如儀地讚頌精神生活――然後替每一位畢業生所面臨的危險前途捏一把冷汗。巴德學院的校長里昂.波茨坦(Leon Botstein)感嘆地說,美國全國的高等教育越來越不利於人文學門。受邀來演講的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則警告在座畢業生,找工作「可能會很可怕」,還說:「諸位當中有些人找工作的時間恐怕會拖得長一點。」
儘管如此,朱赫還是成功了――並且不需要為了謀職而扼殺自己的性格、興趣或獨特的人生觀點。
本書以朱赫的故事作為開頭,因為在舉國上下對大學教育的價值感到焦慮之際,這則故事充分顯示,我們在這片焦慮之中,恐怕失落了一項基本真理。好奇心、創造力、同理心並非狂放不羈、必須加以約束才能確保成功的特質。恰恰相反,如今在職場上,人性化比以往更不可或缺。你不需要為了讓雇主出錢買你的能力而掩飾自己真實的身分;你不需要因為自己在大學選修那些據說不切實際的課程或是學習所謂的軟性技能而說抱歉。就業市場目前每個星期都在默默創造成千上萬個職缺,目標就是那些能為迅速變遷的高科技未來帶來優美人文氣息的人才。
想像一張試算表,橫跨上方的所有欄位代表人類的各種力量,而側面的每一直行則代表支持該力量的技術學門。橫欄與直行每一次交會,就定義出一種新的工作型態。好奇心+數據科學=市場研究。同理心+基因定序=遺傳諮詢。創意+資訊網絡=社群媒體管理人。這是個豐富、奇妙的矩陣。我們將會在本書中探索人文教育與社會需求兩者合契的種種方式。
中心思想是這樣的:例行事務越自動化,就越會創造出水準低落的數位連結力,越容易陷在大數據纏夾不清的龐雜與盲點之中,因此,將人類判斷力帶進數位生活的連接點就越形重要。我們很容易被身邊的數位工具所迷惑:社交用的Snapchat與臉書;計畫旅行用的TripAdvisor和Airbnb;還有裝著攝影機的無人飛機,天曉得是做什麼用的。人們很自然就會對建造這些工具的軟體工程師奉若神明,可是如果沒有人進行勸誘、交心、說服、辯論、教導、反抗、互動,每一項科技突破都只是個空殼子。基本上,我們都是社會動物,與人競爭、結交,渴求別人的尊敬,懲罰自己的敵人。人們的行為方式令工程師感到挫敗,但是看在文科背景的人眼裡,卻顯得理所當然。打從兩萬年前某人在阿爾泰米拉山洞(Cave of Altamira)望著一幅野牛的原始素描,然後對著鄰居說:「真好看!你該多畫一些。」這個道理就沒有改變過。
實驗室和工程師創新的東西越多,就為能夠從事人文範疇工作的人才創造出更多職務。在倉庫或工廠裡,科技也許會消滅很多職位。毫無疑問,在有規則可循的瑣碎事務方面,機器確實表現卓越,比人做得更快、更便宜、更可靠。然而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機器(甚至是以軟體為基礎的人工智慧)只是笨拙的入侵者,他們不懂如何應付比較微妙的情況;在那些情況裡,情緒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也沒有明文規範可以參考。可是我們懂。
如果兒時習慣可以預示成年後的命運,那麼從一幅家庭照片中,就能看出朱赫的起點。當時還在蹣跚學步的朱赫站在一張椅子上,手裡拿著一支螺絲起子,正設法拆除牆壁上的插座。
小男孩一臉認真(和自信),讓人希望他能成功――哪怕謹慎的自我忍不住想尖叫:馬上給我從椅子上下來!照片上的影像讓人揮之不去,我花很多時間推想,為什麼像朱赫這類愛探險的人,會不斷巧遇事業機會,而其他人卻對同樣的機會視而不見?朱赫(還有你!)的一部分好運氣,可以追溯到一個好習慣:在生活中保留一絲初始的驚奇感。
隨著朱赫慢慢長大,好奇心繼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著他走,包括七年級時很不明智地嘗試騎腳踏車上學,結果闖進一條快速道路。到了該選擇上哪一所大學時,朱赫忽略班上謹慎的同學所偏愛的職業道路,反而選擇了巴德學院,該校位在紐約市北方一百一十英里外,以破除陳規陋習而聞名。這所學校的校友包括史提利丹(Steely Dan)搖滾樂團的幾名創辦人,還有數十個知名畫家、藝術家、演員、作曲家。多年來該校有多位赫赫有名的寫作老師,像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梭爾.貝羅(Saul Bellow)、齊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巴德學院沒有商學院。
對朱赫來說,巴德學院擁有源源不絕的魅惑來源。大一的第一個星期,他選修的文化人類學課堂上,老師拿出一把指甲刀,剪下幾片自己的指甲――然後在學生之間傳閱。她的論點是:本來在我們指尖上看起來乾淨整齊的指甲,一旦剪下來,就忽然變得很噁心。「泥巴」、「髒汙」這類字眼不是絕對的,必須取決於它們所處的場合與文化。對於課桌旁激動的新鮮人朱赫來說,這不啻是真理給他的一記當頭棒喝。後來朱赫告訴我,教授的訊息「澈底重塑我的世界觀」。
在巴德學院讀完四年,朱赫曉得如何在短短一週內創作一齣短劇,如何在最不可思議的地點安排戲劇演出,這些地點包括學校收發室和廢棄穀倉。他累積了大量不切實際的技能,但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辦法,能夠將這些技能轉變成體面的工作。朱赫閒散了一段時間後,決定改念法學院,結果這項嘗試走進了死胡同:法律是父親的志向,不是他的。
為了幫忙支付就讀法學院的費用,朱赫成立「區塊工廠(Block Factory)」這項副業,專為使用蘋果麥金塔電腦的小公司提供技術支援。朱赫成了提工具箱的人,他在「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分類廣告網站上打廣告,幫人安裝投影機、網路纜線和其他設備。他的「辦公室」靠近布魯克林區(Brooklyn)的格瓦納斯運河(Gowanus Canal),在一處共用工作站裡分租了一張辦公桌,每月租金四百五十美元。他的住家則是祖母家閣樓的一張床鋪,挺克難的。後來朱赫解釋:「我曉得自己嫻熟電腦,還喜歡拆東西。」
如果你見過那時候的朱赫,大概會以為他是遊手好閒的混混,可是實際上他正在鍛鍊巴德學院教他的一項關鍵技能:如何傾聽。朱赫的新客戶――特別是曼哈頓地區的一批藝廊――需要比AV端子更好的連接方法。他們想要一個友善的聽眾,不但能安撫他們的心靈,同時具有同理心,替他們解決技術問題。朱赫告訴我:「我大部分的客戶都感到焦慮,只要有東西壞了,就會開始責備自己。他們會說:『你一定覺得我是白痴吧。我覺得好失敗。』這種費盡脣舌安撫對方的場合非常多,我會說:『錯不在你;是技術的問題。這玩意兒設計得太爛了。』我先把情況搞定,接著再談公事。」
不過,兩年之後,朱赫渴望做不一樣的工作,想要利用更廣義的方式,解決科技挫敗的問題。朱赫說:「我開始心力交瘁,不再滿意於為了小小的資訊技術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設計巧妙的應急對策。」他的新目標是組織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團隊,創造對使用者友善的技術,從頭開始妥善顧及每一個層面。朱赫空閒的時候,開始和數位設計師、實用性(usability)專家往來,他從來沒有寄過任何履歷表,卻透過人際網絡,疏通自己前進下一份工作的道路。朱赫跑去參加曼哈頓的一場派對,慶祝一本關於市場研究和訪談使用者的書籍出版――卻發現他打交道的對象,是一群嗓門大、活力足、欣賞奇妙設計的人。朱赫受到這次因緣際會的鼓舞,報名參加坐落在曼哈頓的視覺藝術學校(School of Visual Arts)的一項互動設計課程,在那兒,除了早就擁有同理心與好奇心的優點,他又結合了與設計、市場研究和些許計算機編碼有關的新技能。
朱赫說:「對我來說,那是神奇的時刻。我找到了自己的群落,有那麼一刻,我的眼裡泛出淚來。」過不了多久,朱赫就明白科技最新的轉折,恰好使他在大學的訓練變得更具價值。迅速成長的新公司所需要的,是懂一點點科技、外加懂很多人類本質的通才。
三條不同的道路引導朱赫前往Etsy,這是一家位在布魯克林的公司,經營線上工藝品市集,產品從手工卡片到珠寶無所不包,市值約十億美元。朱赫在視覺藝術學校的幾個朋友和老師都在那裡工作,某一次會議中,他聆聽Etsy執行長查德.狄克森(Chad Dickerson)講述該公司的故事,喜歡上Etsy市集支持小企業銷售藝品的方式,因此一聽說這家公司有職缺,馬上就應徵了。
Etsy不只在徵人,而且特別喜歡擁有多元背景的人。狄克森本人曾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主修英文,Etsy有許多軟體工程師和數據分析師,大學時的主修領域是文學史、日本研究、哲學。這是文科背景的員工不必隱藏個人過往的一家公司,他們可以取笑珍妮.侯哲爾(Jenny Holzer)的觀念藝術作品,然後把理論轉化為實務應用。對朱赫來說,Etsy聽起來就像自己的家一樣親切。
如今朱赫在Etsy負責數位時代版本的人種史與田野研究,他利用GoToMeeting和Google Hangouts等軟體,連結全世界各地的藝術創作者和買家,弄清楚他們如何運用Etsy,以及如何改進,使對方更加滿意。朱赫是很有耐心的聽眾,抽絲剝繭弄明白藝術家建立工作室的細節,還有他們克制不住的創作動力從何而來。好奇心與溫暖人心的作風,幫助朱赫深入了解Etsy的顧客,這些是標準化問卷怎麼也得不到的答案。朱赫向我解釋:「每一個人是自身故事的體現,外面有一百萬個人,而且他們都不會變老。」
我們可以把朱赫想成執行任務的人類學家,關注買家的偏好,那些偏好就像我們對指甲的觀感一樣,既原始又難以解釋。同事們很珍惜他的發現,靠這些發現指引公司推出新服務與新功能。朱赫說:「我站在買家和賣家的立場,永遠敞開心房,關心他們體驗科技的方式。」我們可以日以繼夜地辯論朱赫未經規畫的旅程,為什麼發展得這麼順利。很明顯地,你在大學所發展的好奇心、創意、同理心,幫助你找到自己的運氣。快速、破壞力強的變遷並未摧毀你的前途,反而對你有利。
二○○六年,經濟學家大衛.奧圖(David Autor)、勞倫斯.凱茲(Laurence Katz)、梅莉莎.卡爾妮(Melissa Kearney)出版了一項劃時代的研究,檢視科技如何改變人們的收入、命運,以及如何保住人們工作的能力。這三位學者(分別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全國經濟研究所)爬梳美國人口普查局、勞工部與其他政府機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數據,解開一九八○年以來,美國每一份薪資所隱藏的祕祕密。從此之後,奧圖、凱茲和卡爾妮所發掘出來的資料,便影響了公眾對於科技的魅力與危險的討論。
儘管新科技目前幾乎沒有波及低薪的勞力工作,譬如在餐廳端盤子,但是卻打擊了數以百萬計有規則可循、任務導向的工作,這類工作傳統上是中產階級的入門磚。數十年來,工廠作業員早就嘗過這個滋味,因為機器不斷取代生產線上的焊工和組裝工。可是奧圖、凱茲、卡爾妮的研究所呈現的,卻是高科技死神針對商店、辦公室、銀行,以及其他白領工作堡壘的威脅程度。事務員的工作不斷被軟體取代,編輯、銀行櫃員、行政祕祕書、接線生也一一遭到淘汰。麥肯錫(McKinsey)顧問公司的研究人員估計,當代社會有高達百分之四十五的工作,面臨了自動化的危險。風險資本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觀察指出:「軟體正在吞食整個世界。」當美國經濟在二○○八到二○一○年間碰上麻煩時,有八百八十萬個美國人丟了工作。後來經濟終於轉好,但是很多工作並沒有恢復。奧圖、凱茲和卡爾妮指出原因:科技進步擠掉了處理例行公事的那些工作。即使是向來吹捧尖端工程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也在二○一三年推出一期封面故事:「科技正在如何摧毀工作」,隨即掀起一陣騷動。麻省理工學院的管理學教授安德魯.麥克菲(Andrew McAfee)在那篇文章中,對於一個充斥自動駕駛車輛和倉儲機器人的未來,表達緊張的思慮。他問:「當這些科幻小說中的技術都成為現實,我們還需要人力做什麼?」
隨著大眾的焦慮上升,有個念頭逐漸抬頭:科技部門本身也許能夠提供答案。這一派的論調是,如果我們訓練出足夠的軟體工程師,那麼新的世代就可以找到優渥的工作。於是從舊金山到底特律的眾多城市中,數以百計的電腦程式設計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任內頻頻呼籲,從事各行各業的青少年都應該充實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這些課程,這樣他們也能成為程式設計鬼才。《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之類的電影,美化了深夜鑽研程式設計的行為,連我們使用的語言也自我重塑,彷彿扭曲伸展迎向陽光的植物。有些與電腦相關的用語,也因此被納入字典,像是「開放來源」(open source)、「反向相容」(backward-compatible)、「駭客松」(hackathon)、「駭客空間」(hackerspace)等等。
可惜這裡有個令人痛苦的轉折:軟體部門並沒有打算保護自己的員工不受自動化所害;反之,軟體業不斷淘汰自己比較老的工作,速度幾乎和創造新工作一樣快。幾年前程式設計師以人力做的很多事情,現在都已經變成自動化的工具組、程式庫、副程式(subroutines)。從二○一二年五月到二○一六年五月,美國的一千零一十萬個淨新增工作機會當中,電腦部門只占百分之五,也就是五十四萬一千個工作機會。編寫商業軟體、管理電腦網路、創造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能力,在求才雇主的招攬名單中,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十的缺額,對於其他的求職人才來說,工作機會是在別的地方。
科技狂熱分子忽略了,數位進步的廣義後果,其實就像漣漪一般,不斷擴散到經濟的其餘部分。每一世紀總會有一、兩次出現科技改革的浪潮,不只影響單一產業,而是影響人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二十世紀前半葉汽車工業興起,不僅帶動亨利福特汽車廠大舉招募員工,從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全美各地出現了好幾百萬個新型態工作機會,汽車普及的美國社會如今所需要、渴望的東西,推動這些新工作應運而生。所有的城鎮自行重新建設,以容納汽車機械工人、道路營建工人、駕駛訓練學校、汽車買賣商家、洗車店、汽車保險代理、交通安全官員、停車場管理員、地圖繪製員、車禍傷患委託律師。
現在歷史正在重演。
仔細看看二○一二年五月以來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你會發現成長最快的領域往往是與科技革命非直接相關的行業。舉例來說,拜廉價網路民調和大數據分析之賜,美國現在有超過五十五萬個市場研究員和行銷專家,比二○一二年大幅增加百分之三十。像Qualtrics、Survey-Monkey、Clicktools、FluidSurveys這類民調服務,不但能立刻得到調查結果,而且成本低廉,根本不需要多少軟體工程師投入,就能做得到。巨大的衝擊在於這些無所不在的工具的利用方式,如今我們常常對自己做意見調查;過去一年中,不管願不願意,你很可能已經在網路上一路點選,填寫過至少十幾份這樣的民調。企業需要的數據無所不包,從航空公司的服務,到你家寵物上次看獸醫的經驗。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研究已經從不怎麼起眼的專業,脫胎換骨成為顯學,從業人數比克利夫蘭市(Cleveland)的人口還多。
二○○七年,喬書.朱赫(Josh Sucher)從紐約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畢業時,對怎樣才能找到工作毫無頭緒。他花了四年的時間(以及父母的一大筆錢)攻讀人類學專業,學會了如何以局內人或局外人的身分進行人類學研究;他能告訴你不同社會裡最叫人瞠目結舌的巫術故事。他的畢業論文主題,是分析一部價值一百美元的筆記型電腦的「建構主義基礎」,他形容這臺電腦是「一部內建政治意涵的機器」。朱赫浸淫在這所文理學院的校園中,各方面的表現都可圈可點。然而用美國一流雇主比較嚴苛的標準來看,朱赫就像暴風雪中的一株蘭花,一無是處。
朱赫的許多同學也遭遇類似的挫折。巴德學院的校園文化崇尚自由精神,學院畢業生理當找份待遇優渥的職業,但是這兩者似乎連繫不起來。朱赫的父親覺得這種情況悲慘到荒謬的地步,一度評論道:「你怎麼不去人類學工廠啊?我聽說他們在徵人。」連在畢業典禮上致詞的巴德學院畢業生,也沒辦法抹去那片陰霾,他們行禮如儀地讚頌精神生活――然後替每一位畢業生所面臨的危險前途捏一把冷汗。巴德學院的校長里昂.波茨坦(Leon Botstein)感嘆地說,美國全國的高等教育越來越不利於人文學門。受邀來演講的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則警告在座畢業生,找工作「可能會很可怕」,還說:「諸位當中有些人找工作的時間恐怕會拖得長一點。」
儘管如此,朱赫還是成功了――並且不需要為了謀職而扼殺自己的性格、興趣或獨特的人生觀點。
本書以朱赫的故事作為開頭,因為在舉國上下對大學教育的價值感到焦慮之際,這則故事充分顯示,我們在這片焦慮之中,恐怕失落了一項基本真理。好奇心、創造力、同理心並非狂放不羈、必須加以約束才能確保成功的特質。恰恰相反,如今在職場上,人性化比以往更不可或缺。你不需要為了讓雇主出錢買你的能力而掩飾自己真實的身分;你不需要因為自己在大學選修那些據說不切實際的課程或是學習所謂的軟性技能而說抱歉。就業市場目前每個星期都在默默創造成千上萬個職缺,目標就是那些能為迅速變遷的高科技未來帶來優美人文氣息的人才。
想像一張試算表,橫跨上方的所有欄位代表人類的各種力量,而側面的每一直行則代表支持該力量的技術學門。橫欄與直行每一次交會,就定義出一種新的工作型態。好奇心+數據科學=市場研究。同理心+基因定序=遺傳諮詢。創意+資訊網絡=社群媒體管理人。這是個豐富、奇妙的矩陣。我們將會在本書中探索人文教育與社會需求兩者合契的種種方式。
中心思想是這樣的:例行事務越自動化,就越會創造出水準低落的數位連結力,越容易陷在大數據纏夾不清的龐雜與盲點之中,因此,將人類判斷力帶進數位生活的連接點就越形重要。我們很容易被身邊的數位工具所迷惑:社交用的Snapchat與臉書;計畫旅行用的TripAdvisor和Airbnb;還有裝著攝影機的無人飛機,天曉得是做什麼用的。人們很自然就會對建造這些工具的軟體工程師奉若神明,可是如果沒有人進行勸誘、交心、說服、辯論、教導、反抗、互動,每一項科技突破都只是個空殼子。基本上,我們都是社會動物,與人競爭、結交,渴求別人的尊敬,懲罰自己的敵人。人們的行為方式令工程師感到挫敗,但是看在文科背景的人眼裡,卻顯得理所當然。打從兩萬年前某人在阿爾泰米拉山洞(Cave of Altamira)望著一幅野牛的原始素描,然後對著鄰居說:「真好看!你該多畫一些。」這個道理就沒有改變過。
實驗室和工程師創新的東西越多,就為能夠從事人文範疇工作的人才創造出更多職務。在倉庫或工廠裡,科技也許會消滅很多職位。毫無疑問,在有規則可循的瑣碎事務方面,機器確實表現卓越,比人做得更快、更便宜、更可靠。然而生活中有很多方面,機器(甚至是以軟體為基礎的人工智慧)只是笨拙的入侵者,他們不懂如何應付比較微妙的情況;在那些情況裡,情緒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也沒有明文規範可以參考。可是我們懂。
如果兒時習慣可以預示成年後的命運,那麼從一幅家庭照片中,就能看出朱赫的起點。當時還在蹣跚學步的朱赫站在一張椅子上,手裡拿著一支螺絲起子,正設法拆除牆壁上的插座。
小男孩一臉認真(和自信),讓人希望他能成功――哪怕謹慎的自我忍不住想尖叫:馬上給我從椅子上下來!照片上的影像讓人揮之不去,我花很多時間推想,為什麼像朱赫這類愛探險的人,會不斷巧遇事業機會,而其他人卻對同樣的機會視而不見?朱赫(還有你!)的一部分好運氣,可以追溯到一個好習慣:在生活中保留一絲初始的驚奇感。
隨著朱赫慢慢長大,好奇心繼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著他走,包括七年級時很不明智地嘗試騎腳踏車上學,結果闖進一條快速道路。到了該選擇上哪一所大學時,朱赫忽略班上謹慎的同學所偏愛的職業道路,反而選擇了巴德學院,該校位在紐約市北方一百一十英里外,以破除陳規陋習而聞名。這所學校的校友包括史提利丹(Steely Dan)搖滾樂團的幾名創辦人,還有數十個知名畫家、藝術家、演員、作曲家。多年來該校有多位赫赫有名的寫作老師,像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梭爾.貝羅(Saul Bellow)、齊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巴德學院沒有商學院。
對朱赫來說,巴德學院擁有源源不絕的魅惑來源。大一的第一個星期,他選修的文化人類學課堂上,老師拿出一把指甲刀,剪下幾片自己的指甲――然後在學生之間傳閱。她的論點是:本來在我們指尖上看起來乾淨整齊的指甲,一旦剪下來,就忽然變得很噁心。「泥巴」、「髒汙」這類字眼不是絕對的,必須取決於它們所處的場合與文化。對於課桌旁激動的新鮮人朱赫來說,這不啻是真理給他的一記當頭棒喝。後來朱赫告訴我,教授的訊息「澈底重塑我的世界觀」。
在巴德學院讀完四年,朱赫曉得如何在短短一週內創作一齣短劇,如何在最不可思議的地點安排戲劇演出,這些地點包括學校收發室和廢棄穀倉。他累積了大量不切實際的技能,但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辦法,能夠將這些技能轉變成體面的工作。朱赫閒散了一段時間後,決定改念法學院,結果這項嘗試走進了死胡同:法律是父親的志向,不是他的。
為了幫忙支付就讀法學院的費用,朱赫成立「區塊工廠(Block Factory)」這項副業,專為使用蘋果麥金塔電腦的小公司提供技術支援。朱赫成了提工具箱的人,他在「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分類廣告網站上打廣告,幫人安裝投影機、網路纜線和其他設備。他的「辦公室」靠近布魯克林區(Brooklyn)的格瓦納斯運河(Gowanus Canal),在一處共用工作站裡分租了一張辦公桌,每月租金四百五十美元。他的住家則是祖母家閣樓的一張床鋪,挺克難的。後來朱赫解釋:「我曉得自己嫻熟電腦,還喜歡拆東西。」
如果你見過那時候的朱赫,大概會以為他是遊手好閒的混混,可是實際上他正在鍛鍊巴德學院教他的一項關鍵技能:如何傾聽。朱赫的新客戶――特別是曼哈頓地區的一批藝廊――需要比AV端子更好的連接方法。他們想要一個友善的聽眾,不但能安撫他們的心靈,同時具有同理心,替他們解決技術問題。朱赫告訴我:「我大部分的客戶都感到焦慮,只要有東西壞了,就會開始責備自己。他們會說:『你一定覺得我是白痴吧。我覺得好失敗。』這種費盡脣舌安撫對方的場合非常多,我會說:『錯不在你;是技術的問題。這玩意兒設計得太爛了。』我先把情況搞定,接著再談公事。」
不過,兩年之後,朱赫渴望做不一樣的工作,想要利用更廣義的方式,解決科技挫敗的問題。朱赫說:「我開始心力交瘁,不再滿意於為了小小的資訊技術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設計巧妙的應急對策。」他的新目標是組織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團隊,創造對使用者友善的技術,從頭開始妥善顧及每一個層面。朱赫空閒的時候,開始和數位設計師、實用性(usability)專家往來,他從來沒有寄過任何履歷表,卻透過人際網絡,疏通自己前進下一份工作的道路。朱赫跑去參加曼哈頓的一場派對,慶祝一本關於市場研究和訪談使用者的書籍出版――卻發現他打交道的對象,是一群嗓門大、活力足、欣賞奇妙設計的人。朱赫受到這次因緣際會的鼓舞,報名參加坐落在曼哈頓的視覺藝術學校(School of Visual Arts)的一項互動設計課程,在那兒,除了早就擁有同理心與好奇心的優點,他又結合了與設計、市場研究和些許計算機編碼有關的新技能。
朱赫說:「對我來說,那是神奇的時刻。我找到了自己的群落,有那麼一刻,我的眼裡泛出淚來。」過不了多久,朱赫就明白科技最新的轉折,恰好使他在大學的訓練變得更具價值。迅速成長的新公司所需要的,是懂一點點科技、外加懂很多人類本質的通才。
三條不同的道路引導朱赫前往Etsy,這是一家位在布魯克林的公司,經營線上工藝品市集,產品從手工卡片到珠寶無所不包,市值約十億美元。朱赫在視覺藝術學校的幾個朋友和老師都在那裡工作,某一次會議中,他聆聽Etsy執行長查德.狄克森(Chad Dickerson)講述該公司的故事,喜歡上Etsy市集支持小企業銷售藝品的方式,因此一聽說這家公司有職缺,馬上就應徵了。
Etsy不只在徵人,而且特別喜歡擁有多元背景的人。狄克森本人曾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主修英文,Etsy有許多軟體工程師和數據分析師,大學時的主修領域是文學史、日本研究、哲學。這是文科背景的員工不必隱藏個人過往的一家公司,他們可以取笑珍妮.侯哲爾(Jenny Holzer)的觀念藝術作品,然後把理論轉化為實務應用。對朱赫來說,Etsy聽起來就像自己的家一樣親切。
如今朱赫在Etsy負責數位時代版本的人種史與田野研究,他利用GoToMeeting和Google Hangouts等軟體,連結全世界各地的藝術創作者和買家,弄清楚他們如何運用Etsy,以及如何改進,使對方更加滿意。朱赫是很有耐心的聽眾,抽絲剝繭弄明白藝術家建立工作室的細節,還有他們克制不住的創作動力從何而來。好奇心與溫暖人心的作風,幫助朱赫深入了解Etsy的顧客,這些是標準化問卷怎麼也得不到的答案。朱赫向我解釋:「每一個人是自身故事的體現,外面有一百萬個人,而且他們都不會變老。」
我們可以把朱赫想成執行任務的人類學家,關注買家的偏好,那些偏好就像我們對指甲的觀感一樣,既原始又難以解釋。同事們很珍惜他的發現,靠這些發現指引公司推出新服務與新功能。朱赫說:「我站在買家和賣家的立場,永遠敞開心房,關心他們體驗科技的方式。」我們可以日以繼夜地辯論朱赫未經規畫的旅程,為什麼發展得這麼順利。很明顯地,你在大學所發展的好奇心、創意、同理心,幫助你找到自己的運氣。快速、破壞力強的變遷並未摧毀你的前途,反而對你有利。
二○○六年,經濟學家大衛.奧圖(David Autor)、勞倫斯.凱茲(Laurence Katz)、梅莉莎.卡爾妮(Melissa Kearney)出版了一項劃時代的研究,檢視科技如何改變人們的收入、命運,以及如何保住人們工作的能力。這三位學者(分別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全國經濟研究所)爬梳美國人口普查局、勞工部與其他政府機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數據,解開一九八○年以來,美國每一份薪資所隱藏的祕祕密。從此之後,奧圖、凱茲和卡爾妮所發掘出來的資料,便影響了公眾對於科技的魅力與危險的討論。
儘管新科技目前幾乎沒有波及低薪的勞力工作,譬如在餐廳端盤子,但是卻打擊了數以百萬計有規則可循、任務導向的工作,這類工作傳統上是中產階級的入門磚。數十年來,工廠作業員早就嘗過這個滋味,因為機器不斷取代生產線上的焊工和組裝工。可是奧圖、凱茲、卡爾妮的研究所呈現的,卻是高科技死神針對商店、辦公室、銀行,以及其他白領工作堡壘的威脅程度。事務員的工作不斷被軟體取代,編輯、銀行櫃員、行政祕祕書、接線生也一一遭到淘汰。麥肯錫(McKinsey)顧問公司的研究人員估計,當代社會有高達百分之四十五的工作,面臨了自動化的危險。風險資本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觀察指出:「軟體正在吞食整個世界。」當美國經濟在二○○八到二○一○年間碰上麻煩時,有八百八十萬個美國人丟了工作。後來經濟終於轉好,但是很多工作並沒有恢復。奧圖、凱茲和卡爾妮指出原因:科技進步擠掉了處理例行公事的那些工作。即使是向來吹捧尖端工程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也在二○一三年推出一期封面故事:「科技正在如何摧毀工作」,隨即掀起一陣騷動。麻省理工學院的管理學教授安德魯.麥克菲(Andrew McAfee)在那篇文章中,對於一個充斥自動駕駛車輛和倉儲機器人的未來,表達緊張的思慮。他問:「當這些科幻小說中的技術都成為現實,我們還需要人力做什麼?」
隨著大眾的焦慮上升,有個念頭逐漸抬頭:科技部門本身也許能夠提供答案。這一派的論調是,如果我們訓練出足夠的軟體工程師,那麼新的世代就可以找到優渥的工作。於是從舊金山到底特律的眾多城市中,數以百計的電腦程式設計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任內頻頻呼籲,從事各行各業的青少年都應該充實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這些課程,這樣他們也能成為程式設計鬼才。《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之類的電影,美化了深夜鑽研程式設計的行為,連我們使用的語言也自我重塑,彷彿扭曲伸展迎向陽光的植物。有些與電腦相關的用語,也因此被納入字典,像是「開放來源」(open source)、「反向相容」(backward-compatible)、「駭客松」(hackathon)、「駭客空間」(hackerspace)等等。
可惜這裡有個令人痛苦的轉折:軟體部門並沒有打算保護自己的員工不受自動化所害;反之,軟體業不斷淘汰自己比較老的工作,速度幾乎和創造新工作一樣快。幾年前程式設計師以人力做的很多事情,現在都已經變成自動化的工具組、程式庫、副程式(subroutines)。從二○一二年五月到二○一六年五月,美國的一千零一十萬個淨新增工作機會當中,電腦部門只占百分之五,也就是五十四萬一千個工作機會。編寫商業軟體、管理電腦網路、創造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能力,在求才雇主的招攬名單中,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十的缺額,對於其他的求職人才來說,工作機會是在別的地方。
科技狂熱分子忽略了,數位進步的廣義後果,其實就像漣漪一般,不斷擴散到經濟的其餘部分。每一世紀總會有一、兩次出現科技改革的浪潮,不只影響單一產業,而是影響人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二十世紀前半葉汽車工業興起,不僅帶動亨利福特汽車廠大舉招募員工,從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全美各地出現了好幾百萬個新型態工作機會,汽車普及的美國社會如今所需要、渴望的東西,推動這些新工作應運而生。所有的城鎮自行重新建設,以容納汽車機械工人、道路營建工人、駕駛訓練學校、汽車買賣商家、洗車店、汽車保險代理、交通安全官員、停車場管理員、地圖繪製員、車禍傷患委託律師。
現在歷史正在重演。
仔細看看二○一二年五月以來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你會發現成長最快的領域往往是與科技革命非直接相關的行業。舉例來說,拜廉價網路民調和大數據分析之賜,美國現在有超過五十五萬個市場研究員和行銷專家,比二○一二年大幅增加百分之三十。像Qualtrics、Survey-Monkey、Clicktools、FluidSurveys這類民調服務,不但能立刻得到調查結果,而且成本低廉,根本不需要多少軟體工程師投入,就能做得到。巨大的衝擊在於這些無所不在的工具的利用方式,如今我們常常對自己做意見調查;過去一年中,不管願不願意,你很可能已經在網路上一路點選,填寫過至少十幾份這樣的民調。企業需要的數據無所不包,從航空公司的服務,到你家寵物上次看獸醫的經驗。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研究已經從不怎麼起眼的專業,脫胎換骨成為顯學,從業人數比克利夫蘭市(Cleveland)的人口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