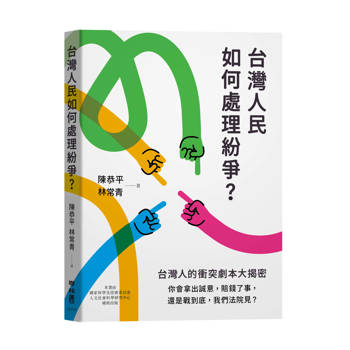第三章 紛爭類型及個人社經背景
第一節 社經背景的重要性
在研究民眾如何處理紛爭及其經驗之前,首先必須知道他們究竟遭遇了哪些問題、各類問題的發生頻率,以及發生的型態。這一章的目的,除了描繪受訪者遭遇各類問題的型態、次數及頻率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瞭解上述的形態及頻率與受訪者的個人特性及社經背景之間的關聯性。我們有能力做這樣探討的主要原因,是「2011 年面訪」在篩選部分的問卷裡,收集了相當詳細的個人社經背景資料。這有別於 Paths to Justice 這本書所使用的面訪設計,僅只收集了受訪者的性別、年齡等簡單資訊。
在討論各類問題及其頻率之前,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紛爭的產生並不是隨機的。換句話說,紛爭會在何時發生在誰身上,並非隨機抽樣,而是和個人背景息息相關的。圖 3.1 為所有受訪者所遭遇問題的次數的分布。如果每個人遭遇問題的可能性是隨機的,那麼它應該類似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事實卻是一個 U 型分配。顯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左右了個人遭遇問題的可能。van Velthoven and ter Voert (2005) 引用了參與理論(Participation Theory),來闡釋一個人遭遇到「有可能產生法律紛爭的問題」的風險,和與這個人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程度必然呈正相關。隨著個人背景的不同,社會和經濟活動程度較高的人,遭遇問題的可能較大,也從而產生圖 3.1 的結果。但社會參與及經濟活動,又與社經與人口特質有關。若某個社經族群較另一族群較易面臨某一類問題,極可能是因為這一族群較另一族群在這類的活動上有更多的參與。比如說,一位卡車司機遭遇事故意外問題的可能性,一定高於一位每天搭乘捷運上班的廚師,這是因為卡車司機產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遠高於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另外,除了問題類型之外,個人的其他特性,像工作、婚姻,乃至教育程度、年齡等等,都和紛爭的產生有關係。總之,個人背景不但影響到個人遭遇問題的次數,也影響到遭遇問題的類型。事實上,甚至連問題類型之間,彼此都有關聯性。例如,由於土地及房屋交易金額較大,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較容易有土地房屋問題的人,也較容易遭遇金錢借貸的問題。
第二節 問題的遭遇率(Incidence)、普遍率(Prevalence),及基本統計
在討論遭遇紛爭的頻率時,兩個常用的指標是,問題的「遭遇率」及「普遍率」。前者定義為曾經遭遇到某一類問題的受訪者,占所有受訪者的比例。這是以人為衡量單位的指標,它代表一個隨機抽樣的民眾,會遭遇到某一類問題的機率。但由於同一個人可能會重複遭遇同一類型的問題,因此如果以問題為單位,用來衡量某一類問題的發生有多普遍的指標,就是問題的普遍率。它的定義為,所有受訪者遭遇某特定類別問題的總次數,占所有類別的問題之總和次數的比例。其所代表的是在所有發生的問題裡,某一類型的問題發生的比例。
我們首先將臺灣面訪在各類問題的遭遇率整理於表 3.1。該表除了列出臺灣面訪的遭遇率外,在括號內的也分別列出日本 2005 年調查和英格蘭及威爾斯 1997 年調查的遭遇率。但要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日本面訪對問題的分類和臺灣面訪一致,英格蘭及威爾斯面訪則有相當的差異(請見該表的說明)。臺灣面訪的某些問題類型,並不能在英格蘭、威爾斯面訪找到相對的分類,反之亦然。其次,一個面訪的某個問題,在另一個面訪裡可能被歸類為好幾個分開的問題。
在「2011 年面訪」的 5,601 位受訪者中,有 3,169 人在最近五年內至少遭遇一個問題,約占整體樣本的 56.58%。如前一章所言,這個遭遇率不僅高過英格蘭與威爾斯面訪的 40%,也高過(除了荷蘭的網路訪查)其他地區的調查的發生率。相較於和台灣文化接近的日本,其 2005 年調查的 12,408 位受訪者(約為此次台灣調查樣本數的二倍)中,僅有 2,343 位(約 18.9%)受訪者在過去五年內曾遭遇過問題。當然這也許與民族特性、風俗民情,或社會結構有關,但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很多原因。第一,日本面訪詢問的是個人的問題,而臺灣面訪則為個人及子女,由於臺灣面訪涵蓋的當事人範圍較大,自然回答曾遭遇的受訪者會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面訪的詢問為「您是否曾和任何人經歷下列問題」(have you experienced any problem with another person ...),其對「問題」的界定,其實很寬鬆。因此在比例上這麼懸殊的差異,是否僅為「個人」與「個人和子女」之間的差別,我們不得而知。第二,臺灣面訪的回溯期為 5 年,這比其他大多數的調查長。第三,臺灣面訪的訪員在短卷及長卷的報酬不同(長卷每份 580 元,短卷 380 元)。因此,他們在面訪當下可能會過度提示問題的存在。
臺灣面訪所得到的遭遇率高於其他地區的現象,雖然有上述各種解釋,但我們覺得最可能的解釋,為臺灣面訪問卷的用詞為「可能會發生紛爭的問題」。由於對問題的描述,僅止於「可能」,並不表示已有紛爭。因此在心理上可能會讓受訪者將一些不太重要,也不太可能真正會做正式處理的問題都算進來。而英格蘭及威爾斯面訪的用語各為「您是否曾經歷任何難以解決的問題或紛爭」(have you had any problem or dispute that were difficult to solve ...)。這在語氣上較台灣的面訪嚴重得多。另外,Genn (1999) 以受訪者有沒有處理(Take Actions)來當作問題篩選的標準,如果受訪者對該問題沒有處理,就不進入主問卷。各問題的遭遇率,除了就醫問題外,其他各類問題於遭遇率在有無篩選之間的差異都沒有超過 1%。這似乎表示該面訪的受訪者對問題的界定答覆,已經相當程度過濾了較瑣碎而沒有去處理的問題。但在臺灣面訪裡,受訪者在回答有無親自與對方接觸時(題組 C10)只有 73.97% 回答是肯定的。這表示台灣的受訪者,對有否遭遇問題的界定,相對上較寬鬆,也因而使調查所得到的問題遭遇率較高。
在問題的遭遇率上,由圖 3.2 可知,臺灣面訪的受訪者最常遭遇的三個類型及其遭遇率依序為:事故意外 (25.92%)、購買商品服務 (24.68%),以及鄰居相關 (20.24%)。相似於日本最遭遇率最高的問題類型依序為事故意外(7.29%)、鄰居相關(5.29%),以及購買商品服務(4.81%)。購買商品服務紛爭為最常遭遇的問題之一,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事實上,不只台灣及日本如此,在美國、紐西蘭及三次英格蘭及威爾斯(1997,2001,2004)調查裡,購買商品服務紛爭的遭遇率都是最高的(表 2.2;Pleasence & Balmer, 2009)。現代社會日常各種商品及勞務交易的頻繁,早已讓它成為人民生活中最容易產生紛爭的問題之一。雖然台灣和日本在遭遇率最高的紛爭類型上很類似,但其他地區和台灣卻有相當的差異。例如英格蘭及威爾斯的調查,在 2001 年及 2004 年的第二及第三高的遭遇紛爭為鄰居相關及金錢借貸問題;加拿大及荷蘭的調查則是工作場所相關問題最高。由於加拿大的調查對象為低收入者,這似乎表示相較於一般民眾,低收入者較容易遭遇到和工作場所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及日本的調查裡,家庭問題的遭遇率在各類問題中都排在中段,但在英格蘭及威爾斯調查裡都極高。臺灣面訪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結果是,雖然上述三類問題的遭遇率都在 20%以上,但這三者之外的問題,遭遇率大幅降低。例如排名第四的工作場所相關問題也僅 13%。
遭遇率最低的三個問題類型,如果不計歸類為「其他」的問題,分別為保險相關(3.59%)、土地房屋買賣(4.61%)及土地房屋租賃(6.43%)。而日本面訪和台灣在這方面也很相似,其遭遇率最低的三個問題(同樣的,「其他」不計)分別為政府相關(0.99%)、保險相關(1.35%)及土地房屋租賃(1.41%)。日本的土地房屋買賣問題雖為第四最低,但和土地房屋租賃問題遭遇率幾乎無差異。在臺灣面訪中,工作與政府相關的問題都有相對較高的遭遇率 (分別是 13.17%與 11.19%)。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雇傭就業的問題在日本面訪中雖為第四常發生的問題種類(3.0%),但是在十個「可能會產生紛爭的問題」種類中,政府相關的問題幾乎是最低的(1.0%),只高過「其他」這個補充性質的問題種類。台灣受訪者和政府之間似遠較日本容易產生問題。
第一節 社經背景的重要性
在研究民眾如何處理紛爭及其經驗之前,首先必須知道他們究竟遭遇了哪些問題、各類問題的發生頻率,以及發生的型態。這一章的目的,除了描繪受訪者遭遇各類問題的型態、次數及頻率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瞭解上述的形態及頻率與受訪者的個人特性及社經背景之間的關聯性。我們有能力做這樣探討的主要原因,是「2011 年面訪」在篩選部分的問卷裡,收集了相當詳細的個人社經背景資料。這有別於 Paths to Justice 這本書所使用的面訪設計,僅只收集了受訪者的性別、年齡等簡單資訊。
在討論各類問題及其頻率之前,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紛爭的產生並不是隨機的。換句話說,紛爭會在何時發生在誰身上,並非隨機抽樣,而是和個人背景息息相關的。圖 3.1 為所有受訪者所遭遇問題的次數的分布。如果每個人遭遇問題的可能性是隨機的,那麼它應該類似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事實卻是一個 U 型分配。顯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左右了個人遭遇問題的可能。van Velthoven and ter Voert (2005) 引用了參與理論(Participation Theory),來闡釋一個人遭遇到「有可能產生法律紛爭的問題」的風險,和與這個人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程度必然呈正相關。隨著個人背景的不同,社會和經濟活動程度較高的人,遭遇問題的可能較大,也從而產生圖 3.1 的結果。但社會參與及經濟活動,又與社經與人口特質有關。若某個社經族群較另一族群較易面臨某一類問題,極可能是因為這一族群較另一族群在這類的活動上有更多的參與。比如說,一位卡車司機遭遇事故意外問題的可能性,一定高於一位每天搭乘捷運上班的廚師,這是因為卡車司機產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遠高於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另外,除了問題類型之外,個人的其他特性,像工作、婚姻,乃至教育程度、年齡等等,都和紛爭的產生有關係。總之,個人背景不但影響到個人遭遇問題的次數,也影響到遭遇問題的類型。事實上,甚至連問題類型之間,彼此都有關聯性。例如,由於土地及房屋交易金額較大,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較容易有土地房屋問題的人,也較容易遭遇金錢借貸的問題。
第二節 問題的遭遇率(Incidence)、普遍率(Prevalence),及基本統計
在討論遭遇紛爭的頻率時,兩個常用的指標是,問題的「遭遇率」及「普遍率」。前者定義為曾經遭遇到某一類問題的受訪者,占所有受訪者的比例。這是以人為衡量單位的指標,它代表一個隨機抽樣的民眾,會遭遇到某一類問題的機率。但由於同一個人可能會重複遭遇同一類型的問題,因此如果以問題為單位,用來衡量某一類問題的發生有多普遍的指標,就是問題的普遍率。它的定義為,所有受訪者遭遇某特定類別問題的總次數,占所有類別的問題之總和次數的比例。其所代表的是在所有發生的問題裡,某一類型的問題發生的比例。
我們首先將臺灣面訪在各類問題的遭遇率整理於表 3.1。該表除了列出臺灣面訪的遭遇率外,在括號內的也分別列出日本 2005 年調查和英格蘭及威爾斯 1997 年調查的遭遇率。但要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日本面訪對問題的分類和臺灣面訪一致,英格蘭及威爾斯面訪則有相當的差異(請見該表的說明)。臺灣面訪的某些問題類型,並不能在英格蘭、威爾斯面訪找到相對的分類,反之亦然。其次,一個面訪的某個問題,在另一個面訪裡可能被歸類為好幾個分開的問題。
在「2011 年面訪」的 5,601 位受訪者中,有 3,169 人在最近五年內至少遭遇一個問題,約占整體樣本的 56.58%。如前一章所言,這個遭遇率不僅高過英格蘭與威爾斯面訪的 40%,也高過(除了荷蘭的網路訪查)其他地區的調查的發生率。相較於和台灣文化接近的日本,其 2005 年調查的 12,408 位受訪者(約為此次台灣調查樣本數的二倍)中,僅有 2,343 位(約 18.9%)受訪者在過去五年內曾遭遇過問題。當然這也許與民族特性、風俗民情,或社會結構有關,但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很多原因。第一,日本面訪詢問的是個人的問題,而臺灣面訪則為個人及子女,由於臺灣面訪涵蓋的當事人範圍較大,自然回答曾遭遇的受訪者會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面訪的詢問為「您是否曾和任何人經歷下列問題」(have you experienced any problem with another person ...),其對「問題」的界定,其實很寬鬆。因此在比例上這麼懸殊的差異,是否僅為「個人」與「個人和子女」之間的差別,我們不得而知。第二,臺灣面訪的回溯期為 5 年,這比其他大多數的調查長。第三,臺灣面訪的訪員在短卷及長卷的報酬不同(長卷每份 580 元,短卷 380 元)。因此,他們在面訪當下可能會過度提示問題的存在。
臺灣面訪所得到的遭遇率高於其他地區的現象,雖然有上述各種解釋,但我們覺得最可能的解釋,為臺灣面訪問卷的用詞為「可能會發生紛爭的問題」。由於對問題的描述,僅止於「可能」,並不表示已有紛爭。因此在心理上可能會讓受訪者將一些不太重要,也不太可能真正會做正式處理的問題都算進來。而英格蘭及威爾斯面訪的用語各為「您是否曾經歷任何難以解決的問題或紛爭」(have you had any problem or dispute that were difficult to solve ...)。這在語氣上較台灣的面訪嚴重得多。另外,Genn (1999) 以受訪者有沒有處理(Take Actions)來當作問題篩選的標準,如果受訪者對該問題沒有處理,就不進入主問卷。各問題的遭遇率,除了就醫問題外,其他各類問題於遭遇率在有無篩選之間的差異都沒有超過 1%。這似乎表示該面訪的受訪者對問題的界定答覆,已經相當程度過濾了較瑣碎而沒有去處理的問題。但在臺灣面訪裡,受訪者在回答有無親自與對方接觸時(題組 C10)只有 73.97% 回答是肯定的。這表示台灣的受訪者,對有否遭遇問題的界定,相對上較寬鬆,也因而使調查所得到的問題遭遇率較高。
在問題的遭遇率上,由圖 3.2 可知,臺灣面訪的受訪者最常遭遇的三個類型及其遭遇率依序為:事故意外 (25.92%)、購買商品服務 (24.68%),以及鄰居相關 (20.24%)。相似於日本最遭遇率最高的問題類型依序為事故意外(7.29%)、鄰居相關(5.29%),以及購買商品服務(4.81%)。購買商品服務紛爭為最常遭遇的問題之一,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事實上,不只台灣及日本如此,在美國、紐西蘭及三次英格蘭及威爾斯(1997,2001,2004)調查裡,購買商品服務紛爭的遭遇率都是最高的(表 2.2;Pleasence & Balmer, 2009)。現代社會日常各種商品及勞務交易的頻繁,早已讓它成為人民生活中最容易產生紛爭的問題之一。雖然台灣和日本在遭遇率最高的紛爭類型上很類似,但其他地區和台灣卻有相當的差異。例如英格蘭及威爾斯的調查,在 2001 年及 2004 年的第二及第三高的遭遇紛爭為鄰居相關及金錢借貸問題;加拿大及荷蘭的調查則是工作場所相關問題最高。由於加拿大的調查對象為低收入者,這似乎表示相較於一般民眾,低收入者較容易遭遇到和工作場所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及日本的調查裡,家庭問題的遭遇率在各類問題中都排在中段,但在英格蘭及威爾斯調查裡都極高。臺灣面訪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結果是,雖然上述三類問題的遭遇率都在 20%以上,但這三者之外的問題,遭遇率大幅降低。例如排名第四的工作場所相關問題也僅 13%。
遭遇率最低的三個問題類型,如果不計歸類為「其他」的問題,分別為保險相關(3.59%)、土地房屋買賣(4.61%)及土地房屋租賃(6.43%)。而日本面訪和台灣在這方面也很相似,其遭遇率最低的三個問題(同樣的,「其他」不計)分別為政府相關(0.99%)、保險相關(1.35%)及土地房屋租賃(1.41%)。日本的土地房屋買賣問題雖為第四最低,但和土地房屋租賃問題遭遇率幾乎無差異。在臺灣面訪中,工作與政府相關的問題都有相對較高的遭遇率 (分別是 13.17%與 11.19%)。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雇傭就業的問題在日本面訪中雖為第四常發生的問題種類(3.0%),但是在十個「可能會產生紛爭的問題」種類中,政府相關的問題幾乎是最低的(1.0%),只高過「其他」這個補充性質的問題種類。台灣受訪者和政府之間似遠較日本容易產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