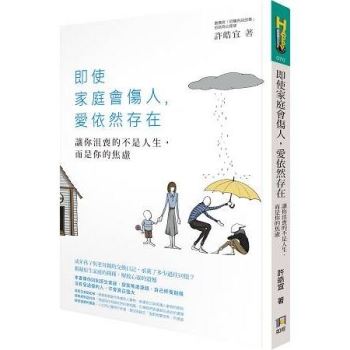能力有限的焦慮
—據說在父母使壞前,創傷就存在了
親愛的媽媽:
我常常在想,人出生以後如何感知這個世界?
有人說,新生兒之所以大哭,是因為知道自己要來世間還債;科學發現則不然:初啼是由於新生兒離開母體後,吸進了第一口空氣,緊接著的呼吸動作迫使空氣排出肺部,氣體通過聲帶發出的震動聲響,便形成初生時聽來強而有力的哭聲。
隨著肺呼吸完成,新生兒的血液循環開始運作,體內的臟器紛紛各司其職,原本仰賴臍帶與母體的連結宣告終止。一個新生命獨立了。
離開悠遊自得的水中世界,突然接觸到既明亮又冰冷、喧鬧又疏離的嶄新環境,更多刺激撫上口、鼻,竄入甫動工的胸腔、肺臟,促使聲帶發出更強烈的呱呱哭喊,引來周圍的大人照顧自己。新生命的獨立是如此微妙:有形的臍帶只是化成無形的羈絆,剪不斷。
小晴兒剛出生沒多久,護士將饑餓啼哭的她送來我身邊,解開產後汁液頻頻匯聚的乳房,來停止饞饞小嘴的渴望與不安。
嬰兒的口和母親的乳房—不該是天經地義的結合,是世上最初最美的接觸才對?
然而當她小嘴來到我胸前,這美好的片刻才不過數秒,她就吐出原本含住的柔軟,用力啼哭。
「哎呀,吸不到奶。加油啊小東西。」護士在旁為小晴兒和我打氣。
含,吐,哭。
咬,吐,吼。
她尋找乳房的力道和氣息逐漸加重,哭泣聲也從小溪流轉成急湍瀑布。
然後我們都累了。乳房的脹痛更劇,乳汁卻一丁點也不見排出。小東西的饑餓更深,珍貴初乳卻連一滴都吝於給予。
「算了,太難了。」我被小晴兒哭得心急,喚家人幫忙拿來事先準備好的電動吸乳器,咬著牙用熱燙的毛巾舒緩漲如巨石的乳房,在馬達的強力擠壓下,鵝黃色的乳汁終於通過管道進入透明的奶瓶。
為數不多的液體,放在手上還有方離開母體的溫度。
小嬰兒如獲至寶,嘴邊肉前後蠕動,短暫解去剛才的渴。但初乳稀有豈能滿足嬰兒的胃口?哭泣取代「不夠不夠」的抗議聲再次響起,也重新帶起為母如我心裡的無盡挫折。
隔壁產房的那位媽媽顯然比我爭氣。
哭哭停停的嬰兒啼聲後,一陣歡呼從隔壁房裡響起。「你看,他會了他會了。」
「他的小嘴好可愛。」
想必是那廂的新生兒在掙扎後,學會以自己的口去吸吮母親的乳房。
禁不住好奇,我拖著產後尚無力的腳步前去探望。隔壁媽媽顧不得袒露乳房的春光,大手招呼我進房。
我看見嬰兒皺巴巴的臉龐,穩穩貼合著母親胸前雪白的山峰。嬰兒微微拱起的身軀形成一種獨特的招式,就像某種高超的瑜伽技巧般,旁人學不來;搭配著母親呼吸氣息的起伏,產生一種規則的律動。
太美的畫面了,耀眼得令我幾乎睜不開眼。
好景不常,隔壁房的寧靜並沒有維持太久。明明已經學會吸吮乳房的新生兒,啼哭音量卻越來越大。
豐腴的母親日夜進補,食材中也加入各種傳說可以「通乳」的成分,但寶寶仍像個深不見底的大胃王,用強烈的哭聲來表達饑餓。
那母親臉上的慈愛光輝逐漸被憂愁取代。每每我和她並排站在育嬰室前探望寶寶,她總自責乳汁不足,我則感嘆錯過了親餵的時機。
幾天過去,加入我們「懺悔媽媽團」的人數日益龐大。我們才知道,原來那家的寶寶才剛因為黃疸指數過高而去接受光療,另一家的寶寶夜半總因胃脹氣大哭而無法入眠……
媽,到底是誰說「為母則強」這種鬼話?
當了母親以後,明明膽小得要命,孩子隨便一哭都讓我們心碎,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根本無法應付所有未知的威脅。
就像克萊茵女士所言:母親不可能完全滿足嬰兒,嬰兒亦缺乏理解世界的能力。兩者的有限性加在一起,必然經歷混亂與創傷。
我們總以為是父母做了什麼造成孩子的創傷,殊不知在生命最初,創傷可能早就被設定存在了。
恩恩親愛的恩恩:
妳生產當天的情景媽媽印象深刻,妳擠奶露出痛苦表情也讓我十分心急。恩恩,即便知道妳已經是個大人了,媽媽也無法將與妳有關的一切置身事外,妳的挫折仍引發我幫不上忙的焦慮。是的,媽媽必須承認自己能力有限,即便生養過兩個小孩,面對初為人母的妳依然使不上力。
然而人好像就是這樣,越焦慮於自己使不上力,就越想要給妳亂出主意。我永遠記得妳產後某天,突然像吃了炸藥一般對我說:「妳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落井下石,不要再一直碎碎唸:『妳看,我就跟妳說過……』我知道妳很厲害,我知道妳是我媽,可是妳能不能給我一點自己的空間,讓我依自己的方式來養小孩!」
媽媽一方面感到難過,一方面也自責—我知道對一個遭遇挫折的新手媽媽而言,這些話就像在責備她一般。
媽媽只想讓妳知道,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媽媽
◆
親愛的媽媽:
焦慮真的會讓人做出許多不見得貼近本意的行為。
就像您不斷地想要幫忙我,就像我忍不住大發脾氣。
我們都還無法承受自己能力有限、允許自己能力有限。我們太常用「全能」的自我期待來掌控自己的生活,折磨身邊的人。
然而,唯有面對天地萬物、大山大海時,我卻能看見自己的渺小,體會「能力有限」其實就是身為一個人最大的快樂。
親愛的媽媽,面對能力有限的焦慮,我們努力讓自己不再努力,直到真正願意放手的那一天。
恩恩
幻想世界的焦慮
—面對充滿焦慮的世界,人學會了「幻想」
親愛的媽媽: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趁酣睡時把您抓走。
迷迷糊糊地,您在搖晃的太空船中醒來,睜眼所見,是一大片您從未見過、有著奇異長相的外星物體。他們比手畫腳說著您聽不懂的外星語言,並且圍繞著您,用您未曾感知過的體溫在您身上磨蹭。
您不知道他們是表達親近還是敵意,也不知道在這奇特的環境裡會遭遇什麼事。
您心裡的感受會是什麼?
我想我會感到背脊發涼,心裡浮現焦慮恐慌。
人初誕生在世上的感覺,八成就是如此。一個新生命對世界的理解實在太少,任何周邊事物都可能引發焦慮。焦慮感於是用一種扭曲而背離現實的存在,與人連結。所以克萊茵說:我們最早經驗到的現實是幻想式的,並被不真實的現實給包圍。
此時,我們心智中大部分的能量,都被拿去對抗面對新環境刺激的焦慮;雖然具備人形,卻不過是一副器官能夠運作的軀體,而稱不上是兼備自我意識的個體。直到發展出足以解決焦慮的能力,新刺激才逐漸被我們給消化承擔,成為內在的一部分。
在克萊茵女士的臨床觀察中,「幻想」是孩童最常用來排除焦慮的方式。
小晴兒一歲之前,我是個超級忙碌的媽媽,心裡懷抱著沒辦法好好照顧她的歉疚感,又忍不住希望她能按表操課,以規律的作息運行她每天的生活日常。
我選擇四小時喝一次奶的餵養法,克制自己的不捨,避免在時間未到時讓小晴兒接觸到奶瓶。我時常得忍受小晴兒可憐的嗚咽聲,於是我送給她一只安撫奶嘴,來減輕自己無從消解的罪惡感。
一開始,她吸吮那根本不會有乳汁流出的奶嘴時,沒多久就會伸舌頭將它推出嘴外。毫無經驗的我,也只能再把奶嘴(假奶)塞回她嘴裡—有時搭配輕拍她胸口的節奏,有時來回撫摸她的額頭,或哼上幾首不成調的曲子。
我注意到,當她發現不管自己怎麼努力,都無法把惱人的奶嘴(假奶)丟棄、得到真正的乳汁後,她不但沒有抓狂,原本深鎖的眉頭反而逐漸舒緩,在一種仿若夢境的恍然中睡去。
接著,每當她等不到奶時,開始轉而主動吸吮自己的手指頭;只要仍聽見媽媽的聲音,感受到我的手停留在她的臉頰,即使沒有喝奶也能逐漸入眠。
我相信她在美妙的幻想中,將奶嘴與手指頭和著唾液的甘甜,想像成能夠帶給自己滿足的汁液。
這真是一件相當詭異的心理機制:在創傷中,我們似乎真學會了解決焦慮的方式。
孩子幻想著。母親也幻想孩子正在幻想著。
然而在人的幻想世界裡,仍是晴時多雲偶陣雨。
小晴兒並非無時無刻都像個甜美天使,更多時候她會哭鬧踢腿,不管你怎麼換尿布、送奶水,都不能令她滿意地停止那惱人的尖叫聲。
她會揮手拒絕你遞上的各種善意,朝你所在的方向發出怨恨般的嘶吼(喔,在母親的想像裡,這可一點都不誇張……)倘若你無法淡定地等著她情緒過去,那麼就有可能演變成一場讓雙方都筋疲力盡的戰役。我是直到小晴兒會說話後才能體會,原來小孩哭泣聲的含義,遠比語言所能表達的多。
那天,我和小晴兒陪她爸爸去買新衣服,她爸爸開個玩笑,惹怒了她。
她很快別過頭去,嘴裡唸唸有詞。我湊近她身邊偷聽,一連串「我討厭爸爸」「我最討厭爸爸」「我不要爸爸」……從她口中反覆播送出來。
我牽著她的手往前走,遇上一尊穿著展示服的假人模特兒。只見她瞬間撲上假人,在她(假人)身上左揮打、右拍擊,「我要把爸爸踢下來」「我要把爸爸打下來」……
當我提醒小晴兒,爸爸是男生,而她所攻擊的模特兒是個女生時,她又反應靈敏地撲上另一座男性身型的假人,重複剛剛的動作。
我猜,小晴兒正在幻想中給她爸爸一記左勾拳,右手扯著爸爸的頭髮不放,報復那可惡的臉孔直到她氣消為止。
所以我拉起小晴兒的手說:「走,媽媽帶妳去打爸爸。」
她頓時停下原本的舉動,退縮地搖搖頭。
「沒關係,媽媽幫妳。」
我帶著小晴兒往她爸爸的方向走去,對著她幻想中的可惡男人說:「你剛剛說錯話了,現在我們要來打你屁屁。」我向老公使了個眼色,用誇張的動作,抓起小晴兒的手往她爸爸的屁屁揮去。
一下、兩下……
她笑聲咯咯,逐漸掃去臉上的陰霾。過一會兒,她蹦蹦跳跳地重新玩耍起來,彷彿剛才的不愉快從未發生。
我好像看見她內心的焦慮感從幻想躍進現實世界,得到釋放。
我心裡不免埋怨自己,過去總愛阻撓她幻想,老覺得那些配不上孩童純真的「邪惡」念頭,她最好連想都別想。遇見心理學和克萊茵女士之前,我實在很少想過要為她搭建一個基地,讓她焦慮時的幻想,能在安全狀態中發生。
媽,其實「幻想」,不就是人性中最偉大的自由嗎?
唯有壓抑,才為幻想世界裡的恨意帶來真實的危險。
恩恩
◆
親愛的恩恩:
我想,不只小孩會幻想,媽媽我都已經是個老人家了,還是時常在幻想。
比方說我看見妳提到「壓抑」兩個字,心裡不免幻想:妳是不是在指責我小時候也壓抑妳的幻想?
不管我怎麼揮揮手想要趕走這樣的念頭,或告訴自己妳可能沒這樣的意思,覺得自己被責怪的感受還是揮之不去。
妳說的沒錯,母親的心就是這麼脆弱:我們幻想自己要當個好媽媽,又忍不住幻想自己在兒女心裡可能不是個好媽媽。頁數 6/13
很多成年的子女可能不知道,父母並不見得心智就比較成熟,我們也時常幻想自己還能像過去一般被孩子需要,彷彿還能當個被孩子依賴的好父母,就有繼續生存下去的價值。
這種感覺還真難說出口:看著各方面好像都強過自己的孩子,心裡一方面為你們感到驕傲,一方面又幻想自己肯定還有什麼能夠教導你們。所以忍不住要嘮叨碎唸,忍不住要告訴你們什麼事情該怎麼做,忍不住要把「我是為你好」掛在嘴邊……
因為怕有天不再被你們需要了,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怎麼辦才好?恩恩。我真高興妳能這麼分析事理,開始當個不同於我的媽媽;但我也更感受到,原來子女越是青出於藍,也就越有離開父母的本事和能力了……
唉,幻想世界真是讓人焦慮。
我只能幻想,長大後的你還是會記得回來。
媽媽
◆
親愛的媽媽:
孩子總有玩心。但只要您開口,我都會記得回來。
恩恩
「這世界上沒有人真的愛我」
—幻想未能和現實做檢核,就形成心魔
親愛的恩恩:
妳說這世界上有很多種愛,媽媽和爸爸吵了一輩子是一種愛,妳聽我們吵了一輩子也是一種愛,我們母女倆現在還能在這裡交換日記更是一種愛。但是恩恩,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人,怎麼努力也沒辦法擁有愛。
前陣子,退休同事來找我吃飯,拉我一起幫一位正在適婚年齡的女同事做媒人。女同事長得清清秀秀,碩士畢業的學歷,說話也輕聲細語,為人又乖巧,卻快四十歲了還沒有適合的對象。退休同事有個遠房姪子,恰好也是單身,我們想把他倆湊成對,那天就去吃了頓相親飯,並且在氣氛正好的時候退場,識相地留給他們獨處空間。
果然,兩個熟齡的單身男女,馬上就走在一塊了。說起來,男方也算一表人才,站在一起很是登對,我們都希望可以趕快吃到他們的喜酒,也算是成全了美事一樁。沒想到,前兩天女同事來找我們,一開口就拚命對我們說「阿姨對不起」「阿姨我該怎麼辦?」原來,他們倆才交往沒多久,甜蜜時光還沒過夠,女同事就發現男方有非常強烈的控制欲。比方說,女同事對男方說她會加班到八點,然後她可能很快就投入自己的工作,忙得沒有注意時間,等她想到的時候,手機裡已經有超過一百封男方傳來的訊息,以及無數個未接來電。
「還沒好嗎?」
「妳還沒好嗎?」
「妳真的還沒好嗎?」
「要到什麼時候?」「妳怎麼這麼慢?」
「妳現在在做什麼?」
「回家了嗎?」
「我怎麼找不到妳?」
「結束打給我?」
「還沒結束嗎?」……
恩恩,女同事拿這些訊息給我看時,我還真嚇了一跳。明明是一個看起來很有禮貌的男孩,相處起來卻給人這麼大的壓力,無時無刻緊迫盯人。我那退休同事聽到這個狀況,臉色也沉了下來,她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姪子在愛情中原來是這樣的。哎,這就是做媒人的風險啊,以為是自己親戚就不會出問題,現在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阿姨對不起,我不應該跟你們說這些的,可是我真的好害怕……」女同事都快急哭了,才告訴我們,她之前在愛情裡常常遇到這樣的人,所以交往過程中總被折磨,然後在巨大的衝突下分手,以致她戀情始終夭折,常常單身一人。女同事說,她真的很努力了,可是最終都對抗不了老天爺安排的命運。
「阿姨,老天爺是不是覺得,我不配擁有愛啊?」
恩恩,聽她這麼說,媽真的心疼啊。
媽媽
◆
親愛的媽媽:
交換日記了大半年,我想您一定理解我心裡的那個公式:當一個成年人發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時,我們便試著用對待小孩的立場來感受他,想像一下這些行為背後的焦慮是什麼—也就是他內在小孩的模樣。
我們先來想像一下這位男士的心情:女朋友不在身邊時會不斷追蹤,訊息像機關槍一樣連續發出,彷彿內心的焦慮完全停不下來。媽,您們稱這舉動為「控制」,然而「控制狂」的真相,其實是「害怕無法控制」,對「脫序」有強烈幻想式的焦慮,腦袋中裝了許多事情脫序後可能會出現的可怕後果,只是他們幾乎不去檢視這些可怕後果的真實性,便任憑那些幻想無限擴大,變成掌控內心的魔鬼。換句話說,這該是位極無安全感的男士吧?而且我想,焦慮感一定不是只在這段關係裡頭發生而已,或許他已經歷過多次相仿的愛情。
當然,我們也會好奇,這些強烈的、令人恐懼的幻想到底是怎麼來的,如果可以,我們真想這些焦慮永遠都不要找上我。精神分析稱這為「超我」,您可以將它理解成一種「良心」的發展—一開始是害怕做錯事情被責備,但良心發展太過,就變成一種「控制」了。媽,所以說「道德」和「瘋狂」永遠是一線之隔啊。克萊茵女士曾說,她在接近三歲與四歲的幼兒身上,就已經觀察到完整的超我運作,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因為小小孩將父母的形象給攝入到自己心裡了。簡而言之,父母就像一種背後靈,當面對外界事物時,我們幻想著他們的形象在身後指手畫腳,批評我們為人處世的態度。克萊茵女士還發現,小小孩對背後靈的感受,遠比兒童和成人恐怖得多,於是脆弱的心靈就這樣被幻想中的惡魔給深深蹂躪著,偏偏你又不敢將惡魔一腳踹開(開玩笑,那背後靈可是我爸我媽呀,踹開他們的話,我不就無父無母了?)。當背後靈跟著我們久了,和自我形象之間的界線便模糊了—我們開始不太清楚自己真實的想法、真實的感受,只好用那背後靈的形象,也開始點評我們所遇到的人。因此我聽過很多成年人痛恨地說:「可惡,我真的跟我爸(或我媽)好像啊。」
是的,如果我們有天感覺自己像個控制狂,八成和父母脫離不了關係,但這不代表現實中的父母,真的這麼嚴厲控制我們,導致我們內心衰弱,成為控制狂;而是我「想像」他們一直控制著我,然後因這份「想像」,進而逐漸變成一個控制狂。好吧,即便現實中我們真遇上控制型的父母,內心幻想的本能也會把這些控制放大了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這就是心魔啊,媽。心魔其實是藏在我們心頭的幻想。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要擺脫心魔很難。我想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們很難發現它的存在,其二是我們往往缺乏擺脫心魔的信心。
媽,這點是我閱讀克萊茵女士後的啟發,當然,也是我在臨床工作中多次嘗試的結論:擺脫心魔其實不難,只要勇敢地將內心世界的恐怖幻想,提取出來與現實生活作檢核,就會明白內心的幻想往往不會成真(是的,人本來就容易往最糟的地方想去)。
有人可能會對這個結論嗤之以鼻:哼哼,控制狂哪有可能這麼理智,還檢核現實哩?如果他們有這麼冷靜,哪來被控制的人的痛苦?但我所見到的現實卻是:常常,被控制的人也不太冷靜,所以在控制的循環中,跟著一起墜入痛苦。媽,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要指責被控制的人做錯了什麼。而是依照「A等同B」的焦慮法則,有時我們會無意識地過度類化自己所面臨的情境—比方說:認識一個控制狂的男人,便無意識連結到原生家庭中充滿控制欲的父親,所以怎麼都無法放下這個男人不管,卻又在被控制的感受中深深焦慮。您還記得嗎?這就是我們先前提過的,「A等同B」的焦慮。
這種焦慮的運作,就像一條詭異的月老紅線,將心裡有相似問題的世間男男女女牽引在一起;因為敏感於同樣的困擾,便形成一種「臭味相投」的吸引力。相投的「臭味」是彼此都無法遠離痛苦的原因,也讓我們無法冷靜下來,去檢核幻想其實不等同於現實。
媽,既然我們倆是局外人,就試著以旁觀者的立場來翻譯一下男人的控制語言好了:
「還沒好嗎?」「妳還沒好嗎?」「妳真的還沒好嗎?」(這是在表達一種等待的焦慮)
「要到什麼時候?」「妳怎麼那麼慢?」「妳現在在做什麼?」(這是在表達伴侶沒有依約在八點回家—事情脫序—的生氣)
「回家了嗎?」「我怎麼找不到妳?」(這表達了對伴侶的擔憂,可能內心已經開始對脫序的事情產生某些幻想)
「結束打給我?」「還沒結束嗎?」(這些表達中參雜了焦慮和擔憂的不一致感,既擔心又生氣的矛盾,令人心裡發毛……)
媽,一個人如果能用一致的態度表達生氣,相處久了我們比較容易明白,怎麼單純應付對方可能生氣的點;同樣的,一個人如果能一致表達脆弱,我們也容易明白怎麼安撫他的脆弱。然而,有些伴侶之所以會被形容成「恐怖情人」,往往在於他們的表達裡頭,參雜了生氣和脆弱等不一致的訊息,讓人錯亂地不知如何回應才好。媽,或許女同事需要的是將對方的表達邏輯澄清清楚,才能決定:我究竟還要不要繼續陪伴這個人的生氣、脆弱,甚至是把我搞瘋了的矛盾?
當然,我的確認識一些「愛到卡慘死」的當事人,他們雖然在被控制的痛苦中,卻深知自己愛著對方,因此努力覺察對方控制行為背後的邏輯,以致能用「維持界限」的回應來面對控制型的伴侶:「對不起,我錯過和你相約的時間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擔心我,但是我需要你給我一些時間來完成自己的事情。」有些人在與伴侶不斷相互協調中,可能發展出一種相處模式:「因為我理解你的焦慮,所以我願意在忙碌的時候,以一種不會過於勉強的姿態,提醒自己在約定的時間打給你。」媽,有很多當是人會這麼問我:幹嘛要愛得這麼累?幹嘛要這樣妥協?
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常常用一個過高的標準來看待「愛」,誤以為「愛」就一定是自由自在地「接受」與「被接受」。然而,從克萊茵女士身上,我學習到:「愛」其實是一種能夠「付出」與「能夠被付出」的能力—前者,是一種「心甘情願」,後者,則是「感恩」。
「心甘情願」和「感恩」的主控權都在自己手上—它不是等來的,是一點一滴學習來的。所以說,人人都可以擁有愛,也都配擁有愛。
恩恩
通往心靈穩定的「哀悼」之路,
需要預備三種勇氣
親愛的媽媽:
如果是開始交換日記前,我大概免不了用埋怨來回應您的疑問:是啊!您身為我媽,怎麼說不出一句同理我的話?
又是克萊茵女士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和您提過的「論孤獨」,真是克萊茵女士的作品中,最能表達人生淒涼美感的一篇文章,裡頭這麼描述母嬰之間的關係:和母親(她指的是「乳房」,或具有象徵「乳房」意義的「奶瓶」)之間的早期關係,意味著嬰兒與母親潛意識上的親密接觸,也奠定了被了解的經驗。一個享受吸吮且心滿意足的嬰兒,會緩和母親的焦慮,而母親正向的哺乳經驗,也將呈現在她餵食嬰兒的方式當中。換句話說,嬰兒開心喝奶,母親就能開心餵奶;開心餵奶的母親,也能讓嬰兒開心喝奶。這是一種母嬰循環,彼此之間都需要負起相當的責任。
當然,叫一個還在吃奶的小嬰兒懂得「責任」這件事,對嬰兒來講未免也太沉重了。所以,許多心理學家的表達,總是認為母親要多擔待一點,要扛起更大部分的責任。然而,我真覺得克萊茵女士是一位相當堅強的女性,即便她本人與母親的關係並不如意,我幾乎沒見她在論述中講過母親壞話,她總是堅強又努力地,從孩子的立場去找出一條不用倚賴母親的路。
閱讀至今日,我實在是同意克萊茵女士這點的。如果生命註定是一場克服磨難的過程,那麼不管我們遇上什麼樣的父母,都只是為了造就出我們這樣的性格。可能有好的、有壞的,但都是獨特的、值得我們珍惜的。性格是一份禮物,重點是我們怎麼用這份禮物,去走向未來;哀悼那些渴求而不可得的失落,我們才能真心憐憫自己,真正邁向內在的穩定與成熟。
—據說在父母使壞前,創傷就存在了
親愛的媽媽:
我常常在想,人出生以後如何感知這個世界?
有人說,新生兒之所以大哭,是因為知道自己要來世間還債;科學發現則不然:初啼是由於新生兒離開母體後,吸進了第一口空氣,緊接著的呼吸動作迫使空氣排出肺部,氣體通過聲帶發出的震動聲響,便形成初生時聽來強而有力的哭聲。
隨著肺呼吸完成,新生兒的血液循環開始運作,體內的臟器紛紛各司其職,原本仰賴臍帶與母體的連結宣告終止。一個新生命獨立了。
離開悠遊自得的水中世界,突然接觸到既明亮又冰冷、喧鬧又疏離的嶄新環境,更多刺激撫上口、鼻,竄入甫動工的胸腔、肺臟,促使聲帶發出更強烈的呱呱哭喊,引來周圍的大人照顧自己。新生命的獨立是如此微妙:有形的臍帶只是化成無形的羈絆,剪不斷。
小晴兒剛出生沒多久,護士將饑餓啼哭的她送來我身邊,解開產後汁液頻頻匯聚的乳房,來停止饞饞小嘴的渴望與不安。
嬰兒的口和母親的乳房—不該是天經地義的結合,是世上最初最美的接觸才對?
然而當她小嘴來到我胸前,這美好的片刻才不過數秒,她就吐出原本含住的柔軟,用力啼哭。
「哎呀,吸不到奶。加油啊小東西。」護士在旁為小晴兒和我打氣。
含,吐,哭。
咬,吐,吼。
她尋找乳房的力道和氣息逐漸加重,哭泣聲也從小溪流轉成急湍瀑布。
然後我們都累了。乳房的脹痛更劇,乳汁卻一丁點也不見排出。小東西的饑餓更深,珍貴初乳卻連一滴都吝於給予。
「算了,太難了。」我被小晴兒哭得心急,喚家人幫忙拿來事先準備好的電動吸乳器,咬著牙用熱燙的毛巾舒緩漲如巨石的乳房,在馬達的強力擠壓下,鵝黃色的乳汁終於通過管道進入透明的奶瓶。
為數不多的液體,放在手上還有方離開母體的溫度。
小嬰兒如獲至寶,嘴邊肉前後蠕動,短暫解去剛才的渴。但初乳稀有豈能滿足嬰兒的胃口?哭泣取代「不夠不夠」的抗議聲再次響起,也重新帶起為母如我心裡的無盡挫折。
隔壁產房的那位媽媽顯然比我爭氣。
哭哭停停的嬰兒啼聲後,一陣歡呼從隔壁房裡響起。「你看,他會了他會了。」
「他的小嘴好可愛。」
想必是那廂的新生兒在掙扎後,學會以自己的口去吸吮母親的乳房。
禁不住好奇,我拖著產後尚無力的腳步前去探望。隔壁媽媽顧不得袒露乳房的春光,大手招呼我進房。
我看見嬰兒皺巴巴的臉龐,穩穩貼合著母親胸前雪白的山峰。嬰兒微微拱起的身軀形成一種獨特的招式,就像某種高超的瑜伽技巧般,旁人學不來;搭配著母親呼吸氣息的起伏,產生一種規則的律動。
太美的畫面了,耀眼得令我幾乎睜不開眼。
好景不常,隔壁房的寧靜並沒有維持太久。明明已經學會吸吮乳房的新生兒,啼哭音量卻越來越大。
豐腴的母親日夜進補,食材中也加入各種傳說可以「通乳」的成分,但寶寶仍像個深不見底的大胃王,用強烈的哭聲來表達饑餓。
那母親臉上的慈愛光輝逐漸被憂愁取代。每每我和她並排站在育嬰室前探望寶寶,她總自責乳汁不足,我則感嘆錯過了親餵的時機。
幾天過去,加入我們「懺悔媽媽團」的人數日益龐大。我們才知道,原來那家的寶寶才剛因為黃疸指數過高而去接受光療,另一家的寶寶夜半總因胃脹氣大哭而無法入眠……
媽,到底是誰說「為母則強」這種鬼話?
當了母親以後,明明膽小得要命,孩子隨便一哭都讓我們心碎,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根本無法應付所有未知的威脅。
就像克萊茵女士所言:母親不可能完全滿足嬰兒,嬰兒亦缺乏理解世界的能力。兩者的有限性加在一起,必然經歷混亂與創傷。
我們總以為是父母做了什麼造成孩子的創傷,殊不知在生命最初,創傷可能早就被設定存在了。
恩恩親愛的恩恩:
妳生產當天的情景媽媽印象深刻,妳擠奶露出痛苦表情也讓我十分心急。恩恩,即便知道妳已經是個大人了,媽媽也無法將與妳有關的一切置身事外,妳的挫折仍引發我幫不上忙的焦慮。是的,媽媽必須承認自己能力有限,即便生養過兩個小孩,面對初為人母的妳依然使不上力。
然而人好像就是這樣,越焦慮於自己使不上力,就越想要給妳亂出主意。我永遠記得妳產後某天,突然像吃了炸藥一般對我說:「妳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落井下石,不要再一直碎碎唸:『妳看,我就跟妳說過……』我知道妳很厲害,我知道妳是我媽,可是妳能不能給我一點自己的空間,讓我依自己的方式來養小孩!」
媽媽一方面感到難過,一方面也自責—我知道對一個遭遇挫折的新手媽媽而言,這些話就像在責備她一般。
媽媽只想讓妳知道,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媽媽
◆
親愛的媽媽:
焦慮真的會讓人做出許多不見得貼近本意的行為。
就像您不斷地想要幫忙我,就像我忍不住大發脾氣。
我們都還無法承受自己能力有限、允許自己能力有限。我們太常用「全能」的自我期待來掌控自己的生活,折磨身邊的人。
然而,唯有面對天地萬物、大山大海時,我卻能看見自己的渺小,體會「能力有限」其實就是身為一個人最大的快樂。
親愛的媽媽,面對能力有限的焦慮,我們努力讓自己不再努力,直到真正願意放手的那一天。
恩恩
幻想世界的焦慮
—面對充滿焦慮的世界,人學會了「幻想」
親愛的媽媽: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趁酣睡時把您抓走。
迷迷糊糊地,您在搖晃的太空船中醒來,睜眼所見,是一大片您從未見過、有著奇異長相的外星物體。他們比手畫腳說著您聽不懂的外星語言,並且圍繞著您,用您未曾感知過的體溫在您身上磨蹭。
您不知道他們是表達親近還是敵意,也不知道在這奇特的環境裡會遭遇什麼事。
您心裡的感受會是什麼?
我想我會感到背脊發涼,心裡浮現焦慮恐慌。
人初誕生在世上的感覺,八成就是如此。一個新生命對世界的理解實在太少,任何周邊事物都可能引發焦慮。焦慮感於是用一種扭曲而背離現實的存在,與人連結。所以克萊茵說:我們最早經驗到的現實是幻想式的,並被不真實的現實給包圍。
此時,我們心智中大部分的能量,都被拿去對抗面對新環境刺激的焦慮;雖然具備人形,卻不過是一副器官能夠運作的軀體,而稱不上是兼備自我意識的個體。直到發展出足以解決焦慮的能力,新刺激才逐漸被我們給消化承擔,成為內在的一部分。
在克萊茵女士的臨床觀察中,「幻想」是孩童最常用來排除焦慮的方式。
小晴兒一歲之前,我是個超級忙碌的媽媽,心裡懷抱著沒辦法好好照顧她的歉疚感,又忍不住希望她能按表操課,以規律的作息運行她每天的生活日常。
我選擇四小時喝一次奶的餵養法,克制自己的不捨,避免在時間未到時讓小晴兒接觸到奶瓶。我時常得忍受小晴兒可憐的嗚咽聲,於是我送給她一只安撫奶嘴,來減輕自己無從消解的罪惡感。
一開始,她吸吮那根本不會有乳汁流出的奶嘴時,沒多久就會伸舌頭將它推出嘴外。毫無經驗的我,也只能再把奶嘴(假奶)塞回她嘴裡—有時搭配輕拍她胸口的節奏,有時來回撫摸她的額頭,或哼上幾首不成調的曲子。
我注意到,當她發現不管自己怎麼努力,都無法把惱人的奶嘴(假奶)丟棄、得到真正的乳汁後,她不但沒有抓狂,原本深鎖的眉頭反而逐漸舒緩,在一種仿若夢境的恍然中睡去。
接著,每當她等不到奶時,開始轉而主動吸吮自己的手指頭;只要仍聽見媽媽的聲音,感受到我的手停留在她的臉頰,即使沒有喝奶也能逐漸入眠。
我相信她在美妙的幻想中,將奶嘴與手指頭和著唾液的甘甜,想像成能夠帶給自己滿足的汁液。
這真是一件相當詭異的心理機制:在創傷中,我們似乎真學會了解決焦慮的方式。
孩子幻想著。母親也幻想孩子正在幻想著。
然而在人的幻想世界裡,仍是晴時多雲偶陣雨。
小晴兒並非無時無刻都像個甜美天使,更多時候她會哭鬧踢腿,不管你怎麼換尿布、送奶水,都不能令她滿意地停止那惱人的尖叫聲。
她會揮手拒絕你遞上的各種善意,朝你所在的方向發出怨恨般的嘶吼(喔,在母親的想像裡,這可一點都不誇張……)倘若你無法淡定地等著她情緒過去,那麼就有可能演變成一場讓雙方都筋疲力盡的戰役。我是直到小晴兒會說話後才能體會,原來小孩哭泣聲的含義,遠比語言所能表達的多。
那天,我和小晴兒陪她爸爸去買新衣服,她爸爸開個玩笑,惹怒了她。
她很快別過頭去,嘴裡唸唸有詞。我湊近她身邊偷聽,一連串「我討厭爸爸」「我最討厭爸爸」「我不要爸爸」……從她口中反覆播送出來。
我牽著她的手往前走,遇上一尊穿著展示服的假人模特兒。只見她瞬間撲上假人,在她(假人)身上左揮打、右拍擊,「我要把爸爸踢下來」「我要把爸爸打下來」……
當我提醒小晴兒,爸爸是男生,而她所攻擊的模特兒是個女生時,她又反應靈敏地撲上另一座男性身型的假人,重複剛剛的動作。
我猜,小晴兒正在幻想中給她爸爸一記左勾拳,右手扯著爸爸的頭髮不放,報復那可惡的臉孔直到她氣消為止。
所以我拉起小晴兒的手說:「走,媽媽帶妳去打爸爸。」
她頓時停下原本的舉動,退縮地搖搖頭。
「沒關係,媽媽幫妳。」
我帶著小晴兒往她爸爸的方向走去,對著她幻想中的可惡男人說:「你剛剛說錯話了,現在我們要來打你屁屁。」我向老公使了個眼色,用誇張的動作,抓起小晴兒的手往她爸爸的屁屁揮去。
一下、兩下……
她笑聲咯咯,逐漸掃去臉上的陰霾。過一會兒,她蹦蹦跳跳地重新玩耍起來,彷彿剛才的不愉快從未發生。
我好像看見她內心的焦慮感從幻想躍進現實世界,得到釋放。
我心裡不免埋怨自己,過去總愛阻撓她幻想,老覺得那些配不上孩童純真的「邪惡」念頭,她最好連想都別想。遇見心理學和克萊茵女士之前,我實在很少想過要為她搭建一個基地,讓她焦慮時的幻想,能在安全狀態中發生。
媽,其實「幻想」,不就是人性中最偉大的自由嗎?
唯有壓抑,才為幻想世界裡的恨意帶來真實的危險。
恩恩
◆
親愛的恩恩:
我想,不只小孩會幻想,媽媽我都已經是個老人家了,還是時常在幻想。
比方說我看見妳提到「壓抑」兩個字,心裡不免幻想:妳是不是在指責我小時候也壓抑妳的幻想?
不管我怎麼揮揮手想要趕走這樣的念頭,或告訴自己妳可能沒這樣的意思,覺得自己被責怪的感受還是揮之不去。
妳說的沒錯,母親的心就是這麼脆弱:我們幻想自己要當個好媽媽,又忍不住幻想自己在兒女心裡可能不是個好媽媽。頁數 6/13
很多成年的子女可能不知道,父母並不見得心智就比較成熟,我們也時常幻想自己還能像過去一般被孩子需要,彷彿還能當個被孩子依賴的好父母,就有繼續生存下去的價值。
這種感覺還真難說出口:看著各方面好像都強過自己的孩子,心裡一方面為你們感到驕傲,一方面又幻想自己肯定還有什麼能夠教導你們。所以忍不住要嘮叨碎唸,忍不住要告訴你們什麼事情該怎麼做,忍不住要把「我是為你好」掛在嘴邊……
因為怕有天不再被你們需要了,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怎麼辦才好?恩恩。我真高興妳能這麼分析事理,開始當個不同於我的媽媽;但我也更感受到,原來子女越是青出於藍,也就越有離開父母的本事和能力了……
唉,幻想世界真是讓人焦慮。
我只能幻想,長大後的你還是會記得回來。
媽媽
◆
親愛的媽媽:
孩子總有玩心。但只要您開口,我都會記得回來。
恩恩
「這世界上沒有人真的愛我」
—幻想未能和現實做檢核,就形成心魔
親愛的恩恩:
妳說這世界上有很多種愛,媽媽和爸爸吵了一輩子是一種愛,妳聽我們吵了一輩子也是一種愛,我們母女倆現在還能在這裡交換日記更是一種愛。但是恩恩,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人,怎麼努力也沒辦法擁有愛。
前陣子,退休同事來找我吃飯,拉我一起幫一位正在適婚年齡的女同事做媒人。女同事長得清清秀秀,碩士畢業的學歷,說話也輕聲細語,為人又乖巧,卻快四十歲了還沒有適合的對象。退休同事有個遠房姪子,恰好也是單身,我們想把他倆湊成對,那天就去吃了頓相親飯,並且在氣氛正好的時候退場,識相地留給他們獨處空間。
果然,兩個熟齡的單身男女,馬上就走在一塊了。說起來,男方也算一表人才,站在一起很是登對,我們都希望可以趕快吃到他們的喜酒,也算是成全了美事一樁。沒想到,前兩天女同事來找我們,一開口就拚命對我們說「阿姨對不起」「阿姨我該怎麼辦?」原來,他們倆才交往沒多久,甜蜜時光還沒過夠,女同事就發現男方有非常強烈的控制欲。比方說,女同事對男方說她會加班到八點,然後她可能很快就投入自己的工作,忙得沒有注意時間,等她想到的時候,手機裡已經有超過一百封男方傳來的訊息,以及無數個未接來電。
「還沒好嗎?」
「妳還沒好嗎?」
「妳真的還沒好嗎?」
「要到什麼時候?」「妳怎麼這麼慢?」
「妳現在在做什麼?」
「回家了嗎?」
「我怎麼找不到妳?」
「結束打給我?」
「還沒結束嗎?」……
恩恩,女同事拿這些訊息給我看時,我還真嚇了一跳。明明是一個看起來很有禮貌的男孩,相處起來卻給人這麼大的壓力,無時無刻緊迫盯人。我那退休同事聽到這個狀況,臉色也沉了下來,她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姪子在愛情中原來是這樣的。哎,這就是做媒人的風險啊,以為是自己親戚就不會出問題,現在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阿姨對不起,我不應該跟你們說這些的,可是我真的好害怕……」女同事都快急哭了,才告訴我們,她之前在愛情裡常常遇到這樣的人,所以交往過程中總被折磨,然後在巨大的衝突下分手,以致她戀情始終夭折,常常單身一人。女同事說,她真的很努力了,可是最終都對抗不了老天爺安排的命運。
「阿姨,老天爺是不是覺得,我不配擁有愛啊?」
恩恩,聽她這麼說,媽真的心疼啊。
媽媽
◆
親愛的媽媽:
交換日記了大半年,我想您一定理解我心裡的那個公式:當一個成年人發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時,我們便試著用對待小孩的立場來感受他,想像一下這些行為背後的焦慮是什麼—也就是他內在小孩的模樣。
我們先來想像一下這位男士的心情:女朋友不在身邊時會不斷追蹤,訊息像機關槍一樣連續發出,彷彿內心的焦慮完全停不下來。媽,您們稱這舉動為「控制」,然而「控制狂」的真相,其實是「害怕無法控制」,對「脫序」有強烈幻想式的焦慮,腦袋中裝了許多事情脫序後可能會出現的可怕後果,只是他們幾乎不去檢視這些可怕後果的真實性,便任憑那些幻想無限擴大,變成掌控內心的魔鬼。換句話說,這該是位極無安全感的男士吧?而且我想,焦慮感一定不是只在這段關係裡頭發生而已,或許他已經歷過多次相仿的愛情。
當然,我們也會好奇,這些強烈的、令人恐懼的幻想到底是怎麼來的,如果可以,我們真想這些焦慮永遠都不要找上我。精神分析稱這為「超我」,您可以將它理解成一種「良心」的發展—一開始是害怕做錯事情被責備,但良心發展太過,就變成一種「控制」了。媽,所以說「道德」和「瘋狂」永遠是一線之隔啊。克萊茵女士曾說,她在接近三歲與四歲的幼兒身上,就已經觀察到完整的超我運作,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因為小小孩將父母的形象給攝入到自己心裡了。簡而言之,父母就像一種背後靈,當面對外界事物時,我們幻想著他們的形象在身後指手畫腳,批評我們為人處世的態度。克萊茵女士還發現,小小孩對背後靈的感受,遠比兒童和成人恐怖得多,於是脆弱的心靈就這樣被幻想中的惡魔給深深蹂躪著,偏偏你又不敢將惡魔一腳踹開(開玩笑,那背後靈可是我爸我媽呀,踹開他們的話,我不就無父無母了?)。當背後靈跟著我們久了,和自我形象之間的界線便模糊了—我們開始不太清楚自己真實的想法、真實的感受,只好用那背後靈的形象,也開始點評我們所遇到的人。因此我聽過很多成年人痛恨地說:「可惡,我真的跟我爸(或我媽)好像啊。」
是的,如果我們有天感覺自己像個控制狂,八成和父母脫離不了關係,但這不代表現實中的父母,真的這麼嚴厲控制我們,導致我們內心衰弱,成為控制狂;而是我「想像」他們一直控制著我,然後因這份「想像」,進而逐漸變成一個控制狂。好吧,即便現實中我們真遇上控制型的父母,內心幻想的本能也會把這些控制放大了數十倍、甚至數百倍……
這就是心魔啊,媽。心魔其實是藏在我們心頭的幻想。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要擺脫心魔很難。我想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們很難發現它的存在,其二是我們往往缺乏擺脫心魔的信心。
媽,這點是我閱讀克萊茵女士後的啟發,當然,也是我在臨床工作中多次嘗試的結論:擺脫心魔其實不難,只要勇敢地將內心世界的恐怖幻想,提取出來與現實生活作檢核,就會明白內心的幻想往往不會成真(是的,人本來就容易往最糟的地方想去)。
有人可能會對這個結論嗤之以鼻:哼哼,控制狂哪有可能這麼理智,還檢核現實哩?如果他們有這麼冷靜,哪來被控制的人的痛苦?但我所見到的現實卻是:常常,被控制的人也不太冷靜,所以在控制的循環中,跟著一起墜入痛苦。媽,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要指責被控制的人做錯了什麼。而是依照「A等同B」的焦慮法則,有時我們會無意識地過度類化自己所面臨的情境—比方說:認識一個控制狂的男人,便無意識連結到原生家庭中充滿控制欲的父親,所以怎麼都無法放下這個男人不管,卻又在被控制的感受中深深焦慮。您還記得嗎?這就是我們先前提過的,「A等同B」的焦慮。
這種焦慮的運作,就像一條詭異的月老紅線,將心裡有相似問題的世間男男女女牽引在一起;因為敏感於同樣的困擾,便形成一種「臭味相投」的吸引力。相投的「臭味」是彼此都無法遠離痛苦的原因,也讓我們無法冷靜下來,去檢核幻想其實不等同於現實。
媽,既然我們倆是局外人,就試著以旁觀者的立場來翻譯一下男人的控制語言好了:
「還沒好嗎?」「妳還沒好嗎?」「妳真的還沒好嗎?」(這是在表達一種等待的焦慮)
「要到什麼時候?」「妳怎麼那麼慢?」「妳現在在做什麼?」(這是在表達伴侶沒有依約在八點回家—事情脫序—的生氣)
「回家了嗎?」「我怎麼找不到妳?」(這表達了對伴侶的擔憂,可能內心已經開始對脫序的事情產生某些幻想)
「結束打給我?」「還沒結束嗎?」(這些表達中參雜了焦慮和擔憂的不一致感,既擔心又生氣的矛盾,令人心裡發毛……)
媽,一個人如果能用一致的態度表達生氣,相處久了我們比較容易明白,怎麼單純應付對方可能生氣的點;同樣的,一個人如果能一致表達脆弱,我們也容易明白怎麼安撫他的脆弱。然而,有些伴侶之所以會被形容成「恐怖情人」,往往在於他們的表達裡頭,參雜了生氣和脆弱等不一致的訊息,讓人錯亂地不知如何回應才好。媽,或許女同事需要的是將對方的表達邏輯澄清清楚,才能決定:我究竟還要不要繼續陪伴這個人的生氣、脆弱,甚至是把我搞瘋了的矛盾?
當然,我的確認識一些「愛到卡慘死」的當事人,他們雖然在被控制的痛苦中,卻深知自己愛著對方,因此努力覺察對方控制行為背後的邏輯,以致能用「維持界限」的回應來面對控制型的伴侶:「對不起,我錯過和你相約的時間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擔心我,但是我需要你給我一些時間來完成自己的事情。」有些人在與伴侶不斷相互協調中,可能發展出一種相處模式:「因為我理解你的焦慮,所以我願意在忙碌的時候,以一種不會過於勉強的姿態,提醒自己在約定的時間打給你。」媽,有很多當是人會這麼問我:幹嘛要愛得這麼累?幹嘛要這樣妥協?
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常常用一個過高的標準來看待「愛」,誤以為「愛」就一定是自由自在地「接受」與「被接受」。然而,從克萊茵女士身上,我學習到:「愛」其實是一種能夠「付出」與「能夠被付出」的能力—前者,是一種「心甘情願」,後者,則是「感恩」。
「心甘情願」和「感恩」的主控權都在自己手上—它不是等來的,是一點一滴學習來的。所以說,人人都可以擁有愛,也都配擁有愛。
恩恩
通往心靈穩定的「哀悼」之路,
需要預備三種勇氣
親愛的媽媽:
如果是開始交換日記前,我大概免不了用埋怨來回應您的疑問:是啊!您身為我媽,怎麼說不出一句同理我的話?
又是克萊茵女士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和您提過的「論孤獨」,真是克萊茵女士的作品中,最能表達人生淒涼美感的一篇文章,裡頭這麼描述母嬰之間的關係:和母親(她指的是「乳房」,或具有象徵「乳房」意義的「奶瓶」)之間的早期關係,意味著嬰兒與母親潛意識上的親密接觸,也奠定了被了解的經驗。一個享受吸吮且心滿意足的嬰兒,會緩和母親的焦慮,而母親正向的哺乳經驗,也將呈現在她餵食嬰兒的方式當中。換句話說,嬰兒開心喝奶,母親就能開心餵奶;開心餵奶的母親,也能讓嬰兒開心喝奶。這是一種母嬰循環,彼此之間都需要負起相當的責任。
當然,叫一個還在吃奶的小嬰兒懂得「責任」這件事,對嬰兒來講未免也太沉重了。所以,許多心理學家的表達,總是認為母親要多擔待一點,要扛起更大部分的責任。然而,我真覺得克萊茵女士是一位相當堅強的女性,即便她本人與母親的關係並不如意,我幾乎沒見她在論述中講過母親壞話,她總是堅強又努力地,從孩子的立場去找出一條不用倚賴母親的路。
閱讀至今日,我實在是同意克萊茵女士這點的。如果生命註定是一場克服磨難的過程,那麼不管我們遇上什麼樣的父母,都只是為了造就出我們這樣的性格。可能有好的、有壞的,但都是獨特的、值得我們珍惜的。性格是一份禮物,重點是我們怎麼用這份禮物,去走向未來;哀悼那些渴求而不可得的失落,我們才能真心憐憫自己,真正邁向內在的穩定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