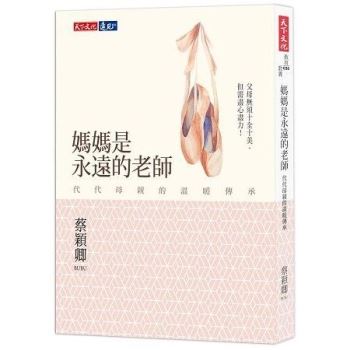母親的關懷
我是一個非常主張父母要深度關心孩子功課的資深母親,支持我這種想法的理由很簡單:
一是,我從小時候好好做功課的習慣裡,養成了日後自己取得或補上工作能力的方法,也延伸出面對工作難題時可以耐下心來的習慣。
二是,當了母親後,兩個女兒在離開大學之前,我一直都對他們的功課表達深度的關懷和濃厚的興趣。這個習慣到了後來,自然而然轉變成我們分享彼此工作的關心。
從小,我們對孩子的行為禮貌要求都很嚴格。只有在知識的討論上,孩子跟我們是平起平坐的好朋友。
前不久,《中國時報》開卷版有位記者電訪我對《正午惡魔》這本書的看法。她問我為什麼會看這本書,我記得那是七、八年前跟大女兒在談話中,討論到一名員工的憂鬱症,當時,我們的觀點有些不同,於是,去看一本資料豐富的書是擴展討論的好方法。
這本書是女兒介紹我看的,她一提出建議,我立刻上網買了書,認真看,因為我想跟她有深刻的溝通。
在我當母親這三十年,孩子所看的書有些是因為我們的引介而讀的,我也有不少書是因為她們的推薦才讀的。但這種習慣,並不是一開始就以一本本書的規模出現,而是他們小的時候,我總是關心她們的功課或留心看一張考卷得來的了解。無論形式是什麼,「內容」才是父母安放關心與發展了解最好的位置。
三是,以眼前社會的發展來看,知識程度就像一種基本配備。一個成績太差的孩子,即使有專家提出不少美好的理論,來支持「不一定要讀書」的人生路,但父母除了暫時感到寬心之外,又有什麼方法能夠讓幼年的孩子來發展自己?先不要說發展,就說小學或國中不好好讀書,整天要做什麼?既然社會已經比較富裕了,允許他們延長依賴期,把義務教育推向十二年,這代表他們是一定要在學校裡好好過完十八歲以前的人生。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幫助他們把每一天過得踏實一點?不要逃著書本,躲避學習。
把書讀好,跟在工作上好好表現是一樣的態度。沒有耐力解決課業困難的孩子,也往往在其他工作上表現出只有三份熱情的態度。絕對不能隨便找幾個成功的例子推論出「不會讀書會工作」的必然。無論讀書或工作,能吃苦的人都會比較出色。
四是,父母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因材施教,各成其才」的教育,但從教育現況看來,集體教育是現實,不管規模大小,我們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團體裡受教育。只要是集體教育,師資的素養與教導的時間,就難以全面達到父母對「因材施教」的期待。而在這種口號之下,孩子反而更早被放棄。父母對孩子這塊「材料」了解的最清楚,對「成才」的期望最殷切。如果父母懂得根據學校授課的不足,給予關懷,孩子即使被老師放棄,也不會真正失去機會。
不久前,有位媽媽跟我說,她下定決心,要好好關心老二荒廢了好一段時間的功課,所以她跟孩子提議:「我們每天早起,媽媽先陪你讀一點落後的進度,你再去上學。」沒想到隔天孩子更早起,在她還沒開始陪讀之前就跑到學校去了。
當這位煩惱的媽媽傾訴時,我只問她一句話:「他的功課內容你知道嗎?」她搖搖頭,我於是提議:「不用跟孩子宣告你要開始關心他的功課或陪他讀書,先把學校上什麼內容弄清楚。」
我告訴她,就算你起得比孩子更早,把他抓住,卻不知道功課的內容,也只能進行無話可說的監督。父母先檢討自己的態度,了解課業內容,就可以幫助大家進入踏實的關懷。
又一個早上,我收到一名學員寄來的 E-mail,她已經幫孩子請了數學家教,很謝謝我對孩子的關心。我立刻給她回信說,不是請家教就能解決問題,她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三十六分或五十二分代表了什麼樣的學習狀態。我請她過幾天來找我,我鼓勵她在我面前演算幾題孩子的數學題。
我這樣做是想讓她了解,一份考題裡,提供了多少幫助父母了解孩子的機會,還可以改善親子相處的氣氛。人如果真正同工,想專心把事做好,會自動不吵架,轉為對事不對人;看孩子功課就是要從這種心情開始,才會慢慢升等為更高階、更豐富的關心。
媽媽教信任
沒有責任做為中介,人不能表達「信任」,也不能了解「被信任」的意義。但是責任的規模可以小到很小、大到很大;如果想要盡早教會親子「信任」這一課,絕對可以從幼兒時期就落實於生活,而不是空喊「媽媽相信你,你一定做得到」,就能建立孩子的信心。
媽媽們往往忽略了自己是一個多麼不信任孩子的指導者;有時是怕孩子去完成責任,會帶來更多麻煩;有時是怕他們在完成責任當中受傷害;但更多時候,是因為不了解擺在眼前的,原來就是一個可以完成責任與信任循環的機會。
讓小小孩自己倒一杯水、打一個蛋這種生活學習,如今已是媽媽們願意也了解的信任教導;但同樣的父母,卻不一定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拿起筆,把眼前的一個水杯好好畫出來,或在教導下穿針引線之後,就可以自己縫紉。很多其實需要一點耐心或逐步克服一點小困難的工作,往往就被父母自行歸類於興趣或才能的一方。而孩子逐步要面對的課業也一樣,父母很少運用信任所能發揮的力量。
信任不是禮物,不能愈送愈大。在我的眼裡,信任就像滾元宵。父母先投出一個善意,那點「信任孩子做得到」的善意就是餡。這個善意滾上薄薄的第一層粉之後,信任就轉為能力。而後繼續一次次的努力、再努力,最後滾成了一顆元宵,擴大的全是屬於能力的粉,而不是餡。但誰來判斷一次次努力的規模呢?當然是父母。父母保持彈性的進退,何時該給予鼓舞,何時可以強力要求,才是「信任」的實務工作。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教我做家務,以整理一隻燙過毛的雞來說,就分為十幾次才完全放手讓我做。將近五十年前,家裡一個月頂多兩次會以整隻雞做為食材,母親在規劃這個教導時持續了好幾個月,是因為她了解,養成能力對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來說,需要一步、一步來;但那一步、一步當中,又不能只是看過或做過就好,絕不能疏於練習,逢有機會就溫故。
我記得頭幾次媽媽在燙雞時,只讓我在一旁看,看她怎麼穩穩抓住雞的兩腳,在煮開的水裡翻身燙毛,但她不會讓這麼小的我就嘗試這種事。我也很乖,不會不管大人的生活現實,習慣得寸就進尺。我因為早早學會尊重大人的判斷與決定,更增強了母親對我的信任。陪伴過媽媽拔兩次雞毛,仔細的示範怎麼處理大羽毛和需要用眉毛夾處理的小細毛之後,母親才放心的讓我自己處理,分身去做其他事。
我為了想學拔毛之後更細部的工作處理,一心一意把眼前所會的工作,做到能贏得母親的讚賞,那就是除了交給她一隻乾淨俐落的光雞之外,我還把毛都包好了拿去丟,也把地都洗得乾乾淨淨。得到信任之後,母親開始教我怎麼取內臟,做米血。我每學會一件事,就代表下一次不用任何提醒,能從頭至尾完成同樣的工作。
母親用信任,養出我一生受惠無窮的工作習慣──從計劃到完成。她不是發號施令,也不會不停的協助我,更不會在我的工作成果並不夠好的時候,敷衍了事的說我「已經很棒了」。她總是客觀、誠懇、平心靜氣的跟我檢討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方法。記憶裡,我的生活裡不是由稱讚或責備填寫起來的,而是充滿了信任的、一個大過一個規模的「能力訓練」。
我的弱點,因為母親信任我而能更好的得到提升,我的強處,也因為母親對我的信任而得以盡情發揮。比這兩者更好的是,這種教育的養成,使我在面對任何責任時都習慣對事不對人;習慣要求自己,勝過要求他人。
我是一個非常主張父母要深度關心孩子功課的資深母親,支持我這種想法的理由很簡單:
一是,我從小時候好好做功課的習慣裡,養成了日後自己取得或補上工作能力的方法,也延伸出面對工作難題時可以耐下心來的習慣。
二是,當了母親後,兩個女兒在離開大學之前,我一直都對他們的功課表達深度的關懷和濃厚的興趣。這個習慣到了後來,自然而然轉變成我們分享彼此工作的關心。
從小,我們對孩子的行為禮貌要求都很嚴格。只有在知識的討論上,孩子跟我們是平起平坐的好朋友。
前不久,《中國時報》開卷版有位記者電訪我對《正午惡魔》這本書的看法。她問我為什麼會看這本書,我記得那是七、八年前跟大女兒在談話中,討論到一名員工的憂鬱症,當時,我們的觀點有些不同,於是,去看一本資料豐富的書是擴展討論的好方法。
這本書是女兒介紹我看的,她一提出建議,我立刻上網買了書,認真看,因為我想跟她有深刻的溝通。
在我當母親這三十年,孩子所看的書有些是因為我們的引介而讀的,我也有不少書是因為她們的推薦才讀的。但這種習慣,並不是一開始就以一本本書的規模出現,而是他們小的時候,我總是關心她們的功課或留心看一張考卷得來的了解。無論形式是什麼,「內容」才是父母安放關心與發展了解最好的位置。
三是,以眼前社會的發展來看,知識程度就像一種基本配備。一個成績太差的孩子,即使有專家提出不少美好的理論,來支持「不一定要讀書」的人生路,但父母除了暫時感到寬心之外,又有什麼方法能夠讓幼年的孩子來發展自己?先不要說發展,就說小學或國中不好好讀書,整天要做什麼?既然社會已經比較富裕了,允許他們延長依賴期,把義務教育推向十二年,這代表他們是一定要在學校裡好好過完十八歲以前的人生。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幫助他們把每一天過得踏實一點?不要逃著書本,躲避學習。
把書讀好,跟在工作上好好表現是一樣的態度。沒有耐力解決課業困難的孩子,也往往在其他工作上表現出只有三份熱情的態度。絕對不能隨便找幾個成功的例子推論出「不會讀書會工作」的必然。無論讀書或工作,能吃苦的人都會比較出色。
四是,父母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因材施教,各成其才」的教育,但從教育現況看來,集體教育是現實,不管規模大小,我們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團體裡受教育。只要是集體教育,師資的素養與教導的時間,就難以全面達到父母對「因材施教」的期待。而在這種口號之下,孩子反而更早被放棄。父母對孩子這塊「材料」了解的最清楚,對「成才」的期望最殷切。如果父母懂得根據學校授課的不足,給予關懷,孩子即使被老師放棄,也不會真正失去機會。
不久前,有位媽媽跟我說,她下定決心,要好好關心老二荒廢了好一段時間的功課,所以她跟孩子提議:「我們每天早起,媽媽先陪你讀一點落後的進度,你再去上學。」沒想到隔天孩子更早起,在她還沒開始陪讀之前就跑到學校去了。
當這位煩惱的媽媽傾訴時,我只問她一句話:「他的功課內容你知道嗎?」她搖搖頭,我於是提議:「不用跟孩子宣告你要開始關心他的功課或陪他讀書,先把學校上什麼內容弄清楚。」
我告訴她,就算你起得比孩子更早,把他抓住,卻不知道功課的內容,也只能進行無話可說的監督。父母先檢討自己的態度,了解課業內容,就可以幫助大家進入踏實的關懷。
又一個早上,我收到一名學員寄來的 E-mail,她已經幫孩子請了數學家教,很謝謝我對孩子的關心。我立刻給她回信說,不是請家教就能解決問題,她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三十六分或五十二分代表了什麼樣的學習狀態。我請她過幾天來找我,我鼓勵她在我面前演算幾題孩子的數學題。
我這樣做是想讓她了解,一份考題裡,提供了多少幫助父母了解孩子的機會,還可以改善親子相處的氣氛。人如果真正同工,想專心把事做好,會自動不吵架,轉為對事不對人;看孩子功課就是要從這種心情開始,才會慢慢升等為更高階、更豐富的關心。
媽媽教信任
沒有責任做為中介,人不能表達「信任」,也不能了解「被信任」的意義。但是責任的規模可以小到很小、大到很大;如果想要盡早教會親子「信任」這一課,絕對可以從幼兒時期就落實於生活,而不是空喊「媽媽相信你,你一定做得到」,就能建立孩子的信心。
媽媽們往往忽略了自己是一個多麼不信任孩子的指導者;有時是怕孩子去完成責任,會帶來更多麻煩;有時是怕他們在完成責任當中受傷害;但更多時候,是因為不了解擺在眼前的,原來就是一個可以完成責任與信任循環的機會。
讓小小孩自己倒一杯水、打一個蛋這種生活學習,如今已是媽媽們願意也了解的信任教導;但同樣的父母,卻不一定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拿起筆,把眼前的一個水杯好好畫出來,或在教導下穿針引線之後,就可以自己縫紉。很多其實需要一點耐心或逐步克服一點小困難的工作,往往就被父母自行歸類於興趣或才能的一方。而孩子逐步要面對的課業也一樣,父母很少運用信任所能發揮的力量。
信任不是禮物,不能愈送愈大。在我的眼裡,信任就像滾元宵。父母先投出一個善意,那點「信任孩子做得到」的善意就是餡。這個善意滾上薄薄的第一層粉之後,信任就轉為能力。而後繼續一次次的努力、再努力,最後滾成了一顆元宵,擴大的全是屬於能力的粉,而不是餡。但誰來判斷一次次努力的規模呢?當然是父母。父母保持彈性的進退,何時該給予鼓舞,何時可以強力要求,才是「信任」的實務工作。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教我做家務,以整理一隻燙過毛的雞來說,就分為十幾次才完全放手讓我做。將近五十年前,家裡一個月頂多兩次會以整隻雞做為食材,母親在規劃這個教導時持續了好幾個月,是因為她了解,養成能力對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來說,需要一步、一步來;但那一步、一步當中,又不能只是看過或做過就好,絕不能疏於練習,逢有機會就溫故。
我記得頭幾次媽媽在燙雞時,只讓我在一旁看,看她怎麼穩穩抓住雞的兩腳,在煮開的水裡翻身燙毛,但她不會讓這麼小的我就嘗試這種事。我也很乖,不會不管大人的生活現實,習慣得寸就進尺。我因為早早學會尊重大人的判斷與決定,更增強了母親對我的信任。陪伴過媽媽拔兩次雞毛,仔細的示範怎麼處理大羽毛和需要用眉毛夾處理的小細毛之後,母親才放心的讓我自己處理,分身去做其他事。
我為了想學拔毛之後更細部的工作處理,一心一意把眼前所會的工作,做到能贏得母親的讚賞,那就是除了交給她一隻乾淨俐落的光雞之外,我還把毛都包好了拿去丟,也把地都洗得乾乾淨淨。得到信任之後,母親開始教我怎麼取內臟,做米血。我每學會一件事,就代表下一次不用任何提醒,能從頭至尾完成同樣的工作。
母親用信任,養出我一生受惠無窮的工作習慣──從計劃到完成。她不是發號施令,也不會不停的協助我,更不會在我的工作成果並不夠好的時候,敷衍了事的說我「已經很棒了」。她總是客觀、誠懇、平心靜氣的跟我檢討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方法。記憶裡,我的生活裡不是由稱讚或責備填寫起來的,而是充滿了信任的、一個大過一個規模的「能力訓練」。
我的弱點,因為母親信任我而能更好的得到提升,我的強處,也因為母親對我的信任而得以盡情發揮。比這兩者更好的是,這種教育的養成,使我在面對任何責任時都習慣對事不對人;習慣要求自己,勝過要求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