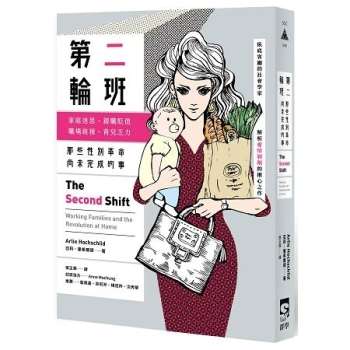第四章 喬伊問題:南茜與伊凡。霍特
南茜。霍特下班回到家,一手抱著兒子喬伊,另一手拎著一袋剛採購好的用品。她放下手上東西把門打開後,便看見玄關地板上散落一堆信件,桌上是喬伊吃剩的肉桂土司,電話機上閃著紅色燈號。眼前這般景象讓人不難想像今天早上,這一家人是如何匆忙地衝向外面的世界。三十歲的南茜,當了七年的社工,有著金色削薄短髮,講話跟動作速度都很快。她一邊脫掉大衣,一邊俐落的把信件收到桌上,然後走向廚房。喬伊緊緊黏在媽媽身後,興沖沖地說著自動卸貨卡車怎麼卸貨。喬伊四歲,有著圓圓的臉頰,活潑好動,只要有點讓他感到開心的事情都會不住咯咯笑。
南茜的丈夫,伊凡,停好紅色休旅車後便走進屋內,把大衣掛起來。伊凡接南茜下班一起回家。他顯然沒打算要面對廚房的騷亂,也不好意思馬上到客廳看報紙放鬆,於是慢慢地查看桌上的信件。伊凡也三十歲,是個家具批發商業務,有一頭薄薄的淡金髮,體格結實,站立時習慣把重心放在一隻腳上。他待人接物的態度親切同時有些游移不定。
南茜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描繪為一名「熱切的女性主義者」,要求各方面的平衡以及對等的權力。在婚姻生活的一開始,她希望自己跟伊凡能同時保持對親職和事業的認同,但是明顯地偏向於親職。伊凡的態度則是,只要南茜能夠把家庭顧好,他可以接受南茜擁有事業。
在我到他們家中進行觀察的某個晚上,我注意到這個家庭的一池春水正泛起小漣漪。忙碌的廚房裏頭傳來南茜的叫聲:「伊凡——,可以麻煩你擺一下餐具嗎?」「麻煩」這兩個字帶著明顯的惱怒口氣。那時,南茜在冰箱、水槽和爐灶之間忙進忙出,喬伊又黏在她腳跟。她希望伊凡能夠幫忙。雖然她開口要求了,卻討厭自己這麼做。她似乎很不喜歡這個要求的動作(稍後她向我吐露,「我討厭求人;我為甚麼要這麼做呢?那讓我感覺在乞討。」)。聽到妻子的叫聲,伊凡從信件中抬起頭,惱怒地瞥了一眼廚房,他可能被這種缺乏尊重的要求刺了一下。他開始擺設刀叉,問南茜是否會用到湯匙云云。此刻門鈴響了,伊凡前去應門。是位鄰居的小孩。伊凡向鄰居小孩表示,喬伊現在不能出去玩哦。一觸即發的時刻便這樣度過。
在我稍晚分開訪談他們兩人時,南茜和伊凡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的家庭生活十分快樂——除了喬伊帶來的「問題」。因為喬伊很難入睡,他們開始試著在晚上八點就哄他睡覺。伊凡總是受到喬伊的抗拒,南茜的運氣則較好。直到八點半,好不容易把喬伊弄上床了,他卻在那爬啊、跳啊地玩個沒停。過了九點,他還在那吵著要玩具或喝水,或者偷偷摸摸地爬下床開燈。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九點半、十點,然後十點半。到了十一點時,喬伊抱怨自己的床讓他「怕怕」,一定要到爸爸媽媽的臥房睡。筋疲力竭的南茜,只得接受兒子的提議。這是他們夫妻倆目前的協議,哄喬伊睡覺屬於「南茜的工作」。南茜跟伊凡即便累壞了,到午夜或更晚都還沒辦法睡覺。南茜告訴我,過去她很享受兩人之間的性愛,但現在,性對她好像是「多出來的工作」。霍特夫婦將他們疲倦、貧瘠的性生活,視為這個喬伊問題帶來的結果。
喬伊問題的官方歷史,也就是根據南茜和伊凡有共識的說法,是始於喬伊與南茜兩人間強烈的依附關係。某個午後,我們一同在金門公園散步時,南茜緊緊關注著喬伊的一舉一動。喬伊看見松鼠,南茜便告訴我她下次一定要記得帶點核果來。喬伊爬上溜滑梯,南茜就注意到他的褲子太短,晚上要把褲子放長。母子兩人享受著彼此的親密相處。而在官方說法之外,鄰居跟褓姆都表示南茜是位很棒的母親,但接著又私下談論到,南茜有多「像個單親媽媽。」
至於伊凡,則沒花那麼多時間在喬伊身上。他晚上固定在地下室做點自己的事情,而且喬伊與母親在一起時總是看起來很快樂。事實上,喬伊對伊凡沒什麼興趣,而伊凡不知道要不要把這個現象視為問題。帶著點哲學味,他解釋道:「小孩子都這樣啦,需要媽媽超過需要爸爸」;「所有小男生都會經歷過這種戀母情結的階段。」
於是發生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經過某個漫長的一天後,母親、父親和兒子坐下來一同享用晚餐。這是一整天下來,伊凡與南茜首度有機會交談,然而兩人均焦慮地轉向喬伊,準備好面對兒子心情的惡化。南茜問喬伊,你是不是想在芹菜上面加一點花生醬,喬伊說對。「你確定真的要這樣加嗎?」「對。」然後是一陣坐立不安,「我不喜歡我芹菜上面的纖維」。「芹菜就是這些纖維做的啊」。「但這個芹菜太大了。」南茜沈著臉把芹菜切細,某種緊張氣氛升起。每次夫妻兩人剛開始要交談,喬伊便會打斷,例如說「我沒有東西可以喝」,南茜便拿果汁給他。最後,喬伊便嚷嚷著:「餵我。」貫穿整個晚餐,無人可以阻礙喬伊的勝利。他佔有母親不情願的關注,父親只好轉向啤酒。而在稍晚與他們兩人的對話中,他們都告訴我:「有小孩這樣是正常的。」
有時,當伊凡去褓姆那裡接喬伊,喬伊的視線會繞過父親,找尋他身後的另一張面孔:「媽媽呢?」有時候他直接拒絕跟爸爸一塊回家。漸漸地,喬伊甚至會用力拍打他爸爸,有一次,喬伊「沒有任何理由」就很大力地打在伊凡臉上。這使人再也無法將喬伊與伊凡的關係想像為「稀鬆平常」。伊凡和南茜開始嚴肅地討論這個「用力拍打問題」。
前面提及,伊凡與南茜對喬伊問題的官方說法是,喬伊對母親的依附是男童正常的戀母情結。但是,伊凡及南茜也補充解釋,他們認為喬伊問題的日益惡化,是因為伊凡不是一個積極的父親。他們覺得,這可能是受到伊凡與他父親的互動經驗影響。伊凡的父親是個不茍言笑、不擅於自我表達的商人。伊凡告訴我,「等喬伊長大些,我們會一起去玩籃球、釣魚。」
經過訪談和觀察,我在記錄下喬伊問題的官方說法時,心裡開始對這個說法產生懷疑。在某個尋常的夜晚,從他們三人腳步聲的模式中,另種詮釋喬伊問題的詮釋的線索浮現出來了。那個晚上,南茜以她平日的步調在廚房準備晚餐,她在冰箱、櫥櫃和爐子之間來回 Z字形移動。喬伊輕快的腳步聲以大大「8」字型穿梭房子各處,從他的通卡卡車衝向摩托車人玩具,在這些他的東西之間,重新確認對家的歸屬感。晚餐後,南茜與伊凡在廚房一起收拾的腳步聲混在一起。
接著,南茜又開始動作,一會跑到地下室把衣服丟洗衣機,一會又從鋪著地毯的樓梯,砰砰地跑回一樓。接著她到浴室幫喬伊洗澡、到喬伊的房間拿東西,又回到浴室。相較之下,伊凡的移動軌跡簡單得多,從客廳椅子上走到廚房幫忙南茜,然後又回到客廳。他到飯廳吃晚餐,之後到廚房協助清理。晚餐後,他會到他自己在地下室的工作室整理工具,晚些走上來喝杯啤酒,然後再回到地下室。他們的腳步聲透露:是南茜在承擔第二輪班的工作。
腳步聲背後
每天早上八點五分到下午六點五分,南茜與伊凡都不在家裡,他們在外投入「第一輪班」的全職工作。其餘的時間他們用來處理第二輪班大大小小的事務:採買、煮飯、付帳單、照顧汽車、打點花園和後院,以及與伊凡的母親博感情。伊凡的母親時常順道拜訪兒子跟媳婦,關心喬伊的近況。同時,他們也需經營與鄰居、健談的褓姆,以及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在南茜的談話中,流露出她腦中各種關於第二輪班事務的思緒,諸如「我們的烤肉醬要用完了……喬伊需要萬聖節服裝……喬伊需要剪頭髮了」等。這反映出她對第二輪班事務的敏感度,也反映出她對於不斷重新在孩子、配偶、家庭和職場之間找尋情緒平衡這項任務,有持續的覺察。
在他們婚姻進入第五年的某個晚上,南茜告訴我,當喬伊兩個月大時(幾乎是在我認識霍特夫婦的四年前),她第一次嚴肅地跟伊凡提起家務分工的問題。「我告訴他:『伊凡,這樣是行不通的。家事我在做,喬伊也是我在照顧,我同時還有自己的正職工作。我真的生氣了。這家你也有份啊,喬伊也是你的小孩啊。不該都是我一個人在照顧家庭和孩子吧。』等我冷靜下來後,我對他說『那你看這樣好不好,禮拜一、三、五我負責煮飯,二、四、六你負責,週日我們一起煮或出去吃。』」
根據南茜的說法,伊凡說他不喜歡「這麼嚴格的日程表。」他說自己對家務的標準跟南茜不一定一樣,也不喜歡南茜硬要把自己的標準加在他身上。尤其是有時候他覺得南茜是把工作「推給他」。但是他原則上同意這個作法。南茜回憶這個計畫付諸實行的第一週,情況是這樣的:週一時,她依約定煮飯。到了週二,伊凡忘記採買他要煮晚餐的材料,他回到家發現冰箱或櫥櫃裏沒有他可以用的東西,因此向南茜提議出去吃中國菜。週三,南茜煮飯。
週四早上,南茜特意提醒伊凡,「今晚你要負責哦。」當晚伊凡準備了漢堡和炸薯條,南茜趕緊稱讚他。週五,南茜負責。到了週六,伊凡再度忘記他要煮飯。
南茜出於挫折,開始在言語上拐彎抹角地戳伊凡,例如說「我不知道晚上要煮什麼。」邊說還邊嘆口大氣。或者「我現在沒法煮飯,因為我必須先去洗一大堆的衣服。」而當伊凡對家事哪裡做得不妥當,表達出一絲絲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都會令南茜神經緊繃。南茜認為如果他一點家事都不做,就根本沒有權利對我做的方式指指點點。有時,她還會勃然大怒:「上了一天班,我的腳跟你的腳一樣累。工作中我必須上緊發條,就跟你一樣。但我回到家,還必須煮飯、洗衣服和打掃家裡。我們還在計畫要不要生第二個孩子,但我連目前這個都應付不來了。」
在初次拜訪霍特夫婦大約兩年後,我開始將他們的問題,視為在他們兩人之間,兩種性別觀念的衝突。兩人的性別觀各自都承載了許多個人符號。南茜想要成為那種不論在家中或職場,都被需要與被認可的女性。她想要的是,伊凡能夠明瞭她作為一名關懷他人的社工、謹守承諾的妻子,以及十分稱職的母親的價值。但她同樣在意的是,她也能夠因為伊凡在家裡的付出而感謝他,而非僅僅因為伊凡有在賺錢養家。那麼,在她向女性友人提及自己嫁了這樣一個男人時,她會覺得很驕傲。
性別意識形態往往根植於早期經驗,並且被早年生活中的某些警世故事形成的動機所強化。對南茜而言亦如此,她說:「我的母親是個很好的女人,真的有種貴族氣質,但家庭主婦的身份使她變得非常消沉。我父親待她就像一塊門前的腳踏墊,使她完全失去自信。我長大後都還記得她一直很抑鬱,因此我決心,絕不重蹈她的命運,也絕不嫁個像我父親一樣的男人。每當伊凡不願做家事,我就覺得他快要跟我爸爸一樣了——回到家、兩腿一蹺,使喚我媽伺候他。這是我最大的恐懼,也是我長久來的惡夢。」
南茜認為在跟她同齡的女性友人中,步入傳統婚姻的,都不免遭遇類似的下場。她描述一個高中時代的朋友:「瑪莎很勉強才從市立學院畢業,她對學習任何事物都沒興趣。她有九年的時間就這樣每天跟在她丈夫身後。真是一段悲慘的婚姻。
她手洗丈夫所有的襯衫。她人生的高峰是十八歲的時候,我跟她兩人開著野馬敞篷車在邁阿密海灘奔馳。現在她體重多了七十磅、並且討厭自己的人生。」對南茜而言,瑪莎是她母親的年輕翻版,消沈、缺乏自尊。這個警世故事傳遞的道德訓誡是:「如果你想要有個幸福人生,就去建立自己的事業,並且讓丈夫開始分擔家務吧。」一次又一次要求伊凡動手幫忙,是個困難的工作,但這對南茜來說,也是避免自己踏上瑪莎或自己母親命運的努力。
伊凡也有自己的理由,使他對事情有十分不同的想像。他愛南茜,並且很樂意也很驕傲地支持南茜熱愛的社工工作。他明白因為南茜對待每個案子都十分認真,需要全心投入。但同時他不明白,為什麼因為南茜自己選擇了一個要求很高的事業,他就要為此改變自己的生活。為什麼她可以因為個人抉擇,而要求他在家中做更多?南茜的收入大約是伊凡的三分之二,這對於家計有很大幫助,但也如她吐露:「真正得抉擇的話,我們也可以放棄這份收入。」她從事社工是因為她喜愛這份工作。而對伊凡來說,做家事吃力不討好,他也肯定不需要妻子在這點上體認到他的價值。均分第二輪班,意味著要降低他個人的生活水平。撇開相關的高調不論,他個人並未真正認同任何形式的協議。如果南茜需要,他很樂意在家事上提供協助,這他可以接受。這也合理。但是要他對某種正式的家務均分計畫做承諾,他覺得很有問題也很奇怪。
另外有兩種信念,可能也加強了他的抗拒行為。第一個信念是,他在想,如果自己與南茜共同分擔第二輪班,南茜將會支配他。南茜會要求他做這做那。伊凡覺得,這就很像南茜獲得許多小勝利,而使得他必須在別處設下界線。南茜有某種宣示性人格;如她坦承:「伊凡的母親曾要我坐下來談談,提醒我太強勢了,伊凡需要擁有更多作主的感覺。」南茜與伊凡均認為,伊凡對事業和自我的意識其實沒有南茜堅定。伊凡曾經歷失業,南茜沒有;伊凡曾有一陣子染上酒癮,而南茜從不喝酒。伊凡認為分攤家務會破壞一種文化上正確的權力平衡。他掌握家中的經濟大權,大筆支出都由他決定(例如買房子),因為他「擁有較豐富的財務知識」,也因為在結婚時,伊凡貢獻了比較多財產在兩人名下。他在事業上的顛簸,降低了他的自尊。
而作為夫婦,他們兩人達成某種無法言喻的平衡,如果為了家務分攤的平等去矯正這個平衡,將會導致伊凡讓步「太多」,雖然南茜顯然認為這是對伊凡有利的說法。南茜在某種焦慮的驅動下,採取了扮演主動協商者的策略,而這個南茜的焦慮,使伊凡將他們的協議視為他的「讓步」。當他在工作上出現負面感受時,便會對於妻子在家裡對他頤指氣使這樣的念頭感到擔憂懼怕。
在這些感受背後,伊凡可能也是在擔憂南茜是在逃避照顧他。伊凡的母親酗酒,逐漸忘卻了母親的角色,讓伊凡幾乎都是獨自一人度過。這是我的揣測,伊凡並未如此闡述──也許,由於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他的婚姻中,這種個人動機,構成他消極抵抗策略的基礎。伊凡的恐懼,並非全然可歸咎於他。同時,他覺得自己曾給過南茜機會,看是要待在家裡,還是減少工作時數,但他覺得南茜拒絕了他的禮物。而就南茜的感受來說,伊凡的提議恐怕遠遠稱不上是禮物。
經過七年的恩愛婚姻,南茜與伊凡最後走到了糟糕的僵局。他們開始怒斥、批評對方,並且吹毛求疵。雙方都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對伊凡而言,他提出的適合安排都不被接受,而對南茜來說,則是因為伊凡不按照她認為公平的方式行事。
雙方的苦鬥延燒到他們的性生活。最初問題直接顯現在南茜身上,接著是喬伊造成的問題。南茜一直以來都鄙視任何利用女性魅力操弄、博取好處的形式,她不屑這種傳統女性用來對付男性的手段。她的家人視她為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者,南茜也這麼看自己。「在我的青少年時期」,她陷入思緒,低聲地說,「我就發誓我絕不利用性從男人身上得到我想要的。這樣不自重也有損尊嚴。但當伊凡拒絕承擔他的家務責任時,我卻這麼幹了,我利用了性。我對伊凡說:『要不是每天早上一醒來要面對這麼多事情,我也不會每晚這麼疲憊、性趣缺缺。』」她覺得自己退到傳統的策略,而她的現代觀念讓她對此感到羞愧。但是她也沒有任何其他「現代」的途徑可用了。
分居的念頭出現了,這讓他們感到驚恐。南茜看一看身邊帶著年幼小孩的年輕夫婦婚姻惡化,接著離婚的案例。一個他們認識的不快樂的丈夫,變得與家庭十分疏離(他們不確定,是因為他不快樂導致他的疏離,還是他的疏離,導致他的妻子變得不快樂),最終妻子離他而去。在另一個例子,南茜覺得那位妻子對丈夫嘮叨過度,導致丈夫離開她,投向另一個女人的懷抱。在這兩個案例中,這些夫婦離婚之後並沒有過得比離婚前快樂。兩個妻子都帶走小孩,與前夫爭奪子女的撫養權,為了錢和時間辛苦不已。南茜開始評估,並問自己「為何要為了一個髒鍋子讓婚姻沉船呢?」這真的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