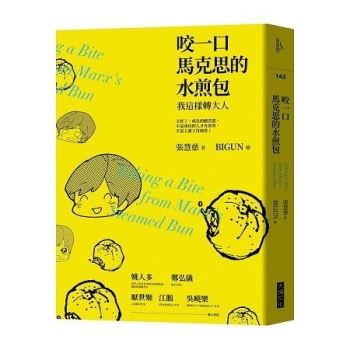二姑姑的白鯧魚
有讀書不代表就不傳統,我爸那邊,是非常傳統的重男輕女家庭。
爸爸是長子也是獨子,在國小畢業後,因為對讀書毫無興趣,所以就跟著阿公做土水。在台北跟當時做美髮的母親認識,進而結婚。雲林小子與嘉義女孩,戀愛結婚,然後生下了四個小孩,在新莊定居下來。
父母感情並不好,從我有記憶開始,一直都在吵架,至今還是每天都在吵,維持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床頭吵不一定會床尾合,某市長拿這句話來當兩岸關係的註解,我覺得是沒有看見幸福家庭以外的世界。
因此,從小到大我都覺得他們一定是相親結婚。這大概是一種大腦的保護機制,為了要讓我可以合理化他們的感情失和,為了要讓我對於小時候的不好回憶都有統計學上的理由。但是,悲劇的,他們就是戀愛結婚的。
感情的持續惡化,我跟大妹大概也推波助瀾了一下。爸爸是獨子,妻子沒辦法一舉得男,二舉也沒有得男,勢必會非常緊張,緊張到全家族都在想辦法。是否應該離婚再娶一個?還是要繼續努力?這樣的討論從來沒有停過,連帶我們也沒有被受到重視。
好險,媽媽在第三胎,終於生下了一個男孩。
男孩跟救世主一樣被生下來,就好像在海上遇難漂流的漁民,終於遇到他們心中的女神林默娘一樣,備受期待。
小時候,我一直以為我的小名叫大隻,我妹叫作小隻。直到我弟出生後,我才知道,我以為的小名,不過就是對於牲畜的叫法。因為我們是女生啊,沒有記得名字或是呼喊名字的需要。只要用大隻小隻形容就好。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這個男孩,在一歲半時,被長庚的腎臟科醫師診斷錯誤,從感冒引起的腎臟發炎,惡化成慢性腎臟病。弟弟一夕之間從受寵的長孫,變成了受盡冷落、嘲諷的生病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媽媽只能邊工作,邊照顧弟弟。自然而然的,照顧最小妹妹的責任,也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說起我這個最小的妹妹,她的出生完全是個民間傳說。傳說中,生了一個男孩,下一個也會是男孩。所以,媽媽為了證明這個傳說是個無稽之談,就賭氣生了我最小的妹妹。緊接著,弟弟就發病了,媽媽也僅能將大半的心力放到這個弟弟身上。妹妹的出生,什麼也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就是大妹的小名從小隻,變成了中隻。小隻,被我最小的妹妹給繼承了。這樣的情況下,媽媽其實也沒辦法太照顧到我們。應該說,一直以來,媽媽都沒有什麼時間照顧我們。大妹放在鄉下,讓二嬸婆顧著。等到有一天我媽發現,妹妹為什麼還不會講話。才突然意識到,孩子對於語言的掌握,是透過學習的。二嬸婆跟姑姑非常疼愛妹妹,但姑姑工作繁忙,二嬸婆是個啞巴,沒有人跟我妹講話,自然,我妹就不會講話。
最後,我媽只好把我妹接回來,請住在一條街外的阿姨幫忙照看著。然後,請外公外婆幫忙照看小妹,我則是當時還沒出嫁的二姑姑照顧著。
二姑姑可以說是我當時的人生典範。
三十歲,有著穩定的紡織廠的工作,有一定的投資,沒有打算結婚,完全是個都會新女性形象。她常常帶著我去紡織廠工作,把我放在他的針車附近,然後我乖乖的看書,或者是在不干擾二姑姑工作的情況下,在一格格好像棋盤的針車房裡面遊走,到處跟不同的姐姐阿姨聊天,然後得到很多點心。
中午的時候,大家都會一起吃飯。我跟著二姑姑以及她的同事們一起去員工餐廳吃飯,員工餐廳裡面是一張張圓桌,上面會有不同的炒青菜、白飯、湯,以及一條白鯧魚。
煎白鯧魚一直都是我最愛的一道料理,從外型到味道,無一不討喜。煎白鯧魚之前,一定要先在兩面的魚身上劃上兩刀,再放入油燒得滾熱但平靜的煎鍋中。滋滋作響的油聲,是美味白鯧魚的進行曲。煎成赤赤、金黃色的白鯧魚起鍋後,一定要用方形的瓷盤盛裝。
白鯧魚是非常具有幾何美的生物,四四方方的身體,該尖的地方尖,該流線的地方就是完美的拋物線。有圓潤有尖銳,一定要用最正的盤子來凸顯這樣的美感。並且,放在圓桌上,看起來有對比的樣子。
每次白鯧魚一上桌,二姑姑跟同事們總是會先讓我夾。我的手不長,但我都夾得到。我把幾乎半隻的魚夾到我的盤子裡面,品嘗卡滋卡滋的聲音在我的嘴裡奏著。必須要有很多聲音,才能讓我心靈安定。必須要有動作,才能讓我有所依靠。吃,是最好的動作。吃,也是一種保護機制。
其實午餐時間也沒有很久,匆匆的吃完後,跟著二姑姑回到她的縫紉機旁。聽著車衣服的聲音,聞著棉絮以及針車油的味道,我通常都會睡著。
其實我也真不記得我到底都在做些什麼,或者在想些什麼。可能只想著白鯧魚,或者是下午都會買來吃的炸彈麵包。炸彈麵包物如其名,做得就像炸彈一樣,其實更接近的,是飛行船的樣子。炸彈麵包比我的臉還要大,比我的手還要大,我兩手無法握好握滿炸彈麵包。我通常都先從一邊吃起,咬去炸彈填充火藥的地方,裡面露出一顆顆紫黑色的葡萄乾。接著,用短短的手指去拿起一粒葡萄乾。先咬一半,把鹹澀的皮給咬去。伸出舌頭舔一舔裡面軟嫩,帶著酸味甜味的內裡,然後再吃掉。將舉目所及的所有葡萄乾都吃完後,再繼續啃咬外層如同波蘿麵包一樣,帶著椰香的酥皮,直到又再度露出新的葡萄乾苗圃。
重複著這樣的動作,直到整個炸彈麵包吃完,大概可以用掉一個小時。一來一往,大概也就剩下兩個小時,二姑姑便下班了。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其實我都知道,我知道二姑姑沒有那麼喜歡我,沒有那麼想照顧我。試著想想看,一個獨立、花樣的都會女性,必須要幫忙哥哥照顧他的小孩,還要上班,誰會心甘情願呢?再加上當時我並不是一個討喜的小孩,我也不知道,原來我吃掉的白鯧魚,是姑姑必須要額外花錢請廚房多煎給我的。
但我很喜歡二姑姑,即使她比較喜歡我那個童年因為不會講話而安靜討喜的妹妹,我還是很喜歡二姑姑。
我一直覺得,二姑姑的人生,是被我阿公跟爸爸給毀了。
活得獨立自主的女性,還是逃不離傳統的枷鎖,走入了婚姻。這個婚姻,不是她自己選的,是他的父親,他的兄長,從對方的財務狀況表徵中,精挑細選的。好像沒有人問過她願不願意,只記得有一天,我自己跑去二姑姑的房間,她看著牆壁上貼著的《尼羅河女兒》的海報,頭戴很多金飾,身穿埃及造型衣物的女孩,倚靠在一樣頭戴很多金飾,看起來就是高富帥的男人身上,女孩眼神透露著驚恐,並沒有因為她倚靠在男人懷裡有半點消去。
我看著這樣的姑姑,過了一會兒,她說:
「足足(慈的閩南語發音),查某囝仔不一定要結婚,自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妳甘知?」
因此,當阿公在醫院彌留,二姑姑從南部趕上來後,劈頭指著我們說:
「阿公是被你們害死的,你們都會有報應」的那個時候,我無法恨她,也不埋怨她。只是想到童年的白鯧魚,那煎得赤赤黃黃,裝在方盤裡面的白鯧魚,已經很久沒吃了。白鯧魚跟著姑姑的青春與亮麗,流向那名為傳統的大海裡了。再也捕撈不到,再也不敢想了。要做大事
說到底,小六那時候對於數學課變成體育課的不爽,也單單只是對於要流汗的厭惡以及對運動的厭煩,對於反攻大陸,我卻是一點也沒有懷疑的。
部編版的學生,應該都對這一課有印象吧?國文課本,第二冊第一課,〈立志做大事〉。課文是這樣寫的:
「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並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地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不得不承認,我真的深受感動。回家後,一直跟爸媽說:
「我以後要做大事,賺大錢,不要做大官。」
話說完後,忘了媽媽還是爸爸還是阿公,接著就說:「做啥攏好,不通摻政治。」
不通摻政治,跟不要做大官是同樣的事情,所以,當時我並沒有覺得奇怪,只是滿心思考:要做哪些大事才可以賺大錢呢?對一個國小學童來說,思考如何賺大錢實在是非常困難,畢竟身邊擁有的錢也就只有下課後得以在學校的對面,買半塊炸雞排以及抽一次獎的錢。
至於身邊的長輩,也沒辦法給我太多意見,生活就夠他們疲於奔命了。
我的父母都是南部小孩,為了要討生活,才遷移至台北工作。爸爸是跟隨阿公腳步上台北的。很早就知道種田無法養活一家人,所以阿公早早就上台北了。阿公從攪拌混凝土開始,一路蓋房子,建起了台灣的黃金時代,養活了一家人。最後,終於在新莊買了公寓二樓二十坪左右的房子。
阿公是日本統治時代末期出生的,在我的記憶中,阿公是個哈日族。小時候阿公會拿五十音給我們背,還會拿〈桃太郎〉的歌譜給我們,並且教我們唱。
那時候我簡直可以參加日本小學歌唱大賽。
我唱歌並不好聽,到現在也還是。但當時,我真的很會唱〈桃太郎〉,是全部每一段歌詞都會唱的那一種。然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有錢能使鬼推磨。阿公祭出了高額的獎金,只要背五十音,就有五十塊。唱〈桃太郎〉,就有五十元。加起來就是一百元了。
人客啊,知影一百元對於一九九五年的新莊小孩有多大嗎?以我這個新莊孩子為例,媽媽每天給我五十元,讓我去吃早餐。當時的早餐店跟盧廣仲所唱的〈早安晨之美〉差不多,只是沒有好多好多的早餐在這裡,就是一些簡單的紅茶奶茶咖啡可樂以及吐司跟蘿蔔糕煎餃蛋餅這類歷久彌新的基本款,選擇不多,但也足夠,當時真的很容易滿足。
每個小朋友一拿到錢的那一剎那,就已經是個小小精算師了。五十元,是我的總財產。我每天必須要做到幾件事情:
一、吃早餐。
二、抽獎。
三、吃點心。
做到這幾件事情,才能算是完成每日任務。
早餐通常是這樣的,一個巧克力土司加上一杯冰紅茶,二十元。
抽獎一次五元,兩次十元,我都會抽兩次。
下課後,會去買炸肉串加上炸薯條,這樣也是二十元。或是奢華一點,直接吃炸雞排,也是二十元。這樣,一整天的花費剛好五十元。然而,下午如果沒有辦法去福利社買飲料或是點心之類的,在班上會有一點邊緣。但我們家有四個小孩,我沒有勇氣再跟媽媽多拿錢了。因此,開源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背一背五十音,唱一唱〈桃太郎〉,就有一百元。一百元不僅可以讓我每天下午都去福利社買東西,還可以存下來買貼紙或多抽一點獎。這根本就是生存的大事了,所以,我小時候日語還滿溜的。
當時即便如此,對於日本,我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看法,在課本裡、課堂上,日本都是中華民國的仇人。日軍殺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侵略我國領土,最後是正義之士美軍投了兩個原子彈,才中止了日軍的侵略。
在家裡,日本人是為台灣帶來進步、安全的好政府,只要人民乖乖,再窮也可以讀書。晚上不用關門,沒有人會做壞事,因為有警察大人。
現在想來非常神奇,在當時我居然沒有精神混亂。我那時候覺得,課本裡寫的日本人,應該都在台北,所以很壞。但我阿公遇到的日本人,都是在南部,所以人比較好。只是當阿公罵國民政府,特別是蔣中正的時候,我會非常生氣。我記得有一天,我還跟老師說我阿公在家都說日本人比較好,蔣中正是壞人。老師冷冷的跟我說:「阿公沒讀書。」
阿公是有讀書的,而且阿公很喜歡讀書。直到阿公過世後,我都很後悔當時沒有跟老師說:「我阿公很會讀書,他日文真的很好。」阿公在日本統治時期,有就讀公學校,是識字的。我爸那邊一直是務農的,阿公是長子,上面有一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身為長男,基本上是被認為要繼承家業的。但阿公喜歡讀書,而且聽說他真的超會讀書。所以,當時阿公一定在想:「我認真讀書,就可以讓厝邊隔壁看得起,可以讓全家人過好日子,可以較過得去,不用一直辛苦種田,有一頓沒二頓的。」
一個想著未來可以坐辦公室,讓家裡的人過好日子的雲林小子。怎麼想也想不到,給他希望的日本統治者,會有被打倒的一天。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緊接而來,在後代課本裡面記載如同救世主般的國民政府,真正的毀去他的夢想。他沒辦法念書了。他所學習的日語以及相關知識,都沒有任何的用處。他慣用的母語閩南語,也因為是不入流的方言,而被禁止。瞬間,他人生的一切都被否定,他所想像的未來再也無法企及。他們之前存下來的錢,因為四萬換一塊,也瞬間蒸發。所以,他只能回去種田。只能去當學徒,學拌混泥土、蓋房子,來養活一家大小。然後,管好自己的嘴。
Working (on) Holiday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上帝關了一扇門,必打開另扇窗。」
高中時,我沒有太多時間傷春悲秋。在我高中的時候,弟弟的病情急速惡化。弟弟國中一年級,出席的時間幾乎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曾經討論過是否休學,以利銜接上學業。弟弟不想,當然也就作罷。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花費難免會變高。除了本來就要自費施打的免疫球蛋白,一罐一萬元以外;住院費等雜費也越來越高,妹妹也確診出了中度氣喘,小妹不明原因頭痛,霎時我變成全家最健康的孩子。醫藥與讀書費用增加,媽媽加班加得更勤了,幾乎不曾休假,為的就是多賺一點錢。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好的不會一直來,壞的不會只來一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上帝關了一扇門,一定不會忘記把窗戶也一併關上,還不准你開空調。
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有打工經驗。打工成為年輕人接觸社會的模式,近幾年政府也不斷鼓勵年輕人在寒暑假多充實自己的經驗。打工,是我生存的條件。
從我有意識開始,我的雙手就沒有停過。頁數 7/9
弟妹陸續出生,因為要照顧的關係,媽媽很早就放棄做美髮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大量的手工回家做。我一直跟朋友說,我們家是假性貧窮。我出生那年房地產起飛,課本都有寫。做土木工程的爸爸賺了非常多的錢,但都沒有拿回家。所以,小時候我真的以為我們家很窮,窮到爸爸一個月只能拿五千不到給媽媽。養四個小孩,負擔家裡所有的開銷。再後來,弟弟就生病了。
五千元,那個年代,一九九〇後了,是一碗陽春麵要二十五元的年代,是一把青菜要十元的年代。除了房價,一般民生物價其實跟現在相差真的不遠。要讀書、要上幼稚園、要看醫生,即使每天都吃白麵條加青菜,也是不夠用的。
我的手真的很快,巧是說不上。做手工要的是手快,手巧不是必備。一張拜拜用的,60X60大的摺疊桌攤開,就是工作的區塊。有時候是別針,媽媽把針帽插上別針,這個步驟比較危險。妹妹把別針放進小塑膠袋,我負責釘上釘書機。有時候是髮夾,我很害怕髮夾,下層鐵片有兩個突出的小鐵點,把小鐵點先上後下塞入髮夾上層鐵洞後,「啪」的一聲固定的這個步驟,我很常夾到手。髮夾、別針,都是暖身商品。到了後期,最大宗的就是電子插件的手工。
媽媽有一張桌子,是小學生兩個人可以用的,前方還有筆槽的木桌。媽媽買了一張非常厚的透明墊放在上頭,充當工作桌使用。我跟媽媽各坐一個位子,把一塊很像流蘇條,長度相等偏硬的金屬片,插入格數與流蘇條相等的塑膠殼裡,調整好角度,前頓一下,後頓一下,卡好卡滿,這樣算完成一個。一個好像是一角吧?「卡」這個動作我練了非常久,只要用力不當,就會把金屬插件給弄壞。弄壞的金屬觸角會卡在洞裡,要一根根拔出,非常浪費時間。毀損率過高也會影響到下次可以拿件的數量,所以我謹慎以待。整個國小,都在卡、頓聲中度過。
媽媽的墊子上,早就已經沒有完好的地方了。
國中開始,媽媽去哪裡工作,假日我就去哪裡打工。泳鏡工廠、無敵CD辭典工廠、電子工廠等等,都有我的足跡。雖然一天的薪水只有幾百元,但還有供餐,一來一往,省去不少,也認識了很多媽媽的同事,有時還會獲得額外的點心。比起在家裡煮飯給弟妹吃,還要擔心爸爸會不會生氣。出來工作,有錢賺又輕鬆,很有尊嚴。到了家庭組成截然不同的高中,我自怨自艾了一陣子後,主動跟老師坦白家庭狀況。在老師的推薦下,我中午在學校的設備組打工,分類化學物品以及洗洗燒杯試管。一週兩天,一個月兩千。我跟惠青只要領到錢,就會去借漫畫跟喝星巴克。看漫畫是興趣,星巴克是洗禮。透過星巴克,我覺得我跟同班同學的距離有漸漸縮短。充滿美式風格的建築物,很像梅杜莎的頭像的綠色LOGO印在白色的紙杯上,裡頭的褐色液體,飄散出大人的、高級的、上流的味道。一定要是熱的,才有上流感。我不懂得欣賞裡面的液體,但我希望透過這些苦澀(雖然已經是全糖)的汁液,汰換流竄全身,充滿貧窮味的血液。
高二時,媽媽突然問我,暑假要不要去她工作的電子工廠打工,一個月有三萬。比起不穩定的打工,到工廠工作,似乎更有賺頭,我便答應了。
縱使有媽媽推薦,還是有一些過場要走。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面試。拿著履歷表,穿著制服,下課後坐著公車搖搖晃晃的到達靠近新莊迴龍的工廠。確定時間與待遇後,暑假的第一天,我就到工廠報到了。
原則上都是媽媽上班順便載我去,我們先吃完早餐,然後再一起上班。上班前,媽媽買了一台收音機給我,避免我無聊,可以聽廣播工作。那兩個月,是我跟媽媽最親近的兩個月。每天形影不離的。雖然我們在不同廠區工作,但中午的時候,媽媽會幫我訂便當,我再走去跟媽媽一起吃。
第一次遇到來自東南亞的勞工,也是在那個時候。安妮是來自印尼的勞工,跟工廠簽契約的,全年無休,賺得錢全部都拿回家鄉,讓家鄉蓋房子。換了兩三次名字,待了快十年了,終於,今年期滿,可以回家結婚了。她是媽媽的好朋友,也比誰對我都還好。安妮教我很多工作技巧,也曾經在我打瞌睡,差點把削刀削過我的手臂時,即時把我的手臂拉走,讓我現在還可以用電腦打字。工廠的規定很嚴格,是安妮教我可以偷偷在廁所睡覺,多長時間內不會被發現。
我很勤快,比幾個來打工的大學生都還要厲害,很快就站上了更高的職位,主管還問我畢業後要不要直接來工作。因為我受重用,導致我在裡面其實有點被排擠。常常工作都是做最重的,有什麼通知都不會告訴我,犯錯也都怪到我身上。但也因為我很任勞任怨,後來有些出差都會派我去,也讓我碰觸到更多關於這個行業的點滴。最重要的,可以吃很好的牛肉麵。媽媽很常帶我們去吃巷口的牛肉麵。
牛肉麵的老闆叫老王,是外省老兵,跟著國民政府來台,因為回不去了,所以在台灣娶妻生子,用家鄉的手藝,在新莊的小巷子裡擺攤。老王的老婆是台灣人,我們都叫她阿姨。一碗牛肉麵五十元,湯麵三十元。我都吃湯麵,比較便宜,而且我不喜歡吃牛肉。老王牛肉麵湯頭很特別,是黑色的。跟市售的不一樣,帶點甜味,老王說是山東口味。他們家最好吃的還有滷菜,豬耳朵、豆乾、海帶,偶爾奢侈點會吃牛肚。肚子很餓時,還會加點水餃。一家五口三百元,還可以一人買一瓶阿薩姆紅茶、速纖或生活花茶。老王跟阿姨很喜歡我們,我們挑的小菜永遠切出來都會比別人多,麵都大碗量小碗價。我們喜歡聽老王講他家鄉的故事,聽他說撤退來台的故事,聽他在台灣落腳的故事。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彎彎繞繞,沒有那麼多國家力量,只是一個小老百姓,被迫跟來台灣,落地生根,一個大時代促成的悲劇。後來,開放省親時他有回家,帶著老婆一起回去。前妻帶著孩子改嫁了,如同那個年代的眾多故事。沒辦法happy ending,但終究是活著回去看了一眼。後來,不管我到哪裡去,回家時總是叫媽媽帶我們去吃老王牛肉麵。一路吃著,老王中風、生病、過世,兒子學藝不精,開了幾年就沒開了。
出差的牛肉麵,只是一種高級的象徵,說不上好吃還是不好吃。跟我一起出差的,是一個長得很像《麻辣鮮師》中萬人美老師的阿姨。她對我也很好,常常任我點。最後一次出差,她告訴我,好好讀書,才是孝順媽媽的最好方式。
平日晚上加班的是媽媽,假日加班的是我,完美的錯開,確實的加班費入袋。我用那些錢,買了一支Nokia 3310。剩下的錢一半給媽媽,一半我自己花。
有自己的錢可以用,才有活著的真實感。
工廠的打工過後,媽媽問我:「想在工廠工作,還是去讀書?」
我說:「讀書比較輕鬆,我以後要坐辦公室吹冷氣,讓大家過好生活。」
有讀書不代表就不傳統,我爸那邊,是非常傳統的重男輕女家庭。
爸爸是長子也是獨子,在國小畢業後,因為對讀書毫無興趣,所以就跟著阿公做土水。在台北跟當時做美髮的母親認識,進而結婚。雲林小子與嘉義女孩,戀愛結婚,然後生下了四個小孩,在新莊定居下來。
父母感情並不好,從我有記憶開始,一直都在吵架,至今還是每天都在吵,維持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床頭吵不一定會床尾合,某市長拿這句話來當兩岸關係的註解,我覺得是沒有看見幸福家庭以外的世界。
因此,從小到大我都覺得他們一定是相親結婚。這大概是一種大腦的保護機制,為了要讓我可以合理化他們的感情失和,為了要讓我對於小時候的不好回憶都有統計學上的理由。但是,悲劇的,他們就是戀愛結婚的。
感情的持續惡化,我跟大妹大概也推波助瀾了一下。爸爸是獨子,妻子沒辦法一舉得男,二舉也沒有得男,勢必會非常緊張,緊張到全家族都在想辦法。是否應該離婚再娶一個?還是要繼續努力?這樣的討論從來沒有停過,連帶我們也沒有被受到重視。
好險,媽媽在第三胎,終於生下了一個男孩。
男孩跟救世主一樣被生下來,就好像在海上遇難漂流的漁民,終於遇到他們心中的女神林默娘一樣,備受期待。
小時候,我一直以為我的小名叫大隻,我妹叫作小隻。直到我弟出生後,我才知道,我以為的小名,不過就是對於牲畜的叫法。因為我們是女生啊,沒有記得名字或是呼喊名字的需要。只要用大隻小隻形容就好。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這個男孩,在一歲半時,被長庚的腎臟科醫師診斷錯誤,從感冒引起的腎臟發炎,惡化成慢性腎臟病。弟弟一夕之間從受寵的長孫,變成了受盡冷落、嘲諷的生病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媽媽只能邊工作,邊照顧弟弟。自然而然的,照顧最小妹妹的責任,也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說起我這個最小的妹妹,她的出生完全是個民間傳說。傳說中,生了一個男孩,下一個也會是男孩。所以,媽媽為了證明這個傳說是個無稽之談,就賭氣生了我最小的妹妹。緊接著,弟弟就發病了,媽媽也僅能將大半的心力放到這個弟弟身上。妹妹的出生,什麼也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就是大妹的小名從小隻,變成了中隻。小隻,被我最小的妹妹給繼承了。這樣的情況下,媽媽其實也沒辦法太照顧到我們。應該說,一直以來,媽媽都沒有什麼時間照顧我們。大妹放在鄉下,讓二嬸婆顧著。等到有一天我媽發現,妹妹為什麼還不會講話。才突然意識到,孩子對於語言的掌握,是透過學習的。二嬸婆跟姑姑非常疼愛妹妹,但姑姑工作繁忙,二嬸婆是個啞巴,沒有人跟我妹講話,自然,我妹就不會講話。
最後,我媽只好把我妹接回來,請住在一條街外的阿姨幫忙照看著。然後,請外公外婆幫忙照看小妹,我則是當時還沒出嫁的二姑姑照顧著。
二姑姑可以說是我當時的人生典範。
三十歲,有著穩定的紡織廠的工作,有一定的投資,沒有打算結婚,完全是個都會新女性形象。她常常帶著我去紡織廠工作,把我放在他的針車附近,然後我乖乖的看書,或者是在不干擾二姑姑工作的情況下,在一格格好像棋盤的針車房裡面遊走,到處跟不同的姐姐阿姨聊天,然後得到很多點心。
中午的時候,大家都會一起吃飯。我跟著二姑姑以及她的同事們一起去員工餐廳吃飯,員工餐廳裡面是一張張圓桌,上面會有不同的炒青菜、白飯、湯,以及一條白鯧魚。
煎白鯧魚一直都是我最愛的一道料理,從外型到味道,無一不討喜。煎白鯧魚之前,一定要先在兩面的魚身上劃上兩刀,再放入油燒得滾熱但平靜的煎鍋中。滋滋作響的油聲,是美味白鯧魚的進行曲。煎成赤赤、金黃色的白鯧魚起鍋後,一定要用方形的瓷盤盛裝。
白鯧魚是非常具有幾何美的生物,四四方方的身體,該尖的地方尖,該流線的地方就是完美的拋物線。有圓潤有尖銳,一定要用最正的盤子來凸顯這樣的美感。並且,放在圓桌上,看起來有對比的樣子。
每次白鯧魚一上桌,二姑姑跟同事們總是會先讓我夾。我的手不長,但我都夾得到。我把幾乎半隻的魚夾到我的盤子裡面,品嘗卡滋卡滋的聲音在我的嘴裡奏著。必須要有很多聲音,才能讓我心靈安定。必須要有動作,才能讓我有所依靠。吃,是最好的動作。吃,也是一種保護機制。
其實午餐時間也沒有很久,匆匆的吃完後,跟著二姑姑回到她的縫紉機旁。聽著車衣服的聲音,聞著棉絮以及針車油的味道,我通常都會睡著。
其實我也真不記得我到底都在做些什麼,或者在想些什麼。可能只想著白鯧魚,或者是下午都會買來吃的炸彈麵包。炸彈麵包物如其名,做得就像炸彈一樣,其實更接近的,是飛行船的樣子。炸彈麵包比我的臉還要大,比我的手還要大,我兩手無法握好握滿炸彈麵包。我通常都先從一邊吃起,咬去炸彈填充火藥的地方,裡面露出一顆顆紫黑色的葡萄乾。接著,用短短的手指去拿起一粒葡萄乾。先咬一半,把鹹澀的皮給咬去。伸出舌頭舔一舔裡面軟嫩,帶著酸味甜味的內裡,然後再吃掉。將舉目所及的所有葡萄乾都吃完後,再繼續啃咬外層如同波蘿麵包一樣,帶著椰香的酥皮,直到又再度露出新的葡萄乾苗圃。
重複著這樣的動作,直到整個炸彈麵包吃完,大概可以用掉一個小時。一來一往,大概也就剩下兩個小時,二姑姑便下班了。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其實我都知道,我知道二姑姑沒有那麼喜歡我,沒有那麼想照顧我。試著想想看,一個獨立、花樣的都會女性,必須要幫忙哥哥照顧他的小孩,還要上班,誰會心甘情願呢?再加上當時我並不是一個討喜的小孩,我也不知道,原來我吃掉的白鯧魚,是姑姑必須要額外花錢請廚房多煎給我的。
但我很喜歡二姑姑,即使她比較喜歡我那個童年因為不會講話而安靜討喜的妹妹,我還是很喜歡二姑姑。
我一直覺得,二姑姑的人生,是被我阿公跟爸爸給毀了。
活得獨立自主的女性,還是逃不離傳統的枷鎖,走入了婚姻。這個婚姻,不是她自己選的,是他的父親,他的兄長,從對方的財務狀況表徵中,精挑細選的。好像沒有人問過她願不願意,只記得有一天,我自己跑去二姑姑的房間,她看著牆壁上貼著的《尼羅河女兒》的海報,頭戴很多金飾,身穿埃及造型衣物的女孩,倚靠在一樣頭戴很多金飾,看起來就是高富帥的男人身上,女孩眼神透露著驚恐,並沒有因為她倚靠在男人懷裡有半點消去。
我看著這樣的姑姑,過了一會兒,她說:
「足足(慈的閩南語發音),查某囝仔不一定要結婚,自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妳甘知?」
因此,當阿公在醫院彌留,二姑姑從南部趕上來後,劈頭指著我們說:
「阿公是被你們害死的,你們都會有報應」的那個時候,我無法恨她,也不埋怨她。只是想到童年的白鯧魚,那煎得赤赤黃黃,裝在方盤裡面的白鯧魚,已經很久沒吃了。白鯧魚跟著姑姑的青春與亮麗,流向那名為傳統的大海裡了。再也捕撈不到,再也不敢想了。要做大事
說到底,小六那時候對於數學課變成體育課的不爽,也單單只是對於要流汗的厭惡以及對運動的厭煩,對於反攻大陸,我卻是一點也沒有懷疑的。
部編版的學生,應該都對這一課有印象吧?國文課本,第二冊第一課,〈立志做大事〉。課文是這樣寫的:
「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並不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地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不得不承認,我真的深受感動。回家後,一直跟爸媽說:
「我以後要做大事,賺大錢,不要做大官。」
話說完後,忘了媽媽還是爸爸還是阿公,接著就說:「做啥攏好,不通摻政治。」
不通摻政治,跟不要做大官是同樣的事情,所以,當時我並沒有覺得奇怪,只是滿心思考:要做哪些大事才可以賺大錢呢?對一個國小學童來說,思考如何賺大錢實在是非常困難,畢竟身邊擁有的錢也就只有下課後得以在學校的對面,買半塊炸雞排以及抽一次獎的錢。
至於身邊的長輩,也沒辦法給我太多意見,生活就夠他們疲於奔命了。
我的父母都是南部小孩,為了要討生活,才遷移至台北工作。爸爸是跟隨阿公腳步上台北的。很早就知道種田無法養活一家人,所以阿公早早就上台北了。阿公從攪拌混凝土開始,一路蓋房子,建起了台灣的黃金時代,養活了一家人。最後,終於在新莊買了公寓二樓二十坪左右的房子。
阿公是日本統治時代末期出生的,在我的記憶中,阿公是個哈日族。小時候阿公會拿五十音給我們背,還會拿〈桃太郎〉的歌譜給我們,並且教我們唱。
那時候我簡直可以參加日本小學歌唱大賽。
我唱歌並不好聽,到現在也還是。但當時,我真的很會唱〈桃太郎〉,是全部每一段歌詞都會唱的那一種。然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有錢能使鬼推磨。阿公祭出了高額的獎金,只要背五十音,就有五十塊。唱〈桃太郎〉,就有五十元。加起來就是一百元了。
人客啊,知影一百元對於一九九五年的新莊小孩有多大嗎?以我這個新莊孩子為例,媽媽每天給我五十元,讓我去吃早餐。當時的早餐店跟盧廣仲所唱的〈早安晨之美〉差不多,只是沒有好多好多的早餐在這裡,就是一些簡單的紅茶奶茶咖啡可樂以及吐司跟蘿蔔糕煎餃蛋餅這類歷久彌新的基本款,選擇不多,但也足夠,當時真的很容易滿足。
每個小朋友一拿到錢的那一剎那,就已經是個小小精算師了。五十元,是我的總財產。我每天必須要做到幾件事情:
一、吃早餐。
二、抽獎。
三、吃點心。
做到這幾件事情,才能算是完成每日任務。
早餐通常是這樣的,一個巧克力土司加上一杯冰紅茶,二十元。
抽獎一次五元,兩次十元,我都會抽兩次。
下課後,會去買炸肉串加上炸薯條,這樣也是二十元。或是奢華一點,直接吃炸雞排,也是二十元。這樣,一整天的花費剛好五十元。然而,下午如果沒有辦法去福利社買飲料或是點心之類的,在班上會有一點邊緣。但我們家有四個小孩,我沒有勇氣再跟媽媽多拿錢了。因此,開源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背一背五十音,唱一唱〈桃太郎〉,就有一百元。一百元不僅可以讓我每天下午都去福利社買東西,還可以存下來買貼紙或多抽一點獎。這根本就是生存的大事了,所以,我小時候日語還滿溜的。
當時即便如此,對於日本,我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看法,在課本裡、課堂上,日本都是中華民國的仇人。日軍殺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侵略我國領土,最後是正義之士美軍投了兩個原子彈,才中止了日軍的侵略。
在家裡,日本人是為台灣帶來進步、安全的好政府,只要人民乖乖,再窮也可以讀書。晚上不用關門,沒有人會做壞事,因為有警察大人。
現在想來非常神奇,在當時我居然沒有精神混亂。我那時候覺得,課本裡寫的日本人,應該都在台北,所以很壞。但我阿公遇到的日本人,都是在南部,所以人比較好。只是當阿公罵國民政府,特別是蔣中正的時候,我會非常生氣。我記得有一天,我還跟老師說我阿公在家都說日本人比較好,蔣中正是壞人。老師冷冷的跟我說:「阿公沒讀書。」
阿公是有讀書的,而且阿公很喜歡讀書。直到阿公過世後,我都很後悔當時沒有跟老師說:「我阿公很會讀書,他日文真的很好。」阿公在日本統治時期,有就讀公學校,是識字的。我爸那邊一直是務農的,阿公是長子,上面有一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身為長男,基本上是被認為要繼承家業的。但阿公喜歡讀書,而且聽說他真的超會讀書。所以,當時阿公一定在想:「我認真讀書,就可以讓厝邊隔壁看得起,可以讓全家人過好日子,可以較過得去,不用一直辛苦種田,有一頓沒二頓的。」
一個想著未來可以坐辦公室,讓家裡的人過好日子的雲林小子。怎麼想也想不到,給他希望的日本統治者,會有被打倒的一天。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緊接而來,在後代課本裡面記載如同救世主般的國民政府,真正的毀去他的夢想。他沒辦法念書了。他所學習的日語以及相關知識,都沒有任何的用處。他慣用的母語閩南語,也因為是不入流的方言,而被禁止。瞬間,他人生的一切都被否定,他所想像的未來再也無法企及。他們之前存下來的錢,因為四萬換一塊,也瞬間蒸發。所以,他只能回去種田。只能去當學徒,學拌混泥土、蓋房子,來養活一家大小。然後,管好自己的嘴。
Working (on) Holiday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上帝關了一扇門,必打開另扇窗。」
高中時,我沒有太多時間傷春悲秋。在我高中的時候,弟弟的病情急速惡化。弟弟國中一年級,出席的時間幾乎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曾經討論過是否休學,以利銜接上學業。弟弟不想,當然也就作罷。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花費難免會變高。除了本來就要自費施打的免疫球蛋白,一罐一萬元以外;住院費等雜費也越來越高,妹妹也確診出了中度氣喘,小妹不明原因頭痛,霎時我變成全家最健康的孩子。醫藥與讀書費用增加,媽媽加班加得更勤了,幾乎不曾休假,為的就是多賺一點錢。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好的不會一直來,壞的不會只來一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上帝關了一扇門,一定不會忘記把窗戶也一併關上,還不准你開空調。
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有打工經驗。打工成為年輕人接觸社會的模式,近幾年政府也不斷鼓勵年輕人在寒暑假多充實自己的經驗。打工,是我生存的條件。
從我有意識開始,我的雙手就沒有停過。頁數 7/9
弟妹陸續出生,因為要照顧的關係,媽媽很早就放棄做美髮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大量的手工回家做。我一直跟朋友說,我們家是假性貧窮。我出生那年房地產起飛,課本都有寫。做土木工程的爸爸賺了非常多的錢,但都沒有拿回家。所以,小時候我真的以為我們家很窮,窮到爸爸一個月只能拿五千不到給媽媽。養四個小孩,負擔家裡所有的開銷。再後來,弟弟就生病了。
五千元,那個年代,一九九〇後了,是一碗陽春麵要二十五元的年代,是一把青菜要十元的年代。除了房價,一般民生物價其實跟現在相差真的不遠。要讀書、要上幼稚園、要看醫生,即使每天都吃白麵條加青菜,也是不夠用的。
我的手真的很快,巧是說不上。做手工要的是手快,手巧不是必備。一張拜拜用的,60X60大的摺疊桌攤開,就是工作的區塊。有時候是別針,媽媽把針帽插上別針,這個步驟比較危險。妹妹把別針放進小塑膠袋,我負責釘上釘書機。有時候是髮夾,我很害怕髮夾,下層鐵片有兩個突出的小鐵點,把小鐵點先上後下塞入髮夾上層鐵洞後,「啪」的一聲固定的這個步驟,我很常夾到手。髮夾、別針,都是暖身商品。到了後期,最大宗的就是電子插件的手工。
媽媽有一張桌子,是小學生兩個人可以用的,前方還有筆槽的木桌。媽媽買了一張非常厚的透明墊放在上頭,充當工作桌使用。我跟媽媽各坐一個位子,把一塊很像流蘇條,長度相等偏硬的金屬片,插入格數與流蘇條相等的塑膠殼裡,調整好角度,前頓一下,後頓一下,卡好卡滿,這樣算完成一個。一個好像是一角吧?「卡」這個動作我練了非常久,只要用力不當,就會把金屬插件給弄壞。弄壞的金屬觸角會卡在洞裡,要一根根拔出,非常浪費時間。毀損率過高也會影響到下次可以拿件的數量,所以我謹慎以待。整個國小,都在卡、頓聲中度過。
媽媽的墊子上,早就已經沒有完好的地方了。
國中開始,媽媽去哪裡工作,假日我就去哪裡打工。泳鏡工廠、無敵CD辭典工廠、電子工廠等等,都有我的足跡。雖然一天的薪水只有幾百元,但還有供餐,一來一往,省去不少,也認識了很多媽媽的同事,有時還會獲得額外的點心。比起在家裡煮飯給弟妹吃,還要擔心爸爸會不會生氣。出來工作,有錢賺又輕鬆,很有尊嚴。到了家庭組成截然不同的高中,我自怨自艾了一陣子後,主動跟老師坦白家庭狀況。在老師的推薦下,我中午在學校的設備組打工,分類化學物品以及洗洗燒杯試管。一週兩天,一個月兩千。我跟惠青只要領到錢,就會去借漫畫跟喝星巴克。看漫畫是興趣,星巴克是洗禮。透過星巴克,我覺得我跟同班同學的距離有漸漸縮短。充滿美式風格的建築物,很像梅杜莎的頭像的綠色LOGO印在白色的紙杯上,裡頭的褐色液體,飄散出大人的、高級的、上流的味道。一定要是熱的,才有上流感。我不懂得欣賞裡面的液體,但我希望透過這些苦澀(雖然已經是全糖)的汁液,汰換流竄全身,充滿貧窮味的血液。
高二時,媽媽突然問我,暑假要不要去她工作的電子工廠打工,一個月有三萬。比起不穩定的打工,到工廠工作,似乎更有賺頭,我便答應了。
縱使有媽媽推薦,還是有一些過場要走。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面試。拿著履歷表,穿著制服,下課後坐著公車搖搖晃晃的到達靠近新莊迴龍的工廠。確定時間與待遇後,暑假的第一天,我就到工廠報到了。
原則上都是媽媽上班順便載我去,我們先吃完早餐,然後再一起上班。上班前,媽媽買了一台收音機給我,避免我無聊,可以聽廣播工作。那兩個月,是我跟媽媽最親近的兩個月。每天形影不離的。雖然我們在不同廠區工作,但中午的時候,媽媽會幫我訂便當,我再走去跟媽媽一起吃。
第一次遇到來自東南亞的勞工,也是在那個時候。安妮是來自印尼的勞工,跟工廠簽契約的,全年無休,賺得錢全部都拿回家鄉,讓家鄉蓋房子。換了兩三次名字,待了快十年了,終於,今年期滿,可以回家結婚了。她是媽媽的好朋友,也比誰對我都還好。安妮教我很多工作技巧,也曾經在我打瞌睡,差點把削刀削過我的手臂時,即時把我的手臂拉走,讓我現在還可以用電腦打字。工廠的規定很嚴格,是安妮教我可以偷偷在廁所睡覺,多長時間內不會被發現。
我很勤快,比幾個來打工的大學生都還要厲害,很快就站上了更高的職位,主管還問我畢業後要不要直接來工作。因為我受重用,導致我在裡面其實有點被排擠。常常工作都是做最重的,有什麼通知都不會告訴我,犯錯也都怪到我身上。但也因為我很任勞任怨,後來有些出差都會派我去,也讓我碰觸到更多關於這個行業的點滴。最重要的,可以吃很好的牛肉麵。媽媽很常帶我們去吃巷口的牛肉麵。
牛肉麵的老闆叫老王,是外省老兵,跟著國民政府來台,因為回不去了,所以在台灣娶妻生子,用家鄉的手藝,在新莊的小巷子裡擺攤。老王的老婆是台灣人,我們都叫她阿姨。一碗牛肉麵五十元,湯麵三十元。我都吃湯麵,比較便宜,而且我不喜歡吃牛肉。老王牛肉麵湯頭很特別,是黑色的。跟市售的不一樣,帶點甜味,老王說是山東口味。他們家最好吃的還有滷菜,豬耳朵、豆乾、海帶,偶爾奢侈點會吃牛肚。肚子很餓時,還會加點水餃。一家五口三百元,還可以一人買一瓶阿薩姆紅茶、速纖或生活花茶。老王跟阿姨很喜歡我們,我們挑的小菜永遠切出來都會比別人多,麵都大碗量小碗價。我們喜歡聽老王講他家鄉的故事,聽他說撤退來台的故事,聽他在台灣落腳的故事。那時候,沒有那麼多彎彎繞繞,沒有那麼多國家力量,只是一個小老百姓,被迫跟來台灣,落地生根,一個大時代促成的悲劇。後來,開放省親時他有回家,帶著老婆一起回去。前妻帶著孩子改嫁了,如同那個年代的眾多故事。沒辦法happy ending,但終究是活著回去看了一眼。後來,不管我到哪裡去,回家時總是叫媽媽帶我們去吃老王牛肉麵。一路吃著,老王中風、生病、過世,兒子學藝不精,開了幾年就沒開了。
出差的牛肉麵,只是一種高級的象徵,說不上好吃還是不好吃。跟我一起出差的,是一個長得很像《麻辣鮮師》中萬人美老師的阿姨。她對我也很好,常常任我點。最後一次出差,她告訴我,好好讀書,才是孝順媽媽的最好方式。
平日晚上加班的是媽媽,假日加班的是我,完美的錯開,確實的加班費入袋。我用那些錢,買了一支Nokia 3310。剩下的錢一半給媽媽,一半我自己花。
有自己的錢可以用,才有活著的真實感。
工廠的打工過後,媽媽問我:「想在工廠工作,還是去讀書?」
我說:「讀書比較輕鬆,我以後要坐辦公室吹冷氣,讓大家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