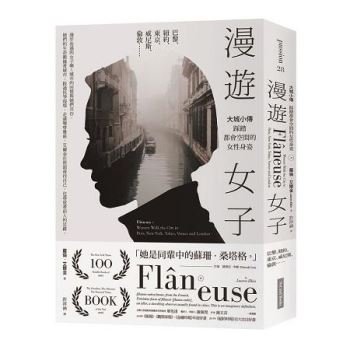〈巴黎‧在咖啡館,他們〉
〔……〕
八十年後的巴黎像個未受承認的文明中心。我對自己的好運難以置信,我走入的這座城市,在河岸書攤就能買到便宜的二手書,或一份內容充實(新聞,而不是娛樂消息)的報紙,然後找間咖啡店坐下來讀好幾小時。任何一間書店(那裡有上百間,到處都是)入門陳列的架上,多的是德希達、傅柯、德勒茲一流的書。巴黎是個知性的觀念混合體,極度有型,耐人尋味。我喜歡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圓拱咖啡館,因為它有裝飾風的廊柱和馬賽克。如果你坐在吧檯邊點杯基爾酒,酒上來時還會附贈一碟乾果。菁英咖啡館我也很喜歡,它兼顧了現代和傳統,門下那些專業無庸置疑、穿燕尾服的侍者則風趣佻達。
在這個觀念混合體中,我品味的不只是知性的觀念,還有屬於個人的,不過那時它們並無二致。我到巴黎後不久,在朋友的派對遇上一個美國人。我們在第二區一間煙汗羼雜的酒吧桌上,跳舞直到凌晨四點。他也是長島來的,也在外念書。他長得就像猶太版的派屈克.丹普西。我不知如何是好,訝異這麼帥的人竟會對我有興趣。一開始,我們聊到我的背景。他問我:「艾爾金是哪裡的名字?」我答:「俄羅斯。」「所以你有猶太血統嘍?」「一半,」我說。但對保守派猶太教徒而言,沒有一半的猶太人,你要嘛是猶太人,要嘛不是猶太人。我不夠「猶太」所以當不成他的女朋友,成了他的女性友人,希望他有天回心轉意。
我還沒發現名義上的共識有多重要。我以為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怎麼稱呼不要緊。但我們在一起越久,這段關係變得越令人不悅,甚至有點羞辱人。我們同床共枕、一起出遊,但如果我摸他的臉,他會把我推開。他擺明了不會在關係中放入一點愛,也不會鬆手讓裡面的愛流走。他把「非猶太」──或「不夠猶太」──搞得很像階級不平等,好像他是來日要媒妁世家的公子哥兒,而我只是他年少輕狂的印子。後來我讀瑞絲根據她和蘭斯洛的關係寫成的《在黑暗中航行》,關於一個合唱團女孩如何變成一個紳士的情婦。他會帶她外出,在某些場合展示她,某些則不,久而久之對她失去興趣。瑞絲的小說幫我看清我和猶太版派屈克.丹普西是怎麼一回事。我是他的合唱團女孩!但和他分手絕不可能的。他是留學生之間特定朋友圈的班底。每次派對、酒吧聚會、每則對話裡都有他。我不可能避開他。而且反正我不想放棄。我相信他總有一天會回應我──反正這又不真的是瑞絲的小說。從別人口中,我得知自己是他睡的第一個女生。我沾沾自喜這算是點成績。
噢,親愛的,可別沾沾自喜啊!我聽見瑞絲咯咯笑出了聲。
*
在瑞絲和藍格勒之間,命運有時是眷顧的,有時是殘酷的。她懷的孩子在出生幾週後,染肺病死了。他們倆在巴黎也無法久留。不出幾個月,藍格勒被派往維也納,接著往布達佩斯,然後是布魯塞爾。瑞絲在布魯塞爾生下了第二胎。藍格勒似乎總有門路讓他們在這些城市的生活小康無虞,唯一的代價是,他們得時時躲債,然後再度躲回巴黎。當藍格勒嘗試從巴黎到阿姆斯特丹尋求庇護時,因為偷竊罪嫌被逮捕了。瑞絲囊空如洗又無人照應,只好把女兒送去布魯塞爾的一間診所託人照養,一九二四年同一個名叫姵羅.亞當的記者朋友遷去該城。
珍,做得好!在二○年代的巴黎,一切都得靠人脈。把自己交給朋友照顧牽起了她成為作家的那條線。她得說故事,請姵羅.亞當替藍格勒找新聞工作的事。亞當不在乎藍格勒的作品,她反而問瑞絲本身有沒有寫作。瑞絲便把一些日記拿給她看。亞當留下了好印象,將之編纂成三節故事,題為《蘇西說》,每節以不同男子的名字為題。她把稿子寄給了《大西洋兩岸評論》當時的編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他決定指導瑞絲,當她第一本書《左岸故事集》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時,他替她寫了序。瑞絲置身巴黎外國人的社交圈外。雖然她筆下的波希米亞生活發生在第五、第六區,在河畔的聖米歇爾和聖日耳曼兩條大道一帶,她自己則住在貧困的十三區──巴黎南方窮陋之氣至今猶存的區域。在一封一九六四年寫給黛安娜.阿提爾的信中,瑞絲說大家──亨利.米勒、海明威之輩──筆下的「巴黎」,根本不是巴黎,分明是美國在巴黎,或英國在巴黎。真正的巴黎和那掛人沒干係──那些觀光客一來,真正的蒙帕納斯人 便收拾包袱,走了。透過福特,她認識了海明威、葛楚.史坦和愛麗絲.托克拉斯 。傳說中的「波西米亞女王」妮娜.漢奈特管她叫「福特的女孩」。但她自外於他們的圈子。
福特是個大塊頭──海明威說他根本像海象──權勢也不小。貴為《大西洋兩岸評論》和《英國評論》的編輯,他出過D.H .勞倫斯、溫德罕.路易斯的作品,自己寫過《優良士兵》(一九一五年出版)。他的意見在文壇名聲響亮,而且舉足輕重。不過,他的私生活倒是有些令常人難以苟同之處。他塊頭雖然大,但很有異性緣。他不落俗的感情生活引發了醜聞,在一九二○年代初迫使他與他的情人,澳洲畫家史黛拉.鮑溫離開倫敦,住到國外去。喬伊斯曾這麼說他:
「噢天父,噢福特,你真不是蓋的。
為了擁有你,少女、賢妻和寡婦通通求之不得。」
福特不是瑞絲一再尋覓的那種踏實可靠的類型。他建議她把原本的名字艾拉.藍格勒改成珍.瑞絲,可說是創造了她。福特不只幫她成為了一名作家,同時讓她將自己視為作家。出於工作原則,她會關在房裡數小時寫稿,而他教會了她如何做文字的取捨。當一篇故事寫得太濫情,他教會她辨別過分在哪裡,他還給她寫作練習:如果一句話不對勁,他建議她把句子翻譯成法文,如果還是行不通,刪掉它。福特年輕時曾和年紀較長的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同住,全天候合作,同寫了三本小說。瑞絲一來和福特、史黛拉.鮑溫住,就輪到他來當她的駐點導師了。但瑞絲可不是蓄著鬍子的中年波蘭水手。對精力旺盛如福特的男人而言,客居家裡的漂亮小姐令他難以招架。他們之間的關係無可避免地超出了教與學。當然,這沒有好下場。瑞絲後來察覺他對她造成的衝擊難以掌控。在給法蘭西斯.溫德罕的信中,她說:「我認為他沒有影響我的寫作,但他影響我太深了,結果是一樣的。﹝……﹞我恐怕無法前後一致地述說這一切,也不會嘗試。」這段感情的文學潛力簡直無可限量,後來他們都各自寫下了小說版本的糾纏:瑞絲寫了《四重奏》(一九二八年的初版,題為《態勢》);福特寫了《當那個壞男人》(一九三二年出版);鮑溫完成了自傳《汲自人生》(一九四一年出版──瑞絲在裡頭被稱為「實在悲劇的女子,寫了本出版不了的壞胚子小說。」);藍格勒也寫了部小說,題為《禁錮下》(一九三二年出版)。雖然小說荒誕不經,瑞絲親自將《禁錮下》翻成了英文,好好編修了一番,苦苦讓出版定案,作者化名為愛德華.德.涅夫。有人覺得她根本重寫了那本小說,讀起來倒很像是她自己的作品。
*
一九九九年在巴黎,我沒得向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學習,但我有海明威。自信滿滿的海明威,他生命的每個時期都是個彈孔。評論家雅各.麥可.里蘭曾說:「海明威的主人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去了某些男子氣概,他便用各種傢伙補回來──在上密西根州是一根釣竿或一把小刀,在非洲則是一桿獵槍。」那個把風情萬種的哈德麗.理察森娶走了的男人,為了寶琳.波飛芙拋棄了她,接著又為了瑪莎.葛虹離開寶琳。葛虹身為作家兼記者,是第一個和他並駕齊驅的女人。當她讓他感到相形遜色時,他會試圖鬥智,設法在報導上搶先她。(他們的婚姻崩解後,如果誰提起她和海老爹的婚姻,葛虹會拂袖而去。)我向這不太有師範的老師學習,直到我發現了珍.瑞絲。若只說我覺得《流動的饗宴》很有啟發性,恐怕還不足道盡它的好──雖然今天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這本書會很丟臉(我在教《太陽依舊升起》時,拒絕在地鐵中從包包亮出這本書)。但一九九九年的我傻傻還不懂事,會在住處附近的咖啡館坐下來樂樂地讀,偶爾停下來寫些東西。從第一章開始,年輕的海明威把我即將愛上的城市呈現在眼前──哪樣的咖啡館適合工作,寫故事時好好來杯咖啡牛奶、聖詹姆士蘭姆酒、一打生蠔和半瓶白酒,同時打量咖啡館裡所有的人──我就知道這本書和我之前讀過的都不一樣。青春期多數的日子裡,我讀著所有能到手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柯馬克公共圖書館史密斯鎮分館的所有藏書。從麥德琳.蘭歌和童妮.摩里森到雪維亞.普拉絲,以及背景設在攝政王時期的浪漫小說(活潑的約瑟芬到底會嫁給士兵還是花心浪子?)。連我大學時看的書,像是珍奈.溫特森的《熱情》、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通通是小說,和我自己的經驗天差地遠。但《流動的饗宴》給我的是一個在巴黎左岸的年輕美國人,上咖啡館、學著當作家。那時的海明威沒比我大多少,雖然他經歷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了婚,更不用提他還是條雄糾糾的漢子。而我則是個郊區來的大學生,年輕天真,見識過的戰爭是由美國媒體機器先消化過的電視報導和照片。就算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經歷,我感覺我們有著一樣的直覺。咖啡館裡快樂的交會,佐著一切的刺激事,工作以及在城裡路上萍水相逢的人,給了我理想的寫作環境。
我在拉法葉百貨公司的文具店找到了兩本線圈筆記本。它們不大,跟平裝書差不多,用的是沒壓線的好紙,厚度適中,一本封面是薄荷綠,另一本是香草色。我便在巴黎一路帶著筆記本,有空便在上頭塗塗寫寫。現在我走到哪兒,身上仍會帶本筆記本。這是我從海明威學來的。但海明威慣於以駕馭之姿對待巴黎和巴黎人,這點使我不悅。在咖啡館監視著門邊一個漂亮的年輕小姐,他說他找到了把她「放入」一個密西根故事的靈感。但他又寫道:「她選了個可以看見街上和門口的位置,我知道她在等人。」這幾乎是個不合邏輯的推論,海明威彷彿將要解釋為什麼他無法將她寫進去,所以將就著說她在等人,好像她屬於別人和別的地方,因此無法被「放入」海明威想把她挪進的地方。他悠然跳過了她男友,寫下了出名的「我見過你了,美人。現在你是我的了,管你在等誰,或我之後不會再見到你了。你屬於我,全巴黎也屬於我,而我屬於這本筆記本和這枝鉛筆。」我在咖啡館環顧四周,沒見到什麼帥哥美女,如果我有見到,我也很難覺得他們屬於我。海明威把觀看和權力相提並論,很難不冒犯到今天的我──女人、巴黎,凡是他細細打量的東西都「屬於」他和他的鉛筆。我感覺到的正好相反,並非占有,而是歸屬。
*
瑞絲之所以變成作家,也是場意外,一場買了筆記本之後發生的意外。她和蘭斯洛分手後在倫敦便無所用心,接著搬進了間落魄寂寥的套房,社區的名字恰好叫世界的盡頭。「我得買些花或盆栽什麼的,」她回憶道,所以她出門去尋找。
「我經過了一間文具店,櫥窗裡陳列著許許多多羽毛筆,紅的、藍的、綠的、黃的。如果把一些筆放在玻璃瓶裡,應該會挺好的,這樣便能點綴我的桌子了。我進去買了一打左右的筆。櫃檯上有些黑色練習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筆記本和現在市面上的練習簿不一樣。大概是兩倍的厚度,封皮硬厚烏亮,線圈與邊線是紅的,內頁有線。我也買了些,不知為何買的,就因為喜歡它們的樣子吧!我還帶了一盒樣式我喜歡的筆頭、陽春的筆筒、墨水,和一個便宜的墨水瓶架。我想,現在那張舊桌子就不會那麼空虛了。」
邁向寫作的這一大步來自漫遊,來自妝點一張醜桌的需求,為了打造一間自己的房間。那些筆記本有著瑞絲之後會拿給姵羅.亞當看的稿子。
瑞絲以一種吳爾芙稱為「觀點上的不同」看世界。這個特質蘊含在她的女性角色中:她們無法穿搭或應對合宜,也無法提出正確答案,她們話中的資訊一下過多,一下太少,一下又答非所問。在巴黎,我們終於可以做自己;但就算在巴黎,別人的眼光總是免不了的。用瑞絲故事裡的話說,我們當中有些人「活在機器之外」;這篇同名故事中,一個為憂鬱所苦的英國女子在一間法國診所中,等待著一場名目不明的手術。她把護士與其他病患看作是「機械的零件」,具有她所缺乏的「力量,一種肯定感」,同時她認定他們有天會發現她缺乏那些東西。那機器永遠都是對的,而且會淘汰故障的零件:「『這個,沒用』,他們會這樣講。」瑞絲一九六九年發表一篇名為〈我監視著陌生人〉的故事,故事中蘿拉在戰時的英國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機器開始與她合而為一的過程中,甚至意圖殺掉她:「每件事和每個人都有機械的一面,很嚇人的。每每我買地鐵票、上公車、逛商店,我覺得我就像機器中的一個齒輪,和其他元件互動,而不是一個和其他人有交集的人。被拽進一座想殺我的機器的感覺,成為了一種偏執。」
瑞絲筆下的女人遇上的男人都是「在機器裡」好端端的一群人,因為作為金錢和保護的提供者,他們必須在機器裡。《離開麥肯錫先生之後》的同名主角體現了英式的道德常規。麥肯錫先生被形容為一個曾經擁有浪漫懷抱的人。瑞絲寫道,「年輕的時候,他出版過一本小小的詩集」,但他隨後發覺「那些任憑情感與衝動之風吹拂的人,都不快樂。」於是他「樹立了一種態度,一種他鮮少背離的道德規範和舉止。」這就是他想要讓茱莉亞遵循的規範。《四重奏》裡像福特的角色──海德勒,他平靜地說:「我親愛的孩子啊,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為了大家好,你得改改。」她得學會打理儀容。就在海德勒持續批評時,瑪莉亞心中想:「他的樣子活脫脫就是維多利亞女王。」
作家瑞絲比平常時的她風趣多了。規範,機器,遊戲一場。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瑞絲的女主角玩不了這場遊戲,她駁斥那些非人和任意設下的規矩──那些衝著她來的規矩。她為什麼融不進來呢?她身旁的人忖著。很顯然她並沒有付出努力。「當乖乖牌,或離開,」《在黑暗中航行》的安娜這麼想著。我也有同感,當社會壓迫使瑞絲筆下的女人無從脫身,並一而再再而三從那沒剩幾條的出路選了最糟的,我還能逃向巴黎,逃避我試圖融入但終究失敗的地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挑了這個長島男孩,在國內他決計不會是屬於我的類型。和他約會,不管我會遭受多少羞辱,可以證明(但向誰呢?)其實如果我願意,大可融入。但我多少心知肚明:我只是在自欺欺人。
*
我和瑞絲一同走在蒙帕納斯街頭。我在大道上來回,來往於學校和家裡。我在附近的餐廳吃飯,坐在圓拱咖啡館裡,在那裡五法郎能換到一大盅咖啡、同樣大盅的熱牛奶,能待上好幾小時。有時候我會去菁英咖啡館,和裡頭的大懶貓玩。在少數情況下,我會換去圓亭咖啡館,只是換換。瑞絲筆下的女人光顧咖啡館,點的會是餐前酒,一杯接一杯,直到某個好心男子請她們吃晚餐。我不知道怎麼找到會付我晚餐錢的男子,這招在巴納德學院是學不到的。取而代之,我花好幾小時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在一頁頁紙上煩惱我的人生到底怎麼了。我懷疑所有為他百轉的愁腸,分析他說的隻字片語,只是為了逃避現實──我們不會有結果,他是個混帳。但我決定了,我愛他,我要愛到底。
〔……〕
八十年後的巴黎像個未受承認的文明中心。我對自己的好運難以置信,我走入的這座城市,在河岸書攤就能買到便宜的二手書,或一份內容充實(新聞,而不是娛樂消息)的報紙,然後找間咖啡店坐下來讀好幾小時。任何一間書店(那裡有上百間,到處都是)入門陳列的架上,多的是德希達、傅柯、德勒茲一流的書。巴黎是個知性的觀念混合體,極度有型,耐人尋味。我喜歡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圓拱咖啡館,因為它有裝飾風的廊柱和馬賽克。如果你坐在吧檯邊點杯基爾酒,酒上來時還會附贈一碟乾果。菁英咖啡館我也很喜歡,它兼顧了現代和傳統,門下那些專業無庸置疑、穿燕尾服的侍者則風趣佻達。
在這個觀念混合體中,我品味的不只是知性的觀念,還有屬於個人的,不過那時它們並無二致。我到巴黎後不久,在朋友的派對遇上一個美國人。我們在第二區一間煙汗羼雜的酒吧桌上,跳舞直到凌晨四點。他也是長島來的,也在外念書。他長得就像猶太版的派屈克.丹普西。我不知如何是好,訝異這麼帥的人竟會對我有興趣。一開始,我們聊到我的背景。他問我:「艾爾金是哪裡的名字?」我答:「俄羅斯。」「所以你有猶太血統嘍?」「一半,」我說。但對保守派猶太教徒而言,沒有一半的猶太人,你要嘛是猶太人,要嘛不是猶太人。我不夠「猶太」所以當不成他的女朋友,成了他的女性友人,希望他有天回心轉意。
我還沒發現名義上的共識有多重要。我以為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怎麼稱呼不要緊。但我們在一起越久,這段關係變得越令人不悅,甚至有點羞辱人。我們同床共枕、一起出遊,但如果我摸他的臉,他會把我推開。他擺明了不會在關係中放入一點愛,也不會鬆手讓裡面的愛流走。他把「非猶太」──或「不夠猶太」──搞得很像階級不平等,好像他是來日要媒妁世家的公子哥兒,而我只是他年少輕狂的印子。後來我讀瑞絲根據她和蘭斯洛的關係寫成的《在黑暗中航行》,關於一個合唱團女孩如何變成一個紳士的情婦。他會帶她外出,在某些場合展示她,某些則不,久而久之對她失去興趣。瑞絲的小說幫我看清我和猶太版派屈克.丹普西是怎麼一回事。我是他的合唱團女孩!但和他分手絕不可能的。他是留學生之間特定朋友圈的班底。每次派對、酒吧聚會、每則對話裡都有他。我不可能避開他。而且反正我不想放棄。我相信他總有一天會回應我──反正這又不真的是瑞絲的小說。從別人口中,我得知自己是他睡的第一個女生。我沾沾自喜這算是點成績。
噢,親愛的,可別沾沾自喜啊!我聽見瑞絲咯咯笑出了聲。
*
在瑞絲和藍格勒之間,命運有時是眷顧的,有時是殘酷的。她懷的孩子在出生幾週後,染肺病死了。他們倆在巴黎也無法久留。不出幾個月,藍格勒被派往維也納,接著往布達佩斯,然後是布魯塞爾。瑞絲在布魯塞爾生下了第二胎。藍格勒似乎總有門路讓他們在這些城市的生活小康無虞,唯一的代價是,他們得時時躲債,然後再度躲回巴黎。當藍格勒嘗試從巴黎到阿姆斯特丹尋求庇護時,因為偷竊罪嫌被逮捕了。瑞絲囊空如洗又無人照應,只好把女兒送去布魯塞爾的一間診所託人照養,一九二四年同一個名叫姵羅.亞當的記者朋友遷去該城。
珍,做得好!在二○年代的巴黎,一切都得靠人脈。把自己交給朋友照顧牽起了她成為作家的那條線。她得說故事,請姵羅.亞當替藍格勒找新聞工作的事。亞當不在乎藍格勒的作品,她反而問瑞絲本身有沒有寫作。瑞絲便把一些日記拿給她看。亞當留下了好印象,將之編纂成三節故事,題為《蘇西說》,每節以不同男子的名字為題。她把稿子寄給了《大西洋兩岸評論》當時的編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他決定指導瑞絲,當她第一本書《左岸故事集》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時,他替她寫了序。瑞絲置身巴黎外國人的社交圈外。雖然她筆下的波希米亞生活發生在第五、第六區,在河畔的聖米歇爾和聖日耳曼兩條大道一帶,她自己則住在貧困的十三區──巴黎南方窮陋之氣至今猶存的區域。在一封一九六四年寫給黛安娜.阿提爾的信中,瑞絲說大家──亨利.米勒、海明威之輩──筆下的「巴黎」,根本不是巴黎,分明是美國在巴黎,或英國在巴黎。真正的巴黎和那掛人沒干係──那些觀光客一來,真正的蒙帕納斯人 便收拾包袱,走了。透過福特,她認識了海明威、葛楚.史坦和愛麗絲.托克拉斯 。傳說中的「波西米亞女王」妮娜.漢奈特管她叫「福特的女孩」。但她自外於他們的圈子。
福特是個大塊頭──海明威說他根本像海象──權勢也不小。貴為《大西洋兩岸評論》和《英國評論》的編輯,他出過D.H .勞倫斯、溫德罕.路易斯的作品,自己寫過《優良士兵》(一九一五年出版)。他的意見在文壇名聲響亮,而且舉足輕重。不過,他的私生活倒是有些令常人難以苟同之處。他塊頭雖然大,但很有異性緣。他不落俗的感情生活引發了醜聞,在一九二○年代初迫使他與他的情人,澳洲畫家史黛拉.鮑溫離開倫敦,住到國外去。喬伊斯曾這麼說他:
「噢天父,噢福特,你真不是蓋的。
為了擁有你,少女、賢妻和寡婦通通求之不得。」
福特不是瑞絲一再尋覓的那種踏實可靠的類型。他建議她把原本的名字艾拉.藍格勒改成珍.瑞絲,可說是創造了她。福特不只幫她成為了一名作家,同時讓她將自己視為作家。出於工作原則,她會關在房裡數小時寫稿,而他教會了她如何做文字的取捨。當一篇故事寫得太濫情,他教會她辨別過分在哪裡,他還給她寫作練習:如果一句話不對勁,他建議她把句子翻譯成法文,如果還是行不通,刪掉它。福特年輕時曾和年紀較長的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同住,全天候合作,同寫了三本小說。瑞絲一來和福特、史黛拉.鮑溫住,就輪到他來當她的駐點導師了。但瑞絲可不是蓄著鬍子的中年波蘭水手。對精力旺盛如福特的男人而言,客居家裡的漂亮小姐令他難以招架。他們之間的關係無可避免地超出了教與學。當然,這沒有好下場。瑞絲後來察覺他對她造成的衝擊難以掌控。在給法蘭西斯.溫德罕的信中,她說:「我認為他沒有影響我的寫作,但他影響我太深了,結果是一樣的。﹝……﹞我恐怕無法前後一致地述說這一切,也不會嘗試。」這段感情的文學潛力簡直無可限量,後來他們都各自寫下了小說版本的糾纏:瑞絲寫了《四重奏》(一九二八年的初版,題為《態勢》);福特寫了《當那個壞男人》(一九三二年出版);鮑溫完成了自傳《汲自人生》(一九四一年出版──瑞絲在裡頭被稱為「實在悲劇的女子,寫了本出版不了的壞胚子小說。」);藍格勒也寫了部小說,題為《禁錮下》(一九三二年出版)。雖然小說荒誕不經,瑞絲親自將《禁錮下》翻成了英文,好好編修了一番,苦苦讓出版定案,作者化名為愛德華.德.涅夫。有人覺得她根本重寫了那本小說,讀起來倒很像是她自己的作品。
*
一九九九年在巴黎,我沒得向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學習,但我有海明威。自信滿滿的海明威,他生命的每個時期都是個彈孔。評論家雅各.麥可.里蘭曾說:「海明威的主人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去了某些男子氣概,他便用各種傢伙補回來──在上密西根州是一根釣竿或一把小刀,在非洲則是一桿獵槍。」那個把風情萬種的哈德麗.理察森娶走了的男人,為了寶琳.波飛芙拋棄了她,接著又為了瑪莎.葛虹離開寶琳。葛虹身為作家兼記者,是第一個和他並駕齊驅的女人。當她讓他感到相形遜色時,他會試圖鬥智,設法在報導上搶先她。(他們的婚姻崩解後,如果誰提起她和海老爹的婚姻,葛虹會拂袖而去。)我向這不太有師範的老師學習,直到我發現了珍.瑞絲。若只說我覺得《流動的饗宴》很有啟發性,恐怕還不足道盡它的好──雖然今天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這本書會很丟臉(我在教《太陽依舊升起》時,拒絕在地鐵中從包包亮出這本書)。但一九九九年的我傻傻還不懂事,會在住處附近的咖啡館坐下來樂樂地讀,偶爾停下來寫些東西。從第一章開始,年輕的海明威把我即將愛上的城市呈現在眼前──哪樣的咖啡館適合工作,寫故事時好好來杯咖啡牛奶、聖詹姆士蘭姆酒、一打生蠔和半瓶白酒,同時打量咖啡館裡所有的人──我就知道這本書和我之前讀過的都不一樣。青春期多數的日子裡,我讀著所有能到手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柯馬克公共圖書館史密斯鎮分館的所有藏書。從麥德琳.蘭歌和童妮.摩里森到雪維亞.普拉絲,以及背景設在攝政王時期的浪漫小說(活潑的約瑟芬到底會嫁給士兵還是花心浪子?)。連我大學時看的書,像是珍奈.溫特森的《熱情》、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通通是小說,和我自己的經驗天差地遠。但《流動的饗宴》給我的是一個在巴黎左岸的年輕美國人,上咖啡館、學著當作家。那時的海明威沒比我大多少,雖然他經歷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了婚,更不用提他還是條雄糾糾的漢子。而我則是個郊區來的大學生,年輕天真,見識過的戰爭是由美國媒體機器先消化過的電視報導和照片。就算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經歷,我感覺我們有著一樣的直覺。咖啡館裡快樂的交會,佐著一切的刺激事,工作以及在城裡路上萍水相逢的人,給了我理想的寫作環境。
我在拉法葉百貨公司的文具店找到了兩本線圈筆記本。它們不大,跟平裝書差不多,用的是沒壓線的好紙,厚度適中,一本封面是薄荷綠,另一本是香草色。我便在巴黎一路帶著筆記本,有空便在上頭塗塗寫寫。現在我走到哪兒,身上仍會帶本筆記本。這是我從海明威學來的。但海明威慣於以駕馭之姿對待巴黎和巴黎人,這點使我不悅。在咖啡館監視著門邊一個漂亮的年輕小姐,他說他找到了把她「放入」一個密西根故事的靈感。但他又寫道:「她選了個可以看見街上和門口的位置,我知道她在等人。」這幾乎是個不合邏輯的推論,海明威彷彿將要解釋為什麼他無法將她寫進去,所以將就著說她在等人,好像她屬於別人和別的地方,因此無法被「放入」海明威想把她挪進的地方。他悠然跳過了她男友,寫下了出名的「我見過你了,美人。現在你是我的了,管你在等誰,或我之後不會再見到你了。你屬於我,全巴黎也屬於我,而我屬於這本筆記本和這枝鉛筆。」我在咖啡館環顧四周,沒見到什麼帥哥美女,如果我有見到,我也很難覺得他們屬於我。海明威把觀看和權力相提並論,很難不冒犯到今天的我──女人、巴黎,凡是他細細打量的東西都「屬於」他和他的鉛筆。我感覺到的正好相反,並非占有,而是歸屬。
*
瑞絲之所以變成作家,也是場意外,一場買了筆記本之後發生的意外。她和蘭斯洛分手後在倫敦便無所用心,接著搬進了間落魄寂寥的套房,社區的名字恰好叫世界的盡頭。「我得買些花或盆栽什麼的,」她回憶道,所以她出門去尋找。
「我經過了一間文具店,櫥窗裡陳列著許許多多羽毛筆,紅的、藍的、綠的、黃的。如果把一些筆放在玻璃瓶裡,應該會挺好的,這樣便能點綴我的桌子了。我進去買了一打左右的筆。櫃檯上有些黑色練習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筆記本和現在市面上的練習簿不一樣。大概是兩倍的厚度,封皮硬厚烏亮,線圈與邊線是紅的,內頁有線。我也買了些,不知為何買的,就因為喜歡它們的樣子吧!我還帶了一盒樣式我喜歡的筆頭、陽春的筆筒、墨水,和一個便宜的墨水瓶架。我想,現在那張舊桌子就不會那麼空虛了。」
邁向寫作的這一大步來自漫遊,來自妝點一張醜桌的需求,為了打造一間自己的房間。那些筆記本有著瑞絲之後會拿給姵羅.亞當看的稿子。
瑞絲以一種吳爾芙稱為「觀點上的不同」看世界。這個特質蘊含在她的女性角色中:她們無法穿搭或應對合宜,也無法提出正確答案,她們話中的資訊一下過多,一下太少,一下又答非所問。在巴黎,我們終於可以做自己;但就算在巴黎,別人的眼光總是免不了的。用瑞絲故事裡的話說,我們當中有些人「活在機器之外」;這篇同名故事中,一個為憂鬱所苦的英國女子在一間法國診所中,等待著一場名目不明的手術。她把護士與其他病患看作是「機械的零件」,具有她所缺乏的「力量,一種肯定感」,同時她認定他們有天會發現她缺乏那些東西。那機器永遠都是對的,而且會淘汰故障的零件:「『這個,沒用』,他們會這樣講。」瑞絲一九六九年發表一篇名為〈我監視著陌生人〉的故事,故事中蘿拉在戰時的英國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機器開始與她合而為一的過程中,甚至意圖殺掉她:「每件事和每個人都有機械的一面,很嚇人的。每每我買地鐵票、上公車、逛商店,我覺得我就像機器中的一個齒輪,和其他元件互動,而不是一個和其他人有交集的人。被拽進一座想殺我的機器的感覺,成為了一種偏執。」
瑞絲筆下的女人遇上的男人都是「在機器裡」好端端的一群人,因為作為金錢和保護的提供者,他們必須在機器裡。《離開麥肯錫先生之後》的同名主角體現了英式的道德常規。麥肯錫先生被形容為一個曾經擁有浪漫懷抱的人。瑞絲寫道,「年輕的時候,他出版過一本小小的詩集」,但他隨後發覺「那些任憑情感與衝動之風吹拂的人,都不快樂。」於是他「樹立了一種態度,一種他鮮少背離的道德規範和舉止。」這就是他想要讓茱莉亞遵循的規範。《四重奏》裡像福特的角色──海德勒,他平靜地說:「我親愛的孩子啊,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為了大家好,你得改改。」她得學會打理儀容。就在海德勒持續批評時,瑪莉亞心中想:「他的樣子活脫脫就是維多利亞女王。」
作家瑞絲比平常時的她風趣多了。規範,機器,遊戲一場。你的觀點和人生觀徹頭徹尾地行不通。瑞絲的女主角玩不了這場遊戲,她駁斥那些非人和任意設下的規矩──那些衝著她來的規矩。她為什麼融不進來呢?她身旁的人忖著。很顯然她並沒有付出努力。「當乖乖牌,或離開,」《在黑暗中航行》的安娜這麼想著。我也有同感,當社會壓迫使瑞絲筆下的女人無從脫身,並一而再再而三從那沒剩幾條的出路選了最糟的,我還能逃向巴黎,逃避我試圖融入但終究失敗的地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挑了這個長島男孩,在國內他決計不會是屬於我的類型。和他約會,不管我會遭受多少羞辱,可以證明(但向誰呢?)其實如果我願意,大可融入。但我多少心知肚明:我只是在自欺欺人。
*
我和瑞絲一同走在蒙帕納斯街頭。我在大道上來回,來往於學校和家裡。我在附近的餐廳吃飯,坐在圓拱咖啡館裡,在那裡五法郎能換到一大盅咖啡、同樣大盅的熱牛奶,能待上好幾小時。有時候我會去菁英咖啡館,和裡頭的大懶貓玩。在少數情況下,我會換去圓亭咖啡館,只是換換。瑞絲筆下的女人光顧咖啡館,點的會是餐前酒,一杯接一杯,直到某個好心男子請她們吃晚餐。我不知道怎麼找到會付我晚餐錢的男子,這招在巴納德學院是學不到的。取而代之,我花好幾小時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在一頁頁紙上煩惱我的人生到底怎麼了。我懷疑所有為他百轉的愁腸,分析他說的隻字片語,只是為了逃避現實──我們不會有結果,他是個混帳。但我決定了,我愛他,我要愛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