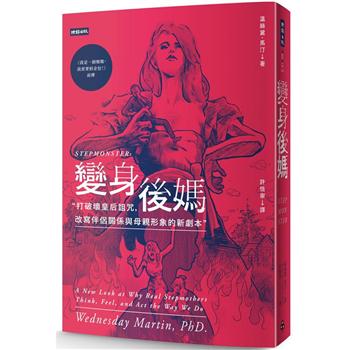「你又不是我孩子!」: 憤怒、嫉妒、憎恨
壞心繼母的故事,令我們反感、憤怒、豎起耳朵聽。趕走並迫害丈夫孩子的繼母,同時令我們不安又放心:那個女人怎麼會這麼邪惡,果然如同我們想的一樣。我研究所的朋友用不屑的口氣講著,「我爸的老婆……」——我朋友通常那樣叫對方。
我覺得好刺激,聽起來既成熟又疏遠、叛逆,就好像在說:她不是我媽媽,甚至不是我繼母; 她對我來說什麼都不是——「……她有夠討厭的,就跟人們講得一樣,有夠壞。」朋友繼續講她大學的時候,她父親和這位妻子,這個第二任老婆,搬到鎮上的另一頭,結果沒給女兒新家鑰匙。我感到不可思議,怎麼會如此把繼女「拒於門外」。那可是她爸爸的房子,不也就等於我朋友的房子?我朋友難道不該有這個權利自由進出?怎麼會有繼母如此厚顏無恥,還真的就跟傳說中的邪惡繼母一樣——吃醋、冷血、小心眼,不肯讓繼女上門?她連鑰匙都不肯給你?你爸也就真的聽她的?多年前,我朋友和她們的繼母故事讓我感興趣的地方,在於這些事件令我難以理解。我有好多問題想問:你的繼母怎麼那麼壞?她怎麼會那樣啊?
二十年後,我的感受不同了。現在我明白朋友的繼母做的事,不是為了把別人鎖在外面,而是想把自己關在安全的地方。外人眼中最疏離的繼母,通常正處於最脆弱疲憊的時刻。經歷了多年沒人感謝、甚至是被攻擊的日子後,她們是在採取行動保護自己。我發現,令人感到把每個人拒於門外、憤怒、嫉妒、怨恨,或單純就是冷酷繼母的想法,實情可能正好與此相反。
多年聽見繼子女明示暗示冷嘲熱諷「你不是我媽」後,我們可能會採取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的模式,你又不是我孩子,並做出符合這種態度的行為。我們的動機,比單純的以牙還牙還複雜得多。 從某方面來講,所有不快樂的繼母都是一樣的。我們的性別似乎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女性想與人連結,想當「工匠」,修補好功能失調的繼親家庭荒廢的房子,我們想「修補關係」,把「前孩子」帶回家照顧。我們想當好人,感化不聽話的叛逆繼子女,讓他們浪子回頭,雙方成為一輩子最要好的朋友。對女性來說,我們不只很想這麼做,這種要對抗現實的事,甚至令我們感到不做不行。到底為什麼要接下這種難如登天、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即使理智勸我們不要?因為我們就是一定得做。專家告訴我們,女性的自我價值,以及她最根本的身分認同,與她的人際關係成不成功密切相關,甚至分割不了。社會學家與家庭專家維吉尼亞.施瓦茲博士(Virginia Rutter)的結論是,「大量的研究顯示,女性的自尊與人際關係是否融洽息息相關,繼親家庭也是一樣的情況。」簡單來說,我們女性需要喜歡別人,也需要被別人喜歡,缺一不可,否則我們會感到自己沒做好,是一個失敗者。
我們認為需要解決繼親家庭碰上的問題,把問題當成自己的責任。這種看法根深蒂固(數十年來,父母與社會都是那樣告訴我們),幾乎不可能抗拒。伊麗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是美國威徹斯特郡家庭治療學會(Family Institute of Westchester)的創辦人與榮譽主任,以及《無形的網:家庭關係中的性別模式》(The Invisible Web: Gender Pattern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的共同作者。她指出,「女性被教養成認為必須替每一個人負責。繼母要是看見孩子不開心,或是丈夫無能……她就會過去幫忙。女性會想辦法解決問題——不論那究竟該不該由她們想辦法。」我們知道繼親家庭有大量問題,有著人際關係的障礙與煩心事;我們有大量的理由懷疑自己、責怪自己,覺得自己沒做好。事實上,貝勒大學的貝雷博士發現,在再婚家庭裡,繼母是所有家庭成員中最會批評與責怪自己的人。
在這一點上,我們和男性有著天壤之別。研究顯示4,繼父參與繼子女事務的程度低非常多——內心也沒那麼多的衝突、壓力、罪惡感。此外,我們的先生不論本身是不是繼父,對我們認為必須把每個人團結在一起的想法,以及我們心底深處深深的挫敗感,皆感到相當困惑不解。女性與男性看待繼親家庭問題的性別差異,有可能讓夫妻之間無法同心,增加妻子的疏離感與挫敗感。我們全都能明白繼母布蘭達的感受。布蘭達有兩個小小孩,還有一個青春期繼子,她告訴我,「有時我會恨自己不能做得更好,無法讓我們成為一個家,永遠在和先生吵他兒子的事。」
女性有時會對無法建立連結、無法解決問題,感到耿耿於懷。或許那解釋了為什麼在我的訪談過程中,好幾位有繼子女的女性,告訴我相同的故事,或是某種版本類似的故事,以相似到出奇的方式,談彼此共同的憂慮。我們努力溝通,但無法溝通,誤會與誤解產生,我們一再感受到挫敗與怨念——必須面對男方的孩子時,他們有時會引發我們心中醜陋的情緒,那些我們覺得自己不該有的禁忌情緒。那種感覺就像某位繼母告訴我的話,「救命啊!我困在電影裡!」
某位女性的繼子女每週(或是一個月幾次)打電話回家,每次都在電話答錄機上留下相同的留言,「嗨,爸爸,是我。希望你一切平安。我想你。打電話給我。掰掰,爸爸。」數十通留言,從來不曾有一通向爸爸的妻子打招呼。答錄機上的錄音是繼母的聲音,平日也是她在聽留言(好吧,繼子不知道這件事,但還是一樣……)。更糟的情況是,繼母可能得和繼子女同住一段時間,在隔週的週末到火車站接送,還寄給繼子生日卡,或是協助繼女籌備婚禮,不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優先順序,投入多年光陰,努力建立關係,因為現實就是她嫁的人有孩子。 告訴我電話答錄機故事的女性,不認為自己過分敏感,但坦承繼子的留言令她不舒服。繼子一再假裝她不存在,她怎麼可能沒留意到?最糟的是,光是想到這件事、光是有不舒服的情緒(先生的孩子從不在留言中向自己打招呼),她就覺得自己很小心眼。這是典型的邪惡繼母困境——其實不是任何人的錯,但因為她不舒服,所以這件事變成她的問題。她可以想像,要是下次繼子女打電話過來,她告訴他們,「嗨,近來好嗎?太好了,是這樣的,我想講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但你每次打電話過來留言,從來沒跟我說嗨,只和你爸爸打招呼,我有一點……傷心。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她知道自己永遠無法把這些話說出口,要是說了,也只不過是節外生枝。她原本就察覺繼子女在說她的閒話,這下子更是被抓到把柄——繼母是個控制狂、情緒緊繃、管東管西、不懂得放手、她在嫉妒。
女人心想:還是算了,別跟繼子女提那些話,順口提醒先生一下就好。她不想鬧出什麼事,只是暗示一下,希望告知情況後,先生就會懂她的意思,「好奇怪,每次提姆打電話過來,雖然他聽到答錄機上是我的聲音,他都會說,『嗨,爸。』不曾說過,『嗨,琴。』」然而,先生點點頭,看起來心不在焉,或是覺得有點煩,接著就改變話題。繼子繼續留一樣的電話留言。幾個月後,或是一年後,女性再也不試圖暗示先生。當然,她平常不是那麼畏畏縮縮的人——我的訪談對象用急促、防衛心強的語調,講出故事的這個部分。她害怕就算同為繼母,我仍會在心中想,你這個女人怎麼會那樣。她怕我批評她居然有這麼典型的邪惡念頭,即便只是一閃而過的想法。
她心慌意亂,受到傷害。沒錯,只是一些小事,但成為一家人都已經這麼久了,她仍不免感到,繼子女的這類作為是在故意無視她,拒絕承認她這個人的存在(即便只是無意間)。然而,她是大人了,她決定要當個情緒成熟的人,正大光明地面對,不要偷偷懷恨在心。她不要生悶氣,讓傷口化膿,讓小事不必要地鬧大,她要再次提醒先生這件事。她告訴自己:先生一定會理解的,一定會告訴他的孩子,這樣的「不小心漏掉」有點奇怪。聽到電話答錄機上是繼母的聲音時,有禮貌的做法是同時向雙方打招呼,「嗨,爸。嗨,琴。我是提姆。」
然而,先生一下子惱羞成怒,「為什麼又要提這件事?根本從頭到尾就沒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先生替兒子說話,「他已經盡量不出現在你眼前了,你卻還是有辦法挑他的毛病。你太敏感了。為什麼就是不能放過這件事?」
女人跳腳,「我只是說出你兒子做了什麼。為什麼要把矛頭指向我?」她嚇了一跳,失望又茫然。她真的太過分了嗎?她還以為,自己只是在說出心中的感受,請先生幫忙。為什麼她只是說出他的孩子做了什麼,夫妻間就有了裂痕?難道她的感受不重要?是她太蠻橫了?難道說她要求的事不合理嗎?她覺得沒有啊,可是她也不確定。她不懂,憑什麼要她忍氣吞聲。他的孩子的確做了沒禮貌或傷人的事,為什麼要她視若無睹,為什麼要裝沒事?
壞心繼母的故事,令我們反感、憤怒、豎起耳朵聽。趕走並迫害丈夫孩子的繼母,同時令我們不安又放心:那個女人怎麼會這麼邪惡,果然如同我們想的一樣。我研究所的朋友用不屑的口氣講著,「我爸的老婆……」——我朋友通常那樣叫對方。
我覺得好刺激,聽起來既成熟又疏遠、叛逆,就好像在說:她不是我媽媽,甚至不是我繼母; 她對我來說什麼都不是——「……她有夠討厭的,就跟人們講得一樣,有夠壞。」朋友繼續講她大學的時候,她父親和這位妻子,這個第二任老婆,搬到鎮上的另一頭,結果沒給女兒新家鑰匙。我感到不可思議,怎麼會如此把繼女「拒於門外」。那可是她爸爸的房子,不也就等於我朋友的房子?我朋友難道不該有這個權利自由進出?怎麼會有繼母如此厚顏無恥,還真的就跟傳說中的邪惡繼母一樣——吃醋、冷血、小心眼,不肯讓繼女上門?她連鑰匙都不肯給你?你爸也就真的聽她的?多年前,我朋友和她們的繼母故事讓我感興趣的地方,在於這些事件令我難以理解。我有好多問題想問:你的繼母怎麼那麼壞?她怎麼會那樣啊?
二十年後,我的感受不同了。現在我明白朋友的繼母做的事,不是為了把別人鎖在外面,而是想把自己關在安全的地方。外人眼中最疏離的繼母,通常正處於最脆弱疲憊的時刻。經歷了多年沒人感謝、甚至是被攻擊的日子後,她們是在採取行動保護自己。我發現,令人感到把每個人拒於門外、憤怒、嫉妒、怨恨,或單純就是冷酷繼母的想法,實情可能正好與此相反。
多年聽見繼子女明示暗示冷嘲熱諷「你不是我媽」後,我們可能會採取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的模式,你又不是我孩子,並做出符合這種態度的行為。我們的動機,比單純的以牙還牙還複雜得多。 從某方面來講,所有不快樂的繼母都是一樣的。我們的性別似乎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女性想與人連結,想當「工匠」,修補好功能失調的繼親家庭荒廢的房子,我們想「修補關係」,把「前孩子」帶回家照顧。我們想當好人,感化不聽話的叛逆繼子女,讓他們浪子回頭,雙方成為一輩子最要好的朋友。對女性來說,我們不只很想這麼做,這種要對抗現實的事,甚至令我們感到不做不行。到底為什麼要接下這種難如登天、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即使理智勸我們不要?因為我們就是一定得做。專家告訴我們,女性的自我價值,以及她最根本的身分認同,與她的人際關係成不成功密切相關,甚至分割不了。社會學家與家庭專家維吉尼亞.施瓦茲博士(Virginia Rutter)的結論是,「大量的研究顯示,女性的自尊與人際關係是否融洽息息相關,繼親家庭也是一樣的情況。」簡單來說,我們女性需要喜歡別人,也需要被別人喜歡,缺一不可,否則我們會感到自己沒做好,是一個失敗者。
我們認為需要解決繼親家庭碰上的問題,把問題當成自己的責任。這種看法根深蒂固(數十年來,父母與社會都是那樣告訴我們),幾乎不可能抗拒。伊麗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是美國威徹斯特郡家庭治療學會(Family Institute of Westchester)的創辦人與榮譽主任,以及《無形的網:家庭關係中的性別模式》(The Invisible Web: Gender Patterns in Family Relationships)的共同作者。她指出,「女性被教養成認為必須替每一個人負責。繼母要是看見孩子不開心,或是丈夫無能……她就會過去幫忙。女性會想辦法解決問題——不論那究竟該不該由她們想辦法。」我們知道繼親家庭有大量問題,有著人際關係的障礙與煩心事;我們有大量的理由懷疑自己、責怪自己,覺得自己沒做好。事實上,貝勒大學的貝雷博士發現,在再婚家庭裡,繼母是所有家庭成員中最會批評與責怪自己的人。
在這一點上,我們和男性有著天壤之別。研究顯示4,繼父參與繼子女事務的程度低非常多——內心也沒那麼多的衝突、壓力、罪惡感。此外,我們的先生不論本身是不是繼父,對我們認為必須把每個人團結在一起的想法,以及我們心底深處深深的挫敗感,皆感到相當困惑不解。女性與男性看待繼親家庭問題的性別差異,有可能讓夫妻之間無法同心,增加妻子的疏離感與挫敗感。我們全都能明白繼母布蘭達的感受。布蘭達有兩個小小孩,還有一個青春期繼子,她告訴我,「有時我會恨自己不能做得更好,無法讓我們成為一個家,永遠在和先生吵他兒子的事。」
女性有時會對無法建立連結、無法解決問題,感到耿耿於懷。或許那解釋了為什麼在我的訪談過程中,好幾位有繼子女的女性,告訴我相同的故事,或是某種版本類似的故事,以相似到出奇的方式,談彼此共同的憂慮。我們努力溝通,但無法溝通,誤會與誤解產生,我們一再感受到挫敗與怨念——必須面對男方的孩子時,他們有時會引發我們心中醜陋的情緒,那些我們覺得自己不該有的禁忌情緒。那種感覺就像某位繼母告訴我的話,「救命啊!我困在電影裡!」
某位女性的繼子女每週(或是一個月幾次)打電話回家,每次都在電話答錄機上留下相同的留言,「嗨,爸爸,是我。希望你一切平安。我想你。打電話給我。掰掰,爸爸。」數十通留言,從來不曾有一通向爸爸的妻子打招呼。答錄機上的錄音是繼母的聲音,平日也是她在聽留言(好吧,繼子不知道這件事,但還是一樣……)。更糟的情況是,繼母可能得和繼子女同住一段時間,在隔週的週末到火車站接送,還寄給繼子生日卡,或是協助繼女籌備婚禮,不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優先順序,投入多年光陰,努力建立關係,因為現實就是她嫁的人有孩子。 告訴我電話答錄機故事的女性,不認為自己過分敏感,但坦承繼子的留言令她不舒服。繼子一再假裝她不存在,她怎麼可能沒留意到?最糟的是,光是想到這件事、光是有不舒服的情緒(先生的孩子從不在留言中向自己打招呼),她就覺得自己很小心眼。這是典型的邪惡繼母困境——其實不是任何人的錯,但因為她不舒服,所以這件事變成她的問題。她可以想像,要是下次繼子女打電話過來,她告訴他們,「嗨,近來好嗎?太好了,是這樣的,我想講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但你每次打電話過來留言,從來沒跟我說嗨,只和你爸爸打招呼,我有一點……傷心。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她知道自己永遠無法把這些話說出口,要是說了,也只不過是節外生枝。她原本就察覺繼子女在說她的閒話,這下子更是被抓到把柄——繼母是個控制狂、情緒緊繃、管東管西、不懂得放手、她在嫉妒。
女人心想:還是算了,別跟繼子女提那些話,順口提醒先生一下就好。她不想鬧出什麼事,只是暗示一下,希望告知情況後,先生就會懂她的意思,「好奇怪,每次提姆打電話過來,雖然他聽到答錄機上是我的聲音,他都會說,『嗨,爸。』不曾說過,『嗨,琴。』」然而,先生點點頭,看起來心不在焉,或是覺得有點煩,接著就改變話題。繼子繼續留一樣的電話留言。幾個月後,或是一年後,女性再也不試圖暗示先生。當然,她平常不是那麼畏畏縮縮的人——我的訪談對象用急促、防衛心強的語調,講出故事的這個部分。她害怕就算同為繼母,我仍會在心中想,你這個女人怎麼會那樣。她怕我批評她居然有這麼典型的邪惡念頭,即便只是一閃而過的想法。
她心慌意亂,受到傷害。沒錯,只是一些小事,但成為一家人都已經這麼久了,她仍不免感到,繼子女的這類作為是在故意無視她,拒絕承認她這個人的存在(即便只是無意間)。然而,她是大人了,她決定要當個情緒成熟的人,正大光明地面對,不要偷偷懷恨在心。她不要生悶氣,讓傷口化膿,讓小事不必要地鬧大,她要再次提醒先生這件事。她告訴自己:先生一定會理解的,一定會告訴他的孩子,這樣的「不小心漏掉」有點奇怪。聽到電話答錄機上是繼母的聲音時,有禮貌的做法是同時向雙方打招呼,「嗨,爸。嗨,琴。我是提姆。」
然而,先生一下子惱羞成怒,「為什麼又要提這件事?根本從頭到尾就沒什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先生替兒子說話,「他已經盡量不出現在你眼前了,你卻還是有辦法挑他的毛病。你太敏感了。為什麼就是不能放過這件事?」
女人跳腳,「我只是說出你兒子做了什麼。為什麼要把矛頭指向我?」她嚇了一跳,失望又茫然。她真的太過分了嗎?她還以為,自己只是在說出心中的感受,請先生幫忙。為什麼她只是說出他的孩子做了什麼,夫妻間就有了裂痕?難道她的感受不重要?是她太蠻橫了?難道說她要求的事不合理嗎?她覺得沒有啊,可是她也不確定。她不懂,憑什麼要她忍氣吞聲。他的孩子的確做了沒禮貌或傷人的事,為什麼要她視若無睹,為什麼要裝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