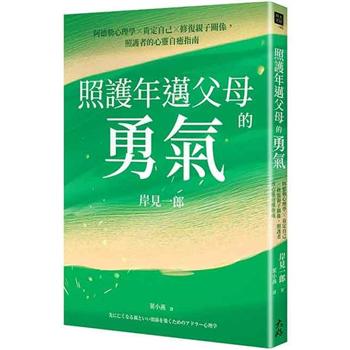為何自己一個人承受?
每當看到與照顧父母相關的事件報導,我總是想:為何他會自己一個人承受,難道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去做嗎?但現在我明白了,姑且不論短時間的暫代問題,「事實上」他應該就是處於無人可代替的狀況下,有可能代替和真正可以代替是不一樣的。
孩子還小的時候,我岳母總是說,有需要的話,她隨時可以過來幫忙。幸好孩子們幾乎沒有發生過類似突然發燒這樣的狀況,但曾經因為孩子病了,我卻偏偏得去工作,心裡盤算著是該聯絡一下岳母來幫忙,結果她卻說因為手邊有工作,臨時才通知她,很難安排。只要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就會覺得岳母並非可靠的求助對象,也就不會想著要仰賴她了。
雖然大家都會說:「不是應該多向他人求助才對嗎?」事實是這樣沒錯,但即使心裡這樣認為,現實生活中有些事情還是旁人無法代勞的。周遭的人會說些類似「又不是只有你一個小孩」或是「還有其他兄弟姊妹啊」這樣的話;可是實際上,不是每個孩子都有辦法照顧父母。如果住得遠,就很難照顧得到,或是派駐海外的人,也是一樣沒辦法。提出無法照顧的理由,就像選家長會幹部一樣,說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推辭的人,就會被選為幹部。幹部通常頂多一年就可以卸任,照護的職責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想到應該有人比父親還嚴重,也是讓我一個人扛下照護職責的原因。我會想:「雖然白天要盯著,但是晚上他不是可以自己一個人嗎?」或者「他又不是癱在床上,如果這樣的照護就喊累的話,那些更辛苦的人會怎麼想?」等等。還有:「雖然他沒辦法自己做飯,但只要幫他準備好了,根本不用我的協助就能自己吃得很好啊。」一想到這些,便覺得自己怎麼可以因為這麼一點事就叫苦。
可是,如同前面也看到的,實際上不論對象需要接受照護的程度多寡,照護在任何狀況下都是辛苦的。我認為,大可以坦率地承認這件事。在照護上與他人做比較,毫無意義,因為不論任何狀況必然有其辛苦之處,並不像照護需求鑑定,或申請安養機構時所做的檢測,可以用分數來辨別照護的需求度。這當中,有些人認為「照護」這件事,只能自己認命去做,而一個人扛著。上野千鶴子用了「逞強式照護」這個說法──「似乎愈是執拗逞強地在做照護這件事,愈傾向拚了命做到最好的態度,給自己加重負擔。」──《年老的準備》(老いる準備,暫譯)
上野說,雖然女性站在「媳婦」的立場,會以這種「逞強式照護」來束縛自己,但是照護自己的父母時,卻不會如此鑽牛角尖。其實我雖然是兒子的角色,卻也無法在照護父親的這件事情上撇清「逞強」的部分,所以無關性別或立場,採用「逞強式照護」的人想必很多吧。
使用照護服務,或是讓父母進入安養機構的確很花錢;再來,也有人認為自己照顧會比讓外人照顧好得多,可是長期下來是很辛苦的。我可以想像,這就類似現在仍然有人認為「小孩在三歲之前不該交給別人,應該要父母自己帶」的想法一樣。
不過,照護很辛苦這件事,由於我自己有著深刻的體會,請原諒我斗膽說出一些重話。即使是執拗逞強式的照護,如果可以把父母照顧好當然沒問題,但如果自己一個人扛下,到了無能為力、被逼入困境的地步,以至於變成棄之不顧時,不免遭人指責沒有責任感。希望在演變成以那種方式放棄之前,可以認真考量一下,即使不是全部也無妨,將部分照護的擔子委託他人,並善用照護服務。
重新開始與父母的關係
與年邁的父母共同生活或進行照護時,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訂定無法達成的目標。面臨要照護的關頭,才與父母和睦相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在他們需要照護之前,關係已經和樂融融的話,照護過程中要和睦共處也許不難;但如果不是的話,屆時才打算努力實現關係融洽的目標,儘管不是不可能,只怕難度很高。
不只限於照護的時候,一般來說,人們回想過去而懊悔、思慮未來而不安。可是我們(現在)既無法回到已經消逝的過去,(此刻)為了還沒到來的未來煩憂也毫無意義,就連自以為肯定會到來的明天,也不見得必然到來。相信應該有不少人都曾經思考過這樣的事。在照護上,要將自己與父母之間的過往都當作不存在,或許有點困難。但是要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必須抱著「從頭開始」的心態去相處。這樣的做法意味著──如果過去與父母關係不佳,現在就不要將焦點放在這件事情上。不只如此,像是子女後來才察覺到「父母其實早就需要照護」的事實,為了「自己該早點發現才對」而感到後悔的情況也一樣,因為這樣的懊悔根本無濟於事。
所以不論過去如何,今後只能逐步建立與父母的關係。不過如果一開始就以親子間的良好關係為目標,將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苦惱。
一開始,先過著平靜無波、沒有大爭端的日子應該就可以了。原本就跟父母沒什麼話說,而且經常一開口就大吵一架的人,現在突然要與父母變得親近,沒那麼容易。
所以只要從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先開始,慢慢改變彼此的關係就行,例如至少做到可以待在同一個空間,保持和睦氣氛之類的。
我母親過世之後,由於父親不是情緒化就是愛叨唸,所以我總是感到退縮無奈。年幼的子女陪我跟他在一起的話,雖然可以避免與他發生衝突,不過一旦只有我們兩人共處的時候,氣氛就變得很凝重。我與父親再度共同生活的最初目標是能夠與他共處一室。
事實上,父親在回來這裡的十年前左右,曾經主動拉近與我的距離。由於他突然表示:「我想接受你在做的那個心理諮商。」於是我每個月與父親見一次面,聽他說話。雖然談不上是幫父親做了心理諮商,但是我們能夠與年輕時不同,保持一點距離冷靜地對話,對於後來要開始照顧他來說是很好的經驗。不過也必須說,偶爾碰個面與每天長時間共處一室,畢竟是有極大差異的。
只能與「眼前所見」的父母一起過日子
很明確的一點是──不論腦部狀態如何,不管有沒有出現腦部萎縮、海馬迴萎縮的現象,我們只能與眼前所見的父母一起走下去。
父母並不會因為被診斷為阿茲海默,或是其他類型的失智症,就變成了別人。即使他的言行表現,好像與過去年輕時完全不同,他還是原來的那個人;相反地,有時候我們反而會因為「父母所說的話簡直跟過去沒兩樣」而感到驚訝。無論如何,父母依然是父母。
人,為了成為一個具備「人格(身而為人的資格)」的個體,除了生物學上所謂人類的條件之外,還必須加上自我意識。
問題是,當我們以「擁有自我意識」為條件時,受精卵儘管是生物學上的人類,卻不能說是具備人格的個體。依這樣的想法,有些人便主張失智症患者並不具備人格,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那麼,就社會上的意義承認他是一個個體,並以能夠達到最低限度的溝通為成立條件的話,失智症患者具備人格,可是腦死患者則被排除在外。相信腦死病患的家屬,應該很難接受這樣的說法。
舉例來說,對感覺到胎動的母親而言,胎兒並不是物品。之前,我母親雖然不是處於腦死狀態,但因為腦中風而失去意識,既沒有自我意識,也沒辦法進行溝通,如果要告訴我:母親是一個不具備人格的個體。我肯定是很難接受。
戴著帽子的人,脫了帽子還是同一個人,不論有沒有自我意識、能不能進行溝通,人在任何時刻都是具備「人格」的個體。即便進入昏睡狀態,人也不會變成物品。
如果要問為何可以這麼說,那是因為我認為這裡所提出的「人格」,必須要納為「人類」的一部分來考量。人,無法獨自「身而為人」;換句話說,人,沒有辦法脫離人際關係。從人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即使被認定沒有自我意識、處於腦死狀態的人,對於過去還未腦死時就已經認識他的人來說,他還是同樣一個人(人格)。就連已經過世的人,只要有人還記得他,他的人格便能繼續存在。
再說回來,雖然我父親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但不論他的腦部狀態如何,或因此失去之前的記憶,甚至看起來簡直變了一個人,父親在與我和家人的關係之中,依然還是父親。思考「怎麼做?」而不是「為什麼?」
夏季裡開滿花朵的朱槿,季節更迭後不再有花苞,也見不到花開。每逢繁花盛開,父親就會說:「你看!朱槿花開了。」然而吃過早飯後小憩到中午,再醒來時的他,便看著那花說:「是昨天開的。」彷彿是父親的日子過得特別快。也許他是睡了一覺就算過了一天。
讓父親滿心期待的朱槿不再開花時,我依然每天澆水。有一天,我發現了花苞。夏天時,花苞一天大過一天,等待花開要不了多少時間,可是一到秋天,花苞就不怎麼長了。不過我沒放棄繼續澆水,終於有一天,久違的碩大花朵綻放開來。
仔細一看,還有其他小小花苞,今天開的這朵就算謝了,明天我肯定還是繼續照顧它。不是因為它會開花才費心呵護,而是不論何種狀況下,都會照顧它;也就是說,即使不再開花了,應該也不會停止對它的關照吧。頓時想起,這就好像我對父親的心意一樣。就算醫生說失智症醫不好,家人也不會因此而選擇放棄,什麼也不做。
照護的時候,發生任何狀況都只能接受。也就是在照護上沒有Why(為什麼)只有How(怎麼做)。即使去思考為什麼父母會變成這樣,應該也得不到答案,照護的日子不由分說就是這麼開始了。
每當看到與照顧父母相關的事件報導,我總是想:為何他會自己一個人承受,難道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去做嗎?但現在我明白了,姑且不論短時間的暫代問題,「事實上」他應該就是處於無人可代替的狀況下,有可能代替和真正可以代替是不一樣的。
孩子還小的時候,我岳母總是說,有需要的話,她隨時可以過來幫忙。幸好孩子們幾乎沒有發生過類似突然發燒這樣的狀況,但曾經因為孩子病了,我卻偏偏得去工作,心裡盤算著是該聯絡一下岳母來幫忙,結果她卻說因為手邊有工作,臨時才通知她,很難安排。只要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就會覺得岳母並非可靠的求助對象,也就不會想著要仰賴她了。
雖然大家都會說:「不是應該多向他人求助才對嗎?」事實是這樣沒錯,但即使心裡這樣認為,現實生活中有些事情還是旁人無法代勞的。周遭的人會說些類似「又不是只有你一個小孩」或是「還有其他兄弟姊妹啊」這樣的話;可是實際上,不是每個孩子都有辦法照顧父母。如果住得遠,就很難照顧得到,或是派駐海外的人,也是一樣沒辦法。提出無法照顧的理由,就像選家長會幹部一樣,說不出任何理由可以推辭的人,就會被選為幹部。幹部通常頂多一年就可以卸任,照護的職責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想到應該有人比父親還嚴重,也是讓我一個人扛下照護職責的原因。我會想:「雖然白天要盯著,但是晚上他不是可以自己一個人嗎?」或者「他又不是癱在床上,如果這樣的照護就喊累的話,那些更辛苦的人會怎麼想?」等等。還有:「雖然他沒辦法自己做飯,但只要幫他準備好了,根本不用我的協助就能自己吃得很好啊。」一想到這些,便覺得自己怎麼可以因為這麼一點事就叫苦。
可是,如同前面也看到的,實際上不論對象需要接受照護的程度多寡,照護在任何狀況下都是辛苦的。我認為,大可以坦率地承認這件事。在照護上與他人做比較,毫無意義,因為不論任何狀況必然有其辛苦之處,並不像照護需求鑑定,或申請安養機構時所做的檢測,可以用分數來辨別照護的需求度。這當中,有些人認為「照護」這件事,只能自己認命去做,而一個人扛著。上野千鶴子用了「逞強式照護」這個說法──「似乎愈是執拗逞強地在做照護這件事,愈傾向拚了命做到最好的態度,給自己加重負擔。」──《年老的準備》(老いる準備,暫譯)
上野說,雖然女性站在「媳婦」的立場,會以這種「逞強式照護」來束縛自己,但是照護自己的父母時,卻不會如此鑽牛角尖。其實我雖然是兒子的角色,卻也無法在照護父親的這件事情上撇清「逞強」的部分,所以無關性別或立場,採用「逞強式照護」的人想必很多吧。
使用照護服務,或是讓父母進入安養機構的確很花錢;再來,也有人認為自己照顧會比讓外人照顧好得多,可是長期下來是很辛苦的。我可以想像,這就類似現在仍然有人認為「小孩在三歲之前不該交給別人,應該要父母自己帶」的想法一樣。
不過,照護很辛苦這件事,由於我自己有著深刻的體會,請原諒我斗膽說出一些重話。即使是執拗逞強式的照護,如果可以把父母照顧好當然沒問題,但如果自己一個人扛下,到了無能為力、被逼入困境的地步,以至於變成棄之不顧時,不免遭人指責沒有責任感。希望在演變成以那種方式放棄之前,可以認真考量一下,即使不是全部也無妨,將部分照護的擔子委託他人,並善用照護服務。
重新開始與父母的關係
與年邁的父母共同生活或進行照護時,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訂定無法達成的目標。面臨要照護的關頭,才與父母和睦相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在他們需要照護之前,關係已經和樂融融的話,照護過程中要和睦共處也許不難;但如果不是的話,屆時才打算努力實現關係融洽的目標,儘管不是不可能,只怕難度很高。
不只限於照護的時候,一般來說,人們回想過去而懊悔、思慮未來而不安。可是我們(現在)既無法回到已經消逝的過去,(此刻)為了還沒到來的未來煩憂也毫無意義,就連自以為肯定會到來的明天,也不見得必然到來。相信應該有不少人都曾經思考過這樣的事。在照護上,要將自己與父母之間的過往都當作不存在,或許有點困難。但是要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必須抱著「從頭開始」的心態去相處。這樣的做法意味著──如果過去與父母關係不佳,現在就不要將焦點放在這件事情上。不只如此,像是子女後來才察覺到「父母其實早就需要照護」的事實,為了「自己該早點發現才對」而感到後悔的情況也一樣,因為這樣的懊悔根本無濟於事。
所以不論過去如何,今後只能逐步建立與父母的關係。不過如果一開始就以親子間的良好關係為目標,將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苦惱。
一開始,先過著平靜無波、沒有大爭端的日子應該就可以了。原本就跟父母沒什麼話說,而且經常一開口就大吵一架的人,現在突然要與父母變得親近,沒那麼容易。
所以只要從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先開始,慢慢改變彼此的關係就行,例如至少做到可以待在同一個空間,保持和睦氣氛之類的。
我母親過世之後,由於父親不是情緒化就是愛叨唸,所以我總是感到退縮無奈。年幼的子女陪我跟他在一起的話,雖然可以避免與他發生衝突,不過一旦只有我們兩人共處的時候,氣氛就變得很凝重。我與父親再度共同生活的最初目標是能夠與他共處一室。
事實上,父親在回來這裡的十年前左右,曾經主動拉近與我的距離。由於他突然表示:「我想接受你在做的那個心理諮商。」於是我每個月與父親見一次面,聽他說話。雖然談不上是幫父親做了心理諮商,但是我們能夠與年輕時不同,保持一點距離冷靜地對話,對於後來要開始照顧他來說是很好的經驗。不過也必須說,偶爾碰個面與每天長時間共處一室,畢竟是有極大差異的。
只能與「眼前所見」的父母一起過日子
很明確的一點是──不論腦部狀態如何,不管有沒有出現腦部萎縮、海馬迴萎縮的現象,我們只能與眼前所見的父母一起走下去。
父母並不會因為被診斷為阿茲海默,或是其他類型的失智症,就變成了別人。即使他的言行表現,好像與過去年輕時完全不同,他還是原來的那個人;相反地,有時候我們反而會因為「父母所說的話簡直跟過去沒兩樣」而感到驚訝。無論如何,父母依然是父母。
人,為了成為一個具備「人格(身而為人的資格)」的個體,除了生物學上所謂人類的條件之外,還必須加上自我意識。
問題是,當我們以「擁有自我意識」為條件時,受精卵儘管是生物學上的人類,卻不能說是具備人格的個體。依這樣的想法,有些人便主張失智症患者並不具備人格,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那麼,就社會上的意義承認他是一個個體,並以能夠達到最低限度的溝通為成立條件的話,失智症患者具備人格,可是腦死患者則被排除在外。相信腦死病患的家屬,應該很難接受這樣的說法。
舉例來說,對感覺到胎動的母親而言,胎兒並不是物品。之前,我母親雖然不是處於腦死狀態,但因為腦中風而失去意識,既沒有自我意識,也沒辦法進行溝通,如果要告訴我:母親是一個不具備人格的個體。我肯定是很難接受。
戴著帽子的人,脫了帽子還是同一個人,不論有沒有自我意識、能不能進行溝通,人在任何時刻都是具備「人格」的個體。即便進入昏睡狀態,人也不會變成物品。
如果要問為何可以這麼說,那是因為我認為這裡所提出的「人格」,必須要納為「人類」的一部分來考量。人,無法獨自「身而為人」;換句話說,人,沒有辦法脫離人際關係。從人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即使被認定沒有自我意識、處於腦死狀態的人,對於過去還未腦死時就已經認識他的人來說,他還是同樣一個人(人格)。就連已經過世的人,只要有人還記得他,他的人格便能繼續存在。
再說回來,雖然我父親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但不論他的腦部狀態如何,或因此失去之前的記憶,甚至看起來簡直變了一個人,父親在與我和家人的關係之中,依然還是父親。思考「怎麼做?」而不是「為什麼?」
夏季裡開滿花朵的朱槿,季節更迭後不再有花苞,也見不到花開。每逢繁花盛開,父親就會說:「你看!朱槿花開了。」然而吃過早飯後小憩到中午,再醒來時的他,便看著那花說:「是昨天開的。」彷彿是父親的日子過得特別快。也許他是睡了一覺就算過了一天。
讓父親滿心期待的朱槿不再開花時,我依然每天澆水。有一天,我發現了花苞。夏天時,花苞一天大過一天,等待花開要不了多少時間,可是一到秋天,花苞就不怎麼長了。不過我沒放棄繼續澆水,終於有一天,久違的碩大花朵綻放開來。
仔細一看,還有其他小小花苞,今天開的這朵就算謝了,明天我肯定還是繼續照顧它。不是因為它會開花才費心呵護,而是不論何種狀況下,都會照顧它;也就是說,即使不再開花了,應該也不會停止對它的關照吧。頓時想起,這就好像我對父親的心意一樣。就算醫生說失智症醫不好,家人也不會因此而選擇放棄,什麼也不做。
照護的時候,發生任何狀況都只能接受。也就是在照護上沒有Why(為什麼)只有How(怎麼做)。即使去思考為什麼父母會變成這樣,應該也得不到答案,照護的日子不由分說就是這麼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