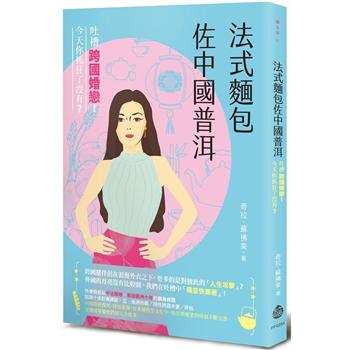3.飲食及生活細節
【醬油色的食物不是食物】
跨國婚姻的相關書籍裡常常會提及因為飲食習慣差異所造成的各種趣聞,因為飲食是婚姻生活裡最日常,也最顯見的問題。奇拉嘗試從更細節處,帶你一覽跨國婚戀中的吃喝瑣事。
初到法國時,奇拉認識了一位中國南方女人郝英,人很有個性,說話也直率、辛辣。奇拉春節時偶爾會去她家參加年度大聚會,每次都是一進屋就看到圍坐了一大桌子的中國女人。郝英下廚做大餐,大家也每人帶一道拿手菜:糖醋排骨、檸檬雞、海帶燉肉、醬肘子……再一起包一頓大餡兒餃子。那種鄉音的喧嘩與熟悉的美味總能慰藉一顆顆久居異鄉的漂泊心。
在奇拉眼裡,郝英絕對是位戰神級的媽。原因是她有四個孩子,大點兒的一個男孩兒和一個女孩兒都已經超過十歲,是跟已逝的前夫生的。定居法國後,前夫去世,她又帶著兩個孩子找了第二任丈夫丹尼爾—一位法籍的突尼斯人。奇拉在法國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跟丹尼爾生了一個男孩兒,剛剛一歲。三年後,她又再生了一個男孩兒,用她的話說是為了兩個孩子能作伴一起長大。
對於這種生孩子的勇氣,奇拉絕對敬佩無地,這輩子都頂禮膜拜,估計下輩子也趕超不了。
如果你不明白奇拉為什麼這麼說,那估計你是還沒結婚,或者結婚了還沒有孩子。如果你有孩子,大概就能心領神會,並且像奇拉一樣佩服郝英三十七、八歲的年紀,在異鄉又生了兩胎的勇氣。這裡略過奇拉生孩子的二十萬字血淚史,繼續說郝英。
每次去郝英家參加聚會,很多中國女人也會帶上自己的法國丈夫,所以飯桌上的情形一般是一群中國女人用漢語肆無忌憚地聊自己的,法國丈夫們用法語聊他們的。因為這些法國丈夫(除了老張以外)都聽不懂漢語,或者只會極少幾句,所以都直接被排除在中國女人的談話之外,他們就自己湊到一起吐槽自己老婆去了。
去了幾次之後,奇拉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就是郝英的丈夫丹尼爾極少在聚會中出現,偶爾露個面,也就是說個「Bonjour(你好)」,然後就又出去了。做飯的時候他不在,吃飯的時候他還不在。等到跟郝英比較熟了,奇拉就問她:
「你老公是不是嫌我們吵啊?吵得他都不回來吃飯了。」
「甭管他,他自己出去吃披薩。」郝英一臉不在乎。
「這麼一大桌好吃的,他還出去吃披薩?」奇拉看著飯桌上正在胡吃海塞中國菜的老張,有點驚訝地問。
「他不吃這些?」
「啊?」
「我跟你說吧,醬油色的東西他都不吃,他只吃紅色的。」郝英非常有總結性地吐槽道。
「什麼意思?」奇拉還沒太明白。
「他們家鄉的菜一般都是番茄醬的顏色,所以中餐裡只有醬汁是紅色的菜,他還願意嘗嘗,而且也不一定喜歡。其他像咱們紅燒的、或者醬爆的等等,都是棕色的嘛,就是醬油色的,他就連嘗也不願意嘗,他覺得那都是東西壞了才是那個顏色。」
奇拉當時就震驚了。媽呀,這可真是入寶山空手而歸,郝英做的糖醋排骨真的是一絕,各種滷品也不遑多讓。娶了一個這麼會做飯的中國老婆,卻連嘗也不願意去嘗那些醬油色的菜。丹尼爾先生絕對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那你們倆日子怎麼過呀?」奇拉不解地問。
「就這麼過唄。我有心情的時候就給他做他願意吃的,或者做漢堡、牛排之類的西餐,沒心情的時候我就做我和孩子們想吃的,讓他自己吃披薩去。」
「那他沒意見呀?」
「切,我管他有沒有意見呢。不吃活該。」郝英衝著家門口披薩店的方向翻了個白眼。
夫妻兩個吃不到一塊兒,其實不是只在跨國婚姻裡存在的問題。就像在中國一個北方人要吃麵食,南方人要吃米飯,或者是一個辣不沾唇,一個無辣不歡……只不過跨國婚姻裡的「飲食不合」總有些更奇葩的理由。只要是醬油色就不吃,這個已經蠻神奇,不過其實你的異國伴侶還可能有更多令你瞠目結舌的奇葩飲食習慣。
【我愛你……所以給你吃那些不能吃的東西】
記得剛跟老張在一起的時候,奇拉還不太會做西餐,一次老張買了一塊蠻貴的小牛肉(Veau)牛排,奇拉做飯的時候正好要炒蘑菇沒有肉,就把他那牛排切成小塊,給炒了蘑菇。
吃飯的時候,老張就開始找他的高級小牛肉牛排,遍尋不見就問奇拉:
「我買的小牛肉牛排,你沒做嗎?那個比較高級,應該快點吃,別放壞了。」
「我做了啊。」奇拉心不在焉地回答。
「啊?」老張頓時懵了。
「在炒蘑菇裡。」奇拉毫無罪惡感地指著炒蘑菇裡的小牛肉丁說道。
「啊!?」老張頓時急了:「你把那麼好的牛排給浪費了。」
奇拉一聽也急了:「我做成中國菜就是浪費了?吃到你嘴裡怎麼是浪費了?我又沒給扔到地上!我下了班辛辛苦苦給你做飯,你還說我浪費了?下次你的東西你自己做,我不管了!」
老張一聽當然也覺得自己似乎有些用詞不當,趕緊說:
「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的、比較好的牛排,我們都是煎著吃,而且不會吃全熟的。像我一般吃saignant(五分熟)的,也有人吃更生一點或者更熟一點的,不過通常很少有人吃全熟的,因為全熟的肉就硬了,口感就不好了。」
奇拉也覺得自己反應有點過大,畢竟自己不熟悉西餐的做法,況且漢語又不是老張的母語,詞不達意或者用詞不當的情況還是偶爾會發生,可能他本來想表達的意思未必有很多貶義或者責備的意思。
後來奇拉便學著煎牛排:自己的牛排要煎得幾乎全熟,老張的牛排又得是半熟,所以奇拉就把他的煎到一半提前拿出來。等老張一吃,又委婉地表示不滿,因為他覺得等奇拉的牛排煎好,他的牛排已經涼了。他說牛排就得趁熱吃,不能吃涼的。於是經過再三練習,奇拉終於學會了把老張的牛排後下,然後兩個牛排同時煎好趁熱吃,並且能熟練地把老張的牛排煎成他想要的半生狀態—一塊牛排切開,橫截面的中間一小半是紅色的生肉,兩邊兩層是淡棕色的熟肉。
牛排是西方玩意,弄不好也就算了,可你不會想到連煮麵條都能出問題。法國這邊的麵條基本上都是那種有點半透明的、硬硬的義大利面,跟中國的掛麵還不太一樣。奇拉煮的時候就按中國掛麵那麼煮,老張卻總嫌煮得太熟了。雖然基本上也會不動聲色地吃下去,但很明顯他的法國胃口並沒有得到滿足。
奇拉就讓老張煮了一次他覺得最好的麵條給奇拉吃,奇拉吃了一口就明白了—原來他想吃的是對奇拉來說還沒煮熟的麵條。
等到奇拉熟練掌握諸多西餐技能,並且把老張的奇特飲食習性爛熟於心的時候,老張開心得不得了,奇拉卻總結出了一句神吐槽:
「感覺你最開心的就是我做各種我覺得不能吃的東西給你吃啊。」
老張會欣然吞下的「不能吃的東西」還包括:
藍紋臭乳酪
各種臭乳酪
一種叫做「Tartare」的菜
……
Tartare的中文翻譯是「韃靼牛肉」。這道菜是生牛肉餡混合洋蔥等香料做成的,那涼絲絲的、黏膩的生肉口感以及生牛肉味道混合了各種香料味,上面再打一個稀湯掛水兒、黏黏糊糊的生雞蛋,攪和在一起成為一坨……看著老張津津有味享用美食的樣子,奇拉也真不是沒嘗試過,憑良心說味道其實也還好。不過鑒於奇拉心理以及腸胃的承受能力,在法國多年也就嘗過這麼一小口而已。
至於臭乳酪,那需要專門花兩個段落來吐槽。如果老張在冰箱裡放進一塊開了封的臭乳酪,那麼當奇拉打開冰箱門的時候,撲面而來那味道讓奇拉覺得自己打開的,不是自家冰箱的門,而是高中軍訓時那扇記憶中的藍色油漆木門—木門的後面是沒有遮攔的十幾個水泥廁坑和地上滿滿蠕動著的白蛆。好吧,這裡需要說句公道話:法國乳酪的種類極多,也有不少挺好吃的乳酪……所以奇拉不明白,老張為什麼非要買發臭的。
奇拉有一次跟婆婆吐槽了自家冰箱的味道,婆婆很能理解。因為她雖然身為地道的法國人,卻除了白乳酪(fromage blanc,一種口味介於優酪乳和奶油之間、幾乎沒什麼味道的乳酪)以外,不吃任何乳酪。婆婆譴責了她兒子之後,過兩天就送來了一個法國專門裝乳酪的密封盒子。而老張看到這個盒子後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
「哎喲,太好了,我們可以用這個把奇拉的臭韓國泡菜裝進去,這樣我們的冰箱就香了。」
如此大言不慚,你們說他是不是欠扁?奇拉一年只有五天會吃辣,一年最多也就買一袋韓國辣白菜吃上幾天。天天吃乳酪的人還敢吐槽泡菜臭?
另一方面,老張覺得奇拉會欣然吞下的「不能吃/喝的東西」有:
韓國泡菜
日本綠芥末
老北京豆汁
香菜
粥
熱水
前三樣也就算了,畢竟在中國也不是人人都喜歡。香菜雖然也有中國人不吃,可是老張對香菜味的厭惡簡直是登峰造極。連別人盤子裡有香菜,他都幾乎要退避三舍。他的名言是:「這菜怎麼可能叫香菜?應該叫臭菜。」
至於粥,對老張來說問題是:第一,這裡面什麼都沒有,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菜;第二,什麼味道都沒有,吃起來口感還怪怪的。這些都是老張說的莫名言論,奇拉也懶得吐槽。
【醬油色的食物不是食物】
跨國婚姻的相關書籍裡常常會提及因為飲食習慣差異所造成的各種趣聞,因為飲食是婚姻生活裡最日常,也最顯見的問題。奇拉嘗試從更細節處,帶你一覽跨國婚戀中的吃喝瑣事。
初到法國時,奇拉認識了一位中國南方女人郝英,人很有個性,說話也直率、辛辣。奇拉春節時偶爾會去她家參加年度大聚會,每次都是一進屋就看到圍坐了一大桌子的中國女人。郝英下廚做大餐,大家也每人帶一道拿手菜:糖醋排骨、檸檬雞、海帶燉肉、醬肘子……再一起包一頓大餡兒餃子。那種鄉音的喧嘩與熟悉的美味總能慰藉一顆顆久居異鄉的漂泊心。
在奇拉眼裡,郝英絕對是位戰神級的媽。原因是她有四個孩子,大點兒的一個男孩兒和一個女孩兒都已經超過十歲,是跟已逝的前夫生的。定居法國後,前夫去世,她又帶著兩個孩子找了第二任丈夫丹尼爾—一位法籍的突尼斯人。奇拉在法國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跟丹尼爾生了一個男孩兒,剛剛一歲。三年後,她又再生了一個男孩兒,用她的話說是為了兩個孩子能作伴一起長大。
對於這種生孩子的勇氣,奇拉絕對敬佩無地,這輩子都頂禮膜拜,估計下輩子也趕超不了。
如果你不明白奇拉為什麼這麼說,那估計你是還沒結婚,或者結婚了還沒有孩子。如果你有孩子,大概就能心領神會,並且像奇拉一樣佩服郝英三十七、八歲的年紀,在異鄉又生了兩胎的勇氣。這裡略過奇拉生孩子的二十萬字血淚史,繼續說郝英。
每次去郝英家參加聚會,很多中國女人也會帶上自己的法國丈夫,所以飯桌上的情形一般是一群中國女人用漢語肆無忌憚地聊自己的,法國丈夫們用法語聊他們的。因為這些法國丈夫(除了老張以外)都聽不懂漢語,或者只會極少幾句,所以都直接被排除在中國女人的談話之外,他們就自己湊到一起吐槽自己老婆去了。
去了幾次之後,奇拉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就是郝英的丈夫丹尼爾極少在聚會中出現,偶爾露個面,也就是說個「Bonjour(你好)」,然後就又出去了。做飯的時候他不在,吃飯的時候他還不在。等到跟郝英比較熟了,奇拉就問她:
「你老公是不是嫌我們吵啊?吵得他都不回來吃飯了。」
「甭管他,他自己出去吃披薩。」郝英一臉不在乎。
「這麼一大桌好吃的,他還出去吃披薩?」奇拉看著飯桌上正在胡吃海塞中國菜的老張,有點驚訝地問。
「他不吃這些?」
「啊?」
「我跟你說吧,醬油色的東西他都不吃,他只吃紅色的。」郝英非常有總結性地吐槽道。
「什麼意思?」奇拉還沒太明白。
「他們家鄉的菜一般都是番茄醬的顏色,所以中餐裡只有醬汁是紅色的菜,他還願意嘗嘗,而且也不一定喜歡。其他像咱們紅燒的、或者醬爆的等等,都是棕色的嘛,就是醬油色的,他就連嘗也不願意嘗,他覺得那都是東西壞了才是那個顏色。」
奇拉當時就震驚了。媽呀,這可真是入寶山空手而歸,郝英做的糖醋排骨真的是一絕,各種滷品也不遑多讓。娶了一個這麼會做飯的中國老婆,卻連嘗也不願意去嘗那些醬油色的菜。丹尼爾先生絕對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那你們倆日子怎麼過呀?」奇拉不解地問。
「就這麼過唄。我有心情的時候就給他做他願意吃的,或者做漢堡、牛排之類的西餐,沒心情的時候我就做我和孩子們想吃的,讓他自己吃披薩去。」
「那他沒意見呀?」
「切,我管他有沒有意見呢。不吃活該。」郝英衝著家門口披薩店的方向翻了個白眼。
夫妻兩個吃不到一塊兒,其實不是只在跨國婚姻裡存在的問題。就像在中國一個北方人要吃麵食,南方人要吃米飯,或者是一個辣不沾唇,一個無辣不歡……只不過跨國婚姻裡的「飲食不合」總有些更奇葩的理由。只要是醬油色就不吃,這個已經蠻神奇,不過其實你的異國伴侶還可能有更多令你瞠目結舌的奇葩飲食習慣。
【我愛你……所以給你吃那些不能吃的東西】
記得剛跟老張在一起的時候,奇拉還不太會做西餐,一次老張買了一塊蠻貴的小牛肉(Veau)牛排,奇拉做飯的時候正好要炒蘑菇沒有肉,就把他那牛排切成小塊,給炒了蘑菇。
吃飯的時候,老張就開始找他的高級小牛肉牛排,遍尋不見就問奇拉:
「我買的小牛肉牛排,你沒做嗎?那個比較高級,應該快點吃,別放壞了。」
「我做了啊。」奇拉心不在焉地回答。
「啊?」老張頓時懵了。
「在炒蘑菇裡。」奇拉毫無罪惡感地指著炒蘑菇裡的小牛肉丁說道。
「啊!?」老張頓時急了:「你把那麼好的牛排給浪費了。」
奇拉一聽也急了:「我做成中國菜就是浪費了?吃到你嘴裡怎麼是浪費了?我又沒給扔到地上!我下了班辛辛苦苦給你做飯,你還說我浪費了?下次你的東西你自己做,我不管了!」
老張一聽當然也覺得自己似乎有些用詞不當,趕緊說:
「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的、比較好的牛排,我們都是煎著吃,而且不會吃全熟的。像我一般吃saignant(五分熟)的,也有人吃更生一點或者更熟一點的,不過通常很少有人吃全熟的,因為全熟的肉就硬了,口感就不好了。」
奇拉也覺得自己反應有點過大,畢竟自己不熟悉西餐的做法,況且漢語又不是老張的母語,詞不達意或者用詞不當的情況還是偶爾會發生,可能他本來想表達的意思未必有很多貶義或者責備的意思。
後來奇拉便學著煎牛排:自己的牛排要煎得幾乎全熟,老張的牛排又得是半熟,所以奇拉就把他的煎到一半提前拿出來。等老張一吃,又委婉地表示不滿,因為他覺得等奇拉的牛排煎好,他的牛排已經涼了。他說牛排就得趁熱吃,不能吃涼的。於是經過再三練習,奇拉終於學會了把老張的牛排後下,然後兩個牛排同時煎好趁熱吃,並且能熟練地把老張的牛排煎成他想要的半生狀態—一塊牛排切開,橫截面的中間一小半是紅色的生肉,兩邊兩層是淡棕色的熟肉。
牛排是西方玩意,弄不好也就算了,可你不會想到連煮麵條都能出問題。法國這邊的麵條基本上都是那種有點半透明的、硬硬的義大利面,跟中國的掛麵還不太一樣。奇拉煮的時候就按中國掛麵那麼煮,老張卻總嫌煮得太熟了。雖然基本上也會不動聲色地吃下去,但很明顯他的法國胃口並沒有得到滿足。
奇拉就讓老張煮了一次他覺得最好的麵條給奇拉吃,奇拉吃了一口就明白了—原來他想吃的是對奇拉來說還沒煮熟的麵條。
等到奇拉熟練掌握諸多西餐技能,並且把老張的奇特飲食習性爛熟於心的時候,老張開心得不得了,奇拉卻總結出了一句神吐槽:
「感覺你最開心的就是我做各種我覺得不能吃的東西給你吃啊。」
老張會欣然吞下的「不能吃的東西」還包括:
藍紋臭乳酪
各種臭乳酪
一種叫做「Tartare」的菜
……
Tartare的中文翻譯是「韃靼牛肉」。這道菜是生牛肉餡混合洋蔥等香料做成的,那涼絲絲的、黏膩的生肉口感以及生牛肉味道混合了各種香料味,上面再打一個稀湯掛水兒、黏黏糊糊的生雞蛋,攪和在一起成為一坨……看著老張津津有味享用美食的樣子,奇拉也真不是沒嘗試過,憑良心說味道其實也還好。不過鑒於奇拉心理以及腸胃的承受能力,在法國多年也就嘗過這麼一小口而已。
至於臭乳酪,那需要專門花兩個段落來吐槽。如果老張在冰箱裡放進一塊開了封的臭乳酪,那麼當奇拉打開冰箱門的時候,撲面而來那味道讓奇拉覺得自己打開的,不是自家冰箱的門,而是高中軍訓時那扇記憶中的藍色油漆木門—木門的後面是沒有遮攔的十幾個水泥廁坑和地上滿滿蠕動著的白蛆。好吧,這裡需要說句公道話:法國乳酪的種類極多,也有不少挺好吃的乳酪……所以奇拉不明白,老張為什麼非要買發臭的。
奇拉有一次跟婆婆吐槽了自家冰箱的味道,婆婆很能理解。因為她雖然身為地道的法國人,卻除了白乳酪(fromage blanc,一種口味介於優酪乳和奶油之間、幾乎沒什麼味道的乳酪)以外,不吃任何乳酪。婆婆譴責了她兒子之後,過兩天就送來了一個法國專門裝乳酪的密封盒子。而老張看到這個盒子後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
「哎喲,太好了,我們可以用這個把奇拉的臭韓國泡菜裝進去,這樣我們的冰箱就香了。」
如此大言不慚,你們說他是不是欠扁?奇拉一年只有五天會吃辣,一年最多也就買一袋韓國辣白菜吃上幾天。天天吃乳酪的人還敢吐槽泡菜臭?
另一方面,老張覺得奇拉會欣然吞下的「不能吃/喝的東西」有:
韓國泡菜
日本綠芥末
老北京豆汁
香菜
粥
熱水
前三樣也就算了,畢竟在中國也不是人人都喜歡。香菜雖然也有中國人不吃,可是老張對香菜味的厭惡簡直是登峰造極。連別人盤子裡有香菜,他都幾乎要退避三舍。他的名言是:「這菜怎麼可能叫香菜?應該叫臭菜。」
至於粥,對老張來說問題是:第一,這裡面什麼都沒有,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菜;第二,什麼味道都沒有,吃起來口感還怪怪的。這些都是老張說的莫名言論,奇拉也懶得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