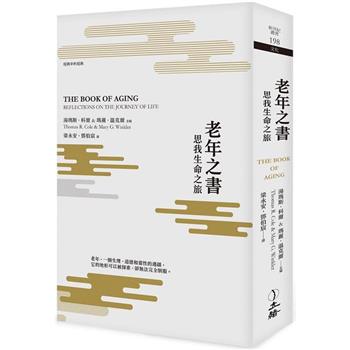緒言/T. R. 科爾
本書之編選係出於一個體認:「老年」在今日西方已成為一個尋找目的感的階段。有史以來第一次,大部分西方人可望尚能健康地活到七十多歲;有史以來第一次,八十五歲以上人士是西方人口裡增加最快速的年齡群。偏偏就在這時候,《傳道書》(Ecclesiastes)的名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卻顯得不太適用於人生的後半階段。
在十六世紀至廿世紀約一九七〇年代之間,受現代社會發展的刺激,西方人對老年的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古代和中世紀都視年老為世間永恆秩序的一個神祕部分,但這觀念卻逐漸被一種世俗、科學和個人主義的年老觀所取代。老年不再被視為生命靈性之旅的其中一站,反而被重新界定為一個有待科學和醫學來對治的問題(problem),在廿世紀中葉,老年人是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剩下給他們的主要身分只是病人和退休年金的領取者。
由於長壽變得普遍而非例外,又由於集體意義系統再已無能力給老年階段灌注廣泛共用的意義,以致我們對於老年階段意義何在的問題,變得非常茫然。古代的神話和現代的刻板印象俱無法處理或反映愈來愈長壽的老年世代的不確定感。老年的「現代化」催生出一籮筐懸而未解的問題:老年階段真是具有內在目的性嗎?在把孩子養大和退休之後,一個人還真有什麼重要事好做嗎?老年是人生的極致嗎?它包含著自我完成的潛力嗎?入老後的靈性成長道路何在?老年人具有何種的角色、權利和責任?老年階段的特殊力量和德性何在?真有所謂的「美好」老年嗎?
一九七九年,英國作家布萊思(Ronald Blythe) 在《冬天觀點》(The View in Winter)一書中指出,「活得老的普遍性」太過新穎了,以致還沒有人能體會箇中意涵。他說,現在的老年人等於是「被判了終身監禁,變成一個公共課題。他們是第一代的全職老人,也是第一批必須由國家提供特殊支援的人口——國家做這事時又吝惜和舉棋不定。」布萊思相信,再過不久,人們便有必要在學會如何長大時就要去學習如何入老。
這番意見深有見地,但從今日看來卻像是昨日黃花。因為,在廿世紀晚期的西方,已經漲湧許久的現代性(modernity)大潮出現了逆轉:在「老人潮」(age wave)的助長下,各種未經勘察的文化潮流紛紛打破了各種有關老邁與老年的約定俗成意象、規範與預期。政府把大比例的經濟與醫療資源投入照顧老年人之舉亦引發出激烈的辯論,因為一些人相信,在規模日漸萎縮的福利國家裡,這種做法是在助長世代間的不平等。與此同時,作家、製片家、老人權的鼓吹者與老年人自己亦紛紛挑戰人們對老年階段的負面刻板印象。
例如,近年愈來愈多小說把老年人寫得複雜而耐人尋味,大異其趣於法國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一九七〇年所作的粗糙概括。波娃曾在《老之將至》(The Coming of Age)一書中斷言,文學不會對老年人內心世界感興趣,因為老年人被認為是「定了型的,沒有前景,沒有發展性可言。」今日的發展卻大相逕庭:許多描寫中年人或老年生活的當代小說(本書選錄了一部分)都不只是關注喪親之痛或身體的衰損。代之以,它們體現出西方文化想要探索老年經驗愈來愈強的衝動,相信老年是向著某種積極的目標邁進(這些可能的目標包括):知性的統一;與他人建立愛的關係;好奇心的復返;接受人必有一死的事實;上帝等。例如,在小說《老年之泉》(The Fountain of Age, 1935)中,貝蒂.弗利丹(Berry Friedan)以自己的老年經驗為藍本,揭示出一個老人如何能夠同時兼顧自己的自由並關懷他人。現在,媒體裡的老年人開始扮演一些新的角色,老人教育不斷推陳出新,退休人士從事各種進修與生產性活動,關懷老年生活的理論與文學作品愈來愈多——凡此都是一些跡象,顯示出我們的高齡化社會正在繪畫一幅「耳目一新的人生地圖」(A Fresh Map of Life,這是美國歷史學者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著作的書名)。
所以,我們的世紀提供了一些新的契機,使我們可重拾老年的道德與靈性向度,使我們可以設法嫁接生命與科學的鴻溝,使我們可以調和現代人重視個人發展的價值觀,和古代人接受自然侷限性和社會責任的價值觀。然而,讓人望而生畏的障礙仍然存在。很多最讓我們困惑的兩難,都與西方文化迄今未能接受身體衰退和人必有一死的事實有關。基本上,西方文化仍然把身體衰退和死亡視為一種個人的失敗或醫學的失敗,不認為其中包含任何社會意涵或更廣的意涵。
面對喪親之痛、體能衰退、疾病纏身、離死不遠和依賴他人照顧的事實,我們很難安然面對時間流逝:我們會焦慮,會夢想返老還童,會因為失去獨立生活而自覺羞愧或低人一等。這些障礙似乎會把時間的流動性給堵塞住,製造出一種停滯的感覺,讓人覺得被僵固。在西方文化裡,中年和中年以後的人往往在自己和別人眼中顯得是個陌生人,是個模糊人物。不過,隨著現代文化一些強烈偏見(如相信「進步」會使舊事物過時,「新」勝於「舊」、「年輕」勝於「年老」等)逐漸被侵蝕,我們社會對老年的惶恐不安和逃避老年的鴕鳥心態也逐漸降低。愈來愈多人願意正視這個有趣的真理:老年人是我們中間的一員。
科學研究和醫學科技無疑將會繼續改寫人類生命的生物可能性,但它們永不可能把我們從種種必然的侷限性中給解放出來。無影無形的「時間」大概是最謎樣的一種侷限性。老去是生活在時間中的必然結果。我們總是在某一時刻誕生到這個世界,然後又會在後來某個未知的時刻離開這世界,並註定會在一生中經歷一些重大的變化。對個人乃至於群體,時間都會帶來形式與環境的改變。荷蘭人類學家范根內(Arnold van Gennep)在《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 1908)一書中指出:「每個人都總是有新的門檻要跨過:冬與夏 的門檻、季與年的門檻……出生的門檻、青春期的門檻、成熟的門檻、死亡的門檻,再來還有(對信徒來說如此)死後生命的門檻。」
雖然老化設定了生死的大哉問,但它卻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或毫不含糊的答案。誠如英國作家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在《長老的藝術》(The Art of Growing Old, 1944)一書裡指出的:「如果到六十歲我們還不明白生命是一個弔詭與矛盾的結,不知道我們的每個行為裡糅雜了多少的善與惡,不知道我們的女主人真理女士(Lady of Truth)性格有多麼妥協,那就表示我們是白老了。」有關老去的道德真理與靈性真理都是可能獲得和必須獲得的,但它們並沒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穿的尺碼。
要讓道德真理和靈性真理成為個人能合穿,這些真理必須是從特定文化的歷史布料裡剪裁出來,先經過個人經驗來量身訂造,再透過「朝聖者」的靈性演化過程給縫紉起來。八十出頭時的弗羅麗達.史考特—麥斯威爾(Florida Scott-Maxwell)在《我日子的尺度》(The Measure of My Days, 1968)裡說過:「我們這些老者知道老年所意味的並不只是失能。那是一種強烈和多樣性的體驗,有時幾乎不是我們所能承受,但又需要我們去細細品味。如果那是一趟漫長的失敗,那它也是一場勝利,對時間的初學者來說充滿意義,哪怕它不是那些無法走出得夠遠的人所能承擔。」用更斯多噶派的語言來說,長老(growing old)並不光是年歲的累積。「年齡並不重要,」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 1919)裡說過,「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以訓練有素的韌性,面對人生的諸般現實,並在內心鼓起勇氣加以應對。」《老年之書》(The Book of Aging)的編選方針正是要擴大讀者的能力,來面對和應對晚年生活的挑戰與契機。
人本主義老人學 (humanistic gerontology)和社會老人學(social gerontology)近年最有趣的一個發現,大概就是這個:不分年紀老少,創造性始終是成長的有力泉源。雖然創造性通常都會體現在一件具體的事物上(如一幅畫、一首詩、一本書或一件家具)但也常常可以體現在不那麼具體的結果:個人或群體自我意象的改變;對於一個人該如何過生活的理解的改變;一種長期關係的深化;更瞭解到自己在家庭、一個宗教群體或自然界裡的地位。
正如美國學者暨作家卡斯滕鮑姆(Robert Kastenbaum)在《世代》(Generations, 1991)一書中指出的,創造性大概是「老年人對生命侷限性和不確定性最有力的回應……事實上,創造活動包含的歡樂與活力可以以其自身的方式,勝過衰弱的入侵與時間不捨晝夜的流逝……而如果生命的每一瞬間都是一種過渡、一種變遷與衰壞,那這種經驗的創造性整合,不是也要求人去珍惜已過去的時光和擁抱尚未來到的時光?」把這番話用在長老的工作上,創造性(它涉及肯定生命和願意冒險)所要求的便是一個人在不斷改變的內在與外在環境中,持續地與侷限性角力。
《老年之書》鼓勵讀者進行這一類與天使的角力。全書共分九章,各章的主題分別象徵和闡明老年的歡樂、神祕、痛苦,以及人追求自我認知的理念和力求把人生歲月活得充實的抱負。每一章的詩文選都大致分為幾單元,每一單元的內在關連性會在章前的前言有所說明。換言之,編者在每一章一開始都會交代他們是根據什麼理由安排觀念、意象與感情的移動推進。不過,入選的詩文都是獨立的文本,完全容許讀者自行作出詮釋和反應。
在為每一章選定主題時,我們力求迴避一些僵固的範疇,以免讓人誤以為,老年所應該追求的是一些抽象和靜態的目標,如智慧、健康、靈性或休閒等。另外,我們也迴避一些對立的範疇,如得╱失、健康╱疾病、工作╱休閒、年輕╱年老,生╱死等。
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對老年的許多文化盲點,都是源於中產階級的刻板印象,源自細緻思考而雅好文化的二元論(例如「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很多人都無法站在年輕、健康、事業成功的主流價值觀之外理解自己的經驗。傳統智慧固然無法再讓人信服,但刻版印象卻會模糊想像力。兩者皆未能提供予人自我更新的象徵途徑,又會抑制我們對日常生活簡單真實(梭羅〔Thoreau〕稱之為「繁花盛放的當下時刻」)的鑑賞力,透過把一些常被認為是對立的觀念與意象並置,本書設法建構出一些可以引發驚奇、張力、弔詭、曖昧和矛盾的範疇。
本書把許多不同或相反的觀點共冶一爐(有時甚至同一位作者也會表現出分歧觀點),以鼓勵讀者多接觸不同的觀念或心緒。例如,本書之所以會收錄好幾段《傳道書》的文字,便是因為它包含著豐富的文學對話,讓懷疑主義和虔誠心態各有發聲的機會,正如美國古典學家佩里(T. A Perry)在《與傳道者對話》(Dialogues with Kohelet, 1993)一書所力主的,《傳道書》會提出「一切人類努力最終皆屬徒勞」這個命題,不是把它當成一個結論,而是視之為一種可辯論的立場。所以,它一方面強調時間的流逝會吞噬一切歡樂與成就,另一方面又強調上帝把萬物創造得美好和各有其時。
《老年之書》想要呈現的多種多樣的經驗與抱負,不是有關老年與人類精神的單一真理,正如弗羅麗達.史考特—麥斯威爾所說的:「我懷疑,老年人最在乎的莫過於真理,而他們無法找到,說不定,真理是紛紜的,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尋找屬於自己的真理。」在本書中,讀者既會找到失望、愚蠢、貪婪和未得實現的渴望的表述,也會找到成功、喜樂、平和與智慧的意象。本書的詩文選是要提供一種創造性對話的精神,以鼓勵個人或社會就有關老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進行討論。
本書挑選的詩文許多都是來自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傳統,也有許多是立足於美國和歐洲的文化史。我們也從其他文化、宗教傳統和族裔背景大量取樣。所以,讀者除了會讀到許多熟悉的作品(如莎士比亞的第七十三首十四行詩和西塞羅的〈論老年〉),還會碰到許多始料不及的篇章,如非洲民間故事、伊斯蘭詩歌、古希伯來警語、歷代醫學作品、個人日記的片段和當代佛教僧人的開示。
除詩歌、小說和戲劇外,我們也收錄了一些宗教聖典的文字,哲學思辨、報章訪談記、書簡、日記、雜文、諷刺詩,以及科學與醫學作品。本書既有莎孚(Sappho)、但丁、葉慈這些大作家的作品,但也有一些感人至深的聲音是來自讀書不多的發聲者,如美國黑奴亞歷山大(Gus Alexander)。
除了在文化幅度與文類幅度上涵蓋廣泛,本書在歷史幅度上同樣涵蓋廣泛。人們常常以為,在十九世紀以前,幾乎無人為文討論過老去和老年的課題。這只有部分是事實,沒錯,不管在科學探索、醫學、哲學思辨、個人沉思,以及文學藝術的表達上,老邁成為一個獨立課題的時間不超過一百五十年。然而,因為人們有關時間的觀點總是鑲嵌在他們有關社會、大自然與宇宙的更大觀點之中,是以老邁的課題幾乎見於所有的歷史階 段與所有的人類文化。事實是,在歷史上,一個文化如何看待老年的意義,總是離不開該文化對人生整體的看待方式。
(全文未完)
本書之編選係出於一個體認:「老年」在今日西方已成為一個尋找目的感的階段。有史以來第一次,大部分西方人可望尚能健康地活到七十多歲;有史以來第一次,八十五歲以上人士是西方人口裡增加最快速的年齡群。偏偏就在這時候,《傳道書》(Ecclesiastes)的名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卻顯得不太適用於人生的後半階段。
在十六世紀至廿世紀約一九七〇年代之間,受現代社會發展的刺激,西方人對老年的觀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古代和中世紀都視年老為世間永恆秩序的一個神祕部分,但這觀念卻逐漸被一種世俗、科學和個人主義的年老觀所取代。老年不再被視為生命靈性之旅的其中一站,反而被重新界定為一個有待科學和醫學來對治的問題(problem),在廿世紀中葉,老年人是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剩下給他們的主要身分只是病人和退休年金的領取者。
由於長壽變得普遍而非例外,又由於集體意義系統再已無能力給老年階段灌注廣泛共用的意義,以致我們對於老年階段意義何在的問題,變得非常茫然。古代的神話和現代的刻板印象俱無法處理或反映愈來愈長壽的老年世代的不確定感。老年的「現代化」催生出一籮筐懸而未解的問題:老年階段真是具有內在目的性嗎?在把孩子養大和退休之後,一個人還真有什麼重要事好做嗎?老年是人生的極致嗎?它包含著自我完成的潛力嗎?入老後的靈性成長道路何在?老年人具有何種的角色、權利和責任?老年階段的特殊力量和德性何在?真有所謂的「美好」老年嗎?
一九七九年,英國作家布萊思(Ronald Blythe) 在《冬天觀點》(The View in Winter)一書中指出,「活得老的普遍性」太過新穎了,以致還沒有人能體會箇中意涵。他說,現在的老年人等於是「被判了終身監禁,變成一個公共課題。他們是第一代的全職老人,也是第一批必須由國家提供特殊支援的人口——國家做這事時又吝惜和舉棋不定。」布萊思相信,再過不久,人們便有必要在學會如何長大時就要去學習如何入老。
這番意見深有見地,但從今日看來卻像是昨日黃花。因為,在廿世紀晚期的西方,已經漲湧許久的現代性(modernity)大潮出現了逆轉:在「老人潮」(age wave)的助長下,各種未經勘察的文化潮流紛紛打破了各種有關老邁與老年的約定俗成意象、規範與預期。政府把大比例的經濟與醫療資源投入照顧老年人之舉亦引發出激烈的辯論,因為一些人相信,在規模日漸萎縮的福利國家裡,這種做法是在助長世代間的不平等。與此同時,作家、製片家、老人權的鼓吹者與老年人自己亦紛紛挑戰人們對老年階段的負面刻板印象。
例如,近年愈來愈多小說把老年人寫得複雜而耐人尋味,大異其趣於法國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一九七〇年所作的粗糙概括。波娃曾在《老之將至》(The Coming of Age)一書中斷言,文學不會對老年人內心世界感興趣,因為老年人被認為是「定了型的,沒有前景,沒有發展性可言。」今日的發展卻大相逕庭:許多描寫中年人或老年生活的當代小說(本書選錄了一部分)都不只是關注喪親之痛或身體的衰損。代之以,它們體現出西方文化想要探索老年經驗愈來愈強的衝動,相信老年是向著某種積極的目標邁進(這些可能的目標包括):知性的統一;與他人建立愛的關係;好奇心的復返;接受人必有一死的事實;上帝等。例如,在小說《老年之泉》(The Fountain of Age, 1935)中,貝蒂.弗利丹(Berry Friedan)以自己的老年經驗為藍本,揭示出一個老人如何能夠同時兼顧自己的自由並關懷他人。現在,媒體裡的老年人開始扮演一些新的角色,老人教育不斷推陳出新,退休人士從事各種進修與生產性活動,關懷老年生活的理論與文學作品愈來愈多——凡此都是一些跡象,顯示出我們的高齡化社會正在繪畫一幅「耳目一新的人生地圖」(A Fresh Map of Life,這是美國歷史學者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著作的書名)。
所以,我們的世紀提供了一些新的契機,使我們可重拾老年的道德與靈性向度,使我們可以設法嫁接生命與科學的鴻溝,使我們可以調和現代人重視個人發展的價值觀,和古代人接受自然侷限性和社會責任的價值觀。然而,讓人望而生畏的障礙仍然存在。很多最讓我們困惑的兩難,都與西方文化迄今未能接受身體衰退和人必有一死的事實有關。基本上,西方文化仍然把身體衰退和死亡視為一種個人的失敗或醫學的失敗,不認為其中包含任何社會意涵或更廣的意涵。
面對喪親之痛、體能衰退、疾病纏身、離死不遠和依賴他人照顧的事實,我們很難安然面對時間流逝:我們會焦慮,會夢想返老還童,會因為失去獨立生活而自覺羞愧或低人一等。這些障礙似乎會把時間的流動性給堵塞住,製造出一種停滯的感覺,讓人覺得被僵固。在西方文化裡,中年和中年以後的人往往在自己和別人眼中顯得是個陌生人,是個模糊人物。不過,隨著現代文化一些強烈偏見(如相信「進步」會使舊事物過時,「新」勝於「舊」、「年輕」勝於「年老」等)逐漸被侵蝕,我們社會對老年的惶恐不安和逃避老年的鴕鳥心態也逐漸降低。愈來愈多人願意正視這個有趣的真理:老年人是我們中間的一員。
科學研究和醫學科技無疑將會繼續改寫人類生命的生物可能性,但它們永不可能把我們從種種必然的侷限性中給解放出來。無影無形的「時間」大概是最謎樣的一種侷限性。老去是生活在時間中的必然結果。我們總是在某一時刻誕生到這個世界,然後又會在後來某個未知的時刻離開這世界,並註定會在一生中經歷一些重大的變化。對個人乃至於群體,時間都會帶來形式與環境的改變。荷蘭人類學家范根內(Arnold van Gennep)在《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 1908)一書中指出:「每個人都總是有新的門檻要跨過:冬與夏 的門檻、季與年的門檻……出生的門檻、青春期的門檻、成熟的門檻、死亡的門檻,再來還有(對信徒來說如此)死後生命的門檻。」
雖然老化設定了生死的大哉問,但它卻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或毫不含糊的答案。誠如英國作家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在《長老的藝術》(The Art of Growing Old, 1944)一書裡指出的:「如果到六十歲我們還不明白生命是一個弔詭與矛盾的結,不知道我們的每個行為裡糅雜了多少的善與惡,不知道我們的女主人真理女士(Lady of Truth)性格有多麼妥協,那就表示我們是白老了。」有關老去的道德真理與靈性真理都是可能獲得和必須獲得的,但它們並沒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穿的尺碼。
要讓道德真理和靈性真理成為個人能合穿,這些真理必須是從特定文化的歷史布料裡剪裁出來,先經過個人經驗來量身訂造,再透過「朝聖者」的靈性演化過程給縫紉起來。八十出頭時的弗羅麗達.史考特—麥斯威爾(Florida Scott-Maxwell)在《我日子的尺度》(The Measure of My Days, 1968)裡說過:「我們這些老者知道老年所意味的並不只是失能。那是一種強烈和多樣性的體驗,有時幾乎不是我們所能承受,但又需要我們去細細品味。如果那是一趟漫長的失敗,那它也是一場勝利,對時間的初學者來說充滿意義,哪怕它不是那些無法走出得夠遠的人所能承擔。」用更斯多噶派的語言來說,長老(growing old)並不光是年歲的累積。「年齡並不重要,」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 1919)裡說過,「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以訓練有素的韌性,面對人生的諸般現實,並在內心鼓起勇氣加以應對。」《老年之書》(The Book of Aging)的編選方針正是要擴大讀者的能力,來面對和應對晚年生活的挑戰與契機。
人本主義老人學 (humanistic gerontology)和社會老人學(social gerontology)近年最有趣的一個發現,大概就是這個:不分年紀老少,創造性始終是成長的有力泉源。雖然創造性通常都會體現在一件具體的事物上(如一幅畫、一首詩、一本書或一件家具)但也常常可以體現在不那麼具體的結果:個人或群體自我意象的改變;對於一個人該如何過生活的理解的改變;一種長期關係的深化;更瞭解到自己在家庭、一個宗教群體或自然界裡的地位。
正如美國學者暨作家卡斯滕鮑姆(Robert Kastenbaum)在《世代》(Generations, 1991)一書中指出的,創造性大概是「老年人對生命侷限性和不確定性最有力的回應……事實上,創造活動包含的歡樂與活力可以以其自身的方式,勝過衰弱的入侵與時間不捨晝夜的流逝……而如果生命的每一瞬間都是一種過渡、一種變遷與衰壞,那這種經驗的創造性整合,不是也要求人去珍惜已過去的時光和擁抱尚未來到的時光?」把這番話用在長老的工作上,創造性(它涉及肯定生命和願意冒險)所要求的便是一個人在不斷改變的內在與外在環境中,持續地與侷限性角力。
《老年之書》鼓勵讀者進行這一類與天使的角力。全書共分九章,各章的主題分別象徵和闡明老年的歡樂、神祕、痛苦,以及人追求自我認知的理念和力求把人生歲月活得充實的抱負。每一章的詩文選都大致分為幾單元,每一單元的內在關連性會在章前的前言有所說明。換言之,編者在每一章一開始都會交代他們是根據什麼理由安排觀念、意象與感情的移動推進。不過,入選的詩文都是獨立的文本,完全容許讀者自行作出詮釋和反應。
在為每一章選定主題時,我們力求迴避一些僵固的範疇,以免讓人誤以為,老年所應該追求的是一些抽象和靜態的目標,如智慧、健康、靈性或休閒等。另外,我們也迴避一些對立的範疇,如得╱失、健康╱疾病、工作╱休閒、年輕╱年老,生╱死等。
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對老年的許多文化盲點,都是源於中產階級的刻板印象,源自細緻思考而雅好文化的二元論(例如「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很多人都無法站在年輕、健康、事業成功的主流價值觀之外理解自己的經驗。傳統智慧固然無法再讓人信服,但刻版印象卻會模糊想像力。兩者皆未能提供予人自我更新的象徵途徑,又會抑制我們對日常生活簡單真實(梭羅〔Thoreau〕稱之為「繁花盛放的當下時刻」)的鑑賞力,透過把一些常被認為是對立的觀念與意象並置,本書設法建構出一些可以引發驚奇、張力、弔詭、曖昧和矛盾的範疇。
本書把許多不同或相反的觀點共冶一爐(有時甚至同一位作者也會表現出分歧觀點),以鼓勵讀者多接觸不同的觀念或心緒。例如,本書之所以會收錄好幾段《傳道書》的文字,便是因為它包含著豐富的文學對話,讓懷疑主義和虔誠心態各有發聲的機會,正如美國古典學家佩里(T. A Perry)在《與傳道者對話》(Dialogues with Kohelet, 1993)一書所力主的,《傳道書》會提出「一切人類努力最終皆屬徒勞」這個命題,不是把它當成一個結論,而是視之為一種可辯論的立場。所以,它一方面強調時間的流逝會吞噬一切歡樂與成就,另一方面又強調上帝把萬物創造得美好和各有其時。
《老年之書》想要呈現的多種多樣的經驗與抱負,不是有關老年與人類精神的單一真理,正如弗羅麗達.史考特—麥斯威爾所說的:「我懷疑,老年人最在乎的莫過於真理,而他們無法找到,說不定,真理是紛紜的,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尋找屬於自己的真理。」在本書中,讀者既會找到失望、愚蠢、貪婪和未得實現的渴望的表述,也會找到成功、喜樂、平和與智慧的意象。本書的詩文選是要提供一種創造性對話的精神,以鼓勵個人或社會就有關老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進行討論。
本書挑選的詩文許多都是來自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傳統,也有許多是立足於美國和歐洲的文化史。我們也從其他文化、宗教傳統和族裔背景大量取樣。所以,讀者除了會讀到許多熟悉的作品(如莎士比亞的第七十三首十四行詩和西塞羅的〈論老年〉),還會碰到許多始料不及的篇章,如非洲民間故事、伊斯蘭詩歌、古希伯來警語、歷代醫學作品、個人日記的片段和當代佛教僧人的開示。
除詩歌、小說和戲劇外,我們也收錄了一些宗教聖典的文字,哲學思辨、報章訪談記、書簡、日記、雜文、諷刺詩,以及科學與醫學作品。本書既有莎孚(Sappho)、但丁、葉慈這些大作家的作品,但也有一些感人至深的聲音是來自讀書不多的發聲者,如美國黑奴亞歷山大(Gus Alexander)。
除了在文化幅度與文類幅度上涵蓋廣泛,本書在歷史幅度上同樣涵蓋廣泛。人們常常以為,在十九世紀以前,幾乎無人為文討論過老去和老年的課題。這只有部分是事實,沒錯,不管在科學探索、醫學、哲學思辨、個人沉思,以及文學藝術的表達上,老邁成為一個獨立課題的時間不超過一百五十年。然而,因為人們有關時間的觀點總是鑲嵌在他們有關社會、大自然與宇宙的更大觀點之中,是以老邁的課題幾乎見於所有的歷史階 段與所有的人類文化。事實是,在歷史上,一個文化如何看待老年的意義,總是離不開該文化對人生整體的看待方式。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