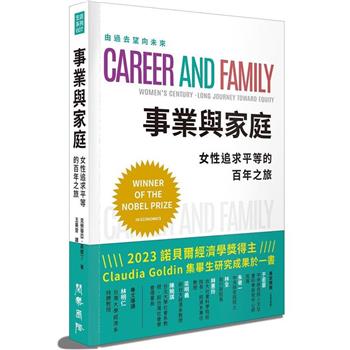第一章
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現在的夫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掙扎著平衡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就整個國家來說,我們正意識到「照護」(caregiving)對現今以及未來世代的重要性和價值。我們開始充分意識到照護的成本,包括失去的收入、事業的停滯不前、夫妻(不論是異性或同性)之間的權衡取捨,以及對於單身母親和父親所造成的沉重壓力。我們在新冠疫情前就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但是新冠疫情更凸顯了事情的嚴重性。
1963年,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寫到受過大學教育女性成為全職主婦的挫折感時提到,她們的問題「沒有名字」(has no name)。60年後,大多數大學畢業女性都已步上事業軌道,但是她們的待遇和升遷相對於和她們同時畢業的男性來看,就像遭到了橫向撞擊,停滯不前。她們也同樣有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problem with no name)。
但同時,她們的問題卻被冠予各種不同的名字:性別歧視、性別偏見、玻璃天花板、媽媽軌道;立即的解決方案也應運而生,我們應該訓練女性變得更有競爭性,以及更懂得談判;我們應該揭露經理人們「隱而不宣的偏見」;政府應該要強制企業董事會實施性別平權以及同工同酬的工作倫理。
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性比以往更大聲疾呼,希望找出可能的答案。她們的關切散落在各個媒體的標題和書的封面上。她們需要更多的動力嗎? 她們需要更加挺身而進(lean in)嗎?為什麼女性無法像男性以同樣的速度攀爬事業階梯?為什麼她們無法獲得與年資和經驗相稱的待遇?
許多女性心中存著更多只能和十分親近的人分享的的私人疑慮。你應該和一個事業和你一樣忙碌的人約會嗎?你是否應該延遲成家的時間,即使你知道你想要有個家?如果35歲還沒找到伴侶,你是否應該考慮凍卵?你是否願意為了撫養小孩,暫時放棄你自從考大學能力測驗(SAT)以來就建立的遠大事業目標?如果不,那麼誰要每天替小孩帶便當、在小孩游泳練習完後接小孩回家,接聽學校護士打來的,令人緊張的電話。
女性持續感覺沒有被公平對待。她們在職位上落後,待遇也不如她們的先生和男同事。她們被告知這些結果是咎由自取,因為她們不夠有競爭心、談判不夠有效率,她們未能爭取會議桌上的一席,當她們爭取到一席時,卻又要得不夠多。但此同時,女性又被告知,這些其實不是她們的問題(即使有時候的確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她們其實是被占了便宜,被騷擾了,被摒棄於男孩俱樂部的大門之外。
這些因素的確都存在。但它們是事情的根源嗎?它們加總的效果真能解釋男性與女性待遇和事業上的差距嗎?如果這些問題全都神奇地解決了,那麼這個世界上的男女、夫妻和年輕的父母,是否就會看起來完全不同呢?或者它們其實是集體的「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雖然大眾媒體和私人對談已把這個重要的問題帶到鎂光燈的焦點下,但我們對這個規模之大、綿延時間之長的性別差距卻沒有給予足夠關注。某個公司受到小小的處分、某個女性成功進入了董事會、少數一些科技新貴領導人實行陪產假;這些解答,就經濟的層面來說,如同把OK繃丟給得黑死病的人一樣。
上述的反應並無法消弭性別待遇差異的問題,它們也無法為兩性平權提供解答,因為它們只是治標不治本。它們無法真的協助女性,在同樣程度上,像男性一樣達成同時擁有家庭和事業的目標。如果要消弭或甚至只是縮小待遇差距,我們首先必須深入探討這些挫折的根源,並且給這個問題一個比較正確的名字: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我希望當你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新冠疫情已經消退,我們也從中學到艱困但難得的一課。新冠疫情放大了一些問題,加速了另外一些,也暴露了一些長期存在但一直潛伏的問題。但其實照護與工作之間的拉鋸戰早在我們面對這個全球災難性疾病之前就已存在了。達成並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旅程早在百年前就已啟動。
整個20世紀大半的時間,性別歧視是女性無法擁有事業的主要障礙。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歷史文獻鐵證如山地呈現出這些歧視––––雇用和待遇歧視的實際證據。1930年代後期,公司的主管告訴民調機構,「放款工作不適合女性」,「這項工作(指汽車銷售)需要和大眾接觸…無法任用女性」以及「不會把女性放在銷業務代表售工作上」。當時正是大蕭條結束的時候。但即使是1950年代,勞動市場吃緊的時候,公司的代表們還是會發出淡然的聲明,「不雇用年輕的母親」,「不鼓勵已婚有年輕小孩的女性回來上班」,以及「懷孕視同自動辭職,雖然當小孩長大些,譬如初中的時候,我們還是十分歡迎這些女性回來。」
婚姻禁令(marriage bars)––––法律或公司政策限制已婚婦女的聘僱––––直到1940年代都還甚囂塵上,它們演變成懷孕禁令(pregnancy bars),將有嬰兒和年輕的婦女排除在工作的大門外。學術單位和政府機構有裙帶關係禁令(nepotism bars)。無數的工作有性別、婚姻狀況的限制,當然還有,種族的限制。
今天,我們看不到這樣明目張膽的歧視。數據顯示,儘管薪資和就業的歧視仍然存在,但是相對要少得多。這並非意味著女性不須再面對歧視和偏見,或者是工作場所已不存在性騷擾或性侵害。全國性的#MeToo運動,並非無的放矢。1990年代後期,莉莉.萊德貝特(Lilly Ledbetter)向公平機會就業委員會對固特異輪胎提起性騷擾案,並且獲得訴訟的權利。那對她來說是一個真正的勝利,但是她在被恢復主管的職位之後,放棄了訴訟。萊德貝特在事情發生了幾年後才提出訴訟。由於男性下屬對她的歧視行為,以及最高主管對下屬的性別歧視視而不見,好幾年的時間,萊德貝特都獲得非常低的績效評等,也幾乎沒有加薪。在她的個案中,她和同輩之間的待遇差距,100%來自性別歧視。
那麼何以當工作上的性別平權似乎已觸手可及,而從所未見的更多職位也對女性開放的同時,待遇差距仍然屹立不搖。同樣的工作,女性真的得到比較低的報酬嗎?大體上來說,差距不再這麼大。現今,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歧視僅占整體待遇差距的一小部分。今天的問題不一樣。
有些人把性別待遇差距歸於「職業隔離」(occupational segregations),意思是說男性或女性選擇或被導引進入的職業,原本就有性別差異(好比是醫生vs.護士,或是教授vs.教師),而這些工作的待遇本來就有差距,但是我們的數據卻顯示了不同的故事。美國人口普查登記的500項工作顯示,2/3的待遇差距發生在同一項工作中。即使女性遵循男性職業的分佈––––也就是如果女性是醫生,男性是護士––––也只能弭平1/3的差距。因此,我們從實證的觀點可以知道,待遇差異另有原因。
我們可以從縱向數據––––追蹤個人生活和待遇的資料––––中看到,大學或研究所剛畢業時,男性和女性的薪資幾乎相同。在工作的前幾年當中,大學畢業生和新科MBA們的薪資差異和所就讀的科系和選擇的職業相關,但是和男女性別無關。男性和女性的起跑點是公平的,他們有類似的機會,但不同的選擇讓他們在一開始時,薪資就有微小的差距。
男女巨大的薪資差距,大約在大學畢業十年之後,才凸顯出來。他們在職場不同的行業,為不同的公司工作,這些差距通常在小孩出生後的一、兩年開始,而且幾乎都是對女性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男女薪資差距其實在女性結婚後就開始擴大。
女性事業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家庭和經濟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永遠無法瞭解性別待遇差距的根源,除非我們能夠瞭解這個表象背後所隱藏更大問題的軌跡。性別待遇差距來自事業差距,而事業差距則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夫妻不平等(couple inequality)。要深切掌握這些意味著甚麼,我們需要來一趟百年之旅,瞭解美國女性在美國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隨著時間轉變。
我們的重點將放在大學畢業的女性,因為她們最有機會成就事業,而且她們的人數也已擴張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2020年的資料顯示,有45%二十五歲的女性已經或即將從四年制的大學畢業。相較之下,男性只有36%。女性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並非總是遙遙領先。長時間以來,因為各種的因素,女性上大學和從大學畢業都面臨很大的挑戰。1960年,四年制大學的男女比例是1.6比1。但是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事情開始有了轉變,到1980年,男性的優勢已經消失,女性從四年制大學畢業的人數正式超過男性。
不僅大學的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女性還不斷設立更高的目標;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積極地追求學士後的學位,以便取得更具挑戰的工作。2007年在經濟大衰退之前,有23%的女性取得最高的律師、博士、醫生或MBA等的專業學位,比前四十年多出40%,男性的百分比則是四十年來都維持在30%左右。有計畫地取得長期、高薪和高成就感的女性不斷增加,這些持續努力的成就,也成為她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她們大多數都有小孩––––是自嬰兒潮以來人數最多的一群。80%目前40歲中期或晚期的大學畢業女性都至少生過一個小孩,領養小孩的則大約有1.5%。15年前,大約只有73%的大學畢業女性,在45歲左右時生育過一個以上的子女。換句話說,1970年代誕生的大學畢業女性較195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畢業女性有較高的生育率。現在50多歲,同時擁有成功事業和家庭的女性,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包括凱莎.蘭斯.博頓斯(Keisha Lance Bottoms),麗茲.錢尼(Liz Cheney),譚美.達克沃斯(Tammy Duckworth),莎曼珊.包爾(Samantha Power)以及洛瑞.特拉漢(Lori Trahan)。
大學畢業女性不再接受只有事業沒有家庭的選擇,也不再滿足於只有家庭沒有工作。大體上來說,大學畢業女性希望在兩個領域裡都能成功,但是要達成這個目標除了需要在各種時間衝突上折衝協調,也必須做出許多困難的決定。
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我們每個人擁有的時間都相同,在分配時都要做出困難的決定。大學畢業女性企圖獲致家庭和事業成功的基本問題就來自於時間衝突。事業成功通常意味著在事業初期,你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但這正好也是你「應該」生小孩的時候,享受家庭生活也同樣需要相當的時間。這些決策的後果深遠,而且很難回頭弭補。五十年前,一位成功的執行長和三個小孩的媽媽給後進的建議是,「的確很難––––但就去做吧!」
我們總是在做抉擇,像是參加派對或是讀書,選簡單的課或是較難的課。有些抉擇的後果比較重大,像是早點結婚或晚點結婚;讀研究所或直接工作;現在生小孩,以免將來生不出來;花時間在小孩還是在客戶身上。這些重大的時間分配的決定,從大學畢業女性拿到學士文憑時就開始了。
才不久前,結婚的年齡驚人的早。1970年前,女性結婚的年齡中位數是23歲,緊接著,第一個小孩隨即出生。早婚通常排除了女性繼續深造的可能性,至少在最初幾年。新婚夫妻通常會因為先生,而非太太的工作搬家。女性通常無法最大化自己本身的事業前景,她們會為了家庭的整體福利,犧牲自己的事業。
對於畢業於1940到1960年代的女性而言,遲婚是一種挑戰。一旦對象固定,且已發展出認真(和性)的關係,早婚是避免未婚生子的最佳保險。在一個沒有女性可以控制的有效避孕方式的世界裡,選擇相當有限。
1961年,避孕藥發展出來,而且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大量已婚的女性也開始購買。但是國家法律和社會習俗不允許把避孕藥賣給未婚的女性。1970年代左右,這些限制開始崩塌,給予大學畢業女性規畫自己生活的嶄新能力;第一項障礙消除了。她們可以報名參加耗時的學士後研究課程和訓練,婚姻和小孩可以稍稍延遲;她們可以先為長久的事業奠定一些基礎。
事情至此有了急劇的變化。1970年後,女性結婚的年齡逐年攀升,現今女性第一次婚姻的年齡中位數是28歲。
雖然時間限制的難題解決了,別的問題卻又隨之而起。學士後研究課程開始得較遲而且年限較長。例如在學術、保健、法律以及顧問等的專業領域裡,第一次的升遷時間不斷地被延後;時間的堆疊與拖延造成另外一個必須折衝協調的時間衝突。
十年前,人們的第一個升遷大約發生在三十出頭歲,近年來則延遲到30歲中晚期。人們無法在第一個升遷後––––不論是合夥人、終身教職或其他晉升––––再生第一個小孩,小孩經常會顛覆事業,而事業則顛覆女人生育小孩的能力。
時機稍縱即逝。對於想要有家庭的女性而言,等到三十歲中期再來生小孩,無疑會危及成功擁有小孩和家庭的機會。大學畢業女性試著用各種輔助生殖技術克服難關。最近剛滿45歲的這一群女性,擁有小孩的百分比驚人的高。出生率的上升並無法降低努力過卻失敗的女性的挫折感、悲傷和身體上的疼痛。對於那些成功的人來說,這也不代表她們可以一直保持她們的事業。
儘管困難重重,許多的改變都仍朝著正面發展,帶我們更接近女性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性別平權。女性更能掌控自己的生育權,婚姻較晚開始但維持得較久,女性現在佔大學畢業生人數壓倒性的多數,許多更進入學士後的研究課程,並且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她們成為許多最好的公司、組織和部門爭相徵聘的對象。那,然後呢?
就在女性的事業有機會茁壯長大,她又同時擁有小孩時,最終時間的衝突又會開始浮現;小孩要花時間,工作要花時間。即使最富有的夫妻也無法外包所有照顧小孩的工作,再說,如果你不想要養育和愛自己的小孩,何必要把他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呢?
時間的限制下,夫妻之間最基本的協商就是誰要對家庭待命,也就是,誰可以在緊要關頭時立刻離開辦公室;這可以是雙親中的任何一個。夫妻平權的結果應該是各佔50%。但是家庭會因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很大!現今的夫妻,比以往都更瞭解這個問題。
隨著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的野心增加,大多數事業的某個部份變得更清晰可見、更加的關鍵。工作,對於許多在事業軌道上的人來說,是貪婪的。能夠加班,同時在週末,甚至夜晚也願意工作的人,待遇要多很多––––多的程度,如果換算起來,就連時薪也相對變高了。
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工作的貪婪(the greediness of work)意味著,有小孩的夫妻或者有其他有照顧他人責任的人能夠因分工(specialization)而受益。這項分工並非意味著將時光倒回到《天才小麻煩》(Leave It to Beaver)男主外女主內的世界。在這裡的分工,女性仍舊可以追求較有挑戰的工作,但是夫妻之一必須要有一方對家庭隨時待命,在片刻通知之內,就隨時可以離開辦公室或工作場所。這個人的職位要比較有彈性,而且通常不會被期待在晚上10點回email或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這個人也不需要因為購併案(M&A)而錯過小孩的足球賽;另外一方則必須完全相反的,對公司隨時待命。不同的分工對於升遷和加薪的影響潛力顯而易見。
專業人士和經理人的工作一向都是貪婪的工作。律師一向是焚膏繼晷;以智力產出受評斷的學術研究者,經常通宵達旦地思考,鮮少在一日將盡時就關閉其大腦;而大多數醫生和獸醫也都有過一天24小時,一週7天(24/7)的待診經驗。
自1980年代早期開始,貪婪工作的價值隨著所得不平等而增加,所得分配最頂端的人,收入急遽增加,跳得最高的員工得到最大的獎勵,最需要長時間和最沒有彈性的工作,待遇不成比例的高,其他工作的待遇則停滯不前。過去幾十年來,原本女性就較難進入的工作領域,像是財務金融等,正是薪資增加最多的地方。從頭到尾追蹤案子發展、負責困難的模型、參加每一個會議和深夜晚餐的私募股權合夥人,最有機會拿到豐厚的紅利和夢想的升遷。
儘管女性的資歷和職位有改善,但是貪婪工作的出現導致所得不平等的加劇,可能是男女大學畢業生的待遇差距卻不見改善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1980和1990年代初期,大學畢業生性別待遇差距較整個母群裡男女待遇差異較大的原因。女性力爭上游,卓然有成,但是卻在待遇平等上遇到強大的漩渦。
貪婪的工作也意味著夫妻平權會因為家庭整體收入的原因而被拋棄。當夫妻平權被丟出窗外的同時,性別平權也難以為繼(同性伴侶除外)。我們繼承的性別規範以多種方式得到強化,讓我們將較多的育兒責任分配給母親,較多的家庭照顧責任給成年的女兒。
我們可以來看一對我認識的夫妻伊莎貝爾(Isabel)和盧卡斯的例子。他們倆位都擁有大學文理學院的學位,也都繼續進修得到資訊科技的碩士學位。他們兩個同時受雇於一家,我們姑且命名為資訊服務(InfoServices)的公司。
資訊服務公司給他們每個人兩個選項。第一個,標準的工作時間,而且上下班的時間較有彈性。第二個,傍晚或週末可能需要隨時待命,雖然一整年下來,總工作時數不見得更多。為了要吸引願意在不確定的時間上班的人才,第二個工作的待遇要比第一個多出20%。公司選擇經理人時,也會以第二個人才庫為考慮對象。這是一個貪婪的工作,也是伊莎貝爾和盧卡斯起初的共同選項。同樣的有能力,同樣的沒有其他外在的責任,兩個人最初幾年享受同樣的工作職級和待遇。
接近三十歲時,伊莎貝爾決定她需要較多的彈性和空間,以便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生病的母親。她仍舊待在資訊服務公司,但是轉而選擇工作時數相同,但是上下班時間比較有彈性的工作。這個工作較不貪婪,但是待遇也就沒有那麼豐厚。
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現在的夫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掙扎著平衡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就整個國家來說,我們正意識到「照護」(caregiving)對現今以及未來世代的重要性和價值。我們開始充分意識到照護的成本,包括失去的收入、事業的停滯不前、夫妻(不論是異性或同性)之間的權衡取捨,以及對於單身母親和父親所造成的沉重壓力。我們在新冠疫情前就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但是新冠疫情更凸顯了事情的嚴重性。
1963年,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寫到受過大學教育女性成為全職主婦的挫折感時提到,她們的問題「沒有名字」(has no name)。60年後,大多數大學畢業女性都已步上事業軌道,但是她們的待遇和升遷相對於和她們同時畢業的男性來看,就像遭到了橫向撞擊,停滯不前。她們也同樣有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problem with no name)。
但同時,她們的問題卻被冠予各種不同的名字:性別歧視、性別偏見、玻璃天花板、媽媽軌道;立即的解決方案也應運而生,我們應該訓練女性變得更有競爭性,以及更懂得談判;我們應該揭露經理人們「隱而不宣的偏見」;政府應該要強制企業董事會實施性別平權以及同工同酬的工作倫理。
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性比以往更大聲疾呼,希望找出可能的答案。她們的關切散落在各個媒體的標題和書的封面上。她們需要更多的動力嗎? 她們需要更加挺身而進(lean in)嗎?為什麼女性無法像男性以同樣的速度攀爬事業階梯?為什麼她們無法獲得與年資和經驗相稱的待遇?
許多女性心中存著更多只能和十分親近的人分享的的私人疑慮。你應該和一個事業和你一樣忙碌的人約會嗎?你是否應該延遲成家的時間,即使你知道你想要有個家?如果35歲還沒找到伴侶,你是否應該考慮凍卵?你是否願意為了撫養小孩,暫時放棄你自從考大學能力測驗(SAT)以來就建立的遠大事業目標?如果不,那麼誰要每天替小孩帶便當、在小孩游泳練習完後接小孩回家,接聽學校護士打來的,令人緊張的電話。
女性持續感覺沒有被公平對待。她們在職位上落後,待遇也不如她們的先生和男同事。她們被告知這些結果是咎由自取,因為她們不夠有競爭心、談判不夠有效率,她們未能爭取會議桌上的一席,當她們爭取到一席時,卻又要得不夠多。但此同時,女性又被告知,這些其實不是她們的問題(即使有時候的確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她們其實是被占了便宜,被騷擾了,被摒棄於男孩俱樂部的大門之外。
這些因素的確都存在。但它們是事情的根源嗎?它們加總的效果真能解釋男性與女性待遇和事業上的差距嗎?如果這些問題全都神奇地解決了,那麼這個世界上的男女、夫妻和年輕的父母,是否就會看起來完全不同呢?或者它們其實是集體的「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雖然大眾媒體和私人對談已把這個重要的問題帶到鎂光燈的焦點下,但我們對這個規模之大、綿延時間之長的性別差距卻沒有給予足夠關注。某個公司受到小小的處分、某個女性成功進入了董事會、少數一些科技新貴領導人實行陪產假;這些解答,就經濟的層面來說,如同把OK繃丟給得黑死病的人一樣。
上述的反應並無法消弭性別待遇差異的問題,它們也無法為兩性平權提供解答,因為它們只是治標不治本。它們無法真的協助女性,在同樣程度上,像男性一樣達成同時擁有家庭和事業的目標。如果要消弭或甚至只是縮小待遇差距,我們首先必須深入探討這些挫折的根源,並且給這個問題一個比較正確的名字: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我希望當你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新冠疫情已經消退,我們也從中學到艱困但難得的一課。新冠疫情放大了一些問題,加速了另外一些,也暴露了一些長期存在但一直潛伏的問題。但其實照護與工作之間的拉鋸戰早在我們面對這個全球災難性疾病之前就已存在了。達成並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旅程早在百年前就已啟動。
整個20世紀大半的時間,性別歧視是女性無法擁有事業的主要障礙。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歷史文獻鐵證如山地呈現出這些歧視––––雇用和待遇歧視的實際證據。1930年代後期,公司的主管告訴民調機構,「放款工作不適合女性」,「這項工作(指汽車銷售)需要和大眾接觸…無法任用女性」以及「不會把女性放在銷業務代表售工作上」。當時正是大蕭條結束的時候。但即使是1950年代,勞動市場吃緊的時候,公司的代表們還是會發出淡然的聲明,「不雇用年輕的母親」,「不鼓勵已婚有年輕小孩的女性回來上班」,以及「懷孕視同自動辭職,雖然當小孩長大些,譬如初中的時候,我們還是十分歡迎這些女性回來。」
婚姻禁令(marriage bars)––––法律或公司政策限制已婚婦女的聘僱––––直到1940年代都還甚囂塵上,它們演變成懷孕禁令(pregnancy bars),將有嬰兒和年輕的婦女排除在工作的大門外。學術單位和政府機構有裙帶關係禁令(nepotism bars)。無數的工作有性別、婚姻狀況的限制,當然還有,種族的限制。
今天,我們看不到這樣明目張膽的歧視。數據顯示,儘管薪資和就業的歧視仍然存在,但是相對要少得多。這並非意味著女性不須再面對歧視和偏見,或者是工作場所已不存在性騷擾或性侵害。全國性的#MeToo運動,並非無的放矢。1990年代後期,莉莉.萊德貝特(Lilly Ledbetter)向公平機會就業委員會對固特異輪胎提起性騷擾案,並且獲得訴訟的權利。那對她來說是一個真正的勝利,但是她在被恢復主管的職位之後,放棄了訴訟。萊德貝特在事情發生了幾年後才提出訴訟。由於男性下屬對她的歧視行為,以及最高主管對下屬的性別歧視視而不見,好幾年的時間,萊德貝特都獲得非常低的績效評等,也幾乎沒有加薪。在她的個案中,她和同輩之間的待遇差距,100%來自性別歧視。
那麼何以當工作上的性別平權似乎已觸手可及,而從所未見的更多職位也對女性開放的同時,待遇差距仍然屹立不搖。同樣的工作,女性真的得到比較低的報酬嗎?大體上來說,差距不再這麼大。現今,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歧視僅占整體待遇差距的一小部分。今天的問題不一樣。
有些人把性別待遇差距歸於「職業隔離」(occupational segregations),意思是說男性或女性選擇或被導引進入的職業,原本就有性別差異(好比是醫生vs.護士,或是教授vs.教師),而這些工作的待遇本來就有差距,但是我們的數據卻顯示了不同的故事。美國人口普查登記的500項工作顯示,2/3的待遇差距發生在同一項工作中。即使女性遵循男性職業的分佈––––也就是如果女性是醫生,男性是護士––––也只能弭平1/3的差距。因此,我們從實證的觀點可以知道,待遇差異另有原因。
我們可以從縱向數據––––追蹤個人生活和待遇的資料––––中看到,大學或研究所剛畢業時,男性和女性的薪資幾乎相同。在工作的前幾年當中,大學畢業生和新科MBA們的薪資差異和所就讀的科系和選擇的職業相關,但是和男女性別無關。男性和女性的起跑點是公平的,他們有類似的機會,但不同的選擇讓他們在一開始時,薪資就有微小的差距。
男女巨大的薪資差距,大約在大學畢業十年之後,才凸顯出來。他們在職場不同的行業,為不同的公司工作,這些差距通常在小孩出生後的一、兩年開始,而且幾乎都是對女性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男女薪資差距其實在女性結婚後就開始擴大。
女性事業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家庭和經濟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永遠無法瞭解性別待遇差距的根源,除非我們能夠瞭解這個表象背後所隱藏更大問題的軌跡。性別待遇差距來自事業差距,而事業差距則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夫妻不平等(couple inequality)。要深切掌握這些意味著甚麼,我們需要來一趟百年之旅,瞭解美國女性在美國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隨著時間轉變。
我們的重點將放在大學畢業的女性,因為她們最有機會成就事業,而且她們的人數也已擴張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2020年的資料顯示,有45%二十五歲的女性已經或即將從四年制的大學畢業。相較之下,男性只有36%。女性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並非總是遙遙領先。長時間以來,因為各種的因素,女性上大學和從大學畢業都面臨很大的挑戰。1960年,四年制大學的男女比例是1.6比1。但是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事情開始有了轉變,到1980年,男性的優勢已經消失,女性從四年制大學畢業的人數正式超過男性。
不僅大學的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女性還不斷設立更高的目標;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積極地追求學士後的學位,以便取得更具挑戰的工作。2007年在經濟大衰退之前,有23%的女性取得最高的律師、博士、醫生或MBA等的專業學位,比前四十年多出40%,男性的百分比則是四十年來都維持在30%左右。有計畫地取得長期、高薪和高成就感的女性不斷增加,這些持續努力的成就,也成為她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她們大多數都有小孩––––是自嬰兒潮以來人數最多的一群。80%目前40歲中期或晚期的大學畢業女性都至少生過一個小孩,領養小孩的則大約有1.5%。15年前,大約只有73%的大學畢業女性,在45歲左右時生育過一個以上的子女。換句話說,1970年代誕生的大學畢業女性較195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畢業女性有較高的生育率。現在50多歲,同時擁有成功事業和家庭的女性,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包括凱莎.蘭斯.博頓斯(Keisha Lance Bottoms),麗茲.錢尼(Liz Cheney),譚美.達克沃斯(Tammy Duckworth),莎曼珊.包爾(Samantha Power)以及洛瑞.特拉漢(Lori Trahan)。
大學畢業女性不再接受只有事業沒有家庭的選擇,也不再滿足於只有家庭沒有工作。大體上來說,大學畢業女性希望在兩個領域裡都能成功,但是要達成這個目標除了需要在各種時間衝突上折衝協調,也必須做出許多困難的決定。
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我們每個人擁有的時間都相同,在分配時都要做出困難的決定。大學畢業女性企圖獲致家庭和事業成功的基本問題就來自於時間衝突。事業成功通常意味著在事業初期,你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但這正好也是你「應該」生小孩的時候,享受家庭生活也同樣需要相當的時間。這些決策的後果深遠,而且很難回頭弭補。五十年前,一位成功的執行長和三個小孩的媽媽給後進的建議是,「的確很難––––但就去做吧!」
我們總是在做抉擇,像是參加派對或是讀書,選簡單的課或是較難的課。有些抉擇的後果比較重大,像是早點結婚或晚點結婚;讀研究所或直接工作;現在生小孩,以免將來生不出來;花時間在小孩還是在客戶身上。這些重大的時間分配的決定,從大學畢業女性拿到學士文憑時就開始了。
才不久前,結婚的年齡驚人的早。1970年前,女性結婚的年齡中位數是23歲,緊接著,第一個小孩隨即出生。早婚通常排除了女性繼續深造的可能性,至少在最初幾年。新婚夫妻通常會因為先生,而非太太的工作搬家。女性通常無法最大化自己本身的事業前景,她們會為了家庭的整體福利,犧牲自己的事業。
對於畢業於1940到1960年代的女性而言,遲婚是一種挑戰。一旦對象固定,且已發展出認真(和性)的關係,早婚是避免未婚生子的最佳保險。在一個沒有女性可以控制的有效避孕方式的世界裡,選擇相當有限。
1961年,避孕藥發展出來,而且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大量已婚的女性也開始購買。但是國家法律和社會習俗不允許把避孕藥賣給未婚的女性。1970年代左右,這些限制開始崩塌,給予大學畢業女性規畫自己生活的嶄新能力;第一項障礙消除了。她們可以報名參加耗時的學士後研究課程和訓練,婚姻和小孩可以稍稍延遲;她們可以先為長久的事業奠定一些基礎。
事情至此有了急劇的變化。1970年後,女性結婚的年齡逐年攀升,現今女性第一次婚姻的年齡中位數是28歲。
雖然時間限制的難題解決了,別的問題卻又隨之而起。學士後研究課程開始得較遲而且年限較長。例如在學術、保健、法律以及顧問等的專業領域裡,第一次的升遷時間不斷地被延後;時間的堆疊與拖延造成另外一個必須折衝協調的時間衝突。
十年前,人們的第一個升遷大約發生在三十出頭歲,近年來則延遲到30歲中晚期。人們無法在第一個升遷後––––不論是合夥人、終身教職或其他晉升––––再生第一個小孩,小孩經常會顛覆事業,而事業則顛覆女人生育小孩的能力。
時機稍縱即逝。對於想要有家庭的女性而言,等到三十歲中期再來生小孩,無疑會危及成功擁有小孩和家庭的機會。大學畢業女性試著用各種輔助生殖技術克服難關。最近剛滿45歲的這一群女性,擁有小孩的百分比驚人的高。出生率的上升並無法降低努力過卻失敗的女性的挫折感、悲傷和身體上的疼痛。對於那些成功的人來說,這也不代表她們可以一直保持她們的事業。
儘管困難重重,許多的改變都仍朝著正面發展,帶我們更接近女性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性別平權。女性更能掌控自己的生育權,婚姻較晚開始但維持得較久,女性現在佔大學畢業生人數壓倒性的多數,許多更進入學士後的研究課程,並且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她們成為許多最好的公司、組織和部門爭相徵聘的對象。那,然後呢?
就在女性的事業有機會茁壯長大,她又同時擁有小孩時,最終時間的衝突又會開始浮現;小孩要花時間,工作要花時間。即使最富有的夫妻也無法外包所有照顧小孩的工作,再說,如果你不想要養育和愛自己的小孩,何必要把他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呢?
時間的限制下,夫妻之間最基本的協商就是誰要對家庭待命,也就是,誰可以在緊要關頭時立刻離開辦公室;這可以是雙親中的任何一個。夫妻平權的結果應該是各佔50%。但是家庭會因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很大!現今的夫妻,比以往都更瞭解這個問題。
隨著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的野心增加,大多數事業的某個部份變得更清晰可見、更加的關鍵。工作,對於許多在事業軌道上的人來說,是貪婪的。能夠加班,同時在週末,甚至夜晚也願意工作的人,待遇要多很多––––多的程度,如果換算起來,就連時薪也相對變高了。
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工作的貪婪(the greediness of work)意味著,有小孩的夫妻或者有其他有照顧他人責任的人能夠因分工(specialization)而受益。這項分工並非意味著將時光倒回到《天才小麻煩》(Leave It to Beaver)男主外女主內的世界。在這裡的分工,女性仍舊可以追求較有挑戰的工作,但是夫妻之一必須要有一方對家庭隨時待命,在片刻通知之內,就隨時可以離開辦公室或工作場所。這個人的職位要比較有彈性,而且通常不會被期待在晚上10點回email或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這個人也不需要因為購併案(M&A)而錯過小孩的足球賽;另外一方則必須完全相反的,對公司隨時待命。不同的分工對於升遷和加薪的影響潛力顯而易見。
專業人士和經理人的工作一向都是貪婪的工作。律師一向是焚膏繼晷;以智力產出受評斷的學術研究者,經常通宵達旦地思考,鮮少在一日將盡時就關閉其大腦;而大多數醫生和獸醫也都有過一天24小時,一週7天(24/7)的待診經驗。
自1980年代早期開始,貪婪工作的價值隨著所得不平等而增加,所得分配最頂端的人,收入急遽增加,跳得最高的員工得到最大的獎勵,最需要長時間和最沒有彈性的工作,待遇不成比例的高,其他工作的待遇則停滯不前。過去幾十年來,原本女性就較難進入的工作領域,像是財務金融等,正是薪資增加最多的地方。從頭到尾追蹤案子發展、負責困難的模型、參加每一個會議和深夜晚餐的私募股權合夥人,最有機會拿到豐厚的紅利和夢想的升遷。
儘管女性的資歷和職位有改善,但是貪婪工作的出現導致所得不平等的加劇,可能是男女大學畢業生的待遇差距卻不見改善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1980和1990年代初期,大學畢業生性別待遇差距較整個母群裡男女待遇差異較大的原因。女性力爭上游,卓然有成,但是卻在待遇平等上遇到強大的漩渦。
貪婪的工作也意味著夫妻平權會因為家庭整體收入的原因而被拋棄。當夫妻平權被丟出窗外的同時,性別平權也難以為繼(同性伴侶除外)。我們繼承的性別規範以多種方式得到強化,讓我們將較多的育兒責任分配給母親,較多的家庭照顧責任給成年的女兒。
我們可以來看一對我認識的夫妻伊莎貝爾(Isabel)和盧卡斯的例子。他們倆位都擁有大學文理學院的學位,也都繼續進修得到資訊科技的碩士學位。他們兩個同時受雇於一家,我們姑且命名為資訊服務(InfoServices)的公司。
資訊服務公司給他們每個人兩個選項。第一個,標準的工作時間,而且上下班的時間較有彈性。第二個,傍晚或週末可能需要隨時待命,雖然一整年下來,總工作時數不見得更多。為了要吸引願意在不確定的時間上班的人才,第二個工作的待遇要比第一個多出20%。公司選擇經理人時,也會以第二個人才庫為考慮對象。這是一個貪婪的工作,也是伊莎貝爾和盧卡斯起初的共同選項。同樣的有能力,同樣的沒有其他外在的責任,兩個人最初幾年享受同樣的工作職級和待遇。
接近三十歲時,伊莎貝爾決定她需要較多的彈性和空間,以便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生病的母親。她仍舊待在資訊服務公司,但是轉而選擇工作時數相同,但是上下班時間比較有彈性的工作。這個工作較不貪婪,但是待遇也就沒有那麼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