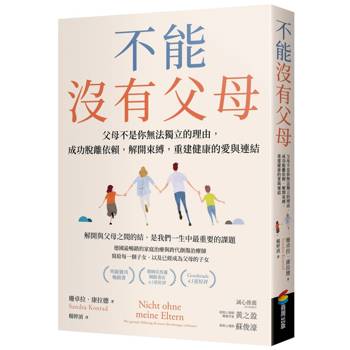在父母的面前我就像個小孩子,常常被各種情緒淹沒。
父母是我的責任。
我對父母很失望,因為他們始終不是我想像中的父母。
我們之間沒有界線。
我必須成為他們的驕傲。
向他們透露自己真實的感受,我根本做不到。
父母最清楚什麼對我有利。
我知道怎麼做對他們最好。
與父母相處對我來說是苦差事,即便如此,我仍要求自己固定與他們碰面。
我不再和父母聯繫,因為他們對不起我。
無法滿足父母讓我總是心懷愧疚。
和他們的關係是一場絕世抗爭。
我是受害者,他們是凶手,搗毀了我生活。
我期待他們認同我所有的決定,否則我會難過。
就算我告訴他們自己小時候被傷害得有多深,他們也絕對不會向我道歉。
我必須不斷在父母面前捍衛自己。
我不能說出或做出任何一點傷害他們的事。
父母是我在人際關係中的主要爭執點。
他們的感受和需要總是比我自己的還重要。
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我的父母並不了解我。
如果我順應自己的心過生活就可能失去父母的歡心。
我不想讓他們受苦,能讓他們快樂的事,我會竭盡所能完成。
我無法心平氣和地與父母交流內心的想法。
我常常想向他們證明自己是對的。
我希望父母最終能變成我所渴望的樣子,而且遲遲無法放下這執念。
我的所做所為始終和父母的願望背道而馳。
我不做任何會讓父母不開心的決定。
我和父母之間懸而未解之題,成了我與他人關係之中的爭執點。
我害怕知道父母的反應,所以閉口不談生活裡的大事。
如果父母不在人世了該有多好,我恨他們。
如果父母不在了,我也會失去活下去的勇氣和喜悅。
如果你也認同上述任何一句話,表示你仍然糾結著自己與父母的關係,還沒有辦法澈底放下。
這本書正是為你而寫:書中將告訴你,一個人的成熟度會如何影響自身的(人際關係)生活,並且特別為你指出解開糾結的道路。你的個人蛻變將置於首位,你的家庭關係並不會因此蒙上陰影。
這本書無法取代心理治療,但是能幫助你更認識自己、了解父母和你的互動關係,幫助你擺脫愧疚感、憤怒和失望。每一個章節會帶你反思、重新定位自己,並且和父母(包含你身邊的人)建立起更成熟的關係,是這本書最想要達成的目標。
我診間裡的個案故事訴說著脫離父母成為成熟大人過程中的難題是如何形成的,要怎麼克服這些難題。你可能會在某幾個案例中看見自己的身影,甚至挑起你難過或憤怒的情緒。請不要擔心!正因為我們有所感才會出現情緒。在理想的情況下,感受會引發行動,並朝著對我們有益的方向前進。
離開父母獨立是一段漫長的過程。有時會進展神速,但多數時候是一步步地推進。我祝福你在這條路上能認識自己、保持勇氣,並給自己無比的耐心。
我希望你鼓起勇氣擺脫種種束縛;因為,離開父母並不代表愛變少了,而是能用更成熟的方式去愛。
即使獨立了,也不會斷了與家的連結。每個人都可以。
生命中最難的課題
對大多數人來說,離開父母很難。在這件事情上,許多人能做的很有限,而且往往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劇烈影響,特別是他們仍受制於不合理的要求或被有毒的父母箝制,或是他們一生都在渴望理想的父母,希望卻一次次落空。
這裡說的告別並不是指在父母臨終前所說的話,而是透過大大小小的步驟剪斷與父母之間的臍帶,無論他們活著或已不在人世。簡單來說,就是活出自己的人生,變得越來越自主,隨著年歲增長越來越獨立,能替自己做出決定,這是我說的告別父母。然而,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許多人覺得被束縛,無法擺脫父母的期望。每當他們不像個乖孩子,聽從父母的指示選擇工作、挑選另一半、決定性別或政治傾向,甚至讓父母決定穿著打扮與生活方式,他們會被愧疚感折磨。當事人往往不自知,在父母指定的人生規畫中苦苦掙扎。因為他們應該要實現父母未盡的夢想,因為他們不能過得比父母更好,這些人扮演著延續父母人生的角色。
告別父母,意味著放下父母的期待和要求,不受他們的意見左右才能完全走出自己的路。聽起來很理性又簡單的事,卻引發許多家庭衝突。父母毫不掩飾地展現出擔心孩子、不滿意孩子的人生;某些成年子女受不了父母的批評,當自己的決定沒有得到父母認可,他們憤怒、委屈也感到受傷。有些人的心中因此衍生出強烈的自責感,有些人擔憂失去父母的愛,於是傾向跟隨父母的標準生活,還有人一輩子和父母抗衡,人生羅盤永遠指往相反的方向。
不過,告別父母不僅僅是拒絕不合理或是難以承受的要求,還要檢視自己對父母的期待,並且和他們說再見。
許多孩子終其一生在父母身上尋求不可能獲得的東西:無條件的愛、溫暖的情感、對自己的關注和認同。我們在襁褓時雖然依賴父母,但做為成年人,我們能夠照顧自己,打造自己想要的人生。因此,告別父母也代表著放下對理想父母的渴望。要放下這個念頭十分痛苦,許多人情願一生追逐不存在的父母,也不願意接受現實的不完美,始終盼望著奇蹟會出現。
其實,告別父母是我們成為成熟大人的轉捩點:只要我們不再要求父母做一些他們根本辦不到的事。這是條荊棘之路,因為我們要痛心面對一直以來試圖否認、粉飾或逃避的事;要覺察我們童年時沒有被滿足的經驗,並且為之哀悼(或許是你的第一次);看見父母真實的模樣,即便不解,也要認清他們過去和現在都無法好好照顧我們,原因通常是他們也有相同(未被滿足)的經驗。不過,說起來輕鬆做起來卻不容易,童年時期經歷的情感匱乏越多,我們想要填滿的空虛感也更大。
許多人逃避面對這件事,停留在「如果⋯⋯就會⋯⋯」的想像裡,於是從沒有機會真正了解父母本來的模樣,永遠無法獲得情感的滋養,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不完美的父母,寧願抱著希望,總有一天他們一定會成為一百分的父母。
這種渴望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我們不斷給予父母讓我們失望的權力,第二,我們無法接納和消化對父母的失望情緒,因此常常連帶波及到與他人的關係:過去父母無法給予無條件的愛,現在就應該由伴侶來達成。未能與父母分離會阻礙每一段成熟、健康的愛情。最糟的情況是,我們的孩子必須像我們的父母一樣,向我們證明他們的愛,而不是我們向孩子表現愛,最後受傷的將會是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和不健康的家庭糾葛將會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
這本書談的是所有人都會面臨的人生課題:好好地與父母說再見。
這樣的道別並不意味失去,而是獲得替人生做主的機會,為自己的大小決定負起責任,不再只是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
在許多情況下,在情緒上與父母切割不代表要切斷往來;相反的,這麼做能與他們建立比過去更好的關係,不講求輩分、沒有依賴感或內疚感,而是一段對等的關係。
此外,剪開與父母之間的依附關係時,最重要的不是與他們建立新的關係,而是與自己建立起愛的連結。
和父母好好說再見是什麼?又該怎麼做?
「我要澈底離開媽媽,不管她再怎麼貶低我和傷害我,我都不必再因此生氣了。」我問三十二歲的諾米來做治療的目的,她這麼回答。
澈底離開——這不是每個人的心願嗎?不過諾米和許多人一樣,認為澈底離開就是對各種攻擊感到麻木甚至委曲求全,也就是冷漠無感並且把自己武裝起來,這麼做也意味著承受一切怒罵、不為自己辯護、默默地忍受傷害。
好好地離開父母恰好相反,你要理解自己的感受,並且能與他人連結,這麼做才能溝通並畫出彼此的界線。心理學家將這種能力稱為「自我分化」。
不憎恨或是一昧犧牲自我、服從父母的束縛,而是放過自己,讓自己有能力選擇原諒、拒絕以及放下執著,這才是所謂好好地離開父母。
這件事無法一步到位,也不是做一次決定就能辨到,分離的旅程十分漫長,往往要走上一輩子。某些路段能輕鬆前進,有些地方崎嶇難行,還有一些甚至彷彿難以跨越。但我跟你保證,在旅途中你的視野將更寬闊,擁有喘息的空間,因此可以用旁觀者的角度觀察許多事物,看事情也更清晰。
世界上最自然的事就是長大,並且絕非易事,成長的路上少不了傷痛,並且是心理成熟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是誰?這是我想要的嗎?我做對了嗎?別人會不會因為我選擇自己的路就不愛我了?」我們都問過自己這些存在意義的問題。當我們知道,這些問題只能由自己來回答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因為自由代表承擔責任,為自己的感受、需求、願望和夢想,也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與父母分離的步驟
長大聽起來很容易,似乎只要依循一定的步驟:成年、考駕照、搬出家裡、接受職業訓練或讀大學,然後我們或多或少要承擔工作上的責任,找到好的伴侶,或許生幾個孩子,我們就這樣長大了。
但是長大到底是什麼?代表我們離開父母了嗎?
在某個下午去探望父母時,我們突然又回到了五歲、十歲或十五歲。儘管我們因為工作不順遂需要安慰,父親卻沉默不語,早就長大的我們在憤怒與難過的情緒之間擺盪;母親煩惱著我們的未來,聽不進我們的話,只是批評並指責我們一再犯錯、想太多或是想太少,已是成人的我們板著臉,暗自決定不再吐露一丁點自己的生活。然後,當父母稱讚姊姊的婚姻美滿、有兩個乖巧的孩子、剛獲得夢想中的工作,我們開始火冒三丈;長久以來的不公平對待、怒氣和自卑的感覺就像一股海浪把我們擊垮。
能否離開父母和我們的年紀並沒有太大的關係。當然,隨著年齡增長,大多數的人會變得更自主。我們不再告訴父母自己做的每一個決定,不再徵求他們的同意,經濟也變得獨立。然而,情感上卻還是離不開那條隱形的臍帶,嚴重時阻擋了我們獨立前行。
離開母親的身體來到世上被視為自然邁向獨立的第一步。在我們的文化裡,通常是父親在孩子出生後剪斷臍帶。這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動作,因為父親(或是第二個依附對象)從那時起是幫助孩子和母親切斷共生狀態的重要第三方。隨著孩子與父母雙方建立連結,形成一段三人成行的關係。理想情況下會有其他可信賴的依附對象能給予孩子安全感和愛,並拓展他的依附關係。孩子在父母身邊感覺越安全,就越容易去探索自己的周遭環境,並且變得更自主。
隨著孩子上幼稚園,接著上小學,也開啟了下一個與父母分離的重要階段。孩子每天上午和父母分開,在其他照顧者及同儕身上體驗到超越父母關係的凝聚力和意義。
年復一年,孩子漸漸獨立了:第一次在朋友家過夜、第一次班遊、第一個祕密、第一次墜入情網、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性愛、第一次沒有父母陪伴的假期、第一次戀愛、第一次一個人住、第一份工作、第一份薪水——這些都是脫離父母道路上的里程碑。
父母能夠在一路上陪伴支持孩子是再好不過的,因為健康的依附關係來自於可信賴的父母以及他們循序漸進的放手。有句話更能表達出這個意境:「父母應該給予孩子兩樣東西:根芽和翅膀。」
德裔美籍精神分析學家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把童年到成人的生命階段稱為「心理的延期償付」時期,孩子在這段期間逐漸和父母及自我分離。雖然我們的父母仍在身邊,給我們建議或指揮著我們做決定:從事什麼職業、選擇什麼樣的伴侶、過什麼樣的生活,但最終承擔決定的是我們,而非他們。在尋找自我的時期裡可能會有迷失方向的時候,特別是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有很大的空間探索自己的定位,相形之下,傳統或獨裁社會傾向於指定每個人的角色。
根據艾瑞克森的階段模型,生命的每個階段都必須克服某些成長任務,這些對我們健全的人格發展至關重要。讓我們仔細看看個別階段的內容:
信任與不信任(一歲)
孩子剛出生的頭一年完全依賴他的照顧者,這個時期也決定了他能否建立健康的基本信任,或是因為太多的失望而懷疑這個世界。理想情況下,孩子能得到充分的照顧,並且感受自己的需求能獲得外界的肯認。
自主行動與羞怯懷疑(二到三歲)
孩子會在這個時期發展出自主性,邁出離開母親的第一步,學會走路、說話和上厠所。佛洛伊德把這個時期稱為肛門期,孩子學會抓放物品,也第一次面對羞怯與懷疑。這個年紀的孩子也會產生「我」和「你」的概念,他意識到自己是獨立於母親和她的乳房之外的個體。自主性能超越懷疑與羞怯感的話,孩子就能度過這個階段,這也是最理想的結果。
主動與內疚(四到五歲)
在四到五歲之間,孩子會更廣泛且更獨立地探索他的周遭、真實世界和自我,他會問很多問題,在遊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孩子也會探究他的性別,並對父親或母親展現出性方面的占有慾,這就是所謂的伊底帕斯期。孩子內心的良知逐漸形成並產生內疚。理想的情況是,孩子在這個階段一方面學會採取主動,另一方面也學會面對自身的歉疚。
勤奮與自卑(六歲至青春期)
從六歲起,從開始上學一直到青春期,孩子會在勤奮與自卑之間找尋平衡。除了玩耍的渴望之外,孩子養成一種工作的意識,想要做些有用的事情並學習。為了消弭自卑感,成功的經歷就顯得無比重要。這個時期可能會出現固執,反映在對失敗的恐懼或普遍性的焦慮,甚至是長期缺乏自信。最好能讓孩子盡情展現自己,並且適度地鼓勵他們,讓他們能享有充分的成就感,才能建立起穩定的自信心。
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十三歲至二十歲)
這個階段的首要議題是身分認同——我是誰?——更進一步是和過去比較,和他人比較,和父母、朋友和社會對孩子的期望比較。青少年此時傾注心力在自身、其他性別同儕、角色規範和自我的需求上。理想的情況下,許多美好經驗和健康的自信心能建構自我認同。若不是如此,孩子會產生自我認同混淆,包含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迷惘。沒有成功發展出穩定自我認同的孩子,經常會感到失落並尋求支持,例如組織結構明確的團體。一旦無法應對這個階段的任務,將對往後的人生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為缺乏身分認同的人很難與他人建立真正的關係。
親密團結與孤獨(成年早期)
人生的這個階段就是尋找伴侶和親密關係,如同艾瑞克森說的:「迷失自我,在他人中找到自我。」擁有明確自我認同的人能夠發展出穩定且滿足的伴侶關係,因為他們開放自我的同時也懂得忠於自己;反之,缺乏自我認同的人將感到被孤立及自身的寂寞和空虛。此外,能夠忍受這個時期的孤獨感,不會同時失去對他人和自我的信任感,這件事對每個人來說都十分重要。能順利度過生命前幾個階段,往後面對成年早期到中期的挑戰時就越能成功。
生育與停滯頹廢(成年中期)
艾瑞克森把生育定義為教養後代。因為許多人在這個階段都已經有家庭,且往往會有替後代子孫創造、傳承和保障價值觀的需求。沒有孩子的人也會在這個時期投身其他事物,將時間、知識或財力等資源分享給他人。能夠在不忽視自我的前提下,養成關懷他人的能力是最理想的狀態。因為人際關係失和或是只專注於自身而沒有發展出這階段該有的能力,通常會導致自我封閉、孤單和發展停滯。
自我統整與絕望(成熟期)
接受目前為止的生活是這個時期的任務。那些未能接受人生現狀,對生活感到失望和不滿的人,經常會對生活感到厭惡和(或)憂鬱。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已達到成熟的狀態,並預備接納我們這一段獨一無二生命週期的必然性和無可取代性。全然接納現在的自己,讓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看待生命的終點,不那麼畏懼死亡。面對現狀不再絕望、苦苦掙扎,而是變得睿智。
父母是我的責任。
我對父母很失望,因為他們始終不是我想像中的父母。
我們之間沒有界線。
我必須成為他們的驕傲。
向他們透露自己真實的感受,我根本做不到。
父母最清楚什麼對我有利。
我知道怎麼做對他們最好。
與父母相處對我來說是苦差事,即便如此,我仍要求自己固定與他們碰面。
我不再和父母聯繫,因為他們對不起我。
無法滿足父母讓我總是心懷愧疚。
和他們的關係是一場絕世抗爭。
我是受害者,他們是凶手,搗毀了我生活。
我期待他們認同我所有的決定,否則我會難過。
就算我告訴他們自己小時候被傷害得有多深,他們也絕對不會向我道歉。
我必須不斷在父母面前捍衛自己。
我不能說出或做出任何一點傷害他們的事。
父母是我在人際關係中的主要爭執點。
他們的感受和需要總是比我自己的還重要。
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我的父母並不了解我。
如果我順應自己的心過生活就可能失去父母的歡心。
我不想讓他們受苦,能讓他們快樂的事,我會竭盡所能完成。
我無法心平氣和地與父母交流內心的想法。
我常常想向他們證明自己是對的。
我希望父母最終能變成我所渴望的樣子,而且遲遲無法放下這執念。
我的所做所為始終和父母的願望背道而馳。
我不做任何會讓父母不開心的決定。
我和父母之間懸而未解之題,成了我與他人關係之中的爭執點。
我害怕知道父母的反應,所以閉口不談生活裡的大事。
如果父母不在人世了該有多好,我恨他們。
如果父母不在了,我也會失去活下去的勇氣和喜悅。
如果你也認同上述任何一句話,表示你仍然糾結著自己與父母的關係,還沒有辦法澈底放下。
這本書正是為你而寫:書中將告訴你,一個人的成熟度會如何影響自身的(人際關係)生活,並且特別為你指出解開糾結的道路。你的個人蛻變將置於首位,你的家庭關係並不會因此蒙上陰影。
這本書無法取代心理治療,但是能幫助你更認識自己、了解父母和你的互動關係,幫助你擺脫愧疚感、憤怒和失望。每一個章節會帶你反思、重新定位自己,並且和父母(包含你身邊的人)建立起更成熟的關係,是這本書最想要達成的目標。
我診間裡的個案故事訴說著脫離父母成為成熟大人過程中的難題是如何形成的,要怎麼克服這些難題。你可能會在某幾個案例中看見自己的身影,甚至挑起你難過或憤怒的情緒。請不要擔心!正因為我們有所感才會出現情緒。在理想的情況下,感受會引發行動,並朝著對我們有益的方向前進。
離開父母獨立是一段漫長的過程。有時會進展神速,但多數時候是一步步地推進。我祝福你在這條路上能認識自己、保持勇氣,並給自己無比的耐心。
我希望你鼓起勇氣擺脫種種束縛;因為,離開父母並不代表愛變少了,而是能用更成熟的方式去愛。
即使獨立了,也不會斷了與家的連結。每個人都可以。
生命中最難的課題
對大多數人來說,離開父母很難。在這件事情上,許多人能做的很有限,而且往往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劇烈影響,特別是他們仍受制於不合理的要求或被有毒的父母箝制,或是他們一生都在渴望理想的父母,希望卻一次次落空。
這裡說的告別並不是指在父母臨終前所說的話,而是透過大大小小的步驟剪斷與父母之間的臍帶,無論他們活著或已不在人世。簡單來說,就是活出自己的人生,變得越來越自主,隨著年歲增長越來越獨立,能替自己做出決定,這是我說的告別父母。然而,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許多人覺得被束縛,無法擺脫父母的期望。每當他們不像個乖孩子,聽從父母的指示選擇工作、挑選另一半、決定性別或政治傾向,甚至讓父母決定穿著打扮與生活方式,他們會被愧疚感折磨。當事人往往不自知,在父母指定的人生規畫中苦苦掙扎。因為他們應該要實現父母未盡的夢想,因為他們不能過得比父母更好,這些人扮演著延續父母人生的角色。
告別父母,意味著放下父母的期待和要求,不受他們的意見左右才能完全走出自己的路。聽起來很理性又簡單的事,卻引發許多家庭衝突。父母毫不掩飾地展現出擔心孩子、不滿意孩子的人生;某些成年子女受不了父母的批評,當自己的決定沒有得到父母認可,他們憤怒、委屈也感到受傷。有些人的心中因此衍生出強烈的自責感,有些人擔憂失去父母的愛,於是傾向跟隨父母的標準生活,還有人一輩子和父母抗衡,人生羅盤永遠指往相反的方向。
不過,告別父母不僅僅是拒絕不合理或是難以承受的要求,還要檢視自己對父母的期待,並且和他們說再見。
許多孩子終其一生在父母身上尋求不可能獲得的東西:無條件的愛、溫暖的情感、對自己的關注和認同。我們在襁褓時雖然依賴父母,但做為成年人,我們能夠照顧自己,打造自己想要的人生。因此,告別父母也代表著放下對理想父母的渴望。要放下這個念頭十分痛苦,許多人情願一生追逐不存在的父母,也不願意接受現實的不完美,始終盼望著奇蹟會出現。
其實,告別父母是我們成為成熟大人的轉捩點:只要我們不再要求父母做一些他們根本辦不到的事。這是條荊棘之路,因為我們要痛心面對一直以來試圖否認、粉飾或逃避的事;要覺察我們童年時沒有被滿足的經驗,並且為之哀悼(或許是你的第一次);看見父母真實的模樣,即便不解,也要認清他們過去和現在都無法好好照顧我們,原因通常是他們也有相同(未被滿足)的經驗。不過,說起來輕鬆做起來卻不容易,童年時期經歷的情感匱乏越多,我們想要填滿的空虛感也更大。
許多人逃避面對這件事,停留在「如果⋯⋯就會⋯⋯」的想像裡,於是從沒有機會真正了解父母本來的模樣,永遠無法獲得情感的滋養,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不完美的父母,寧願抱著希望,總有一天他們一定會成為一百分的父母。
這種渴望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我們不斷給予父母讓我們失望的權力,第二,我們無法接納和消化對父母的失望情緒,因此常常連帶波及到與他人的關係:過去父母無法給予無條件的愛,現在就應該由伴侶來達成。未能與父母分離會阻礙每一段成熟、健康的愛情。最糟的情況是,我們的孩子必須像我們的父母一樣,向我們證明他們的愛,而不是我們向孩子表現愛,最後受傷的將會是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和不健康的家庭糾葛將會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
這本書談的是所有人都會面臨的人生課題:好好地與父母說再見。
這樣的道別並不意味失去,而是獲得替人生做主的機會,為自己的大小決定負起責任,不再只是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
在許多情況下,在情緒上與父母切割不代表要切斷往來;相反的,這麼做能與他們建立比過去更好的關係,不講求輩分、沒有依賴感或內疚感,而是一段對等的關係。
此外,剪開與父母之間的依附關係時,最重要的不是與他們建立新的關係,而是與自己建立起愛的連結。
和父母好好說再見是什麼?又該怎麼做?
「我要澈底離開媽媽,不管她再怎麼貶低我和傷害我,我都不必再因此生氣了。」我問三十二歲的諾米來做治療的目的,她這麼回答。
澈底離開——這不是每個人的心願嗎?不過諾米和許多人一樣,認為澈底離開就是對各種攻擊感到麻木甚至委曲求全,也就是冷漠無感並且把自己武裝起來,這麼做也意味著承受一切怒罵、不為自己辯護、默默地忍受傷害。
好好地離開父母恰好相反,你要理解自己的感受,並且能與他人連結,這麼做才能溝通並畫出彼此的界線。心理學家將這種能力稱為「自我分化」。
不憎恨或是一昧犧牲自我、服從父母的束縛,而是放過自己,讓自己有能力選擇原諒、拒絕以及放下執著,這才是所謂好好地離開父母。
這件事無法一步到位,也不是做一次決定就能辨到,分離的旅程十分漫長,往往要走上一輩子。某些路段能輕鬆前進,有些地方崎嶇難行,還有一些甚至彷彿難以跨越。但我跟你保證,在旅途中你的視野將更寬闊,擁有喘息的空間,因此可以用旁觀者的角度觀察許多事物,看事情也更清晰。
世界上最自然的事就是長大,並且絕非易事,成長的路上少不了傷痛,並且是心理成熟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是誰?這是我想要的嗎?我做對了嗎?別人會不會因為我選擇自己的路就不愛我了?」我們都問過自己這些存在意義的問題。當我們知道,這些問題只能由自己來回答時,我們才是自由的。因為自由代表承擔責任,為自己的感受、需求、願望和夢想,也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與父母分離的步驟
長大聽起來很容易,似乎只要依循一定的步驟:成年、考駕照、搬出家裡、接受職業訓練或讀大學,然後我們或多或少要承擔工作上的責任,找到好的伴侶,或許生幾個孩子,我們就這樣長大了。
但是長大到底是什麼?代表我們離開父母了嗎?
在某個下午去探望父母時,我們突然又回到了五歲、十歲或十五歲。儘管我們因為工作不順遂需要安慰,父親卻沉默不語,早就長大的我們在憤怒與難過的情緒之間擺盪;母親煩惱著我們的未來,聽不進我們的話,只是批評並指責我們一再犯錯、想太多或是想太少,已是成人的我們板著臉,暗自決定不再吐露一丁點自己的生活。然後,當父母稱讚姊姊的婚姻美滿、有兩個乖巧的孩子、剛獲得夢想中的工作,我們開始火冒三丈;長久以來的不公平對待、怒氣和自卑的感覺就像一股海浪把我們擊垮。
能否離開父母和我們的年紀並沒有太大的關係。當然,隨著年齡增長,大多數的人會變得更自主。我們不再告訴父母自己做的每一個決定,不再徵求他們的同意,經濟也變得獨立。然而,情感上卻還是離不開那條隱形的臍帶,嚴重時阻擋了我們獨立前行。
離開母親的身體來到世上被視為自然邁向獨立的第一步。在我們的文化裡,通常是父親在孩子出生後剪斷臍帶。這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動作,因為父親(或是第二個依附對象)從那時起是幫助孩子和母親切斷共生狀態的重要第三方。隨著孩子與父母雙方建立連結,形成一段三人成行的關係。理想情況下會有其他可信賴的依附對象能給予孩子安全感和愛,並拓展他的依附關係。孩子在父母身邊感覺越安全,就越容易去探索自己的周遭環境,並且變得更自主。
隨著孩子上幼稚園,接著上小學,也開啟了下一個與父母分離的重要階段。孩子每天上午和父母分開,在其他照顧者及同儕身上體驗到超越父母關係的凝聚力和意義。
年復一年,孩子漸漸獨立了:第一次在朋友家過夜、第一次班遊、第一個祕密、第一次墜入情網、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性愛、第一次沒有父母陪伴的假期、第一次戀愛、第一次一個人住、第一份工作、第一份薪水——這些都是脫離父母道路上的里程碑。
父母能夠在一路上陪伴支持孩子是再好不過的,因為健康的依附關係來自於可信賴的父母以及他們循序漸進的放手。有句話更能表達出這個意境:「父母應該給予孩子兩樣東西:根芽和翅膀。」
德裔美籍精神分析學家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把童年到成人的生命階段稱為「心理的延期償付」時期,孩子在這段期間逐漸和父母及自我分離。雖然我們的父母仍在身邊,給我們建議或指揮著我們做決定:從事什麼職業、選擇什麼樣的伴侶、過什麼樣的生活,但最終承擔決定的是我們,而非他們。在尋找自我的時期裡可能會有迷失方向的時候,特別是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有很大的空間探索自己的定位,相形之下,傳統或獨裁社會傾向於指定每個人的角色。
根據艾瑞克森的階段模型,生命的每個階段都必須克服某些成長任務,這些對我們健全的人格發展至關重要。讓我們仔細看看個別階段的內容:
信任與不信任(一歲)
孩子剛出生的頭一年完全依賴他的照顧者,這個時期也決定了他能否建立健康的基本信任,或是因為太多的失望而懷疑這個世界。理想情況下,孩子能得到充分的照顧,並且感受自己的需求能獲得外界的肯認。
自主行動與羞怯懷疑(二到三歲)
孩子會在這個時期發展出自主性,邁出離開母親的第一步,學會走路、說話和上厠所。佛洛伊德把這個時期稱為肛門期,孩子學會抓放物品,也第一次面對羞怯與懷疑。這個年紀的孩子也會產生「我」和「你」的概念,他意識到自己是獨立於母親和她的乳房之外的個體。自主性能超越懷疑與羞怯感的話,孩子就能度過這個階段,這也是最理想的結果。
主動與內疚(四到五歲)
在四到五歲之間,孩子會更廣泛且更獨立地探索他的周遭、真實世界和自我,他會問很多問題,在遊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孩子也會探究他的性別,並對父親或母親展現出性方面的占有慾,這就是所謂的伊底帕斯期。孩子內心的良知逐漸形成並產生內疚。理想的情況是,孩子在這個階段一方面學會採取主動,另一方面也學會面對自身的歉疚。
勤奮與自卑(六歲至青春期)
從六歲起,從開始上學一直到青春期,孩子會在勤奮與自卑之間找尋平衡。除了玩耍的渴望之外,孩子養成一種工作的意識,想要做些有用的事情並學習。為了消弭自卑感,成功的經歷就顯得無比重要。這個時期可能會出現固執,反映在對失敗的恐懼或普遍性的焦慮,甚至是長期缺乏自信。最好能讓孩子盡情展現自己,並且適度地鼓勵他們,讓他們能享有充分的成就感,才能建立起穩定的自信心。
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十三歲至二十歲)
這個階段的首要議題是身分認同——我是誰?——更進一步是和過去比較,和他人比較,和父母、朋友和社會對孩子的期望比較。青少年此時傾注心力在自身、其他性別同儕、角色規範和自我的需求上。理想的情況下,許多美好經驗和健康的自信心能建構自我認同。若不是如此,孩子會產生自我認同混淆,包含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迷惘。沒有成功發展出穩定自我認同的孩子,經常會感到失落並尋求支持,例如組織結構明確的團體。一旦無法應對這個階段的任務,將對往後的人生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因為缺乏身分認同的人很難與他人建立真正的關係。
親密團結與孤獨(成年早期)
人生的這個階段就是尋找伴侶和親密關係,如同艾瑞克森說的:「迷失自我,在他人中找到自我。」擁有明確自我認同的人能夠發展出穩定且滿足的伴侶關係,因為他們開放自我的同時也懂得忠於自己;反之,缺乏自我認同的人將感到被孤立及自身的寂寞和空虛。此外,能夠忍受這個時期的孤獨感,不會同時失去對他人和自我的信任感,這件事對每個人來說都十分重要。能順利度過生命前幾個階段,往後面對成年早期到中期的挑戰時就越能成功。
生育與停滯頹廢(成年中期)
艾瑞克森把生育定義為教養後代。因為許多人在這個階段都已經有家庭,且往往會有替後代子孫創造、傳承和保障價值觀的需求。沒有孩子的人也會在這個時期投身其他事物,將時間、知識或財力等資源分享給他人。能夠在不忽視自我的前提下,養成關懷他人的能力是最理想的狀態。因為人際關係失和或是只專注於自身而沒有發展出這階段該有的能力,通常會導致自我封閉、孤單和發展停滯。
自我統整與絕望(成熟期)
接受目前為止的生活是這個時期的任務。那些未能接受人生現狀,對生活感到失望和不滿的人,經常會對生活感到厭惡和(或)憂鬱。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已達到成熟的狀態,並預備接納我們這一段獨一無二生命週期的必然性和無可取代性。全然接納現在的自己,讓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看待生命的終點,不那麼畏懼死亡。面對現狀不再絕望、苦苦掙扎,而是變得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