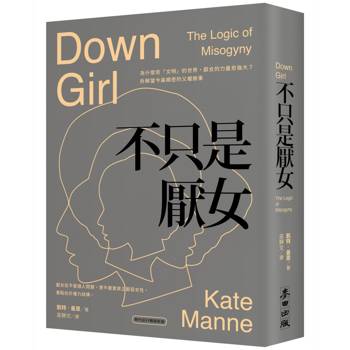摘至第一章〈威脅女性〉
厭女情結可能是什麼
在此,我們可以藉由提問重新開始:依據前述內容,我們可能自然而然地「期待」厭女情結是什麼樣子?換句話說,那股導向女性的敵意和憤怒(就算不完全是,但至少一定程度是因為她們的性別)的天然基礎是什麼?而其中哪些可以用來理解厭女情結如何作為父權意識形態的一面,或表現形式之一?有鑑於父權文化裡,一些女性的社會角色是提供男性注意力與關愛的從屬者,這指出了一種明顯的可能性值得深思:若察覺到女性反抗、破壞了用以定義這些社會角色的規範和期待,這類反應便可能自然地被觸發。從一個體貼而關懷的從屬角色叛逃──還有什麼能為敵意和憤怒提供更天然的基礎?我們可以預期,這會讓典型的性別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男性)感到權力遭奪且被忽視,而從情緒方面來看,這個組合可能會招致大禍。
模擬一個簡單的日常畫面可能有助思考。想像一個人在餐廳,他不但期待自己要獲得恭敬的對待(顧客永遠都是對的),還期待他的餐點要被殷勤奉上,伴著笑容。他期待餐廳讓他感到備受照顧且與眾不同,同時他的餐點會被送到面前(對他來說,這是個既有點弱勢又富有權力的位置)。現在,想像這位客人感到失望──因為他的服務生沒在服務他,雖然是因為她在招呼別桌客人。或者她可能看來像在閒晃;或者她單純在做自己的事、不知何以地忽視了他。還能更糟:她可能露出一副期待「他服務她」的模樣,使兩人的角色發生了令人困惑的反轉。不論哪一種情況,她的舉止態度都不是他在這類情境中習慣的。我們很容易想像此人會變得迷惘,進而怨懟;很容易想像他用湯匙敲餐桌;很容易想像他在挫折中暴怒。
這舉例顯然很簡略,但我認為這確實為進一步的闡述和延伸奠定了大有可為的基礎。我們看到了一個易懂的比擬──當事情涉及這種近乎仇視和敵意的態度,部分是因為女性自身的性別,在此例中,部分也是認為她破壞了父權的規範與期待。此外,如果我們同意這是一個有效的例子,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厭女情結「不必是」什麼。一方面,它不需要針對所有女性,相反,它可以只針對特定女性,例如那些被看作不服從的、怠忽職守的,或違反規則的女性。另一方面,這個模型終結了一種想法:厭女情結和性渴望從某種角度來說不相容(儘管莫名其妙,但正如我們所見,還是有人擁護這種想法)。羅傑對阿法斐姊妹會女性成員的性渴望,以及他希望她們也想要他的渴望,在他醞釀憤怒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表示,面對她們時,他感到無力。從他的角度看來,她們「掌握」了他,而他對於即將發生的羞辱感到深深的憤怒,如同一名飢餓的用餐者,他所感受到的弱勢地位很可能導致他對擅離職守的服務生暴怒。
這個模型也初步預測了某些典型的厭女情結攻擊目標和受害者。前者包括那些被認定「不稱職」的女人--性別理念的叛徒、壞女人、「難以控制」的女人。受害者經常會包括進入了對男性而言具有權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避開或選擇逃脫服務男性的女性。
(未完)
摘自第六章〈赦免男性〉
同理他心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歲的史丹佛大學學生布洛克.透納接受審判,因為他把一名二十二歲的年輕女性當成俎上肉對待──一場校園派對之後,他在一輛垃圾車後方性侵了她;他侵犯的這名女性來此探望自己的妹妹,被發現時已不省人事。在布洛克被捕後以及整個審判期間,他父親的主要擔憂是兒子再也無法享受一塊現烤的美味肋眼牛排,他失去了胃口。我們之中許多人在閱讀丹.透納寫給法官的信時也胃口盡失。在信中,他沉痛感嘆,他的兒子不再是過去那個「隨遇而安」、「好相處」的大學運動員。但是,他本來是嗎?
本案法官艾倫.裴斯基也同樣擔憂有罪判決會對透納的未來造成「重大影響」,因而判了他就一般標準而言非常寬大的刑期(於郡監獄中服刑六個月與三年緩刑,他最終只服刑三個月)。整個審理與判決過程中,布洛克.透納的高超泳技被再三強調。而丹.透納仍舊不滿意,認為兒子根本不應該坐牢;根據他的描述,他兒子的犯罪僅僅是二十年的良好表現裡「二十分鐘的行為」。
但是,就如同殺人犯不能因為他沒有殺害的人邀功,透納也不會因為他沒有侵犯的女性而改變他的強暴犯身分。我們也必須說:當有了一個受害者,往往就有更多受害者。因此他父親估計的比例可能偏低了。
這個案例生動闡明了一個經常受到忽略的厭女情結鏡像,我稱之為:同理『他』心。它被忽視的程度之高,使它成了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借用貝蒂,傅瑞丹出自《女性迷思》一書的知名用語,但這不是因為同理他心的問題很罕見,相反的,正因如此常見,導致我們將其視為日常。
在此,同理他心在此展示的型態,是一種對性暴力的男性加害者表現出的過度同情。在當代的美國社會裡,這經常被延伸到白人、身心健全,以及在其他方面具有特權的「模範金童」身上,例如透納,他是史丹佛游泳獎學金的獲獎人。隨之而來,人們不願意相信指控這些男人的女性,或甚至不願懲罰罪證確鑿的模範金童──透納一案再次是個例證。
造成這種否定心理的原因之一是一種錯誤的認知,認為強暴犯必然具備某種樣貌:令人發毛、怪異,並且明目張膽表現出他們缺乏人性。布洛克.透納不是一個怪物,他的一名女性友人在信裡這樣寫,並指責政治正確導致了他被判有罪。他是「夏令營般的校園環境」下的受害者,在這裡,事情因為酒精和「被蒙蔽的判斷能力」而「失去控制」。透納的罪行「完全不同於一名女性去停車場取車遭綁架強暴」的情況;她寫道,「那是強暴犯,而我肯定布洛克不是那種人。」
她隨後補充,她認識布洛克多年,他總是非常關心、尊重她,對她很親切,因此布洛克不是一個強暴犯,他的友人再次堅持。法官裴斯基同意她的評價,「這在我聽來很有道理, 某程度上和相關證詞中對他在事發前的性格描述一致,都很正面。」
布洛克的友人與本案法官似乎都依照以下的推論模式進行思考:一名模範金童不是強暴犯,一名模範金童是如此這般的樣貌,因此如此這般的樣貌不是一個強暴犯。這就是「正人君子布魯特斯」問題。
是時候讓我們放棄模範金童的迷思了,拒絕這個重大假設,學著在適當的時刻以後件否定前件。透納在垃圾車後的小巷裡被人當場撞見,他正在性侵受害者,她因為酒醉而失去意識。這是強暴,而強暴他人的人等於強暴犯,故透納是一個強暴犯──他也是一名模範金童。因此……
我們太常移開目光,拒絕面對性暴力在美國整體社會,尤其是在大學校園內的普及程度和特性。我們向自己保證,真正的強暴犯會是帶角和乾草叉的惡魔樣貌,或如同怪物那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生物)出現在我們的雷達上;怪物無法被理解、詭異,而且在外表上令人害怕。強暴犯的可怕之處就在於,除了他們多數時候皆為男性這點以外,他們缺少可辨識的記號與特徵,強暴犯是人類,太像人類的人類,而他們就存在於我們之中。透過誇張的描寫,強暴犯如同怪物的想法達到了赦免的功效。
另一個迷思則是強暴犯是精神變態,他們被描繪成無情、沒有感覺、殘酷成性;這個描述對兩方群體而言都不正確(不是指兩者之間並無重疊,因為現實中確實有)。許多性侵害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性侵者對他人沒有任何掛念或覺察,而是因為侵略、挫折、控制欲望, 以及再一次,一種我理應得的權利感──無論是已受到侵害的,還是仍被期待著的權利。這也表示,儘管酒精與其他影響意識的物質,還有兄弟會文化都毫無疑問促成了性侵害的普及程度,但它們比較像是啟動機制,而非動機。
即使是在已準備好承認性侵害有多普遍並同意上述這類迷思的人之中,也存在著一種隱約、常見的一廂情願,認為造成大學校園內性侵害的主因是青年的經驗不足和無知,而排除了厭女侵略、連續性的性掠奪,以及鼓勵並保護犯罪者的規範──也就是強暴文化。丹.透納說,他的兒子承諾全心投入教育其他人「飲酒和亂『性』的危險」,法官裴斯基贊同這個計畫。但性不是問題,暴力才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主張布洛克.透納可以是個合適的反性暴力代言人,這個建議最寬容地說都令人感到屈辱。在擅自幫別人上課之前,他需要自己先上一堂道德課,而在透過性暴力取得上風之後,竟如此著急想站上道德高地,強烈說明在這件事上,他還沒有學到關鍵的一課:在任何權力階序裡的卓越位置,都不是他與生俱來的道德權利。
然而,對他的父親、法官、友人生氣很容易,某程度上也合理。但若認為他們反映了另一個層次的道德愚昧,那就錯了。他們其實只是處在一條「同情男性」的光譜的極端,而我們許多人同樣身處這條光譜之中。為布洛克.透納說話的人展現了原諒的傾向,打造了赦免敘事。這些敘事太常被延伸到與他處境相同的男性身上;這種傾向主要源自於我們鮮少批判的能力和特質,例如同情心、同理心、對友人的信任、對子女的奉獻,以及在證據允許的情況下,對他人的良善性格抱持最高度的信心。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些確實都是重要的能力和特質,但當其他條件並不相等,它們也可能有不好的一面。比方說,當社會仍舊廣泛不平等,天真地挪用它們,將可能使已比他人擁有更多不合理特權的人更進一步獲得特權,且代價可能是不公地抨擊、責怪、羞辱,進一步危害與消抹他們的受害者當中最弱勢的一群。在一些情況裡,意識到這一點的犯罪者會以此為基礎挑選受害者。我將在本章最後談這個主題,同時討論丹尼爾.霍茲克洛一案中清楚展現的厭黑女情結。
對布洛克.透納這類犯罪者的過度同情心可以歸咎於──同時也促成了──在面對其受害者的傷害、羞辱和(某種程度上歷久不衰的)創傷時,我們的關懷不足。同時,它來自並導致一種傾向,讓歷史上的支配群體者在面對一直以來的從屬群體者時,得以逍遙法外──譬喻上或實際層面上皆是。在男性支配的情境裡,我們會先同情他,而這基本上就讓他成了自身犯罪的受害者。因為如果強暴者在一開始就先因為失去食欲或游泳獎學金獲得同情,他在故事裡便將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我將於下一章裡談到,一位受害者的敘事裡需要一名反派或一名加害者(至少在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裡是如此)。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誰是造成強暴者落入這個「要不是」(but-for)的境地?除了那名作證指認他的人之外,別無其他,他的受害者因此便可能被重新賦予反派的角色。
我懷疑這是一套經常促成責怪受害者現象的機制,而這之所以有害,一部分是因為這完全改變了敘事,促成這個邪惡的道德角色反轉。
在此案例裡,法官和父親都沒有責怪受害者(但布洛克的女性友人有,儘管她否認);然而他們採取了一種同樣的、甚至可能更狡詐的做法:他們把受害者從敘事中徹底消抹了。在他們的故事裡,她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但於此案裡,受害者拒絕無聲離去。她被允許在法庭上讀出她強而有力、撼動人心的聲明,她以費盡苦心的清明思路揭露了布洛克.透納的犯罪對她的影響。他不僅違背她的意願,甚至在事後改寫她的心智;在他的行為於她記憶所留的空白上,他套上自己的故事,伴隨著許多省略和編造。(「根據他的說詞,我很享受。我很享受。」她恐懼且不可置信地在一篇報導裡讀到這件事──她也從同篇報導裡得知自己被發現時的狀態:半裸與無意識。)於是, 在那場性侵裡,無論是關於她的身體,還是她身體的故事,這名受害者都被奪去了正當的發言權威。她接著說明:
「我收到警告,因為他現在知道我不記得了,他將能夠撰寫劇本;他可以說任何他想說的,沒有人可以抗議。我沒有權力,沒有聲音,我毫無防禦。我的失憶將被用來攻擊我,我的證詞薄弱、不完整,而我被說服相信,也許我不夠好,無法贏得這場官司。他的律師不斷提醒陪審團,我們唯一能夠相信的人是布洛克,因為她不記得了。無助感使我飽受創傷。
(中略)這場性侵是這麼鐵錚錚的事實,我卻得在審判庭上,回答這類問題:
妳年紀多大?體重多少?妳那天吃了什麼?好吧,妳那天晚餐吃了什麼?(中略)誰給妳飲料的?妳平常會喝多少?誰載妳去派對?幾點?但具體是哪裡?妳穿什麼?(中略)妳曾醉到失去意識多少次?妳參加兄弟會的派對嗎?妳和男朋友是認真的嗎?妳和他發生過性關係嗎?妳們從什麼時候開始交往?妳有沒有可能偷吃?妳偷吃過嗎?當妳說妳想要獎勵他,妳是什麼意思?妳記不記得妳是幾點醒來的?妳還穿著妳的羊毛衫嗎?妳的羊毛衫是什麼顏色?對那晚妳還記得些什麼?不記得了?好的,我們讓布洛克補充。
(中略)在一場身體侵害後,我被一連串意在攻擊我的問題侵害,好讓他們可以說,看吧,她的說法前後不一致,她頭腦不清楚,她基本上是一個酒鬼,她大概想要一夜情,他是一個運動員對吧,他們兩個人都醉了。無論如何,她記得的那些醫院裡的事情都是之後的事了,為什麼要納入考量呢?布洛克正處於人生重要的關卡,此刻他非常難受。」
這最後一句話清楚說明了同理他心的問題:當我們的立場偏袒強暴犯,我們便在他帶給受害者的傷害之上,再加諸深重的道德侮辱。我們也可能會忽略,在法律的眼中,他的罪行乃針對「人民」,也就是我們所有人,理論上如此。而針對這名挺身而出、為他的犯罪作證做著辛苦的工作,反而認為她試圖尋求個人的復仇和道德懲罰。更有甚者,她可能會被看作不知寬恕,試著從她的強暴者身上「拿走」什麼,而非為維持法律和秩序做出貢獻的人。
當我們詢問,「這是為了誰呢?」與「她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便侵蝕了一名強暴受害者作證時的立足點:在她的身體上,發生了一起對社會的罪行。我們應該認可到,儘管她的身體屬於她且只屬於她,我們卻應該集體致力於保障這個身體主人的利益。至少理應如此:這是一個道德抱負。
厭女情結可能是什麼
在此,我們可以藉由提問重新開始:依據前述內容,我們可能自然而然地「期待」厭女情結是什麼樣子?換句話說,那股導向女性的敵意和憤怒(就算不完全是,但至少一定程度是因為她們的性別)的天然基礎是什麼?而其中哪些可以用來理解厭女情結如何作為父權意識形態的一面,或表現形式之一?有鑑於父權文化裡,一些女性的社會角色是提供男性注意力與關愛的從屬者,這指出了一種明顯的可能性值得深思:若察覺到女性反抗、破壞了用以定義這些社會角色的規範和期待,這類反應便可能自然地被觸發。從一個體貼而關懷的從屬角色叛逃──還有什麼能為敵意和憤怒提供更天然的基礎?我們可以預期,這會讓典型的性別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男性)感到權力遭奪且被忽視,而從情緒方面來看,這個組合可能會招致大禍。
模擬一個簡單的日常畫面可能有助思考。想像一個人在餐廳,他不但期待自己要獲得恭敬的對待(顧客永遠都是對的),還期待他的餐點要被殷勤奉上,伴著笑容。他期待餐廳讓他感到備受照顧且與眾不同,同時他的餐點會被送到面前(對他來說,這是個既有點弱勢又富有權力的位置)。現在,想像這位客人感到失望──因為他的服務生沒在服務他,雖然是因為她在招呼別桌客人。或者她可能看來像在閒晃;或者她單純在做自己的事、不知何以地忽視了他。還能更糟:她可能露出一副期待「他服務她」的模樣,使兩人的角色發生了令人困惑的反轉。不論哪一種情況,她的舉止態度都不是他在這類情境中習慣的。我們很容易想像此人會變得迷惘,進而怨懟;很容易想像他用湯匙敲餐桌;很容易想像他在挫折中暴怒。
這舉例顯然很簡略,但我認為這確實為進一步的闡述和延伸奠定了大有可為的基礎。我們看到了一個易懂的比擬──當事情涉及這種近乎仇視和敵意的態度,部分是因為女性自身的性別,在此例中,部分也是認為她破壞了父權的規範與期待。此外,如果我們同意這是一個有效的例子,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厭女情結「不必是」什麼。一方面,它不需要針對所有女性,相反,它可以只針對特定女性,例如那些被看作不服從的、怠忽職守的,或違反規則的女性。另一方面,這個模型終結了一種想法:厭女情結和性渴望從某種角度來說不相容(儘管莫名其妙,但正如我們所見,還是有人擁護這種想法)。羅傑對阿法斐姊妹會女性成員的性渴望,以及他希望她們也想要他的渴望,在他醞釀憤怒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表示,面對她們時,他感到無力。從他的角度看來,她們「掌握」了他,而他對於即將發生的羞辱感到深深的憤怒,如同一名飢餓的用餐者,他所感受到的弱勢地位很可能導致他對擅離職守的服務生暴怒。
這個模型也初步預測了某些典型的厭女情結攻擊目標和受害者。前者包括那些被認定「不稱職」的女人--性別理念的叛徒、壞女人、「難以控制」的女人。受害者經常會包括進入了對男性而言具有權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避開或選擇逃脫服務男性的女性。
(未完)
摘自第六章〈赦免男性〉
同理他心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歲的史丹佛大學學生布洛克.透納接受審判,因為他把一名二十二歲的年輕女性當成俎上肉對待──一場校園派對之後,他在一輛垃圾車後方性侵了她;他侵犯的這名女性來此探望自己的妹妹,被發現時已不省人事。在布洛克被捕後以及整個審判期間,他父親的主要擔憂是兒子再也無法享受一塊現烤的美味肋眼牛排,他失去了胃口。我們之中許多人在閱讀丹.透納寫給法官的信時也胃口盡失。在信中,他沉痛感嘆,他的兒子不再是過去那個「隨遇而安」、「好相處」的大學運動員。但是,他本來是嗎?
本案法官艾倫.裴斯基也同樣擔憂有罪判決會對透納的未來造成「重大影響」,因而判了他就一般標準而言非常寬大的刑期(於郡監獄中服刑六個月與三年緩刑,他最終只服刑三個月)。整個審理與判決過程中,布洛克.透納的高超泳技被再三強調。而丹.透納仍舊不滿意,認為兒子根本不應該坐牢;根據他的描述,他兒子的犯罪僅僅是二十年的良好表現裡「二十分鐘的行為」。
但是,就如同殺人犯不能因為他沒有殺害的人邀功,透納也不會因為他沒有侵犯的女性而改變他的強暴犯身分。我們也必須說:當有了一個受害者,往往就有更多受害者。因此他父親估計的比例可能偏低了。
這個案例生動闡明了一個經常受到忽略的厭女情結鏡像,我稱之為:同理『他』心。它被忽視的程度之高,使它成了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借用貝蒂,傅瑞丹出自《女性迷思》一書的知名用語,但這不是因為同理他心的問題很罕見,相反的,正因如此常見,導致我們將其視為日常。
在此,同理他心在此展示的型態,是一種對性暴力的男性加害者表現出的過度同情。在當代的美國社會裡,這經常被延伸到白人、身心健全,以及在其他方面具有特權的「模範金童」身上,例如透納,他是史丹佛游泳獎學金的獲獎人。隨之而來,人們不願意相信指控這些男人的女性,或甚至不願懲罰罪證確鑿的模範金童──透納一案再次是個例證。
造成這種否定心理的原因之一是一種錯誤的認知,認為強暴犯必然具備某種樣貌:令人發毛、怪異,並且明目張膽表現出他們缺乏人性。布洛克.透納不是一個怪物,他的一名女性友人在信裡這樣寫,並指責政治正確導致了他被判有罪。他是「夏令營般的校園環境」下的受害者,在這裡,事情因為酒精和「被蒙蔽的判斷能力」而「失去控制」。透納的罪行「完全不同於一名女性去停車場取車遭綁架強暴」的情況;她寫道,「那是強暴犯,而我肯定布洛克不是那種人。」
她隨後補充,她認識布洛克多年,他總是非常關心、尊重她,對她很親切,因此布洛克不是一個強暴犯,他的友人再次堅持。法官裴斯基同意她的評價,「這在我聽來很有道理, 某程度上和相關證詞中對他在事發前的性格描述一致,都很正面。」
布洛克的友人與本案法官似乎都依照以下的推論模式進行思考:一名模範金童不是強暴犯,一名模範金童是如此這般的樣貌,因此如此這般的樣貌不是一個強暴犯。這就是「正人君子布魯特斯」問題。
是時候讓我們放棄模範金童的迷思了,拒絕這個重大假設,學著在適當的時刻以後件否定前件。透納在垃圾車後的小巷裡被人當場撞見,他正在性侵受害者,她因為酒醉而失去意識。這是強暴,而強暴他人的人等於強暴犯,故透納是一個強暴犯──他也是一名模範金童。因此……
我們太常移開目光,拒絕面對性暴力在美國整體社會,尤其是在大學校園內的普及程度和特性。我們向自己保證,真正的強暴犯會是帶角和乾草叉的惡魔樣貌,或如同怪物那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生物)出現在我們的雷達上;怪物無法被理解、詭異,而且在外表上令人害怕。強暴犯的可怕之處就在於,除了他們多數時候皆為男性這點以外,他們缺少可辨識的記號與特徵,強暴犯是人類,太像人類的人類,而他們就存在於我們之中。透過誇張的描寫,強暴犯如同怪物的想法達到了赦免的功效。
另一個迷思則是強暴犯是精神變態,他們被描繪成無情、沒有感覺、殘酷成性;這個描述對兩方群體而言都不正確(不是指兩者之間並無重疊,因為現實中確實有)。許多性侵害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性侵者對他人沒有任何掛念或覺察,而是因為侵略、挫折、控制欲望, 以及再一次,一種我理應得的權利感──無論是已受到侵害的,還是仍被期待著的權利。這也表示,儘管酒精與其他影響意識的物質,還有兄弟會文化都毫無疑問促成了性侵害的普及程度,但它們比較像是啟動機制,而非動機。
即使是在已準備好承認性侵害有多普遍並同意上述這類迷思的人之中,也存在著一種隱約、常見的一廂情願,認為造成大學校園內性侵害的主因是青年的經驗不足和無知,而排除了厭女侵略、連續性的性掠奪,以及鼓勵並保護犯罪者的規範──也就是強暴文化。丹.透納說,他的兒子承諾全心投入教育其他人「飲酒和亂『性』的危險」,法官裴斯基贊同這個計畫。但性不是問題,暴力才是。在這個時間點上主張布洛克.透納可以是個合適的反性暴力代言人,這個建議最寬容地說都令人感到屈辱。在擅自幫別人上課之前,他需要自己先上一堂道德課,而在透過性暴力取得上風之後,竟如此著急想站上道德高地,強烈說明在這件事上,他還沒有學到關鍵的一課:在任何權力階序裡的卓越位置,都不是他與生俱來的道德權利。
然而,對他的父親、法官、友人生氣很容易,某程度上也合理。但若認為他們反映了另一個層次的道德愚昧,那就錯了。他們其實只是處在一條「同情男性」的光譜的極端,而我們許多人同樣身處這條光譜之中。為布洛克.透納說話的人展現了原諒的傾向,打造了赦免敘事。這些敘事太常被延伸到與他處境相同的男性身上;這種傾向主要源自於我們鮮少批判的能力和特質,例如同情心、同理心、對友人的信任、對子女的奉獻,以及在證據允許的情況下,對他人的良善性格抱持最高度的信心。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些確實都是重要的能力和特質,但當其他條件並不相等,它們也可能有不好的一面。比方說,當社會仍舊廣泛不平等,天真地挪用它們,將可能使已比他人擁有更多不合理特權的人更進一步獲得特權,且代價可能是不公地抨擊、責怪、羞辱,進一步危害與消抹他們的受害者當中最弱勢的一群。在一些情況裡,意識到這一點的犯罪者會以此為基礎挑選受害者。我將在本章最後談這個主題,同時討論丹尼爾.霍茲克洛一案中清楚展現的厭黑女情結。
對布洛克.透納這類犯罪者的過度同情心可以歸咎於──同時也促成了──在面對其受害者的傷害、羞辱和(某種程度上歷久不衰的)創傷時,我們的關懷不足。同時,它來自並導致一種傾向,讓歷史上的支配群體者在面對一直以來的從屬群體者時,得以逍遙法外──譬喻上或實際層面上皆是。在男性支配的情境裡,我們會先同情他,而這基本上就讓他成了自身犯罪的受害者。因為如果強暴者在一開始就先因為失去食欲或游泳獎學金獲得同情,他在故事裡便將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我將於下一章裡談到,一位受害者的敘事裡需要一名反派或一名加害者(至少在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裡是如此)。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誰是造成強暴者落入這個「要不是」(but-for)的境地?除了那名作證指認他的人之外,別無其他,他的受害者因此便可能被重新賦予反派的角色。
我懷疑這是一套經常促成責怪受害者現象的機制,而這之所以有害,一部分是因為這完全改變了敘事,促成這個邪惡的道德角色反轉。
在此案例裡,法官和父親都沒有責怪受害者(但布洛克的女性友人有,儘管她否認);然而他們採取了一種同樣的、甚至可能更狡詐的做法:他們把受害者從敘事中徹底消抹了。在他們的故事裡,她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但於此案裡,受害者拒絕無聲離去。她被允許在法庭上讀出她強而有力、撼動人心的聲明,她以費盡苦心的清明思路揭露了布洛克.透納的犯罪對她的影響。他不僅違背她的意願,甚至在事後改寫她的心智;在他的行為於她記憶所留的空白上,他套上自己的故事,伴隨著許多省略和編造。(「根據他的說詞,我很享受。我很享受。」她恐懼且不可置信地在一篇報導裡讀到這件事──她也從同篇報導裡得知自己被發現時的狀態:半裸與無意識。)於是, 在那場性侵裡,無論是關於她的身體,還是她身體的故事,這名受害者都被奪去了正當的發言權威。她接著說明:
「我收到警告,因為他現在知道我不記得了,他將能夠撰寫劇本;他可以說任何他想說的,沒有人可以抗議。我沒有權力,沒有聲音,我毫無防禦。我的失憶將被用來攻擊我,我的證詞薄弱、不完整,而我被說服相信,也許我不夠好,無法贏得這場官司。他的律師不斷提醒陪審團,我們唯一能夠相信的人是布洛克,因為她不記得了。無助感使我飽受創傷。
(中略)這場性侵是這麼鐵錚錚的事實,我卻得在審判庭上,回答這類問題:
妳年紀多大?體重多少?妳那天吃了什麼?好吧,妳那天晚餐吃了什麼?(中略)誰給妳飲料的?妳平常會喝多少?誰載妳去派對?幾點?但具體是哪裡?妳穿什麼?(中略)妳曾醉到失去意識多少次?妳參加兄弟會的派對嗎?妳和男朋友是認真的嗎?妳和他發生過性關係嗎?妳們從什麼時候開始交往?妳有沒有可能偷吃?妳偷吃過嗎?當妳說妳想要獎勵他,妳是什麼意思?妳記不記得妳是幾點醒來的?妳還穿著妳的羊毛衫嗎?妳的羊毛衫是什麼顏色?對那晚妳還記得些什麼?不記得了?好的,我們讓布洛克補充。
(中略)在一場身體侵害後,我被一連串意在攻擊我的問題侵害,好讓他們可以說,看吧,她的說法前後不一致,她頭腦不清楚,她基本上是一個酒鬼,她大概想要一夜情,他是一個運動員對吧,他們兩個人都醉了。無論如何,她記得的那些醫院裡的事情都是之後的事了,為什麼要納入考量呢?布洛克正處於人生重要的關卡,此刻他非常難受。」
這最後一句話清楚說明了同理他心的問題:當我們的立場偏袒強暴犯,我們便在他帶給受害者的傷害之上,再加諸深重的道德侮辱。我們也可能會忽略,在法律的眼中,他的罪行乃針對「人民」,也就是我們所有人,理論上如此。而針對這名挺身而出、為他的犯罪作證做著辛苦的工作,反而認為她試圖尋求個人的復仇和道德懲罰。更有甚者,她可能會被看作不知寬恕,試著從她的強暴者身上「拿走」什麼,而非為維持法律和秩序做出貢獻的人。
當我們詢問,「這是為了誰呢?」與「她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便侵蝕了一名強暴受害者作證時的立足點:在她的身體上,發生了一起對社會的罪行。我們應該認可到,儘管她的身體屬於她且只屬於她,我們卻應該集體致力於保障這個身體主人的利益。至少理應如此:這是一個道德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