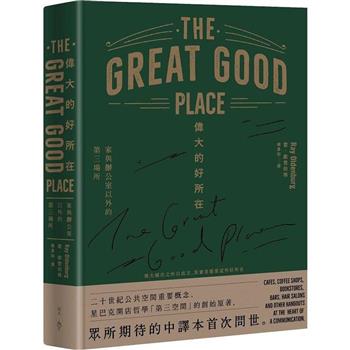第14章 邁向更好的時代……和場所
第二次世界大戰標誌著美國非正式公共生活開始衰退的歷史關頭。那場戰爭之後,無論是勝利者的土地上,還是被征服者的土地上,人們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德國人躲在家庭這種小得可憐的單位中尋求庇護,因為他們的整個社會秩序已經被戰爭摧毀,沒留下什麼其他東西。事實證明,美國人不願意、抑或者無法保護或創造足以滿足社區生活要求的都市棲地,我們躲在家和圍欄院子裡,因為周圍更大的世界漸漸失去了如家一般的品質。
正如許多細心的學者所記錄的,美國人一直存在著一種孤立的傾向,但我們的群居行為也很明顯,這點從小鎮就看得出來。有些人充分利用了這樣的生活環境,認識了許多人,也享受他們的陪伴,有些人則拒絕了這個機會。但是自從戰爭以來,即使是我們當中最善於交際的人也感受到挫折,彷彿有人合力要讓社會的非正式公共生活停止運作。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我們可能已經失去了半數本世紀中期仍存在的休閒聚會場所,這些場所維繫著輕鬆、非正式,但具有社會約束力的人際關係,是社區生活的基礎。舊街區本身和其間的咖啡館、小酒館和街角商店,已經因為都市更新、高速公路擴建和住宅規畫而生變,新的住宅區忽視了和諧團結的重要性。同時,晚近的住宅區是在消極的土地分區法規下發展起來的,
法規明令禁止所有這類社交空間,不讓在地居民舉辦非正式的聚會。
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核心環境式微,同時間人們對公共設施的興趣也普遍喪失。有人指出,當代美國人與制定憲法的那一代美國人之間最大的區別,主要就在這個面向上。我們殖民時代的先祖對公共利益非常關注,但我們已經不再關心了。一般公民對公共或社區事物的興趣,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淡薄的」和「表面的」。個人目前與集體的關係既空洞又公平:社區不為他們做什麼,他們也不為社區做什麼。而我們繼續形塑環境的方式,好像是為了維護這種危險的安排。隔離、孤立、分隔和消毒,似乎是都市成長和都市更新的指導原則。
不合適的棲地,助長了人們逃離的欲望。私人土地提供了個人負擔得起的「光榮的孤立」,尤其跟公共領域的惡化狀況相比時,私人土地顯得加倍好。但是,一個不合適的棲地,是否最終也會助長人們改變它的欲望呢?我們能解決美國的場所問題嗎?帕特里克.戈德林描繪了我所見過的當代城市生活中最黯淡的場面之一,並在過程中點出大量的證據,但他仍然相信,社區最終會取得勝利。他寫道:
我相信人類追尋真正的社區和尊嚴的本能,能夠挺過任何變化,並在危機中堅守住立場。遲早有一天,這場看似不可阻攔,如螻蟻般相殘、為組織而組織的運動,終會得到控制。
令人振奮的是,根據歷史學家對時間的衡量,「人為造成的美國困境」尚稱最近的產物。普通人還沒有意識到場所的問題,仍然傾向把糟糕的城市設計帶來的種種困難,歸咎於其他因素。舉個關鍵的例子,現代生活的空間組織,給婚姻和家庭生活帶來了很大的難題,但父母和配偶仍然老是將不良的人類棲地所固有的問題,歸咎於個性和關係。另外,也是直到最近,我們才能夠彌補城市規劃者的有限視野。我們過去掌管的大多數非正式公共生活,都代表空間使用者戰勝了空間規劃者——我們只不過接管了為其他目的所創造的場所和空間。新環境的革命之處,不是它的高速公路迷宮,或森然高聳、由深灰色玻璃外殼構成的矩形摩天大樓,而是它對於使用者主導的變更行為,有著前所未有的阻力。
但隨著規劃者的作風越來越強硬,對空間濫用的容忍度也逐漸降低。各場所無所不用其極,把人們不想要的東西強加給人類社區,這種對空間使用方式的硬性規定,會招致更多與公眾的衝突。關於人類有機體如何適應棲地,以及環境如何配合有機體的需求,美國的未來幾代人將比我們學到更多。這是一場他們被迫接受的教育。
我們要學習的事情,並非由那些寫文章或寫書的人來傳授,而是在一個設計不良的環境中,試圖享受生活的經驗所教導的。它已經在發生中。美國一些最好的城市棲地,都是民間努力對抗粗暴平庸的都市更新計畫,進而保存或恢復的。我跟戈德林一樣,相信人類愛好社區的本能最終會占上風,儘管我也同意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的觀點,認為城市政府是美國一個顯著的失敗。
許多教訓將會被吸取,也正在被吸取當中,最後會漸漸養成一群知情的公眾,願意起身對抗那些擾亂社會生活的力量。我要討論的主題已近尾聲,從這個主題所涉及的研究領域角度來看,我預料美國人的觀點和態度終究會在三種層面發生變化,每個層面都有利於繼續發展和重新發現一種非正式公共生活,也就是社區本身。
「即使我有第三場所,我也沒有時間去享受它。」這是人們常見的反應,他們欣賞參與第三場所的優點,但傾向認定這些令人愉快且帶來社交安定感的小型機構,只適合單純的往日時光和緩慢的生活節奏。想到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來建立第三場所或更普遍的社區生活,可能會把人給嚇跑。時間和精力是非常寶貴的事物,我們多半已經所剩無幾。
最終,美國人將瞭解,城市生活的節奏之所以快速和緊張,並不是因為現代化,而是因為糟糕的都市規畫。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如此荒腔走板,竟然鼓勵人們放棄最基本的承諾,為的只是要應付生活導致的種種複雜情境。試圖將一個人散落在各處的存在拼湊在一起是很困難的,即使對於那些沒什麼家累、形單影隻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當代美國社會宣稱自己為「便利文化」(convenience culture),是其中一種最荒唐的錯誤形象。便利是我們的生活和廣告媒體裡一貫的主題,只因為人們對它有迫切的需求。但我們也唯有靠著把瑣碎的便利與必要的便利混為一談,才能騙騙自己。在一個真正方便的文化中,生活必需品就在人們的住所附近,都在步行距離之內。在便利文化中,歐洲客人不會像美國的客人一樣說出「我的天,做什麼都得用車!」
我們為了糟糕的城市規畫,犧牲所有真正的便利,然後試圖在小事上做補償,來獲得便利的虛假名聲。不幸的是,塑膠信用卡、自動販賣機咖啡、電動開罐器、預先包裝好的冷凍晚餐等便利措施,對於解決一個不方便的社會的基本問題毫無幫助。它們所節省的時間,是以降低品味、鑑別度和紀律,以及喪失重要社會儀式為代價。
對大多數人來說,上班不再是苦差事。工作具有連貫性,也很單純,經常需要的東西就在手邊。如果住宅區也能獲得相同的品質,如果生活和生產一樣重要,那麼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會更加簡單和充實。在美國,生產活動的領域安排得相當好,但社區和家庭生活的領域卻嚴重失調。工作以外的時間安排常有範圍過大、事情過於雜亂、發散的困擾,職場世界倒是毫不受影響。因此,很多人發現,工作很容易,但生活很艱難。
能在步行範圍之內獲得必需品,是鄰里街區是否具有活力的決定性特徵,亦是其共同點。如果當地居民只在家裡吃飯、睡覺和看電視,對社區的利用並不多,那麼便利性就不會出現。但在某些地方,只要輕鬆散個步就能買到郵票、乾洗服務、雜貨店、雜誌、甜麵包捲和一杯咖啡,私人住宅以外也會有生活感。
不必開車、停車、走路、在收銀檯前排隊、走路,然後又開車,就能夠買到忘了買的一條麵包或一加侖牛奶,實在很方便;想要換個環境或場合時,都不用靠開車就能辦到,實在很方便;要是可以派不會開車的家人去買雜貨、郵寄包裹或歸還借來的物品,也很方便。現代社區的基礎設施非常差勁,兒童再也無法被派去做點有用的差事,他們沒事情可以做,也就幫不上什麼忙。白天已經疲於奔命的父母,晚上還要繼續跑來跑去,孩子能親自體驗和發揮作用的機會太少了,他們再也無法從跑腿接觸到的人身上學習。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得要長大到可以開車或為家計奔波時,才能變得比較有用。然而,也正是在這個階段,年輕的駕駛人開始為其他人帶來不便,日益增長的汽車交通流量,堵塞住我們的城市。
當地居民會定期步行過來使用附近的設施,有效地創造了一個休閒的社會環境,他們也從中受益。步行移動開啟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開車則排除了這類互動。人們得以認識周邊的商家和鄰居,眾人之中總有幾個合拍的。鄰里街區跟小城鎮一樣,從來都不是「幸福的大家庭」,之所以便利的關鍵是,它們促成了注定要互相倚重的人之間,發現彼此和輕鬆互動的機會。寡婦和熟齡單身女性找到一起購物、吃午餐和打橋牌的夥伴;業餘機械工和木匠發現了同好,於是參與在彼此的事務當中,變得對彼此有用,同時又相處愉快。憑著當地的小道消息,撲克玩家、馬蹄鐵遊戲的投擲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成員都互相知道彼此的存在,可以自由交往互動。從眾多人當中,會隨機結交到一群朋友。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份美好的禮物——一種深刻、持久的友誼,而且其他成員也住在附近,常有機會遇到。對所有人來說,它是一個控制閥,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要接觸和參與鄰里到什麼程度,有些不想這麼做的人,可能就會順其自然。
這種環境被形容成隨機(casual)著實貼切,因為其中的意外和非正式成分很高。漫步在隨機的環境裡頭時,一個人生活所需要和享受的許多東西,都很輕鬆而且不經意地出現。無需計劃、安排或準備,人只要處在熟悉和隨機的環境中,就能獲得正向的社會經驗:他們巧遇朋友;他們天天都有新鮮感、消遣和社會支持。在平常的日子裡,有幸在自己的鄰里街區有一間像樣的小酒館的人,可能會享受到更棒的「派對」,比辦公室那些人籌劃了一個月的聚會好太多了。
人們在鄰里之間的隨機接觸,使他們瞭解到彼此的情況,因此可以互相提供幫助。嬰兒床、自行車、童裝等物品,都是從不再需要這些東西的人手上傳下來的。準備購買昂貴割草機的人從有割草機的鄰居那裡得到的評估,比從試圖賣割草機給他的陌生人那裡得到的更可靠。社區居民若認識某個家庭,會對其最年輕的成員投以關愛的目光。在這種監督之下,孩子們可以受到保護,通常對撫養孩子也有所幫助。
隨機的環境無需付出努力,就能滿足許多需求,而且不會像理性規畫那樣低效率,甚至還能照顧到個人未辨識出的需求。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心理學家所說的認知偏誤,特別是與社區生活隔絕的人。那種認知的基本概念是,個人在無知的情況下,認為自己明白自身所有的需求,以及如何滿足它們。這不是真的。跟各種各樣的人一起生活在隨機的環境中,才能提供人們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而那些人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在前面討論「朋友群」的時候,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定期參與第三場所的人,漸漸會跟聚集在那裡的幾乎整個群體成為朋友。這些關係的廣度,令人感到溫暖充實。支離破碎的世界變得更加完整,而更廣泛接觸到生活的各種層面,增加了一個人的智慧和自信。在其他地方,個人往往較狹隘、較策略性地選擇朋友,通常都限於特定的職業和社會階層,因而就喪失了更廣泛的人際關係帶來的好處。隨機的社區為人們帶來更多朋友和點頭之交,遠多於個人所做出的選擇,以及選擇背後的原因,人們自然而然會從中受益。
隨機的環境,終究才是第三場所的自然棲地。第三場所的背景,其實不過就是人們在認識某個地區的人後,渴望與他們交遊的一種物理體現。能夠滿足地方需求,進而使人們相互接觸的多樣性措施,同樣也會欣然接受第三場所。美國郊區的基本缺陷是缺乏多樣性,這一缺陷可能對第三場所來說很致命。至少,一些規劃者已經看到了可能的影響。長島的一位規劃師總結說,如果郊區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反映出更多老城區和小城鎮的多樣性特徵,這種「創造和接納多樣性的意願,將是衡量郊區是否保持活力的標準。」
最近在洛杉磯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人願意接受他們的住宅區具有更高的多樣性,超過目前的土地使用分區允許的程度。對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所做的居民抽樣調查顯示,大家都極度渴望有藥局、市場、圖書館和郵局。更令人驚訝的是,只有低收入的黑人眾聲反對在附近開設酒吧。該研究還顯現,居住在一個鄰里社區,最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人際關係。社交活躍的程度排名第一;隨和、友善的氣氛第二;人身和財產安全排在第八位;安靜排第十,也是最後一位。便利性高於安全性。
美國對汽車變得過度依賴,於是消毒或淨化過的社區大量湧現,裡頭除了房屋之外,什麼都沒有。「一無所有的街區」之所以出現,只是因為人們指望汽車來滿足家庭所不能滿足的每一個需求和願望。最後,我們對汽車的過度依賴,造成生活品質惡化,很少有人能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自1970年代初或中期以來,美國人開始對汽車形成一種矛盾的態度。高速公路是通往無毒社區的生命線,但正漸漸堵塞,較小的動脈也是同樣命運。汽車每年都排放數億磅的一氧化碳,空氣變得污濁不堪。車禍造成的生命損失與每個公民密切相關。汽車相關的支出也高得離譜。
隨著消費者群體要求提高汽車安全性;隨著更多的舊街區被夷為平地,為的是擴建高速公路;隨著公民團體要求對酒駕者加重制裁;以及隨著汽車的成本開始與住宅的成本並駕齊驅,美國人將繼續為汽車運輸做出犧牲,無論他們是否願意。然而,他們最終會意識到,越來越多的犧牲和越來越下降的生活品質,是為了一個根本不健全的系統所付出的代價。當我們開始明白,依賴極度便利的結果,就是讓生活變得支離破碎又麻煩,情況就會開始改變。
最後再提一下便利性跟把鄰里恢復成隨機環境這回事,我承認偶爾有研究聲稱,根據調查,住在某個住宅區裡的人並不希望共享生活,因為他們幾乎對所有社會和個人關心的議題都缺乏共識。我只能斷定,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容易本末倒置。「共識」,如果我們這樣稱呼它的話,往往發生在互動和參與之後,而不是之前。個人和社區一樣,都在不斷演變、發展。當人們聚在一起時,他們發現有很多東西可以喜歡、可以依戀、可以為生活增添色彩,也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當他們彼此分開時(這就是無菌發展對他們的影響),共識程度哪有什麼要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標誌著美國非正式公共生活開始衰退的歷史關頭。那場戰爭之後,無論是勝利者的土地上,還是被征服者的土地上,人們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德國人躲在家庭這種小得可憐的單位中尋求庇護,因為他們的整個社會秩序已經被戰爭摧毀,沒留下什麼其他東西。事實證明,美國人不願意、抑或者無法保護或創造足以滿足社區生活要求的都市棲地,我們躲在家和圍欄院子裡,因為周圍更大的世界漸漸失去了如家一般的品質。
正如許多細心的學者所記錄的,美國人一直存在著一種孤立的傾向,但我們的群居行為也很明顯,這點從小鎮就看得出來。有些人充分利用了這樣的生活環境,認識了許多人,也享受他們的陪伴,有些人則拒絕了這個機會。但是自從戰爭以來,即使是我們當中最善於交際的人也感受到挫折,彷彿有人合力要讓社會的非正式公共生活停止運作。
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我們可能已經失去了半數本世紀中期仍存在的休閒聚會場所,這些場所維繫著輕鬆、非正式,但具有社會約束力的人際關係,是社區生活的基礎。舊街區本身和其間的咖啡館、小酒館和街角商店,已經因為都市更新、高速公路擴建和住宅規畫而生變,新的住宅區忽視了和諧團結的重要性。同時,晚近的住宅區是在消極的土地分區法規下發展起來的,
法規明令禁止所有這類社交空間,不讓在地居民舉辦非正式的聚會。
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核心環境式微,同時間人們對公共設施的興趣也普遍喪失。有人指出,當代美國人與制定憲法的那一代美國人之間最大的區別,主要就在這個面向上。我們殖民時代的先祖對公共利益非常關注,但我們已經不再關心了。一般公民對公共或社區事物的興趣,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淡薄的」和「表面的」。個人目前與集體的關係既空洞又公平:社區不為他們做什麼,他們也不為社區做什麼。而我們繼續形塑環境的方式,好像是為了維護這種危險的安排。隔離、孤立、分隔和消毒,似乎是都市成長和都市更新的指導原則。
不合適的棲地,助長了人們逃離的欲望。私人土地提供了個人負擔得起的「光榮的孤立」,尤其跟公共領域的惡化狀況相比時,私人土地顯得加倍好。但是,一個不合適的棲地,是否最終也會助長人們改變它的欲望呢?我們能解決美國的場所問題嗎?帕特里克.戈德林描繪了我所見過的當代城市生活中最黯淡的場面之一,並在過程中點出大量的證據,但他仍然相信,社區最終會取得勝利。他寫道:
我相信人類追尋真正的社區和尊嚴的本能,能夠挺過任何變化,並在危機中堅守住立場。遲早有一天,這場看似不可阻攔,如螻蟻般相殘、為組織而組織的運動,終會得到控制。
令人振奮的是,根據歷史學家對時間的衡量,「人為造成的美國困境」尚稱最近的產物。普通人還沒有意識到場所的問題,仍然傾向把糟糕的城市設計帶來的種種困難,歸咎於其他因素。舉個關鍵的例子,現代生活的空間組織,給婚姻和家庭生活帶來了很大的難題,但父母和配偶仍然老是將不良的人類棲地所固有的問題,歸咎於個性和關係。另外,也是直到最近,我們才能夠彌補城市規劃者的有限視野。我們過去掌管的大多數非正式公共生活,都代表空間使用者戰勝了空間規劃者——我們只不過接管了為其他目的所創造的場所和空間。新環境的革命之處,不是它的高速公路迷宮,或森然高聳、由深灰色玻璃外殼構成的矩形摩天大樓,而是它對於使用者主導的變更行為,有著前所未有的阻力。
但隨著規劃者的作風越來越強硬,對空間濫用的容忍度也逐漸降低。各場所無所不用其極,把人們不想要的東西強加給人類社區,這種對空間使用方式的硬性規定,會招致更多與公眾的衝突。關於人類有機體如何適應棲地,以及環境如何配合有機體的需求,美國的未來幾代人將比我們學到更多。這是一場他們被迫接受的教育。
我們要學習的事情,並非由那些寫文章或寫書的人來傳授,而是在一個設計不良的環境中,試圖享受生活的經驗所教導的。它已經在發生中。美國一些最好的城市棲地,都是民間努力對抗粗暴平庸的都市更新計畫,進而保存或恢復的。我跟戈德林一樣,相信人類愛好社區的本能最終會占上風,儘管我也同意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的觀點,認為城市政府是美國一個顯著的失敗。
許多教訓將會被吸取,也正在被吸取當中,最後會漸漸養成一群知情的公眾,願意起身對抗那些擾亂社會生活的力量。我要討論的主題已近尾聲,從這個主題所涉及的研究領域角度來看,我預料美國人的觀點和態度終究會在三種層面發生變化,每個層面都有利於繼續發展和重新發現一種非正式公共生活,也就是社區本身。
「即使我有第三場所,我也沒有時間去享受它。」這是人們常見的反應,他們欣賞參與第三場所的優點,但傾向認定這些令人愉快且帶來社交安定感的小型機構,只適合單純的往日時光和緩慢的生活節奏。想到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來建立第三場所或更普遍的社區生活,可能會把人給嚇跑。時間和精力是非常寶貴的事物,我們多半已經所剩無幾。
最終,美國人將瞭解,城市生活的節奏之所以快速和緊張,並不是因為現代化,而是因為糟糕的都市規畫。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如此荒腔走板,竟然鼓勵人們放棄最基本的承諾,為的只是要應付生活導致的種種複雜情境。試圖將一個人散落在各處的存在拼湊在一起是很困難的,即使對於那些沒什麼家累、形單影隻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當代美國社會宣稱自己為「便利文化」(convenience culture),是其中一種最荒唐的錯誤形象。便利是我們的生活和廣告媒體裡一貫的主題,只因為人們對它有迫切的需求。但我們也唯有靠著把瑣碎的便利與必要的便利混為一談,才能騙騙自己。在一個真正方便的文化中,生活必需品就在人們的住所附近,都在步行距離之內。在便利文化中,歐洲客人不會像美國的客人一樣說出「我的天,做什麼都得用車!」
我們為了糟糕的城市規畫,犧牲所有真正的便利,然後試圖在小事上做補償,來獲得便利的虛假名聲。不幸的是,塑膠信用卡、自動販賣機咖啡、電動開罐器、預先包裝好的冷凍晚餐等便利措施,對於解決一個不方便的社會的基本問題毫無幫助。它們所節省的時間,是以降低品味、鑑別度和紀律,以及喪失重要社會儀式為代價。
對大多數人來說,上班不再是苦差事。工作具有連貫性,也很單純,經常需要的東西就在手邊。如果住宅區也能獲得相同的品質,如果生活和生產一樣重要,那麼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會更加簡單和充實。在美國,生產活動的領域安排得相當好,但社區和家庭生活的領域卻嚴重失調。工作以外的時間安排常有範圍過大、事情過於雜亂、發散的困擾,職場世界倒是毫不受影響。因此,很多人發現,工作很容易,但生活很艱難。
能在步行範圍之內獲得必需品,是鄰里街區是否具有活力的決定性特徵,亦是其共同點。如果當地居民只在家裡吃飯、睡覺和看電視,對社區的利用並不多,那麼便利性就不會出現。但在某些地方,只要輕鬆散個步就能買到郵票、乾洗服務、雜貨店、雜誌、甜麵包捲和一杯咖啡,私人住宅以外也會有生活感。
不必開車、停車、走路、在收銀檯前排隊、走路,然後又開車,就能夠買到忘了買的一條麵包或一加侖牛奶,實在很方便;想要換個環境或場合時,都不用靠開車就能辦到,實在很方便;要是可以派不會開車的家人去買雜貨、郵寄包裹或歸還借來的物品,也很方便。現代社區的基礎設施非常差勁,兒童再也無法被派去做點有用的差事,他們沒事情可以做,也就幫不上什麼忙。白天已經疲於奔命的父母,晚上還要繼續跑來跑去,孩子能親自體驗和發揮作用的機會太少了,他們再也無法從跑腿接觸到的人身上學習。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人,得要長大到可以開車或為家計奔波時,才能變得比較有用。然而,也正是在這個階段,年輕的駕駛人開始為其他人帶來不便,日益增長的汽車交通流量,堵塞住我們的城市。
當地居民會定期步行過來使用附近的設施,有效地創造了一個休閒的社會環境,他們也從中受益。步行移動開啟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開車則排除了這類互動。人們得以認識周邊的商家和鄰居,眾人之中總有幾個合拍的。鄰里街區跟小城鎮一樣,從來都不是「幸福的大家庭」,之所以便利的關鍵是,它們促成了注定要互相倚重的人之間,發現彼此和輕鬆互動的機會。寡婦和熟齡單身女性找到一起購物、吃午餐和打橋牌的夥伴;業餘機械工和木匠發現了同好,於是參與在彼此的事務當中,變得對彼此有用,同時又相處愉快。憑著當地的小道消息,撲克玩家、馬蹄鐵遊戲的投擲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成員都互相知道彼此的存在,可以自由交往互動。從眾多人當中,會隨機結交到一群朋友。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份美好的禮物——一種深刻、持久的友誼,而且其他成員也住在附近,常有機會遇到。對所有人來說,它是一個控制閥,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要接觸和參與鄰里到什麼程度,有些不想這麼做的人,可能就會順其自然。
這種環境被形容成隨機(casual)著實貼切,因為其中的意外和非正式成分很高。漫步在隨機的環境裡頭時,一個人生活所需要和享受的許多東西,都很輕鬆而且不經意地出現。無需計劃、安排或準備,人只要處在熟悉和隨機的環境中,就能獲得正向的社會經驗:他們巧遇朋友;他們天天都有新鮮感、消遣和社會支持。在平常的日子裡,有幸在自己的鄰里街區有一間像樣的小酒館的人,可能會享受到更棒的「派對」,比辦公室那些人籌劃了一個月的聚會好太多了。
人們在鄰里之間的隨機接觸,使他們瞭解到彼此的情況,因此可以互相提供幫助。嬰兒床、自行車、童裝等物品,都是從不再需要這些東西的人手上傳下來的。準備購買昂貴割草機的人從有割草機的鄰居那裡得到的評估,比從試圖賣割草機給他的陌生人那裡得到的更可靠。社區居民若認識某個家庭,會對其最年輕的成員投以關愛的目光。在這種監督之下,孩子們可以受到保護,通常對撫養孩子也有所幫助。
隨機的環境無需付出努力,就能滿足許多需求,而且不會像理性規畫那樣低效率,甚至還能照顧到個人未辨識出的需求。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心理學家所說的認知偏誤,特別是與社區生活隔絕的人。那種認知的基本概念是,個人在無知的情況下,認為自己明白自身所有的需求,以及如何滿足它們。這不是真的。跟各種各樣的人一起生活在隨機的環境中,才能提供人們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而那些人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在前面討論「朋友群」的時候,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定期參與第三場所的人,漸漸會跟聚集在那裡的幾乎整個群體成為朋友。這些關係的廣度,令人感到溫暖充實。支離破碎的世界變得更加完整,而更廣泛接觸到生活的各種層面,增加了一個人的智慧和自信。在其他地方,個人往往較狹隘、較策略性地選擇朋友,通常都限於特定的職業和社會階層,因而就喪失了更廣泛的人際關係帶來的好處。隨機的社區為人們帶來更多朋友和點頭之交,遠多於個人所做出的選擇,以及選擇背後的原因,人們自然而然會從中受益。
隨機的環境,終究才是第三場所的自然棲地。第三場所的背景,其實不過就是人們在認識某個地區的人後,渴望與他們交遊的一種物理體現。能夠滿足地方需求,進而使人們相互接觸的多樣性措施,同樣也會欣然接受第三場所。美國郊區的基本缺陷是缺乏多樣性,這一缺陷可能對第三場所來說很致命。至少,一些規劃者已經看到了可能的影響。長島的一位規劃師總結說,如果郊區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反映出更多老城區和小城鎮的多樣性特徵,這種「創造和接納多樣性的意願,將是衡量郊區是否保持活力的標準。」
最近在洛杉磯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人願意接受他們的住宅區具有更高的多樣性,超過目前的土地使用分區允許的程度。對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所做的居民抽樣調查顯示,大家都極度渴望有藥局、市場、圖書館和郵局。更令人驚訝的是,只有低收入的黑人眾聲反對在附近開設酒吧。該研究還顯現,居住在一個鄰里社區,最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人際關係。社交活躍的程度排名第一;隨和、友善的氣氛第二;人身和財產安全排在第八位;安靜排第十,也是最後一位。便利性高於安全性。
美國對汽車變得過度依賴,於是消毒或淨化過的社區大量湧現,裡頭除了房屋之外,什麼都沒有。「一無所有的街區」之所以出現,只是因為人們指望汽車來滿足家庭所不能滿足的每一個需求和願望。最後,我們對汽車的過度依賴,造成生活品質惡化,很少有人能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自1970年代初或中期以來,美國人開始對汽車形成一種矛盾的態度。高速公路是通往無毒社區的生命線,但正漸漸堵塞,較小的動脈也是同樣命運。汽車每年都排放數億磅的一氧化碳,空氣變得污濁不堪。車禍造成的生命損失與每個公民密切相關。汽車相關的支出也高得離譜。
隨著消費者群體要求提高汽車安全性;隨著更多的舊街區被夷為平地,為的是擴建高速公路;隨著公民團體要求對酒駕者加重制裁;以及隨著汽車的成本開始與住宅的成本並駕齊驅,美國人將繼續為汽車運輸做出犧牲,無論他們是否願意。然而,他們最終會意識到,越來越多的犧牲和越來越下降的生活品質,是為了一個根本不健全的系統所付出的代價。當我們開始明白,依賴極度便利的結果,就是讓生活變得支離破碎又麻煩,情況就會開始改變。
最後再提一下便利性跟把鄰里恢復成隨機環境這回事,我承認偶爾有研究聲稱,根據調查,住在某個住宅區裡的人並不希望共享生活,因為他們幾乎對所有社會和個人關心的議題都缺乏共識。我只能斷定,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容易本末倒置。「共識」,如果我們這樣稱呼它的話,往往發生在互動和參與之後,而不是之前。個人和社區一樣,都在不斷演變、發展。當人們聚在一起時,他們發現有很多東西可以喜歡、可以依戀、可以為生活增添色彩,也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當他們彼此分開時(這就是無菌發展對他們的影響),共識程度哪有什麼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