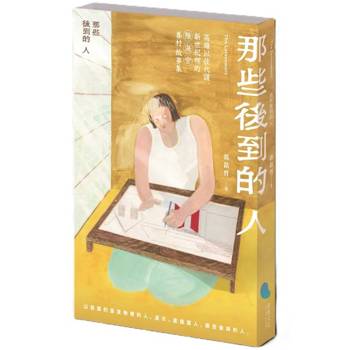行動 X 流動部落/屋合之眾:從一場場社會實驗裡玩出的我到我們
從民宿「破豆基地」開始醞釀,到流動部落這些年來匯聚出的涓涓細流,再到現在更形奔放無拘的「屋合之眾」行動,這些都是兩個女孩盧佳鈴(以下簡稱小V )和黃婉容(以下簡稱安柏)在建業新村裡掀起的一波波擾動。而一切的原點要拉回二○一六年讓她們彼此相遇的桃園地景藝術節。
彼時小V和安柏分屬不同團隊,各自貢獻著專業,是藝術節裡的「環境劇場」讓她們產生交集。藝術節結束後,志同道合的她們一路兜轉體驗人生,並在二○一八年透過以住代護申請攜手進駐到建業新村裡頭生活,最初她們不曾想過會創業,只是單純喜歡眷村的環境,又找到了適合的屋舍安身,沒想到因此一路歪斜至今,二○二○年春末,在取得合法民宿證後,第一個開始嘗試在村子裡經營的是民宿「破豆基地」。
「一路歪斜怕甚麼,青春無敵,負負會得正。實驗開始!」
正所謂萬事起頭難,當開始和空間相處後,天馬行空的想法在她們腦子裡源源不絕冒出,但現實裡諸多骨感的挑戰也隨之跟上。膽識驅使著她們不會就學,學不通就找人想辦法,頭過身不會跟著過,一次次失敗也一次次破關,這些以青春換來的珍貴歷練都將深深鑲嵌在她們身體裡,面對考驗,先獨立思考,再合體解決。進駐前後的種種細瑣她們都有明確分工,老屋修繕從木作、泥作 接電、油漆的期程規劃,到圖像的創作、排版、設計等由安柏來主導,小V則是負責空間佈置、房務工作、後續的內外資源串聯整合,還有文字創作與行銷企劃。
她們最後把申請到的眷舍空間運用得淋漓盡致,既有住宿床位可賣,能開小型工作坊、辦電影放映會,還能挪出私人空間給自己生活和創作。會將民宿取作「破豆」(phò-tāu),係因台語有「閒聊」之意,常用在熟識親友間久未碰面時總會暖心問候一句邀請對方得空時相聚聊聊,只是在她們的空間裡,聊天功能有點過分強大,常常不同的想法在這激盪後,就聊出了一朵朵亮麗的花。隨著時間與經驗累積,空間也因應需求不斷變型,她們越玩越大,好比集結村子內進駐戶們各類品牌的「建業百貨公司」,就是從破豆小房間裡變出的企劃。
如果單獨談起空間,她們也深刻察覺到,當個性、成長背景、品味偏好都不同的人被放進同一個空間裡時,感受和關注的細節可能天差地遠,但這正是最有趣的地方。安柏說,「像我喜歡觀察,以空間來說,光是面對空間和裝潢就能形成各種排列組合後的大哉問。」每當有人短暫進到空間裡時,觀察這些人會如何與空間互動也是另一件讓她們感興趣的事。互動會創造可能性,當每個角落都被妥善照顧與使用時,人與屋舍撞盪出的能量就是飽滿多元的,一種由內而外透出去的明亮狀態,這樣的狀態也都成為日後發起企劃與行動時能持續供應的能量。
「流動部落,學習型觀光的倡議行動家」
「流動部落」是小V和安柏在搬進村子後另一件積極在做的事,她們為此提出理念希望「透過學習型觀光,以『老屋生活提案的100種可能』來進行場域活化。」一百這個數字象徵著無限,但村子裡的每一戶進駐都是有時間效期的,來和去都是可預見的未來,流速可快可慢,因此如果在有限時間內,鄰里間不僅能交流情誼,也能結合彼此專長產生順流,讓村子打開後被好好看見,那就會有一種、二種、三種、N種新的認識眷村的方式能被留下來。流動背後被賦予的意義叫珍惜,原本大家只是各自守護著自己申請的屋舍,但串聯後凝聚力保護住的將是整個眷村。
她們藉由初期的觀察與試探嘗試在鄰里間擾動,進而慢慢串聯進駐戶參與企劃活動以建立共同意識,從點到線再拉成一個面。在思考如何規劃年度活動時,小V說:「我和安柏喜歡討論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然後評論它,去想像如果是我們會怎麼做!有些時候,是需求自己找上我們,在想方設法的過程裡逐步形成行動。有時則是透過閱讀,萌生了想法,就會希望通過行動去驗證。」
至今流動部落已在村子裡執行過無數有趣的企劃,好比「人人都是大導演 建業新村開麥拉」、「貓頭鷹散步計畫」、「建業人」、「趣遊眷村」、「建業童書」、「聯合眷募」、「建業百貨公司」、「設計思考工作坊」等。像「聯合眷募」就是一場大型的行動採集 向各眷戶和外界文化人發出募集邀請,集體自由創作眷村裡對家的想像,不必學有專精,只要畫畫當下的狀態是快樂的,能享受過程最重要,畫好後她們再將這些蒐集而來村子裡最真實的狀態透過策展去和外部交流,甚至產生連結。「紅門電影院」則是連續九個晚上她們在各家各戶門前,放映導演許慧如的建業新村修屋紀錄片作品《穿越時空的紅色大門》(Return to Red Gate),將影像投映在最能代表眷村意象之一的紅色家門上企圖以此堆砌時空。
可以說她們想出了好多有別於過往新奇又帶妙趣的串門子方式,但裡頭串的核心並沒有變動,只是突顯出村子裡家家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創作新型態的眷村生活,那可能是一件商品、一道料理、一段談話、一場行動等,但絕對都是建業人的日常延伸。多元行動會催化聚落保持朝氣,所有嘗試舖疊出的探索路徑,都是召喚,來為自己留下腳印。
「屋合之眾,眷村行動宇宙的再再擴充」
「屋合之眾」則是小V和安柏再次透過新一期以住代護計畫,準備打造的文化和教育基地。申請到的六十八之九號和六十八之十號眷舍,初步規劃有老屋實驗室、食農實驗室、獨立書店,還會有占卜空間,未來可以舉辦主題講座、辦讀書會、開設自力修屋的基礎修繕課程、各種工作坊等,命名核心當然還是環繞在這些沒有血緣的家人們因屋舍聚合而發生的故事,她們找尋理念契合的夥伴,彼此支撐夢想,相伴前行,願我變成我們。
由於修繕範圍和難度相較過往都巨幅升級,因此修屋過程她們根據每個階段的需求,透過社群以「打開工地的100種方式」號召有志者協力打造。從土牆前置、省視結構、敷土、上灰泥、土地板製作、蓋屋頂、養灰、油漆、土椅製作,按部就班,找老師邊學邊做,並在每個環節結束後在粉專開設相簿整理紀錄心得給有需要的朋友們參考。這真的是一場耗時數月超大型的修屋行動和社會實驗,在面對空間丟出的種種難題時,她們也同步梳理著自己和夥伴新覺察到的感受和需求並練習回應。
屋合之眾總共有三棟主建物,其中一棟她們交由「樂聲手釀綠屋」的青玿姐來主導,青玿姐一家在原申請的屋舍五年到期離開後又把整個綠屋的核心都搬了過來。她們為了造一個窯,跟著開了一個戶外廚房工作坊,沒有要隨便玩玩,過程中可是請來專業老師帶領,分四個階段照表操課,最後成功讓村子裡出現了一座絕美的灶窯。
首場食物派對在慎重開窯和起火後,喜氣洋洋地迎來了自製窯烤比薩那一幕幕畫面裡歡鬧而愉悅的笑語,強勁的能量在每個角落間流動著,那是真真正正的活著,活出了一個里程碑。這裡的生活都不只是用「過」的,可以玩,可以鬧,可以靜,可以動,所有發生過的和即將發生的都只能眼見為憑,因為宇宙的擴充,you never know!
從基地、部落再到屋合之眾行動,喜歡她們在講座上和聆聽者分享的這段話:「個人立場來自過去的生活經驗,多面向的觀察與學習是地基,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判斷,將有助於打破立場。」終歸眷村的存在是因為人,任何立場都存在對視面,向老屋學習的「學」字,在這裡不是陳腔濫調,而是被賦予的實際行動,因為惟有行動,下一個階段的交集才有可能到來。
從民宿「破豆基地」開始醞釀,到流動部落這些年來匯聚出的涓涓細流,再到現在更形奔放無拘的「屋合之眾」行動,這些都是兩個女孩盧佳鈴(以下簡稱小V )和黃婉容(以下簡稱安柏)在建業新村裡掀起的一波波擾動。而一切的原點要拉回二○一六年讓她們彼此相遇的桃園地景藝術節。
彼時小V和安柏分屬不同團隊,各自貢獻著專業,是藝術節裡的「環境劇場」讓她們產生交集。藝術節結束後,志同道合的她們一路兜轉體驗人生,並在二○一八年透過以住代護申請攜手進駐到建業新村裡頭生活,最初她們不曾想過會創業,只是單純喜歡眷村的環境,又找到了適合的屋舍安身,沒想到因此一路歪斜至今,二○二○年春末,在取得合法民宿證後,第一個開始嘗試在村子裡經營的是民宿「破豆基地」。
「一路歪斜怕甚麼,青春無敵,負負會得正。實驗開始!」
正所謂萬事起頭難,當開始和空間相處後,天馬行空的想法在她們腦子裡源源不絕冒出,但現實裡諸多骨感的挑戰也隨之跟上。膽識驅使著她們不會就學,學不通就找人想辦法,頭過身不會跟著過,一次次失敗也一次次破關,這些以青春換來的珍貴歷練都將深深鑲嵌在她們身體裡,面對考驗,先獨立思考,再合體解決。進駐前後的種種細瑣她們都有明確分工,老屋修繕從木作、泥作 接電、油漆的期程規劃,到圖像的創作、排版、設計等由安柏來主導,小V則是負責空間佈置、房務工作、後續的內外資源串聯整合,還有文字創作與行銷企劃。
她們最後把申請到的眷舍空間運用得淋漓盡致,既有住宿床位可賣,能開小型工作坊、辦電影放映會,還能挪出私人空間給自己生活和創作。會將民宿取作「破豆」(phò-tāu),係因台語有「閒聊」之意,常用在熟識親友間久未碰面時總會暖心問候一句邀請對方得空時相聚聊聊,只是在她們的空間裡,聊天功能有點過分強大,常常不同的想法在這激盪後,就聊出了一朵朵亮麗的花。隨著時間與經驗累積,空間也因應需求不斷變型,她們越玩越大,好比集結村子內進駐戶們各類品牌的「建業百貨公司」,就是從破豆小房間裡變出的企劃。
如果單獨談起空間,她們也深刻察覺到,當個性、成長背景、品味偏好都不同的人被放進同一個空間裡時,感受和關注的細節可能天差地遠,但這正是最有趣的地方。安柏說,「像我喜歡觀察,以空間來說,光是面對空間和裝潢就能形成各種排列組合後的大哉問。」每當有人短暫進到空間裡時,觀察這些人會如何與空間互動也是另一件讓她們感興趣的事。互動會創造可能性,當每個角落都被妥善照顧與使用時,人與屋舍撞盪出的能量就是飽滿多元的,一種由內而外透出去的明亮狀態,這樣的狀態也都成為日後發起企劃與行動時能持續供應的能量。
「流動部落,學習型觀光的倡議行動家」
「流動部落」是小V和安柏在搬進村子後另一件積極在做的事,她們為此提出理念希望「透過學習型觀光,以『老屋生活提案的100種可能』來進行場域活化。」一百這個數字象徵著無限,但村子裡的每一戶進駐都是有時間效期的,來和去都是可預見的未來,流速可快可慢,因此如果在有限時間內,鄰里間不僅能交流情誼,也能結合彼此專長產生順流,讓村子打開後被好好看見,那就會有一種、二種、三種、N種新的認識眷村的方式能被留下來。流動背後被賦予的意義叫珍惜,原本大家只是各自守護著自己申請的屋舍,但串聯後凝聚力保護住的將是整個眷村。
她們藉由初期的觀察與試探嘗試在鄰里間擾動,進而慢慢串聯進駐戶參與企劃活動以建立共同意識,從點到線再拉成一個面。在思考如何規劃年度活動時,小V說:「我和安柏喜歡討論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然後評論它,去想像如果是我們會怎麼做!有些時候,是需求自己找上我們,在想方設法的過程裡逐步形成行動。有時則是透過閱讀,萌生了想法,就會希望通過行動去驗證。」
至今流動部落已在村子裡執行過無數有趣的企劃,好比「人人都是大導演 建業新村開麥拉」、「貓頭鷹散步計畫」、「建業人」、「趣遊眷村」、「建業童書」、「聯合眷募」、「建業百貨公司」、「設計思考工作坊」等。像「聯合眷募」就是一場大型的行動採集 向各眷戶和外界文化人發出募集邀請,集體自由創作眷村裡對家的想像,不必學有專精,只要畫畫當下的狀態是快樂的,能享受過程最重要,畫好後她們再將這些蒐集而來村子裡最真實的狀態透過策展去和外部交流,甚至產生連結。「紅門電影院」則是連續九個晚上她們在各家各戶門前,放映導演許慧如的建業新村修屋紀錄片作品《穿越時空的紅色大門》(Return to Red Gate),將影像投映在最能代表眷村意象之一的紅色家門上企圖以此堆砌時空。
可以說她們想出了好多有別於過往新奇又帶妙趣的串門子方式,但裡頭串的核心並沒有變動,只是突顯出村子裡家家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創作新型態的眷村生活,那可能是一件商品、一道料理、一段談話、一場行動等,但絕對都是建業人的日常延伸。多元行動會催化聚落保持朝氣,所有嘗試舖疊出的探索路徑,都是召喚,來為自己留下腳印。
「屋合之眾,眷村行動宇宙的再再擴充」
「屋合之眾」則是小V和安柏再次透過新一期以住代護計畫,準備打造的文化和教育基地。申請到的六十八之九號和六十八之十號眷舍,初步規劃有老屋實驗室、食農實驗室、獨立書店,還會有占卜空間,未來可以舉辦主題講座、辦讀書會、開設自力修屋的基礎修繕課程、各種工作坊等,命名核心當然還是環繞在這些沒有血緣的家人們因屋舍聚合而發生的故事,她們找尋理念契合的夥伴,彼此支撐夢想,相伴前行,願我變成我們。
由於修繕範圍和難度相較過往都巨幅升級,因此修屋過程她們根據每個階段的需求,透過社群以「打開工地的100種方式」號召有志者協力打造。從土牆前置、省視結構、敷土、上灰泥、土地板製作、蓋屋頂、養灰、油漆、土椅製作,按部就班,找老師邊學邊做,並在每個環節結束後在粉專開設相簿整理紀錄心得給有需要的朋友們參考。這真的是一場耗時數月超大型的修屋行動和社會實驗,在面對空間丟出的種種難題時,她們也同步梳理著自己和夥伴新覺察到的感受和需求並練習回應。
屋合之眾總共有三棟主建物,其中一棟她們交由「樂聲手釀綠屋」的青玿姐來主導,青玿姐一家在原申請的屋舍五年到期離開後又把整個綠屋的核心都搬了過來。她們為了造一個窯,跟著開了一個戶外廚房工作坊,沒有要隨便玩玩,過程中可是請來專業老師帶領,分四個階段照表操課,最後成功讓村子裡出現了一座絕美的灶窯。
首場食物派對在慎重開窯和起火後,喜氣洋洋地迎來了自製窯烤比薩那一幕幕畫面裡歡鬧而愉悅的笑語,強勁的能量在每個角落間流動著,那是真真正正的活著,活出了一個里程碑。這裡的生活都不只是用「過」的,可以玩,可以鬧,可以靜,可以動,所有發生過的和即將發生的都只能眼見為憑,因為宇宙的擴充,you never know!
從基地、部落再到屋合之眾行動,喜歡她們在講座上和聆聽者分享的這段話:「個人立場來自過去的生活經驗,多面向的觀察與學習是地基,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判斷,將有助於打破立場。」終歸眷村的存在是因為人,任何立場都存在對視面,向老屋學習的「學」字,在這裡不是陳腔濫調,而是被賦予的實際行動,因為惟有行動,下一個階段的交集才有可能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