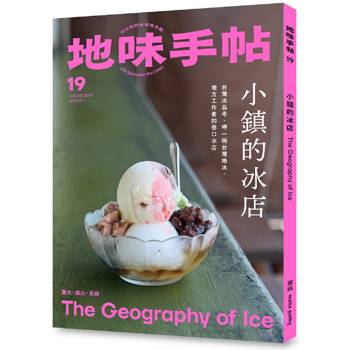〈Apyang Imiq:返鄉辛苦,但很浪漫〉
(內文)
初夏午後,清水溪的水聲尚未抵達只容一人步行的窄仄山徑,Apyang Imiq(程廷)已經開始描述溪的模樣。他走在前頭,踩著夾腳拖的腳步輕盈,一邊撥開及膝的颱風草、彎腰鑽過前日被暴雨衝倒的矮木,一邊說:「每年暑假,我們一群小孩每天自己走長長的山路來這裡報到。」
走下河堤前,他點上三支菸,跟祖靈打招呼,帶著我們攀過乾涸鋪滿巨石的河谷走到「第二關」,這裡是他童年時學會游泳的地方。太魯閣族人稱清水溪為「Yayung Qicing」,Yayung是河流, Qicing是太陽照不到之地,族人們用身體感官為這片有山林遮蔭的銀灰色河谷命名,孩子們則用遊戲闖關的方式記憶他們的夏日遊憩勝地。
「好美啊!」Apyang從未踏進同一條Yayung Qicing兩次,眼睛裡帶著彷彿初來乍到、滿出來的喜歡與驚奇,「很奇怪吼?我每天在這裡,怎麼還是覺得這麼美!」
回到深邃的河谷
約莫在十年前,Apyang回到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問他理由,他雲淡風輕:「我就覺得想要,是自然而然。」
「支亞干」音譯自太魯閣語「Ciyakang」,意為深邃的河谷,此處還有一個古老的名字「Rangal Qhuni」打開的樹洞,源於部落裡的支亞干溪上游幽閉曲折,綿延至靠近部落所在的溪口,河道頓時開闊,陽光拂照,彷彿深邃洞穴被打開。這些年,Apyang走回樹洞,進入支亞干,學族語、種小米、打獵、搭工寮、學編織,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田野調查工作,創立「阿改玩生活」旅遊體驗公司,以《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二〇二一)給家鄉的炙熱情書,於太魯閣語與中文之間自在橫跳,獲該年度台灣文學獎.蓓蕾獎、OPENBOOK好書獎。
讓人意外的是,母語文化看似深入骨髓的Apyang,卻如八、九〇年代多數部落長大的孩子,被忙於生計的務實父母放養長大,小學六年只上過一堂族語課,部落沒有在少年時期的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高中畢業後,他還沒想過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生活,只是順理成章地往大都市、好學校走,相信智慧在他方,必須遠赴取經,沒料到政大民族系、台大城鄉所等學院訓練為他指向一條回家的路。
Apyang認為在台北的十年是學習的歷程。但該學什麼,才能轉變自身?他在民族學中學習田野調查的方法,在城鄉所則鍛鍊出盤整社區營造繁雜事務的核心。這些訓練,都是為了讓他更靠近自己的部落、自己的家,但理論與身體經驗相距甚遠。他還記得,大學時班上一位來自桃園拉拉山的泰雅族同學,族語流暢得不得了,「我嚇一跳,明明大家年紀一樣,但我們的落差這麼大。」他苦於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描述世界,「那時候就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很想要再回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他的碩士論文以支亞干部落為研究對象,摸索近代太魯閣族部落空間變遷,他拜訪部落耆老想回顧、梳整家鄉的故事,卻面臨語言不通的失語窘境,只好求助學長翻譯。從那時起,他有意識地一字一句學習族語,鋪展回家的路,先是接下政大民族系教授的科技部計畫研究助理,「我是有預謀的!」如他預期,同一計畫在東華大學開缺,他旋即請調回花蓮,此後密集參與支亞干社區發展協會的文史調查工作,如製作部落立體地圖、舉辦各項課程、活動等。
對部落的研究走向經驗與實證,知識從土地中開展出身體,Apyang在每日的行動、觀察、描述與再現中,找到了自己的語言。
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Apyang在《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寫自己的部落,訴說日常周遭的植物、自己的家、自己愛的人,那種誠實與熱烈,完全是陽光底下的感覺。
但在部落的日子並非毫無陰影,他不諱言說出口前的糾結與黑暗,「剛返鄉的前幾年,我不可能去跟家人講,因為教會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不可能公開。」在個人、家族、公共性緊密交織的部落社群中,說不出口的是性向。他回憶,二〇一八年台灣同婚公投共有三項與同性婚姻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提案,「部落很多人都在發傳單,要你投下同意票,也有人直接給我傳單,我表面上說『好好好』收起來,回頭就把它撕掉了。」他有些咬牙切齒地說起那些傳單、那次充斥排擠與歧視的公投結果,「從那時候開始,幾乎能講的,我就會講。」
父母從最開始的否認、憤怒,到現在坦然接受Apyang的真實模樣與他的伴侶,是他透過不斷地溝通與實踐換來的,「我不再只是在地方學習知識與文化,也想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持續在這裡生活。如果這個地方不能變成我住起來舒服的地方,年輕人也不可能願意留下來啊。」
今年九月,他即將出版短篇小說集《大腿山》,從各種性與性別的多元樣貌,反思欲望、自由、性別、認同與權力關係,「我覺得談性是很自然的,可以看出社群的關係。」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三、四年,許多故事是基於現實的轉譯。書名取自太魯閣語中人體與山體的映照關係,「Btriq」意指山的底部,也指人的大腿,「我好像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地方創作。」
他說,喜歡是做出來的,「如果可以讓地方產生一些改變,我滿願意做的。」進入支亞干,他對於自己是誰、相信的事情、堅守的價值,都更加明確。「我不會因為跟我的想法不一致,就想要離開,我把它視為常態,在能力範圍之內,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他不再只是文化的學徒,也逐漸成為部落的參與者與榜樣,包含整合返鄉後的田野經驗,創立「阿改玩生活」規劃六條部落體驗路線,包含與當地族人、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及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合作規劃的「支亞干遺址」走讀,不只帶領遊客體驗支亞干的過去與現在,未來也將串聯更多不同部落的青年創生地方,「有滿多年輕人私下跟我說,他們是看到了阿改,覺得很羨慕,也觸動他們可以回部落,多做一些事情。」
「當我覺得一件事情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我不會輕易放過。要一直做,不能做一次受挫就不做了,要一直做下去。」部落有太多眼睛,名聲得自己掙來,他驕傲地笑著說:「如果你去部落裡面問:Apyang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應該會說:『他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在地方建立歸屬
歸屬也是做出來的,Apyang說起三石灶(rqda)的故事。
每回帶旅人走進部落,他總會介紹三顆不起眼的石頭。太魯閣族以小家庭為核心,當孩子長大,父母會協助他找到土地,搬出家門,立下三石灶,開始自己的生活。三石灶象徵父、母、孩子,不只是炊事結構,是家庭、流動社會的縮影,也是一種關係的記憶。過去,獵人如果在山中找不到食物,可以去別人家的三石灶挖掘,其中可能藏著前一位獵人煙燻好的肉,用葉子包裹、埋在灰燼下。獵人吃下後,補足體力,再去打獵,把肉重新埋回原位。這樣的共享機制,支撐山林裡的互助信任,「這是一個相互幫忙的循環,我覺得這個故事很美。」
獵人互助的故事,是一位部落姐姐告訴Apyang的,這也是她幾年前過世的父親向她訴說的故事,如今又透過Apyang傳遞。記憶與關係像是埋在灶下的肉,要有人翻土、吃下、交換,才能延續,就像Apyang田裡的五十顆洛神。
去年他訪談地方店家時,一位隔壁部落哥哥聽說他喜歡洛神,今年主動培了五十棵苗送來,只說了一句:「你種下去,留給我一棵。」這樣的交換,讓彼此的生命產生交集與連結。Apyang說,如果是剛回來的時候,他不會懂這是什麼——不懂這不是送禮,而是「共享」,是在地方建立歸屬,參與時間更長、關係更厚的生命情誼。
「這樣的歸屬感,是一來一往的過程。」Apyang說,這是gaya(註1)傳遞的智慧。
建立存在的價值
他鑽進支亞干愈來愈多的迴圈裡,不只是人際關係,還有日常細瑣的物事,讓他對所在的地方更好奇、更敏感、更有反應。
他興致勃勃地說起部落裡常見的血桐。原先,他對血桐葉的認識僅止於包裹食物的用途,「但我最近開始想:我一直在這裡,血桐也一直在這裡,它在不同的季節有變化,比方我有一次看到蝸牛在吃它的嫩葉,還有一次看到小花蔓澤蘭攀附它,衝破它的葉子。我看著這些葉子的變化,就覺得⋯⋯原來我還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我真的很喜歡在這個地方,太好玩了!」這些流動的日常,讓他感到快樂、富足,「那些小小的變化,都讓我反思過去怎麼這麼淺薄?它還有那麼多可以寫啊!我是在持續做的過程中,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
有人說,返鄉是一種浪漫的理想主義。Apyang同意,「前提是你有一個標準的、所謂『舒服的人生』是怎麼過的。」而他的「舒服」並不建立在一個方便的世界,「在這裡,沒有模板,我們得不斷自己去嘗試。我們從小被教育所謂『好的東西』的樣貌,但你打破它,你找到其它可能,走到另一個地方。辛苦,但很浪漫啊!」
我想起那株長在Yayung Qicing岸邊的黃藤。那時,Apyang指著長滿刺的莖葉,眉眼飛揚地說起部落裡的一位baki(註2)。有一回,Apyang與一群年輕人配戴粗繩、結了竹竿的長柄彎刀與直刀,跟著baki上山採藤。眾人鎖定目標,清除障礙物,合力拉扯,揮灑汗水,彷彿與黃藤拔河。刷地一聲,粗壯的莖幹從天而降,把baki打得滿頭血痕。眾人手足無措之際,baki卻咧嘴大笑。
他大聲地宣告:「不要管我!我很開心!」
(註)
1. gaya在太魯閣族的語義中,包含祖訓、傳統規範、戒律與禁忌等。
2. baki為太魯閣語的男性長輩、耆老之意。
(內文)
初夏午後,清水溪的水聲尚未抵達只容一人步行的窄仄山徑,Apyang Imiq(程廷)已經開始描述溪的模樣。他走在前頭,踩著夾腳拖的腳步輕盈,一邊撥開及膝的颱風草、彎腰鑽過前日被暴雨衝倒的矮木,一邊說:「每年暑假,我們一群小孩每天自己走長長的山路來這裡報到。」
走下河堤前,他點上三支菸,跟祖靈打招呼,帶著我們攀過乾涸鋪滿巨石的河谷走到「第二關」,這裡是他童年時學會游泳的地方。太魯閣族人稱清水溪為「Yayung Qicing」,Yayung是河流, Qicing是太陽照不到之地,族人們用身體感官為這片有山林遮蔭的銀灰色河谷命名,孩子們則用遊戲闖關的方式記憶他們的夏日遊憩勝地。
「好美啊!」Apyang從未踏進同一條Yayung Qicing兩次,眼睛裡帶著彷彿初來乍到、滿出來的喜歡與驚奇,「很奇怪吼?我每天在這裡,怎麼還是覺得這麼美!」
回到深邃的河谷
約莫在十年前,Apyang回到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問他理由,他雲淡風輕:「我就覺得想要,是自然而然。」
「支亞干」音譯自太魯閣語「Ciyakang」,意為深邃的河谷,此處還有一個古老的名字「Rangal Qhuni」打開的樹洞,源於部落裡的支亞干溪上游幽閉曲折,綿延至靠近部落所在的溪口,河道頓時開闊,陽光拂照,彷彿深邃洞穴被打開。這些年,Apyang走回樹洞,進入支亞干,學族語、種小米、打獵、搭工寮、學編織,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田野調查工作,創立「阿改玩生活」旅遊體驗公司,以《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二〇二一)給家鄉的炙熱情書,於太魯閣語與中文之間自在橫跳,獲該年度台灣文學獎.蓓蕾獎、OPENBOOK好書獎。
讓人意外的是,母語文化看似深入骨髓的Apyang,卻如八、九〇年代多數部落長大的孩子,被忙於生計的務實父母放養長大,小學六年只上過一堂族語課,部落沒有在少年時期的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高中畢業後,他還沒想過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生活,只是順理成章地往大都市、好學校走,相信智慧在他方,必須遠赴取經,沒料到政大民族系、台大城鄉所等學院訓練為他指向一條回家的路。
Apyang認為在台北的十年是學習的歷程。但該學什麼,才能轉變自身?他在民族學中學習田野調查的方法,在城鄉所則鍛鍊出盤整社區營造繁雜事務的核心。這些訓練,都是為了讓他更靠近自己的部落、自己的家,但理論與身體經驗相距甚遠。他還記得,大學時班上一位來自桃園拉拉山的泰雅族同學,族語流暢得不得了,「我嚇一跳,明明大家年紀一樣,但我們的落差這麼大。」他苦於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描述世界,「那時候就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很想要再回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他的碩士論文以支亞干部落為研究對象,摸索近代太魯閣族部落空間變遷,他拜訪部落耆老想回顧、梳整家鄉的故事,卻面臨語言不通的失語窘境,只好求助學長翻譯。從那時起,他有意識地一字一句學習族語,鋪展回家的路,先是接下政大民族系教授的科技部計畫研究助理,「我是有預謀的!」如他預期,同一計畫在東華大學開缺,他旋即請調回花蓮,此後密集參與支亞干社區發展協會的文史調查工作,如製作部落立體地圖、舉辦各項課程、活動等。
對部落的研究走向經驗與實證,知識從土地中開展出身體,Apyang在每日的行動、觀察、描述與再現中,找到了自己的語言。
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Apyang在《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寫自己的部落,訴說日常周遭的植物、自己的家、自己愛的人,那種誠實與熱烈,完全是陽光底下的感覺。
但在部落的日子並非毫無陰影,他不諱言說出口前的糾結與黑暗,「剛返鄉的前幾年,我不可能去跟家人講,因為教會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不可能公開。」在個人、家族、公共性緊密交織的部落社群中,說不出口的是性向。他回憶,二〇一八年台灣同婚公投共有三項與同性婚姻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的提案,「部落很多人都在發傳單,要你投下同意票,也有人直接給我傳單,我表面上說『好好好』收起來,回頭就把它撕掉了。」他有些咬牙切齒地說起那些傳單、那次充斥排擠與歧視的公投結果,「從那時候開始,幾乎能講的,我就會講。」
父母從最開始的否認、憤怒,到現在坦然接受Apyang的真實模樣與他的伴侶,是他透過不斷地溝通與實踐換來的,「我不再只是在地方學習知識與文化,也想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持續在這裡生活。如果這個地方不能變成我住起來舒服的地方,年輕人也不可能願意留下來啊。」
今年九月,他即將出版短篇小說集《大腿山》,從各種性與性別的多元樣貌,反思欲望、自由、性別、認同與權力關係,「我覺得談性是很自然的,可以看出社群的關係。」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三、四年,許多故事是基於現實的轉譯。書名取自太魯閣語中人體與山體的映照關係,「Btriq」意指山的底部,也指人的大腿,「我好像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地方創作。」
他說,喜歡是做出來的,「如果可以讓地方產生一些改變,我滿願意做的。」進入支亞干,他對於自己是誰、相信的事情、堅守的價值,都更加明確。「我不會因為跟我的想法不一致,就想要離開,我把它視為常態,在能力範圍之內,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他不再只是文化的學徒,也逐漸成為部落的參與者與榜樣,包含整合返鄉後的田野經驗,創立「阿改玩生活」規劃六條部落體驗路線,包含與當地族人、花蓮縣考古博物館及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合作規劃的「支亞干遺址」走讀,不只帶領遊客體驗支亞干的過去與現在,未來也將串聯更多不同部落的青年創生地方,「有滿多年輕人私下跟我說,他們是看到了阿改,覺得很羨慕,也觸動他們可以回部落,多做一些事情。」
「當我覺得一件事情很有趣,也很有意義,我不會輕易放過。要一直做,不能做一次受挫就不做了,要一直做下去。」部落有太多眼睛,名聲得自己掙來,他驕傲地笑著說:「如果你去部落裡面問:Apyang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應該會說:『他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在地方建立歸屬
歸屬也是做出來的,Apyang說起三石灶(rqda)的故事。
每回帶旅人走進部落,他總會介紹三顆不起眼的石頭。太魯閣族以小家庭為核心,當孩子長大,父母會協助他找到土地,搬出家門,立下三石灶,開始自己的生活。三石灶象徵父、母、孩子,不只是炊事結構,是家庭、流動社會的縮影,也是一種關係的記憶。過去,獵人如果在山中找不到食物,可以去別人家的三石灶挖掘,其中可能藏著前一位獵人煙燻好的肉,用葉子包裹、埋在灰燼下。獵人吃下後,補足體力,再去打獵,把肉重新埋回原位。這樣的共享機制,支撐山林裡的互助信任,「這是一個相互幫忙的循環,我覺得這個故事很美。」
獵人互助的故事,是一位部落姐姐告訴Apyang的,這也是她幾年前過世的父親向她訴說的故事,如今又透過Apyang傳遞。記憶與關係像是埋在灶下的肉,要有人翻土、吃下、交換,才能延續,就像Apyang田裡的五十顆洛神。
去年他訪談地方店家時,一位隔壁部落哥哥聽說他喜歡洛神,今年主動培了五十棵苗送來,只說了一句:「你種下去,留給我一棵。」這樣的交換,讓彼此的生命產生交集與連結。Apyang說,如果是剛回來的時候,他不會懂這是什麼——不懂這不是送禮,而是「共享」,是在地方建立歸屬,參與時間更長、關係更厚的生命情誼。
「這樣的歸屬感,是一來一往的過程。」Apyang說,這是gaya(註1)傳遞的智慧。
建立存在的價值
他鑽進支亞干愈來愈多的迴圈裡,不只是人際關係,還有日常細瑣的物事,讓他對所在的地方更好奇、更敏感、更有反應。
他興致勃勃地說起部落裡常見的血桐。原先,他對血桐葉的認識僅止於包裹食物的用途,「但我最近開始想:我一直在這裡,血桐也一直在這裡,它在不同的季節有變化,比方我有一次看到蝸牛在吃它的嫩葉,還有一次看到小花蔓澤蘭攀附它,衝破它的葉子。我看著這些葉子的變化,就覺得⋯⋯原來我還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我真的很喜歡在這個地方,太好玩了!」這些流動的日常,讓他感到快樂、富足,「那些小小的變化,都讓我反思過去怎麼這麼淺薄?它還有那麼多可以寫啊!我是在持續做的過程中,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
有人說,返鄉是一種浪漫的理想主義。Apyang同意,「前提是你有一個標準的、所謂『舒服的人生』是怎麼過的。」而他的「舒服」並不建立在一個方便的世界,「在這裡,沒有模板,我們得不斷自己去嘗試。我們從小被教育所謂『好的東西』的樣貌,但你打破它,你找到其它可能,走到另一個地方。辛苦,但很浪漫啊!」
我想起那株長在Yayung Qicing岸邊的黃藤。那時,Apyang指著長滿刺的莖葉,眉眼飛揚地說起部落裡的一位baki(註2)。有一回,Apyang與一群年輕人配戴粗繩、結了竹竿的長柄彎刀與直刀,跟著baki上山採藤。眾人鎖定目標,清除障礙物,合力拉扯,揮灑汗水,彷彿與黃藤拔河。刷地一聲,粗壯的莖幹從天而降,把baki打得滿頭血痕。眾人手足無措之際,baki卻咧嘴大笑。
他大聲地宣告:「不要管我!我很開心!」
(註)
1. gaya在太魯閣族的語義中,包含祖訓、傳統規範、戒律與禁忌等。
2. baki為太魯閣語的男性長輩、耆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