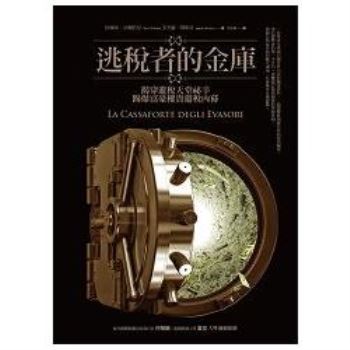第一部 我向世界的主人下戰書
祕密特工計畫
再過幾分鐘就是晚上八點,我快要到家了。那是二○○八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耶誕假期將至,我一邊走在日內瓦的街道,一邊試圖說服自己相信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剛剛才去了警察局一趟。計畫已經動了起來。現在,我只須完成已經啟動的工作。為了眼前的這一刻,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
一到家,我就開始找電話,那是特勤人員交給我的一種特殊裝置。一只白色的緊急裝置,體積只有一張信用卡那麼大,薄到可以被藏在一本書裡面,而且沒有鍵盤。他們向我解釋這是一支「乾淨」的手機——它不會留下任何線索,而且可以迴避監聽。我不能向外發話,只能要求回電。找到適當的時機,我便可以發出信號,而電話接通之後,我只能靜靜地聆聽。他們監視著我,他們知道那天在警察局裡所發生的事,他們已經準備好執行長久以來我們鉅細靡遺設計好的一切。
我按下了按鈕,我想知道離開日內瓦的時刻是否已經來到,或者我必須繼續等待。
等待他們回電的同時,我試著入睡,但沒有睡著。我想著我的女兒,尋思對她而言究竟是移居到法國比較好,還是回到我們一直住到不久前才離開的蒙地卡羅好。幸好我們還可以選擇。蒙地卡羅有幾個優點:讓我的家人住在那裡等於是向摩納哥當局表明我們中立的立場,讓他們知道我並沒有要與他們為敵。另一方面,我得到法國去完成計畫。
我把接下來的對策全盤想了一次。我再次思考了與法國稅務機關之間的合作,思考了我跟特勤人員與稅務稽查人員所建立的關係。當初,不是由我本人主動聯繫特務組織的,是透過滙豐銀行日內瓦支部的某些人。他們並非瑞士的特勤人員,我不清楚他們的國籍,但他們是隸屬於某個偽裝得極為完美、分工極為精密的機構的成員。在瑞士,我了解到了一件事,沒有一件事是跟表面上看起來一樣的。
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愛德華˙史諾登也在日內瓦,這位資訊專家揭發了世界最強大的情報部門美國國安局(NSA)祕密監控全世界的醜聞,他從二○一三年六月起流亡俄羅斯。史諾登當時在外交部門的掩護之下為美國中情局(Cia)工作。正如他本人在二○一四年八月接受《連線》月刊(Wired)採訪時所宣稱的, 二○○七年至二○○九年之間,他是某個常駐在日內瓦的情報團隊的一員。史諾登的團隊所管理的通訊系統跟我所使用過的那些非常相似。
至於我的案例,一切始於二○○六年。情報單位的人提供了我一個軟體,用來調查從滙豐私人銀行收集來的數據是否完整,以及這些資料對負責該案的法官是否有用。有鑑於我在銀行裡並沒有調閱機密資訊的權限,我必須調查出看管那些資訊的人是誰,並將情報轉告給特務人員。穿針引線地與那些資訊管理者搭上線,說服他們與我們合作,就是特務人員的工作了。以下便是二○○七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將資訊從銀行的資料庫取出然後存至雲端的人不是我,是滙豐銀行的其他員工。我的責任是每天檢查存檔的資訊,看看還少了哪些,以及還有其他哪些可取得的項目。一直到資料庫於二○○八年二月由於安全因素被凍結為止,資料庫都時有資訊新增。凌晨四點,我收到了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向我確認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並告訴我在離家不遠的一個停車場裡,已有兩輛待命的汽車。我會在指定的地點與相關人員碰頭,我的家人則會搭乘另一輛汽車,越過瑞士邊境,抵達法國境內的某處。而我和我太太先前就被告知了在法國境內會合的時間與地點。
電話鈴聲喚醒我的妻子,她過來廚房找我,便立刻了解到那一刻已然來臨。幾年來,我們都談論著這一刻,我們都知道遲早有一天警察會登門造訪。她不清楚這項行動的諸多細節,但她知道若是事態危險,我們將不得不匆匆離開瑞士。她信任我。我們有四個小時的時間為出發做準備。
我們無需收拾行李,行李早已備好,因為我們原本就計畫要在耶誕假期去旅行。特務人員會確保我們離開瑞士時沒人會在我們家門口徘徊或跟蹤。
八點的時候,我陪我的妻子和女兒去到離家不遠的停車場乘車,並向她們道別。我自己則搭乘另一輛車,前往距離日內瓦不遠的約定地點。我打電話給巴黎的法國公共財務總局(Dnef)的人,知會他我要上路了,長期以來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
旅途當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我在邊境彼方與家人重新聚首。然後我們一起繼續前往法國蔚藍海岸的小鎮卡代(Cap d’Ail),我們將在安全人員的看守保護下,在那兒停留兩個禮拜。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曾說到:如果制度不透明,有罪不罰的現象便會稱霸,最善良的牧人也會開始殺人放火。因此,想要有效打擊犯罪,我們必須更有效地宣傳我們的目標,並制定能夠吸引並聚集有志之士的計畫。我們不應忘記,當今仍有一些企業靠著貧富不均而大發利市:這些企業便是所有的離岸銀行。而金融為什麼給我們帶來問題?因為套利是銀行的基礎,銀行靠著貧富不均的狀況求生存,而銀行之所以可以這樣子恣意妄為,是因為大家對此事並不知情。一旦我們了解了這個機制,我們便能改變它。不了解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我正要離開日內瓦,去挑戰世界上規模和勢力最強大的銀行之一。我之所以會冒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險這麼做,與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向來不欣賞強者的傲慢,也未曾接受過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我住在一個避稅天堂裡,親眼見識了這種金融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巨大的財富抵達蒙地卡羅,金錢來源地的國家陷入貧窮的泥沼。我之所以選擇起身反抗而不願聽天由命,也是因為我想要留給我女兒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我不願讓她在一個一切向錢看、恃強凌弱、貪贓枉法的價值觀成為常態的世界裡長大。
而我將對抗一個鼓勵貪腐與逃漏稅、給富人提供逃稅方法,以榨乾各國政府保留給弱勢貧窮民眾的資源的銀行體制。銀行系統性的違法行為令我感到十分不齒。
我不是傻子,也不是一個透視未來的狂人,我很清楚自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我確實相信自己可以觸發一種轉變,而這種轉化的過程若是慢慢地蔓延開來,假以時日應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我想提供證據,向公共輿論和司法單位陳述金融體系的運作模式。
祕密特工計畫
再過幾分鐘就是晚上八點,我快要到家了。那是二○○八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耶誕假期將至,我一邊走在日內瓦的街道,一邊試圖說服自己相信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剛剛才去了警察局一趟。計畫已經動了起來。現在,我只須完成已經啟動的工作。為了眼前的這一刻,我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
一到家,我就開始找電話,那是特勤人員交給我的一種特殊裝置。一只白色的緊急裝置,體積只有一張信用卡那麼大,薄到可以被藏在一本書裡面,而且沒有鍵盤。他們向我解釋這是一支「乾淨」的手機——它不會留下任何線索,而且可以迴避監聽。我不能向外發話,只能要求回電。找到適當的時機,我便可以發出信號,而電話接通之後,我只能靜靜地聆聽。他們監視著我,他們知道那天在警察局裡所發生的事,他們已經準備好執行長久以來我們鉅細靡遺設計好的一切。
我按下了按鈕,我想知道離開日內瓦的時刻是否已經來到,或者我必須繼續等待。
等待他們回電的同時,我試著入睡,但沒有睡著。我想著我的女兒,尋思對她而言究竟是移居到法國比較好,還是回到我們一直住到不久前才離開的蒙地卡羅好。幸好我們還可以選擇。蒙地卡羅有幾個優點:讓我的家人住在那裡等於是向摩納哥當局表明我們中立的立場,讓他們知道我並沒有要與他們為敵。另一方面,我得到法國去完成計畫。
我把接下來的對策全盤想了一次。我再次思考了與法國稅務機關之間的合作,思考了我跟特勤人員與稅務稽查人員所建立的關係。當初,不是由我本人主動聯繫特務組織的,是透過滙豐銀行日內瓦支部的某些人。他們並非瑞士的特勤人員,我不清楚他們的國籍,但他們是隸屬於某個偽裝得極為完美、分工極為精密的機構的成員。在瑞士,我了解到了一件事,沒有一件事是跟表面上看起來一樣的。
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愛德華˙史諾登也在日內瓦,這位資訊專家揭發了世界最強大的情報部門美國國安局(NSA)祕密監控全世界的醜聞,他從二○一三年六月起流亡俄羅斯。史諾登當時在外交部門的掩護之下為美國中情局(Cia)工作。正如他本人在二○一四年八月接受《連線》月刊(Wired)採訪時所宣稱的, 二○○七年至二○○九年之間,他是某個常駐在日內瓦的情報團隊的一員。史諾登的團隊所管理的通訊系統跟我所使用過的那些非常相似。
至於我的案例,一切始於二○○六年。情報單位的人提供了我一個軟體,用來調查從滙豐私人銀行收集來的數據是否完整,以及這些資料對負責該案的法官是否有用。有鑑於我在銀行裡並沒有調閱機密資訊的權限,我必須調查出看管那些資訊的人是誰,並將情報轉告給特務人員。穿針引線地與那些資訊管理者搭上線,說服他們與我們合作,就是特務人員的工作了。以下便是二○○七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將資訊從銀行的資料庫取出然後存至雲端的人不是我,是滙豐銀行的其他員工。我的責任是每天檢查存檔的資訊,看看還少了哪些,以及還有其他哪些可取得的項目。一直到資料庫於二○○八年二月由於安全因素被凍結為止,資料庫都時有資訊新增。凌晨四點,我收到了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向我確認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並告訴我在離家不遠的一個停車場裡,已有兩輛待命的汽車。我會在指定的地點與相關人員碰頭,我的家人則會搭乘另一輛汽車,越過瑞士邊境,抵達法國境內的某處。而我和我太太先前就被告知了在法國境內會合的時間與地點。
電話鈴聲喚醒我的妻子,她過來廚房找我,便立刻了解到那一刻已然來臨。幾年來,我們都談論著這一刻,我們都知道遲早有一天警察會登門造訪。她不清楚這項行動的諸多細節,但她知道若是事態危險,我們將不得不匆匆離開瑞士。她信任我。我們有四個小時的時間為出發做準備。
我們無需收拾行李,行李早已備好,因為我們原本就計畫要在耶誕假期去旅行。特務人員會確保我們離開瑞士時沒人會在我們家門口徘徊或跟蹤。
八點的時候,我陪我的妻子和女兒去到離家不遠的停車場乘車,並向她們道別。我自己則搭乘另一輛車,前往距離日內瓦不遠的約定地點。我打電話給巴黎的法國公共財務總局(Dnef)的人,知會他我要上路了,長期以來我一直與他保持聯繫。
旅途當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我在邊境彼方與家人重新聚首。然後我們一起繼續前往法國蔚藍海岸的小鎮卡代(Cap d’Ail),我們將在安全人員的看守保護下,在那兒停留兩個禮拜。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曾說到:如果制度不透明,有罪不罰的現象便會稱霸,最善良的牧人也會開始殺人放火。因此,想要有效打擊犯罪,我們必須更有效地宣傳我們的目標,並制定能夠吸引並聚集有志之士的計畫。我們不應忘記,當今仍有一些企業靠著貧富不均而大發利市:這些企業便是所有的離岸銀行。而金融為什麼給我們帶來問題?因為套利是銀行的基礎,銀行靠著貧富不均的狀況求生存,而銀行之所以可以這樣子恣意妄為,是因為大家對此事並不知情。一旦我們了解了這個機制,我們便能改變它。不了解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我正要離開日內瓦,去挑戰世界上規模和勢力最強大的銀行之一。我之所以會冒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險這麼做,與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向來不欣賞強者的傲慢,也未曾接受過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我住在一個避稅天堂裡,親眼見識了這種金融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巨大的財富抵達蒙地卡羅,金錢來源地的國家陷入貧窮的泥沼。我之所以選擇起身反抗而不願聽天由命,也是因為我想要留給我女兒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我不願讓她在一個一切向錢看、恃強凌弱、貪贓枉法的價值觀成為常態的世界裡長大。
而我將對抗一個鼓勵貪腐與逃漏稅、給富人提供逃稅方法,以榨乾各國政府保留給弱勢貧窮民眾的資源的銀行體制。銀行系統性的違法行為令我感到十分不齒。
我不是傻子,也不是一個透視未來的狂人,我很清楚自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我確實相信自己可以觸發一種轉變,而這種轉化的過程若是慢慢地蔓延開來,假以時日應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我想提供證據,向公共輿論和司法單位陳述金融體系的運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