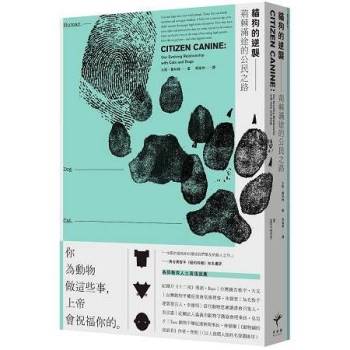P. 137
寵物法案
這項立法起源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一日星期四,就在卡崔娜颶風摧殘墨西哥灣沿岸之後三天。紐奧良大部分被水淹沒,屍體在艷陽下腐爛,紐奧良超級巨蛋變成人間煉獄。缺乏食物與飲水、垃圾及排泄物臭氣沖天、強暴及謀殺謠言四處流竄,《美國今日報》(USA Today)稱之為「人類悲慘命運的中心點」。終於,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的卡車抵達了,幾千人就這樣衝了出來、推著柵欄、擠著彼此,希望能搶到一個位置,好搭車出城。不過,當群眾在高溫下推擠時,熟悉的劇情又重演了。那些費盡千辛萬苦把貓狗帶到超級巨蛋的民眾,這時被告知:貓狗不准上車。有些人不得不因此拋棄他們僅有的家人。隊伍中,有個小男孩緊緊抱著他的小白狗,希望能不被發現。但有個警察看到他後,伸手把狗從那個小孩懷裡扯出來帶走。「雪球(Snowball),雪球!」男孩尖聲大叫。他哭得傷心欲絕,甚至哭到反胃,吐了一地。
雖然全國上下還在為卡崔娜造成的人類浩劫忙得焦頭爛額,動物的處境仍然觸動了大家的同情心。溺死的貓、被困在屋頂上的狗、寵物吃著街上的垃圾,這些景象在報紙電視中經常可見。CNN的安德森.古柏(Anderson Cooper)報導了聖伯納教區一所中學的寵物大屠殺慘劇,當時使用那裡當避難所的當地人在疏散時被迫留下他們的寵物,然後不久之後就有人來把動物都射殺了。全國上下的民眾看著受災者然後說著「那個人有可能會是我啊。」現在他們則改成說,「那也有可能是我的寵物呀。」看到畫面後他們的心都碎了,接著轉為憤怒。為什麼救難人員不救貓狗?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因為他們不能帶貓狗一起走而死去?還有,這些動物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P. 302
彼得,四十六歲,是個被困在不快樂婚姻中的男人。他不跟配偶溝通,他覺得與孩子之間有隔閡。在波士頓市外公園為孩子推盪鞦韆時,他一邊在iPhone上打字跟他的「虛擬妻子」潔德聊天。這兩位一年前於線上模擬遊戲「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結婚,周圍都是虛擬朋友。彼得從來沒有親自見過潔德,但是兩人每天都會聊天,談他們兩人之間的愛及焦慮。他們甚至還會做虛擬性愛。「第二人生給我的人際關係比現實生活還要好,」他說。「在這裡我才能感 覺到真正的我。」他身邊其他父母也都埋頭在行動裝置中。他們也活在第二人生中嗎?
彼得的故事是雪莉.透克(Sherry Turkle)二〇一一年的《群體性孤獨》(Alone Together)書中所描述的,這本書探討科技如何侵蝕我們的社會結構。我們是如何開始與真實世界失去連結,他的經驗可能是極端的例子,但是,我們所有人身上都有一點彼得的影子。一年又一年過 去,我們跟朋友及家人漸行漸遠。我們話講得少了,訊息卻傳得多了。我們喜歡臉書上的朋友甚於親身相處的朋友。我們在家裡、在咖啡館裡聚會,但卻花比較多時間凝視我們的手機,而不是與其他人相處。「我們住在模擬的文化中,」透克寫道。「我們被科技給束縛,當那個『不插電』的世界讓我們感到無足輕重、無法滿足時,我們就動搖了。」
我們跟真實世界的隔閡並不是從網路開始的。我們把社會互動讓渡給科技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電話讓我們可以跟不在同一個房間的朋友家人說話,廣播電視讓我們聚集在它們周遭、而不是聚集在一起。但是,網路延伸範圍及層面既廣又遠,網路衍生的裝置是歷史上前所未聞的。現在美國十八歲以上的成人中,超過百分之八十至少偶爾會使用網路,二〇〇〇年是百分之五十三。三分之二的美國成人會上臉書(Facebook)。我們一天至少花四小時上網,而三十歲以下所花的時間更多。我們跟筆記型電腦說晚安,跟智慧型手機道早安。我們就像彼得,開始用虛擬生活來交換真實生活。
這是很驚人的,尤其考量到以下事實:科技並沒有讓我們更快樂。缺少人類接觸,我們覺得比以前更加孤立。學者稱此為「網路的兩難」(Internet paradox):我們比從前有更多連結,但是也更孤獨。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〇年之間,美國四十五歲以上成人被認為是慢性寂寞者,從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這些數字對我們的健康相當不利。社會疏離的個體有較高風險罹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及心理狀況惡化。肥胖有上升趨勢,憂鬱也是。寂寞正在慢慢殺死我們。
不能什麼都怪我們的iPhone。我們的家庭縮小了,我們把自己從自然世界分割,而如果我們真的能活到一把年紀,孤獨終老的機會會比當代文明任何時間點還要大。在一九五〇年,介於十八歲到二十九歲之間的美國人只有百分之一是自己住,如今則是百分之七。同樣這段期間,六十歲以上的美國獨居人口,本來十個裡面有一個,增加到十個裡面有三個。一九五〇年,只有一個人的家庭少於百分之十,現在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有小孩的婦女只有從前的一半。離婚率衝高。被我們視為是知己的人數則下降。我們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孤立時代;孤獨已成為流行病。把我們連結在一起的關係正在斷裂,而且情況愈來愈糟糕。社會四分五裂,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將我們聚集起來呢?
貓狗可能是其一。同伴動物讓我們定錨在真實世界中,你總不能在臉書上跟你的狗玩,你無法用推特跟你的貓咪抱抱。牠們的愛和溫暖是這個社會日漸冷漠的解毒劑。貓狗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填補了家人朋友缺席而留下的空位。貓是不會離家的孩子,狗是不會甩掉我們而去盯著發光螢幕看的夥伴。將近有三分之一美國人以及半數單身人口說,他們依靠寵物陪伴比他人陪伴還要多。貓狗也能防止寂寞的病態效應:二〇一一年研究顯示,養寵物的人不只比沒有養的人還健康,而且自尊心比較高,比較不會覺得寂寞跟憂鬱。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有貓狗的家戶比有小孩的家戶還多,為什麼社會網絡縮小而養寵物的人遽增。
批評者說,寵物無法完全治療我們的寂寞,因為牠們並不是真正的人類。貓不是小孩,狗不是人類朋友。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們這麼努力把牠們轉變為人。我們比從前更需要與人類接觸,而當真實人類再也無法滿足我們,或是科技及現代生活將人類的存在從我們的生活中奪取,我們就把寵物人類化。寵物轉變為人,牠們就成了社會的救世主。公民的身份對他們而言可說是實至名歸。
P. 376
寵物使我們更文明,但我認為,寵物也讓我們保持野性。寵物所扮演的角色之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薩滿(shaman,主要生活於亞洲北部如西伯利亞、蒙古等地的文化族群中,是能夠與自然靈界溝通的人類巫師。)。與其說寵物牽繫了我們的世界與精神世界,不如說牠們是在都市叢林及真正的叢林之間為我們擔任中介者的角色。所有的寵物都有點流浪貓的影子,橫跨野蠻與馴化、人與野獸之間的那條線。就因為牠們能夠跨越這個邊界,牠們的角色對我們來說就像是一條生命線,與我們過去的動物性連接—也許這是最後一條生命線了。我們不只需要寵物的撫慰或一起玩耍,還需要牠們來提醒我們是誰、我們是從哪裡來的。當我們把貓狗轉變為人,我們就喪失了自身的動物性。難道我們真的準備好要這樣做了嗎?
寵物法案
這項立法起源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一日星期四,就在卡崔娜颶風摧殘墨西哥灣沿岸之後三天。紐奧良大部分被水淹沒,屍體在艷陽下腐爛,紐奧良超級巨蛋變成人間煉獄。缺乏食物與飲水、垃圾及排泄物臭氣沖天、強暴及謀殺謠言四處流竄,《美國今日報》(USA Today)稱之為「人類悲慘命運的中心點」。終於,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的卡車抵達了,幾千人就這樣衝了出來、推著柵欄、擠著彼此,希望能搶到一個位置,好搭車出城。不過,當群眾在高溫下推擠時,熟悉的劇情又重演了。那些費盡千辛萬苦把貓狗帶到超級巨蛋的民眾,這時被告知:貓狗不准上車。有些人不得不因此拋棄他們僅有的家人。隊伍中,有個小男孩緊緊抱著他的小白狗,希望能不被發現。但有個警察看到他後,伸手把狗從那個小孩懷裡扯出來帶走。「雪球(Snowball),雪球!」男孩尖聲大叫。他哭得傷心欲絕,甚至哭到反胃,吐了一地。
雖然全國上下還在為卡崔娜造成的人類浩劫忙得焦頭爛額,動物的處境仍然觸動了大家的同情心。溺死的貓、被困在屋頂上的狗、寵物吃著街上的垃圾,這些景象在報紙電視中經常可見。CNN的安德森.古柏(Anderson Cooper)報導了聖伯納教區一所中學的寵物大屠殺慘劇,當時使用那裡當避難所的當地人在疏散時被迫留下他們的寵物,然後不久之後就有人來把動物都射殺了。全國上下的民眾看著受災者然後說著「那個人有可能會是我啊。」現在他們則改成說,「那也有可能是我的寵物呀。」看到畫面後他們的心都碎了,接著轉為憤怒。為什麼救難人員不救貓狗?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因為他們不能帶貓狗一起走而死去?還有,這些動物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P. 302
彼得,四十六歲,是個被困在不快樂婚姻中的男人。他不跟配偶溝通,他覺得與孩子之間有隔閡。在波士頓市外公園為孩子推盪鞦韆時,他一邊在iPhone上打字跟他的「虛擬妻子」潔德聊天。這兩位一年前於線上模擬遊戲「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結婚,周圍都是虛擬朋友。彼得從來沒有親自見過潔德,但是兩人每天都會聊天,談他們兩人之間的愛及焦慮。他們甚至還會做虛擬性愛。「第二人生給我的人際關係比現實生活還要好,」他說。「在這裡我才能感 覺到真正的我。」他身邊其他父母也都埋頭在行動裝置中。他們也活在第二人生中嗎?
彼得的故事是雪莉.透克(Sherry Turkle)二〇一一年的《群體性孤獨》(Alone Together)書中所描述的,這本書探討科技如何侵蝕我們的社會結構。我們是如何開始與真實世界失去連結,他的經驗可能是極端的例子,但是,我們所有人身上都有一點彼得的影子。一年又一年過 去,我們跟朋友及家人漸行漸遠。我們話講得少了,訊息卻傳得多了。我們喜歡臉書上的朋友甚於親身相處的朋友。我們在家裡、在咖啡館裡聚會,但卻花比較多時間凝視我們的手機,而不是與其他人相處。「我們住在模擬的文化中,」透克寫道。「我們被科技給束縛,當那個『不插電』的世界讓我們感到無足輕重、無法滿足時,我們就動搖了。」
我們跟真實世界的隔閡並不是從網路開始的。我們把社會互動讓渡給科技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電話讓我們可以跟不在同一個房間的朋友家人說話,廣播電視讓我們聚集在它們周遭、而不是聚集在一起。但是,網路延伸範圍及層面既廣又遠,網路衍生的裝置是歷史上前所未聞的。現在美國十八歲以上的成人中,超過百分之八十至少偶爾會使用網路,二〇〇〇年是百分之五十三。三分之二的美國成人會上臉書(Facebook)。我們一天至少花四小時上網,而三十歲以下所花的時間更多。我們跟筆記型電腦說晚安,跟智慧型手機道早安。我們就像彼得,開始用虛擬生活來交換真實生活。
這是很驚人的,尤其考量到以下事實:科技並沒有讓我們更快樂。缺少人類接觸,我們覺得比以前更加孤立。學者稱此為「網路的兩難」(Internet paradox):我們比從前有更多連結,但是也更孤獨。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〇年之間,美國四十五歲以上成人被認為是慢性寂寞者,從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這些數字對我們的健康相當不利。社會疏離的個體有較高風險罹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及心理狀況惡化。肥胖有上升趨勢,憂鬱也是。寂寞正在慢慢殺死我們。
不能什麼都怪我們的iPhone。我們的家庭縮小了,我們把自己從自然世界分割,而如果我們真的能活到一把年紀,孤獨終老的機會會比當代文明任何時間點還要大。在一九五〇年,介於十八歲到二十九歲之間的美國人只有百分之一是自己住,如今則是百分之七。同樣這段期間,六十歲以上的美國獨居人口,本來十個裡面有一個,增加到十個裡面有三個。一九五〇年,只有一個人的家庭少於百分之十,現在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有小孩的婦女只有從前的一半。離婚率衝高。被我們視為是知己的人數則下降。我們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孤立時代;孤獨已成為流行病。把我們連結在一起的關係正在斷裂,而且情況愈來愈糟糕。社會四分五裂,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將我們聚集起來呢?
貓狗可能是其一。同伴動物讓我們定錨在真實世界中,你總不能在臉書上跟你的狗玩,你無法用推特跟你的貓咪抱抱。牠們的愛和溫暖是這個社會日漸冷漠的解毒劑。貓狗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填補了家人朋友缺席而留下的空位。貓是不會離家的孩子,狗是不會甩掉我們而去盯著發光螢幕看的夥伴。將近有三分之一美國人以及半數單身人口說,他們依靠寵物陪伴比他人陪伴還要多。貓狗也能防止寂寞的病態效應:二〇一一年研究顯示,養寵物的人不只比沒有養的人還健康,而且自尊心比較高,比較不會覺得寂寞跟憂鬱。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有貓狗的家戶比有小孩的家戶還多,為什麼社會網絡縮小而養寵物的人遽增。
批評者說,寵物無法完全治療我們的寂寞,因為牠們並不是真正的人類。貓不是小孩,狗不是人類朋友。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們這麼努力把牠們轉變為人。我們比從前更需要與人類接觸,而當真實人類再也無法滿足我們,或是科技及現代生活將人類的存在從我們的生活中奪取,我們就把寵物人類化。寵物轉變為人,牠們就成了社會的救世主。公民的身份對他們而言可說是實至名歸。
P. 376
寵物使我們更文明,但我認為,寵物也讓我們保持野性。寵物所扮演的角色之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薩滿(shaman,主要生活於亞洲北部如西伯利亞、蒙古等地的文化族群中,是能夠與自然靈界溝通的人類巫師。)。與其說寵物牽繫了我們的世界與精神世界,不如說牠們是在都市叢林及真正的叢林之間為我們擔任中介者的角色。所有的寵物都有點流浪貓的影子,橫跨野蠻與馴化、人與野獸之間的那條線。就因為牠們能夠跨越這個邊界,牠們的角色對我們來說就像是一條生命線,與我們過去的動物性連接—也許這是最後一條生命線了。我們不只需要寵物的撫慰或一起玩耍,還需要牠們來提醒我們是誰、我們是從哪裡來的。當我們把貓狗轉變為人,我們就喪失了自身的動物性。難道我們真的準備好要這樣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