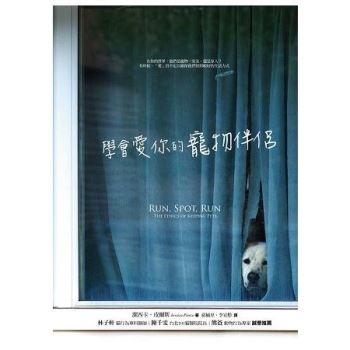第四章 為何飼養寵物伴侶?
有時我會問,為何這些小動物有著苦澀雙眼,為何我們應該照顧牠們?
──喬恩.席肯(Jon Silken),〈關愛動物〉(Caring for Animals)
大家都很清楚人類是如何跟非人類動物建立起社會依附關係的,但我們為何如此著迷於將動物變成寵物伴侶卻依然難以捉摸,就像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們聲明某隻動物是「寵物伴侶」而非食物一樣。幾乎所有的嬰兒和幼兒天生都對動物懷有好奇和興趣,動物毫無疑問對於這些小小孩都具有磁吸效應。當代研究人類飼養寵物伴侶模式最重要的其中一位專家詹姆士.瑟佩爾(James Serpell)指出,飼養寵物伴侶的歷史悠久,即便不能說它存在於時間長河裡所能看到的全世界每一個單一文化,但非常近似於一種普世行為。
然而,年紀較大的孩童和成人跟動物或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差異非常大,無論是不同文化之間或人跟動物之間皆然,而在寵物伴侶方面的落差尤其顯著。有些人熱愛動物,有些人對動物感到害怕或討厭;有些人喜歡狗卻討厭貓;有些人喜歡蛇和蜥蜴,但其他人卻覺得他們令人毛骨悚然。對於動物情感的差異顯然也跟教化有關(身在美國的人具有愛狗傾向,因此很受不了吃狗肉的想法;但某些文化搞不好養狗就跟我們養豬一樣,覺得把狗塗上辣椒醬烤來吃別有一番滋味)。有些則與個人經驗(根據統計,愛狗人往往成長於養狗家庭)或由於因緣際會,致使我們最終決定放棄那種非常會跳又滑不溜丟的寵物,比方像是能放在小朋友手心凹處的小白鼠。然而,只要冒出一種定義,立刻就會有一個反例掠過心頭。我們充其量只能說,「寵物伴侶」是一種隨心所欲的認定、一種社會性概念。
字典中對於「寵物伴侶」的定義是,一種基於樂趣或陪伴需求,並待之以情感而飼養的家畜或馴服的動物。在這樣的定義下,一般都認定寵物伴侶這個動物族群不具有經濟效益或實用功能,所以在道德層面上會把寵物伴侶跟飼養成為食物、實驗室研究之用、作為苦力勞動,或甚至擺在動物園裡展示的動物截然劃分開來。那些實用性動物,我們看待和對待牠們的方式是「東西」,好比生產的產品,這或許有助於解釋何以我們對牠們缺乏道德關懷。反之,寵物伴侶是被圈選和珍愛的。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具有情感連結,他們猶如家人,享有一種近似於「類人格」的道德地位。瑟佩爾同意這樣的論點。他說,寵物伴侶不具備實用功能,因而未被納入我們實利主義的統計對象。「在所有社會裡,對於寵物伴侶的寵愛大抵跟該動物對於社區或家庭經濟的貢獻度無關。」為了說明得更清楚,他把寵物伴侶和食用性動物拿來做比較。在一長串對於註定成為培根的豬隻恐怖而簡略的命運敘述後,他寫道:「這種基於經濟價值考量而剝削家畜的霸道態度,既簡單又直接,且西方世界的大多數人都默許此事。人類有權吃肉;農民有義務以越便宜越好的方式滿足此需求。結果動物無可避免地必須受苦。」不過,他接著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一個截然不同的家畜族群,雖然原因並不很清楚,但牠們無須接受此種待遇。」那就是我們的寵物伴侶。但寵物伴侶並未免於被剝削,而且還跟那些註定擺到超市架上的豬隻一樣成為同種經濟算計下的犧牲者。寵物伴侶不是拿來吃的(通常),但他們滋養我們的心靈,所以絕大多數人都默許養動物當寵物伴侶的權利,而供應商則名正言順地排著隊滿足這樣的需求。結果動物無可避免地必須受苦。
就單一個寵物主人而言,擁有寵物伴侶的好處很少會歸結至經濟層面。我的寵物伴侶們沒帶給我任何經濟效益,老實說,還造成不小的負擔。但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個人飼養寵物伴侶的原因上,就難以看清真相:寵物伴侶可以為某人或很多人創造出龐大的經濟利益,而且確實如此。鼓勵我們飼養寵物伴侶,讓各種動物得以很容易又很便宜取得的那股經濟力量,其實正是促動飼養寵物伴侶風潮背後的關鍵推手之一。寵物伴侶產業營造出一種社會情境,讓身處其中的人覺得飼養寵物伴侶是一件很高尚的事。
然而,撥開所有這些有關態度、慾望和採購習慣的行銷手法以及社會建構後,底層牽著一條連結需求的線。人們尋求寵物伴侶陪伴的主要原因肯定是心理性的;動物讓人覺得快樂,也滿足人類渴望照顧、關愛、連結的基本需求。亨利.朱利亞斯(Henri Julius)偕同同事們寫道:「寵物伴侶或可滿足個別人類尋求一個有著適度慈悲心之伴侶的需求……一個他們可以用相對較低『社會成本』照顧和依附者。例如,貓和狗不會跟你頂嘴,在很多方面也不像人類伴侶這麼苛求。」跟動物之間的關係強調的是情感元素,至於人與人之間可能會導致關係複雜化的那種認知與文化元素則比較罕見。寵物伴侶會依著人類伴侶而進行「不對稱且毫不猶疑」的調整。「選擇某隻動物(當作寵物伴侶)或許取決於該動物的本質是否符合其所預設的態度和願望。」具備社會智能的物種屬於「開放式設計」,所以社會行為是以學習和經驗為主。他們能夠被教化以適應人類的社會環境,並依照我們想要的方式來回應我們。我們認為的理想情境是讓寵物伴侶在幼兒時期就跟著我們,如此一來他或她就能夠適當地「社會化」。社會化過程涉及讓他們牢記我們,而不是牢記他們自己的父母;我們要他們跟我們連結,而且只跟我們。
所以,我們又再次利用了寵物伴侶的不安感,即便情感需求是一種相對較仁慈的剝削形式。我最近問一位獸醫朋友如何看待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時,他一派輕鬆地說:「奴役制度下的奴隸。」我對於他說出這話時的冷漠態度感到震驚和不悅。但我事後回想,他的話之所以讓我如此心煩,是因為觸動了我對於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感到不安的那條神經。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服侍我們。
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在他一九八四年的著作《支配與情感》(Dominance and Affection)中,闡述了有關寵物伴侶飼養的曖昧狀態。他說,把某種生物拿來當作寵物伴侶是一種支配行為,但因其發生於玩樂的範疇,且裹覆於情感下,致使這種異常狀態並未處於我們關注的雷達涵蓋區。雖然已有許多文章談及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濫權,但有關玩樂方面濫權的討論,幾乎是一片荒蕪。
支配或許很殘忍且帶有剝削性,完全沒有情感可言,由此產生出來的只有受害者。但另一方面,支配也可能伴隨著情感,而由此產生出來的就是寵物伴侶。
玩樂性支配的心理特點是:「一個人對其可照顧和資助的對象擁有一種溫情和高一等的感覺。」儘管我很想否認,但他的話隱含真理。有時當我看著貓咪索爾時會想:「是啊,我為了達成我個人的想望把他變成了奴隸,畢竟都是因為我一直想要有一個聰慧、善體人意的熱血生物相伴的緣故啊。」在索爾變成「我的」之前,他原本是慈善之家的財產。我領養了他(就技術層面而言,我用八十美元買下他),如今他屬於我。我確實在家裡有了索爾這樣一位朋友後,從照料他中得到一種溫暖的感覺。而且我認為索爾也很高興能待在我們家,當然啦,他除了加入我們也毫無選擇。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或許涉及支配,但顯然並非全貌。每一個有跟某隻動物建立起緊密關係的人都明白更深一層的道理:他們並非純粹只是東西,單用情分這個字眼都太簡化了我們對他們所懷有的感覺。我對於索爾的感覺,以及我認為他對我的感覺,遠超過情分兩個字。有時,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會到達一個對稱點,而且──我們竟膽敢這麼說──是一個對等點,在彼此的選擇下,人類與動物分享同一個生理與心理空間。雖然索爾的領地僅限於我們家和我們的小山丘,但在這個空間裡,他依其個人意願與這家人共享社交生活。門是開著的,他可以自由來去,但他選擇留下來。
有時我會問,為何這些小動物有著苦澀雙眼,為何我們應該照顧牠們?
──喬恩.席肯(Jon Silken),〈關愛動物〉(Caring for Animals)
大家都很清楚人類是如何跟非人類動物建立起社會依附關係的,但我們為何如此著迷於將動物變成寵物伴侶卻依然難以捉摸,就像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們聲明某隻動物是「寵物伴侶」而非食物一樣。幾乎所有的嬰兒和幼兒天生都對動物懷有好奇和興趣,動物毫無疑問對於這些小小孩都具有磁吸效應。當代研究人類飼養寵物伴侶模式最重要的其中一位專家詹姆士.瑟佩爾(James Serpell)指出,飼養寵物伴侶的歷史悠久,即便不能說它存在於時間長河裡所能看到的全世界每一個單一文化,但非常近似於一種普世行為。
然而,年紀較大的孩童和成人跟動物或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差異非常大,無論是不同文化之間或人跟動物之間皆然,而在寵物伴侶方面的落差尤其顯著。有些人熱愛動物,有些人對動物感到害怕或討厭;有些人喜歡狗卻討厭貓;有些人喜歡蛇和蜥蜴,但其他人卻覺得他們令人毛骨悚然。對於動物情感的差異顯然也跟教化有關(身在美國的人具有愛狗傾向,因此很受不了吃狗肉的想法;但某些文化搞不好養狗就跟我們養豬一樣,覺得把狗塗上辣椒醬烤來吃別有一番滋味)。有些則與個人經驗(根據統計,愛狗人往往成長於養狗家庭)或由於因緣際會,致使我們最終決定放棄那種非常會跳又滑不溜丟的寵物,比方像是能放在小朋友手心凹處的小白鼠。然而,只要冒出一種定義,立刻就會有一個反例掠過心頭。我們充其量只能說,「寵物伴侶」是一種隨心所欲的認定、一種社會性概念。
字典中對於「寵物伴侶」的定義是,一種基於樂趣或陪伴需求,並待之以情感而飼養的家畜或馴服的動物。在這樣的定義下,一般都認定寵物伴侶這個動物族群不具有經濟效益或實用功能,所以在道德層面上會把寵物伴侶跟飼養成為食物、實驗室研究之用、作為苦力勞動,或甚至擺在動物園裡展示的動物截然劃分開來。那些實用性動物,我們看待和對待牠們的方式是「東西」,好比生產的產品,這或許有助於解釋何以我們對牠們缺乏道德關懷。反之,寵物伴侶是被圈選和珍愛的。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具有情感連結,他們猶如家人,享有一種近似於「類人格」的道德地位。瑟佩爾同意這樣的論點。他說,寵物伴侶不具備實用功能,因而未被納入我們實利主義的統計對象。「在所有社會裡,對於寵物伴侶的寵愛大抵跟該動物對於社區或家庭經濟的貢獻度無關。」為了說明得更清楚,他把寵物伴侶和食用性動物拿來做比較。在一長串對於註定成為培根的豬隻恐怖而簡略的命運敘述後,他寫道:「這種基於經濟價值考量而剝削家畜的霸道態度,既簡單又直接,且西方世界的大多數人都默許此事。人類有權吃肉;農民有義務以越便宜越好的方式滿足此需求。結果動物無可避免地必須受苦。」不過,他接著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一個截然不同的家畜族群,雖然原因並不很清楚,但牠們無須接受此種待遇。」那就是我們的寵物伴侶。但寵物伴侶並未免於被剝削,而且還跟那些註定擺到超市架上的豬隻一樣成為同種經濟算計下的犧牲者。寵物伴侶不是拿來吃的(通常),但他們滋養我們的心靈,所以絕大多數人都默許養動物當寵物伴侶的權利,而供應商則名正言順地排著隊滿足這樣的需求。結果動物無可避免地必須受苦。
就單一個寵物主人而言,擁有寵物伴侶的好處很少會歸結至經濟層面。我的寵物伴侶們沒帶給我任何經濟效益,老實說,還造成不小的負擔。但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個人飼養寵物伴侶的原因上,就難以看清真相:寵物伴侶可以為某人或很多人創造出龐大的經濟利益,而且確實如此。鼓勵我們飼養寵物伴侶,讓各種動物得以很容易又很便宜取得的那股經濟力量,其實正是促動飼養寵物伴侶風潮背後的關鍵推手之一。寵物伴侶產業營造出一種社會情境,讓身處其中的人覺得飼養寵物伴侶是一件很高尚的事。
然而,撥開所有這些有關態度、慾望和採購習慣的行銷手法以及社會建構後,底層牽著一條連結需求的線。人們尋求寵物伴侶陪伴的主要原因肯定是心理性的;動物讓人覺得快樂,也滿足人類渴望照顧、關愛、連結的基本需求。亨利.朱利亞斯(Henri Julius)偕同同事們寫道:「寵物伴侶或可滿足個別人類尋求一個有著適度慈悲心之伴侶的需求……一個他們可以用相對較低『社會成本』照顧和依附者。例如,貓和狗不會跟你頂嘴,在很多方面也不像人類伴侶這麼苛求。」跟動物之間的關係強調的是情感元素,至於人與人之間可能會導致關係複雜化的那種認知與文化元素則比較罕見。寵物伴侶會依著人類伴侶而進行「不對稱且毫不猶疑」的調整。「選擇某隻動物(當作寵物伴侶)或許取決於該動物的本質是否符合其所預設的態度和願望。」具備社會智能的物種屬於「開放式設計」,所以社會行為是以學習和經驗為主。他們能夠被教化以適應人類的社會環境,並依照我們想要的方式來回應我們。我們認為的理想情境是讓寵物伴侶在幼兒時期就跟著我們,如此一來他或她就能夠適當地「社會化」。社會化過程涉及讓他們牢記我們,而不是牢記他們自己的父母;我們要他們跟我們連結,而且只跟我們。
所以,我們又再次利用了寵物伴侶的不安感,即便情感需求是一種相對較仁慈的剝削形式。我最近問一位獸醫朋友如何看待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時,他一派輕鬆地說:「奴役制度下的奴隸。」我對於他說出這話時的冷漠態度感到震驚和不悅。但我事後回想,他的話之所以讓我如此心煩,是因為觸動了我對於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感到不安的那條神經。他們的存在是為了服侍我們。
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在他一九八四年的著作《支配與情感》(Dominance and Affection)中,闡述了有關寵物伴侶飼養的曖昧狀態。他說,把某種生物拿來當作寵物伴侶是一種支配行為,但因其發生於玩樂的範疇,且裹覆於情感下,致使這種異常狀態並未處於我們關注的雷達涵蓋區。雖然已有許多文章談及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濫權,但有關玩樂方面濫權的討論,幾乎是一片荒蕪。
支配或許很殘忍且帶有剝削性,完全沒有情感可言,由此產生出來的只有受害者。但另一方面,支配也可能伴隨著情感,而由此產生出來的就是寵物伴侶。
玩樂性支配的心理特點是:「一個人對其可照顧和資助的對象擁有一種溫情和高一等的感覺。」儘管我很想否認,但他的話隱含真理。有時當我看著貓咪索爾時會想:「是啊,我為了達成我個人的想望把他變成了奴隸,畢竟都是因為我一直想要有一個聰慧、善體人意的熱血生物相伴的緣故啊。」在索爾變成「我的」之前,他原本是慈善之家的財產。我領養了他(就技術層面而言,我用八十美元買下他),如今他屬於我。我確實在家裡有了索爾這樣一位朋友後,從照料他中得到一種溫暖的感覺。而且我認為索爾也很高興能待在我們家,當然啦,他除了加入我們也毫無選擇。我們跟寵物伴侶之間的關係或許涉及支配,但顯然並非全貌。每一個有跟某隻動物建立起緊密關係的人都明白更深一層的道理:他們並非純粹只是東西,單用情分這個字眼都太簡化了我們對他們所懷有的感覺。我對於索爾的感覺,以及我認為他對我的感覺,遠超過情分兩個字。有時,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會到達一個對稱點,而且──我們竟膽敢這麼說──是一個對等點,在彼此的選擇下,人類與動物分享同一個生理與心理空間。雖然索爾的領地僅限於我們家和我們的小山丘,但在這個空間裡,他依其個人意願與這家人共享社交生活。門是開著的,他可以自由來去,但他選擇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