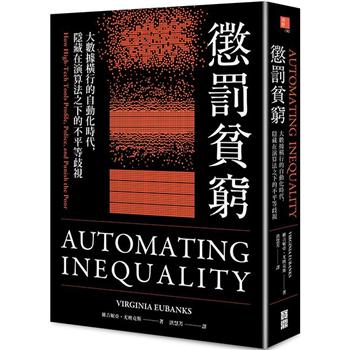第一章:從濟貧院到資料庫
「你要把我送進濟貧院!」
如今多數人提到濟貧院,都只是隨口說說,沒有多想什麼。但濟貧院曾是一種非常貼近現實的可怕機構,很多人聞之色變。鼎盛時期,濟貧院還經常出現在明信片與流行歌曲中。地方社團會為善心人士及一般遊客安排參觀濟貧院的行程。全美各地的城市與鄉鎮中,仍有一些街道是以曾坐落在路邊的濟貧院命名的。例如,緬因州的布里斯托(Bristol)與密西西比州的納奇茲(Natchez)有濟貧院路(Poor Farm Roads);俄亥俄州的馬利斯維(Marysville)與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Greenville)有救濟院路(County Home Roads);維吉尼亞州的文契斯特(Winchester)與加州的聖馬提歐(San Mateo)有濟貧院路(Poorhouse Roads)。有些路已經改名,以掩蓋過去,例如維吉尼亞海灘市(Virginia Beach)的濟貧院路如今易名為繁榮路(Prosperity Road)。
在我的家鄉紐約州特洛伊市,這裡的濟貧院建於一八二一年。由於多數院友病得太重、年紀太老或太小,無法做體力活,體格健全的院友必須負責到占地六一・五公頃的農場及附近的採石場工作,這也是這家濟貧院命名為連瑟勒勞動救濟院(Rensselaer County House of Industry)的由來。一八二四年,約翰・範・內斯・耶茨(John Van Ness Yates)接受紐約州的委託,對「窮人的救濟與安置」做了為期一年的調查。他以特洛伊為例,主張紐約州應該在每個郡都設立一所濟貧院。後來他的提案成功了:十年內,紐約州建了五十五個郡立濟貧院。
儘管有樂觀的預測指出,濟貧院將提供「經濟與人道」救濟,但濟貧院確實是一個讓窮人與勞工階層心生恐懼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一項立法調查發現,勞動濟貧院把精神病患關在長二公尺、寬一・四公尺的房間裡長達六個月。由於他們只能睡在麥稈上,房內又沒有衛生設施,冬天的時候,麥稈與尿液的混合體會凍結在他們身上,「唯有解凍才能清除」,因此導致永久性的殘疾。
一八五七年二月,《特洛伊輝格日報》(Troy Daily Whig)寫道:「目前報導的濟貧院狀況,普遍在各方面都很糟。根據合約,窮人的生計是由出價最低的人承包。這種合約制度是造成濟貧院整體狀況惡劣的主因⋯⋯,這個制度本身已經爛到底了。」該郡的濟貧負責人賈斯汀・葛雷戈里(Justin E. Gregory)承諾以每週一美元的價格照顧貧民,因此競標獲得勞動濟貧院的合約。合約規定,他享有無限使用這些勞力的權利。那年,這所勞動濟貧院靠著飢餓院友所栽種的蔬菜,獲得二千美元的營收。
一八七九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頭版報導,一個「濟貧院犯罪集團」把勞動濟貧院內已故院友的屍體賣給該郡的醫生以進行解剖。一八八五年,一項針對「管理不善」的調查發現,連瑟勒郡的濟貧部門遭竊二萬美元,濟貧院的負責人艾拉・福特(Ira B. Ford)被迫辭職。一八九六年,他的繼任者克爾文・鄧姆(Calvin B. Dunham)被爆出不當的財務行為後,自殺身亡。
一九〇五年,紐約州慈善委員會發起一項調查,揭發了勞動救濟院裡猖獗的性侵行為。護士露絲・席林格(Ruth Schillinger)作證指出,男性醫護人員威廉・威爾莫特(William Wilmot)常試圖強姦女病患。院友堅稱,癱瘓的瑪麗・墨菲(Mary Murphy)遭到威爾莫特性侵。席林格作證時表示:「他們聽到大廳傳來腳步聲時,都說威爾莫特又去那裡了。隔天早上,我發現那個女人的雙腿是叉開的,她的下肢已經癱瘓了,不可能自己移動。」
約翰・基特爾(John Kittell)是勞動濟貧院的負責人,也是威爾莫特的老闆。他為這套管理模式辯解,聲稱他藉由減少院友的照護費用「每年為該郡省下五六千美元」。後來,威爾莫特並未遭到任何指控。直到一九一〇年,才有人採取行動改善勞動濟貧院的狀況。特洛伊的濟貧院一直運作到一九五四年才關閉。
雖然濟貧院實體上已經拆除了,但遺跡依然陰魂不散,仍活躍在如今困住窮人的自動化決策系統中。現代的貧窮管理系統(自動化決策、資料探勘、預測分析)雖有高科技的表象,但依然與過去的濟貧院有顯著的相似之處。新的數位工具源自我們想要懲戒貧窮的道德觀,並打造出一套高科技的遏制與調查系統。數位濟貧院阻止窮人取得公共資源;監管他們的勞動、支出、性行為與子女教養;試圖預測他們未來的行為;懲罰那些不遵守規定的人並加以定罪。過程中,它在「值得幫助」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之間,創造出愈來愈細微的道德區別,並利用分類來合理化美國人民無法關照彼此的問題。
本章將說明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實體的濟貧院如何演變成數位化的翻版。美國從十九世紀的鄉村濟貧院演變到現代數位濟貧院的歷程,可說是一場持久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一方希望消除與減輕貧困,另一方則是指責、監禁和懲罰窮人。
「你要把我送進濟貧院!」
如今多數人提到濟貧院,都只是隨口說說,沒有多想什麼。但濟貧院曾是一種非常貼近現實的可怕機構,很多人聞之色變。鼎盛時期,濟貧院還經常出現在明信片與流行歌曲中。地方社團會為善心人士及一般遊客安排參觀濟貧院的行程。全美各地的城市與鄉鎮中,仍有一些街道是以曾坐落在路邊的濟貧院命名的。例如,緬因州的布里斯托(Bristol)與密西西比州的納奇茲(Natchez)有濟貧院路(Poor Farm Roads);俄亥俄州的馬利斯維(Marysville)與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Greenville)有救濟院路(County Home Roads);維吉尼亞州的文契斯特(Winchester)與加州的聖馬提歐(San Mateo)有濟貧院路(Poorhouse Roads)。有些路已經改名,以掩蓋過去,例如維吉尼亞海灘市(Virginia Beach)的濟貧院路如今易名為繁榮路(Prosperity Road)。
在我的家鄉紐約州特洛伊市,這裡的濟貧院建於一八二一年。由於多數院友病得太重、年紀太老或太小,無法做體力活,體格健全的院友必須負責到占地六一・五公頃的農場及附近的採石場工作,這也是這家濟貧院命名為連瑟勒勞動救濟院(Rensselaer County House of Industry)的由來。一八二四年,約翰・範・內斯・耶茨(John Van Ness Yates)接受紐約州的委託,對「窮人的救濟與安置」做了為期一年的調查。他以特洛伊為例,主張紐約州應該在每個郡都設立一所濟貧院。後來他的提案成功了:十年內,紐約州建了五十五個郡立濟貧院。
儘管有樂觀的預測指出,濟貧院將提供「經濟與人道」救濟,但濟貧院確實是一個讓窮人與勞工階層心生恐懼的地方。一八五七年,一項立法調查發現,勞動濟貧院把精神病患關在長二公尺、寬一・四公尺的房間裡長達六個月。由於他們只能睡在麥稈上,房內又沒有衛生設施,冬天的時候,麥稈與尿液的混合體會凍結在他們身上,「唯有解凍才能清除」,因此導致永久性的殘疾。
一八五七年二月,《特洛伊輝格日報》(Troy Daily Whig)寫道:「目前報導的濟貧院狀況,普遍在各方面都很糟。根據合約,窮人的生計是由出價最低的人承包。這種合約制度是造成濟貧院整體狀況惡劣的主因⋯⋯,這個制度本身已經爛到底了。」該郡的濟貧負責人賈斯汀・葛雷戈里(Justin E. Gregory)承諾以每週一美元的價格照顧貧民,因此競標獲得勞動濟貧院的合約。合約規定,他享有無限使用這些勞力的權利。那年,這所勞動濟貧院靠著飢餓院友所栽種的蔬菜,獲得二千美元的營收。
一八七九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頭版報導,一個「濟貧院犯罪集團」把勞動濟貧院內已故院友的屍體賣給該郡的醫生以進行解剖。一八八五年,一項針對「管理不善」的調查發現,連瑟勒郡的濟貧部門遭竊二萬美元,濟貧院的負責人艾拉・福特(Ira B. Ford)被迫辭職。一八九六年,他的繼任者克爾文・鄧姆(Calvin B. Dunham)被爆出不當的財務行為後,自殺身亡。
一九〇五年,紐約州慈善委員會發起一項調查,揭發了勞動救濟院裡猖獗的性侵行為。護士露絲・席林格(Ruth Schillinger)作證指出,男性醫護人員威廉・威爾莫特(William Wilmot)常試圖強姦女病患。院友堅稱,癱瘓的瑪麗・墨菲(Mary Murphy)遭到威爾莫特性侵。席林格作證時表示:「他們聽到大廳傳來腳步聲時,都說威爾莫特又去那裡了。隔天早上,我發現那個女人的雙腿是叉開的,她的下肢已經癱瘓了,不可能自己移動。」
約翰・基特爾(John Kittell)是勞動濟貧院的負責人,也是威爾莫特的老闆。他為這套管理模式辯解,聲稱他藉由減少院友的照護費用「每年為該郡省下五六千美元」。後來,威爾莫特並未遭到任何指控。直到一九一〇年,才有人採取行動改善勞動濟貧院的狀況。特洛伊的濟貧院一直運作到一九五四年才關閉。
雖然濟貧院實體上已經拆除了,但遺跡依然陰魂不散,仍活躍在如今困住窮人的自動化決策系統中。現代的貧窮管理系統(自動化決策、資料探勘、預測分析)雖有高科技的表象,但依然與過去的濟貧院有顯著的相似之處。新的數位工具源自我們想要懲戒貧窮的道德觀,並打造出一套高科技的遏制與調查系統。數位濟貧院阻止窮人取得公共資源;監管他們的勞動、支出、性行為與子女教養;試圖預測他們未來的行為;懲罰那些不遵守規定的人並加以定罪。過程中,它在「值得幫助」與「不值得幫助」的窮人之間,創造出愈來愈細微的道德區別,並利用分類來合理化美國人民無法關照彼此的問題。
本章將說明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實體的濟貧院如何演變成數位化的翻版。美國從十九世紀的鄉村濟貧院演變到現代數位濟貧院的歷程,可說是一場持久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一方希望消除與減輕貧困,另一方則是指責、監禁和懲罰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