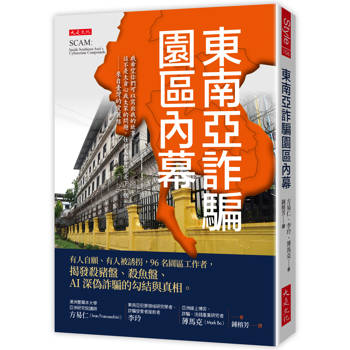惡夢的開場
被騙到緬甸的詐騙園區之前,張先生在中國廣西省廬山植物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新冠疫情期間,他失業了,家人生病與債務壓得他喘不過氣。有著中國科學院博士頭銜的他選擇海外求職,以求更高的薪資。最終他應徵上一間新加坡公司,一切都充滿希望,但是簽證申請流程不斷延後,他的仲介便建議他先到泰國分公司上班。
張先生一開始有些疑慮,因為他看過有人被騙到東南亞做詐騙產業的報導,但他反覆檢查該公司的文件,相信整個入職過程都合法、合理,最終決定相信這位仲介。然而,一抵達泰國,手機、證件、護照就全部被沒收,接著他就被帶到泰緬邊境的緬甸克倫邦苗瓦迪鎮區,進入一個詐騙園區,被迫執行殺豬盤詐騙,假扮女性身分,誘騙歐美人士投資虛擬貨幣。
在園區裡,張先生聽說有些人成功逃脫,因此也開始想著逃跑的事,但很快他就發現,重返自由是難上加難。園區外牆有4公尺到5公尺高,上頭架有高壓電,周圍還有武裝哨兵監視,除此之外,園區外圍每隔幾百公尺就有哨站,還有更多武裝士兵監控著園區的周邊區域。
想逃,就得冒著遇到園區內外武裝士兵的風險。對緬甸不熟,又沒有錢賄賂他人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張先生最終放棄逃跑的想法,轉而向中國媒體求助。中國媒體被他博士的身分吸引,便很快報導了他的故事。
媒體不斷報導張先生的故事,讓囚禁他的詐騙團體面臨極大的壓力,因而同意把贖金從12萬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490,800元)降到5萬9千元人民幣(約合新臺幣241,310元)。張先生的家人付了贖金,他終於得以逃離。
張先生菁英機構出身的博士身分,讓他的故事占據中國媒體版面,激起中國輿論對詐騙產業的憤慨。但不是每一個東南亞詐騙產業的倖存者,都能受到這麼多的關注與同情。
2023年底,大約是張先生的苦難在中國社群媒體爆紅的同一時間,中國四川省有2位年輕人,名叫阿雲和阿沛(皆為音譯),分別只有17歲和20歲,輾轉於家鄉的建築工地之間勉強度日。有一天,他們在中國熱門網路直播平臺快手,看到一個好像很不錯的機會。平臺上這份工作的薪資,是他們每日工資的2倍,還提供食宿。
2人聯繫公司,一得到正面回覆,他們就動身前往廣西省海邊的一個城市,進行實體面試,但他們興奮的情緒瞬間轉為恐懼,因為他們未來的雇主以暴力逼迫他們搭上一艘船,接著2人抵達越南,在重重監視下被迫待在飯店裡數天,隨後便轉移至柬埔寨的邊境小鎮巴韋。
到了巴韋,他們才知道自己應徵的是什麼工作。他們被帶到一座專營線上博弈與網路詐騙的園區,並被告知要做網路詐騙。他們不願意做網路詐騙,所以試圖逃跑,但被保全抓住,遭到毒打,並關在宿舍裡好幾天,最終他們同意學詐騙技巧。
但他們非常幸運,因為他們很快就被轉移到另一個園區,並設法透過微信聯絡上自己在中國的親人。2人的家人立刻向中國當局與柬埔寨中國大使館報案,他們終於在2024年1月由柬埔寨警方救出。
你是我們的,我們買了你
在遙遠的另一個大陸,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正在展開。喬治(George)來自烏干達,是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把握難得的機會,前往印度4年,攻讀資訊科技相關學位。畢業後,他回到烏干達的首都坎帕拉(Kampala),成為自由工作者,從事修電腦、裝設路由器和網路線等工作。
隨著新冠疫情來襲,生活一切停擺,生計也陷入危機。因此到了2020年11月,他決定搬到杜拜生活。一到杜拜,他就發現這裡的生活非常辛苦:「我什麼都做……還算是自由接案吧。像是一些不重要的小工作、打零工、雜活、簡單的工作……做完立刻拿現金。因為我的簽證每3個月要申請延長,還有房租要付,所以我必須一直工作,一邊找正式工作,一邊靠做這些零工維持生計。」
也因為如此,2022年8月,朋友跟他提到一個寮國的高薪資訊科技工作時,他馬上就答應了。喬治回憶著說:「有個公司在找人幫他們管理資料,而且合約只有6個月而已。」朋友把他介紹給該公司一名女子,她跟他談的月薪是1500美元(約合新臺幣43,890元),有津貼和佣金,還附住宿,日常開銷也都包含在內。
她也介紹了這間公司的資訊,一切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喬治同意了,於是該女子便開始辦理簽證、機票、保險事宜。很快的,他就踏上前往金三角的旅程,抵達與緬甸、泰國接壤的寮國邊境。
在金三角,公司要求他簽的合約跟在杜拜說的完全不一樣,這份新合約會讓他欠公司一大筆債。他的護照和手機都被收走,而且工作也換了,變成要用寫好的腳本跟全世界的人聊天,誘騙他們投資。兩個月來他刻意做的拖泥帶水,跟公司堅持說他是做資訊科技的,應該做擅長的事。
某一天,公司把他賣給緬甸另一間詐騙公司,把他賣掉的人不跟他說自己因此賺了多少錢。「他只說:『你是我們的,我們買了你……』這感覺好怪,很像回到了非洲買賣奴隸的那個年代……很難相信會有人跟你說『你是我的』。」他本來只是來工作6個月而已,卻花了整整1年才回到坎帕拉。
自願?
就跟張先生、阿雲、阿沛、喬治一樣,每年都有數千人遭到誘騙、販運、買賣給東南亞與其他地區的詐騙業者。正如我們在前言所見,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估計,2023年有至少12萬人,可能被迫在緬甸從事網路詐騙活動,另有10萬人在柬埔寨。
這個數據仍引發當地官員的強烈質疑,且極難驗證。一方面,許多詐騙園區所在地都難以抵達,因為這些園區都不對外開放,又有嚴密防護,因此要蒐集可靠的資料十分困難;另一方面,詐騙園區員工的背景與動機變化太大。
雖然有些人是被拐騙或賣到這裡,但也有些人進去前就完全了解自己要做的是違法工作,並用一般人上班的心態執行自己的工作,也有人知道(或以為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但等看到真實情況想離開時,才發現自己被困住、身分證件被扣留、欠公司的債也因管理層加了很多荒謬的費用,而累積成驚人天價。
要釐清為何人們會進到詐騙園區,往往很有難度。有些倖存者知道,講出來可能會降低他人幫助的動力,也可能會讓自己在母國,或詐騙業務所在地面臨刑責,因此不想承認一開始是自願進去的。
也有一些案例讓事情變得更複雜:有些倖存者為了引發公眾同情,會把受虐情節誇大,造成其故事脈絡不一致,以致後來事跡敗露時,輿論支持的力道便會削弱。
前一章提到西哈努克市的血奴案就是一個例子。倖存者分享的故事真假參半,釀成非常嚴重的反效果,也讓柬埔寨政府有理由否認該國詐騙園區的存在,甚至還逮捕拯救行動的關鍵人士。
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導致大眾開始不相信倖存者的說詞,讓某個公民社會組織於2022年中宣布,停止特定日期後進入詐騙園區者的救援行動。以這樣的推論來看,此時媒體對於網路詐騙產業的報導已經鋪天蓋地,所以在這之後進入詐騙園區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即將面對的是什麼。
用更宏觀的視角來說,外界一直以來都在討論,道德上該如何看待那些從事詐騙產業的人,他們可能是自願或受脅迫(或在這之間受到不同程度待遇的人)。那些知道(或理應要知道)自己要做的是非法工作,卻仍進入該產業,最後無法脫身的人,我們應該將之視為受害者嗎?以上這些討論往往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使人忽略了讓許多人如此輕易受到該產業誘惑的結構性原因,例如新冠疫情引起的普遍貧窮化(immiseration)問題。
在本章,我們試著藉由梳理東南亞詐騙園區受困者進入該產業的方式,將其整體情況複雜化。我們希望能藉由這個作法,展現許多倖存者是怎麼因為絕望、不走運、輕信他人等原因陷入窘境。
更明確來說,我們會著眼以下7個部分:假徵才廣告、受僱於詐騙業者的專業仲介、經親朋好友介紹、社群媒體網紅的誘導、犯罪組織人口販運、綁架、詐騙園區之間的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