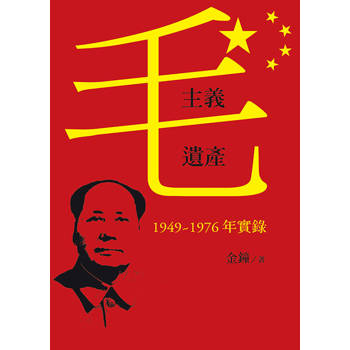第一章—狂瀾
1. 南京陷落與「劃江而治」
【按: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是中國內戰的標誌性事件。國軍從此走向潰敗,政府亦處於危機中。李宗仁代總統力圖實現以長江劃界國共分治,搞兩個中國,雖然在軍事失勢和美國拒絕支持下,無法阻止共軍渡江。卻留下一個插曲:蘇共領袖史達林曾秘密地扮演令毛澤東憤怒的角色。多年後毛恨未消,指罵史達林「不許革命」之罪。內涵禁止深究。其實這是一個質疑中共命運的議題。】
公元1949 年4 月23 日,南京—1912 年建立的中華民國首都,被共軍一夜佔領,沒有攻防激戰,也無社會騷動。這是中國內戰的一個戲劇性事件。歷史上,南京虎踞龍蟠,是著名的「六朝古都」。近代氣數多舛,1842 年鴉片戰爭有「南京條約」;1853年被太平天國劫佔稱為「天京」;1864 年湘軍收復,火焚掠殺,死人十萬;1927 年4 月蔣介石北伐攻占南京,立為首都;1937 年12 月日寇佔領南京,施行大屠殺;1940 年汪精衛在南京自立親日政府至日本投降;1946 年國府還都南京;三年後,被共軍佔領,中共將其首都轉至北京。
國共內戰中的陰謀與叛變比比皆是
南京的陷落,標誌國共內戰大轉折。國民政府一路撤退廣州、重慶、成都,最後台灣,開始隔海對峙七十年的「兩個中國」時代。中共信奉「成王敗寇」史觀,不認台灣中華民國法統。強迫國際社會只認「一中」。然而中國歷史上,兩中、多中的分裂政權,屢見不鮮(如北宋南宋分治達153-168 年)只有版圖大小、時間長短不同而已。誰是正朔,誰是叛逆?1972 年,毛對尼克森總統說,我們和蔣委員長都以「匪」相稱,「匪來匪去的」。至於國共內戰的是非成敗,數十年來,莫衷一是。對比美國內戰、蘇俄內戰和中國內戰,三國內戰,各有性質相異的戰爭形態和評論。本文僅以新的史料分析國共內戰,探討南京撤守被掩蓋的歷史層面,和被扭曲多年的「劃江而治」事件。
為何南京易幟無戰事?當時,共軍已拿到「三大戰役」擊敗國軍主力的優勢而兵臨長江。但以兵力之比,國軍號稱三百五十萬超過共軍之二百萬,加上長江天塹和海空優勢,李宗仁當局自信,有幾十條軍艦、上百架的飛機,江防至少百萬兵,阻止共軍渡江,守住三個月無問題。可是共軍渡江到佔領南京,僅僅兩天!中共幾十年歌頌毛澤東的〈七律:佔領南京〉:「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亦有名畫《佔領總統府》,虛構攻占南京的炮火連天。
事實上,南京處於共軍「射程之內」,中共早已部署一場總體戰,包括策動學潮、輿論,打入財經界、統戰反蔣派,更策劃如荷馬傳奇的現代「木馬屠城記」,以圖不戰而勝。中共內戰逆轉勝,除野戰主場外,兵不厭詐,使用過許多詭計秘端,正是木馬戰術發揮關鍵作用。從東北戰場到川康戰役可謂無役不興:策反將領、利誘叛變、匪諜縱橫……進入南京將紅旗插上總統府的共軍,竟是叛將吳化文指揮的三十五軍!甚至不乏「木馬」潛入代總統官邸的神奇橋段。但是《李宗仁回憶錄》指江防戰役之敗,悉歸蔣介石的戰略錯誤:由他的親信湯恩伯執行「無意守江而守上海」的計劃,調三十萬精銳布防上海,對南京、鎮江、蕪湖一線則以弱勢兵力應付,促使李白政權的垮台……顯示國府內部長期存在的戰略分裂。
國共和談:無異於要求國府無條件投降
南京淪陷正是中共上下其手,欺詐策反,積木馬破城之極的一例。1949 年4 月的「國共和談」便是他們的陰陽大舞台。這次和談的發起者是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世稱李白),他們早是國府內的非蔣派,認為內戰節節失利,是蔣的指揮無能所致,例如蔣貽誤擊敗山東陳毅部之機,而禍延徐蚌大戰(淮海)……三大戰役,精銳盡失。
為保住半壁江山,和中共和談,爭取「劃江而治,組成聯合政府」是李宗仁執政後的最佳選擇。中共方面,經1946 年6 月至1948 年6 月兩年內戰,已經兵臨城下,根本不給對手絲毫討價還價空間。中共回應和談的五個條件,第一條「懲辦戰犯」(毛親手旨定),開出四十三人名單,國府政要及同盟者盡在其中(見附錄),擺明是一份要求「無條件投降」的羞辱書。
李白決以委屈求全之心求得毛周有所讓步,甚至不惜以逼蔣出國,開門揖盜的對策和共黨周旋,派出張治中為首的代表團赴北平(北京)談判。毛的諜報總管周恩來得以玩一場「貓捉老鼠」的死亡遊戲。玩了三個月,四月中旬,六隻老鼠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李蒸、章士釗、劉裴,被南方報紙視為「一批可憐蟲、一群被征服的奴隸」,實則全是親共分子或地下黨(最後都留在北平事共)。甚至,在南京撤退的前一天,邵力子竟打電話勸降李宗仁,要他「留在南京,如果不安全,可以直接飛來北平,一定大受歡迎」……當時國府方面已是兩個權力中心分庭抗禮:南京政府的李宗仁和奉化溪口的蔣介石。蔣不反對談判,卻堅信中共不會接受劃江而治方案,談判能爭得一些時間也好。於是,毛周的殺手鐧得以宣然暢行:絕不同意隔江而治,「談判成不成功,解放軍都要渡江」。化點時間談判,對內對外宣傳有好處,因為大家都要和平;並可藉機分化敵人,利用桂系打倒蔣介石(和談前已佈局的「聯桂反蔣」,李白的私人代表黃啟漢、劉仲容兄弟,已北上密會毛周,商定合作事項)。
毛周的魔手還直接伸到李宗仁身邊。和談開始,竟密派三名民革民盟說客住入南京副總統官邸,向李宗仁面授毛周旨意、威脅誘降。視代總統為牽線木偶。蔣宣告下野,毛立即在戰犯名單撤除李白 ,稱對桂系「由敵對關係改變為交朋友關係」。同時,加緊完成對「江陰要塞」的最後策反。—在中共強勢的渡江謀略下,嚴重暴露國府內憂外患的深重。李宗仁不服於蔣的干政與實力,而漠視蔣政治上的堅強抗共;將派系之爭(蔣李)放在憲政與極權主義的對立之上,這是李宗仁的致命傷。導致他1965年在中共文革暴政前夕靦顏投共而自毀一生。
1. 南京陷落與「劃江而治」
【按: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是中國內戰的標誌性事件。國軍從此走向潰敗,政府亦處於危機中。李宗仁代總統力圖實現以長江劃界國共分治,搞兩個中國,雖然在軍事失勢和美國拒絕支持下,無法阻止共軍渡江。卻留下一個插曲:蘇共領袖史達林曾秘密地扮演令毛澤東憤怒的角色。多年後毛恨未消,指罵史達林「不許革命」之罪。內涵禁止深究。其實這是一個質疑中共命運的議題。】
公元1949 年4 月23 日,南京—1912 年建立的中華民國首都,被共軍一夜佔領,沒有攻防激戰,也無社會騷動。這是中國內戰的一個戲劇性事件。歷史上,南京虎踞龍蟠,是著名的「六朝古都」。近代氣數多舛,1842 年鴉片戰爭有「南京條約」;1853年被太平天國劫佔稱為「天京」;1864 年湘軍收復,火焚掠殺,死人十萬;1927 年4 月蔣介石北伐攻占南京,立為首都;1937 年12 月日寇佔領南京,施行大屠殺;1940 年汪精衛在南京自立親日政府至日本投降;1946 年國府還都南京;三年後,被共軍佔領,中共將其首都轉至北京。
國共內戰中的陰謀與叛變比比皆是
南京的陷落,標誌國共內戰大轉折。國民政府一路撤退廣州、重慶、成都,最後台灣,開始隔海對峙七十年的「兩個中國」時代。中共信奉「成王敗寇」史觀,不認台灣中華民國法統。強迫國際社會只認「一中」。然而中國歷史上,兩中、多中的分裂政權,屢見不鮮(如北宋南宋分治達153-168 年)只有版圖大小、時間長短不同而已。誰是正朔,誰是叛逆?1972 年,毛對尼克森總統說,我們和蔣委員長都以「匪」相稱,「匪來匪去的」。至於國共內戰的是非成敗,數十年來,莫衷一是。對比美國內戰、蘇俄內戰和中國內戰,三國內戰,各有性質相異的戰爭形態和評論。本文僅以新的史料分析國共內戰,探討南京撤守被掩蓋的歷史層面,和被扭曲多年的「劃江而治」事件。
為何南京易幟無戰事?當時,共軍已拿到「三大戰役」擊敗國軍主力的優勢而兵臨長江。但以兵力之比,國軍號稱三百五十萬超過共軍之二百萬,加上長江天塹和海空優勢,李宗仁當局自信,有幾十條軍艦、上百架的飛機,江防至少百萬兵,阻止共軍渡江,守住三個月無問題。可是共軍渡江到佔領南京,僅僅兩天!中共幾十年歌頌毛澤東的〈七律:佔領南京〉:「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亦有名畫《佔領總統府》,虛構攻占南京的炮火連天。
事實上,南京處於共軍「射程之內」,中共早已部署一場總體戰,包括策動學潮、輿論,打入財經界、統戰反蔣派,更策劃如荷馬傳奇的現代「木馬屠城記」,以圖不戰而勝。中共內戰逆轉勝,除野戰主場外,兵不厭詐,使用過許多詭計秘端,正是木馬戰術發揮關鍵作用。從東北戰場到川康戰役可謂無役不興:策反將領、利誘叛變、匪諜縱橫……進入南京將紅旗插上總統府的共軍,竟是叛將吳化文指揮的三十五軍!甚至不乏「木馬」潛入代總統官邸的神奇橋段。但是《李宗仁回憶錄》指江防戰役之敗,悉歸蔣介石的戰略錯誤:由他的親信湯恩伯執行「無意守江而守上海」的計劃,調三十萬精銳布防上海,對南京、鎮江、蕪湖一線則以弱勢兵力應付,促使李白政權的垮台……顯示國府內部長期存在的戰略分裂。
國共和談:無異於要求國府無條件投降
南京淪陷正是中共上下其手,欺詐策反,積木馬破城之極的一例。1949 年4 月的「國共和談」便是他們的陰陽大舞台。這次和談的發起者是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世稱李白),他們早是國府內的非蔣派,認為內戰節節失利,是蔣的指揮無能所致,例如蔣貽誤擊敗山東陳毅部之機,而禍延徐蚌大戰(淮海)……三大戰役,精銳盡失。
為保住半壁江山,和中共和談,爭取「劃江而治,組成聯合政府」是李宗仁執政後的最佳選擇。中共方面,經1946 年6 月至1948 年6 月兩年內戰,已經兵臨城下,根本不給對手絲毫討價還價空間。中共回應和談的五個條件,第一條「懲辦戰犯」(毛親手旨定),開出四十三人名單,國府政要及同盟者盡在其中(見附錄),擺明是一份要求「無條件投降」的羞辱書。
李白決以委屈求全之心求得毛周有所讓步,甚至不惜以逼蔣出國,開門揖盜的對策和共黨周旋,派出張治中為首的代表團赴北平(北京)談判。毛的諜報總管周恩來得以玩一場「貓捉老鼠」的死亡遊戲。玩了三個月,四月中旬,六隻老鼠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李蒸、章士釗、劉裴,被南方報紙視為「一批可憐蟲、一群被征服的奴隸」,實則全是親共分子或地下黨(最後都留在北平事共)。甚至,在南京撤退的前一天,邵力子竟打電話勸降李宗仁,要他「留在南京,如果不安全,可以直接飛來北平,一定大受歡迎」……當時國府方面已是兩個權力中心分庭抗禮:南京政府的李宗仁和奉化溪口的蔣介石。蔣不反對談判,卻堅信中共不會接受劃江而治方案,談判能爭得一些時間也好。於是,毛周的殺手鐧得以宣然暢行:絕不同意隔江而治,「談判成不成功,解放軍都要渡江」。化點時間談判,對內對外宣傳有好處,因為大家都要和平;並可藉機分化敵人,利用桂系打倒蔣介石(和談前已佈局的「聯桂反蔣」,李白的私人代表黃啟漢、劉仲容兄弟,已北上密會毛周,商定合作事項)。
毛周的魔手還直接伸到李宗仁身邊。和談開始,竟密派三名民革民盟說客住入南京副總統官邸,向李宗仁面授毛周旨意、威脅誘降。視代總統為牽線木偶。蔣宣告下野,毛立即在戰犯名單撤除李白 ,稱對桂系「由敵對關係改變為交朋友關係」。同時,加緊完成對「江陰要塞」的最後策反。—在中共強勢的渡江謀略下,嚴重暴露國府內憂外患的深重。李宗仁不服於蔣的干政與實力,而漠視蔣政治上的堅強抗共;將派系之爭(蔣李)放在憲政與極權主義的對立之上,這是李宗仁的致命傷。導致他1965年在中共文革暴政前夕靦顏投共而自毀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