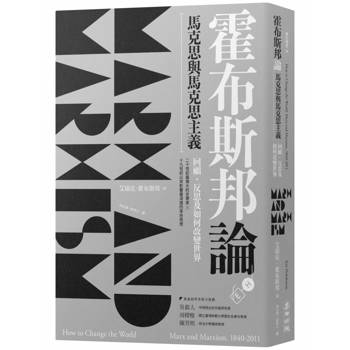第一章 今日的馬克思
一
二〇〇七年,猶太書週於卡爾.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週年前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舉行,地點離馬克思過去最常造訪倫敦的地方──大英博物館圓形閱覽室(Round Reading Room),只有幾步路的距離。賈克.阿塔里與我是立場迥異的社會主義者,卻不約而同來此向他致上敬意。然而,當你想到地點與日期,就會產生一種雙重的意外感受。我們不能說馬克思在一八八三年去世時一事無成,因為他的作品已對德國,特別是對俄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影響,而由他的門徒所領導的運動正逐漸主導德國的勞工運動。但在一八八三年時,馬克思一生的努力似乎還未竟全功。他已經寫了幾部卓越的小書,而那部未完成的作品:《資本論》(Das Kapital),在他人生最後十年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當一名訪客問起他的作品時,他苦澀地反問:「什麼作品?」自從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六四年至七三年所謂的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失敗後,馬克思的政治努力已無成功的可能。馬克思雖然大半生流亡英國,但他在當地的政治或思想界卻未曾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馬克思死後卻享有極高聲譽!在他去世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以他的名字為號召或受他啟迪的歐洲工人階級政黨,在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中獲得百分之十五到四十七的選票──英國是唯一例外。一九一八年後,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政黨都成了執政黨,而不只是反對黨,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法西斯主義結束之後,然而到了這段時期,這些政黨絕大多數卻處心積慮與他們原先的啟蒙者劃清界線。這些政黨至今依然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的門徒也在非民主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革命團體。在馬克思去世的七十年後,有三分之一的人類生活在由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之下,這些政府宣稱他們代表馬克思的觀念並且實現了他的願望。之後,儘管這些執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大幅轉變政策方針,卻仍有兩成以上宣稱他們堅持馬克思路線。簡言之,要說有哪位思想家在二十世紀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那麼此人非馬克思莫屬。走進十九世紀巨擘卡爾.馬克思與赫伯特.斯賓塞埋骨的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耐人尋味的是,兩座墳塋居然彼此對望。當兩人都在世時,人們公認斯賓塞是當時的亞里斯多德,而馬克思不過是住在漢普斯特(Hampstead)矮坡上仰賴朋友資助度日的無名小卒。今日,已無人知道斯賓塞長眠此地,但老一輩來自日本與印度的朝聖者仍前來拜謁馬克思的墓塚,就連流亡海外的伊朗人與伊拉克人也堅持死後應埋葬於此受其庇蔭。
共產黨政權與廣大的共產主義政黨橫行的時代隨著蘇聯崩解劃下句點,即使是共產黨仍繼續存在的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實際上也已放棄列寧式馬克思主義的老教條。一旦各國共黨紛紛放棄昔日計畫,馬克思將發現自己再度陷入無人聞問的處境。共產主義自稱是馬克思唯一的繼承者,而馬克思的觀念也幾乎被等同於共產主義。即使持異議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馬列主義者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抨擊史達林之後建立了少數據點,但他們幾乎一定會被歸類為前共產主義的分離份子。因此,在馬克思去世一百週年後的近二十年來,嚴格來說,他已成為不值一提的過時人物。有些記者甚至認為今晚的討論是為了把馬克思從「歷史的垃圾桶」裡解救出來。然而時至今日,馬克思很可能再次引領風潮,成為二十一世紀人們所關注的思想家。
英國廣播公司(BBC)進行的民調顯示,英國收聽廣播的民眾認為馬克思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但對於這項結果,我認為毋須認真看待。不過,如果用 Google 搜尋馬克思的名字,你將發現他仍是資料條目最多的偉大思想家之一,僅次於達爾文與愛因斯坦,但遙遙領先亞當.斯密與佛洛伊德。
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結束解放了馬克思,人們不再將馬克思等同於理論上的列寧主義與實踐上的列寧主義政權。大家越來越了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九○年代以後浮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都不可思議地被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所言中。我們可以從人們的反應看出這點,一九九八年是《共產黨宣言》這部令人吃驚的小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一年。諷刺的是,再度挖掘出馬克思的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家:極度消沉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能力舉辦這場週年紀念活動。回想起來,有件事也讓我感到驚訝,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機上雜誌的編輯找上我,這份雜誌的讀者有八成是美國商務人士。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共產黨宣言》的文章;這位編輯覺得他的讀者應該會對《共產黨宣言》的相關論題感興趣,於是向我徵詢是否能使用我的文章。更讓我驚訝的還有一件事,在一場世紀之交的午餐會上,喬治.索羅斯問我對馬克思的看法。我知道我們的觀點南轅北轍,為了避免爭論,我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但索羅斯卻說:「這個人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發現資本主義的缺失,而我們到現在才發現。」索羅斯確實注意到馬克思提到的論點。很快地,那些就我所知從來不是共產黨員的作家也開始認真檢視馬克思,而阿塔里寫的馬克思傳記與研究就是一例。阿塔里也認為馬克思的許多想法與那些致力改善今日社會的人若合符節。值得指出的是,光憑這些觀點,今日的我們就有必要好好地思考馬克思。
二〇〇八年十月,當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出這樣的標題:「動盪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onvulsion)時,無庸置疑地,馬克思又回到公眾面前。雖然全球資本主義經歷自一九三○年代初期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但馬克思仍無法自外於這場混亂。另一方面,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將不同於二十世紀的馬克思。
上個世紀對馬克思的看法,主要取決於三項事實。首先是國家的區別,也就是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與未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的區別,後者廣義來說是指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區的已開發國家。從第一項事實而產生了第二項事實:馬克思的傳承自然而然地分成兩派,一派是社會民主主義與修正主義,另一則是革命派,後者完全體現在俄國革命上。第三項事實使這兩派的分歧在一九一七年後更加明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年代晚期,也就是我所謂的「災難的年代」(Age of Catastrophe),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在這段時期逐漸崩解。這場危機嚴重到令許多人懷疑資本主義是否還有可能恢復。資本主義不是已經注定被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嗎?就連完全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的約瑟夫.熊彼得也於一九四○年代做了這樣的預測。事實上,資本主義確實起死回生了,但再也不是過去的形式。另一方面,同一時間在蘇聯,社會主義道路似乎已無崩潰之虞。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六○年間,人們(就連那些反對蘇聯政權政治措施的非社會主義者也如此認為)其實有理由相信,資本主義已經油盡燈枯,而蘇聯正證明它的生產力可以超邁資本主義。在蘇聯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發射那年,這些想法聽起來並不荒謬。蘇聯經濟成果變調的各種證據一直要到一九六〇年後才紛紛出爐。
這些事件及其對政策與理論的影響,完全是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死後才發生的。它們完全超出馬克思自身的經驗與判斷。我們對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判斷並不以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為依據,而是以後世對其著作的詮釋或修正為準則。我們頂多只能主張,在一八九○年代晚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遭遇第一次思想危機時,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與馬克思或更多是與恩格斯有過接觸)已經開始討論與二十世紀相關的一些議題,特別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日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有許多完全屬於二十世紀而不見於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或應該如何的討論,這個議題多半來自於一九一四到一八年大戰經濟以及戰後準革命或革命危機的經驗。
一
二〇〇七年,猶太書週於卡爾.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週年前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舉行,地點離馬克思過去最常造訪倫敦的地方──大英博物館圓形閱覽室(Round Reading Room),只有幾步路的距離。賈克.阿塔里與我是立場迥異的社會主義者,卻不約而同來此向他致上敬意。然而,當你想到地點與日期,就會產生一種雙重的意外感受。我們不能說馬克思在一八八三年去世時一事無成,因為他的作品已對德國,特別是對俄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影響,而由他的門徒所領導的運動正逐漸主導德國的勞工運動。但在一八八三年時,馬克思一生的努力似乎還未竟全功。他已經寫了幾部卓越的小書,而那部未完成的作品:《資本論》(Das Kapital),在他人生最後十年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當一名訪客問起他的作品時,他苦澀地反問:「什麼作品?」自從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六四年至七三年所謂的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失敗後,馬克思的政治努力已無成功的可能。馬克思雖然大半生流亡英國,但他在當地的政治或思想界卻未曾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馬克思死後卻享有極高聲譽!在他去世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以他的名字為號召或受他啟迪的歐洲工人階級政黨,在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中獲得百分之十五到四十七的選票──英國是唯一例外。一九一八年後,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政黨都成了執政黨,而不只是反對黨,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法西斯主義結束之後,然而到了這段時期,這些政黨絕大多數卻處心積慮與他們原先的啟蒙者劃清界線。這些政黨至今依然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的門徒也在非民主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革命團體。在馬克思去世的七十年後,有三分之一的人類生活在由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之下,這些政府宣稱他們代表馬克思的觀念並且實現了他的願望。之後,儘管這些執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大幅轉變政策方針,卻仍有兩成以上宣稱他們堅持馬克思路線。簡言之,要說有哪位思想家在二十世紀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那麼此人非馬克思莫屬。走進十九世紀巨擘卡爾.馬克思與赫伯特.斯賓塞埋骨的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耐人尋味的是,兩座墳塋居然彼此對望。當兩人都在世時,人們公認斯賓塞是當時的亞里斯多德,而馬克思不過是住在漢普斯特(Hampstead)矮坡上仰賴朋友資助度日的無名小卒。今日,已無人知道斯賓塞長眠此地,但老一輩來自日本與印度的朝聖者仍前來拜謁馬克思的墓塚,就連流亡海外的伊朗人與伊拉克人也堅持死後應埋葬於此受其庇蔭。
共產黨政權與廣大的共產主義政黨橫行的時代隨著蘇聯崩解劃下句點,即使是共產黨仍繼續存在的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實際上也已放棄列寧式馬克思主義的老教條。一旦各國共黨紛紛放棄昔日計畫,馬克思將發現自己再度陷入無人聞問的處境。共產主義自稱是馬克思唯一的繼承者,而馬克思的觀念也幾乎被等同於共產主義。即使持異議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馬列主義者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抨擊史達林之後建立了少數據點,但他們幾乎一定會被歸類為前共產主義的分離份子。因此,在馬克思去世一百週年後的近二十年來,嚴格來說,他已成為不值一提的過時人物。有些記者甚至認為今晚的討論是為了把馬克思從「歷史的垃圾桶」裡解救出來。然而時至今日,馬克思很可能再次引領風潮,成為二十一世紀人們所關注的思想家。
英國廣播公司(BBC)進行的民調顯示,英國收聽廣播的民眾認為馬克思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但對於這項結果,我認為毋須認真看待。不過,如果用 Google 搜尋馬克思的名字,你將發現他仍是資料條目最多的偉大思想家之一,僅次於達爾文與愛因斯坦,但遙遙領先亞當.斯密與佛洛伊德。
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結束解放了馬克思,人們不再將馬克思等同於理論上的列寧主義與實踐上的列寧主義政權。大家越來越了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九○年代以後浮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都不可思議地被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所言中。我們可以從人們的反應看出這點,一九九八年是《共產黨宣言》這部令人吃驚的小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一年。諷刺的是,再度挖掘出馬克思的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家:極度消沉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能力舉辦這場週年紀念活動。回想起來,有件事也讓我感到驚訝,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機上雜誌的編輯找上我,這份雜誌的讀者有八成是美國商務人士。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共產黨宣言》的文章;這位編輯覺得他的讀者應該會對《共產黨宣言》的相關論題感興趣,於是向我徵詢是否能使用我的文章。更讓我驚訝的還有一件事,在一場世紀之交的午餐會上,喬治.索羅斯問我對馬克思的看法。我知道我們的觀點南轅北轍,為了避免爭論,我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但索羅斯卻說:「這個人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發現資本主義的缺失,而我們到現在才發現。」索羅斯確實注意到馬克思提到的論點。很快地,那些就我所知從來不是共產黨員的作家也開始認真檢視馬克思,而阿塔里寫的馬克思傳記與研究就是一例。阿塔里也認為馬克思的許多想法與那些致力改善今日社會的人若合符節。值得指出的是,光憑這些觀點,今日的我們就有必要好好地思考馬克思。
二〇〇八年十月,當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出這樣的標題:「動盪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onvulsion)時,無庸置疑地,馬克思又回到公眾面前。雖然全球資本主義經歷自一九三○年代初期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但馬克思仍無法自外於這場混亂。另一方面,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將不同於二十世紀的馬克思。
上個世紀對馬克思的看法,主要取決於三項事實。首先是國家的區別,也就是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與未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的區別,後者廣義來說是指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區的已開發國家。從第一項事實而產生了第二項事實:馬克思的傳承自然而然地分成兩派,一派是社會民主主義與修正主義,另一則是革命派,後者完全體現在俄國革命上。第三項事實使這兩派的分歧在一九一七年後更加明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年代晚期,也就是我所謂的「災難的年代」(Age of Catastrophe),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在這段時期逐漸崩解。這場危機嚴重到令許多人懷疑資本主義是否還有可能恢復。資本主義不是已經注定被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嗎?就連完全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的約瑟夫.熊彼得也於一九四○年代做了這樣的預測。事實上,資本主義確實起死回生了,但再也不是過去的形式。另一方面,同一時間在蘇聯,社會主義道路似乎已無崩潰之虞。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六○年間,人們(就連那些反對蘇聯政權政治措施的非社會主義者也如此認為)其實有理由相信,資本主義已經油盡燈枯,而蘇聯正證明它的生產力可以超邁資本主義。在蘇聯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發射那年,這些想法聽起來並不荒謬。蘇聯經濟成果變調的各種證據一直要到一九六〇年後才紛紛出爐。
這些事件及其對政策與理論的影響,完全是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死後才發生的。它們完全超出馬克思自身的經驗與判斷。我們對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判斷並不以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為依據,而是以後世對其著作的詮釋或修正為準則。我們頂多只能主張,在一八九○年代晚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遭遇第一次思想危機時,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與馬克思或更多是與恩格斯有過接觸)已經開始討論與二十世紀相關的一些議題,特別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日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有許多完全屬於二十世紀而不見於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或應該如何的討論,這個議題多半來自於一九一四到一八年大戰經濟以及戰後準革命或革命危機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