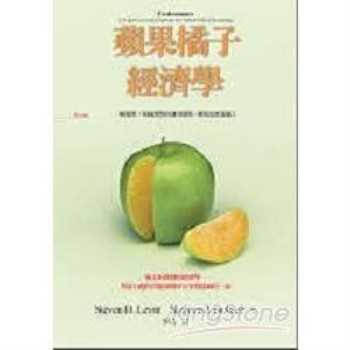由深具名望的知識精英組成的哈佛大學的研究員學會(Society of Fellows)提供年輕學者三年的獎金,自由進行研究。賴維特接受學會面談之初,並不奢望有什麼結果。他自認初出茅廬,算不上知識份子。學會安排他在晚餐時接受一批資深會員的面談,都是舉世知名的哲學家、科學家或歷史學家。賴維特擔心自己沒有充分的話題,可能連第一輪都撐不過。
果不其然,其中一位資深會員問道:「我弄不清楚你的研究工作的一貫主題何在,可否請你解釋一下?」
賴維特為之語塞。他不知道自己的一貫主題何在,甚至不知道是否有這樣的主題存在。
當時尚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申恩(Amartya Sen)出面打圓場,以他的觀點簡要總結賴維特的主題。
沒錯,賴維特殷切地承認,這就是我的主題。
你說的對,賴維特說,這就是我的主題。
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像許多狗爭食一塊骨頭,直到哲學家諾西克(Robert Nozick)插話進來。
他問道:「史蒂夫,你幾歲?」
「二十六。」
諾西克轉身對其他會員說:「他才二十六歲,為什麼就得有一貫的主題?或許他就是那種天賦異稟的人,根本不需要有什麼主題。他只消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回答,這就夠了。」
——《紐約時報雜誌》二○○三年八月三日
緒論 事物隱藏的一面
說明本書的主旨: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經濟學就代表真實的世界運作方式
如果一九九○年代初你住在美國,就算只是偶爾瞄一下電視新聞或翻翻報紙,都可能給嚇個半死。
癥結在於犯罪問題。犯罪案件急遽增加——各城市近幾十年來犯罪率趨勢圖,形狀有如陡峭的滑雪坡道——而且似乎無所不在。槍擊與謀殺案件是家常便飯,劫車、毒品交易、搶劫、強暴等也不算新鮮。暴力犯罪成為人人身邊揮之不去的陰影。然而專家們眾口一辭,認為狀況還會惡化到嚴重得多的地步。
令人畏懼的是所謂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有一陣子,他似乎無所不在,從《新聞週刊》的封面對你怒目而視,由厚厚的政府報告中大搖大擺走來。他被描述成一個瘦削的都市青少年,手握廉價手槍,滿腦子暴力思想。據說全美國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一個殺手世代即將把整個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境。 專家如何曲解事實 之一
一九九五年,犯罪學者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一份呈送司法部長的報告中,嚴肅地詳述即將到來的青少年殺人潮。福克斯提出樂觀與悲觀的版本。在樂觀版本中,他預估青少年殺人案件在未來十年會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在悲觀版本中,更是會增加一倍。他指出:「下一波的犯罪潮十分嚴重,相較之下,一九九五年還算是美好的年代呢。」
其他犯罪學者、政治學者與專業的預測者也描繪類似的恐怖前景,連當時的總統柯林頓也不例外。他指出:「我們還有大約六年的時間扭轉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否則將來就得生活在混亂之中,屆時我的繼任者發表演說時,談的不會是全球經濟的大好機會,因為忙著保障城市街頭的人身安全都來不及了。」押注在犯罪繼續增加這方顯然錯不了。
然而,接下來幾年犯罪率並未節節升高,反而開始下降,並且愈降愈低。犯罪減少還有幾點令人驚訝的特質:首先是全面性,全國各地的各類犯罪全都下跌;而且下跌具有持續性,年復一年地減少。這種現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尤其是原先作出相反預測的專家更是跌破眼鏡。
犯罪率反轉的幅度相當驚人。青少年殺人的比率非但未如福克斯所預估,成長一倍或至少百分之十五,反而在五年內下跌超過百分之五十。到二○○○年,美國整體謀殺率降到三十五年來最低水準,其他各類犯罪也幾乎呈現同樣趨勢,從暴力攻擊到竊車全無例外。
雖然專家對犯罪下跌的預測不靈光——其實就在他們發出嚇人的預測時,下跌趨勢已見端倪——不過現在卻急忙找出解答,而且大多數的理論聽來頗為合理。他們指出,一九九○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扭轉犯罪率,還有就是槍枝管制法規擴大施行,其他諸如紐約市推動創新的治安策略,使謀殺案由一九九○年的二、二四五件下降為二○○三年的五九六件。
這些理論不但合乎邏輯,而且振奮人心,因為犯罪的下跌乃是歸功於近期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說扼制犯罪率靠的是槍枝管制、良好的治安策略與所得提高,那麼我們自己手中其實一直握有打擊犯罪的力量。以後再出現犯罪增加的情況,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這些理論由專家之口傳到記者之耳,再進入大眾腦海中,順理成章地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看法。
只不過有個問題存在:這些理論根本不正確。 專家如何曲解事實 之二
有一項因素倒是對一九九○年代犯罪大幅下跌產生深遠的影響。事情的源起可以從當時往前推二十多年,由德州達拉斯一名叫做諾瑪‧麥柯維(Norma McCorvey)的年輕女子說起。
就像遠方一隻蝴蝶拍動翅翼,最終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風暴,麥柯維也在無意之間扭轉了趨勢。其實當時她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墮胎。這位二十一歲的貧窮女性未受教育,無一技之長,又有酗酒與濫用藥物的惡習,先前生過兩個小孩送人收養。一九七○年,她發現自己再度懷孕。不過當時德州和全美大多數州一樣,墮胎並未合法化。麥柯維的狀況被一些有力人士援引,讓她成為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共同訴訟中領銜的原告,被告則是達拉斯郡地區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這場官司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當時麥柯維已改用珍‧洛伊(Jane Roe)的化名。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法院判決洛伊勝訴,准許全國墮胎合法化。當然,此時墮胎對麥柯維而言已為時太晚,她早就生下小孩,並交由他人收養。(多年後,她放棄贊成墮胎合法化的立場,而倡導尊重生命。)
那麼,洛伊v.韋德案(Roe v. Wade)在過了一個世代後,又是如何發揮作用,導致犯罪率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
以犯罪而言,人人並非生而平等,而且差別還相當大。數十年的研究資料顯示,出生於劣勢家庭環境的小孩,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高得多。數百萬最可能因洛伊v.韋德案而得以墮胎的女性——貧窮、未婚、年輕,沒有錢進行不合法的墮胎——正好就是處於典型的劣勢環境,她們的小孩未來成為罪犯的可能性遠高於水準平均。由於墮胎合法化,這些小孩並沒有生下來。這項強大的因素影響至深且遠:多年之後,當這些未出生小孩達到犯罪年齡之際,犯罪率開始加速下降。
扼止美國犯罪浪潮的功臣並非槍枝管制、經濟繁榮或治安策略,關鍵的因素乃是潛在犯罪者大幅縮減。
現在那些專家(也就是早先提出恐怖預言的同一批人)向媒體解釋犯罪率的下降時,他們推銷的理論中有幾次提到墮胎合法化的影響?
一次也沒有。 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
這本書要談的不是口香糖與競選支出的對比,也不是不盡責的房地產仲介人員,或是墮胎合法化對犯罪的影響。我們當然會提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場景,如子女的教養、作弊的方式、三K黨的內部運作與益智競賽中的種族歧視等。本書希望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觀察內部的狀況如何。我們將提出許多問題,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則攸關生死。我們的答案往往看似突兀,不過在了解事實後,又相當順理成章。我們會由資料中尋找答案——不論這些資料是學童的考試成績、紐約市的犯罪統計或毒販的財務紀錄。(我們經常會運用資料中無意間透露的模式,就像飛機掠過高空時留下的凝結尾。)對某個主題抱持自己的意見或理論當然沒錯,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如果能去除道德立場,誠實地檢驗資料,結果往往會得到嶄新而出人意料的見解。
我們可以說,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而經濟學則代表真實世界的運作方式。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測量的科學,包含一組功能與彈性均相當完善的工具,可以可靠地測量錯綜複雜的資訊,計算出任何一個因素乃至整體的作用大小。所謂「經濟」,不外是:關於工作、房地產、銀行與投資等錯綜複雜的資訊。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可以很輕易地應用到——怎麼說呢?——「更有趣」的主題上。
本書的撰寫立基於一些基本的理念:
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理解——或抽絲剝繭找出——各項誘因,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
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犯罪案件在一九九○年代並未直線上升,單靠金錢無法贏得選舉,還有——可能令你吃驚的是——每天喝八大杯水有助健康,其實一直沒有經過實證資料支持。傳統看法的形成往往相當粗糙,但很難被看穿——不過並非完全不可能。
重大的影響往往源自久遠甚或微不足道的原因。謎團的答案未必全都擺在你的面前。麥柯維對犯罪率下跌的影響,遠超過槍枝管制、經濟繁榮以及創新的治安策略加總起來的效果。我們接下來還會舉出這樣的例子。
專家——從犯罪學者到房地產仲介人員——利用資訊優勢為謀取自己利益。不過面對網際網路的崛起,專家們傳統上的資訊優勢日漸縮水。
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可以讓複雜的世界大為簡化。如果你了解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讀資料,就能解開看似無解的謎團。因為數字的威力無窮,可以剝除層層的混亂與矛盾。
因此本書的目標在於探討每件事情背後隱藏的一面。有時候這麼做吃力不討好,甚至會讓你覺得自己以管窺天或是由哈哈鏡中看世界。不過我們的理念是去觀察許多不同的場景,並運用創新的方式加以檢驗。以這樣的理念來寫一本書似乎有些奇特,大多數書籍都是標明單一的主題,先以一、兩句話簡單勾勒大綱,再完整地講述來龍去脈:鹽的歷史、民主的脆弱、標點符號的運用等等。本書並沒有這種一貫的主題。我們的確短暫地想過圍繞一個中心主題——好比說應用個體經濟學的理論與實務?——來寫作,但隨即決定還是採用尋寶的方式。沒錯,這個方式會用到經濟學中最佳的分析工具,但同時也容許我們追索自己想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因此我們發明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本書所舉例子通常不會出現在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不過這種情況往後可能會改變。經濟學這門科學主要是一組工具,而不是有特定主題,因此任何主題,無論多麼稀奇古怪,未必不能納入它的範疇中。
別忘了,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本是位哲學家,而在致力成為道德家的過程中變成了經濟學家。他於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e Sentiments)時,現代資本主義才剛萌芽。斯密深感於這股新興力量襲捲而來的變革,不過他關注的不僅是客觀數字,還有人類受到的影響,因為個人在特定環境中的所思所行,都會受經濟力量所左右。為什麼有人欺騙、偷竊,有些人就不會?為何某人看似無害的選擇,卻影響到一連串的人?在斯密的年代,因果作用開始急遽加速,各項誘因也擴大好幾倍。這些改變給當時民眾帶來的衝擊與震撼,不遜於現代生活加諸我們的衝擊與震撼。
斯密真正探討的主題乃是個人欲望與社會規範間的磨擦。海爾布洛納(Robert Heilbroner)在《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中驚嘆,斯密能夠把人類這種自利的動物的所作所為,與人類更廣大的道德領域區隔開來。他指出:「斯密認為答案在於我們有能力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變成公正的旁觀者,如此即可形成對某一案例客觀特性看法。」
想像你自己在一位——或兩位——第三者陪同下,積極探索一些有趣案例的客觀特性。這樣的探索一開始通常是提出一個過去沒人問過的問題,比如說:學校老師與相撲選手有什麼共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