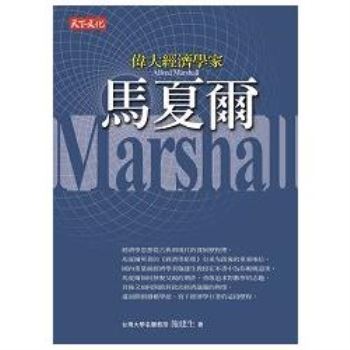當代偉大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曾在他最後一本遺著《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表達,英國經濟思想發展到了1870年代,出現一個「馬夏爾時代」(Marshallian Age)。那麼,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是何許人?他對經濟學有何貢獻?這些就成為大家所關注的問題。當馬夏爾於1924年逝世時,當代另一位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表示對他的老師馬夏爾的崇敬與懷念,曾寫了一本優美完整的《馬夏爾傳》(Alfred Marshall , 1842-1924),對於上述的那些問題都有所解答敘述。現在我們可先以他這本傳記為依據,略作傳述。
一、父親的期盼
馬夏爾於1842年出生於倫敦近郊的Clapham,父親William是英格蘭銀行的一名出納,性格嚴正,為一位篤信福音派新教的虔誠教徒。
馬夏爾九歲時,進入當地的Merchant Taylor’sSchool攻讀。他父親時常想起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如何督促兒子約翰‧司徒‧彌爾(John Stuart Mill)向學的故事,對於馬夏爾在學校中課務的進展一直非常關心,尤其是對其中的希伯來文(猶太文,Hebrew),總是要他念到晚間11時方可休止。
由於在校期間成績優良,1861年時他就獲得獎學金,取得進入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Oxford) 的許諾, 三年後還可升為研究員(Fellowship),其所可享受之未來安全保障,與當時最著名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的伊登獎學金者(Eton Scholar)所能獲得的完全相同。他父親獲知以後感到非常喜悅,因為這是獲得神職任命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希望兒子能成為一位傳教士。但馬夏爾並不感到興奮,因為傳教並不是他將來很想要擔負的職務,他對這種偏重古典文學的獎助並不很傾慕,他當時所喜愛的是數學,但他並不反對正統的神學,他反對的是古典的研習。
二、個人的性向
根據凱恩斯的敘述,馬夏爾後來時常憶起他那位專橫的父親,如何使他晚上不能入睡而專讀希伯來文,以求有良好的成績。他父親同時禁止他讀數學,一見到他拿著數學的書就感到不快。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好在上學時將數學書藏在自己的衣袋中,然後在行走時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加以思索,期能在心中求出解答。他的數學老師覺得他有數學的天才,而他父親卻毫不能理解。
總之,在馬夏爾看來,數學是他的救贖,他不能再到牛津去讀那些死的文字,而要到劍橋去找生命的源泉。但他父親不夠富裕,無法負擔放棄牛津獎學金後所需的費用。在這種困局中,他好心的叔叔Charles願意借錢給他們解決困難。那麼,這位好心的叔叔如何會有這筆款呢?後來到1875年,馬夏爾還想到美國一行,所需旅費也是由這位好心的叔叔借貸的,這筆錢款也非小數,他又何能如此富有呢?據凱恩斯記載,這是因為當澳洲發現金礦時,他攜眷前往,並在那邊創設了一個畜牧場。當金礦業衰落時,他自己規定,凡身體無缺陷的與他同輩的人都不僱用,只僱盲人、跛者與殘障者。當黃金市場旺盛達於極點時,所有體力能勝任的人都回到礦場,結果只有他一家牧場仍能照常營業。他就這樣發了一筆財,回到祖國,而能夠幫助他的侄兒解決一時的窮困,實現他的美夢。
到了1865年,他終於在劍橋聖約翰學院完成了學業,成績極為優良,僅次於後來對於物理科學具有卓越貢獻的瑞利勛爵(Lord Rayleigh),因而立即被任命為研究員。他提出研究分子物理學的計畫,同時在克夫登學院(Clifton College)暫時擔任數學教席以維持生計,並償還對叔叔的債務。不久以後,他回到劍橋指導該校之「數學榮譽學位考試」(Mathematical Tripos)事務一個短期。因此,他更能如此說:「數學已償還了我的積欠,我可以自由抒發我的性癖了。」
三、課題的抉擇
馬夏爾在克夫登期間的關鍵重要性是從而交到了一些朋友,並再由這些朋友接觸到以當時劍橋三一學院道德科學研究員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為中心的朋友。在此以後我們無法證明他曾與同輩比較著名的人士有所交往。但當他回到劍橋以後就成為一個小型討論團體的一個份子。這個團體稱為格爾特學社(Grote Club),是由當時教區牧師兼道德哲學教授格爾特(John Grote)所創,馬夏爾曾如此敘述他被邀參加該會後的情形:
「當我在1867年被邀入社後,積極的社員有F. D. Maurice(Grote的繼任者)、西奇威克、Venn、J. R. Mozley與J. B. Pearson⋯⋯,在1867年或1868年後,該社一度稍見消沉,但自W. K. Clifford與J. F. Moulton參加以後,新的活力立即注入。在一、兩年間,西奇威克、Mozley、Clifford、Moulton和我都是積極活躍的社員,我們都經常出席聚會。Clifford與Moulton在那時只曾少許讀了一些哲學,所以他們在討論會進行的前半段都保持緘默,專心諦聽他人的發言,特別是西奇威克所說的。然後在後半段時他們就讓自己放鬆唇舌,進展都很動人。如果我可從我在這些晚上聽到的十多篇的精彩發言中選一、二篇範例,那就非西奇威克與Clifford的莫屬了。⋯⋯」
就在這一時節以及這些影響力發揮的情景之下,馬夏爾在其心智發展上激起危機,他原有研究物理學的計畫就「因這種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其是它對於神學的關係發生濃厚興趣之突然增加而被打破了。」(馬夏爾自己的言語)。當此時期,先後有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 1859),斯賓塞的《第一原理》(H.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 1860-1862)及彌爾的《William Hamilton哲學之檢討》(J. S. Mill,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 1865)等書的出版,曾在英國哲學界,至少是劍橋哲學界引起對基督教教條之信心的動搖。青年們所關心的都傾向於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倫理
學。在這種情形之下,馬夏爾亦轉入形而上學的研究,然後就由形而上學的探究而轉到倫理學,最後又由倫理學轉入經濟學。他在回顧其心智歷史時曾這樣說:
「我從形而上學走到倫理學,我想要對社會現狀加以辯護是不容易的。有一位朋友曾讀了許多現在稱為道德科學的書,常常說:『啊!如果你瞭解政治經濟學就不會這樣說了。』因此我就讀了彌爾的《政治經濟學》,感到非常興奮。我對於機會不平等的懷疑要超過對於物質安康的不平等。於是我在假日時,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區域,從其中的一個街頭步行到另一街頭,見到許多最貧窮人的臉容,接著我就決定要盡可能地將政治經濟學研讀個透徹。」
在1868年,當他仍在研究形而上學的時期,一種想要對康德(Kant)做原始性研究的欲念驅使他到了德國。他有一次說:「康德是我的導師,是我唯一崇拜的人。但我想再進一步卻不可得,在這外邊似乎為一片陰霧所籠罩,模糊不清,而社會問題總是不知不覺地來到面前。真實的生活難道只限於少數的一群人所能享有的嗎?」他與一位早年曾教過西奇威克的德國教授住在Dresden,黑格爾(Hegel)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of History)大大地影響著他。他同時也接觸到德國的經濟學家,特別是Roscher(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最後聖約翰學院的院長Dr. Bateson給他一個終身職位,即道德科學的特別講座。不久以後,他終於選擇經濟學做為以後研討的主題,雖然他一度也曾擔任道德科學中其他課目如邏輯等短期講師。他這兩年在腦海中所激起的疑慮與動盪終於告一段落,他深切地體悟到今後所要獻身的將是一門對人類福祉與美好生活可以產生決定性功用的學科,因而感到非常滿意。這與早期他父親所期盼他能獲得神聖任命所能肇致的欣慰應無差異。
一、父親的期盼
馬夏爾於1842年出生於倫敦近郊的Clapham,父親William是英格蘭銀行的一名出納,性格嚴正,為一位篤信福音派新教的虔誠教徒。
馬夏爾九歲時,進入當地的Merchant Taylor’sSchool攻讀。他父親時常想起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如何督促兒子約翰‧司徒‧彌爾(John Stuart Mill)向學的故事,對於馬夏爾在學校中課務的進展一直非常關心,尤其是對其中的希伯來文(猶太文,Hebrew),總是要他念到晚間11時方可休止。
由於在校期間成績優良,1861年時他就獲得獎學金,取得進入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Oxford) 的許諾, 三年後還可升為研究員(Fellowship),其所可享受之未來安全保障,與當時最著名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的伊登獎學金者(Eton Scholar)所能獲得的完全相同。他父親獲知以後感到非常喜悅,因為這是獲得神職任命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希望兒子能成為一位傳教士。但馬夏爾並不感到興奮,因為傳教並不是他將來很想要擔負的職務,他對這種偏重古典文學的獎助並不很傾慕,他當時所喜愛的是數學,但他並不反對正統的神學,他反對的是古典的研習。
二、個人的性向
根據凱恩斯的敘述,馬夏爾後來時常憶起他那位專橫的父親,如何使他晚上不能入睡而專讀希伯來文,以求有良好的成績。他父親同時禁止他讀數學,一見到他拿著數學的書就感到不快。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好在上學時將數學書藏在自己的衣袋中,然後在行走時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加以思索,期能在心中求出解答。他的數學老師覺得他有數學的天才,而他父親卻毫不能理解。
總之,在馬夏爾看來,數學是他的救贖,他不能再到牛津去讀那些死的文字,而要到劍橋去找生命的源泉。但他父親不夠富裕,無法負擔放棄牛津獎學金後所需的費用。在這種困局中,他好心的叔叔Charles願意借錢給他們解決困難。那麼,這位好心的叔叔如何會有這筆款呢?後來到1875年,馬夏爾還想到美國一行,所需旅費也是由這位好心的叔叔借貸的,這筆錢款也非小數,他又何能如此富有呢?據凱恩斯記載,這是因為當澳洲發現金礦時,他攜眷前往,並在那邊創設了一個畜牧場。當金礦業衰落時,他自己規定,凡身體無缺陷的與他同輩的人都不僱用,只僱盲人、跛者與殘障者。當黃金市場旺盛達於極點時,所有體力能勝任的人都回到礦場,結果只有他一家牧場仍能照常營業。他就這樣發了一筆財,回到祖國,而能夠幫助他的侄兒解決一時的窮困,實現他的美夢。
到了1865年,他終於在劍橋聖約翰學院完成了學業,成績極為優良,僅次於後來對於物理科學具有卓越貢獻的瑞利勛爵(Lord Rayleigh),因而立即被任命為研究員。他提出研究分子物理學的計畫,同時在克夫登學院(Clifton College)暫時擔任數學教席以維持生計,並償還對叔叔的債務。不久以後,他回到劍橋指導該校之「數學榮譽學位考試」(Mathematical Tripos)事務一個短期。因此,他更能如此說:「數學已償還了我的積欠,我可以自由抒發我的性癖了。」
三、課題的抉擇
馬夏爾在克夫登期間的關鍵重要性是從而交到了一些朋友,並再由這些朋友接觸到以當時劍橋三一學院道德科學研究員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為中心的朋友。在此以後我們無法證明他曾與同輩比較著名的人士有所交往。但當他回到劍橋以後就成為一個小型討論團體的一個份子。這個團體稱為格爾特學社(Grote Club),是由當時教區牧師兼道德哲學教授格爾特(John Grote)所創,馬夏爾曾如此敘述他被邀參加該會後的情形:
「當我在1867年被邀入社後,積極的社員有F. D. Maurice(Grote的繼任者)、西奇威克、Venn、J. R. Mozley與J. B. Pearson⋯⋯,在1867年或1868年後,該社一度稍見消沉,但自W. K. Clifford與J. F. Moulton參加以後,新的活力立即注入。在一、兩年間,西奇威克、Mozley、Clifford、Moulton和我都是積極活躍的社員,我們都經常出席聚會。Clifford與Moulton在那時只曾少許讀了一些哲學,所以他們在討論會進行的前半段都保持緘默,專心諦聽他人的發言,特別是西奇威克所說的。然後在後半段時他們就讓自己放鬆唇舌,進展都很動人。如果我可從我在這些晚上聽到的十多篇的精彩發言中選一、二篇範例,那就非西奇威克與Clifford的莫屬了。⋯⋯」
就在這一時節以及這些影響力發揮的情景之下,馬夏爾在其心智發展上激起危機,他原有研究物理學的計畫就「因這種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其是它對於神學的關係發生濃厚興趣之突然增加而被打破了。」(馬夏爾自己的言語)。當此時期,先後有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 1859),斯賓塞的《第一原理》(H.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 1860-1862)及彌爾的《William Hamilton哲學之檢討》(J. S. Mill,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 1865)等書的出版,曾在英國哲學界,至少是劍橋哲學界引起對基督教教條之信心的動搖。青年們所關心的都傾向於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倫理
學。在這種情形之下,馬夏爾亦轉入形而上學的研究,然後就由形而上學的探究而轉到倫理學,最後又由倫理學轉入經濟學。他在回顧其心智歷史時曾這樣說:
「我從形而上學走到倫理學,我想要對社會現狀加以辯護是不容易的。有一位朋友曾讀了許多現在稱為道德科學的書,常常說:『啊!如果你瞭解政治經濟學就不會這樣說了。』因此我就讀了彌爾的《政治經濟學》,感到非常興奮。我對於機會不平等的懷疑要超過對於物質安康的不平等。於是我在假日時,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區域,從其中的一個街頭步行到另一街頭,見到許多最貧窮人的臉容,接著我就決定要盡可能地將政治經濟學研讀個透徹。」
在1868年,當他仍在研究形而上學的時期,一種想要對康德(Kant)做原始性研究的欲念驅使他到了德國。他有一次說:「康德是我的導師,是我唯一崇拜的人。但我想再進一步卻不可得,在這外邊似乎為一片陰霧所籠罩,模糊不清,而社會問題總是不知不覺地來到面前。真實的生活難道只限於少數的一群人所能享有的嗎?」他與一位早年曾教過西奇威克的德國教授住在Dresden,黑格爾(Hegel)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of History)大大地影響著他。他同時也接觸到德國的經濟學家,特別是Roscher(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最後聖約翰學院的院長Dr. Bateson給他一個終身職位,即道德科學的特別講座。不久以後,他終於選擇經濟學做為以後研討的主題,雖然他一度也曾擔任道德科學中其他課目如邏輯等短期講師。他這兩年在腦海中所激起的疑慮與動盪終於告一段落,他深切地體悟到今後所要獻身的將是一門對人類福祉與美好生活可以產生決定性功用的學科,因而感到非常滿意。這與早期他父親所期盼他能獲得神聖任命所能肇致的欣慰應無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