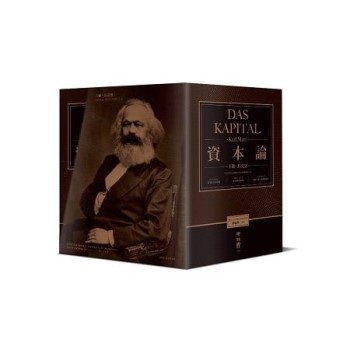內文選摘(節錄)
第十四章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
勞動過程最初是抽象地,撇開它的各種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來考察的。在那裡曾指出:「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在注(7)中還補充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這裡要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後來彼此分離開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後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
因此,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餘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麼,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廠,而投入教育工廠,這並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絕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係,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在闡述理論史的本書第四冊將更詳細地談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剩餘價值的生產看做生產工人的決定性的特徵。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對生產工人所下的定義,隨著它對剩餘價值性質的看法的改變而改變。例如,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提供剩餘價值。在重農學派看來,剩餘價值只存在於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只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的那個點,並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餘勞動,這就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並且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起點。就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來說,工作日一開始就分成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這兩個部分。為了延長剩餘勞動,就要通過以較少的時間生產出工資的等價物的各種方法來縮短必要勞動。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革命。
因此,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種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從屬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種形式上的從屬,又讓位於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
至於各種中間形式,在這裡只要提一下就夠了。在這些中間形式中,剩餘勞動不是用直接強制的辦法從生產者那裡榨取的,生產者也沒有在形式上從屬資本。資本在這裡還沒有直接支配勞動過程。在那些用古老傳統的生產方式從事手工業或農業的獨立生產者的身旁,有高利貸者或商人,有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他們像寄生蟲似地吮吸著這些獨立生產者。這種剝削形式在一個社會內占統治地位,就排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過另一方面,這種剝削形式又可以成為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例如中世紀末期的情況就是這樣。最後,正如現代家庭勞動的例子所表明的B,某些中間形式還會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在某些地方再現出來,雖然它的樣子完全改變了。
對於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來說,只要勞動在形式上從屬於資本就夠了,例如,只要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就夠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也是生產絕對剩餘價值的方法。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C正是表現為大工業的特有的產物。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現在它作為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還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從屬資本的那些產業為它所占領,也就是說,它擴大作用範圍;第二,已經受它支配的產業由於生產方法的改變不斷發生革命。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餘價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超過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絕對延長為前提。絕對剩餘價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餘價值的運動,這種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確立並成為普遍的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只要涉及剩餘價值率的提高,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假定勞動力按其價值支付,那麼,我們就會面臨這樣的抉擇:如果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正常強度已定,剩餘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餘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相對量的變化才能提高,而這種變化在工資不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況下,又以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變化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要的生活資料,那麼他就沒有時間來無償地為第三者勞動。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種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種剩餘時間,就不可能有剩餘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隸主,不可能有封建貴族,一句話,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階級。
因此,可以說剩餘價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比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做食物。絕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各種神祕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繫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餘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係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此外,資本關係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係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繫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各國比較。
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餘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
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一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一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餘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從而節約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裡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榮的祕密。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餘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餘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只有靠剩餘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似乎提供剩餘產品是人類勞動的一種天生的性質。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一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那裡的森林中長著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鑽個孔,確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倒,分成幾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一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採得西米粉300磅,有時可採得500磅至600磅。那裡的居民到森林去採伐麵包,就像我們到森林去砍柴一樣。
假定東亞的一個這樣的麵包採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週需要勞動12小時。自然的恩惠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閒暇時間。要他把這些閒暇時間用於為自己生產,需要一系列的歷史條件;要他把這些時間用於為別人從事剩餘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如果那裡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這個誠實的人為了占有一個工作日的產品,也許每週就得勞動6天。自然的恩惠說明不了,為什麼他現在每週要勞動6天,或者為什麼他要提供5天的剩餘勞動。它只是說明,為什麼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於每週一天。但是,他的剩餘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種天生的神祕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併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到剩餘價值的起源。他把剩餘價值看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看來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他在談到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不是在其中尋找剩餘價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尋找決定剩餘價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學派公開宣稱,勞動生產力是利潤(應讀做剩餘價值)產生的原因。這無論如何總比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因為重商主義者認為,產品的價格超過產品生產費用而形成的餘額是從交換中,從產品高於其價值的出售中產生的。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只是迴避,而沒有解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確的本能,懂得過於深入地研究剩餘價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可是在李嘉圖以後半個世紀,約翰‧史都華‧彌爾先生還在拙劣地重複那些最先把李嘉圖學說庸俗化的人的陳腐遁詞,鄭重其事地宣稱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對此我們該說些什麼呢?
第十四章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
勞動過程最初是抽象地,撇開它的各種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來考察的。在那裡曾指出:「如果整個勞動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在注(7)中還補充說:「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在這裡要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後來彼此分離開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後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
因此,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餘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麼,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入香腸工廠,而投入教育工廠,這並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絕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係,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係,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在闡述理論史的本書第四冊將更詳細地談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剩餘價值的生產看做生產工人的決定性的特徵。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對生產工人所下的定義,隨著它對剩餘價值性質的看法的改變而改變。例如,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提供剩餘價值。在重農學派看來,剩餘價值只存在於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只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的那個點,並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餘勞動,這就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並且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起點。就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來說,工作日一開始就分成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這兩個部分。為了延長剩餘勞動,就要通過以較少的時間生產出工資的等價物的各種方法來縮短必要勞動。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革命。
因此,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種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從屬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種形式上的從屬,又讓位於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
至於各種中間形式,在這裡只要提一下就夠了。在這些中間形式中,剩餘勞動不是用直接強制的辦法從生產者那裡榨取的,生產者也沒有在形式上從屬資本。資本在這裡還沒有直接支配勞動過程。在那些用古老傳統的生產方式從事手工業或農業的獨立生產者的身旁,有高利貸者或商人,有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他們像寄生蟲似地吮吸著這些獨立生產者。這種剝削形式在一個社會內占統治地位,就排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過另一方面,這種剝削形式又可以成為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例如中世紀末期的情況就是這樣。最後,正如現代家庭勞動的例子所表明的B,某些中間形式還會在大工業的基礎上在某些地方再現出來,雖然它的樣子完全改變了。
對於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來說,只要勞動在形式上從屬於資本就夠了,例如,只要從前為自己勞動或者作為行會師傅的幫工的手工業者變成受資本家直接支配的雇傭工人就夠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也是生產絕對剩餘價值的方法。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C正是表現為大工業的特有的產物。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形式。現在它作為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還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從屬資本的那些產業為它所占領,也就是說,它擴大作用範圍;第二,已經受它支配的產業由於生產方法的改變不斷發生革命。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餘價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超過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絕對延長為前提。絕對剩餘價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餘價值的運動,這種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確立並成為普遍的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只要涉及剩餘價值率的提高,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假定勞動力按其價值支付,那麼,我們就會面臨這樣的抉擇:如果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正常強度已定,剩餘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的絕對延長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餘價值率就只有通過工作日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相對量的變化才能提高,而這種變化在工資不降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的情況下,又以勞動生產率或勞動強度的變化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時間來生產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要的生活資料,那麼他就沒有時間來無償地為第三者勞動。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種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種剩餘時間,就不可能有剩餘勞動,從而不可能有資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隸主,不可能有封建貴族,一句話,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階級。
因此,可以說剩餘價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比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做食物。絕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各種神祕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繫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餘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係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著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此外,資本關係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係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繫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各國比較。
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餘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
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一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一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餘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從而節約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裡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榮的祕密。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餘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餘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只有靠剩餘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似乎提供剩餘產品是人類勞動的一種天生的性質。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一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那裡的森林中長著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鑽個孔,確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倒,分成幾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一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採得西米粉300磅,有時可採得500磅至600磅。那裡的居民到森林去採伐麵包,就像我們到森林去砍柴一樣。
假定東亞的一個這樣的麵包採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週需要勞動12小時。自然的恩惠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閒暇時間。要他把這些閒暇時間用於為自己生產,需要一系列的歷史條件;要他把這些時間用於為別人從事剩餘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如果那裡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這個誠實的人為了占有一個工作日的產品,也許每週就得勞動6天。自然的恩惠說明不了,為什麼他現在每週要勞動6天,或者為什麼他要提供5天的剩餘勞動。它只是說明,為什麼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於每週一天。但是,他的剩餘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種天生的神祕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併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李嘉圖從來沒有考慮到剩餘價值的起源。他把剩餘價值看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東西,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他看來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他在談到勞動生產率的時候,不是在其中尋找剩餘價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尋找決定剩餘價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學派公開宣稱,勞動生產力是利潤(應讀做剩餘價值)產生的原因。這無論如何總比重商主義者前進了一步,因為重商主義者認為,產品的價格超過產品生產費用而形成的餘額是從交換中,從產品高於其價值的出售中產生的。不過對這個問題,李嘉圖學派也只是迴避,而沒有解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確的本能,懂得過於深入地研究剩餘價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可是在李嘉圖以後半個世紀,約翰‧史都華‧彌爾先生還在拙劣地重複那些最先把李嘉圖學說庸俗化的人的陳腐遁詞,鄭重其事地宣稱他比重商主義者高明,對此我們該說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