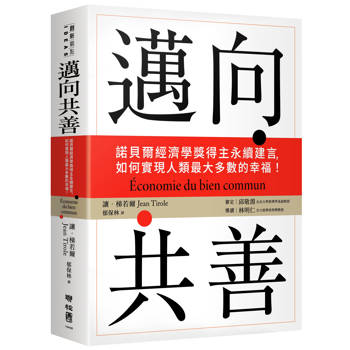第一章 你喜歡經濟學嗎?
除非是經濟學專業出身或從事相關職業,否則你或許對經濟學感到好奇(不然你也不會閱讀本書),但要說喜歡經濟學可能還為時過早。你或許覺得經濟討論晦澀難懂,甚至違反直覺。在這一章裡,我希望解釋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並描述一些認知偏差,因為有時候當我們面對經濟問題時,這些偏差會讓我們心生誤解。此外,我還將指出能夠促進對經濟學普及理解的幾條途徑。
雖然經濟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卻非專家們的專利。只要願意撇開表面現象向下探究,經濟學其實不難理解。一旦我們認清並跨越最初的障礙,經濟學將會變得非常有趣。
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
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一直在探討構成我們信念的推動力。許多認知偏差雖然對我們有幫助(這也許就是它們存在的原因),卻也同時妨礙我們。
本書將從頭到尾說明這些偏差,畢竟它們會左右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有所出入。
我們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們通常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而不是根據證據才相信。正如柏拉圖、亞當.斯密及十九世紀美國偉大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強調的,我們信念的形成和修正,都是為了堅定我們想要擁有的自我形象或周遭世界的形象。這些信念一旦匯聚在國家層級,便決定了經濟、社會、科學或地緣政治的政策。
我們不僅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而且還會經常刻意尋求這些偏差。我們根據自己的信念解釋事實、閱讀報紙、尋找與我們信念一致的人,因此無論這些信念是否正確,我們都固執不變。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卡漢(Dan Kahan)觀察到,面對人為因素造成氣候暖化的科學證據時,美國民主黨的選民更加堅定認為應該採取行動對抗氣候暖化;而許多共和黨人在面對同樣數據時,常堅持自己氣候暖化懷疑論的立場。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不是教育或智力問題─統計數據顯示,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共和黨人中,其拒絕面對現實的程度至少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共和黨人相當!因此,沒有人能自外於這種現象的影響。
世人渴望對未來感到安心,這點在理解經濟現象(以及更普遍的科學現象)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不願面對「對抗氣候變遷會很昂貴」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綠色成長」(croissance verte)這個概念在政治語言中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名稱暗示環境政策會是「百利而無一害」。但如果它真像暗示的那樣不花什麼成本,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全面普及呢?
同樣,我們一廂情願相信意外事故和疾病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我們自己或親人的身上(如此可能導致不良行為,例如開車時降低警覺以及對社會的看法。簡言之,我們所看到的、或想要看到的,可能與現實或忽視醫療預防。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無憂無慮的態度卻也有增進生活品質的好處。)同樣,我們不願正視公共債務或社會保障體系急遽膨脹可能對社會體系的長期穩定造成威脅,或者寧願相信「別人會來埋單」。
我們都夢想活在理想世界,在那裡,行為者不需要法律強制便會自發行善、清理汙染或者自行繳納稅款,即使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也能謹慎行事。這也是為什麼電影導演(不僅是好萊塢的)會安排符合我們期望的結局,因為這些美好的結局能使我們堅信自己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其中美德終將戰勝邪惡(如同社會學家梅爾文.勒納〔Melvin Lerner〕所描述之「相信世界是公正的」)。
然而,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義政黨都在利用這種不知節制的經濟幻想;而那些打破此一童話和太過天真信念的資訊,往往被視為負面,說得客氣些是引發焦慮,說得難聽則是支持全球氣候暖化理論的狂徒,是撙節政策的走狗或人類公敵。這也是經濟學常被戲稱為「陰鬱科學」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見與所未見:初步印象與啟發法
經濟學教學通常依賴於「理性選擇論」(théorie du choix rationnel),即假設經濟行為者(agent économique)的行為總是基於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不論個人是出於自私、無私、追求利潤還是尋求社會認可,或是其他動機,通常都認為他會試圖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這種假設有時過於武斷,因為個人並不總能掌握足夠資訊來做出最正確的選擇。同時,由於認知偏差的影響,個人在評估達成目標的方式時也可能出現錯誤。這些推理或感知上的偏差屢見不鮮。儘管如此,這些偏差並未否定「理性選擇論」做為標準選擇模式的價值(即個人應該做出以自身最大性的最佳行動。
我們採用的「啟發法」一詞,是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重視的概念。啟發法是指提供問題答案的一種簡化的推理形式。這些啟發法經常十分有用,能讓我們迅速做出決定(突然碰上老虎時,我們並不總有時間來評估最佳的回應方式⋯⋯),但也可能遭到誤導。情緒可以成為這些啟發法的動力,有時是可靠的依賴,但有時也很不明智。
讓我們以一個典型的啟發法為例:在面臨決策或單純在做評估時,我們記憶中會浮現一些情境。「電話總是在我們正忙碌或洗澡的時候響起」,這顯然是記憶對我們開的玩笑;我們比較容易記住那些因活動被打斷而感到懊惱的情況,而對於那些電話未造成任何干擾的情況,我們就不記得那麼清楚了。同樣,我們都害怕飛機失事和恐怖攻擊,只因媒體經常大篇幅報導,而我們卻忘記了,普通的車禍和「普通」的謀殺案實際上導致的死亡人數遠遠多於這些相對罕見的情況。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發生了20萬起謀殺案,其中只有50起是由美籍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然而,恐怖攻擊仍然深深印在所有人的腦海中。
康納曼和特沃斯基(Tversky)研究的主要貢獻,是指出這些啟發法經常使我們誤入歧途。這兩位心理學家舉了許多類似現象為例,其中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哈佛大學的醫學生在計算某些症狀惡化成癌症的機率時犯了嚴重的錯誤。這裡我們面對的是美國最優秀的學生。同樣,這又見一個例子,說明即使是非常聰明的頭腦和高水準的教育也未能糾正扭曲的信念。
在經濟學中,第一印象以及專注於最明顯的事物也會蒙蔽我們。我們只看到經濟政策的直接效果,這點容易理解,可是我們就止步於此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並未意識到市場運作中存在的一些內在現象,例如誘因利益為導向的選擇),而只是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選擇不一定總是符合理機制、替代效應或延遲效應等,以至於無法全面理解問題。然而,政策存在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可能輕易使一項善意的政策變得有害。
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但現在且讓我們先舉一個刻意引人深思的例子。之所以選擇這個例子,是因為它能立即顯示出哪種認知偏差會導致對公共決策效果的誤解。假設一個非政府組織從走私者手中沒收象牙,它可以選擇立即銷毀象牙,或祕密地將其重新投入市場。大多數讀者的第一反應會認為第二種做法應該徹底加以譴責。我也不例外,不過且讓我們仔細思考這個例子。
非政府組織除了可將銷售象牙的所得投入其崇高的志業(如增強偵測和調查能力、購買更多的車輛以遏止象牙的非法買賣),象牙銷售還會帶來一個直接的結果:壓低象牙的價格(如果銷售量少,價格下降不多,如果銷售量大,價格下降就較可觀)。走私者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都是理性的:他們會權衡其非法活動的金錢收益,以及被捕入獄或與執法部門交戰的風險;價格下降多多少少能阻止其中一些人獵殺更多的大象。
在這種情況下,非政府組織銷售象牙是否不道德?也許是,因為非政府組織身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組織,公開銷售象牙可能使買家覺得象牙貿易是正當的,從而降低購買象牙的內疚感。但至少在譴責該非政府組織的行為之前,我們應該三思。尤其是此舉並不妨礙公權力履行其固有的職責,亦即追捕偷獵者以及販賣象牙或犀牛角的人,同時可搭配宣導來改變人們的行為。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le protocole de Kyoto)有志在對抗全球暖化的道路上邁出關鍵一步,可是卻以失敗收場,而上述的虛構情境有助於理解其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我們來解釋一下。在環境保護的領域中,「轉移效應」(Les effets de report)在經濟學術語中稱為「洩漏問題」
(problème des fuites)。這是一種機制,即世界某一地區雖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可能對全球汙染問題沒有或只有很少的影響。例如,假設法國減少化石能源(如石油、煤炭)的消耗。這一努力固然值得稱許,而且專家也一致認定,全球必須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將溫度的升高限制在合理範圍內(1.5到2℃)。然而,當我們節省一噸煤或一桶汽油時,將會降低煤炭或石油的價格,進而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增加其消費量。
同樣,如果歐洲要求其投身國際競爭的企業為自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付費,那麼這些企業的高排放生產活動就會轉移到對排放要求較低的國家。如此一來,在一定程度上會全部或部分抵消歐洲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努力,且能產生的生態效果極其有限。任何對抗氣候暖化的嚴肅解決方案都必須著眼於全球。
在經濟問題上,即使出於善意的行為或意圖,如果執行不當或未考慮後果,最終仍可能導致負面結果。
「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
我們的同情心自然會傾向灌注於在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與我們接近的人。此一天生傾向乃源於演化的因素,使得我們同情社群中窮人的程度自然高於同情非洲飢餓孩童的程度,即使我們知道後者其實更需要幫助。一般來說,如果我們能識別受害者是誰,便容易產生感同身受的情愫。心理學家長期以來也在研究這種趨勢,亦即我們往往對可具體認知其身分的人比對無法辨識其身分的人更能付出關懷。這種「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雖是人之常情,也會影響公共政策。有句名言說道(一般認為是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e〕所言,但其出處仍有爭議):「死一個人是悲劇,但死一百萬人不過是統計數字。」例如,一張敘利亞三歲兒童艾蘭(Aylan)被人發現死在土耳其海灘上的悲慘照片,迫使我們正視一個自己本想忽視的現象。這張照片對歐洲人意識的衝擊,比之前成千上萬偷渡客在地中海溺水身亡的統計數據都更為強烈。艾蘭的照片對歐洲移民議題的影響,就像1972年越南戰爭中遭燒夷彈波及的小女孩潘氏金福(Kim Phúc)在路上裸奔的照片那樣,對越戰的影響不可小覷。一個可識別的受害者遠比成千上萬匿名的受害者更能讓我們深深記在腦海。同樣,在反對酒駕的宣導活動中,展示某個路人撞在擋風玻璃上的照片,要比僅僅公布每年受害者人數更加有效(就算後者能提供更豐富的資訊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也影響了我們的就業政策。媒體報導即將失業之無固定期限契約工(CDI)的抗爭,而他們的遭遇在一個很難再找到這類工作的國家裡顯得更加現實。我們看得到這些受害者真實的臉孔,卻看不到那些在失業期、待業補貼期或固定期限契約(CDD)之間掙扎、數目更多的人的面孔,因為他們都只是一個統計數據而已。然而,正如第九章將討論的,他們往往才是制度的受害者。這些制度包括為保護無固定期限契約工所創立的制度,結果使得企業傾向於提供不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靠公共資金補貼的契約,而不願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為什麼我們花費這麼多公共資金和社會保險費用(cotisations sociales),結果不僅削弱企業競爭力,從而影響就業,還犧牲了本可用於教育或醫療的錢,得到的成效如此糟糕?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關注的只是裁員計畫,卻忘記了那些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的人,而兩者實際上是同件事的一體兩面。
這裡經濟學和醫學的對比十分搶眼:醫學與「陰鬱科學」相反,它被公眾視為一門致力於人類福祉的專業(英語中的「caring profession」〔照護職業〕一詞用在這裡特別合適)。然而,經濟學與醫學的目標其實相似:經濟學家和腫瘤學家都會進行診斷,必要時根據自己的知識能力(必然未臻完美)提出最理想的療法;但如果不需治療,則同樣會據實以告。
這種印象上差異的原因很簡單。在醫學上,副作用的受害者與接受治療的人是同一群體(流行病學領域除外,例如抗生素的耐藥性或未能接種疫苗所導致的後果);因此,醫生只需恪遵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者往往與接受治療的人不同,這一點在勞動力市場的例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經濟學家必須考慮到那些不可見的受害者,因此有時會遭人指責,說他們對可見之受害者的痛苦無動於衷。
除非是經濟學專業出身或從事相關職業,否則你或許對經濟學感到好奇(不然你也不會閱讀本書),但要說喜歡經濟學可能還為時過早。你或許覺得經濟討論晦澀難懂,甚至違反直覺。在這一章裡,我希望解釋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並描述一些認知偏差,因為有時候當我們面對經濟問題時,這些偏差會讓我們心生誤解。此外,我還將指出能夠促進對經濟學普及理解的幾條途徑。
雖然經濟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卻非專家們的專利。只要願意撇開表面現象向下探究,經濟學其實不難理解。一旦我們認清並跨越最初的障礙,經濟學將會變得非常有趣。
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
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一直在探討構成我們信念的推動力。許多認知偏差雖然對我們有幫助(這也許就是它們存在的原因),卻也同時妨礙我們。
本書將從頭到尾說明這些偏差,畢竟它們會左右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有所出入。
我們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們通常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而不是根據證據才相信。正如柏拉圖、亞當.斯密及十九世紀美國偉大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強調的,我們信念的形成和修正,都是為了堅定我們想要擁有的自我形象或周遭世界的形象。這些信念一旦匯聚在國家層級,便決定了經濟、社會、科學或地緣政治的政策。
我們不僅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而且還會經常刻意尋求這些偏差。我們根據自己的信念解釋事實、閱讀報紙、尋找與我們信念一致的人,因此無論這些信念是否正確,我們都固執不變。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卡漢(Dan Kahan)觀察到,面對人為因素造成氣候暖化的科學證據時,美國民主黨的選民更加堅定認為應該採取行動對抗氣候暖化;而許多共和黨人在面對同樣數據時,常堅持自己氣候暖化懷疑論的立場。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不是教育或智力問題─統計數據顯示,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共和黨人中,其拒絕面對現實的程度至少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共和黨人相當!因此,沒有人能自外於這種現象的影響。
世人渴望對未來感到安心,這點在理解經濟現象(以及更普遍的科學現象)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不願面對「對抗氣候變遷會很昂貴」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綠色成長」(croissance verte)這個概念在政治語言中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名稱暗示環境政策會是「百利而無一害」。但如果它真像暗示的那樣不花什麼成本,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全面普及呢?
同樣,我們一廂情願相信意外事故和疾病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我們自己或親人的身上(如此可能導致不良行為,例如開車時降低警覺以及對社會的看法。簡言之,我們所看到的、或想要看到的,可能與現實或忽視醫療預防。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無憂無慮的態度卻也有增進生活品質的好處。)同樣,我們不願正視公共債務或社會保障體系急遽膨脹可能對社會體系的長期穩定造成威脅,或者寧願相信「別人會來埋單」。
我們都夢想活在理想世界,在那裡,行為者不需要法律強制便會自發行善、清理汙染或者自行繳納稅款,即使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也能謹慎行事。這也是為什麼電影導演(不僅是好萊塢的)會安排符合我們期望的結局,因為這些美好的結局能使我們堅信自己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其中美德終將戰勝邪惡(如同社會學家梅爾文.勒納〔Melvin Lerner〕所描述之「相信世界是公正的」)。
然而,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義政黨都在利用這種不知節制的經濟幻想;而那些打破此一童話和太過天真信念的資訊,往往被視為負面,說得客氣些是引發焦慮,說得難聽則是支持全球氣候暖化理論的狂徒,是撙節政策的走狗或人類公敵。這也是經濟學常被戲稱為「陰鬱科學」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見與所未見:初步印象與啟發法
經濟學教學通常依賴於「理性選擇論」(théorie du choix rationnel),即假設經濟行為者(agent économique)的行為總是基於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不論個人是出於自私、無私、追求利潤還是尋求社會認可,或是其他動機,通常都認為他會試圖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這種假設有時過於武斷,因為個人並不總能掌握足夠資訊來做出最正確的選擇。同時,由於認知偏差的影響,個人在評估達成目標的方式時也可能出現錯誤。這些推理或感知上的偏差屢見不鮮。儘管如此,這些偏差並未否定「理性選擇論」做為標準選擇模式的價值(即個人應該做出以自身最大性的最佳行動。
我們採用的「啟發法」一詞,是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重視的概念。啟發法是指提供問題答案的一種簡化的推理形式。這些啟發法經常十分有用,能讓我們迅速做出決定(突然碰上老虎時,我們並不總有時間來評估最佳的回應方式⋯⋯),但也可能遭到誤導。情緒可以成為這些啟發法的動力,有時是可靠的依賴,但有時也很不明智。
讓我們以一個典型的啟發法為例:在面臨決策或單純在做評估時,我們記憶中會浮現一些情境。「電話總是在我們正忙碌或洗澡的時候響起」,這顯然是記憶對我們開的玩笑;我們比較容易記住那些因活動被打斷而感到懊惱的情況,而對於那些電話未造成任何干擾的情況,我們就不記得那麼清楚了。同樣,我們都害怕飛機失事和恐怖攻擊,只因媒體經常大篇幅報導,而我們卻忘記了,普通的車禍和「普通」的謀殺案實際上導致的死亡人數遠遠多於這些相對罕見的情況。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發生了20萬起謀殺案,其中只有50起是由美籍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然而,恐怖攻擊仍然深深印在所有人的腦海中。
康納曼和特沃斯基(Tversky)研究的主要貢獻,是指出這些啟發法經常使我們誤入歧途。這兩位心理學家舉了許多類似現象為例,其中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哈佛大學的醫學生在計算某些症狀惡化成癌症的機率時犯了嚴重的錯誤。這裡我們面對的是美國最優秀的學生。同樣,這又見一個例子,說明即使是非常聰明的頭腦和高水準的教育也未能糾正扭曲的信念。
在經濟學中,第一印象以及專注於最明顯的事物也會蒙蔽我們。我們只看到經濟政策的直接效果,這點容易理解,可是我們就止步於此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並未意識到市場運作中存在的一些內在現象,例如誘因利益為導向的選擇),而只是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選擇不一定總是符合理機制、替代效應或延遲效應等,以至於無法全面理解問題。然而,政策存在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可能輕易使一項善意的政策變得有害。
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但現在且讓我們先舉一個刻意引人深思的例子。之所以選擇這個例子,是因為它能立即顯示出哪種認知偏差會導致對公共決策效果的誤解。假設一個非政府組織從走私者手中沒收象牙,它可以選擇立即銷毀象牙,或祕密地將其重新投入市場。大多數讀者的第一反應會認為第二種做法應該徹底加以譴責。我也不例外,不過且讓我們仔細思考這個例子。
非政府組織除了可將銷售象牙的所得投入其崇高的志業(如增強偵測和調查能力、購買更多的車輛以遏止象牙的非法買賣),象牙銷售還會帶來一個直接的結果:壓低象牙的價格(如果銷售量少,價格下降不多,如果銷售量大,價格下降就較可觀)。走私者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都是理性的:他們會權衡其非法活動的金錢收益,以及被捕入獄或與執法部門交戰的風險;價格下降多多少少能阻止其中一些人獵殺更多的大象。
在這種情況下,非政府組織銷售象牙是否不道德?也許是,因為非政府組織身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組織,公開銷售象牙可能使買家覺得象牙貿易是正當的,從而降低購買象牙的內疚感。但至少在譴責該非政府組織的行為之前,我們應該三思。尤其是此舉並不妨礙公權力履行其固有的職責,亦即追捕偷獵者以及販賣象牙或犀牛角的人,同時可搭配宣導來改變人們的行為。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le protocole de Kyoto)有志在對抗全球暖化的道路上邁出關鍵一步,可是卻以失敗收場,而上述的虛構情境有助於理解其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我們來解釋一下。在環境保護的領域中,「轉移效應」(Les effets de report)在經濟學術語中稱為「洩漏問題」
(problème des fuites)。這是一種機制,即世界某一地區雖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可能對全球汙染問題沒有或只有很少的影響。例如,假設法國減少化石能源(如石油、煤炭)的消耗。這一努力固然值得稱許,而且專家也一致認定,全球必須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將溫度的升高限制在合理範圍內(1.5到2℃)。然而,當我們節省一噸煤或一桶汽油時,將會降低煤炭或石油的價格,進而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增加其消費量。
同樣,如果歐洲要求其投身國際競爭的企業為自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付費,那麼這些企業的高排放生產活動就會轉移到對排放要求較低的國家。如此一來,在一定程度上會全部或部分抵消歐洲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努力,且能產生的生態效果極其有限。任何對抗氣候暖化的嚴肅解決方案都必須著眼於全球。
在經濟問題上,即使出於善意的行為或意圖,如果執行不當或未考慮後果,最終仍可能導致負面結果。
「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
我們的同情心自然會傾向灌注於在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與我們接近的人。此一天生傾向乃源於演化的因素,使得我們同情社群中窮人的程度自然高於同情非洲飢餓孩童的程度,即使我們知道後者其實更需要幫助。一般來說,如果我們能識別受害者是誰,便容易產生感同身受的情愫。心理學家長期以來也在研究這種趨勢,亦即我們往往對可具體認知其身分的人比對無法辨識其身分的人更能付出關懷。這種「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雖是人之常情,也會影響公共政策。有句名言說道(一般認為是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e〕所言,但其出處仍有爭議):「死一個人是悲劇,但死一百萬人不過是統計數字。」例如,一張敘利亞三歲兒童艾蘭(Aylan)被人發現死在土耳其海灘上的悲慘照片,迫使我們正視一個自己本想忽視的現象。這張照片對歐洲人意識的衝擊,比之前成千上萬偷渡客在地中海溺水身亡的統計數據都更為強烈。艾蘭的照片對歐洲移民議題的影響,就像1972年越南戰爭中遭燒夷彈波及的小女孩潘氏金福(Kim Phúc)在路上裸奔的照片那樣,對越戰的影響不可小覷。一個可識別的受害者遠比成千上萬匿名的受害者更能讓我們深深記在腦海。同樣,在反對酒駕的宣導活動中,展示某個路人撞在擋風玻璃上的照片,要比僅僅公布每年受害者人數更加有效(就算後者能提供更豐富的資訊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也影響了我們的就業政策。媒體報導即將失業之無固定期限契約工(CDI)的抗爭,而他們的遭遇在一個很難再找到這類工作的國家裡顯得更加現實。我們看得到這些受害者真實的臉孔,卻看不到那些在失業期、待業補貼期或固定期限契約(CDD)之間掙扎、數目更多的人的面孔,因為他們都只是一個統計數據而已。然而,正如第九章將討論的,他們往往才是制度的受害者。這些制度包括為保護無固定期限契約工所創立的制度,結果使得企業傾向於提供不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靠公共資金補貼的契約,而不願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為什麼我們花費這麼多公共資金和社會保險費用(cotisations sociales),結果不僅削弱企業競爭力,從而影響就業,還犧牲了本可用於教育或醫療的錢,得到的成效如此糟糕?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關注的只是裁員計畫,卻忘記了那些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的人,而兩者實際上是同件事的一體兩面。
這裡經濟學和醫學的對比十分搶眼:醫學與「陰鬱科學」相反,它被公眾視為一門致力於人類福祉的專業(英語中的「caring profession」〔照護職業〕一詞用在這裡特別合適)。然而,經濟學與醫學的目標其實相似:經濟學家和腫瘤學家都會進行診斷,必要時根據自己的知識能力(必然未臻完美)提出最理想的療法;但如果不需治療,則同樣會據實以告。
這種印象上差異的原因很簡單。在醫學上,副作用的受害者與接受治療的人是同一群體(流行病學領域除外,例如抗生素的耐藥性或未能接種疫苗所導致的後果);因此,醫生只需恪遵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者往往與接受治療的人不同,這一點在勞動力市場的例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經濟學家必須考慮到那些不可見的受害者,因此有時會遭人指責,說他們對可見之受害者的痛苦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