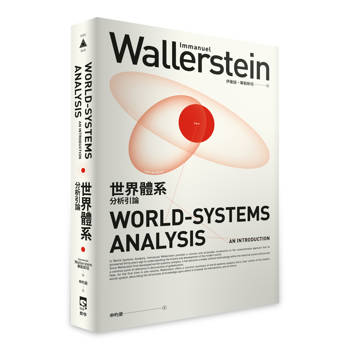第五章 危機中的現代世界體系:分歧、混沌、選項
因此,生產的三大成本——報酬、生產投入、稅金——在過去五百年來都穩定增加,在過去五十年來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即便有效需求增加,售價卻仍無法隨成本增加而提高。畢竟,生產者數量也在逐漸增加,而這便導致賣家更難維持寡佔的局面。這便是所謂的利潤擠壓(squeeze on profits)。值得注意的是,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生產者不斷想顛覆這種處境。但若要理解為何他們成功的可能有限,就必須回頭來看一九六八年的文化衝擊。
在整個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中,最大規模的生產結構擴張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世界經濟。我們先前談及的所有結構性趨勢——報酬成本、生產投入成本、稅金——也在此時大幅提高。與此同時,我們先前談及的反體系運動也有大幅進步,逐漸實現其眼下的目標——在國家結構中掌權。反體系運動在世上各地似乎都開始成就了兩階段計畫中的第一階段。從中歐到東亞(從易北河到鴨綠江)的大片土地,皆由共產黨治理。而在泛歐洲世界(西歐、北美、澳大拉西亞)裡,社會民主黨(或有相同價值的政黨)也開始掌權,或至少開始改變權力結構。在亞洲與非洲的其他地方,民族解放運動也漸漸掌權。而在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運動也掌控了局勢。
樂觀主義因而定義了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幾年。經濟有明亮的未來,而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也看似達成了其目標。而越南這個努力爭取獨立的小國家似乎也讓美國這個霸權不敢為所欲為。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現代世界體系最為光明的時刻。這種情感不但令人振奮,也能穩定人心。
然而,就在此時,有許多人開始對掌權後的群眾運動感到失望。群眾運動實際上離兩階段的第二步——改變世界——越來越遠,似乎難以實現。即便世界體系整體經濟已然增長,但核心與邊陲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而雖然反體系運動也已然掌權,但動員期間群眾參與的熱情似乎也在掌權後便消逝殆盡。此時出現的是新的特權階層,老百姓現在被要求不要對所謂「代表」他們的政府提出好戰的要求。當未來成為當下之際,許多先前運動的好戰參與者開始躊躇不定,最後甚至偏離原先的軌道。
導致一九六八年發生世界革命的,是長久以來對世界體系運作的不滿再加上對反體系運動改變世界的能力的失望。一九六八年的多場大震撼包含兩個在世界各地、不論在地脈絡如何皆不斷重複的主題。其一是拒絕美國的霸權以及對蘇聯的不滿——蘇聯雖然是美國的敵人,但實際上卻與美國共謀維持世界秩序。第二是傳統反體系運動掌權之後並無兌現其承諾。兩者的結合在世界各地不斷重複,最後構築出一場文化地震。世界各處的起義宛如鳳凰一般,雖猛烈卻沒有掌握權力,或掌權期間維持不久。但這些運動賦予先前種種不滿正當性並強化了這些不滿——現在,眾人對舊的反體系運動與其所強化的國家結構感到更加失望。長期演變的希望現在已轉變為恐懼:眾人開始擔心世界體系也許不會再有變化。
世界各地的情感轉變不僅沒有讓現況繼續維持下去,反倒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底層獲得政治支持與文化資源。被壓迫的人不再肯定歷史真的是站在自己這邊,因而也無法再滿足於跛腳的改革。他們不認為自己的孩子與孫侄輩會看見改革的成果,「良善未來」的號召也不再能延宕當下的不滿。簡言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生產者失去了一直以來隱藏在體系中的主要穩定劑——被壓迫者的樂觀。而這發生的時機再糟糕不過,因為,利潤擠壓問題也在此時浮上檯面,成為資本家不得不重視的難題。
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震撼鬆動了打從一八四八年世界革命以來便宰制世界體系的自由主義核心陣營,左右翼都不再是自由主義中間路線的代理人,且開始主張或重新主張其更為基進的價值。世界體系已然進入過渡期,而左右雙方都下定決心要把握這個混沌所帶來的機會,藉此確保其價值能在由此危機而生的新體系中佔上風。
一九六八年世界革命產生的立即效應似乎賦予許多左翼價值正當性,在種族與性這兩個領域尤其如此。種族主義是貫穿現代世界體系存在的特色之一。當然,其合法性已遭受近兩個世紀的質疑。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之後,才開始有大量群眾反對種族主義,而反種族主義倡議也開始成為世界政治場景中的核心現象。這運動有別於先前的運動,其領導者是被壓迫團體本身,而非主流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而此運動採取的型態既是在世界各地積極採取戰鬥姿態的「少數」身份運動,也是重構知識世界的嘗試,努力把長期慢性的種族主義造成的種種問題推進智識論述的核心。
在一九六八年世界革命中與這些種族主義辯論一同處在核心地位的,還有性論述。無論我們談論的是跟性別或性傾向相關的政策,又或者是跨性別身份,都難以忽視一九六八年的衝擊。是六八年的革命讓先前半世紀緩慢轉變的性道德觀(sexual mores)浮上檯面,並在世界社會場景中爆炸,接著對法律、慣習實踐、宗教與智識論述產生極大的影響。
傳統反體系運動主要強調的是國家權力與經濟結構。然而,這兩個議題卻在六八年的戰鬥修辭中或多或少退場了,因為原先的核心地位已讓給了種族與性。這對世界各地的右派造成了非常真實的衝擊:對他們而言,比起社會文化議題,地緣政治與經濟議題要來得簡單多了。因為,雖然中間路線的自由主義者敵視所有掏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基礎政經制度的嘗試,但卻或多或少(但也許比較沒有這麼強硬)支持一九六八年與其後的社會文化轉向。因此,一九六八年之後右派的反應相當分裂: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想要復辟秩序並解決逐漸浮上檯面的利潤擠壓難題,另一方面,他們卻也面對一場基礎較不明確但卻更為兇狠的文化反革命(cultural counterrevolution)。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把兩類議題分開來談,因此也該談論兩組不同的策略結盟。
因此,生產的三大成本——報酬、生產投入、稅金——在過去五百年來都穩定增加,在過去五十年來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即便有效需求增加,售價卻仍無法隨成本增加而提高。畢竟,生產者數量也在逐漸增加,而這便導致賣家更難維持寡佔的局面。這便是所謂的利潤擠壓(squeeze on profits)。值得注意的是,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生產者不斷想顛覆這種處境。但若要理解為何他們成功的可能有限,就必須回頭來看一九六八年的文化衝擊。
在整個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中,最大規模的生產結構擴張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世界經濟。我們先前談及的所有結構性趨勢——報酬成本、生產投入成本、稅金——也在此時大幅提高。與此同時,我們先前談及的反體系運動也有大幅進步,逐漸實現其眼下的目標——在國家結構中掌權。反體系運動在世上各地似乎都開始成就了兩階段計畫中的第一階段。從中歐到東亞(從易北河到鴨綠江)的大片土地,皆由共產黨治理。而在泛歐洲世界(西歐、北美、澳大拉西亞)裡,社會民主黨(或有相同價值的政黨)也開始掌權,或至少開始改變權力結構。在亞洲與非洲的其他地方,民族解放運動也漸漸掌權。而在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運動也掌控了局勢。
樂觀主義因而定義了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幾年。經濟有明亮的未來,而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也看似達成了其目標。而越南這個努力爭取獨立的小國家似乎也讓美國這個霸權不敢為所欲為。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現代世界體系最為光明的時刻。這種情感不但令人振奮,也能穩定人心。
然而,就在此時,有許多人開始對掌權後的群眾運動感到失望。群眾運動實際上離兩階段的第二步——改變世界——越來越遠,似乎難以實現。即便世界體系整體經濟已然增長,但核心與邊陲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而雖然反體系運動也已然掌權,但動員期間群眾參與的熱情似乎也在掌權後便消逝殆盡。此時出現的是新的特權階層,老百姓現在被要求不要對所謂「代表」他們的政府提出好戰的要求。當未來成為當下之際,許多先前運動的好戰參與者開始躊躇不定,最後甚至偏離原先的軌道。
導致一九六八年發生世界革命的,是長久以來對世界體系運作的不滿再加上對反體系運動改變世界的能力的失望。一九六八年的多場大震撼包含兩個在世界各地、不論在地脈絡如何皆不斷重複的主題。其一是拒絕美國的霸權以及對蘇聯的不滿——蘇聯雖然是美國的敵人,但實際上卻與美國共謀維持世界秩序。第二是傳統反體系運動掌權之後並無兌現其承諾。兩者的結合在世界各地不斷重複,最後構築出一場文化地震。世界各處的起義宛如鳳凰一般,雖猛烈卻沒有掌握權力,或掌權期間維持不久。但這些運動賦予先前種種不滿正當性並強化了這些不滿——現在,眾人對舊的反體系運動與其所強化的國家結構感到更加失望。長期演變的希望現在已轉變為恐懼:眾人開始擔心世界體系也許不會再有變化。
世界各地的情感轉變不僅沒有讓現況繼續維持下去,反倒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底層獲得政治支持與文化資源。被壓迫的人不再肯定歷史真的是站在自己這邊,因而也無法再滿足於跛腳的改革。他們不認為自己的孩子與孫侄輩會看見改革的成果,「良善未來」的號召也不再能延宕當下的不滿。簡言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生產者失去了一直以來隱藏在體系中的主要穩定劑——被壓迫者的樂觀。而這發生的時機再糟糕不過,因為,利潤擠壓問題也在此時浮上檯面,成為資本家不得不重視的難題。
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震撼鬆動了打從一八四八年世界革命以來便宰制世界體系的自由主義核心陣營,左右翼都不再是自由主義中間路線的代理人,且開始主張或重新主張其更為基進的價值。世界體系已然進入過渡期,而左右雙方都下定決心要把握這個混沌所帶來的機會,藉此確保其價值能在由此危機而生的新體系中佔上風。
一九六八年世界革命產生的立即效應似乎賦予許多左翼價值正當性,在種族與性這兩個領域尤其如此。種族主義是貫穿現代世界體系存在的特色之一。當然,其合法性已遭受近兩個世紀的質疑。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之後,才開始有大量群眾反對種族主義,而反種族主義倡議也開始成為世界政治場景中的核心現象。這運動有別於先前的運動,其領導者是被壓迫團體本身,而非主流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而此運動採取的型態既是在世界各地積極採取戰鬥姿態的「少數」身份運動,也是重構知識世界的嘗試,努力把長期慢性的種族主義造成的種種問題推進智識論述的核心。
在一九六八年世界革命中與這些種族主義辯論一同處在核心地位的,還有性論述。無論我們談論的是跟性別或性傾向相關的政策,又或者是跨性別身份,都難以忽視一九六八年的衝擊。是六八年的革命讓先前半世紀緩慢轉變的性道德觀(sexual mores)浮上檯面,並在世界社會場景中爆炸,接著對法律、慣習實踐、宗教與智識論述產生極大的影響。
傳統反體系運動主要強調的是國家權力與經濟結構。然而,這兩個議題卻在六八年的戰鬥修辭中或多或少退場了,因為原先的核心地位已讓給了種族與性。這對世界各地的右派造成了非常真實的衝擊:對他們而言,比起社會文化議題,地緣政治與經濟議題要來得簡單多了。因為,雖然中間路線的自由主義者敵視所有掏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基礎政經制度的嘗試,但卻或多或少(但也許比較沒有這麼強硬)支持一九六八年與其後的社會文化轉向。因此,一九六八年之後右派的反應相當分裂: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想要復辟秩序並解決逐漸浮上檯面的利潤擠壓難題,另一方面,他們卻也面對一場基礎較不明確但卻更為兇狠的文化反革命(cultural counterrevolution)。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把兩類議題分開來談,因此也該談論兩組不同的策略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