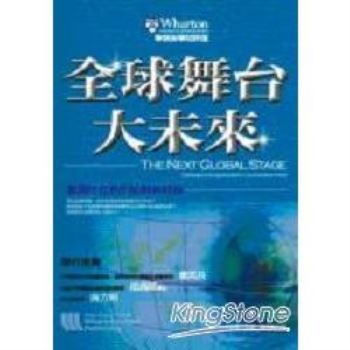情節
我們處於真正互連、互賴的世界,由全球化經濟結合為一。過去的工商業和經濟猶如在個別劇院,針對不同觀眾表演(或許都出於同一作家的作品)。演員各具特色,其表演方式常受到每家劇院的傳統所影響。如今這齣戲是在一個其大無比的全球舞台上搬演。演員有時會為了爭取觀眾的注意力而彼此競爭,不過在舞台上可以來去自如,不會再被過時的道具阻擋。全球舞台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中。《全球舞台大未來》提供腳本,協助讀者在不斷變化的情節發展中,走出自己的路。
多虧資訊技術的進步,我們才能有今日的局面。資料沿著光纖纜線或透過衛星傳輸,自由地傳遞世界各地。資訊挑戰各種障礙,無論是物質或政治壁壘。為簡化技術應用而建立的平台,也促進資訊流通。威力強大的搜尋引擎如Google,使我們能在錯綜複雜的數位迷宮裡,找到並結合不相干的資訊。在類比時代,各自獨立的片斷資訊必須由人工連結,從中找出含意。現在則是無腦機器人透過無數相互連結的電腦,彈指間就能把資訊組合完成,並分析其意義。二○○五年一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八十億網頁的資訊任君取用,從中歸納出某種觀點和知識只需剎那。以前要智者或老經驗的記者,才能發掘不同資訊間的關聯,如今任何外行人只要把幾個字輸入搜尋引擎,就能找出許多看似無關事件之間的關聯。
以往化學家得利用《化學摘要》(Chemical Abstract)尋找所需文章,因為這份權威性刊物蒐羅了全世界化學家所有的著作。買賣股票者則利用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德勵財富資訊(Telerate)、日經(Nikkei)或其他國具影響力的來源,去尋找重要資訊。現在Google及類似搜尋引擎則是常用的入口網站。很可能你要找的資訊,至少是該資訊的線索,大部分均以數位形式存在。因此,雖然未在新的全球劇院舉行正式開幕儀式,人類卻早已進入無疆界的數位世界。
全球劇院具有很多改變世界的含意,其中有些在中國、芬蘭和愛爾蘭等國家已逐一實現。全球化經濟不理睬障礙,但障礙不移除就會造成扭曲。另一個引起摩擦的源頭是傳統的中央集權式國家。這種國家的條件不足,無法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反倒是轄下的各區域常成為吸引和維持繁榮的最佳單位。區域國家是在全球舞台上追求繁榮的理想單位,而區域國家非正式地結合於歐盟(European Union)這類大組織下,將可促進自由貿易、法規統一及市場整合,使它如虎添翼。
資料傳輸技術革命,已對貨幣和資金的流動產生影響。金錢可以毫無限制地流向最高獲利區。老式的企業價值觀因影響力漸增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而倍受挑戰。許多傳統經濟學建立於國家政策基礎上,因此對外界影響力會強烈左右本國經濟的國家而言,老舊的經濟理論已不適用。
請看阿根廷在過去十年裡兩次截然不同的經濟危機。第一次危機發生時,阿根廷全國和許多局外人都陷入恐慌;第二次卻沒有。第二次危機發生時,與阿根廷相關的人,不分國內外,都不再依賴該國貨幣新披索(new peso),因為大家多半把資產換成全球儲蓄及清算的標準:美元。
若全球化經濟如我所認為的,其動力來自技術,那知識就是全球化經濟的貴金屬。例如,印度的優勢本質上歸功於理工科博士人才眾多。新興國家可透過教育推動經濟成長。任何地方不再需要礦藏豐富、人口眾多或軍力強大,才能成為全球化經濟舞台上的主角。經由海外投資就有可能獲得財富和技術知識。外資不再被視為威脅,而應看作是無窮機會的泉源。
全球化經濟固然代表機會,但政府、企業和個人也將面臨挑戰。唯有採取彈性、務實的作法才能通過考驗。 導論
我們心中的構想不會一開始就以完美形式出現,構想是經驗、觀察、期望和靈感的匯集,當它在耀眼的光芒下站上舞台,我們難免有所遲疑,不確定台下觀眾會有什麼反應。這些構想不斷演變發展,並時時留意著外在變動的反應和環境。
《全球舞台大未來》(The Next Global Stage)一書的架構在我腦海裡已演練了二十多年。在我前幾本著作《無國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及《看不見的新大陸》(The Invisible Continent)中,已討論過許多我仍在探索的課題。正如方才所說,構想不會以完美狀態現身。
本書的源起受到兩股力量所推動。
一是見證了外在環境的改變。過去二十年來整個世界變化極大。目前適用的政治、經濟、社會、企業和個人規範,與二十年前的規範幾乎沒有關聯。「時代不同,需要的腳本也不同。」
問題出在我們老是讀同一本陳腐的腳本。全球化經濟擴張帶來的是對商業世界更一致的看法:商業世界自成一體,不受限於國界障礙。這樣的觀點不是來自教科書或學術文章等傳統認知途徑,而是直接得自實際探觸世界,經常遊歷各國,並與各地工商界人士打成一片。然而弔詭的是,這兩者得出的心得卻看似一樣。各地的意見和看法相近,大家認為重要的政治及經濟領域,其發展也大同小異。看法相同,解決之道也就類似。然而,共通的世界觀並不會產生全球舞台所需的非傳統回應及解決之道。
過去三十年藉由擔任顧問、演講和度假的機會,我的足跡遍及六十餘國。例如美國我去過四百次以上;韓國和台灣各兩百次;馬來西亞一百次。最近平均每年到中國六次並且在大連開了一家公司,還製作了十八小時的電視節目,試著解說當地的工商業和政治現況。另外我也在澳洲黃金海岸和加拿大惠斯勒(Whistler)停留不少時間。當然,身為日本公民的我住在東京,更是時常走訪日本各地。
讀者看得出來,我認為沒有比親赴當地考察,參觀公司、與企業負責人、員工和消費者交流更重要的事。這是體會各地實情的方法。我走訪各地時,有時會帶著四十至六十位日本企業高階主管,讓他們第一手觀察吸引全世界資金流入的地區。我們曾到愛爾蘭去考察跨國企業流程委外正如何重塑該國經濟,帶他們看看在全球舞台上欣欣向榮的義大利小城鎮。我們也造訪過北歐國家,了解它們為什麼能成為世上競爭力最強的國家;又到東歐,看那些國家在已成長為二十五個會員國的歐盟中地位如何。這個團體也已訪問過中國和美國兩次,印度、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澳洲各一次。
跟我同行的高階主管都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即使在這網際網路和全球有線新聞發達的時代,四處走走,多聽多看,問些問題,仍是最佳的學習方法。親自體驗世界現況會改變觀感。親眼目睹全球舞台後,主管們會開始用不同的眼光去讀報紙、看電視。他們的視野逐漸變得開闊,對自己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處之泰然。這不容易做到;這需要新技巧。 本書的第二隻推手,是過去二十年來我所直接接觸的一些全球化經濟先驅。
最先贊同真正全球化經濟概念的企業領導人之一是史克美占(Smith Kline Beecham)公司前執行長溫特(Henry Wendt)。他認為跨國策略聯盟有可能成為美國製藥業的救星,也體認到國際性策略聯盟將來就算不是絕對的關鍵,仍具有相當重要性。
溫特發現全球有三大主導市場:美國、日本和遠東,以及歐洲。無論自詡為多麼強盛、多麼優勢的企業,沒有「一家」企業能夠有效單獨經營和服務這三個市場,奢望包辦一個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一萬美元、人口達七億的市場。
一般公司傳統的行銷策略是循序漸進打入每個市場,無論市場是一個區域或是國家。只有當公司本身和產品在A市場站穩後,然後才會再轉向B市場。但溫特主張,如果產品夠好,公司就須採取灑水器模式,「同時」進入各個市場。跨國策略聯盟便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做法之一。
於是溫特與美占公司談判,美占在研發方面享有高聲譽,在歐洲也佔有相當大的市場,最後談判結果是兩家公司合併。他不但選擇合併的路,還特別把企業總部由匹茲堡遷至倫敦,此舉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溫特有遠見與先見之明,他的跨國策略聯盟概念確實極具開創性。當時跨國聯盟和合併不易達成,因為每家大公司都一頭栽進自己的國內市場。這些公司也都在其本國政府的管控之下,與政府的關係密切並十分認同政府。放棄本國市場是非常困難的,看看最近有關委外的呼聲就知道。一方面可能政府反對(就如德、法企業談判合併時常見的現象);一方面媒體評論家像冰凍沼澤裡的遠古長毛象或恐龍,為了生存,把這種行動批評為不愛國或沒有原則。不論什麼合併案,他們都要評斷出「誰輸誰贏」,如戴姆勒克萊斯勒(Daimler Chrysler)的例子。
在國界逐漸消失的世界裡,跨國策略聯盟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唯一出路。以製藥業為例,藥品愈來愈走向標準化。一些重要、有利潤空間的組合成分或配方已逐漸失去獨特性,隨之而來的是天文數字般飛漲的研發費用。新頒布的規定更增加成本和延誤時程。然而投入研發的金額與產品推出後的成績,只有間接的關聯。公司或許可以成立設備頂尖的實驗室、匯集經驗豐富和年輕出色的人才組成最佳研發團隊,但這些努力從不保證一定成功。決定努力的方向對不對以及能不能有所突破,還是有些機運的因素在內。
企業的難處在於,當研發成功,超級好藥誕生,公司卻可能在世界各重要市場缺乏足夠銷售人力。銷售收入減少於是能攤還掉的研發經費就少;而另一方面,公司在無好藥可賣時,也可能得花高薪養很多業務人員。這就是製藥類產業的難題,固定成本高,需要相當的營收規模來分擔這些成本。正因如此,企業需要策略聯盟,有時還得再向前一步採取完全跨國界的購併做法。一九八○年代中期這類例子很少,如今我們幾乎天天可以看到跨國聯盟及購併,發生在金融、航空、零售、發電、汽車、消費與商用電子、機械,以及半導體等產業。 規模及資本額確實扮演了要角。中等藥廠可能在研發上投入十億美元,卻一無所獲,大公司則可能有能力投入三十億美元從事研發。大公司禁得起較多失敗,仍然不致虧損。跨國聯盟能帶給藥廠更多研發測試空間的餘裕,不過這只有把眼光放遠,看到國外市場才辦得到。現在跨國策略聯盟已非新鮮事,溫特開路先鋒的角色值得推崇。
另一位全球化經濟的早期推手是前花旗銀行(Citibank)董事長瑞斯頓(Walters Wriston)。他認為全球化勢在必行,不是基於商管理論,而是基於技術突破他才這麼主張。他曾預言,銀行之間的競爭不會再以金融服務定高下,而是看誰能在技術上領先。事實上,能夠更快做出決定的公司將是贏家,甚至往往得快到比一奈米秒還要短。
瑞斯頓知道明日的銀行業以及全球化經濟會是什麼樣的形式。基本上那是個無國界的世界;會隨著瞬間做出的決定而變動,且這些決定有時不出自於人。技術將是銀行業成功的關鍵,所以花旗銀行的掌舵者一定要精於技術。可惜瑞斯頓的遠見使他成為非主流。二十年前,大多數高階銀行家均屬傳統派,他們認為成功的關鍵不在技術,而在於企業與政府組織之間建立的信任及保密關係。技術固然很好,可是那是後生晚輩的事,銀行家不必多管。
一九八四年瑞斯頓欽點的接班人瑞德(John Reid)就不是傳統美國東岸金融圈出身。瑞德是技術專家,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MIT)。他一直在花旗銀行負責自動櫃員機(ATM)應用和其他電子金融專案。瑞德被任命為董事長時,在公司裡幾乎默默無聞。有人聽說他獲任命的消息時,甚至還問:「是瑞什麼要當董事長?」
瑞斯頓對此決定的辯解是,要教高階銀行家技術很難,可是讓技術專家學會經營銀行相對較容易。至於關係,久而久之自然會建立起來。在瑞德主持之下,花旗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銀行,而這段期間,他也機敏的領導花旗度過拉丁美洲金融危機。
還有一位超越時代的企業領導人,就是新力(Sony)創辦人盛田昭夫。他創辦的公司原名東京通信工業(Tokyo Tsushin Kogyo)簡稱東通工(Totsuko, TTK)。這種名稱即使用簡稱,對西方市場來說都太難了。所以盛田想出Sony四個字母,代表他生產電晶體收音機的音質。在他眼中,全世界是一個大市場,沒有什麼分界。盛田見識遠大,但絕不是個自大狂。他給企業著名的忠告是:「從全球角度思考,從地方角度行動。」日本雜誌《日經商業》(Nikkei Business)率先把這種主張稱為「glocal」,由此出現新名詞「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這三位有遠見的大師對當年逐漸出現的全球化經濟,在許多方面與筆者所見略同,見拙作《三邊勢力》(Triad Power)及《無國界的世界》。自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有幸與他們三位和許多人交換看法。不過在論及區域國家(region-state)的重要性時,總感覺難以掌握,無法定論。直等到中國自一九九八年後的發展,我腦海中在這個議題上才產生實際可行的觀點。 舞台指南
從前述思想歷程出發,我在本書中,首先闡述世界現狀及人們如何加以解讀。在第一篇「舞台」中,第一章的「世界行」談到若干爆炸性成長地區,並指出全球化經濟的一些特點。第二章「開幕之夜」回顧當今新世紀的源起。本篇的尾聲第三章「經濟學的終結」則檢討傳統經濟學及經濟學家未能理解全球化經濟的缺失。
第二篇「舞台指南」,探討了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趨勢。第四章「主導大局」,一開始是介紹民族國家的發展,以及我所謂區域國家的動能,全球化經濟裡最有用、最具威力的經濟組織方式即區域國家。接著第五章「進步平台」說明平台觀念,例如使用英文、Windows作業系統、品牌、美元,做為全球溝通、了解及商務工具。最後談因應新興全球化經濟,經營企業有哪些地方必須改革。其中有些涉及商業制度和流程(第六章『海闊天空』),有些則是產品、人員和物流(第七章『擺脫枷鎖』)。
在第三篇「腳本」中將分析上述的改變及趨勢對政府(第八章『政府再造』)、企業和個人(第九章『未來市場』)有何影響,並舉出某些在全球化經濟階段過後,可能決定世界走向的經濟驅動力(第十章『下一個全球舞台』)。最後一部分則是重溫拙作《策略家的智慧》(The Mind of the Strategist),思考企業發展全球舞台的經營策略時,所使用的架構應當如何變革。
《全球舞台大未來》是用我的世界觀理解當前世界。二十年前,全球化只是一個名詞或理論概念,如今已成為事實。要了解這個新世界所適用的新法則,需要一段過程,本書便屬於這個過程中的一步,而眼前我們往往找不到適當的法則來解釋日常所經歷的種種。本書不是結束,也不是開始,但我期盼它代表企業和個人、區域和國家領袖向前邁進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大前研一,二○○四年九月於東京
我們處於真正互連、互賴的世界,由全球化經濟結合為一。過去的工商業和經濟猶如在個別劇院,針對不同觀眾表演(或許都出於同一作家的作品)。演員各具特色,其表演方式常受到每家劇院的傳統所影響。如今這齣戲是在一個其大無比的全球舞台上搬演。演員有時會為了爭取觀眾的注意力而彼此競爭,不過在舞台上可以來去自如,不會再被過時的道具阻擋。全球舞台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中。《全球舞台大未來》提供腳本,協助讀者在不斷變化的情節發展中,走出自己的路。
多虧資訊技術的進步,我們才能有今日的局面。資料沿著光纖纜線或透過衛星傳輸,自由地傳遞世界各地。資訊挑戰各種障礙,無論是物質或政治壁壘。為簡化技術應用而建立的平台,也促進資訊流通。威力強大的搜尋引擎如Google,使我們能在錯綜複雜的數位迷宮裡,找到並結合不相干的資訊。在類比時代,各自獨立的片斷資訊必須由人工連結,從中找出含意。現在則是無腦機器人透過無數相互連結的電腦,彈指間就能把資訊組合完成,並分析其意義。二○○五年一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八十億網頁的資訊任君取用,從中歸納出某種觀點和知識只需剎那。以前要智者或老經驗的記者,才能發掘不同資訊間的關聯,如今任何外行人只要把幾個字輸入搜尋引擎,就能找出許多看似無關事件之間的關聯。
以往化學家得利用《化學摘要》(Chemical Abstract)尋找所需文章,因為這份權威性刊物蒐羅了全世界化學家所有的著作。買賣股票者則利用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德勵財富資訊(Telerate)、日經(Nikkei)或其他國具影響力的來源,去尋找重要資訊。現在Google及類似搜尋引擎則是常用的入口網站。很可能你要找的資訊,至少是該資訊的線索,大部分均以數位形式存在。因此,雖然未在新的全球劇院舉行正式開幕儀式,人類卻早已進入無疆界的數位世界。
全球劇院具有很多改變世界的含意,其中有些在中國、芬蘭和愛爾蘭等國家已逐一實現。全球化經濟不理睬障礙,但障礙不移除就會造成扭曲。另一個引起摩擦的源頭是傳統的中央集權式國家。這種國家的條件不足,無法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反倒是轄下的各區域常成為吸引和維持繁榮的最佳單位。區域國家是在全球舞台上追求繁榮的理想單位,而區域國家非正式地結合於歐盟(European Union)這類大組織下,將可促進自由貿易、法規統一及市場整合,使它如虎添翼。
資料傳輸技術革命,已對貨幣和資金的流動產生影響。金錢可以毫無限制地流向最高獲利區。老式的企業價值觀因影響力漸增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而倍受挑戰。許多傳統經濟學建立於國家政策基礎上,因此對外界影響力會強烈左右本國經濟的國家而言,老舊的經濟理論已不適用。
請看阿根廷在過去十年裡兩次截然不同的經濟危機。第一次危機發生時,阿根廷全國和許多局外人都陷入恐慌;第二次卻沒有。第二次危機發生時,與阿根廷相關的人,不分國內外,都不再依賴該國貨幣新披索(new peso),因為大家多半把資產換成全球儲蓄及清算的標準:美元。
若全球化經濟如我所認為的,其動力來自技術,那知識就是全球化經濟的貴金屬。例如,印度的優勢本質上歸功於理工科博士人才眾多。新興國家可透過教育推動經濟成長。任何地方不再需要礦藏豐富、人口眾多或軍力強大,才能成為全球化經濟舞台上的主角。經由海外投資就有可能獲得財富和技術知識。外資不再被視為威脅,而應看作是無窮機會的泉源。
全球化經濟固然代表機會,但政府、企業和個人也將面臨挑戰。唯有採取彈性、務實的作法才能通過考驗。 導論
我們心中的構想不會一開始就以完美形式出現,構想是經驗、觀察、期望和靈感的匯集,當它在耀眼的光芒下站上舞台,我們難免有所遲疑,不確定台下觀眾會有什麼反應。這些構想不斷演變發展,並時時留意著外在變動的反應和環境。
《全球舞台大未來》(The Next Global Stage)一書的架構在我腦海裡已演練了二十多年。在我前幾本著作《無國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及《看不見的新大陸》(The Invisible Continent)中,已討論過許多我仍在探索的課題。正如方才所說,構想不會以完美狀態現身。
本書的源起受到兩股力量所推動。
一是見證了外在環境的改變。過去二十年來整個世界變化極大。目前適用的政治、經濟、社會、企業和個人規範,與二十年前的規範幾乎沒有關聯。「時代不同,需要的腳本也不同。」
問題出在我們老是讀同一本陳腐的腳本。全球化經濟擴張帶來的是對商業世界更一致的看法:商業世界自成一體,不受限於國界障礙。這樣的觀點不是來自教科書或學術文章等傳統認知途徑,而是直接得自實際探觸世界,經常遊歷各國,並與各地工商界人士打成一片。然而弔詭的是,這兩者得出的心得卻看似一樣。各地的意見和看法相近,大家認為重要的政治及經濟領域,其發展也大同小異。看法相同,解決之道也就類似。然而,共通的世界觀並不會產生全球舞台所需的非傳統回應及解決之道。
過去三十年藉由擔任顧問、演講和度假的機會,我的足跡遍及六十餘國。例如美國我去過四百次以上;韓國和台灣各兩百次;馬來西亞一百次。最近平均每年到中國六次並且在大連開了一家公司,還製作了十八小時的電視節目,試著解說當地的工商業和政治現況。另外我也在澳洲黃金海岸和加拿大惠斯勒(Whistler)停留不少時間。當然,身為日本公民的我住在東京,更是時常走訪日本各地。
讀者看得出來,我認為沒有比親赴當地考察,參觀公司、與企業負責人、員工和消費者交流更重要的事。這是體會各地實情的方法。我走訪各地時,有時會帶著四十至六十位日本企業高階主管,讓他們第一手觀察吸引全世界資金流入的地區。我們曾到愛爾蘭去考察跨國企業流程委外正如何重塑該國經濟,帶他們看看在全球舞台上欣欣向榮的義大利小城鎮。我們也造訪過北歐國家,了解它們為什麼能成為世上競爭力最強的國家;又到東歐,看那些國家在已成長為二十五個會員國的歐盟中地位如何。這個團體也已訪問過中國和美國兩次,印度、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澳洲各一次。
跟我同行的高階主管都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即使在這網際網路和全球有線新聞發達的時代,四處走走,多聽多看,問些問題,仍是最佳的學習方法。親自體驗世界現況會改變觀感。親眼目睹全球舞台後,主管們會開始用不同的眼光去讀報紙、看電視。他們的視野逐漸變得開闊,對自己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處之泰然。這不容易做到;這需要新技巧。 本書的第二隻推手,是過去二十年來我所直接接觸的一些全球化經濟先驅。
最先贊同真正全球化經濟概念的企業領導人之一是史克美占(Smith Kline Beecham)公司前執行長溫特(Henry Wendt)。他認為跨國策略聯盟有可能成為美國製藥業的救星,也體認到國際性策略聯盟將來就算不是絕對的關鍵,仍具有相當重要性。
溫特發現全球有三大主導市場:美國、日本和遠東,以及歐洲。無論自詡為多麼強盛、多麼優勢的企業,沒有「一家」企業能夠有效單獨經營和服務這三個市場,奢望包辦一個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一萬美元、人口達七億的市場。
一般公司傳統的行銷策略是循序漸進打入每個市場,無論市場是一個區域或是國家。只有當公司本身和產品在A市場站穩後,然後才會再轉向B市場。但溫特主張,如果產品夠好,公司就須採取灑水器模式,「同時」進入各個市場。跨國策略聯盟便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做法之一。
於是溫特與美占公司談判,美占在研發方面享有高聲譽,在歐洲也佔有相當大的市場,最後談判結果是兩家公司合併。他不但選擇合併的路,還特別把企業總部由匹茲堡遷至倫敦,此舉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溫特有遠見與先見之明,他的跨國策略聯盟概念確實極具開創性。當時跨國聯盟和合併不易達成,因為每家大公司都一頭栽進自己的國內市場。這些公司也都在其本國政府的管控之下,與政府的關係密切並十分認同政府。放棄本國市場是非常困難的,看看最近有關委外的呼聲就知道。一方面可能政府反對(就如德、法企業談判合併時常見的現象);一方面媒體評論家像冰凍沼澤裡的遠古長毛象或恐龍,為了生存,把這種行動批評為不愛國或沒有原則。不論什麼合併案,他們都要評斷出「誰輸誰贏」,如戴姆勒克萊斯勒(Daimler Chrysler)的例子。
在國界逐漸消失的世界裡,跨國策略聯盟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唯一出路。以製藥業為例,藥品愈來愈走向標準化。一些重要、有利潤空間的組合成分或配方已逐漸失去獨特性,隨之而來的是天文數字般飛漲的研發費用。新頒布的規定更增加成本和延誤時程。然而投入研發的金額與產品推出後的成績,只有間接的關聯。公司或許可以成立設備頂尖的實驗室、匯集經驗豐富和年輕出色的人才組成最佳研發團隊,但這些努力從不保證一定成功。決定努力的方向對不對以及能不能有所突破,還是有些機運的因素在內。
企業的難處在於,當研發成功,超級好藥誕生,公司卻可能在世界各重要市場缺乏足夠銷售人力。銷售收入減少於是能攤還掉的研發經費就少;而另一方面,公司在無好藥可賣時,也可能得花高薪養很多業務人員。這就是製藥類產業的難題,固定成本高,需要相當的營收規模來分擔這些成本。正因如此,企業需要策略聯盟,有時還得再向前一步採取完全跨國界的購併做法。一九八○年代中期這類例子很少,如今我們幾乎天天可以看到跨國聯盟及購併,發生在金融、航空、零售、發電、汽車、消費與商用電子、機械,以及半導體等產業。 規模及資本額確實扮演了要角。中等藥廠可能在研發上投入十億美元,卻一無所獲,大公司則可能有能力投入三十億美元從事研發。大公司禁得起較多失敗,仍然不致虧損。跨國聯盟能帶給藥廠更多研發測試空間的餘裕,不過這只有把眼光放遠,看到國外市場才辦得到。現在跨國策略聯盟已非新鮮事,溫特開路先鋒的角色值得推崇。
另一位全球化經濟的早期推手是前花旗銀行(Citibank)董事長瑞斯頓(Walters Wriston)。他認為全球化勢在必行,不是基於商管理論,而是基於技術突破他才這麼主張。他曾預言,銀行之間的競爭不會再以金融服務定高下,而是看誰能在技術上領先。事實上,能夠更快做出決定的公司將是贏家,甚至往往得快到比一奈米秒還要短。
瑞斯頓知道明日的銀行業以及全球化經濟會是什麼樣的形式。基本上那是個無國界的世界;會隨著瞬間做出的決定而變動,且這些決定有時不出自於人。技術將是銀行業成功的關鍵,所以花旗銀行的掌舵者一定要精於技術。可惜瑞斯頓的遠見使他成為非主流。二十年前,大多數高階銀行家均屬傳統派,他們認為成功的關鍵不在技術,而在於企業與政府組織之間建立的信任及保密關係。技術固然很好,可是那是後生晚輩的事,銀行家不必多管。
一九八四年瑞斯頓欽點的接班人瑞德(John Reid)就不是傳統美國東岸金融圈出身。瑞德是技術專家,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MIT)。他一直在花旗銀行負責自動櫃員機(ATM)應用和其他電子金融專案。瑞德被任命為董事長時,在公司裡幾乎默默無聞。有人聽說他獲任命的消息時,甚至還問:「是瑞什麼要當董事長?」
瑞斯頓對此決定的辯解是,要教高階銀行家技術很難,可是讓技術專家學會經營銀行相對較容易。至於關係,久而久之自然會建立起來。在瑞德主持之下,花旗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銀行,而這段期間,他也機敏的領導花旗度過拉丁美洲金融危機。
還有一位超越時代的企業領導人,就是新力(Sony)創辦人盛田昭夫。他創辦的公司原名東京通信工業(Tokyo Tsushin Kogyo)簡稱東通工(Totsuko, TTK)。這種名稱即使用簡稱,對西方市場來說都太難了。所以盛田想出Sony四個字母,代表他生產電晶體收音機的音質。在他眼中,全世界是一個大市場,沒有什麼分界。盛田見識遠大,但絕不是個自大狂。他給企業著名的忠告是:「從全球角度思考,從地方角度行動。」日本雜誌《日經商業》(Nikkei Business)率先把這種主張稱為「glocal」,由此出現新名詞「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這三位有遠見的大師對當年逐漸出現的全球化經濟,在許多方面與筆者所見略同,見拙作《三邊勢力》(Triad Power)及《無國界的世界》。自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有幸與他們三位和許多人交換看法。不過在論及區域國家(region-state)的重要性時,總感覺難以掌握,無法定論。直等到中國自一九九八年後的發展,我腦海中在這個議題上才產生實際可行的觀點。 舞台指南
從前述思想歷程出發,我在本書中,首先闡述世界現狀及人們如何加以解讀。在第一篇「舞台」中,第一章的「世界行」談到若干爆炸性成長地區,並指出全球化經濟的一些特點。第二章「開幕之夜」回顧當今新世紀的源起。本篇的尾聲第三章「經濟學的終結」則檢討傳統經濟學及經濟學家未能理解全球化經濟的缺失。
第二篇「舞台指南」,探討了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趨勢。第四章「主導大局」,一開始是介紹民族國家的發展,以及我所謂區域國家的動能,全球化經濟裡最有用、最具威力的經濟組織方式即區域國家。接著第五章「進步平台」說明平台觀念,例如使用英文、Windows作業系統、品牌、美元,做為全球溝通、了解及商務工具。最後談因應新興全球化經濟,經營企業有哪些地方必須改革。其中有些涉及商業制度和流程(第六章『海闊天空』),有些則是產品、人員和物流(第七章『擺脫枷鎖』)。
在第三篇「腳本」中將分析上述的改變及趨勢對政府(第八章『政府再造』)、企業和個人(第九章『未來市場』)有何影響,並舉出某些在全球化經濟階段過後,可能決定世界走向的經濟驅動力(第十章『下一個全球舞台』)。最後一部分則是重溫拙作《策略家的智慧》(The Mind of the Strategist),思考企業發展全球舞台的經營策略時,所使用的架構應當如何變革。
《全球舞台大未來》是用我的世界觀理解當前世界。二十年前,全球化只是一個名詞或理論概念,如今已成為事實。要了解這個新世界所適用的新法則,需要一段過程,本書便屬於這個過程中的一步,而眼前我們往往找不到適當的法則來解釋日常所經歷的種種。本書不是結束,也不是開始,但我期盼它代表企業和個人、區域和國家領袖向前邁進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大前研一,二○○四年九月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