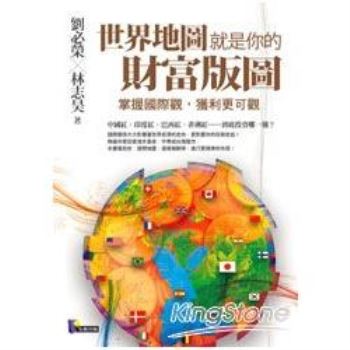第一章 世界變了,投資當然也要跟著變
4.充滿衝突的世界,將顛覆固有的投資邏輯
未來,無論是關心國際關係演變的人、關心全球趨勢的投資人、關心產業變化的研究員,或是一般市井小民,都得準備面對這個少了權威、少了秩序,卻多了紛爭與衝突的世界,而過去習以為常的那一套投資邏輯,也將跟著被徹底顛覆。
舉例來說,在投資市場中打滾已久的人,一定聽過「長期投資」這個觀念。它的意思是,如果看好一個產業或一個國家的長期趨勢,那麼只要死心塌地抱著那檔股票或投資那個國家的基金就一定可以獲利。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觀念,認為成熟國家的股市比較穩定,新興國家的股市比較震盪,所以如果要長期投資,波動低的成熟國家股票一定是「核心部位」,波動高的新興國家股票一定是「衛星部位」,如此才能確保資產的穩健性。
問題是,在金融海嘯之後,成熟國家與新興國家在經濟成長的表現上幾乎逆轉。成熟國家的經濟表現遲緩,新興國家的經濟表現強勁,而且由於成熟國家開始面臨較多的政治與社會衝突,政府財政與企業開始面臨結構性的重組,所以成熟國家股市的波動性,其實並不會比新興市場低。
這就是第一個要被顛覆的投資邏輯:「成熟國家股票比新興國家穩健」這個邏輯,已經成為歷史了。
接著第二個要被顛覆的投資邏輯,是「新興市場具有高報酬特性」這個邏輯。嚴格說來,這裡所指的新興市場,是指以金磚四國為主的新興市場。其實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新興市場就已體認到自身經濟的脆弱,並且開始試圖改革,只不過金融海嘯加速了改革的進程。例如從二○○九年開始,中國和巴西都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要把過去「重出口、重消耗、輕內需」的經濟模式,徹底轉型為「重內需、減消耗與減出口」的經濟模式。至於巴西,二○一○年羅塞芙總統上任之後,宣示將以「縮小貧富差距」為主要的經濟政策。可見對這兩個金磚大國而言,調整經濟結構是未來最重要的政策,而這些政策,將導致這些金磚大國告別過去高報酬的時代。
或許有人會懷疑,中國、巴西,甚至印度,到目前為止都還保有與過去一樣強勁的經濟成長率,為什麼以後股市的表現就無法像過去一樣?原因不難理解。因為要調整經濟結構,一定得「扶植新產業、壓抑舊產業」,可是在股市板塊的分布裡,一定是舊產業居多、新產業居少。換句話說,未來在調整經濟結構之後,金磚大國或許還能維持漂亮的經濟成長率,但股市各類股的表現卻會相當分歧。這一點,從中國股市與巴西股市在二○一○年的走勢即可看出。
在中國股市,新的產業如健康醫療、清潔能源與民生消費等,股價表現都非常好,但是占大盤權重較高的地產、銀行與能源產業卻表現平平,有的甚至還因受到政府打壓房市的影響而出現嚴重的下跌。
巴西股市也是一樣。儘管巴西是以內需經濟為主的國家,但能源與原物料相關類股還是占股市較高的權重,於是只要中國不想再消耗大量的資源,而歐、美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景氣也還沒恢復熱絡,以原物料產業為主的巴西股市必然會受到壓抑。所以說,金磚大國高報酬的時代也已經成為歷史。
第三個被顛覆的投資邏輯,是「股市比債市好賺」這個邏輯。資本市場的特性一定是「過度反應」,因為只有過度反應,市場才有上下來回套利的空間。然而,當過度反應變得比以往更頻繁,再嚴謹的投資模型也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增加誤判的風險。對保守的投資人而言,在面對一個波動如此高的市場時,即使知道未來自己的資產價格總會微幅上揚,但想到要經歷過程中所有上下震盪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卻可能讓他們因此提前退場,轉而去玩另一種遊戲。
二○一○年全球資金從成熟市場的股市撤出,轉往信用債券市場去布局,就是這個道理。歐、美、日等成熟國家正在為自己的經濟問題焦頭爛額,政治人物的政策意見又容易反反覆覆,例如好不容易計畫要做某件事,實施之際又遭遇民意的強烈反彈(例如美國的健保法案、減稅方案,以及其他經濟刺激方案),這勢必會導致政府面臨空轉的狀態,使經濟復甦的速度更加緩慢,而只要投資人對景氣復甦沒信心,資本市場就會因不安全感的增加,而出現不理性的走勢。
成熟國家的股市與資產,過去一向以穩健的波動著稱,而人們也往往認為股市一定比債市好賺,但是在未來,這一切也將成為歷史。
最後一個要被顛覆的投資邏輯,則是「新興市場將取代成熟市場」這個邏輯。在金融海嘯之後,有不少投資人開始認為,兼具高成長與多題材的新興市場,將取代成熟市場而成為全球投資的重心。但是不要忘了,各成熟市場之間有彼此可以順利協調的特性,新興市場卻是一個北起俄羅斯,中經中國,南至印度,再從印度延伸到中東,然後從中東延伸至東歐與非洲,再從非洲延伸至拉丁美洲。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有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彼此有著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價值、不同的恐懼與不同的願景,在如此分歧的結構當中,要讓新興國家彼此團結合作並不容易,有時候甚至還容易起衝突。
尤其在現在這個資本快速移動的年代,資產泡沫很容易形成,同樣也可以很輕易地被戳破。在共同的難關考驗之下,有些新興國家可能得以撐過去,但有些國家必然會因此而垮掉。八○年代拉美國家經濟的崩盤,是這樣引發的;九○年代初期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經濟的崩盤,是這樣引發的;九○年代末期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崩盤,也是這樣引發的;而後一九九九年俄羅斯出現貨幣危機、二○○二年阿根廷出現經濟危機,儘管故事各不相同,劇本的邏輯卻是大同小異。
更何況,從過去五十年的歷史可知,就算經濟泡沫是從西方引爆,付出代價的卻總是新興市場,因為西方國家仍然是全球資本市場的「莊家」,當莊家不想玩了,只要「蓋牌」就沒事,但是那些已經把賭金押在桌上的「玩家」,卻可能面臨全輸的困境。而且,每當有經濟危機發生,必然對新興市場的股市與政治造成強烈的衝擊,資產縮水就罷了,更麻煩的是,由於貨幣價格與產業受到嚴重打擊,人民的生活水準可能倒退數年、甚至十數年。
因此,儘管新興國家在目前已經取代成熟市場,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儘管新興國家有著許多的「故事」,讓人們做出種種看好其經濟成長的推測,但是在泛濫的資金與不健全的經濟體質下,卻不保證資產報酬會比成熟市場來得更高或更穩。
第三章 四大地緣關鍵國,大國爭鋒的受惠者
4.東南亞最大國印尼,最熱門的第五塊金磚
金融海嘯之後,金磚故事的變化,始終圍繞著「誰上誰下」的主題打轉。隨著市場起伏逐漸分出高下,主張把俄羅斯踢出金磚四國的呼聲愈來愈高,呼籲把印尼加入金磚四國的呼聲也愈來愈高。
二○一○年十一月,美國《商業週刊》刊出〈金磚四國之爭:剔除俄羅斯,加入印尼?〉的報導。儘管俄羅斯在過去石油價格飛漲的時代,經濟蒸蒸日上,但過度仰賴石油出口的結果,使得該國經濟在金融風暴之後一切被打回原點。至於印尼,則是財政穩健,政治與社會更趨穩定,特別是尤多諾總統連任成功後,致力改善教育和醫療,所以不只是債券天王葛洛斯、末日博士盧比尼等經濟學家看好印尼,連高盛和摩根士坦利等機構,都主張印尼在未來會比俄國更受投資人青睞。
在《商業週刊》的報導中,除了比較俄羅斯和印尼兩國自二○○九年以來的股市表現,更把人口優勢列為兩國經濟基本面的關鍵差異,例如年齡在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印尼有二七%,俄羅斯只有一四.八%;而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俄羅斯高達一七.八%,在印尼卻只有八.八%。可見俄羅斯的人口老化與內需萎縮問題嚴重,在人口優勢上遠遠落後給印尼(圖3-8)。
隨著市場把印尼納入「第五金磚」的呼聲愈來愈高,投資人對印尼似乎也是信心滿滿。不過,投資人如果還有印象,無論是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還是二○○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印尼都是亞洲國家中受傷最深的國家之一。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但造成印尼盾貶值五○%以上,經濟實力倒退了好幾年,更使得統治印尼將近三十八年的強人蘇哈托下台。至於在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印尼同樣遭到外資無情的砍殺,除了股、匯市下跌慘重,股市更曾經慘跌至連續三日中斷交易。若按照過去的經驗,要相信印尼未來會成為亞洲財富的焦點,實在是有些牽強。過去投資銀行曾經看好印尼,但所給的數據和願景,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到最後令投資人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
然而,本書所建議的地緣國家,絕對不是按照投資銀行的建議起舞。印尼之所以能在未來成為亞洲市場的焦點,除了投資銀行口中的基本面數據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印尼的地緣位置、這個位置未來會發生的變化,以及目前該國領導人想做的事。
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只要別太糟糕,政治上相對穩定,那麼所謂的基本面、經濟數據、預測報告等,其實都不會太難看。這就好比一群基本上健康的人,若比較智力、健康狀況等先天條件,其實都不會差太多。可是,如果把這些人放在不同的情境中,觀察其行為與情境的互動,就會發現,為什麼在這當中,有些人成就非凡,有些人卻沒沒無聞。
印尼,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即便是英雄,也要「乘勢」才能興起,如果沒有了「勢」,英雄只能「氣短」。在觀察未來財富的流向時,國際格局,也就是所謂的「勢」,會比投資銀行的基本面報告更重要。
按照投資銀行的說法,印尼的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有利、經濟成長速度較快、企業獲利高、國民識字率高、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圖3-9)、龐大的內需人口……坦白說,這些所謂「基本面」的條件,難道在過去三十年都未曾發生?不但早就發生,甚至有些國家的條件比印尼還要好。可見光以這些標準來看,開發中國家都是投資市場上的「英雄」。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印尼過去不能紅,非要在這個當兒才能大放異彩呢?就是因為「勢」。在金融海嘯之後,「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印尼這個英雄,現在有了崛起的條件。
第一個「勢」的變化,就是中國和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競賽。先前已經提到,東南亞各國勢必成為中、美兩大強國拉攏的對象,而既然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自然擁有周旋於兩強之間求取最大利益的本錢。
第二個「勢」的變化,就是中國和東協之間的產業轉移。〈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簽訂,讓中國成為東協出口商品最大的市場,而另一方面,中國輕製造、重內需的經濟轉型,也將使製造業從中國外溢(不是外移)到以印尼為首的東協地區。製造業是與人口紅利連結最密切的產業,由於中國製造業的外溢,使得印尼龐大的人口資源與較高的識字率,有機會轉變為「紅利」,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種情況在過去二十年間未曾發生。過去,印尼空有年輕的人口、豐富的資源,以及較高的識字率,在經濟發展上卻難以獲得市場的垂青,因為在當時,蘇聯已經垮台,中國羽翼未豐,美國並不需要拉攏印尼。至於對中國而言,經濟勢力尚未滲入到東協,在外交上「絕不當頭」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所以過去印尼的可利用價值一直很低,等於是空有一身武藝,卻英雄氣短。
時勢當然會造英雄。勢的變化,使印尼未來在投資市場上會有更好的條件。根據美國中情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在GDP和人口規模方面,印尼都勝過其他的東協國家,而以資本市場的發展來看,印尼股市的市值目前僅占該國GDP的五○%,相較於新加坡的二九三%、馬來西亞的一五六%,乘勢而起的印尼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圖3-10)。印尼的確是東協國家中股市發展最具潛力的市場。
另外,在實體經濟方面,相較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等高度仰賴出口的東協國家,印尼的出口占GDP比重僅二五%,再加上中國又要轉型為內需型的經濟體,大大有助於印尼商品出口市場的拓展。換言之,印尼在經濟發展上,受外部環境衝擊的機率將遠比其他東協國家低。也難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二○一一年印尼的經濟成長率將達四.七五%,二○一二年甚至有機會達到六%,傲視東協群雄。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與過去條件相同,印尼未來的際遇卻會與過去如此不同。印尼這個英雄現在終於可以乘勢而起。所以,當印尼再度成為投資銀行眼中的最愛,到底是不是又一次的「狼來了」?如果能看懂「勢」的變化,那麼無論投資銀行說什麼,都不是那麼重要了。
4.充滿衝突的世界,將顛覆固有的投資邏輯
未來,無論是關心國際關係演變的人、關心全球趨勢的投資人、關心產業變化的研究員,或是一般市井小民,都得準備面對這個少了權威、少了秩序,卻多了紛爭與衝突的世界,而過去習以為常的那一套投資邏輯,也將跟著被徹底顛覆。
舉例來說,在投資市場中打滾已久的人,一定聽過「長期投資」這個觀念。它的意思是,如果看好一個產業或一個國家的長期趨勢,那麼只要死心塌地抱著那檔股票或投資那個國家的基金就一定可以獲利。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觀念,認為成熟國家的股市比較穩定,新興國家的股市比較震盪,所以如果要長期投資,波動低的成熟國家股票一定是「核心部位」,波動高的新興國家股票一定是「衛星部位」,如此才能確保資產的穩健性。
問題是,在金融海嘯之後,成熟國家與新興國家在經濟成長的表現上幾乎逆轉。成熟國家的經濟表現遲緩,新興國家的經濟表現強勁,而且由於成熟國家開始面臨較多的政治與社會衝突,政府財政與企業開始面臨結構性的重組,所以成熟國家股市的波動性,其實並不會比新興市場低。
這就是第一個要被顛覆的投資邏輯:「成熟國家股票比新興國家穩健」這個邏輯,已經成為歷史了。
接著第二個要被顛覆的投資邏輯,是「新興市場具有高報酬特性」這個邏輯。嚴格說來,這裡所指的新興市場,是指以金磚四國為主的新興市場。其實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新興市場就已體認到自身經濟的脆弱,並且開始試圖改革,只不過金融海嘯加速了改革的進程。例如從二○○九年開始,中國和巴西都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要把過去「重出口、重消耗、輕內需」的經濟模式,徹底轉型為「重內需、減消耗與減出口」的經濟模式。至於巴西,二○一○年羅塞芙總統上任之後,宣示將以「縮小貧富差距」為主要的經濟政策。可見對這兩個金磚大國而言,調整經濟結構是未來最重要的政策,而這些政策,將導致這些金磚大國告別過去高報酬的時代。
或許有人會懷疑,中國、巴西,甚至印度,到目前為止都還保有與過去一樣強勁的經濟成長率,為什麼以後股市的表現就無法像過去一樣?原因不難理解。因為要調整經濟結構,一定得「扶植新產業、壓抑舊產業」,可是在股市板塊的分布裡,一定是舊產業居多、新產業居少。換句話說,未來在調整經濟結構之後,金磚大國或許還能維持漂亮的經濟成長率,但股市各類股的表現卻會相當分歧。這一點,從中國股市與巴西股市在二○一○年的走勢即可看出。
在中國股市,新的產業如健康醫療、清潔能源與民生消費等,股價表現都非常好,但是占大盤權重較高的地產、銀行與能源產業卻表現平平,有的甚至還因受到政府打壓房市的影響而出現嚴重的下跌。
巴西股市也是一樣。儘管巴西是以內需經濟為主的國家,但能源與原物料相關類股還是占股市較高的權重,於是只要中國不想再消耗大量的資源,而歐、美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景氣也還沒恢復熱絡,以原物料產業為主的巴西股市必然會受到壓抑。所以說,金磚大國高報酬的時代也已經成為歷史。
第三個被顛覆的投資邏輯,是「股市比債市好賺」這個邏輯。資本市場的特性一定是「過度反應」,因為只有過度反應,市場才有上下來回套利的空間。然而,當過度反應變得比以往更頻繁,再嚴謹的投資模型也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增加誤判的風險。對保守的投資人而言,在面對一個波動如此高的市場時,即使知道未來自己的資產價格總會微幅上揚,但想到要經歷過程中所有上下震盪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卻可能讓他們因此提前退場,轉而去玩另一種遊戲。
二○一○年全球資金從成熟市場的股市撤出,轉往信用債券市場去布局,就是這個道理。歐、美、日等成熟國家正在為自己的經濟問題焦頭爛額,政治人物的政策意見又容易反反覆覆,例如好不容易計畫要做某件事,實施之際又遭遇民意的強烈反彈(例如美國的健保法案、減稅方案,以及其他經濟刺激方案),這勢必會導致政府面臨空轉的狀態,使經濟復甦的速度更加緩慢,而只要投資人對景氣復甦沒信心,資本市場就會因不安全感的增加,而出現不理性的走勢。
成熟國家的股市與資產,過去一向以穩健的波動著稱,而人們也往往認為股市一定比債市好賺,但是在未來,這一切也將成為歷史。
最後一個要被顛覆的投資邏輯,則是「新興市場將取代成熟市場」這個邏輯。在金融海嘯之後,有不少投資人開始認為,兼具高成長與多題材的新興市場,將取代成熟市場而成為全球投資的重心。但是不要忘了,各成熟市場之間有彼此可以順利協調的特性,新興市場卻是一個北起俄羅斯,中經中國,南至印度,再從印度延伸到中東,然後從中東延伸至東歐與非洲,再從非洲延伸至拉丁美洲。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有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彼此有著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價值、不同的恐懼與不同的願景,在如此分歧的結構當中,要讓新興國家彼此團結合作並不容易,有時候甚至還容易起衝突。
尤其在現在這個資本快速移動的年代,資產泡沫很容易形成,同樣也可以很輕易地被戳破。在共同的難關考驗之下,有些新興國家可能得以撐過去,但有些國家必然會因此而垮掉。八○年代拉美國家經濟的崩盤,是這樣引發的;九○年代初期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經濟的崩盤,是這樣引發的;九○年代末期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崩盤,也是這樣引發的;而後一九九九年俄羅斯出現貨幣危機、二○○二年阿根廷出現經濟危機,儘管故事各不相同,劇本的邏輯卻是大同小異。
更何況,從過去五十年的歷史可知,就算經濟泡沫是從西方引爆,付出代價的卻總是新興市場,因為西方國家仍然是全球資本市場的「莊家」,當莊家不想玩了,只要「蓋牌」就沒事,但是那些已經把賭金押在桌上的「玩家」,卻可能面臨全輸的困境。而且,每當有經濟危機發生,必然對新興市場的股市與政治造成強烈的衝擊,資產縮水就罷了,更麻煩的是,由於貨幣價格與產業受到嚴重打擊,人民的生活水準可能倒退數年、甚至十數年。
因此,儘管新興國家在目前已經取代成熟市場,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儘管新興國家有著許多的「故事」,讓人們做出種種看好其經濟成長的推測,但是在泛濫的資金與不健全的經濟體質下,卻不保證資產報酬會比成熟市場來得更高或更穩。
第三章 四大地緣關鍵國,大國爭鋒的受惠者
4.東南亞最大國印尼,最熱門的第五塊金磚
金融海嘯之後,金磚故事的變化,始終圍繞著「誰上誰下」的主題打轉。隨著市場起伏逐漸分出高下,主張把俄羅斯踢出金磚四國的呼聲愈來愈高,呼籲把印尼加入金磚四國的呼聲也愈來愈高。
二○一○年十一月,美國《商業週刊》刊出〈金磚四國之爭:剔除俄羅斯,加入印尼?〉的報導。儘管俄羅斯在過去石油價格飛漲的時代,經濟蒸蒸日上,但過度仰賴石油出口的結果,使得該國經濟在金融風暴之後一切被打回原點。至於印尼,則是財政穩健,政治與社會更趨穩定,特別是尤多諾總統連任成功後,致力改善教育和醫療,所以不只是債券天王葛洛斯、末日博士盧比尼等經濟學家看好印尼,連高盛和摩根士坦利等機構,都主張印尼在未來會比俄國更受投資人青睞。
在《商業週刊》的報導中,除了比較俄羅斯和印尼兩國自二○○九年以來的股市表現,更把人口優勢列為兩國經濟基本面的關鍵差異,例如年齡在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印尼有二七%,俄羅斯只有一四.八%;而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俄羅斯高達一七.八%,在印尼卻只有八.八%。可見俄羅斯的人口老化與內需萎縮問題嚴重,在人口優勢上遠遠落後給印尼(圖3-8)。
隨著市場把印尼納入「第五金磚」的呼聲愈來愈高,投資人對印尼似乎也是信心滿滿。不過,投資人如果還有印象,無論是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還是二○○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印尼都是亞洲國家中受傷最深的國家之一。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但造成印尼盾貶值五○%以上,經濟實力倒退了好幾年,更使得統治印尼將近三十八年的強人蘇哈托下台。至於在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印尼同樣遭到外資無情的砍殺,除了股、匯市下跌慘重,股市更曾經慘跌至連續三日中斷交易。若按照過去的經驗,要相信印尼未來會成為亞洲財富的焦點,實在是有些牽強。過去投資銀行曾經看好印尼,但所給的數據和願景,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到最後令投資人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
然而,本書所建議的地緣國家,絕對不是按照投資銀行的建議起舞。印尼之所以能在未來成為亞洲市場的焦點,除了投資銀行口中的基本面數據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印尼的地緣位置、這個位置未來會發生的變化,以及目前該國領導人想做的事。
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只要別太糟糕,政治上相對穩定,那麼所謂的基本面、經濟數據、預測報告等,其實都不會太難看。這就好比一群基本上健康的人,若比較智力、健康狀況等先天條件,其實都不會差太多。可是,如果把這些人放在不同的情境中,觀察其行為與情境的互動,就會發現,為什麼在這當中,有些人成就非凡,有些人卻沒沒無聞。
印尼,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即便是英雄,也要「乘勢」才能興起,如果沒有了「勢」,英雄只能「氣短」。在觀察未來財富的流向時,國際格局,也就是所謂的「勢」,會比投資銀行的基本面報告更重要。
按照投資銀行的說法,印尼的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有利、經濟成長速度較快、企業獲利高、國民識字率高、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圖3-9)、龐大的內需人口……坦白說,這些所謂「基本面」的條件,難道在過去三十年都未曾發生?不但早就發生,甚至有些國家的條件比印尼還要好。可見光以這些標準來看,開發中國家都是投資市場上的「英雄」。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印尼過去不能紅,非要在這個當兒才能大放異彩呢?就是因為「勢」。在金融海嘯之後,「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印尼這個英雄,現在有了崛起的條件。
第一個「勢」的變化,就是中國和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競賽。先前已經提到,東南亞各國勢必成為中、美兩大強國拉攏的對象,而既然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自然擁有周旋於兩強之間求取最大利益的本錢。
第二個「勢」的變化,就是中國和東協之間的產業轉移。〈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簽訂,讓中國成為東協出口商品最大的市場,而另一方面,中國輕製造、重內需的經濟轉型,也將使製造業從中國外溢(不是外移)到以印尼為首的東協地區。製造業是與人口紅利連結最密切的產業,由於中國製造業的外溢,使得印尼龐大的人口資源與較高的識字率,有機會轉變為「紅利」,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種情況在過去二十年間未曾發生。過去,印尼空有年輕的人口、豐富的資源,以及較高的識字率,在經濟發展上卻難以獲得市場的垂青,因為在當時,蘇聯已經垮台,中國羽翼未豐,美國並不需要拉攏印尼。至於對中國而言,經濟勢力尚未滲入到東協,在外交上「絕不當頭」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所以過去印尼的可利用價值一直很低,等於是空有一身武藝,卻英雄氣短。
時勢當然會造英雄。勢的變化,使印尼未來在投資市場上會有更好的條件。根據美國中情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在GDP和人口規模方面,印尼都勝過其他的東協國家,而以資本市場的發展來看,印尼股市的市值目前僅占該國GDP的五○%,相較於新加坡的二九三%、馬來西亞的一五六%,乘勢而起的印尼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圖3-10)。印尼的確是東協國家中股市發展最具潛力的市場。
另外,在實體經濟方面,相較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等高度仰賴出口的東協國家,印尼的出口占GDP比重僅二五%,再加上中國又要轉型為內需型的經濟體,大大有助於印尼商品出口市場的拓展。換言之,印尼在經濟發展上,受外部環境衝擊的機率將遠比其他東協國家低。也難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二○一一年印尼的經濟成長率將達四.七五%,二○一二年甚至有機會達到六%,傲視東協群雄。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與過去條件相同,印尼未來的際遇卻會與過去如此不同。印尼這個英雄現在終於可以乘勢而起。所以,當印尼再度成為投資銀行眼中的最愛,到底是不是又一次的「狼來了」?如果能看懂「勢」的變化,那麼無論投資銀行說什麼,都不是那麼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