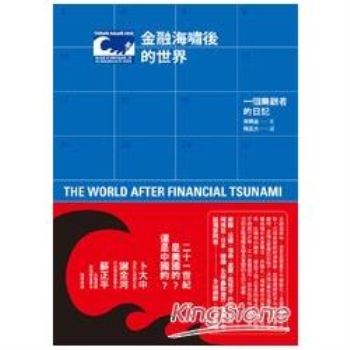經濟需要規律,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2012 年夏季
經濟專家、政治人物和評論員為當前的經濟危機所開的處方,分為兩大類。主張凱因斯理論和政府干預路線的一派,要求政府和中央銀行積極採取措施,以拯救經濟。他們不相信自由市場自我規範的程序,主張藉公共支出製造就業機會,靠低利率讓民間恢復投資和消費。在另一頭,傳統的自由派則說,救經濟沒有急就章的辦法,唯有資本主義的規則恢復穩定、可以預期,市場才會復甦。換句話說,凱因斯理論和主張政府干預的一派相信彈性、隨機應變的經濟政策,傳統自由派認為要有固定的規則。
經濟發展歷史證明後者是較好的選擇,但在民主社會,政治人物往往對前者較有興趣。畢竟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人民期望他們的領袖做點事。不採取行動,只是堅守一些抽象的原則,就得不到廣大民意的支持。但前幾次的經濟衰退顯示,民眾要政府採取行動的壓力,通常會使政府做出不好的決定,導致危機延長或惡化。這就像在足球場上,守門員面對罰 12 碼球的情況。統計顯示,守門員應該站在球門的正中央,這樣把球擋下的機率會比較高,但他往往會在主罰的球員踢球之前的瞬間往左或往右撲,為什麼?因為他覺得看球的人希望他早點行動,但這樣做,會降低守門成功的機率。
全球經濟危機在 2008 年開始以來,各國政府也是一下往左一下往右,卻不見成效。確實,若干有利市場運作的基本規則,例如支持自由貿易、反通膨、反壟斷和反國營化的立場並沒有改變。這樣維持穩定的做法,勝過各國政府在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的反應。當時,國營化和事業壟斷的情況出現,貨物、資本和人員的流通受阻,導致經濟情勢更形惡化。1974 年的危機發生時,情況也是這樣。政府錯誤的因應政策使危機擴大。當時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宣布石油禁運,油價應聲大漲,西方國家的生產成本大幅升高,消費因此減少,經濟陷於停滯。
為了刺激成長,奉行凱因斯理論的經濟專家呼籲中央銀行加印鈔票,西方各國政府都採行這個辦法,導致通膨爆炸。消費者和企業主管看出這是短期的治標做法,因此不願在那樣的氣氛下增加支出,結果出現經濟停滯合併嚴重通貨膨脹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
幸好政府和經濟專家有學到一九三○和一九七○年代的教訓,沒有重蹈覆轍。可能就是因為這樣,這次危機沒有變得更嚴重。但要政府採取行動的壓力還是存在。對於市場如何運作並不是很清楚的政治人物和媒體一直在主張政府要有積極作為,例如2009 年美國就通過了振興經濟方案。選擇這條道路的國家,多數(除了德國和波羅的海國家)出現巨額赤字,對民間投資和創造就業帶來不利影響。振興經濟方案再次失敗,證明凱因斯主張的政策長期而言不會有效果。
政府要如何抗拒採取短期措施的壓力,改用長期、穩定的辦法,以維持經濟的成長?這裡有些建議。美國的傳統自由派與其不斷辯論稅賦和赤字,不如推動修改憲法,對聯邦政府支出設定上限。資本主義的歷史顯示,公共支出多寡對國內生產毛額(GDP) 成長的影響,勝過政府赤字或稅率。美國如果設定政府支出上限,將可緩和企業和消費者的不安,使未來比較容易預測。企業界目前有龐大的資金處於凍結狀態,或投入不具生產力的債券市場。如果公共支出有了上限,企業界就會有誘因將資金投入生產。這個修憲行動,也能重啟一直是美國經濟擴張主要動力的創新活動。
美國政治和金融實力集中在少數幾家銀行手中,這是 2008年世界經濟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而且事情可能重演。如果美國訂定長期的規範,將可結束這樣的情況。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辛加里斯(Luigi Zingales)在他的新書《人民的資本主義》(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中寫道,在經濟方面,美國越來越有可能變成「香蕉共和國」——少數幾家大銀行不事投資,只搞短線炒作,摧毀民眾對自由市場的信心,同時耗盡國家的經濟資源。美國如果訂定新的規範,將可避免銀行過於龐大,恢復競爭的態勢,讓上述的情況不致於發生。
傳統自由派也可以促使聯邦準備理事會提高貨幣政策的可預測性。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半個世紀前就已說明,如果聯準會保持貨幣供應和融資的穩定性,經濟就會穩定成長。如果聯準會增高貨幣供應和融資,通常就會形成投機的泡沫、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者泰勒(John Taylor)提出一套計算公式,可以幫助聯準會根據經濟的需要調整貨幣供應量。國會應該立法使聯準會遵守「泰勒定律」,以免聯準會自行斟酌,採行無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政策。
歐洲也需要嚴格的規範,而不是不斷改變的政策。但在歐洲,比較急迫的事不在於訂定新的規範,而是建立聯邦機構,確保現有的規定能夠落實。如果歐元區會員國遵守公共支出和政府赤字上限的條約,就不會有今天的危機。
藉成長脫離這次危機的做法相對清楚,比較不確定的是,在民主國家要怎麼做到這一點。政治領袖必須說服民眾支持採取長期的規範,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好的辦法是跟民眾說明,長期的規範更可以讓人民當家做主。如果美國設定公共支出上限,政治人物就不能依遊說團體的要求,拿納稅人的錢補貼某個企業。讓金融業恢復競爭的規定,將扭轉這個行業由少數人和少數公司掌控的現象,使美國資本主義恢復民主的特性。在歐洲也是一樣,如果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並成立執行歐元相關規定的聯邦機構,可讓習慣大手筆花錢的政治人物受到更有效的民主節制。
這次危機發生以來,出現許多視當時情況訂定的政策,固定的規範被丟在一邊。要結束這次危機,就要扭轉這樣的情況,讓自由市場經濟回歸它原有的規範。
2012 年夏季
經濟專家、政治人物和評論員為當前的經濟危機所開的處方,分為兩大類。主張凱因斯理論和政府干預路線的一派,要求政府和中央銀行積極採取措施,以拯救經濟。他們不相信自由市場自我規範的程序,主張藉公共支出製造就業機會,靠低利率讓民間恢復投資和消費。在另一頭,傳統的自由派則說,救經濟沒有急就章的辦法,唯有資本主義的規則恢復穩定、可以預期,市場才會復甦。換句話說,凱因斯理論和主張政府干預的一派相信彈性、隨機應變的經濟政策,傳統自由派認為要有固定的規則。
經濟發展歷史證明後者是較好的選擇,但在民主社會,政治人物往往對前者較有興趣。畢竟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人民期望他們的領袖做點事。不採取行動,只是堅守一些抽象的原則,就得不到廣大民意的支持。但前幾次的經濟衰退顯示,民眾要政府採取行動的壓力,通常會使政府做出不好的決定,導致危機延長或惡化。這就像在足球場上,守門員面對罰 12 碼球的情況。統計顯示,守門員應該站在球門的正中央,這樣把球擋下的機率會比較高,但他往往會在主罰的球員踢球之前的瞬間往左或往右撲,為什麼?因為他覺得看球的人希望他早點行動,但這樣做,會降低守門成功的機率。
全球經濟危機在 2008 年開始以來,各國政府也是一下往左一下往右,卻不見成效。確實,若干有利市場運作的基本規則,例如支持自由貿易、反通膨、反壟斷和反國營化的立場並沒有改變。這樣維持穩定的做法,勝過各國政府在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的反應。當時,國營化和事業壟斷的情況出現,貨物、資本和人員的流通受阻,導致經濟情勢更形惡化。1974 年的危機發生時,情況也是這樣。政府錯誤的因應政策使危機擴大。當時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宣布石油禁運,油價應聲大漲,西方國家的生產成本大幅升高,消費因此減少,經濟陷於停滯。
為了刺激成長,奉行凱因斯理論的經濟專家呼籲中央銀行加印鈔票,西方各國政府都採行這個辦法,導致通膨爆炸。消費者和企業主管看出這是短期的治標做法,因此不願在那樣的氣氛下增加支出,結果出現經濟停滯合併嚴重通貨膨脹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
幸好政府和經濟專家有學到一九三○和一九七○年代的教訓,沒有重蹈覆轍。可能就是因為這樣,這次危機沒有變得更嚴重。但要政府採取行動的壓力還是存在。對於市場如何運作並不是很清楚的政治人物和媒體一直在主張政府要有積極作為,例如2009 年美國就通過了振興經濟方案。選擇這條道路的國家,多數(除了德國和波羅的海國家)出現巨額赤字,對民間投資和創造就業帶來不利影響。振興經濟方案再次失敗,證明凱因斯主張的政策長期而言不會有效果。
政府要如何抗拒採取短期措施的壓力,改用長期、穩定的辦法,以維持經濟的成長?這裡有些建議。美國的傳統自由派與其不斷辯論稅賦和赤字,不如推動修改憲法,對聯邦政府支出設定上限。資本主義的歷史顯示,公共支出多寡對國內生產毛額(GDP) 成長的影響,勝過政府赤字或稅率。美國如果設定政府支出上限,將可緩和企業和消費者的不安,使未來比較容易預測。企業界目前有龐大的資金處於凍結狀態,或投入不具生產力的債券市場。如果公共支出有了上限,企業界就會有誘因將資金投入生產。這個修憲行動,也能重啟一直是美國經濟擴張主要動力的創新活動。
美國政治和金融實力集中在少數幾家銀行手中,這是 2008年世界經濟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而且事情可能重演。如果美國訂定長期的規範,將可結束這樣的情況。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辛加里斯(Luigi Zingales)在他的新書《人民的資本主義》(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中寫道,在經濟方面,美國越來越有可能變成「香蕉共和國」——少數幾家大銀行不事投資,只搞短線炒作,摧毀民眾對自由市場的信心,同時耗盡國家的經濟資源。美國如果訂定新的規範,將可避免銀行過於龐大,恢復競爭的態勢,讓上述的情況不致於發生。
傳統自由派也可以促使聯邦準備理事會提高貨幣政策的可預測性。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半個世紀前就已說明,如果聯準會保持貨幣供應和融資的穩定性,經濟就會穩定成長。如果聯準會增高貨幣供應和融資,通常就會形成投機的泡沫、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史丹佛大學的經濟學者泰勒(John Taylor)提出一套計算公式,可以幫助聯準會根據經濟的需要調整貨幣供應量。國會應該立法使聯準會遵守「泰勒定律」,以免聯準會自行斟酌,採行無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政策。
歐洲也需要嚴格的規範,而不是不斷改變的政策。但在歐洲,比較急迫的事不在於訂定新的規範,而是建立聯邦機構,確保現有的規定能夠落實。如果歐元區會員國遵守公共支出和政府赤字上限的條約,就不會有今天的危機。
藉成長脫離這次危機的做法相對清楚,比較不確定的是,在民主國家要怎麼做到這一點。政治領袖必須說服民眾支持採取長期的規範,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好的辦法是跟民眾說明,長期的規範更可以讓人民當家做主。如果美國設定公共支出上限,政治人物就不能依遊說團體的要求,拿納稅人的錢補貼某個企業。讓金融業恢復競爭的規定,將扭轉這個行業由少數人和少數公司掌控的現象,使美國資本主義恢復民主的特性。在歐洲也是一樣,如果提高公共支出的透明度,並成立執行歐元相關規定的聯邦機構,可讓習慣大手筆花錢的政治人物受到更有效的民主節制。
這次危機發生以來,出現許多視當時情況訂定的政策,固定的規範被丟在一邊。要結束這次危機,就要扭轉這樣的情況,讓自由市場經濟回歸它原有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