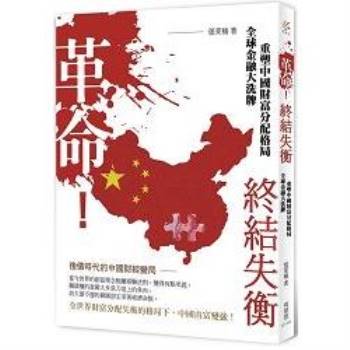中國應更加重視國家財富管理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也將占全球GDP總量的八‧五%左右,然而,中國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卻依然面臨財富分配失衡和貨幣政策自主性被削弱的種種困境。中國必須提高位勢,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
回首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國際國內許多關鍵字會映入我們的眼簾:歐洲債務危機、人民幣匯率問題、量化寬鬆、流動性氾濫、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通膨與資產泡沫問題,凡此種種,在這些經濟亂象中,到底有哪些內在的邏輯關係?
已開發國家是債務問題,自金融危機以來,已開發國家留下了大量的債務,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於是在私人和金融體系去槓桿化的過程中,就由國家再槓桿化使私人債務國家化、國家債務國際化。歐洲由於不能把債務國際化,發生了債務危機,而美國則憑藉美元霸權體系和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將國家債務國際化,由廣大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它的債權國來埋單,造成這些國家的價格總水準急劇上升,這背後實際反映的是已開發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不同國家盈利模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益的交鋒,中國如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管理好自己的國家財富呢?
一、 中國經濟總量今非昔比
事實上,當前,中國經濟總量早已今非昔比,在對外金融領域,中國也出現了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一是從一個外匯短缺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二是從一個吸引外資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淨輸出國;三是從對外債務國轉變為全球第二大對外債權大國。一方面,這一系列的變化,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過程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也對我們管理財富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與這麼大財富相比,我們管理財富的能力卻極其不足。二、 全球債權與債務分佈失衡
與中國很相似,許多新興經濟都已經迅速成為外匯儲備國和新興債權大國。先看看全球的債權分佈,中國擁有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十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香港和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在全球前十大儲備經濟體中,有八個是新興經濟體。
與之相對應的是全球的債務分佈,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十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十位的已開發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比例的八二%,而美國外債餘額已到達一三‧六兆美元,占全球外債餘額的二三‧九%。
三、 真實財富創造與虛擬財富創造的失衡
債務債權的分佈背後反映的是全球真實財富創造與虛擬財富創造之間的失衡。已開發國家是債務國,開發中國家是債權國,全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間的背離也越來越嚴重,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隨著全球分工的深入,世界經濟中存在以金融分工和產業/貿易分工為紐帶的「雙重循環」機制,而恰恰是這兩種機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貿易分工和生產分工體系維繫著實體經濟,金融分工體系維繫著虛擬經濟。
從全球金融分工主導的資本循環來看,以美國為主導的已開發國家是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者,佔據著全球金融分工體系的主導地位。一方面美國等國利用處於金融分工鏈中高端的優勢,試圖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各國在「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中的比較優勢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承擔物質生產的開發中國家的貿易盈餘所形成的儲備資產又通過資本流動回流美國。
四、 全球流動性氾濫下的通膨與通縮現在已開發國家普遍存在的債務問題使得從央行創造貨幣到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傳導機制依然不暢,由於商業銀行不願放貸,不再向社會增加貨幣供應,迫使聯準會直接面向社會提供貨幣。從美國情況來看,自危機爆發至今,美國央行資產已經急劇攀升,銀行現金在全部資產中的占比從歷史平均的三‧二%上升到一○%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仍處於三%的低位。聯準會降低市場利率及促進信貸市場恢復的作用並不明顯,實體經濟部門的銀行貸款同比增速不足一%,銀行惜貸導致美國消費信貸、工商業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增速均處於歷史較低水準,消費信貸更是連續五個季度下滑,無法實現對實體經濟的「造血」和資源配置功能,這是美國經濟難以自我修復的重要原因。
由於歐洲目前的實體經濟還處於修復的過程中,尤其是金融體系的信貸活動還比較疲弱,目前歐洲的廣義貨幣增速和金融部門對私人部門的信貸投放增速緩慢。廣義貨幣以及信貸的低速增長表明實體經濟及金融系統的完全恢復依然有待時日。這些因素一方面表明歐洲金融的恢復依然需要時日,另一方面金融信貸的放緩也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價格總水準。
而對於新興經濟體則是另一番圖景:新興經濟體大都是生產型國家,將本幣盯住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信用貨幣,整個國家的財富都處於巨大風險之中:一方面由於新興經濟體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另一方面,由於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中一般以美元為主要幣種,在美國實行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後,新興經濟體國內或者區內必然是被動超發貨幣,本幣投放過多,同時外部持續大量流入,直接改變了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機制和作用環境,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導致購買力與國內購買力背離,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兩難窘境,日益嚴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對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成本衝擊十分巨大。
五、 外匯儲備不能是「蓄水池」
因此,新興經濟體對於流動性的管理,簡單的對沖避險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因為流動性不僅取決於各國的貨幣政策,也取決於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位勢差,已開發國家在上游,新興經濟體在下游,洪水下來的時候,最先受淹的就是新興經濟體。一九九四年中國外匯體制改革後,外匯儲備迅猛增加,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重達五○%以上,成為影響中國基礎貨幣供應最主要的因素。從歷史經驗來看,自中國經濟的外向性形成之後,通膨壓力、資本流入、貨幣升值這種「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為並行出現的問題,所以這樣看來,外儲不但不是好的池子,反而是很多經濟和金融風險的源頭。中國似乎陷入了一個「財富管理的怪象─流向了增長、流出了財富」,因此調整我們的財富管理模式已經刻不容
緩了。
六、 提高位勢、提高財富管理能力
那未來的道路在哪裡?在我看來,一條路徑就是提高位勢,在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之後,也成為一個金融大國。中國應以解決內外經濟失衡為著眼點,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做出整體謀劃。
第二條路徑,是中短期的,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國金融業尚處於金融淺化階段,在人民幣沒有國際化,在中國尚未建立起真正強大的本土金融市場之前,中國應該適當降低外儲的規模,使其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對此做出調整,儘快建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理順投資與儲蓄不暢的轉化機制,通過增加國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實現財富重整,同時提高國民的財富效應。
七、 中國應更加注重財富管理能力
近年,全球經濟貨幣寬鬆、政府透支、結構失衡、美元走勢、大宗商品價格、通縮通膨、資本流動等多種因素交織,這將使未來全球經濟面臨更為複雜的形勢,特別是美國嚴重依賴政策刺激、歐洲債務危機積弊太久、日本陷入本幣升值和通縮的惡性循環,這決定了東西方分化將是一個顯著特徵,而這種分化也不僅是增長的分化,更是發輾轉型的一種分化。已開發國家創造真實財富的能力越來越弱,而對於迅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而言,我們不僅要關注財富的增長,更要關注財富的分配和財富管理的能力,只有這樣全球經濟才能走向再平衡。中國必須提高位勢,才不至於成為「蓄水池」。在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之後,必須加速推進金融大國的進程。中國應加強「頂層設計」,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人們往往高估五年內的變化,但低估十年內的變化」,相信國家財富的管理理念,將會隨著中國經濟體走向成熟而逐步成熟起來,而今天所有的變革也剛剛開始。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也將占全球GDP總量的八‧五%左右,然而,中國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卻依然面臨財富分配失衡和貨幣政策自主性被削弱的種種困境。中國必須提高位勢,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
回首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國際國內許多關鍵字會映入我們的眼簾:歐洲債務危機、人民幣匯率問題、量化寬鬆、流動性氾濫、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通膨與資產泡沫問題,凡此種種,在這些經濟亂象中,到底有哪些內在的邏輯關係?
已開發國家是債務問題,自金融危機以來,已開發國家留下了大量的債務,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於是在私人和金融體系去槓桿化的過程中,就由國家再槓桿化使私人債務國家化、國家債務國際化。歐洲由於不能把債務國際化,發生了債務危機,而美國則憑藉美元霸權體系和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將國家債務國際化,由廣大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它的債權國來埋單,造成這些國家的價格總水準急劇上升,這背後實際反映的是已開發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不同國家盈利模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益的交鋒,中國如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管理好自己的國家財富呢?
一、 中國經濟總量今非昔比
事實上,當前,中國經濟總量早已今非昔比,在對外金融領域,中國也出現了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一是從一個外匯短缺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二是從一個吸引外資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淨輸出國;三是從對外債務國轉變為全球第二大對外債權大國。一方面,這一系列的變化,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過程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也對我們管理財富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與這麼大財富相比,我們管理財富的能力卻極其不足。二、 全球債權與債務分佈失衡
與中國很相似,許多新興經濟都已經迅速成為外匯儲備國和新興債權大國。先看看全球的債權分佈,中國擁有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十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香港和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在全球前十大儲備經濟體中,有八個是新興經濟體。
與之相對應的是全球的債務分佈,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十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十位的已開發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比例的八二%,而美國外債餘額已到達一三‧六兆美元,占全球外債餘額的二三‧九%。
三、 真實財富創造與虛擬財富創造的失衡
債務債權的分佈背後反映的是全球真實財富創造與虛擬財富創造之間的失衡。已開發國家是債務國,開發中國家是債權國,全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間的背離也越來越嚴重,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隨著全球分工的深入,世界經濟中存在以金融分工和產業/貿易分工為紐帶的「雙重循環」機制,而恰恰是這兩種機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貿易分工和生產分工體系維繫著實體經濟,金融分工體系維繫著虛擬經濟。
從全球金融分工主導的資本循環來看,以美國為主導的已開發國家是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者,佔據著全球金融分工體系的主導地位。一方面美國等國利用處於金融分工鏈中高端的優勢,試圖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各國在「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中的比較優勢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承擔物質生產的開發中國家的貿易盈餘所形成的儲備資產又通過資本流動回流美國。
四、 全球流動性氾濫下的通膨與通縮現在已開發國家普遍存在的債務問題使得從央行創造貨幣到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傳導機制依然不暢,由於商業銀行不願放貸,不再向社會增加貨幣供應,迫使聯準會直接面向社會提供貨幣。從美國情況來看,自危機爆發至今,美國央行資產已經急劇攀升,銀行現金在全部資產中的占比從歷史平均的三‧二%上升到一○%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仍處於三%的低位。聯準會降低市場利率及促進信貸市場恢復的作用並不明顯,實體經濟部門的銀行貸款同比增速不足一%,銀行惜貸導致美國消費信貸、工商業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增速均處於歷史較低水準,消費信貸更是連續五個季度下滑,無法實現對實體經濟的「造血」和資源配置功能,這是美國經濟難以自我修復的重要原因。
由於歐洲目前的實體經濟還處於修復的過程中,尤其是金融體系的信貸活動還比較疲弱,目前歐洲的廣義貨幣增速和金融部門對私人部門的信貸投放增速緩慢。廣義貨幣以及信貸的低速增長表明實體經濟及金融系統的完全恢復依然有待時日。這些因素一方面表明歐洲金融的恢復依然需要時日,另一方面金融信貸的放緩也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價格總水準。
而對於新興經濟體則是另一番圖景:新興經濟體大都是生產型國家,將本幣盯住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信用貨幣,整個國家的財富都處於巨大風險之中:一方面由於新興經濟體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另一方面,由於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中一般以美元為主要幣種,在美國實行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後,新興經濟體國內或者區內必然是被動超發貨幣,本幣投放過多,同時外部持續大量流入,直接改變了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機制和作用環境,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導致購買力與國內購買力背離,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兩難窘境,日益嚴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對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成本衝擊十分巨大。
五、 外匯儲備不能是「蓄水池」
因此,新興經濟體對於流動性的管理,簡單的對沖避險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因為流動性不僅取決於各國的貨幣政策,也取決於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位勢差,已開發國家在上游,新興經濟體在下游,洪水下來的時候,最先受淹的就是新興經濟體。一九九四年中國外匯體制改革後,外匯儲備迅猛增加,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重達五○%以上,成為影響中國基礎貨幣供應最主要的因素。從歷史經驗來看,自中國經濟的外向性形成之後,通膨壓力、資本流入、貨幣升值這種「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為並行出現的問題,所以這樣看來,外儲不但不是好的池子,反而是很多經濟和金融風險的源頭。中國似乎陷入了一個「財富管理的怪象─流向了增長、流出了財富」,因此調整我們的財富管理模式已經刻不容
緩了。
六、 提高位勢、提高財富管理能力
那未來的道路在哪裡?在我看來,一條路徑就是提高位勢,在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之後,也成為一個金融大國。中國應以解決內外經濟失衡為著眼點,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做出整體謀劃。
第二條路徑,是中短期的,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國金融業尚處於金融淺化階段,在人民幣沒有國際化,在中國尚未建立起真正強大的本土金融市場之前,中國應該適當降低外儲的規模,使其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對此做出調整,儘快建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理順投資與儲蓄不暢的轉化機制,通過增加國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實現財富重整,同時提高國民的財富效應。
七、 中國應更加注重財富管理能力
近年,全球經濟貨幣寬鬆、政府透支、結構失衡、美元走勢、大宗商品價格、通縮通膨、資本流動等多種因素交織,這將使未來全球經濟面臨更為複雜的形勢,特別是美國嚴重依賴政策刺激、歐洲債務危機積弊太久、日本陷入本幣升值和通縮的惡性循環,這決定了東西方分化將是一個顯著特徵,而這種分化也不僅是增長的分化,更是發輾轉型的一種分化。已開發國家創造真實財富的能力越來越弱,而對於迅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而言,我們不僅要關注財富的增長,更要關注財富的分配和財富管理的能力,只有這樣全球經濟才能走向再平衡。中國必須提高位勢,才不至於成為「蓄水池」。在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之後,必須加速推進金融大國的進程。中國應加強「頂層設計」,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人們往往高估五年內的變化,但低估十年內的變化」,相信國家財富的管理理念,將會隨著中國經濟體走向成熟而逐步成熟起來,而今天所有的變革也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