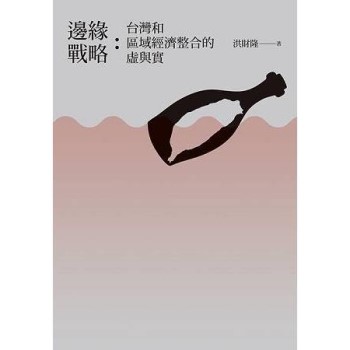台灣:FTA 洽簽風潮中的幽靈國家
1
當台灣發生雄三飛彈誤射事件時,韓劇「太陽的後裔」剛好也在台灣首播。看著劇中劉時鎮大尉帶領的南韓部隊,得以和聯合國、美軍協力合作,一起防治傳染病、打擊犯罪,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任務時,不僅教人感嘆:如果國軍也有這種機會,特別是能夠不時和其他國家聯合軍演、交換資訊與互相觀摩,那麼整體的士氣與戰力也應該會大幅精進。更麻煩的是,這種落差和難堪應該只是冰山一角。
邊緣化症候群
台灣經年累月被國際社會孤立,除了缺乏簽署協定的機會之外,在包括外交、經濟、社會及文化各領域,無論是在人才的培育或最新議題的掌握,往往跟不上時代脈動與國際腳步。後遺症之多、之深,恐怕是超乎想像。
其中尤以公務部門所受到的影響最為深遠。台灣從 1972年失去聯合國的席次之後,公務體系,由於少了各式交流平台和歷練機會更幾乎和國際斷了連結,對各種攸關國家治理的標準與法規、數據與觀念,也就很難有系統地累積、吸收並與時俱進。久而久之,更導致台灣社會對國際規範日益陌生。
舉例而言,美國商會就屢次抱怨台灣的環保標示(圓形)和國際標準規格(三角形)不一樣。然而,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困惑並不是對投資造成障礙,而是難以理解台灣這麼做的邏輯何在。
一方面,台灣在這方面的市場確實不大,國外的廠商不可能為了供應如此規模的市場來調整規格,另一方面此舉也會影響台灣的廠商走向國際。百思不解之餘,他們在 2015 年版的白皮書裡如此推測:
「台灣因為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受到限制,很多時候對其他國家的做法並不十分瞭解,公務人員與立法委員常常會推出台灣獨有的法令規章」。
主要由於現代經濟活動對法制規範與標準相當敏感,一旦我們的法規訂定過程不夠公開透明,內容無法跟國際接軌,執行過程缺乏合理性,不僅會影響外人來台經商的意願,即使連本國人的投資也很容易打退堂鼓。台灣近年來的投資不振,這方面國家治理的落伍應該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像是國內的食品安全法規,也因為觀念和作法跟不上國際規範而屢屢作繭自縛,甚至成為貿易摩擦的來源。特別是在如何處理狂牛症的貿易爭端,國際上早已用風險概念作為處理原則,台灣的食安法規卻仍停留在疫區與非疫區的傳統分類(詳本書:維護食安與國際規範是否為兩難?)。雪上加霜
台灣以往主要是在外交領域被孤立,包括在聯合國及其附屬國際組織都無會籍,近年來則由於區域主義盛行,不利局面也已經擴及到經貿領域。
美國學者藍普敦(David Lampton)即用「累積的孤立」(cumulative isolation)一詞,來描述台灣的這種困頓,可說相當貼切。
當全球各地都在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彼此給予優惠待遇、相互開放市場時,台灣則除了早年和巴拿馬等五個中南美洲邦交國締結協定之外,卻面臨四處敲門都不應的窘境。特別是台灣雖然在地理上位居亞太樞紐,卻在區域經濟整合浪潮中不見蹤影,彷彿是個「幽靈國家」。
被 FTA 風潮排除在外會產生種種不利影響,其中以貿易和投資的折損,最直接也比較容易辨識。更嚴重的後遺症則在於,國家因乏人問津而少了許多回應外在環境變化的機會,一如台灣的情況。
事實上,透過經貿談判的攻防與內部準備,不僅有助於釐清國內外產業的優劣勢所在、累積談判能量,並可刺激公部門提昇治理品質。這些好處一般稱之為「連環衝擊效應」(knock-on effects)。
被 FTA 排除的經濟損失
當其他貿易夥伴因為簽署 FTA 而享有比較低的關稅待遇時,尤其是南韓這個台灣的競爭對手更是積極,我們部分出口產業的訂單就很有可能會被搶走而發生「貿易轉移」效應,這的確會折損部分傳統產業的利潤。尤其是汽車零件、石化與紡織等差異化程度不高的產品,由於報價彈性有限,仍暴露在相關 FTA 的打擊圈內。其次是愈來愈重要的「投資轉移」效應,不管是源於關稅的不利條件,或者出自「原產地規定」:一定比例的原料或中間零組件必須來自FTA 成員國,都會促使企業外移到其他 FTA 成員國家。
話說回來,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 FTA 的蔓延對台灣如此不利?
台灣對外經貿從 1960 年代以來即蓬勃發展,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更陸續對鄰近國家展開投資,如何面對全球競爭和區域佈局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台灣向來既不畏懼,也從未缺席。
特別是經過十年的艱辛準備及談判,台灣終於在 2002 年成功加入號稱是經貿聯合國的 WTO,原本以為至少在經貿領域從此可以海闊天空,不必再因國際地位特殊而蒙受不利待遇,卻沒想到事與願違。一方面是 2001 年開始啟動的 WTO 杜哈回合遲遲無法推展,多邊談判體系面臨瓶頸。另一方面卻看到 FTA 開始蔓延,強調經貿結盟的區域主義從此盛行。
首先,相對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奉行的「非歧視原則」,雙邊或區域FTA 對未能簽署的國家來說,等於是一種歧視,因為否定了其享有國際經貿「機會均等」的權利。
這原本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但也因為各國都能夠自由自在尋求洽簽對象,所以整體來說問題不大,唯獨台灣被 FTA的問題卡住。
此外,就 FTA 的簽署件數而言,以歐洲的密度最高,但從本世紀開始,洽簽重心逐漸移往亞太地區,包括美國、日本、中國、韓國都相當積極。既然這些國家都是台灣最重要的經貿夥伴或競爭對手,台灣一旦被獨漏的不利影響也就會比較顯著。
FTA 的權力關係超過 WTO
最後的關鍵因素則在於,FTA 的權力關係與策略成分,遠遠超過相對著重經貿自由化的 WTO。特別是 FTA 的洽簽過程,需要政府之間的實質政治互動,這使得外交處境困難的台灣,在尋求 FTA 的簽署夥伴時,更容易遭到中國介入與打壓。這正是「中國因素」(China factor)此一詞彙在本世紀初出現時,最原始的用法。
FTA 的內容雖然以經貿議題為主,屬於傳統貿易政策的一環,但選擇洽簽對象時,本質上卻是政治與結盟,也是典型的經濟戰略。
國家可藉由 FTA 此一經濟手段來達到特定目的。譬如美國在選擇洽簽對象時的「區域安全與平衡」考量,以及中國在東南亞將 FTA 與「睦鄰外交」掛鉤,甚至抵制台灣對外洽簽FTA。
1
當台灣發生雄三飛彈誤射事件時,韓劇「太陽的後裔」剛好也在台灣首播。看著劇中劉時鎮大尉帶領的南韓部隊,得以和聯合國、美軍協力合作,一起防治傳染病、打擊犯罪,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任務時,不僅教人感嘆:如果國軍也有這種機會,特別是能夠不時和其他國家聯合軍演、交換資訊與互相觀摩,那麼整體的士氣與戰力也應該會大幅精進。更麻煩的是,這種落差和難堪應該只是冰山一角。
邊緣化症候群
台灣經年累月被國際社會孤立,除了缺乏簽署協定的機會之外,在包括外交、經濟、社會及文化各領域,無論是在人才的培育或最新議題的掌握,往往跟不上時代脈動與國際腳步。後遺症之多、之深,恐怕是超乎想像。
其中尤以公務部門所受到的影響最為深遠。台灣從 1972年失去聯合國的席次之後,公務體系,由於少了各式交流平台和歷練機會更幾乎和國際斷了連結,對各種攸關國家治理的標準與法規、數據與觀念,也就很難有系統地累積、吸收並與時俱進。久而久之,更導致台灣社會對國際規範日益陌生。
舉例而言,美國商會就屢次抱怨台灣的環保標示(圓形)和國際標準規格(三角形)不一樣。然而,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困惑並不是對投資造成障礙,而是難以理解台灣這麼做的邏輯何在。
一方面,台灣在這方面的市場確實不大,國外的廠商不可能為了供應如此規模的市場來調整規格,另一方面此舉也會影響台灣的廠商走向國際。百思不解之餘,他們在 2015 年版的白皮書裡如此推測:
「台灣因為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受到限制,很多時候對其他國家的做法並不十分瞭解,公務人員與立法委員常常會推出台灣獨有的法令規章」。
主要由於現代經濟活動對法制規範與標準相當敏感,一旦我們的法規訂定過程不夠公開透明,內容無法跟國際接軌,執行過程缺乏合理性,不僅會影響外人來台經商的意願,即使連本國人的投資也很容易打退堂鼓。台灣近年來的投資不振,這方面國家治理的落伍應該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像是國內的食品安全法規,也因為觀念和作法跟不上國際規範而屢屢作繭自縛,甚至成為貿易摩擦的來源。特別是在如何處理狂牛症的貿易爭端,國際上早已用風險概念作為處理原則,台灣的食安法規卻仍停留在疫區與非疫區的傳統分類(詳本書:維護食安與國際規範是否為兩難?)。雪上加霜
台灣以往主要是在外交領域被孤立,包括在聯合國及其附屬國際組織都無會籍,近年來則由於區域主義盛行,不利局面也已經擴及到經貿領域。
美國學者藍普敦(David Lampton)即用「累積的孤立」(cumulative isolation)一詞,來描述台灣的這種困頓,可說相當貼切。
當全球各地都在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彼此給予優惠待遇、相互開放市場時,台灣則除了早年和巴拿馬等五個中南美洲邦交國締結協定之外,卻面臨四處敲門都不應的窘境。特別是台灣雖然在地理上位居亞太樞紐,卻在區域經濟整合浪潮中不見蹤影,彷彿是個「幽靈國家」。
被 FTA 風潮排除在外會產生種種不利影響,其中以貿易和投資的折損,最直接也比較容易辨識。更嚴重的後遺症則在於,國家因乏人問津而少了許多回應外在環境變化的機會,一如台灣的情況。
事實上,透過經貿談判的攻防與內部準備,不僅有助於釐清國內外產業的優劣勢所在、累積談判能量,並可刺激公部門提昇治理品質。這些好處一般稱之為「連環衝擊效應」(knock-on effects)。
被 FTA 排除的經濟損失
當其他貿易夥伴因為簽署 FTA 而享有比較低的關稅待遇時,尤其是南韓這個台灣的競爭對手更是積極,我們部分出口產業的訂單就很有可能會被搶走而發生「貿易轉移」效應,這的確會折損部分傳統產業的利潤。尤其是汽車零件、石化與紡織等差異化程度不高的產品,由於報價彈性有限,仍暴露在相關 FTA 的打擊圈內。其次是愈來愈重要的「投資轉移」效應,不管是源於關稅的不利條件,或者出自「原產地規定」:一定比例的原料或中間零組件必須來自FTA 成員國,都會促使企業外移到其他 FTA 成員國家。
話說回來,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 FTA 的蔓延對台灣如此不利?
台灣對外經貿從 1960 年代以來即蓬勃發展,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更陸續對鄰近國家展開投資,如何面對全球競爭和區域佈局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台灣向來既不畏懼,也從未缺席。
特別是經過十年的艱辛準備及談判,台灣終於在 2002 年成功加入號稱是經貿聯合國的 WTO,原本以為至少在經貿領域從此可以海闊天空,不必再因國際地位特殊而蒙受不利待遇,卻沒想到事與願違。一方面是 2001 年開始啟動的 WTO 杜哈回合遲遲無法推展,多邊談判體系面臨瓶頸。另一方面卻看到 FTA 開始蔓延,強調經貿結盟的區域主義從此盛行。
首先,相對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奉行的「非歧視原則」,雙邊或區域FTA 對未能簽署的國家來說,等於是一種歧視,因為否定了其享有國際經貿「機會均等」的權利。
這原本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但也因為各國都能夠自由自在尋求洽簽對象,所以整體來說問題不大,唯獨台灣被 FTA的問題卡住。
此外,就 FTA 的簽署件數而言,以歐洲的密度最高,但從本世紀開始,洽簽重心逐漸移往亞太地區,包括美國、日本、中國、韓國都相當積極。既然這些國家都是台灣最重要的經貿夥伴或競爭對手,台灣一旦被獨漏的不利影響也就會比較顯著。
FTA 的權力關係超過 WTO
最後的關鍵因素則在於,FTA 的權力關係與策略成分,遠遠超過相對著重經貿自由化的 WTO。特別是 FTA 的洽簽過程,需要政府之間的實質政治互動,這使得外交處境困難的台灣,在尋求 FTA 的簽署夥伴時,更容易遭到中國介入與打壓。這正是「中國因素」(China factor)此一詞彙在本世紀初出現時,最原始的用法。
FTA 的內容雖然以經貿議題為主,屬於傳統貿易政策的一環,但選擇洽簽對象時,本質上卻是政治與結盟,也是典型的經濟戰略。
國家可藉由 FTA 此一經濟手段來達到特定目的。譬如美國在選擇洽簽對象時的「區域安全與平衡」考量,以及中國在東南亞將 FTA 與「睦鄰外交」掛鉤,甚至抵制台灣對外洽簽F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