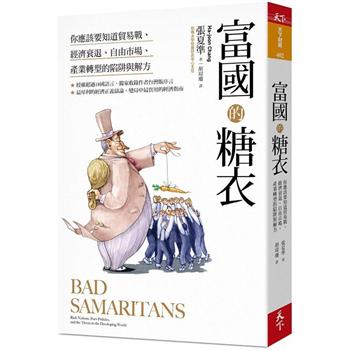●前言 這些「經濟奇蹟」是如何辦到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是十八世紀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其追隨者對於自由經濟(liberal economics)提出的更新版,最早興起於一九六○年代,自一九八○年以來一直是經濟觀點的主流。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自由經濟學家相信,在自由市場無限制的競爭是組織經濟最好的方法,因為這會激發出每個人最大的效率。他們認為政府干預是有害的,因為不管是透過進口管控,或採取壟斷的方式,都會限制潛在競爭者加入市場,進而降低競爭的壓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支持的選項中,有些是舊自由主義學者不支持的,最明顯的是某種型態的壟斷(例如專利權,或中央銀行壟斷紙幣的發行)和政治民主。不過一般說來,他們和舊自由主義一樣,對於自由市場懷抱熱情。只是過去二十五年來,開發中國家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卻接二連三出現許多令人失望的結果,因而造成一些「苦惱」,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也就是放鬆管制、私有化,以及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自一九八○年代起一直維持不變。
富裕國家的政府更向開發中國家推展新自由主義的理念。由美國領軍的富國,並且掌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經濟組織,也就是所謂的「邪惡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居間調停。這些富裕國家政府以金援預算和進軍其國內市場為餌,誘使開發中國家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時這種做法是為了圖利特定的遊說公司,可是通常是為了在開發中國家營造友善外國貨物和投資的環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這些國家貸款是有條件的,要求這些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世界貿易組織更從旁協助,在富裕國家較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在他們比較弱的領域(例如農業或紡織業),制定對自己有利的自由貿易規則。這些政府和國際組織廣為理論家支持,其中有些是訓練有素的學者,這些人理應知道自由市場的極限,但是在提供政策建議時,卻往往忽視這些限制,特別是他們在一九九○年代對前共產經濟體提出的建議。這些機構和個體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由金錢和權力支撐的金融─智識組織。
但是,如果真是如此,富裕國家為什麼不建議開發中國家採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為什麼營造資本主義歷史的假象,而且還是一個不好的假象呢?
在一八四一年,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批評英國自己透過高關稅和大量的補貼方式,攀上經濟的巔峰,卻鼓吹其他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他指控英國在到達世界經濟巔峰的地位後,一腳「踢開梯子」,也就是過河拆橋之意。「這是相當顯而易見且聰明的做法,任何人只要達到卓越的巔峰,便會踢開讓他達成目的的梯子,以防止其他人跟上來。」
如今在富裕國家確實有些人鼓吹貧國採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想要在這些市場掌握更大的占有率,並以先發制人的策略防止潛在的競爭對手崛起。等於是說「照我們說的去做,而不是效法我們以前的作為」,就跟聖經中的「壞薩瑪利亞人」一樣,從別人的困境中攫取好處。最值得憂心的是,現今許多的「壞薩瑪利亞人」並不了解他們的政策傷害了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已經完全被改寫了,以至於富裕國家並沒有察覺,對開發中國家推薦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其實有著雙重的標準。
我在第1章和第2章中,會以檢視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歷史真相開場,希望讀者明白以往接受的「歷史事實」,有許多是謬誤或只有部分屬實。英國和美國並不是自由貿易之家,事實上,長期以來他們都是世界上最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並非所有採取保護和補貼政策的國家都會成功,但成功的國家幾乎都是採取這些措施。就開發中的國家而言,自由貿易通常不是他們能夠選擇的,而是外界勢力不公平的要求,有時甚至是透過武力脅迫。在自由貿易的枷鎖下,這些國家大部分很貧窮,當採取保護主義和補貼措施時,情況就大幅改善。那些表現最亮麗的經濟體,都是採取選擇性和漸進式開放的方式。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秉持自由貿易理念的自由市場政策宣稱犧牲品質以追求成長,事實上卻是兩頭落空,因為過去二十五年來,國界大開和物流自由流通的市場之下,成長速度反而減緩。
接下來,我會在第3章至第9章中,結合經濟理論、歷史和當代的實證,徹底顛覆發展的經驗法則,諸如:
◎自由貿易會降低貧窮國家選擇的自由度。
◎長期而言,或許將外國公司摒除在外是有益處的。
◎投資一家可能會虧損十七年的公司,說不定是個絕佳的提議。
◎有些世界級的頂尖企業是國家控制和國營的。
◎跟生產力較高的外國人「借用」點子,對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低通貨膨脹和政府過於謹慎的態度,可能危害經濟發展。
◎貪腐的存在是因為市場過多,而不是太少。
◎自由市場和民主不是天生的夥伴。
◎國家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人民懶惰。應該說,他們的人民之所以「懶惰」,是因為貧窮。
就像前言一樣,本書最後一章以「未來歷史」的方式提供替代方案,不過這一回卻是非常黯淡的前景。這個情境是刻意悲觀的,卻完全根據現實,如果我們繼續施行壞薩瑪利亞人宣揚的新自由主義,就會更接近這種未來。此外,我還將陳述一些關鍵原則,從書中探討周詳的替代政策措施中,萃取出開發中國家可以提升經濟表現的行動方案。雖然開場白令人沮喪,這也是為什麼本章最後洋溢著樂觀的氛圍,闡述為什麼我會堅信壞薩瑪利亞人可以改變,並且能夠確實幫助開發中國家改善經濟狀況。
新自由主義經濟是十八世紀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和其追隨者對於自由經濟(liberal economics)提出的更新版,最早興起於一九六○年代,自一九八○年以來一直是經濟觀點的主流。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自由經濟學家相信,在自由市場無限制的競爭是組織經濟最好的方法,因為這會激發出每個人最大的效率。他們認為政府干預是有害的,因為不管是透過進口管控,或採取壟斷的方式,都會限制潛在競爭者加入市場,進而降低競爭的壓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支持的選項中,有些是舊自由主義學者不支持的,最明顯的是某種型態的壟斷(例如專利權,或中央銀行壟斷紙幣的發行)和政治民主。不過一般說來,他們和舊自由主義一樣,對於自由市場懷抱熱情。只是過去二十五年來,開發中國家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卻接二連三出現許多令人失望的結果,因而造成一些「苦惱」,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也就是放鬆管制、私有化,以及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自一九八○年代起一直維持不變。
富裕國家的政府更向開發中國家推展新自由主義的理念。由美國領軍的富國,並且掌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經濟組織,也就是所謂的「邪惡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居間調停。這些富裕國家政府以金援預算和進軍其國內市場為餌,誘使開發中國家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時這種做法是為了圖利特定的遊說公司,可是通常是為了在開發中國家營造友善外國貨物和投資的環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這些國家貸款是有條件的,要求這些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世界貿易組織更從旁協助,在富裕國家較擅長的領域,而不是在他們比較弱的領域(例如農業或紡織業),制定對自己有利的自由貿易規則。這些政府和國際組織廣為理論家支持,其中有些是訓練有素的學者,這些人理應知道自由市場的極限,但是在提供政策建議時,卻往往忽視這些限制,特別是他們在一九九○年代對前共產經濟體提出的建議。這些機構和個體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宣傳機器,一個由金錢和權力支撐的金融─智識組織。
但是,如果真是如此,富裕國家為什麼不建議開發中國家採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為什麼營造資本主義歷史的假象,而且還是一個不好的假象呢?
在一八四一年,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批評英國自己透過高關稅和大量的補貼方式,攀上經濟的巔峰,卻鼓吹其他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他指控英國在到達世界經濟巔峰的地位後,一腳「踢開梯子」,也就是過河拆橋之意。「這是相當顯而易見且聰明的做法,任何人只要達到卓越的巔峰,便會踢開讓他達成目的的梯子,以防止其他人跟上來。」
如今在富裕國家確實有些人鼓吹貧國採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想要在這些市場掌握更大的占有率,並以先發制人的策略防止潛在的競爭對手崛起。等於是說「照我們說的去做,而不是效法我們以前的作為」,就跟聖經中的「壞薩瑪利亞人」一樣,從別人的困境中攫取好處。最值得憂心的是,現今許多的「壞薩瑪利亞人」並不了解他們的政策傷害了開發中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已經完全被改寫了,以至於富裕國家並沒有察覺,對開發中國家推薦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其實有著雙重的標準。
我在第1章和第2章中,會以檢視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歷史真相開場,希望讀者明白以往接受的「歷史事實」,有許多是謬誤或只有部分屬實。英國和美國並不是自由貿易之家,事實上,長期以來他們都是世界上最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並非所有採取保護和補貼政策的國家都會成功,但成功的國家幾乎都是採取這些措施。就開發中的國家而言,自由貿易通常不是他們能夠選擇的,而是外界勢力不公平的要求,有時甚至是透過武力脅迫。在自由貿易的枷鎖下,這些國家大部分很貧窮,當採取保護主義和補貼措施時,情況就大幅改善。那些表現最亮麗的經濟體,都是採取選擇性和漸進式開放的方式。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秉持自由貿易理念的自由市場政策宣稱犧牲品質以追求成長,事實上卻是兩頭落空,因為過去二十五年來,國界大開和物流自由流通的市場之下,成長速度反而減緩。
接下來,我會在第3章至第9章中,結合經濟理論、歷史和當代的實證,徹底顛覆發展的經驗法則,諸如:
◎自由貿易會降低貧窮國家選擇的自由度。
◎長期而言,或許將外國公司摒除在外是有益處的。
◎投資一家可能會虧損十七年的公司,說不定是個絕佳的提議。
◎有些世界級的頂尖企業是國家控制和國營的。
◎跟生產力較高的外國人「借用」點子,對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低通貨膨脹和政府過於謹慎的態度,可能危害經濟發展。
◎貪腐的存在是因為市場過多,而不是太少。
◎自由市場和民主不是天生的夥伴。
◎國家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人民懶惰。應該說,他們的人民之所以「懶惰」,是因為貧窮。
就像前言一樣,本書最後一章以「未來歷史」的方式提供替代方案,不過這一回卻是非常黯淡的前景。這個情境是刻意悲觀的,卻完全根據現實,如果我們繼續施行壞薩瑪利亞人宣揚的新自由主義,就會更接近這種未來。此外,我還將陳述一些關鍵原則,從書中探討周詳的替代政策措施中,萃取出開發中國家可以提升經濟表現的行動方案。雖然開場白令人沮喪,這也是為什麼本章最後洋溢著樂觀的氛圍,闡述為什麼我會堅信壞薩瑪利亞人可以改變,並且能夠確實幫助開發中國家改善經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