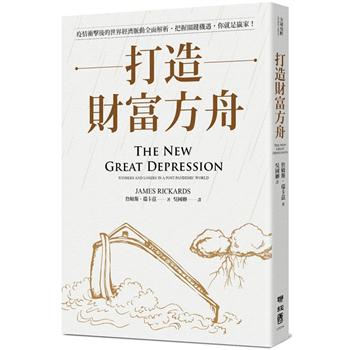內文選摘
崩盤
美國股市在二月二十四日週一下跌三‧六%。比起後來的跌幅,當天的下跌幅度不大,在道瓊歷史跌幅只排名第二十大。但它在許多方面透露了凶兆。它象徵市場參與者心理上的分野。在二月二十四日前,市場的下跌和上漲有序輪替進行,市場指數始終接近歷史高點。市場已學習與「武漢流感」共存,並傾向於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獲得控制。二月二十四日是市場參與者張開眼睛的一天,他們更真切地看到全球性瘟疫的現況,並開始根據較現實的新假設重估股價。股市向來展望未來而忽視根據現狀計算的今日價格。這自然有其道理,但並不是說市場總是看得清楚。市場根據所見的事件估算價格,但對所見事件的了解往往與真相大不相同。當誤解出現時,真相與市場見解間的張力便逐漸升高。真相永遠勝出,但可能需要時間。從一月底到二月二十一日市場普遍對中國和新冠肺炎抱持樂觀看法,表面上病例數逐漸減少,病毒可望獲得控制。在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的週末,義大利的數據粉碎了對中國的幻想。二月二十四日週一,魔咒已被打破,市場終於接受全球病毒危機的現實。
此後市場無情地展開崩跌。二○二○年三月九日,股市重挫七‧七九%(道瓊指數跌二○一三點);三月十二日,股市再挫九‧九九%(道瓊跌二三五二點);三月十六日,股市崩落一二‧九三%(道瓊跌二九九七點),三次下跌在股市單日跌幅史上都是前二十名。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六日的單日跌幅排名史上前五大,三月十六日則為史上第二大,超過第一次大蕭條初始幾日的跌幅,也大於除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重挫二二‧六%以外的任何一日。一九八七年崩盤後設置用來停止交易的熔斷機制(circuit breakers)被不斷觸發,如果以每日跌點而非跌幅來看,史上出現過的十大單日跌點中有八次出現在二○二○年二月或三月。從二月十二日出現的道瓊指數歷史高點二九五五○點,到三月二十三日的波段低點一八五九一點,跌幅高達三七%。這是史無前例的大崩盤,歷來最長的多頭市場已死。
華爾街的啦啦隊出現在金融媒體上,急著指出三七%的崩盤遠遠不如大蕭條期間道瓊指數下跌的八九‧二%。這麼方便的數字比較忽視了八九‧二%崩跌花了三年時間(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事實。道瓊在一九二九年下跌一七‧二%、一九三○年下跌三三‧八%、一九三一年跌五二‧七%,和一九三二年跌二二‧六%。新冠肺炎的崩跌三七%沒有花三年,而是只有六週。沒有人有把握未來的情況不會更糟。
股市從三月底到九月初展開令人刮目相看的漲勢,收復幾乎所有跌幅。這被華爾街誇耀為最糟的情況已經過去的跡象,經濟很快解除封鎖,堅實的V型復甦(下跌快,上漲也快)已經在望。但歷史經驗並非如此。
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下跌八九‧二%的過程中,道瓊曾出現一些亮眼的回升走勢,讓華爾街燃起最糟的已經過去的希望。股市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一九三○年四月二十日上漲了二八‧六%;從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九月七日上漲一三‧二%;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二日股市又漲一七‧五%;最後,從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八日上漲了二二‧二%,這些雙位數比率的上漲發生在史上最大的下跌行情中間。股價記錄道盡故事始末。一九二九年的上漲從道瓊二二八點起漲,一九三○年的上漲從道瓊二一五點開始,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上漲始於道瓊一六三點,一九三一年的上漲則從道瓊一二八點起漲。這些漲勢(和較小的其他上漲)發生在道瓊從三八○點展開漫長而無情的跌勢期間,一直跌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谷底的四二點。這其中不是沒有上漲的波段,也不是沒有一些投資人賺到錢,而是這些上漲的波段無法反映長期的趨勢:推動長期趨勢的力量遠大於短期波動和一廂情願的想法。
第一次大蕭條期間空頭市場中的上漲波段可以從技術面(在一些階段,市場下跌過快和幅度過大,使交易者認為行情勢必回升)和基本面(偶爾會有利多,例如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的復甦計畫刺激股市回升)因素來解釋,雖然整個大環境極為險峻。但同樣的因素無法用來解釋二十一世紀抵押貸款市場崩跌(二○○七到二○○八年)、經濟復甦史無前例的疲弱(二○○九到二○一九年),以及瘟疫(二○二○年)等期間股市的上漲。資產價格膨脹,尤其是股價,主要是被動投資、指數化、指數股票型基金(一種迷你指數)、買回自家股票(實際上是執行長選擇權方案和技術性稅務優惠驅動的結算)、程式交易以「低檔買進」,以及特別是聯準會印鈔和大到不能倒思維而不容許市場下跌等因素造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不能怪投資人爭相投入股市想賺一把。
這些二十一世紀的發明並非市場之福。當主動型投資人不再進行價格發現時,被動投資和指數化的動力將耗竭。當槓桿不再可得和公司的現金流遭侵蝕時,股票買回的力量將用盡。當真正的資金退場觀望時,電腦程式將成為股價下跌前僅剩的買方。程式交易大軍可以繼續轉向其他市場。聯準會將發現,當流通速度(velocity)因為聯準會從來不了解的心理因素而驟減時,印鈔票就再也起不了刺激作用。這種把戲已被看穿,剩下來的就是瘟疫、失業和對未來的恐懼這些巨大的力量。
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模式反映出這些事情。該指數在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攀至歷來最高的三三八六點,然後因為新冠肺炎瘟疫蔓延而開始崩跌。病例人數劇增和失業率飆升在三月四日讓它第二度重挫(從之前的一波小漲)。標普指數在三月二十三日跌至二二三七點低谷,距離高點已有三三%的跌幅,然後展開一波亮麗的回升走勢到九月二日的三五八○點,從低谷漲升了六○%,並且創下歷史新高價。
標普指數是一項市值加權指數,意思是有較大市值公司的股價對整體指數的漲跌會有較大的影響。標普五百指數的高市值公司是大家熟悉的科技巨人,即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Netflix、Facebook和Alphabet(即Google)。這些股票的共同點是對實體零售空間的依賴較小,蘋果有商店,但它們既是銷售店,也是展示間和諮詢中心;亞馬遜擁有全食超市(Whole Foods),但也跨入透過亞馬遜網站下訂單的住家快遞市場。除此之外,這些公司都是大型數位網路公司,提供軟體、串流服務、搜尋、廣告等產品與服務。在這些公司支配市值權值的情況下,稱呼標普五百指數為「標普六指數」可能更合乎現實。
類似的模式出現在以三十家公司為成分公司的道瓊工業指數。這項指數並非以市值加權,而是根據一套複雜的股價公式來計算。但這些成分公司包括了蘋果、思科(Cisco)、IBM、英特爾(Intel)和微軟等科技公司。道瓊也包含電信公司和媒體公司,例如威瑞森(Verizon)和迪士尼(Disney),以及金融公司如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旅行家(Travelers)和威士(Visa)。這些公司總共佔道瓊成分公司的四○%。雖然所有企業都受到瘟疫影響,但科技、電信、媒體和金融業受到的影響遠小於製造業、運輸業和零售業。同樣的,那斯達克(Nasdaq)綜合指數是一項以科技為主的知名指數。總之,我們的主要股價指數背離了真實的經濟,似乎不受六千萬名美國人剛失業和中小型企業幾乎全軍覆沒的影響。
今日的股票不是透過人來交易,它們幾乎全透過機器人。這些機器人被訓練閱讀財務報表、跟隨買賣單並立即採取行動。基本面因素不重要(至少在短期)。如果運算法告訴機器人「跟隨刺激措施買指數」,那麼每次聯準會主席鮑爾(Jay Powelle)公開發言,機器人就買進指數。如果運算法告訴機器人「跟隨更多赤字支出買指數」,每次麥康諾(Mitch McConnelle)和裴洛西(Nancy Pelosi)握手(或碰觸手肘)達成新支出協議,機器人就買進指數。機器人不思考,不分析,而且不展望未來。它們只是遵照指令行事。
最後,現實侵入。即使對機器人來說,破產也是警訊。美國人可能不了解第二波病毒的嚴重性,但他們了解破產。他們可能直接受破產影響;如果你的僱主破產或你的股票變成廢紙,你就能完全了解。即使是不受影響的美國人也感覺到,他們的公司可能很快也會破產。他們可能下個月也會失業,或他們的投資組合將隨著個別的股票暴跌而減損價值。
蕭條不只是統計數字。蕭條是失業和擔心沒有錢繳房租、買餐桌上的食物、尋求醫療照護,和讓孩子受良好教育等個人創傷的可計算總和。失業不只影響你的薪水支票,它們還影響尊嚴、自信和未來的前景。而且蕭條不只是失業。企業遭到摧毀,運氣好的話是虧損。漣漪效應擴大到社區和整個城市。蕭條的衝擊很深,且持續很久;它們可能跨越世代,正如第一次大蕭條的情況。
不過,統計數字可以幫助我們衡量蕭條的深度,作為了解人、企業和社群遭受多大影響的方法。它們也能證明這是一場蕭條,而不是另一波衰退。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並不是有意義的基準。一九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的市場恐慌雖然危及全球金融穩定,卻很快平息,且只直接影響少數人。但這次的蕭條不同,而且數據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
第一、也是最明顯的一點是,超過六千萬名美國人在二○二○年三月一日到十月一日間失業,這些失業者將很快重獲就業的說法是謊言。失業將先是減緩,然後停止。復甦將開始,但這不表示那六千萬名美國人回到工作崗位。每個月增加一百多萬就業人口(以歷史標準來看是個大數字)且持續三年,將不足以讓就業率恢復到二○二○年二月的水準。這項(虛假的)預測還忽略了一個重點,即有許多工作再也沒有恢復。在封鎖期間關門並裁撤二十名員工的餐廳,不會在重新開張時日回僱所有二十名員工。它可能重新僱用十人,並觀望情況的發展。情況很可能不順利。保持社交距離意味餐桌數會減少,被容許進入的客人數受限制。顧客本身因為餘悸猶存而不會全部回流餐廳。當然,這是假設餐廳重新開張;有許多餐廳不會重新開張,而是永遠結束營業。另一方面,未被重新僱用的侍者和酒保會喪失技術和關係,有一些人會離開勞動力,甚至達到雖在技術上不符合政府對失業的定義、但在一般人看法屬於失業的程度。
餐廳的例子是真實的,但只是眾多例子之一。主題標籤#WFH(在家工作)在封鎖期間已變得無所不在。有數百萬人在家工作。僱主發現這個模式運作得比讓員工擠在市區辦公大樓上班還好,除了可以減少後勤成本外,還可節省每年數百萬小時的通勤時間和數百萬美元房租、保險和修繕費用。新的辦公室模式將佔用較少樓層面積、共用的會議室、按日租用的辦公室,和僱用較少的接待員與辦事員。僱主將在辦公室設置儲物櫃供到班人員使用,讓他們下班時把物品置於櫃中。其他時候他們將在家工作。這對僱主是好事。但閒置的辦公室空間、房東的租金、遭裁撤的清潔工、攤販和街頭餐車及餐廳的銷售、空蕩的火車和巴士,以及午餐時間的購物呢?它們全都消失,或減少了八○%。生活將繼續過,但非主要的工作和生產將難以為繼。這是蕭條和衰退的差別。在蕭條時,情況不會恢復正常,因為正常已不復存在。
這不是揣測,而是已經展現在數據的事實。在二○二○年五月,只有三二%的零售商店正常繳房租。其他行業的繳房租比率為:餐廳和酒吧三二%、旅館等住宿業一八%、健身房和運動設施二六%、汽車銷售和服務業二九%、美髮美甲沙龍二五%。其他行業類別的欠繳房租數據也一樣令人驚心。駁斥這些行業都是小企業是罔顧事實。中小型企業佔總就業人口近五○%,創造的產品與勞務總值佔GDP的四五%。以就業和產值來看,它們整體遠比蘋果、微軟、Facebook和Google加起來還重要。欠繳房租意味它們已瀕臨倒閉(最壞的情況),或必須重新協商租約(最好的情況)。這無法靠赤字支出、印鈔票或股市上漲來彌補,它們是痛苦的半永久性損失。
崩盤
美國股市在二月二十四日週一下跌三‧六%。比起後來的跌幅,當天的下跌幅度不大,在道瓊歷史跌幅只排名第二十大。但它在許多方面透露了凶兆。它象徵市場參與者心理上的分野。在二月二十四日前,市場的下跌和上漲有序輪替進行,市場指數始終接近歷史高點。市場已學習與「武漢流感」共存,並傾向於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獲得控制。二月二十四日是市場參與者張開眼睛的一天,他們更真切地看到全球性瘟疫的現況,並開始根據較現實的新假設重估股價。股市向來展望未來而忽視根據現狀計算的今日價格。這自然有其道理,但並不是說市場總是看得清楚。市場根據所見的事件估算價格,但對所見事件的了解往往與真相大不相同。當誤解出現時,真相與市場見解間的張力便逐漸升高。真相永遠勝出,但可能需要時間。從一月底到二月二十一日市場普遍對中國和新冠肺炎抱持樂觀看法,表面上病例數逐漸減少,病毒可望獲得控制。在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的週末,義大利的數據粉碎了對中國的幻想。二月二十四日週一,魔咒已被打破,市場終於接受全球病毒危機的現實。
此後市場無情地展開崩跌。二○二○年三月九日,股市重挫七‧七九%(道瓊指數跌二○一三點);三月十二日,股市再挫九‧九九%(道瓊跌二三五二點);三月十六日,股市崩落一二‧九三%(道瓊跌二九九七點),三次下跌在股市單日跌幅史上都是前二十名。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六日的單日跌幅排名史上前五大,三月十六日則為史上第二大,超過第一次大蕭條初始幾日的跌幅,也大於除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重挫二二‧六%以外的任何一日。一九八七年崩盤後設置用來停止交易的熔斷機制(circuit breakers)被不斷觸發,如果以每日跌點而非跌幅來看,史上出現過的十大單日跌點中有八次出現在二○二○年二月或三月。從二月十二日出現的道瓊指數歷史高點二九五五○點,到三月二十三日的波段低點一八五九一點,跌幅高達三七%。這是史無前例的大崩盤,歷來最長的多頭市場已死。
華爾街的啦啦隊出現在金融媒體上,急著指出三七%的崩盤遠遠不如大蕭條期間道瓊指數下跌的八九‧二%。這麼方便的數字比較忽視了八九‧二%崩跌花了三年時間(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事實。道瓊在一九二九年下跌一七‧二%、一九三○年下跌三三‧八%、一九三一年跌五二‧七%,和一九三二年跌二二‧六%。新冠肺炎的崩跌三七%沒有花三年,而是只有六週。沒有人有把握未來的情況不會更糟。
股市從三月底到九月初展開令人刮目相看的漲勢,收復幾乎所有跌幅。這被華爾街誇耀為最糟的情況已經過去的跡象,經濟很快解除封鎖,堅實的V型復甦(下跌快,上漲也快)已經在望。但歷史經驗並非如此。
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下跌八九‧二%的過程中,道瓊曾出現一些亮眼的回升走勢,讓華爾街燃起最糟的已經過去的希望。股市從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一九三○年四月二十日上漲了二八‧六%;從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九月七日上漲一三‧二%;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二日股市又漲一七‧五%;最後,從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八日上漲了二二‧二%,這些雙位數比率的上漲發生在史上最大的下跌行情中間。股價記錄道盡故事始末。一九二九年的上漲從道瓊二二八點起漲,一九三○年的上漲從道瓊二一五點開始,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上漲始於道瓊一六三點,一九三一年的上漲則從道瓊一二八點起漲。這些漲勢(和較小的其他上漲)發生在道瓊從三八○點展開漫長而無情的跌勢期間,一直跌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谷底的四二點。這其中不是沒有上漲的波段,也不是沒有一些投資人賺到錢,而是這些上漲的波段無法反映長期的趨勢:推動長期趨勢的力量遠大於短期波動和一廂情願的想法。
第一次大蕭條期間空頭市場中的上漲波段可以從技術面(在一些階段,市場下跌過快和幅度過大,使交易者認為行情勢必回升)和基本面(偶爾會有利多,例如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的復甦計畫刺激股市回升)因素來解釋,雖然整個大環境極為險峻。但同樣的因素無法用來解釋二十一世紀抵押貸款市場崩跌(二○○七到二○○八年)、經濟復甦史無前例的疲弱(二○○九到二○一九年),以及瘟疫(二○二○年)等期間股市的上漲。資產價格膨脹,尤其是股價,主要是被動投資、指數化、指數股票型基金(一種迷你指數)、買回自家股票(實際上是執行長選擇權方案和技術性稅務優惠驅動的結算)、程式交易以「低檔買進」,以及特別是聯準會印鈔和大到不能倒思維而不容許市場下跌等因素造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不能怪投資人爭相投入股市想賺一把。
這些二十一世紀的發明並非市場之福。當主動型投資人不再進行價格發現時,被動投資和指數化的動力將耗竭。當槓桿不再可得和公司的現金流遭侵蝕時,股票買回的力量將用盡。當真正的資金退場觀望時,電腦程式將成為股價下跌前僅剩的買方。程式交易大軍可以繼續轉向其他市場。聯準會將發現,當流通速度(velocity)因為聯準會從來不了解的心理因素而驟減時,印鈔票就再也起不了刺激作用。這種把戲已被看穿,剩下來的就是瘟疫、失業和對未來的恐懼這些巨大的力量。
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模式反映出這些事情。該指數在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攀至歷來最高的三三八六點,然後因為新冠肺炎瘟疫蔓延而開始崩跌。病例人數劇增和失業率飆升在三月四日讓它第二度重挫(從之前的一波小漲)。標普指數在三月二十三日跌至二二三七點低谷,距離高點已有三三%的跌幅,然後展開一波亮麗的回升走勢到九月二日的三五八○點,從低谷漲升了六○%,並且創下歷史新高價。
標普指數是一項市值加權指數,意思是有較大市值公司的股價對整體指數的漲跌會有較大的影響。標普五百指數的高市值公司是大家熟悉的科技巨人,即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Netflix、Facebook和Alphabet(即Google)。這些股票的共同點是對實體零售空間的依賴較小,蘋果有商店,但它們既是銷售店,也是展示間和諮詢中心;亞馬遜擁有全食超市(Whole Foods),但也跨入透過亞馬遜網站下訂單的住家快遞市場。除此之外,這些公司都是大型數位網路公司,提供軟體、串流服務、搜尋、廣告等產品與服務。在這些公司支配市值權值的情況下,稱呼標普五百指數為「標普六指數」可能更合乎現實。
類似的模式出現在以三十家公司為成分公司的道瓊工業指數。這項指數並非以市值加權,而是根據一套複雜的股價公式來計算。但這些成分公司包括了蘋果、思科(Cisco)、IBM、英特爾(Intel)和微軟等科技公司。道瓊也包含電信公司和媒體公司,例如威瑞森(Verizon)和迪士尼(Disney),以及金融公司如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旅行家(Travelers)和威士(Visa)。這些公司總共佔道瓊成分公司的四○%。雖然所有企業都受到瘟疫影響,但科技、電信、媒體和金融業受到的影響遠小於製造業、運輸業和零售業。同樣的,那斯達克(Nasdaq)綜合指數是一項以科技為主的知名指數。總之,我們的主要股價指數背離了真實的經濟,似乎不受六千萬名美國人剛失業和中小型企業幾乎全軍覆沒的影響。
今日的股票不是透過人來交易,它們幾乎全透過機器人。這些機器人被訓練閱讀財務報表、跟隨買賣單並立即採取行動。基本面因素不重要(至少在短期)。如果運算法告訴機器人「跟隨刺激措施買指數」,那麼每次聯準會主席鮑爾(Jay Powelle)公開發言,機器人就買進指數。如果運算法告訴機器人「跟隨更多赤字支出買指數」,每次麥康諾(Mitch McConnelle)和裴洛西(Nancy Pelosi)握手(或碰觸手肘)達成新支出協議,機器人就買進指數。機器人不思考,不分析,而且不展望未來。它們只是遵照指令行事。
最後,現實侵入。即使對機器人來說,破產也是警訊。美國人可能不了解第二波病毒的嚴重性,但他們了解破產。他們可能直接受破產影響;如果你的僱主破產或你的股票變成廢紙,你就能完全了解。即使是不受影響的美國人也感覺到,他們的公司可能很快也會破產。他們可能下個月也會失業,或他們的投資組合將隨著個別的股票暴跌而減損價值。
蕭條不只是統計數字。蕭條是失業和擔心沒有錢繳房租、買餐桌上的食物、尋求醫療照護,和讓孩子受良好教育等個人創傷的可計算總和。失業不只影響你的薪水支票,它們還影響尊嚴、自信和未來的前景。而且蕭條不只是失業。企業遭到摧毀,運氣好的話是虧損。漣漪效應擴大到社區和整個城市。蕭條的衝擊很深,且持續很久;它們可能跨越世代,正如第一次大蕭條的情況。
不過,統計數字可以幫助我們衡量蕭條的深度,作為了解人、企業和社群遭受多大影響的方法。它們也能證明這是一場蕭條,而不是另一波衰退。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並不是有意義的基準。一九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的市場恐慌雖然危及全球金融穩定,卻很快平息,且只直接影響少數人。但這次的蕭條不同,而且數據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
第一、也是最明顯的一點是,超過六千萬名美國人在二○二○年三月一日到十月一日間失業,這些失業者將很快重獲就業的說法是謊言。失業將先是減緩,然後停止。復甦將開始,但這不表示那六千萬名美國人回到工作崗位。每個月增加一百多萬就業人口(以歷史標準來看是個大數字)且持續三年,將不足以讓就業率恢復到二○二○年二月的水準。這項(虛假的)預測還忽略了一個重點,即有許多工作再也沒有恢復。在封鎖期間關門並裁撤二十名員工的餐廳,不會在重新開張時日回僱所有二十名員工。它可能重新僱用十人,並觀望情況的發展。情況很可能不順利。保持社交距離意味餐桌數會減少,被容許進入的客人數受限制。顧客本身因為餘悸猶存而不會全部回流餐廳。當然,這是假設餐廳重新開張;有許多餐廳不會重新開張,而是永遠結束營業。另一方面,未被重新僱用的侍者和酒保會喪失技術和關係,有一些人會離開勞動力,甚至達到雖在技術上不符合政府對失業的定義、但在一般人看法屬於失業的程度。
餐廳的例子是真實的,但只是眾多例子之一。主題標籤#WFH(在家工作)在封鎖期間已變得無所不在。有數百萬人在家工作。僱主發現這個模式運作得比讓員工擠在市區辦公大樓上班還好,除了可以減少後勤成本外,還可節省每年數百萬小時的通勤時間和數百萬美元房租、保險和修繕費用。新的辦公室模式將佔用較少樓層面積、共用的會議室、按日租用的辦公室,和僱用較少的接待員與辦事員。僱主將在辦公室設置儲物櫃供到班人員使用,讓他們下班時把物品置於櫃中。其他時候他們將在家工作。這對僱主是好事。但閒置的辦公室空間、房東的租金、遭裁撤的清潔工、攤販和街頭餐車及餐廳的銷售、空蕩的火車和巴士,以及午餐時間的購物呢?它們全都消失,或減少了八○%。生活將繼續過,但非主要的工作和生產將難以為繼。這是蕭條和衰退的差別。在蕭條時,情況不會恢復正常,因為正常已不復存在。
這不是揣測,而是已經展現在數據的事實。在二○二○年五月,只有三二%的零售商店正常繳房租。其他行業的繳房租比率為:餐廳和酒吧三二%、旅館等住宿業一八%、健身房和運動設施二六%、汽車銷售和服務業二九%、美髮美甲沙龍二五%。其他行業類別的欠繳房租數據也一樣令人驚心。駁斥這些行業都是小企業是罔顧事實。中小型企業佔總就業人口近五○%,創造的產品與勞務總值佔GDP的四五%。以就業和產值來看,它們整體遠比蘋果、微軟、Facebook和Google加起來還重要。欠繳房租意味它們已瀕臨倒閉(最壞的情況),或必須重新協商租約(最好的情況)。這無法靠赤字支出、印鈔票或股市上漲來彌補,它們是痛苦的半永久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