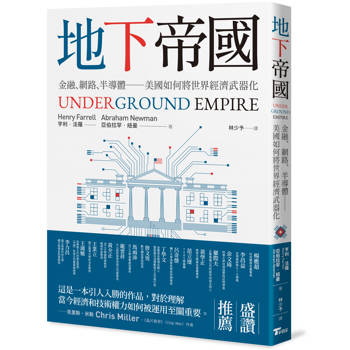〈導言 條條大路通羅馬〉
要進入地下帝國非常容易,到處都有入口,有些甚至設有路標。在我們倆居住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譯註:以下簡稱華盛頓、華府、或華盛頓特區),66號州際公路這條多車道的大動脈連接著美國首都與維吉尼亞州的郊區。這條主要幹道還有一條較小的支路,通往五角大廈及位於蘭利州際公路,連結這個美國首府城市和維吉尼亞州郊區。這條多車道主幹道有一條較小的支道通往五角大廈和位於蘭利社區(Langley)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總部。66號州際公路往東,會先穿過環繞全華府的「環狀線」,再開到底就是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所在地「霧底洞」(Foggy Bottom);美國財政部和白宮就在離國務院不遠的幾個街區外。繼續往東北方向開,就會到達馬里蘭州的米德堡(Fort Meade),這是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和美國網路司令部(Cyber Command)的情報人員和網路專家工作的地方。
這些政府建築是美利堅帝國外在的象徵。有些建築在設計之初就考慮到對大眾展示的目的。白宮和財政部的帕拉迪奧式(Palladian)立面,是根據羅馬建築師、原本在凱撒(Julius Caesar)軍隊中擔任工程官的維特魯威(Vitruvius)發展的原則設計與建造。而其他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則出於實用目的,在圍籬、監視攝影機和武裝警衛後築起另一道防線。
所有的建築物都與地下世界相通。帝國治下每座或為了治理、或為了展示而起造的建築物,要不是靠著密密麻麻的通道和氣送管,像蘑菇的菌絲穿透周圍土壤一樣傳遞資源和訊息,早就變成廢墟了。帝國的脈動是雙向的,他們將資源聚集到中心,同時向外部傳播影響力與施展權力。
古代世界的統治者以斑岩和大理石等珍貴石材建造雄偉的國都,而帝國的運作則更依賴於日常所用之物。貿易路線、糧船和引水道將鄉鎮、城市與農村緊密地編織成一張活躍的經濟網絡。羅馬帝國(Roman Empire)建造了一套廣闊的道路網,不僅便利商人運送貨物,還使軍團能迅速橫跨各行省。當旅人從偏遠的腹地進入羅馬帝國時,他們告別了一個由村莊與蜿蜒牛道構成的世界,迎來的是由貿易城市組成的繁榮帝國。這些城市由筆直而悠長的通衢大道相連,既傳遞商業的繁盛,也傳達統治的力量與威懾。
羅馬帝國衰亡數百年後,一句中世紀諺語仍然流傳:「條條大路通羅馬。」羅馬帝國所建造的基礎設施,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現代經濟。歷史往往因循而行,因為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建設總是較為容易。如今法國和義大利的高速公路,依然沿襲著數千年前羅馬帝國監察官規劃的路線。
到了現代,帝國的核心運作大多已經轉入地下。美利堅帝國依然仰賴軍事力量來維持地表貿易路線的暢通,派遣美國海軍巡弋全球海上航線。然而,美國的權力也隨著埋藏於地下的光纖電纜,迂迴滲入如網際網路和銀行通匯所需的複雜金融基礎設施。全球貿易與製造業在開放市場的旗幟下蓬勃發展,但這開放市場之下,潛藏著一個由智慧財產權與科技專業構築而成、不易察覺的網絡。這又是一個美國領導人擁有無可比擬控制力的典型例證。
這些橫跨全球的系統並非為了取得政治優勢而精心策劃的結果。它們大多由追求效率與利潤的私人企業建造。然而,許多古老的帝國也有類似的模式,它們的軍隊往往亦步亦趨地追隨著商人的腳步前行。
現代帝國已將支持全球市場運作與資訊流通的地下機制──光纖電纜、伺服器農場、金融支付系統,以及生產半導體等複雜產品的製造體系──轉化為脅迫工具。表面上,這些系統和為全球經濟運行所設置的複雜管線,看似既乏味又晦澀難懂。然而,這些管線本身就帶有政治性;正如昔日條條大路通羅馬,如今全球的光纖網路、金融體系和半導體供應鏈都匯向美國,讓美國得以投射其權力與影響力。
的確,如果你想了解這些系統的運作,將它們比作道路會很有幫助。每天早晨,通勤者從他們居住的安靜巷弄出發,轉入更繁忙的街道,然後駛上主幹道。同樣地,每天早晨,人們也進入了地下帝國;他們或打開手機,或登入工作電腦,或者匯款給家人。在不經意間,他們的訊息正透過埋藏於地下的電纜傳送,這些電纜可能連接到全球訊息的主動脈,比如所謂的網際網路骨幹──一條擁有數百萬條車道的高速公路,在這裡,本地與國際的資訊流量不分彼此地交織與傳遞。在這條虛擬高速公路上,美國的汽車車窗上可能貼著與當地相關的標語,比如華盛頓特區的「不讓我們有民代,就別想要我們繳稅」,或是印著「維吉尼亞:情人之州」字樣的車牌。這些汽車在貼有中文、波斯語、法語或俄語標誌的卡車之間穿梭,每輛卡車都奔向自己的目的地。同時,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也正在查看電子郵件、在亞馬遜或其在地競爭對手的網站上購物,或者支付帳單。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使用著同一條網路高速公路。這就像66號州際公路不僅連接華盛頓特區及其周邊的腹地,還無形中蜿蜒穿越北京、安卡拉、巴黎和海參崴等城市,將世界各地全都串連起來。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網路旅人,即使只是在都柏林或基爾庫克(Kirkuk)的不同社區間短途移動,也可能被迫繞道經過華盛頓特區的郊區。當這些不得不繞道的愛爾蘭或庫德族使用者經過國家安全局總部時,該機關可能會拍攝並記錄他們的行蹤,以備美國政府日後查詢他們的身分和去向。若是掛著伊朗車牌的使用者,則可能突然被那些身穿深色西裝、梳理得一絲不苟的財政部幹員攔下盤查。虛擬高速公路上的流量最終可能滲透至實體世界的物流系統。當聯邦政府篩檢網路流量以搜尋資訊時,可能會因為一封電子郵件而查扣一艘從首爾駛往上海、載有先進半導體的貨櫃輪。
二十五年前,前美國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將全球網路的新世界比喻為「資訊高速公路」。他當時也半開玩笑地承認,這個比喻確實並不新穎。高爾之所以採用這個比喻,是希望人們將這些網路視為美國必須投入資金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他雖然反對過度干預的監管,但認為這條「資訊高速公路」仍需要一些交通規則,才能消除瓶頸,並向所有人開放。然而,技術專家們從來不喜歡高爾的這種說法。在他們看來,全球網路應該像網際網路那樣,是由無數網路構成的一個整體,最好是個沒有任何交通警察的狂野天地,讓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其中探索。
如今,網際網路已被馴服。我們回到了一個資訊高速公路的世界,這些高速公路匯流成瓶頸,而美國已將這些瓶頸轉化為控制點,得以監控並主導全球的日常商業與互動往來。這些高速公路承載著全球經濟的流量,支撐著金融服務與生產體系。不出所料,其他國家政府對此相當不滿。有些國家想要建立新的路徑以規避這些瓶頸,有些則希望掌控或建立自己的控制點。這些相互衝突的迫切需求引發了新的紛爭,使跨國企業和個人都陷入交火之中。
一九八九年,我們見證了一個世界秩序戰勝另一個世界秩序的時刻,冷戰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對抗,讓位給了遍布全球的網絡系統。隨著企業利用新獲得的經濟自由,網際網路、全球金融和供應鏈迅速擴張。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政府雖然正處於最脆弱之際,卻意外發現了潛藏於這個新全球經濟體系基礎架構中的政治權力。
一開始,美國試圖利用這項網絡監控能力來對付「壞人」。相關機關和官僚體系專注於應對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的即時威脅,卻未曾預料到,他們所使用的監控權力會如何改變美國與歐洲盟友、競爭對手如中國,以及全球商業界的關係。官員們也未意識到網絡技術的誘惑有多強大:它不僅能用來對付惡徒,還可以用來控制那些早已接受相互依存作為市場效率基石的盟友。為了保護美國,華府逐步且堅定地將蓬勃發展的經濟網絡轉化為宰制的工具。美國如同夢遊般踏入了一場新的帝國爭霸,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墮落。
讀完這本書,你將了解這個地下霸權體系是如何形成的。一個原本開放的網路世界,如何演變成掌握絕對權力的地下帝國,讓美國得以跨越國界擴張影響力,藉此蒐集情報、攔截物資,甚至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更重要的是,本書將幫助你了解當前的局勢,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中國等強權國家,或歐盟等政治實體,將如何自保與反制?若其他勢力試圖建立並擴張自己的地下勢力範圍,會引發什麼後果?而當你的企業身陷其中,又該如何自保?
如今,無論是美國政府官員、外國領導人,還是企業執行長們,都首次開始深入思考已經發生的一切,以及未來的走向。我們將向您說明如何最有效地管理新興帝國之間即將爆發的爭端,並探討如何將帝國的工具運用於其他目標,例如關閉避稅天堂,或協助建立應對氣候變遷的架構。然而,我們無法也不會提供地下帝國的可信逃生路線,因為這並非我們能力所及。進入地下帝國或許輕而易舉,但要脫身卻遠非易事。
* * *
為什麼一個由開放全球網絡構成的世界,會與美國帝國如此契合?有些人認為答案很簡單:帝國和全球網絡是同一個龐大而複雜陰謀的不同階段,這個陰謀在過去數十年中逐步展開。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聲稱,網際網路是一個「中央情報局的計畫」,目的是通過削弱俄羅斯和其他專制國家來增強美國的權力。他似乎認為冷戰從未結束,只是從核對抗陰影下的權力遊戲,演變成半祕密的資訊戰,這場戰爭是透過那些經過精心設計、可作為武器使用的網絡來進行的。
建造這個新世界的人們卻抱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們宣稱,新世界終結了國家之間傳統的地緣政治角力。新時代的傳道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一九九九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個被「圍牆」分隔的舊世界,已經讓位給一個由「網絡」連結的新世界。當時,全球資訊網還是個嶄新的事物,充滿令人振奮的可能性。它成為後冷戰時期世界經濟轉型的一個簡明縮影。像網際網路這樣的資訊網絡,將大量資訊如潮水般跨越國界,隨著企業在各國找到客戶與供應商,新的全球市場逐漸形成。金融網絡的擴張,使資金能夠迅速在全球流動,尋找轉瞬即逝的套利機會或長期投資標的。全球貿易不再只是原材料與製成品的交換,而是轉變為一個錯綜複雜、去中心化的工廠體系:複雜的產品可以在一個國家設計,然後在另一個國家組裝,所需的零組件則來自全球各地。世界,現在是平的。
理論上,在這個新的全球秩序中,資訊將能自由流動,甚至能抵抗最堅決的獨裁者。前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曾告訴中國,試圖控制資訊就像試圖把果凍(Jell-O)釘在牆上一樣──果凍只要左搖右晃地繞過障礙就可以逃脫。政府將不再能控制資金流動;相反地,資金流動將控制政府,因為主權信用評級的變化會讓政客畏縮不前。柯林頓的顧問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曾戲言,他希望下輩子能轉生成為債券市場,這樣他就能「恐嚇所有人」。而佛里曼則認為,在供應鏈全球化的時代,沒有人會想發動戰爭,因為攻擊鄰國無異於打擊自己的經濟。在他看來,這個新世界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市場,而非一個帝國;在這樣的市場中,帝國的概念已顯得無關緊要,甚至過於陳舊。
真相遠比普丁眼中充滿陰謀的世界,或佛里曼筆下的二維平面世界更有趣,也更複雜。若非冷戰結束,全球網絡建設的黃金時代便無法啟動。在一個分裂為互不信任的權力集團的世界中,國家間絕不會容許網絡將它們的經濟體系緊密交織。更重要的是,這些網絡並非由美國政府建造。根據當時的普遍共識,政府官員認為,他們的職責是避免干預私營企業的發展,而這些企業幾乎清一色是美國企業,或將美國視為其主要市場。
與以往的歷史時刻一樣,打造網絡的是企業和企業財團,它們追求的是利潤與效率,而非征服。有政治抱負的人往往更傾向於削弱,而非維持帝國;他們希望打造的是一個網絡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與私人組織能夠自由連結,至於是否符合政府的意願,完全不在考量之列。
然而,這些原本應該瓦解舊有權力政治世界的網絡,卻始終無法擺脫美國冷戰帝國的陰影。具有歷史視野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經常提到「路徑依賴」這一現象,即早期的決定(如城市選址、憲法內容的制定)如何制約了我們今天的行動。全球經濟的新網絡在最直接的意義上展現了路徑依賴的特性。正如中世紀的築路者一樣,這些網絡的建構者通常發現,在舊有基礎上鋪設新路徑更加便利。他們建設完成後,其他人接續其上擴展,更多人再在此基礎上繼續建設,最終形成一個持續累積的過程。這使得他們所建立的路徑沿著舊有的權力脈絡延伸,最終連接到二戰後舊帝國的核心──美利堅合眾國的實體領土。
所謂「沒有帝國的世界」卻顯得異常熟悉。即使沒有任何宏大的規劃,這幅地圖已足以反映並鞏固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將世界連結起來的網絡,不僅沿襲了過去經濟與政治權力關係的輪廓,更定格了一個歷史瞬間―那是美國處於權力巔峰並居於世界中心的短暫時期,從而使這一影響力延續了數十年。
以連接全球通訊系統的海底和地下電纜為例。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估計,到二○○二年,全球各地區之間的網路通訊頻寬中,僅有不到百分之一未經美國傳輸。支撐全球銀行間通訊的系統雖然設於比利時,但其董事會由美國銀行主導,並受其位於維吉尼亞州北部數據中心的管制。國際銀行以美元進行跨國交易,這使它們依賴於「美元清算系統」──由美國監管機關掌控的一套複雜金融安排。即便複雜半導體的製造已從美國轉移至亞洲,美國公司仍將半導體設計和核心智慧財產權的關鍵環節保留在國內。
全球化的管道和運作系統不僅將權力輸送至中心,同時也讓中心變得更加脆弱,易於遭受攻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讓美國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去中心化的通訊系統使恐怖分子能更輕鬆地相互聯繫,而開放的全球金融體系則使他們得以在無人察覺且無人阻止的情況下,將資金與資源自由跨境轉移。
然而,只要美國有意改變現狀,方法可謂俯拾即是。關鍵的全球網路都以美國為中心運作,這使得美國國安局、財政部等機關得以將這些更廣大的網路系統轉為己用。全球經濟仰賴一個早已建成的隧道與管道系統,美國幾乎可以輕而易舉地接管並改造這些系統,如同它們原本就是由軍事工程師專門為此目的設計的一般。通過掌控關鍵節點,美國政府可以祕密監聽對手之間的對話,或將他們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使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一開始,美國政府只是見機行事地、零星地利用這些網路和管道。官員認為,他們的行動是為了應對迫在眉睫的威脅,而非刻意為新型態權力奠定基礎。當美國部署這種力量時,目標是恐怖組織如蓋達,以及朋友寥寥且具有敵對性的國家如北韓。美國的一些行動雖然引發爭議,但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實施新監視技術背後對總統權力的廣泛解釋,二是這些措施對美國公民民權造成的附帶損害。
然而,政府也可能順著既有路徑前行,卻對這些路徑通向何方毫無預期。一旦部門機關開發出新工具,就會不斷尋找新用途。每當發現一種新用途,就可能為其他用途開創先例。而官僚一旦嚐到權力的滋味,就會愛上這種感覺。
要進入地下帝國非常容易,到處都有入口,有些甚至設有路標。在我們倆居住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譯註:以下簡稱華盛頓、華府、或華盛頓特區),66號州際公路這條多車道的大動脈連接著美國首都與維吉尼亞州的郊區。這條主要幹道還有一條較小的支路,通往五角大廈及位於蘭利州際公路,連結這個美國首府城市和維吉尼亞州郊區。這條多車道主幹道有一條較小的支道通往五角大廈和位於蘭利社區(Langley)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總部。66號州際公路往東,會先穿過環繞全華府的「環狀線」,再開到底就是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所在地「霧底洞」(Foggy Bottom);美國財政部和白宮就在離國務院不遠的幾個街區外。繼續往東北方向開,就會到達馬里蘭州的米德堡(Fort Meade),這是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和美國網路司令部(Cyber Command)的情報人員和網路專家工作的地方。
這些政府建築是美利堅帝國外在的象徵。有些建築在設計之初就考慮到對大眾展示的目的。白宮和財政部的帕拉迪奧式(Palladian)立面,是根據羅馬建築師、原本在凱撒(Julius Caesar)軍隊中擔任工程官的維特魯威(Vitruvius)發展的原則設計與建造。而其他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則出於實用目的,在圍籬、監視攝影機和武裝警衛後築起另一道防線。
所有的建築物都與地下世界相通。帝國治下每座或為了治理、或為了展示而起造的建築物,要不是靠著密密麻麻的通道和氣送管,像蘑菇的菌絲穿透周圍土壤一樣傳遞資源和訊息,早就變成廢墟了。帝國的脈動是雙向的,他們將資源聚集到中心,同時向外部傳播影響力與施展權力。
古代世界的統治者以斑岩和大理石等珍貴石材建造雄偉的國都,而帝國的運作則更依賴於日常所用之物。貿易路線、糧船和引水道將鄉鎮、城市與農村緊密地編織成一張活躍的經濟網絡。羅馬帝國(Roman Empire)建造了一套廣闊的道路網,不僅便利商人運送貨物,還使軍團能迅速橫跨各行省。當旅人從偏遠的腹地進入羅馬帝國時,他們告別了一個由村莊與蜿蜒牛道構成的世界,迎來的是由貿易城市組成的繁榮帝國。這些城市由筆直而悠長的通衢大道相連,既傳遞商業的繁盛,也傳達統治的力量與威懾。
羅馬帝國衰亡數百年後,一句中世紀諺語仍然流傳:「條條大路通羅馬。」羅馬帝國所建造的基礎設施,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現代經濟。歷史往往因循而行,因為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建設總是較為容易。如今法國和義大利的高速公路,依然沿襲著數千年前羅馬帝國監察官規劃的路線。
到了現代,帝國的核心運作大多已經轉入地下。美利堅帝國依然仰賴軍事力量來維持地表貿易路線的暢通,派遣美國海軍巡弋全球海上航線。然而,美國的權力也隨著埋藏於地下的光纖電纜,迂迴滲入如網際網路和銀行通匯所需的複雜金融基礎設施。全球貿易與製造業在開放市場的旗幟下蓬勃發展,但這開放市場之下,潛藏著一個由智慧財產權與科技專業構築而成、不易察覺的網絡。這又是一個美國領導人擁有無可比擬控制力的典型例證。
這些橫跨全球的系統並非為了取得政治優勢而精心策劃的結果。它們大多由追求效率與利潤的私人企業建造。然而,許多古老的帝國也有類似的模式,它們的軍隊往往亦步亦趨地追隨著商人的腳步前行。
現代帝國已將支持全球市場運作與資訊流通的地下機制──光纖電纜、伺服器農場、金融支付系統,以及生產半導體等複雜產品的製造體系──轉化為脅迫工具。表面上,這些系統和為全球經濟運行所設置的複雜管線,看似既乏味又晦澀難懂。然而,這些管線本身就帶有政治性;正如昔日條條大路通羅馬,如今全球的光纖網路、金融體系和半導體供應鏈都匯向美國,讓美國得以投射其權力與影響力。
的確,如果你想了解這些系統的運作,將它們比作道路會很有幫助。每天早晨,通勤者從他們居住的安靜巷弄出發,轉入更繁忙的街道,然後駛上主幹道。同樣地,每天早晨,人們也進入了地下帝國;他們或打開手機,或登入工作電腦,或者匯款給家人。在不經意間,他們的訊息正透過埋藏於地下的電纜傳送,這些電纜可能連接到全球訊息的主動脈,比如所謂的網際網路骨幹──一條擁有數百萬條車道的高速公路,在這裡,本地與國際的資訊流量不分彼此地交織與傳遞。在這條虛擬高速公路上,美國的汽車車窗上可能貼著與當地相關的標語,比如華盛頓特區的「不讓我們有民代,就別想要我們繳稅」,或是印著「維吉尼亞:情人之州」字樣的車牌。這些汽車在貼有中文、波斯語、法語或俄語標誌的卡車之間穿梭,每輛卡車都奔向自己的目的地。同時,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也正在查看電子郵件、在亞馬遜或其在地競爭對手的網站上購物,或者支付帳單。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使用著同一條網路高速公路。這就像66號州際公路不僅連接華盛頓特區及其周邊的腹地,還無形中蜿蜒穿越北京、安卡拉、巴黎和海參崴等城市,將世界各地全都串連起來。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網路旅人,即使只是在都柏林或基爾庫克(Kirkuk)的不同社區間短途移動,也可能被迫繞道經過華盛頓特區的郊區。當這些不得不繞道的愛爾蘭或庫德族使用者經過國家安全局總部時,該機關可能會拍攝並記錄他們的行蹤,以備美國政府日後查詢他們的身分和去向。若是掛著伊朗車牌的使用者,則可能突然被那些身穿深色西裝、梳理得一絲不苟的財政部幹員攔下盤查。虛擬高速公路上的流量最終可能滲透至實體世界的物流系統。當聯邦政府篩檢網路流量以搜尋資訊時,可能會因為一封電子郵件而查扣一艘從首爾駛往上海、載有先進半導體的貨櫃輪。
二十五年前,前美國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將全球網路的新世界比喻為「資訊高速公路」。他當時也半開玩笑地承認,這個比喻確實並不新穎。高爾之所以採用這個比喻,是希望人們將這些網路視為美國必須投入資金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他雖然反對過度干預的監管,但認為這條「資訊高速公路」仍需要一些交通規則,才能消除瓶頸,並向所有人開放。然而,技術專家們從來不喜歡高爾的這種說法。在他們看來,全球網路應該像網際網路那樣,是由無數網路構成的一個整體,最好是個沒有任何交通警察的狂野天地,讓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其中探索。
如今,網際網路已被馴服。我們回到了一個資訊高速公路的世界,這些高速公路匯流成瓶頸,而美國已將這些瓶頸轉化為控制點,得以監控並主導全球的日常商業與互動往來。這些高速公路承載著全球經濟的流量,支撐著金融服務與生產體系。不出所料,其他國家政府對此相當不滿。有些國家想要建立新的路徑以規避這些瓶頸,有些則希望掌控或建立自己的控制點。這些相互衝突的迫切需求引發了新的紛爭,使跨國企業和個人都陷入交火之中。
一九八九年,我們見證了一個世界秩序戰勝另一個世界秩序的時刻,冷戰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對抗,讓位給了遍布全球的網絡系統。隨著企業利用新獲得的經濟自由,網際網路、全球金融和供應鏈迅速擴張。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政府雖然正處於最脆弱之際,卻意外發現了潛藏於這個新全球經濟體系基礎架構中的政治權力。
一開始,美國試圖利用這項網絡監控能力來對付「壞人」。相關機關和官僚體系專注於應對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的即時威脅,卻未曾預料到,他們所使用的監控權力會如何改變美國與歐洲盟友、競爭對手如中國,以及全球商業界的關係。官員們也未意識到網絡技術的誘惑有多強大:它不僅能用來對付惡徒,還可以用來控制那些早已接受相互依存作為市場效率基石的盟友。為了保護美國,華府逐步且堅定地將蓬勃發展的經濟網絡轉化為宰制的工具。美國如同夢遊般踏入了一場新的帝國爭霸,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墮落。
讀完這本書,你將了解這個地下霸權體系是如何形成的。一個原本開放的網路世界,如何演變成掌握絕對權力的地下帝國,讓美國得以跨越國界擴張影響力,藉此蒐集情報、攔截物資,甚至將某些國家排除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更重要的是,本書將幫助你了解當前的局勢,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中國等強權國家,或歐盟等政治實體,將如何自保與反制?若其他勢力試圖建立並擴張自己的地下勢力範圍,會引發什麼後果?而當你的企業身陷其中,又該如何自保?
如今,無論是美國政府官員、外國領導人,還是企業執行長們,都首次開始深入思考已經發生的一切,以及未來的走向。我們將向您說明如何最有效地管理新興帝國之間即將爆發的爭端,並探討如何將帝國的工具運用於其他目標,例如關閉避稅天堂,或協助建立應對氣候變遷的架構。然而,我們無法也不會提供地下帝國的可信逃生路線,因為這並非我們能力所及。進入地下帝國或許輕而易舉,但要脫身卻遠非易事。
* * *
為什麼一個由開放全球網絡構成的世界,會與美國帝國如此契合?有些人認為答案很簡單:帝國和全球網絡是同一個龐大而複雜陰謀的不同階段,這個陰謀在過去數十年中逐步展開。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聲稱,網際網路是一個「中央情報局的計畫」,目的是通過削弱俄羅斯和其他專制國家來增強美國的權力。他似乎認為冷戰從未結束,只是從核對抗陰影下的權力遊戲,演變成半祕密的資訊戰,這場戰爭是透過那些經過精心設計、可作為武器使用的網絡來進行的。
建造這個新世界的人們卻抱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們宣稱,新世界終結了國家之間傳統的地緣政治角力。新時代的傳道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一九九九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個被「圍牆」分隔的舊世界,已經讓位給一個由「網絡」連結的新世界。當時,全球資訊網還是個嶄新的事物,充滿令人振奮的可能性。它成為後冷戰時期世界經濟轉型的一個簡明縮影。像網際網路這樣的資訊網絡,將大量資訊如潮水般跨越國界,隨著企業在各國找到客戶與供應商,新的全球市場逐漸形成。金融網絡的擴張,使資金能夠迅速在全球流動,尋找轉瞬即逝的套利機會或長期投資標的。全球貿易不再只是原材料與製成品的交換,而是轉變為一個錯綜複雜、去中心化的工廠體系:複雜的產品可以在一個國家設計,然後在另一個國家組裝,所需的零組件則來自全球各地。世界,現在是平的。
理論上,在這個新的全球秩序中,資訊將能自由流動,甚至能抵抗最堅決的獨裁者。前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曾告訴中國,試圖控制資訊就像試圖把果凍(Jell-O)釘在牆上一樣──果凍只要左搖右晃地繞過障礙就可以逃脫。政府將不再能控制資金流動;相反地,資金流動將控制政府,因為主權信用評級的變化會讓政客畏縮不前。柯林頓的顧問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曾戲言,他希望下輩子能轉生成為債券市場,這樣他就能「恐嚇所有人」。而佛里曼則認為,在供應鏈全球化的時代,沒有人會想發動戰爭,因為攻擊鄰國無異於打擊自己的經濟。在他看來,這個新世界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市場,而非一個帝國;在這樣的市場中,帝國的概念已顯得無關緊要,甚至過於陳舊。
真相遠比普丁眼中充滿陰謀的世界,或佛里曼筆下的二維平面世界更有趣,也更複雜。若非冷戰結束,全球網絡建設的黃金時代便無法啟動。在一個分裂為互不信任的權力集團的世界中,國家間絕不會容許網絡將它們的經濟體系緊密交織。更重要的是,這些網絡並非由美國政府建造。根據當時的普遍共識,政府官員認為,他們的職責是避免干預私營企業的發展,而這些企業幾乎清一色是美國企業,或將美國視為其主要市場。
與以往的歷史時刻一樣,打造網絡的是企業和企業財團,它們追求的是利潤與效率,而非征服。有政治抱負的人往往更傾向於削弱,而非維持帝國;他們希望打造的是一個網絡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與私人組織能夠自由連結,至於是否符合政府的意願,完全不在考量之列。
然而,這些原本應該瓦解舊有權力政治世界的網絡,卻始終無法擺脫美國冷戰帝國的陰影。具有歷史視野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經常提到「路徑依賴」這一現象,即早期的決定(如城市選址、憲法內容的制定)如何制約了我們今天的行動。全球經濟的新網絡在最直接的意義上展現了路徑依賴的特性。正如中世紀的築路者一樣,這些網絡的建構者通常發現,在舊有基礎上鋪設新路徑更加便利。他們建設完成後,其他人接續其上擴展,更多人再在此基礎上繼續建設,最終形成一個持續累積的過程。這使得他們所建立的路徑沿著舊有的權力脈絡延伸,最終連接到二戰後舊帝國的核心──美利堅合眾國的實體領土。
所謂「沒有帝國的世界」卻顯得異常熟悉。即使沒有任何宏大的規劃,這幅地圖已足以反映並鞏固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將世界連結起來的網絡,不僅沿襲了過去經濟與政治權力關係的輪廓,更定格了一個歷史瞬間―那是美國處於權力巔峰並居於世界中心的短暫時期,從而使這一影響力延續了數十年。
以連接全球通訊系統的海底和地下電纜為例。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估計,到二○○二年,全球各地區之間的網路通訊頻寬中,僅有不到百分之一未經美國傳輸。支撐全球銀行間通訊的系統雖然設於比利時,但其董事會由美國銀行主導,並受其位於維吉尼亞州北部數據中心的管制。國際銀行以美元進行跨國交易,這使它們依賴於「美元清算系統」──由美國監管機關掌控的一套複雜金融安排。即便複雜半導體的製造已從美國轉移至亞洲,美國公司仍將半導體設計和核心智慧財產權的關鍵環節保留在國內。
全球化的管道和運作系統不僅將權力輸送至中心,同時也讓中心變得更加脆弱,易於遭受攻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讓美國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去中心化的通訊系統使恐怖分子能更輕鬆地相互聯繫,而開放的全球金融體系則使他們得以在無人察覺且無人阻止的情況下,將資金與資源自由跨境轉移。
然而,只要美國有意改變現狀,方法可謂俯拾即是。關鍵的全球網路都以美國為中心運作,這使得美國國安局、財政部等機關得以將這些更廣大的網路系統轉為己用。全球經濟仰賴一個早已建成的隧道與管道系統,美國幾乎可以輕而易舉地接管並改造這些系統,如同它們原本就是由軍事工程師專門為此目的設計的一般。通過掌控關鍵節點,美國政府可以祕密監聽對手之間的對話,或將他們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使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一開始,美國政府只是見機行事地、零星地利用這些網路和管道。官員認為,他們的行動是為了應對迫在眉睫的威脅,而非刻意為新型態權力奠定基礎。當美國部署這種力量時,目標是恐怖組織如蓋達,以及朋友寥寥且具有敵對性的國家如北韓。美國的一些行動雖然引發爭議,但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實施新監視技術背後對總統權力的廣泛解釋,二是這些措施對美國公民民權造成的附帶損害。
然而,政府也可能順著既有路徑前行,卻對這些路徑通向何方毫無預期。一旦部門機關開發出新工具,就會不斷尋找新用途。每當發現一種新用途,就可能為其他用途開創先例。而官僚一旦嚐到權力的滋味,就會愛上這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