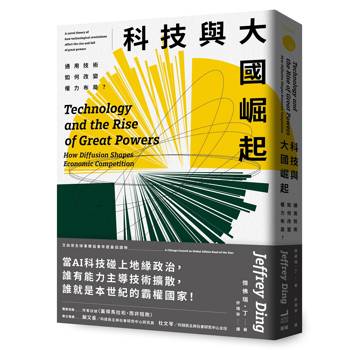二〇一八年七月,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在約翰尼斯堡召開會議,會議主題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共謀包容增長和共同繁榮」。這個主題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比較具體。金磚五國合共約占世界四十%的人口和二十五%的經濟產出, 它們過去的峰會用過一些含糊的口號,例如「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闢更加光明未來」和「展望未來、共享繁榮」。除了二〇一八年的峰會主題,金磚五國領袖在這次會議上的談話內容,也突顯他們確信世界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技術變革──重要到值得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整個會議期間,這五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領袖宣稱,現行技術轉型是加快經濟成長的難得機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另外四國的領袖致辭時,闡述了此一想法的歷史意義:從十八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十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二十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資訊化,一輪又一輪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習近平談到最近人工智慧(AI)之類的先進技術正在不斷突破,並且表示:「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雖然那次金磚五國峰會沒有明確討論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如何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習近平這番話的涵義已悄然浮現。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中國的分析師和學者深入討論習近平談話內容,尤其是他提到的顛覆性技術創新與全球領導地位轉變之間的關聯。 中國共產黨權威刊物《學習時報》網站發表了一篇關於習近平演講的評論,詳述以往科技革命的地緣政治結果:「英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先機,確立了引領世界發展的生產力優勢……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美國從英國手中奪得先進生產力主導權。」 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在分析習近平的談話時表示,中國比美國更有機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勝出。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主要思想家對技術革命可能導致權力移轉的想法也有共鳴。拜登總統在上任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上強調,美國必須在新興技術的競爭中「掌握未來」,他並矢言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目標「不會在他任內實現」。 二〇一八年,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這個有影響力的機構召集主要政府官員、技術專家和社會科學家,研究AI對國家安全的影響。NSCAI的最終報告長達七百五十六頁,將AI的潛在影響與過去的重要技術如電力相提並論,警告美國若不為「AI革命」做好充分準備,其科技領導地位很快將被中國取代。
這些籠統的敘事高度關注矽谷或北京中關村的最新技術進步,但忽略了新興技術如何影響權力移轉。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的興衰?過去幾次工業革命塑造全球權力格局的方式,是否存在某種可辨識的模式?如果這種模式真的存在,又將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美中技術競爭?
關於技術變革驅動權力移轉的傳統觀念
國際關係學者早就觀察到顛覆性技術突破與大國興衰的關係。 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言,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涉及國家之間出現「經濟成長率和技術變革的差異,使得全球經濟格局隨之改變,進而逐漸影響政治和軍事格局。」 但是,一如現在人們對新技術如何影響美中權力格局的揣測,國際關係文獻基本上沒有解釋技術變革如何創造讓大國獨領風騷的條件。學術界仔細研究了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影響大國的全球軍事和政治霸權,但仍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甘迺迪因果鏈中的起始點:技術變革與大國之間長期成長率差異的關聯。
在那些真的審視技術變革如何影響經濟權力移轉的研究中,標準的解釋強調在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也就是俗稱的「領頭羊產業」(leading sectors)掌控了關鍵技術創新。根據這種邏輯,英國當年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生產力最強的經濟體是,因為它掌控改變其蓬勃發展的紡織業的新技術,例如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紡織機(spinning jenny)。同樣道理,德國掌握了化學工業的重大技術突破,是它後來能夠挑戰英國經濟強權的關鍵原因。從歷史分析基礎切入,領頭羊產業論認為,在重大技術變革期間,全球經濟權力的天平會傾向「最先引進最重要創新的國家」。
領頭羊產業創造的利益為什麼會主要由某些國家獲得?各方解釋不盡相同,但多數強調國內制度是否契合顛覆型技術的需求。在一般層面上,有些學者認為,新興強國之所以能夠快速適應新的領頭羊產業,是因為它們不像比較成熟的強國那樣,受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束縛。 另一些學者比較重視特定因素,例如政府的集權程度和產業治理安排。 所有這些觀點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聚焦於使一個國家能夠率先在新興產業取得重大突破的制度。例如在英國崛起這個例子中,許多有影響力的歷史敘事都強調英國支持「英雄」發明家的制度。 同樣地,關於德國領頭羊產業成功的敘事,也將鎂光燈打在德國對科學教育與工業研究實驗室的投資。
領頭羊產業模型的籠統論述,深刻影響了學術和政策制定圈子。在界定了相關領域的一些文本,包括羅伯.吉爾平(Robert Gilpin)和保羅.甘迺迪的著作中,便用了領頭羊產業模型來描繪大國興衰。 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在一篇回顧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的文章中,概括了他們的結論:「歷史上,大國是藉由近乎壟斷領頭羊產業的創新而獲得霸權地位。」
領頭羊產業論也啟發了中國挑戰美國科技領導地位的當代爭論。在關於中國可以如何利用新一輪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一場演講中,習近平呼籲中國發展成「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另一方面,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面對中國在AI等新興技術領域實力日增的情況,也認為相關競爭的關鍵在於哪一個國家能夠在新的領頭羊產業革命性突破。
是誰先做到的?哪個國家先創新的?我們看到令人驚嘆的技術突破時,傾向將焦點放在最初的驚喜發現,而這非常自然。一如習近平在金磚五國峰會的演講,現在的領袖提起過去的工業革命時,會訴諸同樣聚焦於創新時刻、關於技術進步的歷史敘事。 經濟學家暨歷史學家內森.羅森柏格(Nathan Rosenberg)這麼診斷這些以創新為中心的觀點:「新技術被採用和融入生產過程的速度受到的關注少得多,甚至完全遭忽視。事實上,新技術擴散過程往往被當成不存在。」 但是,如果沒有卑微的技術擴散工作,即使是最了不起的進步也無關緊要。
認真考慮擴散問題,就會對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興衰提出不同的解釋。以擴散為中心的框架會探討,當圍繞著創新的炒作過去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它不大關心哪個國家率先引入重大創新,而是將重點放在為什麼有些國家在適應和大規模應用新技術的成就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正如下一節所概述,此一替代理論指引了一條關鍵,也就是在技術變革時期支撐大國領導地位、與眾不同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那些讓與基礎技術有關的工程技能和知識基礎得以普及的制度。
在整個會議期間,這五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的領袖宣稱,現行技術轉型是加快經濟成長的難得機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另外四國的領袖致辭時,闡述了此一想法的歷史意義:從十八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十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二十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資訊化,一輪又一輪的顛覆性技術創新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習近平談到最近人工智慧(AI)之類的先進技術正在不斷突破,並且表示:「如今,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雖然那次金磚五國峰會沒有明確討論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如何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習近平這番話的涵義已悄然浮現。在接下來幾個月裡,中國的分析師和學者深入討論習近平談話內容,尤其是他提到的顛覆性技術創新與全球領導地位轉變之間的關聯。 中國共產黨權威刊物《學習時報》網站發表了一篇關於習近平演講的評論,詳述以往科技革命的地緣政治結果:「英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先機,確立了引領世界發展的生產力優勢……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美國從英國手中奪得先進生產力主導權。」 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在分析習近平的談話時表示,中國比美國更有機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勝出。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主要思想家對技術革命可能導致權力移轉的想法也有共鳴。拜登總統在上任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上強調,美國必須在新興技術的競爭中「掌握未來」,他並矢言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目標「不會在他任內實現」。 二〇一八年,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這個有影響力的機構召集主要政府官員、技術專家和社會科學家,研究AI對國家安全的影響。NSCAI的最終報告長達七百五十六頁,將AI的潛在影響與過去的重要技術如電力相提並論,警告美國若不為「AI革命」做好充分準備,其科技領導地位很快將被中國取代。
這些籠統的敘事高度關注矽谷或北京中關村的最新技術進步,但忽略了新興技術如何影響權力移轉。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的興衰?過去幾次工業革命塑造全球權力格局的方式,是否存在某種可辨識的模式?如果這種模式真的存在,又將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美中技術競爭?
關於技術變革驅動權力移轉的傳統觀念
國際關係學者早就觀察到顛覆性技術突破與大國興衰的關係。 正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言,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涉及國家之間出現「經濟成長率和技術變革的差異,使得全球經濟格局隨之改變,進而逐漸影響政治和軍事格局。」 但是,一如現在人們對新技術如何影響美中權力格局的揣測,國際關係文獻基本上沒有解釋技術變革如何創造讓大國獨領風騷的條件。學術界仔細研究了經濟格局的變化如何影響大國的全球軍事和政治霸權,但仍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甘迺迪因果鏈中的起始點:技術變革與大國之間長期成長率差異的關聯。
在那些真的審視技術變革如何影響經濟權力移轉的研究中,標準的解釋強調在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也就是俗稱的「領頭羊產業」(leading sectors)掌控了關鍵技術創新。根據這種邏輯,英國當年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生產力最強的經濟體是,因為它掌控改變其蓬勃發展的紡織業的新技術,例如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紡織機(spinning jenny)。同樣道理,德國掌握了化學工業的重大技術突破,是它後來能夠挑戰英國經濟強權的關鍵原因。從歷史分析基礎切入,領頭羊產業論認為,在重大技術變革期間,全球經濟權力的天平會傾向「最先引進最重要創新的國家」。
領頭羊產業創造的利益為什麼會主要由某些國家獲得?各方解釋不盡相同,但多數強調國內制度是否契合顛覆型技術的需求。在一般層面上,有些學者認為,新興強國之所以能夠快速適應新的領頭羊產業,是因為它們不像比較成熟的強國那樣,受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束縛。 另一些學者比較重視特定因素,例如政府的集權程度和產業治理安排。 所有這些觀點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聚焦於使一個國家能夠率先在新興產業取得重大突破的制度。例如在英國崛起這個例子中,許多有影響力的歷史敘事都強調英國支持「英雄」發明家的制度。 同樣地,關於德國領頭羊產業成功的敘事,也將鎂光燈打在德國對科學教育與工業研究實驗室的投資。
領頭羊產業模型的籠統論述,深刻影響了學術和政策制定圈子。在界定了相關領域的一些文本,包括羅伯.吉爾平(Robert Gilpin)和保羅.甘迺迪的著作中,便用了領頭羊產業模型來描繪大國興衰。 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在一篇回顧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的文章中,概括了他們的結論:「歷史上,大國是藉由近乎壟斷領頭羊產業的創新而獲得霸權地位。」
領頭羊產業論也啟發了中國挑戰美國科技領導地位的當代爭論。在關於中國可以如何利用新一輪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一場演講中,習近平呼籲中國發展成「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另一方面,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面對中國在AI等新興技術領域實力日增的情況,也認為相關競爭的關鍵在於哪一個國家能夠在新的領頭羊產業革命性突破。
是誰先做到的?哪個國家先創新的?我們看到令人驚嘆的技術突破時,傾向將焦點放在最初的驚喜發現,而這非常自然。一如習近平在金磚五國峰會的演講,現在的領袖提起過去的工業革命時,會訴諸同樣聚焦於創新時刻、關於技術進步的歷史敘事。 經濟學家暨歷史學家內森.羅森柏格(Nathan Rosenberg)這麼診斷這些以創新為中心的觀點:「新技術被採用和融入生產過程的速度受到的關注少得多,甚至完全遭忽視。事實上,新技術擴散過程往往被當成不存在。」 但是,如果沒有卑微的技術擴散工作,即使是最了不起的進步也無關緊要。
認真考慮擴散問題,就會對技術革命如何影響大國興衰提出不同的解釋。以擴散為中心的框架會探討,當圍繞著創新的炒作過去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它不大關心哪個國家率先引入重大創新,而是將重點放在為什麼有些國家在適應和大規模應用新技術的成就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正如下一節所概述,此一替代理論指引了一條關鍵,也就是在技術變革時期支撐大國領導地位、與眾不同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那些讓與基礎技術有關的工程技能和知識基礎得以普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