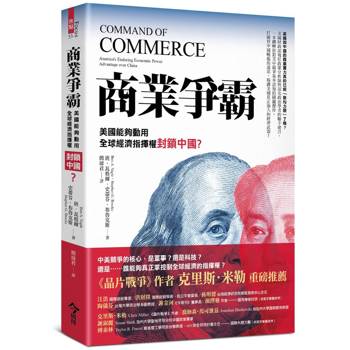第2章 衡量全球商業實力的分布
跨國企業(MNCs)是理解美國與中國之間經濟實力平衡的關鍵。像是蘋果(Apple)、豐田(Toyota)、富士康(Foxconn)、拜耳(Bayer)、阿里巴巴 (Alibaba)、三星(Samsung)等跨國公司,主導著全球供應鏈,並且是商業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2016年汽車、化學品、電子設備及電腦的出口中,超過70%是由跨國公司所製造。早在二十世紀末,公司內部貿易(即一家公司不同部門間的跨境交易)與國際代工(即一家公司向外國供應商採購零組件)的合計價值,估計已占全球貿易額約三分之二。現今,全球商業活動的主體,絕大多數只是跨國公司決定在哪裡以及如何組織其生產活動的副產品而已。
由於跨國企業是經濟實力的重要來源,我們分析美中經濟實力平衡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哪些全球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及其總部所在地。正如我們所指出,美國擁有商業爭權能力:它擁有全球大多數頂尖企業。儘管美國整體商業實力強大,但這種優勢在高科技產業尤其突出,而這些產業正是當前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此外,在這些關鍵產業中,美國的盟友還控制了剩餘產能的絕大部分。
本章架構安排如下。首先,我們說明分析商業實力分布的測量方法。其次,運用全球數千家最具價值企業的資料,比較美國、其盟友與中國的商業實力;我們發現美國及其盟邦無論在整體利潤創造或大多數產業部門都處於領先地位。第三,我們將企業部門分為四大類別──自然資源、金融與商業服務、消費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並測量這些類別的商業實力分布,結果顯示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尤其具有壓倒性優勢。我們也指出,來自美國盟邦的企業構成了其他領先企業的絕大部分。
本章接下來的內容將闡明,這種商業實力分布的失衡結構,如何成為美國藉由切斷目標國與全球企業生產體系的連結來實施制裁的基礎。我們首先分析高科技產業為何在當今地緣政治中具有關鍵性地位,以及任何國家若僅依賴本土企業,為何難以在這些產業持續保持技術領先優勢。接著我們具體說明美國如何運用其影響力,迫使企業配合其外交政策目標──事實上,美國過去已多次採取此類行動。
在本章最後部分,我們探討研究結果可能的謬誤之處。首先說明為何在衡量企業地緣政治影響力時,利潤是比營收、資產或市值更理想的指標。其次關鍵考量在於,美國企業可能有大量股權為外國投資者所持有,這會削弱美國對這些企業的掌控力。為此,我們建立一套全新資料庫,用以分析這些企業的股權結構。
商業實力的衡量
多數對於經濟實力的分析都是依賴於總體性、非以企業為中心的指標,例如:國內生產毛額、高科技產品出口、製造業產值等。這類指標本質上是以領土為基礎的。在生產活動以國家為中心的時代,主要依賴這些指標確實有其道理。然而,當今多數生產活動──特別是對地緣政治競爭至關重要的高科技產業──通常橫跨多個階段和國家,卻僅由少數企業主導著整個生產流程。
●跨國企業與國家實力
我們並非首批指出「經濟實力不應僅限於本國疆界內」的學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早在1980年代末便觀察到:「以服務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結構,正逐漸被以服務全球市場為主的結構所取代」,並特別強調此「全球生產體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成就」。斯特蘭奇進一步主張,正是由於美國企業主導了生產全球化的進程,才使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她的這段精闢論述值得完整引述:
我的主張是:如今真正能賦予權力的,是那些知識密集的職業──無論是否與製造業相關──其重要性已遠超過單純從生產線產出商品的實體產能。其次,我認為生產設施的地理位置,遠不如那些決策者所在的位置來得重要,這些決策者決定生產內容、地點與方式,並且負責設計、管理與全球市場銷售。美國人究竟是該穿著藍領制服操作機器,還是該穿著白領制服主導整個生產體系的設計、管理與資金調度?這正是為何那些常被引用的數據,例如美國製造業產能占全球比重,或是美國製造出口占比下滑,是如此誤導人,因為這些數據都是以領土為計算基礎。更糟的是,這些數據根本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是...由美國企業高階主管所掌控的全球產出比重。
斯特蘭奇最終得出結論:「美國企業的全球影響力,意味著美國政府行使境外影響力與權威的能力,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政府。」
斯特蘭奇的研究成果對於幫助分析師認識到「跨國企業是國家實力的關鍵來源」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她的論述僅停留在概括性層面。雖然斯特蘭奇有力地論證了跨國企業對於全球權力的重要性,但她並未具體說明如何衡量這些企業的影響力。
足足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才有學者開始有系統性地將跨國企業視為國家實力來源進行分析。這項開創性研究出現在政治學者肖恩.斯塔爾斯2013年發表的論文中。斯塔爾斯強調,要正確評估美國的經濟實力,必須同時考量其企業在國內外所掌控的價值。他利用測量全球最大跨國企業的獲利來進行這項分析。根據《富比士》全球2000大企業2012年資料,斯塔爾斯發現美國企業在富比士劃分的25個經濟部門中,有18個部門位居於領先地位。進一步檢視全球各主要經濟區域前20大企業的股權結構後,斯塔爾斯更指出美國股東不僅掌握多數美國企業,還在歐洲企業持有最大單一持股比例,同時擁有眾多日本企業及部分中國企業的股權。
自斯塔爾斯提出上一份有關商業實力分布的重要分析以來,已過去十餘年,而企業為中心型權力的諸多面向仍有待深入探討。我們從三個主要方向延伸斯塔爾斯對《富比士》2000大企業獲利能力的分析:
首先,斯塔爾斯未將《富比士》2000大企業所屬的各產業進行分類歸納。此一限制影響了分析的深度,因為不同產業部門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存有顯著的差異。為此,我們將這些產業部門重新劃分為四大類別。
其次,斯塔爾斯僅分析了美國與中國企業掌握的商業實力比重。然而,美國盟邦所握有的經濟產出占比足可與美國匹敵,將此因素納入考量至關重要。我們進一步將美國盟邦企業納入分析範疇。
第三,尚有更多資料值得深入探討。斯塔爾斯關於外國企業所有權的資料僅涵蓋各地區前20大企業及全球前500大企業。如我們將在下一節探討的內容,本研究檢視了《富比士》2000強中的所有2000家企業。此外,我們取得的企業資料已更新至2022年,較斯塔爾斯進行分析時所使用的資料向後延伸了十年。
●企業層級資料
在展開分析之前,我們先說明《富比士》資料的一些基本特徵。2022年,入選《富比士》2000強的企業總市值達到76.5兆美元。當時全球總市值估計為124兆美元,這意味著這些大型企業約占全球總市值的60%。
資料庫中企業的國籍是由《富比士》判定,且這些企業均為公開上市公司。亦即私有企業被排除在外,但對我們的研究影響不大。麥肯錫(McKinsey)的分析指出,2022年私募資產管理規模達11.7兆美元。這或許未能涵蓋所有私有資產價值,但相較上市公司124兆美元的規模仍只是零頭。在《財星》500強等同時納入上市與私有企業的排行榜中,私有企業占比約為十分之一,這與麥肯錫分析及我們自身研究顯示的1:10公私企業比例相符。
中國境內有許多未上市的優質企業未被納入《富比士》2000強榜單。然而,入選《富比士》2000強的中國上市企業最能代表中國產業生態中最具活力的領域。那些獲利能力最強的中國國有企業均已上市。而未上市的中國企業往往以國內市場為導向──對中國海外經濟影響力的貢獻相對有限。最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發現,這些未上市中國企業的營收大部分來自其上市子公司,而這些子公司已被《富比士》2000強資料庫所收錄。
《富比士》的資料絕非完美,但跨國企業具有橫跨全球的營運特性,其活動難以透過其他方式進行有效的追蹤。各國政府雖然會詳盡收集境內經濟活動統計資料,卻鮮少有系統地彙整本國企業的海外營運狀況。正如曾引用《富比士》資料研究財富不平等問題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指出:「各國政府與統計機構根本追不上資本全球化的速度,他們使用的工具...已不足以分析21世紀的經濟變遷趨勢」。他特別強調,雖然如《富比士》等雜誌提供的分析存在「方法論上的問題,但至少這些資料確實存在,並以某種方式回應了社會對於當代重大議題『全球財富分配及其演變』的迫切資訊需求」。《富比士》全球2000強資料庫仍是分析跨國企業實力的最有效工具,本章我們將運用此資料庫的優勢,有系統性地比較美中兩國的商業爭霸能力。
當前商業爭霸實力的分布狀況
圖2.1顯示《富比士》全球2000強所列各產業的企業獲利分布。2012年,肖恩.斯塔爾斯的研究發現,美國在72%的產業中創造了最大比例的獲利。十年後,我們發現此優勢進一步擴大:2022年,美國(圖中以深灰色加粗體標示)在74%的產業(《富比士》全球2000強劃分的27個產業中的20個)中保持了獲利領先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優勢幾乎總是極為顯著:在這20個產業中,美國有17個產業領先第二名競爭對手達兩位數百分比,平均領先幅度更高達35%。美國的弱勢領域也極為有限:在《富比士》全球2000強的所有產業中,美國沒有任何一個產業的排名低於第三位。
中國(以白色標示)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根據2022年《富比士》全球2000強資料,中國在27個產業類別中的3個保持領先地位:銀行業(37%)、建築業(38%)以及材料業(13%,主要是指礦業及資源開採)。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產業正是斯塔爾斯十年前研究即指出中國當時就已領先的領域,此後中國並未在任何產業中取得領導地位。
美中之間存在顯著的整體差距。就總量而言,2022年美國企業創造了全球38%的企業獲利,中國企業則貢獻了13%。若將香港計算在內,則此比例提升至16%。
美國還擁有一系列經濟活力充沛的盟友,在評估商業爭霸能力的全球分布時必須納入考量。這些經濟連結近年來更常被運用於地緣政治目的。在此環境下,美國的盟邦強化了其經濟外交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美國官員已與歐洲盟邦密切合作數月,共同籌備並協調制裁方案。一位國務院官員事後透露,美方官員平均每周花費「10至15小時透過保密通話或視訊會議與歐盟協調制裁事宜」。美方最終與盟邦就應對俄羅斯入侵的行動方案達成共識。當戰事爆發時,美國與歐洲盟邦迅速採取行動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俄羅斯中央銀行為抵禦美國制裁而累積的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到凍結,同時還喪失了與美歐絕大多數企業和技術的往來管道。美國及其盟邦以單一經濟體形式對俄實施制裁,這意味著在其他潛在衝突中,這些盟邦的經濟實力很可能也將與美國形成疊加效應。
在評估美國盟友體系時,我們僅考慮以下三類國家:(a)北約成員國;(b)與美國簽訂雙邊防禦條約的國家,如澳洲、南韓和日本;(c)被美國列為「主要非北約盟友」的國家──此一稱號是授予那些雖未與美國建立正式同盟但保持著密切策略關係的國家──且2022年在該國境內部署有100名以上美軍。
共有47個國家符合這些標準。這份名單並非衡量美國最能依賴國家的完美指標──某些盟友可能被證明並不可靠,而一些中立國在某些情境下反而可能成為親密夥伴。但這些國家提供了合理的基準線,當美國試圖運用商業實力的不對稱優勢來制約修正主義勢力時,這些國家很可能成為其優先合作的對象。
美國及其盟友的商業實力總和為何?圖2.1顯示了當我們納入美國盟友(以中灰色加粗文字標示)後的商業實力分布情況。在美國未能取得多數利潤的七個產業中,有三個產業是由美國盟友主掌了利潤。美國及其盟友在五個產業的利潤占比前五名中完全占據主導地位,這些產業包括:航太與國防、藥品與生物科技、媒體、半導體,以及公用事業。在另外12個中國進入利潤前五名的產業中,美國及其盟友占據了其餘4個席位。
總體而言,我們計算出美國盟友占全球企業利潤的35%。若將美國本身計算在內,美國及其盟友共創造了全球73%的企業利潤──這顯示他們掌握了全球商業活動的絕大部分。
觀察圖2.1中以淺灰色標示的12個由中立國家占據的欄位也頗具啟發性。瑞士幾乎占據其中半數(5個欄位)。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瑞士參與了對俄實施的經濟制裁。從經濟手段的角度考量,可將其視為美國的盟友。愛爾蘭則占據這12個欄位中的2個,該國同樣參與了對俄制裁行動。其餘5個欄位分別由南非、印度(占2欄,且並非中國友邦)、沙烏地阿拉伯(歷來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夥伴)以及俄羅斯所占據。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在此圖表中僅占據一個欄位。2014年歐巴馬總統曾諷刺道:「俄羅斯什麼都製造不出來。」直指俄國產業無法突破石油與天然氣領域的困境。2022年俄羅斯企業競爭力數據(採用西方制裁前的資料)印證了歐巴馬的論點。俄羅斯雖在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企業利潤排名第三,但在其他領域幾乎無足輕重:僅有三個產業進入前十名(原材料開採第6位、食品市場第8位、銀行業第9位)。
以《富比士》名單劃分產業類型
1992年時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麥可.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應支持半導體產業時回答:「洋芋片、電腦晶片──有什麼差別?」如同所有產業,洋芋片和電腦晶片確實都會貢獻GDP──這顯然是博斯金的考量重點。然而在國際關係的競爭領域中,不同產業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我們將《富比士》全球2000強企業的27個產業劃分為四大類別:自然資源、金融與商業服務、消費性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在自然資源類別中,我們納入了專注於原料開採與加工的產業,如原材料業及石油天然氣產業。
消費性產業則涵蓋食品加工與分銷、家用及個人用品(包含鞋類與紡織品)、零售商店及媒體等領域。此類別既包含提供簡單便利性商品的產業,也包含食品服裝等必需品產業。我們將主要為消費者提供非技術密集型的商品與服務之產業歸類為消費性產業。其中較為特殊的案例是消費耐久財,該類別部分包含汽車等中等複雜度的商品。基於其名稱特性,我們最終仍將消費耐久財歸類為消費性產業。
金融與商業服務涵蓋銀行業、綜合金融業、企業集團及保險業等領域。在該領域的影響力可體現一國的金融成熟度與資本配置效率,同時也能反映其國內外資產持有狀況。然而,若金融業規模相對於經濟其他部門過大,則可能暗示存在膨脹現象──過度投資將導致成本高昂且適得其反的資產泡沫。
最後一類是高科技產業,包含從事尖端技術產品設計與製造的產業領域。此類別涵蓋航太工業、半導體、製藥與生物科技、科技硬體及資訊軟體等需要大量研發投入的產業。同時也包括化學工業等領域──即使涉及較成熟的技術,仍需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術才能在國際市場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高科技產業往往兼具研發密集與知識密集特性,這大幅提高了新進者的競爭門檻。半導體產業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荷蘭公司艾司摩爾(ASML)是目前全球唯一掌握最先進晶片製程所需複雜光刻機技術的企業;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則幾乎包辦了全球所有最精密半導體的生產。
跨國企業(MNCs)是理解美國與中國之間經濟實力平衡的關鍵。像是蘋果(Apple)、豐田(Toyota)、富士康(Foxconn)、拜耳(Bayer)、阿里巴巴 (Alibaba)、三星(Samsung)等跨國公司,主導著全球供應鏈,並且是商業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2016年汽車、化學品、電子設備及電腦的出口中,超過70%是由跨國公司所製造。早在二十世紀末,公司內部貿易(即一家公司不同部門間的跨境交易)與國際代工(即一家公司向外國供應商採購零組件)的合計價值,估計已占全球貿易額約三分之二。現今,全球商業活動的主體,絕大多數只是跨國公司決定在哪裡以及如何組織其生產活動的副產品而已。
由於跨國企業是經濟實力的重要來源,我們分析美中經濟實力平衡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哪些全球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及其總部所在地。正如我們所指出,美國擁有商業爭權能力:它擁有全球大多數頂尖企業。儘管美國整體商業實力強大,但這種優勢在高科技產業尤其突出,而這些產業正是當前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此外,在這些關鍵產業中,美國的盟友還控制了剩餘產能的絕大部分。
本章架構安排如下。首先,我們說明分析商業實力分布的測量方法。其次,運用全球數千家最具價值企業的資料,比較美國、其盟友與中國的商業實力;我們發現美國及其盟邦無論在整體利潤創造或大多數產業部門都處於領先地位。第三,我們將企業部門分為四大類別──自然資源、金融與商業服務、消費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並測量這些類別的商業實力分布,結果顯示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尤其具有壓倒性優勢。我們也指出,來自美國盟邦的企業構成了其他領先企業的絕大部分。
本章接下來的內容將闡明,這種商業實力分布的失衡結構,如何成為美國藉由切斷目標國與全球企業生產體系的連結來實施制裁的基礎。我們首先分析高科技產業為何在當今地緣政治中具有關鍵性地位,以及任何國家若僅依賴本土企業,為何難以在這些產業持續保持技術領先優勢。接著我們具體說明美國如何運用其影響力,迫使企業配合其外交政策目標──事實上,美國過去已多次採取此類行動。
在本章最後部分,我們探討研究結果可能的謬誤之處。首先說明為何在衡量企業地緣政治影響力時,利潤是比營收、資產或市值更理想的指標。其次關鍵考量在於,美國企業可能有大量股權為外國投資者所持有,這會削弱美國對這些企業的掌控力。為此,我們建立一套全新資料庫,用以分析這些企業的股權結構。
商業實力的衡量
多數對於經濟實力的分析都是依賴於總體性、非以企業為中心的指標,例如:國內生產毛額、高科技產品出口、製造業產值等。這類指標本質上是以領土為基礎的。在生產活動以國家為中心的時代,主要依賴這些指標確實有其道理。然而,當今多數生產活動──特別是對地緣政治競爭至關重要的高科技產業──通常橫跨多個階段和國家,卻僅由少數企業主導著整個生產流程。
●跨國企業與國家實力
我們並非首批指出「經濟實力不應僅限於本國疆界內」的學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早在1980年代末便觀察到:「以服務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結構,正逐漸被以服務全球市場為主的結構所取代」,並特別強調此「全球生產體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成就」。斯特蘭奇進一步主張,正是由於美國企業主導了生產全球化的進程,才使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她的這段精闢論述值得完整引述:
我的主張是:如今真正能賦予權力的,是那些知識密集的職業──無論是否與製造業相關──其重要性已遠超過單純從生產線產出商品的實體產能。其次,我認為生產設施的地理位置,遠不如那些決策者所在的位置來得重要,這些決策者決定生產內容、地點與方式,並且負責設計、管理與全球市場銷售。美國人究竟是該穿著藍領制服操作機器,還是該穿著白領制服主導整個生產體系的設計、管理與資金調度?這正是為何那些常被引用的數據,例如美國製造業產能占全球比重,或是美國製造出口占比下滑,是如此誤導人,因為這些數據都是以領土為計算基礎。更糟的是,這些數據根本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是...由美國企業高階主管所掌控的全球產出比重。
斯特蘭奇最終得出結論:「美國企業的全球影響力,意味著美國政府行使境外影響力與權威的能力,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政府。」
斯特蘭奇的研究成果對於幫助分析師認識到「跨國企業是國家實力的關鍵來源」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她的論述僅停留在概括性層面。雖然斯特蘭奇有力地論證了跨國企業對於全球權力的重要性,但她並未具體說明如何衡量這些企業的影響力。
足足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才有學者開始有系統性地將跨國企業視為國家實力來源進行分析。這項開創性研究出現在政治學者肖恩.斯塔爾斯2013年發表的論文中。斯塔爾斯強調,要正確評估美國的經濟實力,必須同時考量其企業在國內外所掌控的價值。他利用測量全球最大跨國企業的獲利來進行這項分析。根據《富比士》全球2000大企業2012年資料,斯塔爾斯發現美國企業在富比士劃分的25個經濟部門中,有18個部門位居於領先地位。進一步檢視全球各主要經濟區域前20大企業的股權結構後,斯塔爾斯更指出美國股東不僅掌握多數美國企業,還在歐洲企業持有最大單一持股比例,同時擁有眾多日本企業及部分中國企業的股權。
自斯塔爾斯提出上一份有關商業實力分布的重要分析以來,已過去十餘年,而企業為中心型權力的諸多面向仍有待深入探討。我們從三個主要方向延伸斯塔爾斯對《富比士》2000大企業獲利能力的分析:
首先,斯塔爾斯未將《富比士》2000大企業所屬的各產業進行分類歸納。此一限制影響了分析的深度,因為不同產業部門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存有顯著的差異。為此,我們將這些產業部門重新劃分為四大類別。
其次,斯塔爾斯僅分析了美國與中國企業掌握的商業實力比重。然而,美國盟邦所握有的經濟產出占比足可與美國匹敵,將此因素納入考量至關重要。我們進一步將美國盟邦企業納入分析範疇。
第三,尚有更多資料值得深入探討。斯塔爾斯關於外國企業所有權的資料僅涵蓋各地區前20大企業及全球前500大企業。如我們將在下一節探討的內容,本研究檢視了《富比士》2000強中的所有2000家企業。此外,我們取得的企業資料已更新至2022年,較斯塔爾斯進行分析時所使用的資料向後延伸了十年。
●企業層級資料
在展開分析之前,我們先說明《富比士》資料的一些基本特徵。2022年,入選《富比士》2000強的企業總市值達到76.5兆美元。當時全球總市值估計為124兆美元,這意味著這些大型企業約占全球總市值的60%。
資料庫中企業的國籍是由《富比士》判定,且這些企業均為公開上市公司。亦即私有企業被排除在外,但對我們的研究影響不大。麥肯錫(McKinsey)的分析指出,2022年私募資產管理規模達11.7兆美元。這或許未能涵蓋所有私有資產價值,但相較上市公司124兆美元的規模仍只是零頭。在《財星》500強等同時納入上市與私有企業的排行榜中,私有企業占比約為十分之一,這與麥肯錫分析及我們自身研究顯示的1:10公私企業比例相符。
中國境內有許多未上市的優質企業未被納入《富比士》2000強榜單。然而,入選《富比士》2000強的中國上市企業最能代表中國產業生態中最具活力的領域。那些獲利能力最強的中國國有企業均已上市。而未上市的中國企業往往以國內市場為導向──對中國海外經濟影響力的貢獻相對有限。最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發現,這些未上市中國企業的營收大部分來自其上市子公司,而這些子公司已被《富比士》2000強資料庫所收錄。
《富比士》的資料絕非完美,但跨國企業具有橫跨全球的營運特性,其活動難以透過其他方式進行有效的追蹤。各國政府雖然會詳盡收集境內經濟活動統計資料,卻鮮少有系統地彙整本國企業的海外營運狀況。正如曾引用《富比士》資料研究財富不平等問題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指出:「各國政府與統計機構根本追不上資本全球化的速度,他們使用的工具...已不足以分析21世紀的經濟變遷趨勢」。他特別強調,雖然如《富比士》等雜誌提供的分析存在「方法論上的問題,但至少這些資料確實存在,並以某種方式回應了社會對於當代重大議題『全球財富分配及其演變』的迫切資訊需求」。《富比士》全球2000強資料庫仍是分析跨國企業實力的最有效工具,本章我們將運用此資料庫的優勢,有系統性地比較美中兩國的商業爭霸能力。
當前商業爭霸實力的分布狀況
圖2.1顯示《富比士》全球2000強所列各產業的企業獲利分布。2012年,肖恩.斯塔爾斯的研究發現,美國在72%的產業中創造了最大比例的獲利。十年後,我們發現此優勢進一步擴大:2022年,美國(圖中以深灰色加粗體標示)在74%的產業(《富比士》全球2000強劃分的27個產業中的20個)中保持了獲利領先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優勢幾乎總是極為顯著:在這20個產業中,美國有17個產業領先第二名競爭對手達兩位數百分比,平均領先幅度更高達35%。美國的弱勢領域也極為有限:在《富比士》全球2000強的所有產業中,美國沒有任何一個產業的排名低於第三位。
中國(以白色標示)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根據2022年《富比士》全球2000強資料,中國在27個產業類別中的3個保持領先地位:銀行業(37%)、建築業(38%)以及材料業(13%,主要是指礦業及資源開採)。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產業正是斯塔爾斯十年前研究即指出中國當時就已領先的領域,此後中國並未在任何產業中取得領導地位。
美中之間存在顯著的整體差距。就總量而言,2022年美國企業創造了全球38%的企業獲利,中國企業則貢獻了13%。若將香港計算在內,則此比例提升至16%。
美國還擁有一系列經濟活力充沛的盟友,在評估商業爭霸能力的全球分布時必須納入考量。這些經濟連結近年來更常被運用於地緣政治目的。在此環境下,美國的盟邦強化了其經濟外交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美國官員已與歐洲盟邦密切合作數月,共同籌備並協調制裁方案。一位國務院官員事後透露,美方官員平均每周花費「10至15小時透過保密通話或視訊會議與歐盟協調制裁事宜」。美方最終與盟邦就應對俄羅斯入侵的行動方案達成共識。當戰事爆發時,美國與歐洲盟邦迅速採取行動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俄羅斯中央銀行為抵禦美國制裁而累積的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到凍結,同時還喪失了與美歐絕大多數企業和技術的往來管道。美國及其盟邦以單一經濟體形式對俄實施制裁,這意味著在其他潛在衝突中,這些盟邦的經濟實力很可能也將與美國形成疊加效應。
在評估美國盟友體系時,我們僅考慮以下三類國家:(a)北約成員國;(b)與美國簽訂雙邊防禦條約的國家,如澳洲、南韓和日本;(c)被美國列為「主要非北約盟友」的國家──此一稱號是授予那些雖未與美國建立正式同盟但保持著密切策略關係的國家──且2022年在該國境內部署有100名以上美軍。
共有47個國家符合這些標準。這份名單並非衡量美國最能依賴國家的完美指標──某些盟友可能被證明並不可靠,而一些中立國在某些情境下反而可能成為親密夥伴。但這些國家提供了合理的基準線,當美國試圖運用商業實力的不對稱優勢來制約修正主義勢力時,這些國家很可能成為其優先合作的對象。
美國及其盟友的商業實力總和為何?圖2.1顯示了當我們納入美國盟友(以中灰色加粗文字標示)後的商業實力分布情況。在美國未能取得多數利潤的七個產業中,有三個產業是由美國盟友主掌了利潤。美國及其盟友在五個產業的利潤占比前五名中完全占據主導地位,這些產業包括:航太與國防、藥品與生物科技、媒體、半導體,以及公用事業。在另外12個中國進入利潤前五名的產業中,美國及其盟友占據了其餘4個席位。
總體而言,我們計算出美國盟友占全球企業利潤的35%。若將美國本身計算在內,美國及其盟友共創造了全球73%的企業利潤──這顯示他們掌握了全球商業活動的絕大部分。
觀察圖2.1中以淺灰色標示的12個由中立國家占據的欄位也頗具啟發性。瑞士幾乎占據其中半數(5個欄位)。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瑞士參與了對俄實施的經濟制裁。從經濟手段的角度考量,可將其視為美國的盟友。愛爾蘭則占據這12個欄位中的2個,該國同樣參與了對俄制裁行動。其餘5個欄位分別由南非、印度(占2欄,且並非中國友邦)、沙烏地阿拉伯(歷來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夥伴)以及俄羅斯所占據。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在此圖表中僅占據一個欄位。2014年歐巴馬總統曾諷刺道:「俄羅斯什麼都製造不出來。」直指俄國產業無法突破石油與天然氣領域的困境。2022年俄羅斯企業競爭力數據(採用西方制裁前的資料)印證了歐巴馬的論點。俄羅斯雖在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企業利潤排名第三,但在其他領域幾乎無足輕重:僅有三個產業進入前十名(原材料開採第6位、食品市場第8位、銀行業第9位)。
以《富比士》名單劃分產業類型
1992年時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麥可.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應支持半導體產業時回答:「洋芋片、電腦晶片──有什麼差別?」如同所有產業,洋芋片和電腦晶片確實都會貢獻GDP──這顯然是博斯金的考量重點。然而在國際關係的競爭領域中,不同產業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我們將《富比士》全球2000強企業的27個產業劃分為四大類別:自然資源、金融與商業服務、消費性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在自然資源類別中,我們納入了專注於原料開採與加工的產業,如原材料業及石油天然氣產業。
消費性產業則涵蓋食品加工與分銷、家用及個人用品(包含鞋類與紡織品)、零售商店及媒體等領域。此類別既包含提供簡單便利性商品的產業,也包含食品服裝等必需品產業。我們將主要為消費者提供非技術密集型的商品與服務之產業歸類為消費性產業。其中較為特殊的案例是消費耐久財,該類別部分包含汽車等中等複雜度的商品。基於其名稱特性,我們最終仍將消費耐久財歸類為消費性產業。
金融與商業服務涵蓋銀行業、綜合金融業、企業集團及保險業等領域。在該領域的影響力可體現一國的金融成熟度與資本配置效率,同時也能反映其國內外資產持有狀況。然而,若金融業規模相對於經濟其他部門過大,則可能暗示存在膨脹現象──過度投資將導致成本高昂且適得其反的資產泡沫。
最後一類是高科技產業,包含從事尖端技術產品設計與製造的產業領域。此類別涵蓋航太工業、半導體、製藥與生物科技、科技硬體及資訊軟體等需要大量研發投入的產業。同時也包括化學工業等領域──即使涉及較成熟的技術,仍需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術才能在國際市場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高科技產業往往兼具研發密集與知識密集特性,這大幅提高了新進者的競爭門檻。半導體產業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荷蘭公司艾司摩爾(ASML)是目前全球唯一掌握最先進晶片製程所需複雜光刻機技術的企業;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則幾乎包辦了全球所有最精密半導體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