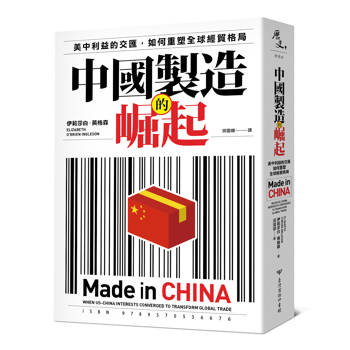一九八○年九月,即《美中貿易協定》生效幾個月後,美國鞋業公司Nike與中國貿易商簽訂了一項交易,該交易類似於幾年前牛津工業公司和威望公司。Nike在上海和天津蓋了四座鞋廠,總值為七萬五千美元。做為回報,Nike獲得等值的鞋子,只花了幾個月時間完成整個過程。此後,Nike開始以低價進口中國製造的鞋子。《中國商業評論》稱讚道,這是「天作之合」。「隨著亞洲其他地區,尤其是韓國和臺灣的勞動成本上升,中國做為生產基地的吸引力也愈來愈大。從「臺灣製造」到「中國製造」的轉變已經開始。該交易目的為直接供應美國市場。從中國工廠進口的Nike鞋幾乎百分之百賣給美國顧客。這對希望透過出口增加外匯收入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很有吸引力。Nike總裁菲利普.奈特(Philip H. Knight)對記者說:「目前我們還沒有在中國銷售的計畫。」幾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並以創紀錄的速度購買品牌鞋和品牌手提包。但為了走到那一步,中國的領導人首先與美國商人攜手合作,打造了一個擁有八億勞工的市場。當中國成為消費大國時,製造和貿易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轉變。
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務實派共同合作,把中國市場從四億顧客轉變為八億勞工的市場。此一轉變構成了美中貿易長期歷史上一個變革性的轉捩點,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略)
由於美國的中國天鵝絨進口量愈來愈大,克朗普頓無法與之競爭,導致克朗普頓在一九八四年十月聲請破產。儘管中國在整個美國市場的份額相對較小,但該公司總裁威廉.洛德二世(William G. Lord II)仍歸咎於中國。洛德的抱怨是針對文化而非經濟。他並不把焦點放在中國的出口數量,而是放在他認為中國引發的消費需求變化。洛德宣稱,中國「改變了天鵝絨服裝的形象」。隨著中國天鵝絨壓低該布料的價格,它「從奢侈品變成了大宗商品……從此再也無法恢復舊觀」。
他的觀點是,低價的中國進口商品削弱了天鵝絨的奢華感。藉由讓一般消費者能夠負擔得起天鵝絨,因而減損了注重身分地位的美國天鵝絨西裝穿著者的購買慾望。如果一件克朗普頓西裝看起來像是在別處買的一樣,為何要付更高的價格?這與一九七○年代讚揚中國產品品質並經常把中國與奢侈品連結的美國進口商不同。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洛德表達了一種新觀點:中國的低成本已經改變了整體天鵝絨市場予人的高端精緻形象。當然,該公司的問題遠不只如此。里奇蒙和洛德都把自己的憤怒和憂慮集中在外國製造的產品上,卻隻字未提競爭對手牛津工業和威望等美國大企業本身追求海外製造是導致進口成長的重要原因。
洛德對中國侵蝕奢侈品市場的評論反映出,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中國的進口產品開始逐漸變成廉價商品和威脅的象徵。這並非一九七○年代人們對中國的文化認知。在貿易的早期階段,中國曾與品質和奢華劃上等號。但隨著中國製造能力擴大(得力於與牛津工業和威望等公司的交易),中國商品的文化聯想也開始改變。
到了一九八四年克朗普頓破產時,中國已不再讓人聯想到優質和奢華,而變成了廉價的代名詞。克朗普頓的破產告訴我們的,不只是中國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美國紡織業面臨了更廣泛的改變。當中國一九七一年開始向美國市場出售少量棉質天鵝絨時,克朗普頓就已陷入困境。洛德或許會把公司陷入困境歸咎於中國進入美國市場,但他的憤怒缺乏根據。美國的紡織公司轉向海外製造對克朗普頓前景造成的傷害比中國更大。
把克朗普頓工廠的關閉和牛津工業公司以及威望公司簽訂的交易結合起來看,揭露出美國企業和商人如何在中國的工業化和美國的去工業化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製造業發生的改變,為中紡提供了順應其發展需求的機會。中紡、牛津工業和威望三家企業共同打造了一個不只著重於吸收美國技術、還著重於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市場。
(中略)
中國發展計畫的這些連續性,有助於解釋美國人與中國市場兩面性關係:一面是大肆宣傳的銷售,另一面則如福尼所說的,是一個緩慢崛起的中國製造業「巨獸」。綜合探究中國市場的這兩個面向,揭示了中國與資本主義貿易體系趨同(convergence)的關鍵要素,是美國企業的轉變,以及其所帶來的全球分工。短期來看,中國購買大規模技術設備,表面上看來似乎預示了一個美國企業的銷售市場將重新崛起。但實際上,中國領導人進行這些採購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造向美國企業提供勞動力的產業體系。
(中略)
一九七八年八月,世界最大的工程集團凱撒工程公司成為第一家與中國達成礦業建設交易的美國公司,其所出售的商品是專業知識。(……)凱撒的交易創下美中貿易關係發展另一個里程碑,這是中國貿易商首次只進口美國的技術知識。
但在兩國「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貿易問題的進展卻仍然遲緩。一九七九年五月解決了債權/資產問題後,下一個主要障礙就是貿易協定。克雷普斯和李強首次談妥貿易協定後,兩國又花了兩個月時間才簽署。延遲的原因有二:紡織品和蘇聯。
由於勞工不斷施壓,而中國又不肯妥協,卡特最終被迫放棄與中國達成共同紡織品協議的努力。
(中略)
阻礙美中貿易協定的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擔心該協定會對美國與蘇聯的關係造成影響。(……)但最終還是蘇聯自己促成美國國會決定批准與中國的貿易協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入侵阿富汗,與中蘇保持對等外交政策的必要性隨之消失。國會在幾天後就通過了《中美貿易關係協定》,並於一九八○年二月一日生效。美蘇關係惡化,而與中國關係改善的情緒則更加高漲。在美國與蘇聯的冷戰緊張局勢升高之際,美國與中國的冷戰分歧則隨之消弭。然而,該貿易協定的生效卻透過移民把貿易與人權連結在一起,而不是透過勞工權利等其他類型的人權。
(中略)
這種改變的部分原因是,《一九七四年貿易法》把徵收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的權力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
法案的支持者假設把權力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將可確保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可以繼續進行貿易。至少四十年來他們的這種想法都是對的。但正是這項立法變革賦予了川普總統權力,在二○一○年代末期透過行政命令限制對中貿易。《一九七四年貿易法》帶來的長期改變協助了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
這是因為該法案包含一項稱為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簡稱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的條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優惠貿易條件。普惠制的長期影響是鼓勵美國公司把勞動外包到國外。正如勞工史家朱迪斯.斯坦(Judith Stein)指出,它「促進、但並未創造」了後來從東亞進入美國的商品流動。普惠制條款是針對壟斷聯盟(cartels)。
(中略)
中國並沒有造成一九七○年代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相反的,失業是華盛頓的政策造成美國資本主義內部改變的結果。
(中略)
中國是「世界工廠」,而推動其發展的正是血汗工廠的勞動力。
(中略)
在十九世紀末期,進行貿易的國家可以用原產國標籤來明確地辨識。但到了廿世紀中葉,日益全球化的貿易和金融流動改變了國家和企業權力間的關係。到了廿世紀末,跨國運作的企業和資本往往超越民族國家的完全管轄和稅收範圍。
貿易不再那麼直接代表國家關係。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政府的利益開始逐漸趨於一致。五十年後, 他們的利益連結得還更加緊密。當他們重新定義中國市場的含義,把它從一個有顧客的地方轉變成一個有工人的地方時,這個進程得到了美國的外交假設的助力:貿易是民間關係的另一種形式;進行貿易的美國商人是非正式的外交官;勞工問題是貿易和外交的阻礙。
如果「中國製造」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將不是呼籲回歸人們想像中的製造業就業理想,而應該是一種以傾聽勞工(包括國內和國際友邦的勞工)的心聲為核心的政治遠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避免把商人幻想成代表國家的非正式外交官。
在一九七○年代,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碰撞改變了、並且最終擴大了美國的實力。但一股較為緩慢且悄然的變化也開始形成,正當相互依存的概念形塑美國外交政策之際, 美國和中國建構起相互依存的貿易關係。透過打造「中國製造」,美國的外交官和商界人士以貿易奠定了某個進程的基礎,而這個進程,或將在未來某天,標誌著美國霸權的終結, 以及,中國霸權的再度崛起。
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務實派共同合作,把中國市場從四億顧客轉變為八億勞工的市場。此一轉變構成了美中貿易長期歷史上一個變革性的轉捩點,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略)
由於美國的中國天鵝絨進口量愈來愈大,克朗普頓無法與之競爭,導致克朗普頓在一九八四年十月聲請破產。儘管中國在整個美國市場的份額相對較小,但該公司總裁威廉.洛德二世(William G. Lord II)仍歸咎於中國。洛德的抱怨是針對文化而非經濟。他並不把焦點放在中國的出口數量,而是放在他認為中國引發的消費需求變化。洛德宣稱,中國「改變了天鵝絨服裝的形象」。隨著中國天鵝絨壓低該布料的價格,它「從奢侈品變成了大宗商品……從此再也無法恢復舊觀」。
他的觀點是,低價的中國進口商品削弱了天鵝絨的奢華感。藉由讓一般消費者能夠負擔得起天鵝絨,因而減損了注重身分地位的美國天鵝絨西裝穿著者的購買慾望。如果一件克朗普頓西裝看起來像是在別處買的一樣,為何要付更高的價格?這與一九七○年代讚揚中國產品品質並經常把中國與奢侈品連結的美國進口商不同。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洛德表達了一種新觀點:中國的低成本已經改變了整體天鵝絨市場予人的高端精緻形象。當然,該公司的問題遠不只如此。里奇蒙和洛德都把自己的憤怒和憂慮集中在外國製造的產品上,卻隻字未提競爭對手牛津工業和威望等美國大企業本身追求海外製造是導致進口成長的重要原因。
洛德對中國侵蝕奢侈品市場的評論反映出,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中國的進口產品開始逐漸變成廉價商品和威脅的象徵。這並非一九七○年代人們對中國的文化認知。在貿易的早期階段,中國曾與品質和奢華劃上等號。但隨著中國製造能力擴大(得力於與牛津工業和威望等公司的交易),中國商品的文化聯想也開始改變。
到了一九八四年克朗普頓破產時,中國已不再讓人聯想到優質和奢華,而變成了廉價的代名詞。克朗普頓的破產告訴我們的,不只是中國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美國紡織業面臨了更廣泛的改變。當中國一九七一年開始向美國市場出售少量棉質天鵝絨時,克朗普頓就已陷入困境。洛德或許會把公司陷入困境歸咎於中國進入美國市場,但他的憤怒缺乏根據。美國的紡織公司轉向海外製造對克朗普頓前景造成的傷害比中國更大。
把克朗普頓工廠的關閉和牛津工業公司以及威望公司簽訂的交易結合起來看,揭露出美國企業和商人如何在中國的工業化和美國的去工業化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製造業發生的改變,為中紡提供了順應其發展需求的機會。中紡、牛津工業和威望三家企業共同打造了一個不只著重於吸收美國技術、還著重於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市場。
(中略)
中國發展計畫的這些連續性,有助於解釋美國人與中國市場兩面性關係:一面是大肆宣傳的銷售,另一面則如福尼所說的,是一個緩慢崛起的中國製造業「巨獸」。綜合探究中國市場的這兩個面向,揭示了中國與資本主義貿易體系趨同(convergence)的關鍵要素,是美國企業的轉變,以及其所帶來的全球分工。短期來看,中國購買大規模技術設備,表面上看來似乎預示了一個美國企業的銷售市場將重新崛起。但實際上,中國領導人進行這些採購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造向美國企業提供勞動力的產業體系。
(中略)
一九七八年八月,世界最大的工程集團凱撒工程公司成為第一家與中國達成礦業建設交易的美國公司,其所出售的商品是專業知識。(……)凱撒的交易創下美中貿易關係發展另一個里程碑,這是中國貿易商首次只進口美國的技術知識。
但在兩國「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貿易問題的進展卻仍然遲緩。一九七九年五月解決了債權/資產問題後,下一個主要障礙就是貿易協定。克雷普斯和李強首次談妥貿易協定後,兩國又花了兩個月時間才簽署。延遲的原因有二:紡織品和蘇聯。
由於勞工不斷施壓,而中國又不肯妥協,卡特最終被迫放棄與中國達成共同紡織品協議的努力。
(中略)
阻礙美中貿易協定的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擔心該協定會對美國與蘇聯的關係造成影響。(……)但最終還是蘇聯自己促成美國國會決定批准與中國的貿易協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入侵阿富汗,與中蘇保持對等外交政策的必要性隨之消失。國會在幾天後就通過了《中美貿易關係協定》,並於一九八○年二月一日生效。美蘇關係惡化,而與中國關係改善的情緒則更加高漲。在美國與蘇聯的冷戰緊張局勢升高之際,美國與中國的冷戰分歧則隨之消弭。然而,該貿易協定的生效卻透過移民把貿易與人權連結在一起,而不是透過勞工權利等其他類型的人權。
(中略)
這種改變的部分原因是,《一九七四年貿易法》把徵收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的權力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
法案的支持者假設把權力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將可確保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可以繼續進行貿易。至少四十年來他們的這種想法都是對的。但正是這項立法變革賦予了川普總統權力,在二○一○年代末期透過行政命令限制對中貿易。《一九七四年貿易法》帶來的長期改變協助了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
這是因為該法案包含一項稱為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簡稱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的條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優惠貿易條件。普惠制的長期影響是鼓勵美國公司把勞動外包到國外。正如勞工史家朱迪斯.斯坦(Judith Stein)指出,它「促進、但並未創造」了後來從東亞進入美國的商品流動。普惠制條款是針對壟斷聯盟(cartels)。
(中略)
中國並沒有造成一九七○年代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相反的,失業是華盛頓的政策造成美國資本主義內部改變的結果。
(中略)
中國是「世界工廠」,而推動其發展的正是血汗工廠的勞動力。
(中略)
在十九世紀末期,進行貿易的國家可以用原產國標籤來明確地辨識。但到了廿世紀中葉,日益全球化的貿易和金融流動改變了國家和企業權力間的關係。到了廿世紀末,跨國運作的企業和資本往往超越民族國家的完全管轄和稅收範圍。
貿易不再那麼直接代表國家關係。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政府的利益開始逐漸趨於一致。五十年後, 他們的利益連結得還更加緊密。當他們重新定義中國市場的含義,把它從一個有顧客的地方轉變成一個有工人的地方時,這個進程得到了美國的外交假設的助力:貿易是民間關係的另一種形式;進行貿易的美國商人是非正式的外交官;勞工問題是貿易和外交的阻礙。
如果「中國製造」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將不是呼籲回歸人們想像中的製造業就業理想,而應該是一種以傾聽勞工(包括國內和國際友邦的勞工)的心聲為核心的政治遠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避免把商人幻想成代表國家的非正式外交官。
在一九七○年代,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碰撞改變了、並且最終擴大了美國的實力。但一股較為緩慢且悄然的變化也開始形成,正當相互依存的概念形塑美國外交政策之際, 美國和中國建構起相互依存的貿易關係。透過打造「中國製造」,美國的外交官和商界人士以貿易奠定了某個進程的基礎,而這個進程,或將在未來某天,標誌著美國霸權的終結, 以及,中國霸權的再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