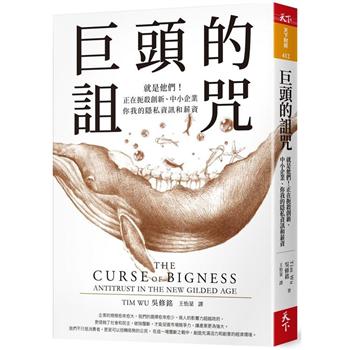●前言 反壟斷是民主政體的必要制衡
我們歷經了三十年政治與經濟的實驗。當美國與其他大國削弱了對工業巨頭之規模和實力的控制時,會發生什麼事?允許集中的私人權力不受限制的成長,並且放棄阻止大多數反競爭行為,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認為,答案相當簡單。我們正在重現一個世紀之前,亦即第一個鍍金年代(Gilded Age)的經濟與政治,依然重演更多二十世紀標誌性錯誤的巨大危險。那個時代的教訓讓我們知道,極端的經濟集中會導致嚴重的不平等與物質痛苦,因而助長人們支持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的領導政權。然而,我們似乎對上個世紀最大的教訓視而不見,並往同樣的道路走去。如果說我們從鍍金年代學到一件事,那就是:通往法西斯主義與獨裁政權的道路上,鋪滿了未能滿足一般大眾需求的經濟政策。
放眼全球經濟,並且目睹集中寡占與壟斷企業的主導狀況,金融、媒體、航空、電信等產業的壟斷可說最為明顯,也就是規模大的公司可以恣意對待顧客與競爭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明顯的,莫過於科技平台的巨大力量,尤其像 Google、Facebook,以及亞馬遜(Amazon),它們對我們的生活有無比的影響力。私人權力的集中帶來財富的再次集中,導致貧富差距更為擴大。
財富和權力的集中化,促使改變和激化選舉政治。就如鍍金年代,心懷不滿且日漸衰落的中產階級,開始支持激進反企業與民族主義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迎合了超越黨派的不滿情緒。在全球重新燃起的經濟民族主義,把中產階級的式微歸咎於外籍勞工、外國產品與菁英階層的陰謀。人們普遍對大企業以及其對待顧客的方式感到憤怒,尤其是那些集中或壟斷的產業,像是保險、製藥、航空,以及其他麻木不仁的企業巨獸。許多人害怕 Google、亞馬遜,以及 Facebook,擔心它們不只能控制商業,還會控制政治、新聞,以及我們的隱私訊息。
我們必須意識到,現在已然再次面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所稱的「巨頭的詛咒」,正如他警告的,此為對民主本身的強烈威脅。如果我們能夠接受產業對選舉與立法的影響力比普通公民還大時,還有什麼好說的呢?當美國製藥界能把藥品價格提高數倍,是因為自信政府不會出手干預?當中產階級對醫療保險、稅收、工作環境、住房,以及其他決定生活方式的政策沒有明顯的影響力,又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這些被忽視超過一個世代的問題。極度的產業集中,是否確實能與公民的大致平等、產業自由,或民主本身的前提相容?我們能否在一個壟斷企業主導的經濟中,創造廣大的財富與創業機會感?私人權力是否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這些企業對政府與大家的生活產生過大的影響力?
我認為,這些問題早有答案。本書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如何恢復以及更新針對企業巨獸的典型解方──反托拉斯法和其他反壟斷法,來迎接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在將近一個世紀中,反托拉斯法一直是反壟斷規範的實踐與理論,它試著限制產業過度集中,並且管制壟斷的行為。
直至上個世紀中葉,西方世界普遍將反托拉斯法理解為一個正常運作民主政體的必要部分,也是對私人權力的終極制衡。然而,才經過一個世代,反托拉斯法已經萎縮成無關緊要的影子,在某種程度上對壟斷的核心問題不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最高法院曾將反托拉斯法稱為「旨在保障自由與不受約束競爭的綜合經濟自由憲章」,但它已不再譴責壟斷,而是變得模稜兩可,有時甚至讚揚壟斷者,彷彿「反托拉斯」的「反」字已經被拋棄。
以下多數內容可以理解為聚焦在恢復這個原則:在制定與反覆強化反托拉斯法的過程中,美國在產業和國家政策上作出了至關重要且符合憲法的選擇。經過一段時間的激烈辯論,包括一九一二年經濟政策成為主要議題的總統大選,國家拒絕了壟斷經濟,並且在過去數十年來,多次選擇了保持其開放與競爭市場的傳統。必須將反托拉斯法的目標理解為尊重這個選擇,正如分權經濟的先知路易斯‧布蘭迪斯所言,反托拉斯法回答了一個問題:「美國的產業政策是競爭政策,或是壟斷政策?」
然而,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目前反托拉斯法正受到過度放縱觀念的傷害,芝加哥大學的羅勃‧伯克(Robert Bork)等人在一九七○年代首先廣為傳播這種思想。伯克的論調令人難以置信,一八九○年國會制定反托拉斯法,只是為了因應一項非常狹隘的危害:讓消費者付出更高的價格,而這個理論的切入點「消費者福利」已然削弱了反托拉斯法。它承諾帶來更高的確定性與科學嚴謹性,可是兩者都沒有實現,更重要的是,它拋棄了太多法律應該在民主國家發揮的作用,亦即限制私人權力無限制擴張,且維護經濟自由。
四十年前,法學家皮托夫斯基(Robert Pitofsky)警告:「在解釋反托拉斯法時排除特定的政治價值觀,是糟糕的歷史、不良的政策,以及劣質的法律。」他說的一點也沒錯。
隨著意識型態的轉變,反托拉斯法也曾陷入冬眠期,但它很快捲土重來以滿足時代的需求。為了實現它的使命,美國的反托拉斯法需要回歸其更廣泛的目標,並且提升其能力。它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評估新形式的市場力量,來衡量宏觀經濟的論點,嚴肅看待產業集中與政治影響力之間的關聯。它需要利用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所提供的一切;它需要更強大的解決方法,包括重新拆分壟斷企業,這些措施的設計必須謹記反托拉斯的更大目標。最後,它需要讓法院重新參與布蘭迪斯所稱「抑制或甚至破壞競爭的行為」的執法工作。
在二十世紀,無法控制私人權力,以及未能照顧國民經濟需求的國家面臨了獨裁者的崛起,他們向人民承諾,會立即將大家從經濟困境中解救出來。一個與壟斷產業合作的政府最高領導人崛起,與法西斯主義與獨裁主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誠然,單靠反托拉斯法不能解除大企業的詛咒,或是消除私人權力的氾濫,但它擊中了問題的根本,重新啟動法律的引擎是解決已達憲法層面問題的重要關鍵。
因此,這本書遠沒有那麼激進,實際上是在呼籲走中間路線,在經濟結構控制我們之前,先控制住它。本書並不認為反托拉斯已退化到無可救藥,也沒有將其實踐者貼上不專業或不明智的標籤。相反的,本書主張,反托拉斯法已經看不見自己的目標,未能完成其核心任務。我提出的種種作法,可能可以重振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托拉斯法,將它恢復為正常運作民主政權中對私人權力的必要制衡。
●我們的鍍金年代,以及其將走向何方?
以前,我們可能以為主要的工業國家已經記取教訓。在經歷了共產主義、法西斯革命、大蕭條,以及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後,集體改變了對經濟及其在民主國家的角色。西方國家揚棄富人的自由放任政策、共產主義對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控制經濟,而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經濟政策的重新民主化,以及財富重分配的政治。這種路線帶來數十年的經濟成長,建立了中產階級,並且達到人類歷史上無法想像的繁榮水準,縮小了貧富間的巨大差距。
那是當時的情況,但是我們現在又回到這裡,就像是困在差勁的電影續集一般。今天就如同一九一○年代,工業化世界有兩個重要的經濟事實。
首先,再次出現貧富懸殊的鴻溝,這種趨勢在美國最為明顯,美國最富有一%的人,其收入占全國所得二三‧八%,控制全國財富的比例高達驚人的三八‧六%。
第二,回歸集中式經濟,亦即產業被更少且更大的公司所主導。正如世界經濟論壇證實,更高比例的全球財富被更少的公司與產業控制。在美國,一九九七年~二○一二年之間,七五%的美國產業更為集中。同樣的,自二○○○年以來,衡量市場集中度的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顯示,全美七五%以上的各行各業集中度增加。當美國公開市場已經失去了近五○%的上市公司,股市實際上是萎縮的。
最顯而易見的合併趨勢就在我們眼前:曾經開放且有競爭力的科技產業,已經集中成為少數幾個巨頭:Facebook、亞馬遜、Google,以及蘋果。這些公司掌握的權力似乎引起了大眾的關注,亦即我們面臨的問題已超越了狹隘的經濟範疇。大型科技公司無所不在,似乎對我們太過了解,似乎對我們的所見、所聞、所做,甚至所感有著過大的影響。當少數幾個人的決定可以對所有人造成極大影響,它重新引發了誰是真正主宰的爭議。套用參議員謝爾曼(John Sherman)的話來說,它們的權力感覺就像「國王的特權,與我們政府的形式並不一致。」
如今的經濟看起來就像是鍍金年代的仿製品,我們的政治與其不謀而合,也就不值得太驚訝了。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勞工遭受殘酷的對待,中小企業遭到破壞,廣泛的經濟苦難,造成廣大民眾的憤怒,以及對全新且不同事物的需求。強勢領導人承諾重新恢復偉大,為勞工提供生計,並且建立新秩序。
如今,經濟上的不滿正導致世界各地出現類似的憤怒民粹主義。一些人把自己的命運歸咎於移民、猶太人、穆斯林、基督徒,或可能是中國人或美國人,從而產生新一代的排外、民族主義,以及種族主義政治。其他人則指責銀行家、科技產業,或一般的企業。由於比父母更貧窮的羞恥感、像是用過即丟的勞工,以及前景遭到忽略等現象的煽動所致,我們目睹了憤怒與暴力政治的回歸。
從二十世紀得到的更好教訓顯示,較不激進的替代方案有其成效:幫助失業者與老年人的計畫,保護工作者與勞工的計畫,以及其他努力諸如削弱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固有的殘酷和不平等。因此,在美國出現了一種不同的運動和方法,來應對累積的私人權力的結構源頭,並以其目標「托拉斯」(trusts)來命名,因此有了「反托拉斯」法。
若有人認為反托拉斯法可以提供不平等或其他經濟問題的完整答案,那就過於誇張,不過它確實觸及私人政治權力的根源:促進政治行動的經濟集中化。提倡復興反托拉斯法並不是要跟其他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經濟提案競爭,但是重新分配財富的法律中,卻遭到集中的產業增強的政治權力所阻礙。經濟結構對於經濟政策領域的所有事物,產生潛在的影響。
為了要了解現在的處境與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回到過去那一刻,那個開始處理今日仍面臨之問題的時刻。
我們歷經了三十年政治與經濟的實驗。當美國與其他大國削弱了對工業巨頭之規模和實力的控制時,會發生什麼事?允許集中的私人權力不受限制的成長,並且放棄阻止大多數反競爭行為,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認為,答案相當簡單。我們正在重現一個世紀之前,亦即第一個鍍金年代(Gilded Age)的經濟與政治,依然重演更多二十世紀標誌性錯誤的巨大危險。那個時代的教訓讓我們知道,極端的經濟集中會導致嚴重的不平等與物質痛苦,因而助長人們支持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的領導政權。然而,我們似乎對上個世紀最大的教訓視而不見,並往同樣的道路走去。如果說我們從鍍金年代學到一件事,那就是:通往法西斯主義與獨裁政權的道路上,鋪滿了未能滿足一般大眾需求的經濟政策。
放眼全球經濟,並且目睹集中寡占與壟斷企業的主導狀況,金融、媒體、航空、電信等產業的壟斷可說最為明顯,也就是規模大的公司可以恣意對待顧客與競爭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明顯的,莫過於科技平台的巨大力量,尤其像 Google、Facebook,以及亞馬遜(Amazon),它們對我們的生活有無比的影響力。私人權力的集中帶來財富的再次集中,導致貧富差距更為擴大。
財富和權力的集中化,促使改變和激化選舉政治。就如鍍金年代,心懷不滿且日漸衰落的中產階級,開始支持激進反企業與民族主義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迎合了超越黨派的不滿情緒。在全球重新燃起的經濟民族主義,把中產階級的式微歸咎於外籍勞工、外國產品與菁英階層的陰謀。人們普遍對大企業以及其對待顧客的方式感到憤怒,尤其是那些集中或壟斷的產業,像是保險、製藥、航空,以及其他麻木不仁的企業巨獸。許多人害怕 Google、亞馬遜,以及 Facebook,擔心它們不只能控制商業,還會控制政治、新聞,以及我們的隱私訊息。
我們必須意識到,現在已然再次面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所稱的「巨頭的詛咒」,正如他警告的,此為對民主本身的強烈威脅。如果我們能夠接受產業對選舉與立法的影響力比普通公民還大時,還有什麼好說的呢?當美國製藥界能把藥品價格提高數倍,是因為自信政府不會出手干預?當中產階級對醫療保險、稅收、工作環境、住房,以及其他決定生活方式的政策沒有明顯的影響力,又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這些被忽視超過一個世代的問題。極度的產業集中,是否確實能與公民的大致平等、產業自由,或民主本身的前提相容?我們能否在一個壟斷企業主導的經濟中,創造廣大的財富與創業機會感?私人權力是否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這些企業對政府與大家的生活產生過大的影響力?
我認為,這些問題早有答案。本書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如何恢復以及更新針對企業巨獸的典型解方──反托拉斯法和其他反壟斷法,來迎接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在將近一個世紀中,反托拉斯法一直是反壟斷規範的實踐與理論,它試著限制產業過度集中,並且管制壟斷的行為。
直至上個世紀中葉,西方世界普遍將反托拉斯法理解為一個正常運作民主政體的必要部分,也是對私人權力的終極制衡。然而,才經過一個世代,反托拉斯法已經萎縮成無關緊要的影子,在某種程度上對壟斷的核心問題不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最高法院曾將反托拉斯法稱為「旨在保障自由與不受約束競爭的綜合經濟自由憲章」,但它已不再譴責壟斷,而是變得模稜兩可,有時甚至讚揚壟斷者,彷彿「反托拉斯」的「反」字已經被拋棄。
以下多數內容可以理解為聚焦在恢復這個原則:在制定與反覆強化反托拉斯法的過程中,美國在產業和國家政策上作出了至關重要且符合憲法的選擇。經過一段時間的激烈辯論,包括一九一二年經濟政策成為主要議題的總統大選,國家拒絕了壟斷經濟,並且在過去數十年來,多次選擇了保持其開放與競爭市場的傳統。必須將反托拉斯法的目標理解為尊重這個選擇,正如分權經濟的先知路易斯‧布蘭迪斯所言,反托拉斯法回答了一個問題:「美國的產業政策是競爭政策,或是壟斷政策?」
然而,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目前反托拉斯法正受到過度放縱觀念的傷害,芝加哥大學的羅勃‧伯克(Robert Bork)等人在一九七○年代首先廣為傳播這種思想。伯克的論調令人難以置信,一八九○年國會制定反托拉斯法,只是為了因應一項非常狹隘的危害:讓消費者付出更高的價格,而這個理論的切入點「消費者福利」已然削弱了反托拉斯法。它承諾帶來更高的確定性與科學嚴謹性,可是兩者都沒有實現,更重要的是,它拋棄了太多法律應該在民主國家發揮的作用,亦即限制私人權力無限制擴張,且維護經濟自由。
四十年前,法學家皮托夫斯基(Robert Pitofsky)警告:「在解釋反托拉斯法時排除特定的政治價值觀,是糟糕的歷史、不良的政策,以及劣質的法律。」他說的一點也沒錯。
隨著意識型態的轉變,反托拉斯法也曾陷入冬眠期,但它很快捲土重來以滿足時代的需求。為了實現它的使命,美國的反托拉斯法需要回歸其更廣泛的目標,並且提升其能力。它需要更好的工具來評估新形式的市場力量,來衡量宏觀經濟的論點,嚴肅看待產業集中與政治影響力之間的關聯。它需要利用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所提供的一切;它需要更強大的解決方法,包括重新拆分壟斷企業,這些措施的設計必須謹記反托拉斯的更大目標。最後,它需要讓法院重新參與布蘭迪斯所稱「抑制或甚至破壞競爭的行為」的執法工作。
在二十世紀,無法控制私人權力,以及未能照顧國民經濟需求的國家面臨了獨裁者的崛起,他們向人民承諾,會立即將大家從經濟困境中解救出來。一個與壟斷產業合作的政府最高領導人崛起,與法西斯主義與獨裁主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誠然,單靠反托拉斯法不能解除大企業的詛咒,或是消除私人權力的氾濫,但它擊中了問題的根本,重新啟動法律的引擎是解決已達憲法層面問題的重要關鍵。
因此,這本書遠沒有那麼激進,實際上是在呼籲走中間路線,在經濟結構控制我們之前,先控制住它。本書並不認為反托拉斯已退化到無可救藥,也沒有將其實踐者貼上不專業或不明智的標籤。相反的,本書主張,反托拉斯法已經看不見自己的目標,未能完成其核心任務。我提出的種種作法,可能可以重振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托拉斯法,將它恢復為正常運作民主政權中對私人權力的必要制衡。
●我們的鍍金年代,以及其將走向何方?
以前,我們可能以為主要的工業國家已經記取教訓。在經歷了共產主義、法西斯革命、大蕭條,以及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後,集體改變了對經濟及其在民主國家的角色。西方國家揚棄富人的自由放任政策、共產主義對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控制經濟,而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經濟政策的重新民主化,以及財富重分配的政治。這種路線帶來數十年的經濟成長,建立了中產階級,並且達到人類歷史上無法想像的繁榮水準,縮小了貧富間的巨大差距。
那是當時的情況,但是我們現在又回到這裡,就像是困在差勁的電影續集一般。今天就如同一九一○年代,工業化世界有兩個重要的經濟事實。
首先,再次出現貧富懸殊的鴻溝,這種趨勢在美國最為明顯,美國最富有一%的人,其收入占全國所得二三‧八%,控制全國財富的比例高達驚人的三八‧六%。
第二,回歸集中式經濟,亦即產業被更少且更大的公司所主導。正如世界經濟論壇證實,更高比例的全球財富被更少的公司與產業控制。在美國,一九九七年~二○一二年之間,七五%的美國產業更為集中。同樣的,自二○○○年以來,衡量市場集中度的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顯示,全美七五%以上的各行各業集中度增加。當美國公開市場已經失去了近五○%的上市公司,股市實際上是萎縮的。
最顯而易見的合併趨勢就在我們眼前:曾經開放且有競爭力的科技產業,已經集中成為少數幾個巨頭:Facebook、亞馬遜、Google,以及蘋果。這些公司掌握的權力似乎引起了大眾的關注,亦即我們面臨的問題已超越了狹隘的經濟範疇。大型科技公司無所不在,似乎對我們太過了解,似乎對我們的所見、所聞、所做,甚至所感有著過大的影響。當少數幾個人的決定可以對所有人造成極大影響,它重新引發了誰是真正主宰的爭議。套用參議員謝爾曼(John Sherman)的話來說,它們的權力感覺就像「國王的特權,與我們政府的形式並不一致。」
如今的經濟看起來就像是鍍金年代的仿製品,我們的政治與其不謀而合,也就不值得太驚訝了。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勞工遭受殘酷的對待,中小企業遭到破壞,廣泛的經濟苦難,造成廣大民眾的憤怒,以及對全新且不同事物的需求。強勢領導人承諾重新恢復偉大,為勞工提供生計,並且建立新秩序。
如今,經濟上的不滿正導致世界各地出現類似的憤怒民粹主義。一些人把自己的命運歸咎於移民、猶太人、穆斯林、基督徒,或可能是中國人或美國人,從而產生新一代的排外、民族主義,以及種族主義政治。其他人則指責銀行家、科技產業,或一般的企業。由於比父母更貧窮的羞恥感、像是用過即丟的勞工,以及前景遭到忽略等現象的煽動所致,我們目睹了憤怒與暴力政治的回歸。
從二十世紀得到的更好教訓顯示,較不激進的替代方案有其成效:幫助失業者與老年人的計畫,保護工作者與勞工的計畫,以及其他努力諸如削弱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固有的殘酷和不平等。因此,在美國出現了一種不同的運動和方法,來應對累積的私人權力的結構源頭,並以其目標「托拉斯」(trusts)來命名,因此有了「反托拉斯」法。
若有人認為反托拉斯法可以提供不平等或其他經濟問題的完整答案,那就過於誇張,不過它確實觸及私人政治權力的根源:促進政治行動的經濟集中化。提倡復興反托拉斯法並不是要跟其他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經濟提案競爭,但是重新分配財富的法律中,卻遭到集中的產業增強的政治權力所阻礙。經濟結構對於經濟政策領域的所有事物,產生潛在的影響。
為了要了解現在的處境與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回到過去那一刻,那個開始處理今日仍面臨之問題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