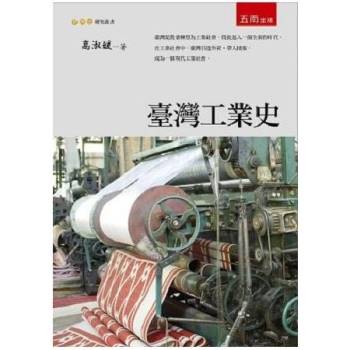第一章 十七世紀臺灣社會的木工技術
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臺灣對臺灣加工生產影響很大。荷蘭以商業立國,積極到各地尋找商業據點與商業機會,17世紀在臺灣建立米、糖經濟的發展模式,明鄭時期繼承之,清代有糖、米、茶及樟腦出口,直到1960年代臺灣經濟的發展基本上以農商連體經濟體系為主軸,延續三百餘年。 17世紀以來,農業與貿易結合為一體的農商連體經濟體系,是臺灣經濟的一大特色。
農商連體經濟體系不僅由農業與商業組成,就如甘蔗農業需要加工技術製成糖,成為商品,農業與商業之間還有加工業的支持。製糖業、燒磚業及在打狗的製鹽業、藍靛業等等很早就被注意, 磚窯業、石灰業、釀造業、包裝業及製蓆業等等也陸陸續續在臺灣建立。 這些加工產業形成農商連體經濟的商品生產基礎,從長時段歷史變遷角度來看,荷蘭時代的工商色彩對臺灣的加工生產活動有何影響?尚未被討論。荷蘭時代重要文獻《熱蘭遮城日誌》中記錄許多與木工相關事項,本章乃選擇以木工技術為線索,討論17世紀臺灣社會的加工生產如何形成,以及其影響。
一、蔗糖貿易與包裝
1624年荷蘭人來到大員時主要目標是建立據點從事中國、日本及東南亞、波斯到歐洲的轉口貿易。貿易需要商品,17世紀國際上流通的四大貿易商品是砂糖、棉布、生絲以及茶。 砂糖、棉布、生絲以及茶的原料都具有農業性質,臺南一帶平原寬廣、土地肥沃,溫度與陽光皆適合植物成長,擁有相當吸引人的農業條件,因而荷蘭人也花心思關注農業生產。1633年荷蘭人開始獎勵種植稻米、甘蔗,接著陸陸續續獎勵種植更多可以加工為商品的農產品。南部的平原缺少水利灌溉之便,稻是旱稻,收穫量不大,小麥、大麥、豆類、棉花、苧麻、煙草、大菁、油菜種子、薑黃等也有少量生產;栽培的各種作物中成績最好的是甘蔗。 荷蘭人也曾試著在臺灣養蠶,1646年種植桑樹,並從中國找來專家,那些專家把第一批蠶引進福爾摩沙(臺灣南部), 但並沒有看到明顯成果。總之,荷蘭人在臺灣栽培甘蔗、棉花、種桑養蠶是為了取得國際貿易商品,具有農業商品經濟性質。荷蘭人在臺灣的諸多嚐試,以種蔗製糖成績最好,則與漢人移民原鄉的社會經濟背景有密切關係。1633年荷蘭人在臺灣島內開始獎勵種植甘蔗時,從福建招募蔗農與製糖工人。從福建招募移民,除了地理上接近的因素之外,應該也有技術方面的考量。中國在很久以前就開始種甘蔗,唐代甘蔗糖業的雛型已經出現。福建栽培甘蔗的記錄最早出現在宋代,成書於12世紀的《糖霜譜》記錄了福建為中國境內糖霜五大產地之一,馬可波羅在1290年左右經過福建時,也盛讚當地糖業興盛。福建所產蔗糖運銷中國各地,也銷售到海外。 馬可波羅的著作在西方廣為流傳,荷蘭人可能有所知。16世紀福建的製糖技術因為國內外市場需求擴大的刺激,發展出一套與新時代對應的技術體系,從甘蔗栽培、品種選擇到壓榨、煎糖及精製成白糖等一系列的生產技術,是當時最進步的,而且這一套技術也隨著移民的足跡到達了東南亞各地。 荷蘭人從福建招募蔗農、製糖工人來臺,等於是透過擁有技術人才的直接移動,將福建進步的種蔗與製糖技術移轉到臺灣,這應該是獎勵種蔗製糖進行順利的重要因素。
1633年開始種植甘蔗,1635年開始生產200-300擔的少量蔗糖, 1636年臺灣生產蔗糖外銷之後,數額年年增加,1636年至1661年蔗糖生產額及外銷量、外銷地點如下〈表1-1〉所示,包含日本、巴達維亞、波斯等地,1650年之後有許多年產量都超過1萬擔。〈表1-1〉的數字不代表1636-1661年間實際生產、輸出的蔗糖數量,應該是代表這段期間有記錄可查的生產、輸出數量,可以看到的趨勢是臺灣的生產穩定成長,外銷量則時有消長。1647年之前大員商館輸出的砂糖量高於臺灣生產額,乃是在臺灣生產之外也收購中國砂糖,進行轉口貿易;1647年之後臺灣出口蔗糖以本地生產為主,到了1650年代末期曾經將蔗糖回銷中國。
砂糖不只是商品,種蔗製糖也帶有加工性質,生產砂糖及銷售過程中衍生出各種加工產業,例如砂糖生產過程需要生產工具,出口時需要包裝,從種植甘蔗、加工製成糖到包裝、島內物流集中到出口的一連串經濟活動中,需要用到的生產工具、包裝用品有蔗車、鐵鍋、竹籠等。荷蘭時代用糖桶、糖箱 包裝砂糖,製桶與製箱技術也出現在臺灣,是臺灣歷史中最早有明確記錄的木工技術。大員商館用糖桶裝砂糖,乃是因為從臺灣將蔗糖運到日本或運回巴達維亞(即今日之印尼雅加達)的海上航程又遠又長。中國商品包裝大部分使用竹籠、藤籠,並不適合長途海上運輸,例如1636年12月就曾發生從臺灣駛回巴達維亞船上載運的數籠砂糖,因遇到壞天氣弄溼溶解造成損失的記錄。 因此大員商館在購入商品後會再進行整理、包裝,將貴重商品重新包裝的更適合長程海上旅行,例如1643年9月記載整天包裝要運回荷蘭的黃色生絲、白絲及絲質布料;1644年6月連續幾天下雨,因此無法修理受損的戎克船,也無法做我們平常的工作,只是天天將運來的糖裝箱。 大員商館貿易量擴大時,商品包裝需求也跟著擴大,荷蘭人聘請中國人從事包裝、整理與挑運,專門製造包裝絲綢的籃子與竹蓆的中國工匠,行情也跟著看漲。 包裝在貿易活動中不太起眼,做起來也似乎不怎麼帶勁,但卻是不可或缺的活動,荷蘭人雇用中國人從事包裝及生產包裝用的籃子與竹蓆,有編織技術的工匠在荷蘭時代也來到了轉口貿易據點的安平。
1630年代荷蘭人使用的糖桶是進口材料後在臺灣加工。1635年7月從福建沿海來到大員的5艘戎克船中有2艘載糖,1艘載木板與米,那些木板是要用來做糖桶的,另2艘載木板與鍋。 1636-1638年從大陸各地至大員船隻所載運的物品中,出現「砂糖桶的木板」之記錄共有15次。 「砂糖桶的木板」一再地出現在商品表單,屬重要商品,但性質上屬原物料,需要加工組裝成糖桶才能使用,從中國進口的木板,合理推測是進口後在大員製成糖桶,然後拿來包裝要出口的糖。當時大員商館雇用的工匠中有箍桶匠,如1637年10月,大員商館出發攻打大武壠時,被留在城堡裡的人有部分軍隊、船員、木匠、水泥匠、冶鐵匠及箍桶匠等。 大員商館雇用箍桶匠,表示糖桶極可能是由大員商館雇用工匠直接生產。
二、漢人農民製造糖桶與糖箱
大員商館進行遠洋貿易,收購商品後重新整理包裝的記載時斷時續。1645-1646年,臺灣蔗糖產量增加時再度出現許多與糖桶相關的記載,呈現的內涵與1630年代的記錄已經不同了。1640年代的最重要變化是漢人農業移民參與了生產糖箱或糖桶的工作,不再只是依賴進口。1640年代中國處在明清改朝換代的混亂期,避難來臺的漢人移民快速增加,蔗糖生產量也隨之增加,荷蘭人乃委託漢人移民製造糖桶。1647年6月,荷蘭東印度大員商館為了避免糖桶缺貨,鼓勵中國人製造更多糖桶,乃跟四個重要的中國人達成協議:如果他們在三個半月內能夠交來大批的糖桶,我們將對最大的糖桶每個多支付0.125里爾,即支付1.125里爾(必須桶子的兩個底層都是以一塊木板製作的),不然就支付1里爾,而最小的糖桶將支付0.875里爾。但是如果他們不能在上述期限交貨,則這條件就失效。 1655年3月,大員商館長官派人去打鑼通告大家說,有意要供應糖箱給大員商館的人,必須於本月15日以前準備好,過了這日期就暫時不再收購任何糖箱(因為缺乏地方來堆放這些糖箱),不過可以準備好製造糖箱的木板,以便大員商館以後一有需要,即可迅速製造糖箱供應。 這些記載告訴我們1640年代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已開始製造糖桶了,交易過程中,大員商館採用價格操作鼓勵漢人移民在規定期限內製造符合大員商館要求的商品,重視時間與效率。
1658年的一筆資料確定製造糖箱的人是農民。1658年1月大員商館收到一份中國人長老、商人及鄉村的農人提出來的陳情書,要求提高收購蔗糖價格。這要求被完全拒絕了,不過在另一方面允許他們說,所有的糖,不分種類品級,將來出口稅都將從每擔支付30 stuyvers(30x0.05=1.5荷盾),減為每擔支付20 stuyvers(1荷盾),如此可望增加糖的出口量。此外,因上述中國人長老與農夫代表懇切的要求,決定將從大員商館的帳號預支七千里爾給他們,用以供應堅固的糖箱給大員商館,條件是他們必須提出可靠的保證人,而且那些糖箱必須於四個月內交貨。 記錄中強調中國人長老與農夫代表,未將一起陳情的商人涵括進去,也告訴我們製造糖箱與農民密切相關。荷蘭人的貿易活動中蔗糖的地位一直很重要,一年需要多少糖箱?可以從一箱大約可以裝多少糖推測。1656年記載「將175,780斤砂糖分裝在750個箱子裡。」則一箱約可裝234斤。翌年有兩筆記載,「分裝在653箱裡的1,527擔白砂糖」;「651箱砂糖即1,514.5擔砂糖」 ,換算的話前者一箱裝2.34擔,後者裝2.33擔。荷蘭時代一擔是100斤,這三筆資料很相近,一箱的重量都在234斤左右。若依這個容量估計,一萬擔砂糖需要4,276個箱子,需要量相當多。17世紀以農業經濟為主流的時代,或說是近代之前社會分工還不太明確的時代,農民與工人、商人間的身分轉換容易,農民在需要時可以參與商業活動,農民們在農閒或有需要時也可以製造加工品,將糖箱板組裝成糖箱或糖桶的工作,所需要的木工技術也不算困難,而且有需求就會吸引人才,就如1630年代大員商館到中國招募有種蔗製糖技術的移民一般,1640年代大員商館的糖桶、糖箱需求,也很可能吸引有木工技術的漢人移民來到臺灣。
農民參與糖桶生產之後,很快地學會用它來裝糖。1648年4月大員商館用告示通告大家,以後糖不可用桶子裝來交貨,要用籃子裝來交貨,因為用桶子裝,如果糖濕了很難再乾,而將損壞。 蔗農模仿荷蘭人用糖桶裝糖交貨被大員商館明令禁止。但在1657年,大員商館改變立場,規定蔗農必須自行將所收穫的糖裝進糖箱裡。這規定予期會有好的效果,公司將可因此排除倉庫的空間不足和因失火遭受損失的問題。 大員商館改變立場的主要考量是糖箱保存的成本很高,空的糖箱占用大量的倉庫空間,糖箱也是易燃物,萬一失火將造成重大損失。在裝糖前再收購糖箱,或是要求蔗農用糖箱裝糖,都是把保存糖箱的工作交給農民,儲存空間及火災等損失也轉嫁給農民負擔。
總之,歷史記錄呈現1640年代來臺的漢人移民不但有製糖技術,也參與糖桶、糖箱生產,擁有木工技術。17世紀中國進步的生產技術,隨著移民足跡遍及東南亞、琉球、朝鮮,然後經由朝鮮帶到日本。 擁有農業種植及加工製糖技術的漢人移民也渡海來到臺灣,並能敏銳因應荷蘭人的蔗糖包裝需求製造糖箱,也是直接透過人才的移動帶來各種加工技術,屬於17世紀漢人技術移民向海外各地擴展的一個篇章。三、木工技術與交通工具
17世紀來臺的漢人移民有木工技術,對臺灣工業史有重要意義。因為18世紀之前物質的世界可以說是木材的時代,運輸工具、家具、榨油機以及大部分的農具都用木材製造。 應用木工技術進行生產的品項很廣,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技術。木工的原料來自樹木,臺灣在17世紀時被稱為福爾摩沙,即以樹林青茂聞名,木材資源豐富。原料與技術具備的臺灣木匠,除了糖箱之外還可以生產些什麼呢?
(一)板輪牛車
引人注意的第一種產品是板輪牛車。1658年1月大員商館派去蒐集建造新領港船木料的木匠工頭寫的一封信,留下了重要相關資訊。他寫說,在鳳山的角彎落(Hoeck van Hongswa)砍伐的栗子樹無法利用水路運出來,因為從那裡到Appeliance的道路盡是沙土、丘陵、灌木和沼澤的混合。那座森林雖然有良好平坦的牛車路,可以從打狗的內河通到森林前面的平地,路程約兩小時,但不知道該森林裡面有多大,因為無法走過那些叢生的荊棘,若能找到進入該森林的通道去砍伐木材,運到打狗的內河裡,那就很容易在東北季風時用小船運出來了。又寫說,那條下淡水河的河水都消失了,有些地方乾涸到連空盪盪的舢舨也無法通航,必須又拖又抬地走過一刻鐘以上的乾地,因此,從那裡也沒有辦法取得木頭,除非由原住民用體力來拖扛,從高處搬運到下面來。我們看完這兩封信,立刻寫回信交給送信來的人帶回去,回答說,他們可以從那附近的農夫調用為搬出那些已經砍伐的木頭所需數量的牛車,也可以從在那裡為中國人工作的鋸木工人當中,雇用所需人數的鋸木工人來為我們工作,答應他們將會支付好價錢給他們。 荷蘭時代在高屏溪流域伐木,農夫們跟隨著伐木工人的足跡進入下淡水溪森林附近耕種,也已經建立了從河邊直通農地的牛車路,也擁有牛車這種適合陸地的運輸工具,有河流之處則利用小船、舢舨。我們可以想像當時臺灣內部的生產情形。米、糖經濟架構下農產品也是經濟商品,米穀與蔗糖都屬於沉重且單價低的商品,運輸需求較大,特別是甘蔗含有超過80%的水分,加工之前很重,更需要運輸工具,因此農夫足跡所到之處如果沒有河運可以利用,建構牛車路是另一種選擇。1658年大員商館所提及可以運送木材的牛車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板輪牛車。板輪牛車是以木板做成兩個大輪子,無軸輻之分並使用牛力拖曳的牛車,其上若編竹為箱,就叫笨車。根據文獻考證,臺灣漢人的原鄉漳、泉及日本、琉球一帶並未發現板輪牛車,因而應該不是漢人移民帶進來的。板輪牛車傳入的路線可能有兩條:一條是荷蘭人統治南臺灣時自歐洲輸入;一條是爪哇的華人領袖蘇鳴崗由南洋一帶傳入,而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板輪牛車傳入臺灣後有很多名字,如牛車、大車、笨車、柴頭車,甚至也被叫做馬車。板輪牛車的車輪由三片木板合併而成,主要使用樟木、烏心木及柜木等材質,車輪直徑五、六尺(約150至170公分),連牛軛總長約4公尺,寬約1.5公尺。木匠做一輛板輪牛車只要五個工作天即可完成。 蘇鳴崗為泉州人,為巴達維亞的華僑領袖,1636年辭去甲必丹之職回中國途中,曾嚮應荷蘭大員商館的開墾號召,落腳臺灣,向漢人通事購屋翻修居住,並招徠移民入墾,1639年3月重返巴城,於1644年客死該地。 蘇鳴崗長期在印尼活動,從印尼間接引進歐洲人使用的板輪牛車是有可能的,因為板輪牛車的源頭是歐洲。在歐洲,人們經常可以見到一對牛拖著實心輪子的木車,而這種牛車在殖民時代也被帶到巴西,潘帕斯草原由牛所拉的笨重牛車使用實心輪子,車軸轉動時吱吱響。 板輪牛車隨著歐洲人足跡進入東南亞,再由蘇鳴崗引進臺灣是可能的,如果真的是由蘇鳴崗引進的,那麼年代就應該落在1636-1639年之間。也有可能是荷蘭人直接帶進來的。不論如何,板輪牛車確定在荷蘭人統治臺灣時已經傳入臺灣。
板輪牛車在荷蘭時代傳入臺灣後迅速在臺灣南部普及,1684年臺灣剛改隸清朝統治時,已經是男女出入、輓運貨物,俱用牛車,如吳越之用舟楫也。 康熙年間,諸羅縣境內土地平曠,便於車行,車輪高五尺多,一頭牛約可運六、七百斤貨物,編竹為車籠以盛五穀;誅茅採薪時則拿掉車籠,梱束以載。行遠則可乘三、四人,貨物更重時則另橫一木於右,摯靷加軛,多用一頭牛來拉。婦女要搭乘時置竹亭於牛車上,或用布帷。因為大家都用牛車,導致牛價騰貴,水牛牯強健者要3萬錢才能買到,漢莊、番社無不家製車而戶畜牛者。 板輪牛車可以載貨、載人,與牛一起在臺灣迅速普及,不分種族,很多農家擁有這種運輸工具。板輪牛車受到大眾歡迎的原因與地理條件有關係,使用高大的圓型木板為車輪,適合南部平原地區的砂質地。
南北路任載及人乘者,均用牛車…蓋臺地雨後潦水停塗,有輻輒障水難行,不如木板便利也。車轍縱橫衢市間,音脆薄,如哀如訴;侵曉夢回時尤不耐聽。
臺灣使用板輪牛車如吳越之用舟楫,需要量相當大,而福建並沒有生產,印尼距離臺灣遙遠,這麼笨重的商品不太可能一直大量遠距離輸送。而且板輪牛車最大的特色是製造技術簡單,臺灣的木匠有能力生產也不是不可能。板輪牛車使用的材料都是取自本地,如土楠可為輔輻,甚堅韌;赤鱗質堅,大者取為車心,小者用為籬柱;麻竹不堅厚,止可製車籠、糖籠、倉笨、篾簟等物。 鳳山地區牛車軌選用堅木為之,中駕一牛引重致遠,旁用一牛佐之,用赤鱗為車心,用土楠為輔輻,用麻竹製車籠。 板輪牛車生產技術相對簡單,且在臺灣可以找到適合的材料,17世紀就在臺灣生產的可能性很大。
板輪牛車在臺灣使用約三百年,到了日本時代還在用。來自溫帶的日本人看到這種牛車,感受到它的原始而獨特的風格,輪子的軋軋聲也敲出南國情緒。當時板輪牛車的地理分布仍然以中南部地方為主,幾乎每家農戶都有一輛車,用來搬運農產品及肥料,東臺灣也有,中北部很少。整部車都是用木材打造的,樟是最受歡迎的材料,雖然看起來粗笨,卻很實用,即使是雨後滿地泥濘也暢行無阻,只要調整牛隻數量,最多可以載5,000斤的貨物。但因板輪是一個大圓盤,會嚴重損傷街道,日本領臺後為了保護道路,乃限制使用場域,只能在私人的田間小路、山腳、溪川的砂礫地及道路不發達的海岸地方使用。禁令發布後,新製板輪牛車的數量就減少了。 政府選擇保護街道,板輪牛車使用空間受到限制,臺灣各地從17世紀一直活躍到20世紀初期,具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因政治因素不再受青睞,也就很少生產,接著火車、腳踏車、機車、汽車等近代運輸工具又取而代之,牛隻也慢慢卸下了運輸的重荷,只殘存在少數地方,引發一絲思古悠情。(二)民用河船、海船的生產
荷蘭時代出現河流用的舢舨,也可能是在地生產的。木材在傳統社會裡是造船的主要材料,船是清代臺灣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這種交通工具的生產型式的主體是船匠。船依用途分為海船以及河船,海船體積大,且依船主身分又可分為官船與民船。官船即所謂軍工戰船,臺灣從康熙年間已經具有造船技術,直到道光年間一直在臺灣打造軍用海船。
臺南軍工廠外有民廠,又名廠仔,在硓古石地方;又有帆廠在其邊,造船亦木匠類也。 民廠較少被重視,並不代表沒有生產。就如蘭嶼人會在海邊自己打造自己的船一般,根據臺灣總督府之調查,擁有木造船技術的船匠並不需要特定的工作場所,在臺灣的大小港灣、漁業據點或河口停船處附近,都可以打造新船或修理舊船。臺灣使用的船,種類相當多,有在海上及河川下游、上游使用的貨船、漁船還有運大肥的特殊用船,如下〈表1-2〉。造船時使用的木材種類很多,船匠選用硬度、靭度適合的材料製造修理,大多數是用臺灣本地所產木材。選材時會考量是在哪裡使用以及用途,如河川上、中、下游各有不同的船,材料條件也會調整,也會依捕魚、載貨或運送大肥等不同用途,使用不同的船,讓人印象深刻。在河川使用的船製造原理與海船相似,不同點是傾向瘦長,而且對於堅牢程度的要求更高。口述調查資料也證實了民廠造船時的機動性,如造船時先在近水的地方搭寮做為臨時工廠,船造好下水後寮就拆掉。造船的木匠需要三年四個月的學徒養成期,技術學成後可得到一本記載船的大小和尺寸的簿子。臺南陳家船廠平時只雇用十餘人,工作繁忙時再加雇熟練工人。 木造船在中國使用很久,臺灣漢人移民的原鄉靠海、擅長造船,擁有木造船的修理及製造技術之可能性很高,渡海來臺之後仍然延續傳統學徒制,代代傳承技術。
木造船之外還有竹筏,主要材料是麻竹與藤。竹筏種類也很多,有沿海漁業專用的漁筏,還有用來搬運貨物的溪筏,兩者型態大同小異。大部分的竹筏是在溪、魚塭中使用的小型竹筏,分布相當普遍,因為臺灣的麻竹產地分布很廣,而且製造費用低廉、製法簡單,是可以自己打造來使用的。臺灣的港口因為有湧,大船很難靠岸,必須用竹筏將旅客與貨物接駁上岸,是清代兩岸行旅與商品往來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臺灣也打造過可以渡海的竹筏,從國際視野進行比較研究,確立其技術的先進, 也證明臺灣民間造船技術頗有水準。
總之,傳統木匠用臺灣的樹林、竹林所產原料,用雙手在海口、河口各地打造竹筏、海船、溪船,加上板輪牛車,這些運輸工具共同串連了海洋、河流與陸地,方便行旅來往各地,也負責將米及砂糖從農村各地集結到港口,然後外銷,形塑了臺灣島內外的物流與人流,是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交通動脈。
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臺灣對臺灣加工生產影響很大。荷蘭以商業立國,積極到各地尋找商業據點與商業機會,17世紀在臺灣建立米、糖經濟的發展模式,明鄭時期繼承之,清代有糖、米、茶及樟腦出口,直到1960年代臺灣經濟的發展基本上以農商連體經濟體系為主軸,延續三百餘年。 17世紀以來,農業與貿易結合為一體的農商連體經濟體系,是臺灣經濟的一大特色。
農商連體經濟體系不僅由農業與商業組成,就如甘蔗農業需要加工技術製成糖,成為商品,農業與商業之間還有加工業的支持。製糖業、燒磚業及在打狗的製鹽業、藍靛業等等很早就被注意, 磚窯業、石灰業、釀造業、包裝業及製蓆業等等也陸陸續續在臺灣建立。 這些加工產業形成農商連體經濟的商品生產基礎,從長時段歷史變遷角度來看,荷蘭時代的工商色彩對臺灣的加工生產活動有何影響?尚未被討論。荷蘭時代重要文獻《熱蘭遮城日誌》中記錄許多與木工相關事項,本章乃選擇以木工技術為線索,討論17世紀臺灣社會的加工生產如何形成,以及其影響。
一、蔗糖貿易與包裝
1624年荷蘭人來到大員時主要目標是建立據點從事中國、日本及東南亞、波斯到歐洲的轉口貿易。貿易需要商品,17世紀國際上流通的四大貿易商品是砂糖、棉布、生絲以及茶。 砂糖、棉布、生絲以及茶的原料都具有農業性質,臺南一帶平原寬廣、土地肥沃,溫度與陽光皆適合植物成長,擁有相當吸引人的農業條件,因而荷蘭人也花心思關注農業生產。1633年荷蘭人開始獎勵種植稻米、甘蔗,接著陸陸續續獎勵種植更多可以加工為商品的農產品。南部的平原缺少水利灌溉之便,稻是旱稻,收穫量不大,小麥、大麥、豆類、棉花、苧麻、煙草、大菁、油菜種子、薑黃等也有少量生產;栽培的各種作物中成績最好的是甘蔗。 荷蘭人也曾試著在臺灣養蠶,1646年種植桑樹,並從中國找來專家,那些專家把第一批蠶引進福爾摩沙(臺灣南部), 但並沒有看到明顯成果。總之,荷蘭人在臺灣栽培甘蔗、棉花、種桑養蠶是為了取得國際貿易商品,具有農業商品經濟性質。荷蘭人在臺灣的諸多嚐試,以種蔗製糖成績最好,則與漢人移民原鄉的社會經濟背景有密切關係。1633年荷蘭人在臺灣島內開始獎勵種植甘蔗時,從福建招募蔗農與製糖工人。從福建招募移民,除了地理上接近的因素之外,應該也有技術方面的考量。中國在很久以前就開始種甘蔗,唐代甘蔗糖業的雛型已經出現。福建栽培甘蔗的記錄最早出現在宋代,成書於12世紀的《糖霜譜》記錄了福建為中國境內糖霜五大產地之一,馬可波羅在1290年左右經過福建時,也盛讚當地糖業興盛。福建所產蔗糖運銷中國各地,也銷售到海外。 馬可波羅的著作在西方廣為流傳,荷蘭人可能有所知。16世紀福建的製糖技術因為國內外市場需求擴大的刺激,發展出一套與新時代對應的技術體系,從甘蔗栽培、品種選擇到壓榨、煎糖及精製成白糖等一系列的生產技術,是當時最進步的,而且這一套技術也隨著移民的足跡到達了東南亞各地。 荷蘭人從福建招募蔗農、製糖工人來臺,等於是透過擁有技術人才的直接移動,將福建進步的種蔗與製糖技術移轉到臺灣,這應該是獎勵種蔗製糖進行順利的重要因素。
1633年開始種植甘蔗,1635年開始生產200-300擔的少量蔗糖, 1636年臺灣生產蔗糖外銷之後,數額年年增加,1636年至1661年蔗糖生產額及外銷量、外銷地點如下〈表1-1〉所示,包含日本、巴達維亞、波斯等地,1650年之後有許多年產量都超過1萬擔。〈表1-1〉的數字不代表1636-1661年間實際生產、輸出的蔗糖數量,應該是代表這段期間有記錄可查的生產、輸出數量,可以看到的趨勢是臺灣的生產穩定成長,外銷量則時有消長。1647年之前大員商館輸出的砂糖量高於臺灣生產額,乃是在臺灣生產之外也收購中國砂糖,進行轉口貿易;1647年之後臺灣出口蔗糖以本地生產為主,到了1650年代末期曾經將蔗糖回銷中國。
砂糖不只是商品,種蔗製糖也帶有加工性質,生產砂糖及銷售過程中衍生出各種加工產業,例如砂糖生產過程需要生產工具,出口時需要包裝,從種植甘蔗、加工製成糖到包裝、島內物流集中到出口的一連串經濟活動中,需要用到的生產工具、包裝用品有蔗車、鐵鍋、竹籠等。荷蘭時代用糖桶、糖箱 包裝砂糖,製桶與製箱技術也出現在臺灣,是臺灣歷史中最早有明確記錄的木工技術。大員商館用糖桶裝砂糖,乃是因為從臺灣將蔗糖運到日本或運回巴達維亞(即今日之印尼雅加達)的海上航程又遠又長。中國商品包裝大部分使用竹籠、藤籠,並不適合長途海上運輸,例如1636年12月就曾發生從臺灣駛回巴達維亞船上載運的數籠砂糖,因遇到壞天氣弄溼溶解造成損失的記錄。 因此大員商館在購入商品後會再進行整理、包裝,將貴重商品重新包裝的更適合長程海上旅行,例如1643年9月記載整天包裝要運回荷蘭的黃色生絲、白絲及絲質布料;1644年6月連續幾天下雨,因此無法修理受損的戎克船,也無法做我們平常的工作,只是天天將運來的糖裝箱。 大員商館貿易量擴大時,商品包裝需求也跟著擴大,荷蘭人聘請中國人從事包裝、整理與挑運,專門製造包裝絲綢的籃子與竹蓆的中國工匠,行情也跟著看漲。 包裝在貿易活動中不太起眼,做起來也似乎不怎麼帶勁,但卻是不可或缺的活動,荷蘭人雇用中國人從事包裝及生產包裝用的籃子與竹蓆,有編織技術的工匠在荷蘭時代也來到了轉口貿易據點的安平。
1630年代荷蘭人使用的糖桶是進口材料後在臺灣加工。1635年7月從福建沿海來到大員的5艘戎克船中有2艘載糖,1艘載木板與米,那些木板是要用來做糖桶的,另2艘載木板與鍋。 1636-1638年從大陸各地至大員船隻所載運的物品中,出現「砂糖桶的木板」之記錄共有15次。 「砂糖桶的木板」一再地出現在商品表單,屬重要商品,但性質上屬原物料,需要加工組裝成糖桶才能使用,從中國進口的木板,合理推測是進口後在大員製成糖桶,然後拿來包裝要出口的糖。當時大員商館雇用的工匠中有箍桶匠,如1637年10月,大員商館出發攻打大武壠時,被留在城堡裡的人有部分軍隊、船員、木匠、水泥匠、冶鐵匠及箍桶匠等。 大員商館雇用箍桶匠,表示糖桶極可能是由大員商館雇用工匠直接生產。
二、漢人農民製造糖桶與糖箱
大員商館進行遠洋貿易,收購商品後重新整理包裝的記載時斷時續。1645-1646年,臺灣蔗糖產量增加時再度出現許多與糖桶相關的記載,呈現的內涵與1630年代的記錄已經不同了。1640年代的最重要變化是漢人農業移民參與了生產糖箱或糖桶的工作,不再只是依賴進口。1640年代中國處在明清改朝換代的混亂期,避難來臺的漢人移民快速增加,蔗糖生產量也隨之增加,荷蘭人乃委託漢人移民製造糖桶。1647年6月,荷蘭東印度大員商館為了避免糖桶缺貨,鼓勵中國人製造更多糖桶,乃跟四個重要的中國人達成協議:如果他們在三個半月內能夠交來大批的糖桶,我們將對最大的糖桶每個多支付0.125里爾,即支付1.125里爾(必須桶子的兩個底層都是以一塊木板製作的),不然就支付1里爾,而最小的糖桶將支付0.875里爾。但是如果他們不能在上述期限交貨,則這條件就失效。 1655年3月,大員商館長官派人去打鑼通告大家說,有意要供應糖箱給大員商館的人,必須於本月15日以前準備好,過了這日期就暫時不再收購任何糖箱(因為缺乏地方來堆放這些糖箱),不過可以準備好製造糖箱的木板,以便大員商館以後一有需要,即可迅速製造糖箱供應。 這些記載告訴我們1640年代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已開始製造糖桶了,交易過程中,大員商館採用價格操作鼓勵漢人移民在規定期限內製造符合大員商館要求的商品,重視時間與效率。
1658年的一筆資料確定製造糖箱的人是農民。1658年1月大員商館收到一份中國人長老、商人及鄉村的農人提出來的陳情書,要求提高收購蔗糖價格。這要求被完全拒絕了,不過在另一方面允許他們說,所有的糖,不分種類品級,將來出口稅都將從每擔支付30 stuyvers(30x0.05=1.5荷盾),減為每擔支付20 stuyvers(1荷盾),如此可望增加糖的出口量。此外,因上述中國人長老與農夫代表懇切的要求,決定將從大員商館的帳號預支七千里爾給他們,用以供應堅固的糖箱給大員商館,條件是他們必須提出可靠的保證人,而且那些糖箱必須於四個月內交貨。 記錄中強調中國人長老與農夫代表,未將一起陳情的商人涵括進去,也告訴我們製造糖箱與農民密切相關。荷蘭人的貿易活動中蔗糖的地位一直很重要,一年需要多少糖箱?可以從一箱大約可以裝多少糖推測。1656年記載「將175,780斤砂糖分裝在750個箱子裡。」則一箱約可裝234斤。翌年有兩筆記載,「分裝在653箱裡的1,527擔白砂糖」;「651箱砂糖即1,514.5擔砂糖」 ,換算的話前者一箱裝2.34擔,後者裝2.33擔。荷蘭時代一擔是100斤,這三筆資料很相近,一箱的重量都在234斤左右。若依這個容量估計,一萬擔砂糖需要4,276個箱子,需要量相當多。17世紀以農業經濟為主流的時代,或說是近代之前社會分工還不太明確的時代,農民與工人、商人間的身分轉換容易,農民在需要時可以參與商業活動,農民們在農閒或有需要時也可以製造加工品,將糖箱板組裝成糖箱或糖桶的工作,所需要的木工技術也不算困難,而且有需求就會吸引人才,就如1630年代大員商館到中國招募有種蔗製糖技術的移民一般,1640年代大員商館的糖桶、糖箱需求,也很可能吸引有木工技術的漢人移民來到臺灣。
農民參與糖桶生產之後,很快地學會用它來裝糖。1648年4月大員商館用告示通告大家,以後糖不可用桶子裝來交貨,要用籃子裝來交貨,因為用桶子裝,如果糖濕了很難再乾,而將損壞。 蔗農模仿荷蘭人用糖桶裝糖交貨被大員商館明令禁止。但在1657年,大員商館改變立場,規定蔗農必須自行將所收穫的糖裝進糖箱裡。這規定予期會有好的效果,公司將可因此排除倉庫的空間不足和因失火遭受損失的問題。 大員商館改變立場的主要考量是糖箱保存的成本很高,空的糖箱占用大量的倉庫空間,糖箱也是易燃物,萬一失火將造成重大損失。在裝糖前再收購糖箱,或是要求蔗農用糖箱裝糖,都是把保存糖箱的工作交給農民,儲存空間及火災等損失也轉嫁給農民負擔。
總之,歷史記錄呈現1640年代來臺的漢人移民不但有製糖技術,也參與糖桶、糖箱生產,擁有木工技術。17世紀中國進步的生產技術,隨著移民足跡遍及東南亞、琉球、朝鮮,然後經由朝鮮帶到日本。 擁有農業種植及加工製糖技術的漢人移民也渡海來到臺灣,並能敏銳因應荷蘭人的蔗糖包裝需求製造糖箱,也是直接透過人才的移動帶來各種加工技術,屬於17世紀漢人技術移民向海外各地擴展的一個篇章。三、木工技術與交通工具
17世紀來臺的漢人移民有木工技術,對臺灣工業史有重要意義。因為18世紀之前物質的世界可以說是木材的時代,運輸工具、家具、榨油機以及大部分的農具都用木材製造。 應用木工技術進行生產的品項很廣,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技術。木工的原料來自樹木,臺灣在17世紀時被稱為福爾摩沙,即以樹林青茂聞名,木材資源豐富。原料與技術具備的臺灣木匠,除了糖箱之外還可以生產些什麼呢?
(一)板輪牛車
引人注意的第一種產品是板輪牛車。1658年1月大員商館派去蒐集建造新領港船木料的木匠工頭寫的一封信,留下了重要相關資訊。他寫說,在鳳山的角彎落(Hoeck van Hongswa)砍伐的栗子樹無法利用水路運出來,因為從那裡到Appeliance的道路盡是沙土、丘陵、灌木和沼澤的混合。那座森林雖然有良好平坦的牛車路,可以從打狗的內河通到森林前面的平地,路程約兩小時,但不知道該森林裡面有多大,因為無法走過那些叢生的荊棘,若能找到進入該森林的通道去砍伐木材,運到打狗的內河裡,那就很容易在東北季風時用小船運出來了。又寫說,那條下淡水河的河水都消失了,有些地方乾涸到連空盪盪的舢舨也無法通航,必須又拖又抬地走過一刻鐘以上的乾地,因此,從那裡也沒有辦法取得木頭,除非由原住民用體力來拖扛,從高處搬運到下面來。我們看完這兩封信,立刻寫回信交給送信來的人帶回去,回答說,他們可以從那附近的農夫調用為搬出那些已經砍伐的木頭所需數量的牛車,也可以從在那裡為中國人工作的鋸木工人當中,雇用所需人數的鋸木工人來為我們工作,答應他們將會支付好價錢給他們。 荷蘭時代在高屏溪流域伐木,農夫們跟隨著伐木工人的足跡進入下淡水溪森林附近耕種,也已經建立了從河邊直通農地的牛車路,也擁有牛車這種適合陸地的運輸工具,有河流之處則利用小船、舢舨。我們可以想像當時臺灣內部的生產情形。米、糖經濟架構下農產品也是經濟商品,米穀與蔗糖都屬於沉重且單價低的商品,運輸需求較大,特別是甘蔗含有超過80%的水分,加工之前很重,更需要運輸工具,因此農夫足跡所到之處如果沒有河運可以利用,建構牛車路是另一種選擇。1658年大員商館所提及可以運送木材的牛車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板輪牛車。板輪牛車是以木板做成兩個大輪子,無軸輻之分並使用牛力拖曳的牛車,其上若編竹為箱,就叫笨車。根據文獻考證,臺灣漢人的原鄉漳、泉及日本、琉球一帶並未發現板輪牛車,因而應該不是漢人移民帶進來的。板輪牛車傳入的路線可能有兩條:一條是荷蘭人統治南臺灣時自歐洲輸入;一條是爪哇的華人領袖蘇鳴崗由南洋一帶傳入,而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板輪牛車傳入臺灣後有很多名字,如牛車、大車、笨車、柴頭車,甚至也被叫做馬車。板輪牛車的車輪由三片木板合併而成,主要使用樟木、烏心木及柜木等材質,車輪直徑五、六尺(約150至170公分),連牛軛總長約4公尺,寬約1.5公尺。木匠做一輛板輪牛車只要五個工作天即可完成。 蘇鳴崗為泉州人,為巴達維亞的華僑領袖,1636年辭去甲必丹之職回中國途中,曾嚮應荷蘭大員商館的開墾號召,落腳臺灣,向漢人通事購屋翻修居住,並招徠移民入墾,1639年3月重返巴城,於1644年客死該地。 蘇鳴崗長期在印尼活動,從印尼間接引進歐洲人使用的板輪牛車是有可能的,因為板輪牛車的源頭是歐洲。在歐洲,人們經常可以見到一對牛拖著實心輪子的木車,而這種牛車在殖民時代也被帶到巴西,潘帕斯草原由牛所拉的笨重牛車使用實心輪子,車軸轉動時吱吱響。 板輪牛車隨著歐洲人足跡進入東南亞,再由蘇鳴崗引進臺灣是可能的,如果真的是由蘇鳴崗引進的,那麼年代就應該落在1636-1639年之間。也有可能是荷蘭人直接帶進來的。不論如何,板輪牛車確定在荷蘭人統治臺灣時已經傳入臺灣。
板輪牛車在荷蘭時代傳入臺灣後迅速在臺灣南部普及,1684年臺灣剛改隸清朝統治時,已經是男女出入、輓運貨物,俱用牛車,如吳越之用舟楫也。 康熙年間,諸羅縣境內土地平曠,便於車行,車輪高五尺多,一頭牛約可運六、七百斤貨物,編竹為車籠以盛五穀;誅茅採薪時則拿掉車籠,梱束以載。行遠則可乘三、四人,貨物更重時則另橫一木於右,摯靷加軛,多用一頭牛來拉。婦女要搭乘時置竹亭於牛車上,或用布帷。因為大家都用牛車,導致牛價騰貴,水牛牯強健者要3萬錢才能買到,漢莊、番社無不家製車而戶畜牛者。 板輪牛車可以載貨、載人,與牛一起在臺灣迅速普及,不分種族,很多農家擁有這種運輸工具。板輪牛車受到大眾歡迎的原因與地理條件有關係,使用高大的圓型木板為車輪,適合南部平原地區的砂質地。
南北路任載及人乘者,均用牛車…蓋臺地雨後潦水停塗,有輻輒障水難行,不如木板便利也。車轍縱橫衢市間,音脆薄,如哀如訴;侵曉夢回時尤不耐聽。
臺灣使用板輪牛車如吳越之用舟楫,需要量相當大,而福建並沒有生產,印尼距離臺灣遙遠,這麼笨重的商品不太可能一直大量遠距離輸送。而且板輪牛車最大的特色是製造技術簡單,臺灣的木匠有能力生產也不是不可能。板輪牛車使用的材料都是取自本地,如土楠可為輔輻,甚堅韌;赤鱗質堅,大者取為車心,小者用為籬柱;麻竹不堅厚,止可製車籠、糖籠、倉笨、篾簟等物。 鳳山地區牛車軌選用堅木為之,中駕一牛引重致遠,旁用一牛佐之,用赤鱗為車心,用土楠為輔輻,用麻竹製車籠。 板輪牛車生產技術相對簡單,且在臺灣可以找到適合的材料,17世紀就在臺灣生產的可能性很大。
板輪牛車在臺灣使用約三百年,到了日本時代還在用。來自溫帶的日本人看到這種牛車,感受到它的原始而獨特的風格,輪子的軋軋聲也敲出南國情緒。當時板輪牛車的地理分布仍然以中南部地方為主,幾乎每家農戶都有一輛車,用來搬運農產品及肥料,東臺灣也有,中北部很少。整部車都是用木材打造的,樟是最受歡迎的材料,雖然看起來粗笨,卻很實用,即使是雨後滿地泥濘也暢行無阻,只要調整牛隻數量,最多可以載5,000斤的貨物。但因板輪是一個大圓盤,會嚴重損傷街道,日本領臺後為了保護道路,乃限制使用場域,只能在私人的田間小路、山腳、溪川的砂礫地及道路不發達的海岸地方使用。禁令發布後,新製板輪牛車的數量就減少了。 政府選擇保護街道,板輪牛車使用空間受到限制,臺灣各地從17世紀一直活躍到20世紀初期,具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因政治因素不再受青睞,也就很少生產,接著火車、腳踏車、機車、汽車等近代運輸工具又取而代之,牛隻也慢慢卸下了運輸的重荷,只殘存在少數地方,引發一絲思古悠情。(二)民用河船、海船的生產
荷蘭時代出現河流用的舢舨,也可能是在地生產的。木材在傳統社會裡是造船的主要材料,船是清代臺灣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這種交通工具的生產型式的主體是船匠。船依用途分為海船以及河船,海船體積大,且依船主身分又可分為官船與民船。官船即所謂軍工戰船,臺灣從康熙年間已經具有造船技術,直到道光年間一直在臺灣打造軍用海船。
臺南軍工廠外有民廠,又名廠仔,在硓古石地方;又有帆廠在其邊,造船亦木匠類也。 民廠較少被重視,並不代表沒有生產。就如蘭嶼人會在海邊自己打造自己的船一般,根據臺灣總督府之調查,擁有木造船技術的船匠並不需要特定的工作場所,在臺灣的大小港灣、漁業據點或河口停船處附近,都可以打造新船或修理舊船。臺灣使用的船,種類相當多,有在海上及河川下游、上游使用的貨船、漁船還有運大肥的特殊用船,如下〈表1-2〉。造船時使用的木材種類很多,船匠選用硬度、靭度適合的材料製造修理,大多數是用臺灣本地所產木材。選材時會考量是在哪裡使用以及用途,如河川上、中、下游各有不同的船,材料條件也會調整,也會依捕魚、載貨或運送大肥等不同用途,使用不同的船,讓人印象深刻。在河川使用的船製造原理與海船相似,不同點是傾向瘦長,而且對於堅牢程度的要求更高。口述調查資料也證實了民廠造船時的機動性,如造船時先在近水的地方搭寮做為臨時工廠,船造好下水後寮就拆掉。造船的木匠需要三年四個月的學徒養成期,技術學成後可得到一本記載船的大小和尺寸的簿子。臺南陳家船廠平時只雇用十餘人,工作繁忙時再加雇熟練工人。 木造船在中國使用很久,臺灣漢人移民的原鄉靠海、擅長造船,擁有木造船的修理及製造技術之可能性很高,渡海來臺之後仍然延續傳統學徒制,代代傳承技術。
木造船之外還有竹筏,主要材料是麻竹與藤。竹筏種類也很多,有沿海漁業專用的漁筏,還有用來搬運貨物的溪筏,兩者型態大同小異。大部分的竹筏是在溪、魚塭中使用的小型竹筏,分布相當普遍,因為臺灣的麻竹產地分布很廣,而且製造費用低廉、製法簡單,是可以自己打造來使用的。臺灣的港口因為有湧,大船很難靠岸,必須用竹筏將旅客與貨物接駁上岸,是清代兩岸行旅與商品往來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臺灣也打造過可以渡海的竹筏,從國際視野進行比較研究,確立其技術的先進, 也證明臺灣民間造船技術頗有水準。
總之,傳統木匠用臺灣的樹林、竹林所產原料,用雙手在海口、河口各地打造竹筏、海船、溪船,加上板輪牛車,這些運輸工具共同串連了海洋、河流與陸地,方便行旅來往各地,也負責將米及砂糖從農村各地集結到港口,然後外銷,形塑了臺灣島內外的物流與人流,是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交通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