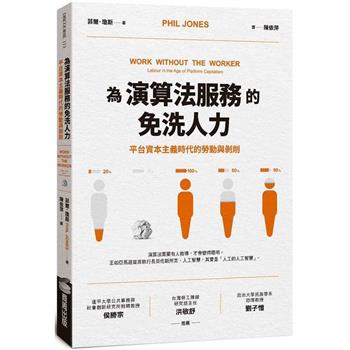導言 土耳其機械人
我們活在科技奇蹟的時代。現今,機器不僅能下圍棋打敗人類,還能寫出流行歌曲、憑自身意志駕駛車子。無人商店讓顧客能在選購產品後,不須經過結帳櫃台即可離開。顯然,若把小型晶片植入人腦中,機械便能開始學習如何讀懂人的心思了。這麼一個矽谷理想國信誓旦旦表示要淨化受毒害的地球,把大家送上火星,實現永生,並使人類脫離庸碌生活抵達超凡境界。這個世界物資豐厚且充滿智慧解決方案,便利程度可謂與奢華程度彼此相襯。
然而,這世界的根基卻疑點重重,看似有著突飛猛進而銳不可擋的科學進展,但其實只不過是某些科技大亨的夢想罷了。反烏托邦的醜惡戳破了模控(cybernetics) 的和諧假象;光鮮亮麗的表層底下是壓迫、監控和原子化(細部分工)的現實。每個影響全球的事件,諸如金融危機或傳染病疫情,都讓我們更快速步入這個世界所擁戴的「零接觸未來」—鼓勵大家多待在家裡避免與他人往來,而住家不再只是個人的居處,同時也兼作辦公室、購物中心、健身房、醫療診斷室以及娛樂場所。 物聯網(IoT)滲入我們的睡眠、會議和心律,並將這些現象的數據回報,其後再以優化的服務回饋到我們的生活,且這一切都是由某個平台來提供。出了家門後,「智慧城市」的監控又高了一層。街上的一無所有者在討生活時,生物識別及臉部辨識技術會監管他們的風險評估檔案。一連串的演算法圍繞著所有團體、空間和機構,形成一張張的機械感知網,密布到各種形態的運算智能宛如隱形一般。透過這種不易察覺的感應器、追蹤器和攝像鏡頭共同組成的多重設置,資本能夠取得新的編碼及認知用性質資訊。從測量學到生物識別技術,從顯微科學到宇宙學,生活受資訊交換的控制程度更甚以往。數據經轉換後輸入各種奇異的機器裝置:自駕車取代計程車和貨車司機,演算法替代主管職權,還能以勝過任何醫師的高精確度診斷癌症。
不過,這個自動化夢想世界的幻想程度居多,而非現實。搜尋引擎、應用程式及智慧裝置背後都有著工作者,這些人通常是在全球體系中被排擠到邊緣的族群,因為別無選擇而被迫要清理資料及管控演算法,領到的錢卻寥寥無幾。臉書和推特的動態貼文系統看似能精準地自動清除暴力內容,但哪些內容算是色情或仇恨言論,並非交由演算法判斷。臉部辨識鏡頭似乎能自動偵測到人群中的一張臉孔,而自駕車不需人為操控就能開動;但實際上,看似神奇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成果,所靠的是標注資料的苦差事。矽谷帶起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現象背後,是過濾仇恨言論、注釋影像以及教導演算法如何偵測出貓的艱辛勞力。
本書主張,這些低薪且損害心神的任務,是讓數位生活得以成形的主要因素,而非演算法。貝佐斯(Jeff Bezos)在亞馬遜的 MTurk 平台正式上線時告訴全世界:「大家可以把這想成是微工作(microwork)。以一美分的價碼,你可以請人告訴你一張照片裡面有沒有人。」在這種性質的網站中,MTurk不僅是首創,且知名度至今仍居第一。這些群包網站用標籤注記影像中出現的人物來訓練人工智慧,這類任務多半只花個一分鐘。就算作業時間拉得較長,通常頂多就一小時。微工作網站讓業主能把大型案件拆分成極短的工作。業主把這些人類智慧任務(Human Intelligence Task,HIT)發布到網站上,於是就會出現在數千名接案者(又稱「託客」﹝Turker﹞)的螢幕上。託客要迅速搶案,而且是論件計酬。每次成功發案後,平台會抽取百分之二十的費用。工作是在遠端完成,而且接案者只會在線上平台顯示虛擬頭像,並不會相互碰面。
MTurk 所開啟的二十一世紀新工作型態對資本很有利,卻讓勞工大受打擊。現在,其他競爭公司如 Appen、Scale 和Clickworker 也仿造同樣模式,提供方便好用的已清理資料和廉價勞力給業主,無論是學術機構,或是資本的現代大代理人,如臉書和 Google。這些網站扮演著以勞動套利的中盤商角色,鎖定戴維斯(Mike Davis)所稱的「過剩人力」(surplus humanity,全球人口中,被視為不在經濟體系主體之內的群體),以見縫插針滿足大科技公司的需求。接案者只在執行任務期間維持承攬關係,因此在就業和無業的狀態之間跳動,且可能在一日之內為不同公司工作。工作波動幅度大,而這些網站以彈性為由,擺出具備前瞻思想的善心守衛者姿態,推行專為新世代工作者設計的新型勞動契約,指稱他們渴望「獨立」更勝於安穩保障及合理報酬。不過這樣的安排之下,受惠方只有發包業主,像是推特、臉書和 Google 等大型科技公司,因為它們能夠規避較典型的聘僱所需負擔的責任。在這些網站工作的人,不再歸類為「勞工」,而是「自由工作者」、「獨立承攬人員」,甚至還有「玩家」(player)的離譜之稱。他們放棄了權益、法規保障以及最後一丁點議價的籌碼。
平台資本的殘酷性質,將本來就已經慘不忍睹的全球勞動景觀,改造為充斥著雜務與臨時工的就業荒土。不過,很多關於微工作的文獻都表示,這些資料處理工作是前所未見的新現象。自信滿滿的「人力雲」、「人即勞務」(Human-as-a-Service,以人作為一種勞務形式,簡稱 HaaS)和「即時人力」等講法,顯現出從過去沉悶的世界,縱身一躍進入了「人機混和式」的大好未來。貝佐斯所謂的「人工的人工智慧/工人智慧」(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表示人與演算法之間的高科技關係,將在「新經濟」中帶來爆炸性成長。9 因此,為了幫助南半球經濟體免於緩慢步入非正式工作、負債以及貧民窟擴大的末日浩劫,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在提出一長串措施時,便將微工作視為其中最新的救世辦法。本書要旨即在讓讀者知道,微工作非但不是南半球的浴火鳳凰,還是致使地球工作陷入進一步危機的推手。微工作由以下各個過程加總而來:成長遲滯、無產階級化,以及勞動力需求降低,這些全都使印度、委內瑞拉和肯亞等國的非正式部門大幅膨脹。如同我們將在第一章看到,這些網站的人數增加,並非資本主義成功的體現,而是反映出越來越多人在正式勞動市場找不到工作的悲慘紀實。其中許多人住在監獄、難民營和貧民窟中,他們完全無業或是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這就是過剩人力的悲歌。
這樣看來,從二○○八年至今這段漫長的經濟失序期間,使用群包網站的人數激增並不奇怪。雖然全球從事微工作的人數沒有精確的統計數據,但目前推估約落在兩千萬左右,其中大半部分的人位在南半球,包括南美洲、東亞以及印
度次大陸。這些人當中不乏受教育人士,但因故脫離了正式勞動市場。北半球的高學歷低就者,數量也正在增加。調查顯示,英國的工作年齡層人口中,高達百分之五每週至少使用一次群包網站。對他們而言,微工作主要是用來拉高工時並在薪資凍漲下增加收入的方法。然而,對其他世界各地眾多的人而言,微工作就是他們的全職工作。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一份調查報告,百分之三十六的接案者每週固定工作七日。
依照個別平台自稱的服務對象數量看來,利用這些網站工作的人數可能遠高於目前的統計數字。過去十年來,光是Clickworker 的使用者人數就增至超過兩百萬人,就連較小型的Appen 等網站現在的使用人數也破一百萬。如果把這些平台的接案者歸類為受聘員工,發包公司就會在現今的僱主名單中名列前茅,僅次於幾個政府和沃爾瑪大賣場(Walmart)。其中很驚人的是,中國群包平台「豬八戒」擁有一千兩百萬名使用者,使得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力承包商。
提倡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18 的機構明顯因AI 科技得益。它們順勢利用仰賴處理零碎資料維生者人數的增加這一點,反駁主流媒體長期對自動化會傷害就業市場的預測。然而,得利與受害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客服中心接電人員受到聊天機器人的威脅,櫃台結帳人員受到無人商店衝擊,他們最容易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風暴中載沉載浮,因此不得不躲進線上接案的收容地。
微工作的擁戴者會堅決表示還是有工作可做。但從「託客」平均時薪不到兩美元這點來看,就算自動化沒有消滅所有勞工,卻也把他們推到快無法生存的邊緣地帶。
這就是本書第二主題。過剩人力不被計入一般人力,長期以來都受到殘酷的國家政策擺布。而現在,他們更是在矽谷菁英進行的實驗中受到非人對待。貝佐斯把 MTurk 描述為「工人智慧」,可見接案者不被當作是人,而是運算設備。用來接洽業主和接案者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原本是工程師用來與電腦互動的工具。而在微工作網站上,業主是與以電腦為形象的人類互動。接案者隱沒在機器底下的長長陰影之中,因此業主能無後顧之憂地盡情操用行銷策略,尤其是平台大客戶。臉書、Google、亞馬遜等尋求取得風險投資的無數新創公司,採用的手法就在於企業模式十分精實,甚少仰賴高風險的勞動力市場,而幾乎是透過複雜的演算法來經營。它們允諾要完結十九世紀馬克思(Karl Marx)預測的進程,即用科學和科技來取代處於資本生產力核心的勞動。雖然各平台正在加速這個進程,但只要看看富士康黑暗的血汗廠房,或是玻利維亞有「吃人山」惡名的塞雷里科錫礦場(Cerro Rico),就會知道這些期望都還沒實現。平台將勞動外包,所以沒有記在帳上,也不會讓使用者、投資人、顧客看見,從而營造出深具科技實力的假象,但實際上跟利用人力處理資料來支應 AI 沒什麼兩樣。
雖然資料是平台的命脈,我們平常卻不會去想到它的製程。我們看得見 iPhone 的硬體,因此能從它的物理性質推論出製造過程所需的勞動,但我們看不見也碰不著軟體內流通的資料。我們壓根不會想到資料也要經歷生產的過程—這麼難以捉摸的無形物質同樣出自人類之手,就跟硬體一樣。由於動手動腦的產物都只顯現為智慧機器的成果,讓人有了科技萬能的錯覺。這種資料拜物教(以為有自動操作的無人機而不用有人標注資料,以為媒體能自動刷新動態而不需要人管理版面)掩蓋了自動化真正的面貌:一群又一群被剝奪正常就業地位的工作者,用如同抽搐般的動作在訓練機器學習。
為了要像馬克思揭露十九世紀工廠那樣拆穿這一面,本書也必須探索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的陰暗處,即在二十一世紀快速竄升至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二○一九年時,亞馬遜、臉書、微軟、字母控股(Alphabet,為 Google 的母公司)及蘋果分別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而中國平台阿里巴巴、京東商城和百度緊跟其後。這些公司能興起,一大關鍵在於擁有巨大的運算能力。隨著數位基礎設施讓使用者有空間能相聚、交際、貿易和消費,各平台獲得了大量個人資訊的特殊存取權限;這些個資取自線上瀏覽、GPS 定位、在社交軟體上與人對話,或是對著語音助理 Siri 說話。這些平台累積越多資料,便能把越多數據輸入 AI,並越能夠提升自動化程度。
但是,就算自動化真的只剩下「最後一里路」,想必也不好走完。縱使矽谷有了奇蹟似的進展而實現夢想,成功讓剛果礦坑自動挖採銅礦、富士康零件都用電腦自動組裝,且Uber 的車輛都學會自動駕駛,這些技術也幾乎都還是要仰賴
人工的資料處理,亦即標注、分級、歸類,科技解決方案尚且應付不來。除了最開始要先清理好資料才能輸入演算法,在開始執行後也要持續監督和修正。如伊拉尼(Lilly Irani)所說:「為了要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必須用人力來配置、校正和調整自動技術;變化包含產品形狀不一,或是有鳥飛入工廠
裡。」
想達成全自動奢華資本主義(fully automated luxury capitalism)的矽谷夢,終究只是個夢,但這樣的宏願卻在二十一世紀遲遲不散;此世紀一開場就是金融危機,其後經濟長期不景氣,民主體制搖搖欲墜,時不時又遇上氣候災害,以及好幾波的緊縮期。現在,想像中的烏托邦與現實中的反烏托邦,一來一往踏著怪誕的舞步赴往劫難。聊天機器人進步時,加州燃起大火;電腦下圍棋勝過人類時,數百萬人染上人畜共通的怪病。人類若無法在歷史的此刻主動出擊改善世界,就只能面臨一輛輛智慧計程車在永恆暴風夜中默默漂來的未來。怪異天氣和流行傳染病使得眾人成為難民、階下囚或是經濟邊緣人,這種在經濟體系主體中找不到安身處的人生重擔,到了矽谷人士的眼中卻變成一串軟體程式碼,任憑他們決定要拿來使用與否。
但在多處的前線,被視為過剩的人口正在起身抵抗,且有機會促使世界變得更好。微工作者光憑一己之力不易組織動員,並實際動搖資本,但在越來越多事件中,可看到平台工作者聯合其他無依無靠的族群付諸行動。本書便是抱持如此期望,謹慎寫下結語。
我們活在科技奇蹟的時代。現今,機器不僅能下圍棋打敗人類,還能寫出流行歌曲、憑自身意志駕駛車子。無人商店讓顧客能在選購產品後,不須經過結帳櫃台即可離開。顯然,若把小型晶片植入人腦中,機械便能開始學習如何讀懂人的心思了。這麼一個矽谷理想國信誓旦旦表示要淨化受毒害的地球,把大家送上火星,實現永生,並使人類脫離庸碌生活抵達超凡境界。這個世界物資豐厚且充滿智慧解決方案,便利程度可謂與奢華程度彼此相襯。
然而,這世界的根基卻疑點重重,看似有著突飛猛進而銳不可擋的科學進展,但其實只不過是某些科技大亨的夢想罷了。反烏托邦的醜惡戳破了模控(cybernetics) 的和諧假象;光鮮亮麗的表層底下是壓迫、監控和原子化(細部分工)的現實。每個影響全球的事件,諸如金融危機或傳染病疫情,都讓我們更快速步入這個世界所擁戴的「零接觸未來」—鼓勵大家多待在家裡避免與他人往來,而住家不再只是個人的居處,同時也兼作辦公室、購物中心、健身房、醫療診斷室以及娛樂場所。 物聯網(IoT)滲入我們的睡眠、會議和心律,並將這些現象的數據回報,其後再以優化的服務回饋到我們的生活,且這一切都是由某個平台來提供。出了家門後,「智慧城市」的監控又高了一層。街上的一無所有者在討生活時,生物識別及臉部辨識技術會監管他們的風險評估檔案。一連串的演算法圍繞著所有團體、空間和機構,形成一張張的機械感知網,密布到各種形態的運算智能宛如隱形一般。透過這種不易察覺的感應器、追蹤器和攝像鏡頭共同組成的多重設置,資本能夠取得新的編碼及認知用性質資訊。從測量學到生物識別技術,從顯微科學到宇宙學,生活受資訊交換的控制程度更甚以往。數據經轉換後輸入各種奇異的機器裝置:自駕車取代計程車和貨車司機,演算法替代主管職權,還能以勝過任何醫師的高精確度診斷癌症。
不過,這個自動化夢想世界的幻想程度居多,而非現實。搜尋引擎、應用程式及智慧裝置背後都有著工作者,這些人通常是在全球體系中被排擠到邊緣的族群,因為別無選擇而被迫要清理資料及管控演算法,領到的錢卻寥寥無幾。臉書和推特的動態貼文系統看似能精準地自動清除暴力內容,但哪些內容算是色情或仇恨言論,並非交由演算法判斷。臉部辨識鏡頭似乎能自動偵測到人群中的一張臉孔,而自駕車不需人為操控就能開動;但實際上,看似神奇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成果,所靠的是標注資料的苦差事。矽谷帶起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現象背後,是過濾仇恨言論、注釋影像以及教導演算法如何偵測出貓的艱辛勞力。
本書主張,這些低薪且損害心神的任務,是讓數位生活得以成形的主要因素,而非演算法。貝佐斯(Jeff Bezos)在亞馬遜的 MTurk 平台正式上線時告訴全世界:「大家可以把這想成是微工作(microwork)。以一美分的價碼,你可以請人告訴你一張照片裡面有沒有人。」在這種性質的網站中,MTurk不僅是首創,且知名度至今仍居第一。這些群包網站用標籤注記影像中出現的人物來訓練人工智慧,這類任務多半只花個一分鐘。就算作業時間拉得較長,通常頂多就一小時。微工作網站讓業主能把大型案件拆分成極短的工作。業主把這些人類智慧任務(Human Intelligence Task,HIT)發布到網站上,於是就會出現在數千名接案者(又稱「託客」﹝Turker﹞)的螢幕上。託客要迅速搶案,而且是論件計酬。每次成功發案後,平台會抽取百分之二十的費用。工作是在遠端完成,而且接案者只會在線上平台顯示虛擬頭像,並不會相互碰面。
MTurk 所開啟的二十一世紀新工作型態對資本很有利,卻讓勞工大受打擊。現在,其他競爭公司如 Appen、Scale 和Clickworker 也仿造同樣模式,提供方便好用的已清理資料和廉價勞力給業主,無論是學術機構,或是資本的現代大代理人,如臉書和 Google。這些網站扮演著以勞動套利的中盤商角色,鎖定戴維斯(Mike Davis)所稱的「過剩人力」(surplus humanity,全球人口中,被視為不在經濟體系主體之內的群體),以見縫插針滿足大科技公司的需求。接案者只在執行任務期間維持承攬關係,因此在就業和無業的狀態之間跳動,且可能在一日之內為不同公司工作。工作波動幅度大,而這些網站以彈性為由,擺出具備前瞻思想的善心守衛者姿態,推行專為新世代工作者設計的新型勞動契約,指稱他們渴望「獨立」更勝於安穩保障及合理報酬。不過這樣的安排之下,受惠方只有發包業主,像是推特、臉書和 Google 等大型科技公司,因為它們能夠規避較典型的聘僱所需負擔的責任。在這些網站工作的人,不再歸類為「勞工」,而是「自由工作者」、「獨立承攬人員」,甚至還有「玩家」(player)的離譜之稱。他們放棄了權益、法規保障以及最後一丁點議價的籌碼。
平台資本的殘酷性質,將本來就已經慘不忍睹的全球勞動景觀,改造為充斥著雜務與臨時工的就業荒土。不過,很多關於微工作的文獻都表示,這些資料處理工作是前所未見的新現象。自信滿滿的「人力雲」、「人即勞務」(Human-as-a-Service,以人作為一種勞務形式,簡稱 HaaS)和「即時人力」等講法,顯現出從過去沉悶的世界,縱身一躍進入了「人機混和式」的大好未來。貝佐斯所謂的「人工的人工智慧/工人智慧」(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表示人與演算法之間的高科技關係,將在「新經濟」中帶來爆炸性成長。9 因此,為了幫助南半球經濟體免於緩慢步入非正式工作、負債以及貧民窟擴大的末日浩劫,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在提出一長串措施時,便將微工作視為其中最新的救世辦法。本書要旨即在讓讀者知道,微工作非但不是南半球的浴火鳳凰,還是致使地球工作陷入進一步危機的推手。微工作由以下各個過程加總而來:成長遲滯、無產階級化,以及勞動力需求降低,這些全都使印度、委內瑞拉和肯亞等國的非正式部門大幅膨脹。如同我們將在第一章看到,這些網站的人數增加,並非資本主義成功的體現,而是反映出越來越多人在正式勞動市場找不到工作的悲慘紀實。其中許多人住在監獄、難民營和貧民窟中,他們完全無業或是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這就是過剩人力的悲歌。
這樣看來,從二○○八年至今這段漫長的經濟失序期間,使用群包網站的人數激增並不奇怪。雖然全球從事微工作的人數沒有精確的統計數據,但目前推估約落在兩千萬左右,其中大半部分的人位在南半球,包括南美洲、東亞以及印
度次大陸。這些人當中不乏受教育人士,但因故脫離了正式勞動市場。北半球的高學歷低就者,數量也正在增加。調查顯示,英國的工作年齡層人口中,高達百分之五每週至少使用一次群包網站。對他們而言,微工作主要是用來拉高工時並在薪資凍漲下增加收入的方法。然而,對其他世界各地眾多的人而言,微工作就是他們的全職工作。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一份調查報告,百分之三十六的接案者每週固定工作七日。
依照個別平台自稱的服務對象數量看來,利用這些網站工作的人數可能遠高於目前的統計數字。過去十年來,光是Clickworker 的使用者人數就增至超過兩百萬人,就連較小型的Appen 等網站現在的使用人數也破一百萬。如果把這些平台的接案者歸類為受聘員工,發包公司就會在現今的僱主名單中名列前茅,僅次於幾個政府和沃爾瑪大賣場(Walmart)。其中很驚人的是,中國群包平台「豬八戒」擁有一千兩百萬名使用者,使得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力承包商。
提倡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18 的機構明顯因AI 科技得益。它們順勢利用仰賴處理零碎資料維生者人數的增加這一點,反駁主流媒體長期對自動化會傷害就業市場的預測。然而,得利與受害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客服中心接電人員受到聊天機器人的威脅,櫃台結帳人員受到無人商店衝擊,他們最容易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風暴中載沉載浮,因此不得不躲進線上接案的收容地。
微工作的擁戴者會堅決表示還是有工作可做。但從「託客」平均時薪不到兩美元這點來看,就算自動化沒有消滅所有勞工,卻也把他們推到快無法生存的邊緣地帶。
這就是本書第二主題。過剩人力不被計入一般人力,長期以來都受到殘酷的國家政策擺布。而現在,他們更是在矽谷菁英進行的實驗中受到非人對待。貝佐斯把 MTurk 描述為「工人智慧」,可見接案者不被當作是人,而是運算設備。用來接洽業主和接案者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原本是工程師用來與電腦互動的工具。而在微工作網站上,業主是與以電腦為形象的人類互動。接案者隱沒在機器底下的長長陰影之中,因此業主能無後顧之憂地盡情操用行銷策略,尤其是平台大客戶。臉書、Google、亞馬遜等尋求取得風險投資的無數新創公司,採用的手法就在於企業模式十分精實,甚少仰賴高風險的勞動力市場,而幾乎是透過複雜的演算法來經營。它們允諾要完結十九世紀馬克思(Karl Marx)預測的進程,即用科學和科技來取代處於資本生產力核心的勞動。雖然各平台正在加速這個進程,但只要看看富士康黑暗的血汗廠房,或是玻利維亞有「吃人山」惡名的塞雷里科錫礦場(Cerro Rico),就會知道這些期望都還沒實現。平台將勞動外包,所以沒有記在帳上,也不會讓使用者、投資人、顧客看見,從而營造出深具科技實力的假象,但實際上跟利用人力處理資料來支應 AI 沒什麼兩樣。
雖然資料是平台的命脈,我們平常卻不會去想到它的製程。我們看得見 iPhone 的硬體,因此能從它的物理性質推論出製造過程所需的勞動,但我們看不見也碰不著軟體內流通的資料。我們壓根不會想到資料也要經歷生產的過程—這麼難以捉摸的無形物質同樣出自人類之手,就跟硬體一樣。由於動手動腦的產物都只顯現為智慧機器的成果,讓人有了科技萬能的錯覺。這種資料拜物教(以為有自動操作的無人機而不用有人標注資料,以為媒體能自動刷新動態而不需要人管理版面)掩蓋了自動化真正的面貌:一群又一群被剝奪正常就業地位的工作者,用如同抽搐般的動作在訓練機器學習。
為了要像馬克思揭露十九世紀工廠那樣拆穿這一面,本書也必須探索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的陰暗處,即在二十一世紀快速竄升至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二○一九年時,亞馬遜、臉書、微軟、字母控股(Alphabet,為 Google 的母公司)及蘋果分別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而中國平台阿里巴巴、京東商城和百度緊跟其後。這些公司能興起,一大關鍵在於擁有巨大的運算能力。隨著數位基礎設施讓使用者有空間能相聚、交際、貿易和消費,各平台獲得了大量個人資訊的特殊存取權限;這些個資取自線上瀏覽、GPS 定位、在社交軟體上與人對話,或是對著語音助理 Siri 說話。這些平台累積越多資料,便能把越多數據輸入 AI,並越能夠提升自動化程度。
但是,就算自動化真的只剩下「最後一里路」,想必也不好走完。縱使矽谷有了奇蹟似的進展而實現夢想,成功讓剛果礦坑自動挖採銅礦、富士康零件都用電腦自動組裝,且Uber 的車輛都學會自動駕駛,這些技術也幾乎都還是要仰賴
人工的資料處理,亦即標注、分級、歸類,科技解決方案尚且應付不來。除了最開始要先清理好資料才能輸入演算法,在開始執行後也要持續監督和修正。如伊拉尼(Lilly Irani)所說:「為了要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必須用人力來配置、校正和調整自動技術;變化包含產品形狀不一,或是有鳥飛入工廠
裡。」
想達成全自動奢華資本主義(fully automated luxury capitalism)的矽谷夢,終究只是個夢,但這樣的宏願卻在二十一世紀遲遲不散;此世紀一開場就是金融危機,其後經濟長期不景氣,民主體制搖搖欲墜,時不時又遇上氣候災害,以及好幾波的緊縮期。現在,想像中的烏托邦與現實中的反烏托邦,一來一往踏著怪誕的舞步赴往劫難。聊天機器人進步時,加州燃起大火;電腦下圍棋勝過人類時,數百萬人染上人畜共通的怪病。人類若無法在歷史的此刻主動出擊改善世界,就只能面臨一輛輛智慧計程車在永恆暴風夜中默默漂來的未來。怪異天氣和流行傳染病使得眾人成為難民、階下囚或是經濟邊緣人,這種在經濟體系主體中找不到安身處的人生重擔,到了矽谷人士的眼中卻變成一串軟體程式碼,任憑他們決定要拿來使用與否。
但在多處的前線,被視為過剩的人口正在起身抵抗,且有機會促使世界變得更好。微工作者光憑一己之力不易組織動員,並實際動搖資本,但在越來越多事件中,可看到平台工作者聯合其他無依無靠的族群付諸行動。本書便是抱持如此期望,謹慎寫下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