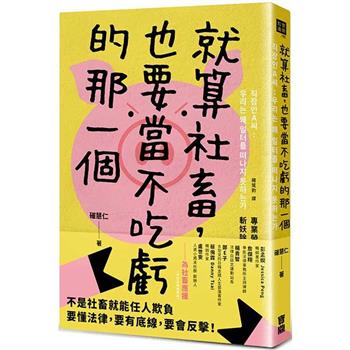第一章 今天的心情
從委屈變成執著
偶爾進行諮詢時,會聽到「為什麼要留在這樣的公司」的話,尤其是在諮詢職場上司的語言暴力太嚴重或行為野蠻到已經非常識所能理解的職場霸凌事例時,更是如此。熙延每天都會遭到上司的辱罵,雖然他們說的都是難以啓齒的下流話語,但長時間待在以男性為主的現場工作,領悟到這是為了生存而使用的溝通方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惡言惡語不僅無法讓人理解,反而壓力愈來愈大,上司的辱罵也愈來愈粗暴。凡是經歷過的人都知道,充滿憤怒的辱罵本身就是一種威脅。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碰到一名男子,他朝我說了一句髒話,這就已經讓我雙腿發顫,想到要被每天都會見面的上司罵髒話,熙延無異於身處在一個不知何時會響起槍聲的戰場。
秀英和上司共用一間公司宿舍,連下班後也要和上司共享生活,這是非常疲憊的事,但是秀英卻經歷超乎了想像的麻煩。上司在下班後要求秀英做晚飯,週末還要她洗衣服,不僅打掃,連採購生活必需品和食材也變成秀英的工作,甚至這些花費都得由秀英負擔。雖然壓力很大,但秀英如果要想繼續上班,就只能繼續共用宿舍,她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忍耐。上司和她共用房子的期間,對小菜的抱怨不知不覺變成了辱罵,就這樣過了三年。熙延和秀英以「法律上不能追究職場上司的責任嗎?」為由要求進行諮詢,但我認為現在已經不是他們接受諮詢的時候了,他們該做的是逃離公司。然而,離開公司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對熙延和秀英來說也是如此。
「公司」並沒有欺負他們,相反地,公司反而是對個人生活有多方助益的地方。基本上,公司會發薪資,而靠著這份薪資,我們可以享受不僅僅只是溫飽的生活,可以購買漂亮的衣服、鞋子和化妝品,也可以看想看的書或演出,還可以和喜歡的人一起旅行,或和家人到不錯的地方吃飯。並且,薪資不只具有單純的物質意義,雖然也有人認為要存錢才能感覺到幸福,但大多數人都會為了度過愉快的時光而欣然支付金錢,而且,只有上班才能拿到這樣的薪資。此外,隸屬於某個地方所帶來的安全感和做著有用的事,也對個人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是一種成長為「有用的大人」的安全感。因此,嚴格來說,讓熙延和秀英備感痛苦的並不是公司,而是「職場上司」,所以他們相信,只要上司消失,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他們認為,如果想要享受公司帶來的好處,就必須承受某種程度的壓力,靠著這樣的信念堅持了很久。
但他們兩人的判斷是正確的嗎?這真的只是職場上司的問題嗎?那麼,長期放任嚴重的辱罵和非正常關係的公司,是否也該負起部分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幸運地,惡劣的上司先離職了,那也只是運氣好而已,類似的事情很可能會反復發生,而且即便如此,當時公司有很高的機率已經目睹了非正常現象,但他們只會裝作不知道。認為承受被霸凌的痛苦,是被霸凌者的責任,因此推卸責任,袖手旁觀。然而,熙延和秀英並非不知道這個事實,只是他們認為,應該離開公司的人不是自己,而是上司。要想這樣做的話,就必須將折磨自己的上司假設為唯一的罪魁禍首,將組織和自己以相同立場來看待,他們的心態,也許只是想藉此在分幫結派中占據優勢,因為愈是陷入困境的人,就愈難面對並接受現實。
明明受到了嚴重的職場霸凌,卻無法辭職的理由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因為經歷過不正當情況的無力感會帶來更強烈的無力感,導致一個人無法做出任何應對的惡性循環,或是即使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被欺負了,因此應該消除委屈的心情才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受害者先離職了,那麼可能會在受害者的身上,形成無法對抗不正當情況而逃跑的雙重傷害,因此就算是為了阻止其他受害者,也必須在這裡切斷霸凌循環的紐帶,但無論如何,我們無法統一規定人心應該要怎麼想,所以在這裡只是回顧一下,如果是我面對這件事的話會怎麼做。
在充滿許多疑惑和欲望的學生時期,當時韓國正在進行反對進口狂牛症牛肉的燭光集會。當時的我什麼都不懂,只是跟著學長姐們在示威廣場上感受到了解放感,並且想要瞭解社會上的各種不合理性。在學校聽課或找書來學習時覺得很平淡,而且侷限性也很明顯,因此我決定暑假兩個月在一個市民團體裡實習,雖然是不支薪的,但還是要提交履歷和自我介紹,面試通過之後才能進到裡面實習。我想學的和想體驗的東西很多,因為充滿了期待,因此也下定決心要好好努力,但是沒過多久,我就完全失去了熱情和欲望,儘管就像普通職場內的霸凌受害者一樣,我幾乎沒有做錯過什麼。
剛開始實習沒多久,老闆的熟人某天來公司,並請大家吃午餐。我每天的工作內容其中一項就是把用公司信用卡結算的餐費收據複印一份,然後存檔,但那天老闆熟人請客,所以沒用公司信用卡。可能因為這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我誤以為是自己忘了拿收據,當時立刻對老闆說「我沒拿收據,所以要去一趟餐館重拿」,但老闆卻大聲地斥責我並說道:「客戶請我們吃飯,為什麼還要拿收據?況且拿收據也不是什麼難事,為什麼連這個都做不好?」我當下覺得太丟臉了,因為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而感到羞愧,而且這是我第一次這樣被人當眾大聲指責,所以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一瞬間只是感到很驚慌,什麼話都說不出口,身體也僵住了。在此之後,這種情況也反復出現了好幾次,即使只是小小的失誤,老闆也會大聲地指責我,而且不在意周圍有誰,只會提高嗓門,憤怒不已。每當這種時候,我覺得自己彷彿成了這個世界上最醜陋的人,自然而然地,想在公司裡好好學習工作的想法逐漸消失了,變得只是希望能夠安靜地打發時間,撐到實習期結束。
因為我是大學生,而且只是無薪實習生,就算辭職,也不會像上班族辭職時那樣受到打擊,當然,還有一點是因為實習合約已經簽了,所以只要稍微忍耐一下就可以了,我並沒有想過要在實習合約結束之前就先辭職。總之,最後我做到實習期滿,甚至還參加了公司為我舉辦的歡送會,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我們在國會議事堂站附近吃了最後的晚餐,我因為有事還先離開了。在二十歲出頭的某個秋天,少了上班族的國會議事堂站旁的小巷格外冷清,我感覺從束縛自己的某個東西中解脫了。我還記得隨著夏天過去,寒風開始吹起的季節到來,就像滾動的落葉般,以輕盈的步伐經過那裡,但是為了治癒這段短暫而粗暴的暴力時間,我需要比這更長的時間來面對我的傷口。我仔細思索,為什麼自己沒有先離開公司,我好像只是因為不想輸而已,我不想先從對我太過苛刻的老闆那裡逃走,帶著一種「因為你是加害者,我是受害者,所以我不會先躲著你」這樣的自尊心。
我想熙延和秀英的心情應該也和當時的我差不多吧。雖然在公司裡意外地遭受職場上的折磨,但是當我們把自己當成「受害者」的瞬間,似乎就會得到某人的支援,或成為需要擺脫這個狀況的一種被動存在。雖然沒有為了積極解決問題而挺身對抗的勇氣,至少不想要屈服,因此只能選擇盡可能長久地堅持下去。但事實上公司直到熙妍和秀英要求諮詢為止,都沒有主動出面提供幫助。雖然這樣的職場霸凌已經嚴重到可以直接舉報,但實際上,如果公司抱持不合作的態度,受害者很難單打獨鬥並獲得勝利。我到現在還會害怕見到曾經實習過的那間公司的老闆,雖然只是兩個月的實習,但我受到的損失卻非常大。之後我下定決心,再也不會忍受被虐待的情況,雖然這明明是理所當然的,但也許是因為不想忍受想要學習的心受到挫敗的失望,以及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卻先放棄的委屈,所以對這份工作產生了一種執著。
在進行職場霸凌的相關諮詢時,常會聽見這樣的話:「雖然我們可以充分瞭解這是不正當的情況,但若考慮自己的健康,直接離開這樣的公司,調整心態後到新的公司工作也是一種選擇。」擺脫職場霸凌的情況,絕不是「逃跑」,而且最好不要期待公司會給予任何幫助,因為大部分的人不太關心別人的事,雖然職場上司有問題是原因,但是對此置之不理的公司也無異於共犯,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沒有為個人發揮積極作用,反而成為以個人的犧牲作為食物,如寄生般的存在。當想法愈複雜時,只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才能夠做出最明智的選擇。
傾斜的運動場
想必大家並不是在第一次聽到「失敗為成功之母」時,就覺得這句話只是謊言而已。我原本也相信即使摔倒,只要堅強地站起來,總有一天就會克服失敗,順利取得成功。但是在放棄第一份工作後,在不安中掙扎時,我很確定失敗絕對不是成功之母。我想著「如果我做著不怎麼樣的工作,那我就不可能東山再起了,因此這次無論如何,我都要通過勞務士的考試。」這句話像咒語般被我每天默唸著,焦慮成為了鞭子,在我的心上留下深深的自我厭惡。與其說是心病,我所苦惱和期望的只是平凡年輕人面對的現實情況而已。
在韓國社會,一旦失敗了,通常就不會再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為了克服這個危機,解僱了工人,開始濫用非正式員工。他們說如果經濟恢復,勞動市場就會重新回到原位,即使暫時成為非正式員工,也只不過是當上正式員工的過程,就這樣以甜蜜的謊言大量「製造」了這些非正式員工。一旦成為非正式員工,就永遠無法擺脫那個位置。非正式員工沒有機會,且他們的經歷對以後想獲得更好的工作也沒有幫助。看著這樣的現實長大的年輕人已經知道,一次的失敗可能會影響自己的整個人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讓我們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默默地接受像命運般無止境的競爭。
但是,尋找好工作的競爭其實並不平等,畢業於好大學,能夠找到好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擁有穩定的環境,並且來自能夠享受各種機會的富足家庭。電視劇《天空之城》(Sky Castle)即講述為了成為上流階級而執著於子女教育和入學考試的家庭面貌。但即使知道入學考試的重要性,卻不是所有人都執著於此,不,應該說「無法執著」。劇中的主要人物藝瑞在「天空之城」這個富裕的環境中,以家中父母出色的情報力和財力為基礎,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但像藝瑞的父母一樣,擁有良好職業和人脈,能夠接觸到有利於大學入學考試資訊的人很少。因此,像醫生世家通常會不斷讓後代也成為醫生,來強化他們的機會和特權。
《20 vs. 80的社會》(Dream Hoarders:How the American Upper Middle Class Is Leaving Everyone Else in the Dust, Why That Is a Problem, and What to Do About It)這本書的作者理查・里夫斯(Richard Reeves)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機會囤積」(opportunity hoarding),也就是說,發展在勞動市場成功所需的能力,實際上依照不同的成長環境,獲取這些能力的機會並不平等。衡量一個人的社會經濟階級受父母所屬階級影響的概念,在經濟學上被稱為「代際所得彈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IGE),愈難以擺脫父母所屬的階級,彈性就愈高。根據代際所得彈性的概念,父母的社經階級會成為子女的絆腳石,假如階級由高到低劃分為一到十,父母的階級是第九級,那麼即使子女有到第一級的成功能力,由於被父母絆住,只能停留在第四級。相反地,如果父母的階級是第一級,那麼即使子女只有第五級左右的能力,也可以因為父母的幫助爬升到第三級。
依靠父母而改變的能力發展機會是「排除」的另一種說法。從一開始就根本無法接觸到機會的人其實更多,社會階級不能說是單靠個人努力所獲得之能力的結果,依照能力獲得公平機會的錯覺,只是把特權正當化而已。實際上要在這個不公正也不平等的社會裡,想靠自己培養能力並取得成功是很難實現的夢想,而夢想著這種事的我們也健康不起來。
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過於龐大,想要在這樣的結構中成為例外的人展開了激烈的生存鬥爭。若想要在傾斜的運動場上進行勝算極低的戰鬥,就必須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更加狠毒,為了不失去屬於自己的那一份,不斷地與他人比較和競爭。愈是不安,就愈不會對他人有利他之心,只會想著自己要如何生存下去,此時所謂的共同體便不復存在,因為我們將會變得無法體諒隊友的失誤,也不能等待他們適應。在不平等的社會中受到的痛苦會成為傷害彼此的刀刃,而我們也將成為互相折磨的加害者和被害者。
在某個媒體的訪談中,曾經被問到職場霸凌的原因,雖然我沒能夠用整理好的句子流暢地回答,但腦中浮現了平常對不平等社會的苦惱。當然,造成職場霸凌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拚命守護的東西愈來愈多。要竭盡全力守住自己的位置,如果失去這個位置就再也沒有機會的迫切感,藉由對同事的尖銳態度和扭曲的補償心理表現出來,造成彼此的痛苦。大多數出生在普通家庭平凡的我們,為了不失去任何一次機會而一直處於不安之中。
雖然透過懲戒加害者可以讓大家對職場霸凌提高警惕,但在沒有職場霸凌的世界裡,從個人身上尋找職場霸凌的原因是不夠的。若是即使沒遇見富裕的父母,不是畢業於名門大學,不在大企業工作,也能過上不錯的生活,那麼競爭和不安才有可能大幅減少。真正放鬆的態度,只有在所有人都能過上好日子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踏實工作最後卻死了
我負責的第一個職業災害案件,是一位水族館的工作人員因為意外而在水中死亡。
從一開始負責這個職業災害死亡案件後,我想起了實習期間記錄的自殺職業災害案件。在那些全都於紙張上方打洞後用繩子綁起來的紀錄之中,有部分用夾子夾住紙張右側而無法翻頁,因為翻閱紙張的習慣,我不自覺地伸手想拿掉夾子,在那瞬間,文件標題「現場調查報告」卻吸引住我,我的手停了下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不該看的文件,裡面的東西可能會在腦中留下長久都難以忘記的殘影。果然直覺是對的,這份報告書裡完完整整地記錄了死者最初被發現時的現場照片。就像每個人所處的情況都不一樣,死者一定也有不得不選擇死亡的處境。負責這種案件的勞務士,必須重新拼湊該勞工自殺前的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要觀察當事人的精神病歷、心理變化、誘發精神壓力的條件、加重壓力的因素以及其他特殊事項等。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被認定為職業災害也不容易,而近距離觀察某個人的死亡這種事,光是想像就已經讓人心情沉重。
健康又年輕的人在工作時間內發生的事故中喪生,雖然乍聽之下會認為是明確的職業災害案件,但仔細一看,也存在一些模糊的討論空間。
第一個討論焦點是該勞工的死亡時間是他可以自由放鬆的休息時間,還是雖然沒有實際工作,但已經開始準備要投入工作的等待時間。休息時間是勞工可以自由使用的時間,因此事故和業務的關聯性會降低,相反地,如果是待機時間,隨時都要開始工作,因此和業務的關聯性會提高。第二個討論焦點是造成事故原因的行為是私人行為還是和工作業務相關的行動。工作時去上洗手間或吃午餐本身雖然不屬於業務範疇,但因為是在工作時間中理所當然會發生的行為,所以去洗手間或吃午飯時摔倒也被認定為職業災害。此外,在休息時間做伸展運動時發生事故,如果可以被看作是準備工作的行動,那麼就能被認可與工作業務有關聯性。我負責的死亡事件同時具有這兩個爭論點,是休息時間進行私人行為而死亡,還是待機時間進行業務相關行為而死亡,還有待商榷。
一般在進行案件釐清時,如果想要拿到必要的資料或確認事實關係,最快也最準確的方法莫過於詢問當事人,但是職業災害死亡案件的當事人已經不在了,無奈之下,我只能詢問死者家屬。雖然我努力不要在工作上參雜個人情緒,但我實在很難做到親自打電話給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當事人父母,具體詢問事故發生原委。儘管我把這件事擺到待辦事項的最後,先處理其他事情,但也不能繼續猶豫下去,我只能打起精神,按下號碼打了電話。
之後連遺屬撫卹金的申請準備都完成了,只剩等待勞動部的判定出爐,但某天卻突然接到通報說要召開判定委員會。勞動法規規定,如果是在工作過程中發生事故而申請職業災害的話,勞動部會自行判定,相反地,如果在工作中患上疾病,則由業務上的疾病判定委員會審議後進行判定。該事件是因執行業務上的事故而死亡的案件,卻突然說要召開判定委員會。此時的我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太生氣了,因為突發事故而死亡的人連一次喊痛的機會都沒有,如果知道這件事,他該會覺得多委屈啊。
臺灣情況:臺灣對於職業災害的認定可以分為因工作中發生的事故而造成的「職業傷害」,以及長期執行職務所導致的「職業病」。無論是職業傷害或職業病,都需要勞工所進行的勞務活動和損害結果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尤其是職業病,需要請醫生開立職業疾病診斷書,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也制訂了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作為依據。若勞雇雙方對診斷內容有爭執,可先向各縣市政府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申請鑑定,若仍有爭議再向勞動部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申請鑑定。
根據勞動部的立場,認為這起事故是由於心臟麻痺之後因腦部損傷而死亡,因此將心臟麻痺視為業務上的疾病,而召開判定委員會。最後我還是參加了判定委員會,並在現場用激昂的聲音對他們說:「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時候抽筋,但卻不會因此而死。就像抽筋這種情況,身體出現了異常症狀,偏偏當事者是在水中工作的人,所以水中這個工作環境特性才是導致死亡的關鍵,因此該事件不屬於判定委員會的審議對象。」
他們接受了我的意見,隔天勞動部表示決定不在判定委員會進行審議,他們會於內部重新審議後再與我聯絡。一週之後勞動部來電,我看了一下手機上的區域號碼,知道是勞動部,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後接起電話,他們說這個案件被認定為職業災害。我當時覺得真是太好了,本來就應該這樣,只是因為存在爭議部分才不得不擔心。
但我並沒有因此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通常在職業災害案件中,我們稱呼勞工時會使用「死者」或「災害者」的表達方式,但這次我卻使用了「該案件的勞工」,因為我不想直接公然寫出已經受傷而生病的人或者因受傷而死去的人。遺屬們可能會看到我寫的書面資料,每當看到死者一詞時,該會有多傷心呢?父母從子女出生到成長的每個瞬間都曾經感到幸福和喜悅,他們現在應該也還記得那個瞬間吧,所以我不想要像其他資料,留下彷彿認證當事人比父母先成為死者那樣的話語。但是職業災害竟然順利被批准了,我在那個瞬間才真的感受到該送他離開的感覺,此時才是真正的離別。
雖然沒有不令人遺憾的死亡,但是接到被認定為職業災害的通知後,卻讓人感到更加悲傷了,當事人不是因為什麼,只是像平常一樣工作,但是卻死了。他不是為了享受什麼榮華富貴,也不是在悠閒玩樂,他只是認真工作而已。他工作到命都沒有了,卻沒有留下最後一句話,也沒能發出一聲疼痛的喊叫,沒有比瞬間到來的死亡還要更為殘酷的事了。負責勞工案件的時候,我總以為贏了就好,但這件事卻讓我的心情很複雜,當然以對在工作中受傷、生病或死亡的補償來看,職業災害能夠順利得到批准當然是好事,但一方面也讓人惋惜為什麼當事人會在工作中死亡。
我無法理解那種當親近的人死去,或者原本存在的人消失了的情況。雖然不知道死亡是什麼,但是我知道死亡會讓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離別是新的相遇」、「結束是新的開始」這種話在死亡面前行不通,死就是死了。因此我們要盡全力預防死亡,《重大災害企業處罰法》就是對沒有預防職業災害發生的企業追究責任的法律。讓未能預防死亡的罪、逃避死亡責任的罪都能得到嚴正地處理,我衷心希望不要有人在工作中死去。我們是為了吃好住好而工作,因此我希望大家認真工作後都能過上好日子。現在到了真的該送走這位當事人的時候了。
臺灣情況:臺灣與職業災害較相關的法律主要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並於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針對一定規模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節及重複違反情形等提高罰鍰額度,嚴懲未盡預防職災之責的企業。
從委屈變成執著
偶爾進行諮詢時,會聽到「為什麼要留在這樣的公司」的話,尤其是在諮詢職場上司的語言暴力太嚴重或行為野蠻到已經非常識所能理解的職場霸凌事例時,更是如此。熙延每天都會遭到上司的辱罵,雖然他們說的都是難以啓齒的下流話語,但長時間待在以男性為主的現場工作,領悟到這是為了生存而使用的溝通方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惡言惡語不僅無法讓人理解,反而壓力愈來愈大,上司的辱罵也愈來愈粗暴。凡是經歷過的人都知道,充滿憤怒的辱罵本身就是一種威脅。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碰到一名男子,他朝我說了一句髒話,這就已經讓我雙腿發顫,想到要被每天都會見面的上司罵髒話,熙延無異於身處在一個不知何時會響起槍聲的戰場。
秀英和上司共用一間公司宿舍,連下班後也要和上司共享生活,這是非常疲憊的事,但是秀英卻經歷超乎了想像的麻煩。上司在下班後要求秀英做晚飯,週末還要她洗衣服,不僅打掃,連採購生活必需品和食材也變成秀英的工作,甚至這些花費都得由秀英負擔。雖然壓力很大,但秀英如果要想繼續上班,就只能繼續共用宿舍,她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忍耐。上司和她共用房子的期間,對小菜的抱怨不知不覺變成了辱罵,就這樣過了三年。熙延和秀英以「法律上不能追究職場上司的責任嗎?」為由要求進行諮詢,但我認為現在已經不是他們接受諮詢的時候了,他們該做的是逃離公司。然而,離開公司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對熙延和秀英來說也是如此。
「公司」並沒有欺負他們,相反地,公司反而是對個人生活有多方助益的地方。基本上,公司會發薪資,而靠著這份薪資,我們可以享受不僅僅只是溫飽的生活,可以購買漂亮的衣服、鞋子和化妝品,也可以看想看的書或演出,還可以和喜歡的人一起旅行,或和家人到不錯的地方吃飯。並且,薪資不只具有單純的物質意義,雖然也有人認為要存錢才能感覺到幸福,但大多數人都會為了度過愉快的時光而欣然支付金錢,而且,只有上班才能拿到這樣的薪資。此外,隸屬於某個地方所帶來的安全感和做著有用的事,也對個人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是一種成長為「有用的大人」的安全感。因此,嚴格來說,讓熙延和秀英備感痛苦的並不是公司,而是「職場上司」,所以他們相信,只要上司消失,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他們認為,如果想要享受公司帶來的好處,就必須承受某種程度的壓力,靠著這樣的信念堅持了很久。
但他們兩人的判斷是正確的嗎?這真的只是職場上司的問題嗎?那麼,長期放任嚴重的辱罵和非正常關係的公司,是否也該負起部分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幸運地,惡劣的上司先離職了,那也只是運氣好而已,類似的事情很可能會反復發生,而且即便如此,當時公司有很高的機率已經目睹了非正常現象,但他們只會裝作不知道。認為承受被霸凌的痛苦,是被霸凌者的責任,因此推卸責任,袖手旁觀。然而,熙延和秀英並非不知道這個事實,只是他們認為,應該離開公司的人不是自己,而是上司。要想這樣做的話,就必須將折磨自己的上司假設為唯一的罪魁禍首,將組織和自己以相同立場來看待,他們的心態,也許只是想藉此在分幫結派中占據優勢,因為愈是陷入困境的人,就愈難面對並接受現實。
明明受到了嚴重的職場霸凌,卻無法辭職的理由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因為經歷過不正當情況的無力感會帶來更強烈的無力感,導致一個人無法做出任何應對的惡性循環,或是即使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被欺負了,因此應該消除委屈的心情才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受害者先離職了,那麼可能會在受害者的身上,形成無法對抗不正當情況而逃跑的雙重傷害,因此就算是為了阻止其他受害者,也必須在這裡切斷霸凌循環的紐帶,但無論如何,我們無法統一規定人心應該要怎麼想,所以在這裡只是回顧一下,如果是我面對這件事的話會怎麼做。
在充滿許多疑惑和欲望的學生時期,當時韓國正在進行反對進口狂牛症牛肉的燭光集會。當時的我什麼都不懂,只是跟著學長姐們在示威廣場上感受到了解放感,並且想要瞭解社會上的各種不合理性。在學校聽課或找書來學習時覺得很平淡,而且侷限性也很明顯,因此我決定暑假兩個月在一個市民團體裡實習,雖然是不支薪的,但還是要提交履歷和自我介紹,面試通過之後才能進到裡面實習。我想學的和想體驗的東西很多,因為充滿了期待,因此也下定決心要好好努力,但是沒過多久,我就完全失去了熱情和欲望,儘管就像普通職場內的霸凌受害者一樣,我幾乎沒有做錯過什麼。
剛開始實習沒多久,老闆的熟人某天來公司,並請大家吃午餐。我每天的工作內容其中一項就是把用公司信用卡結算的餐費收據複印一份,然後存檔,但那天老闆熟人請客,所以沒用公司信用卡。可能因為這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我誤以為是自己忘了拿收據,當時立刻對老闆說「我沒拿收據,所以要去一趟餐館重拿」,但老闆卻大聲地斥責我並說道:「客戶請我們吃飯,為什麼還要拿收據?況且拿收據也不是什麼難事,為什麼連這個都做不好?」我當下覺得太丟臉了,因為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而感到羞愧,而且這是我第一次這樣被人當眾大聲指責,所以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一瞬間只是感到很驚慌,什麼話都說不出口,身體也僵住了。在此之後,這種情況也反復出現了好幾次,即使只是小小的失誤,老闆也會大聲地指責我,而且不在意周圍有誰,只會提高嗓門,憤怒不已。每當這種時候,我覺得自己彷彿成了這個世界上最醜陋的人,自然而然地,想在公司裡好好學習工作的想法逐漸消失了,變得只是希望能夠安靜地打發時間,撐到實習期結束。
因為我是大學生,而且只是無薪實習生,就算辭職,也不會像上班族辭職時那樣受到打擊,當然,還有一點是因為實習合約已經簽了,所以只要稍微忍耐一下就可以了,我並沒有想過要在實習合約結束之前就先辭職。總之,最後我做到實習期滿,甚至還參加了公司為我舉辦的歡送會,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我們在國會議事堂站附近吃了最後的晚餐,我因為有事還先離開了。在二十歲出頭的某個秋天,少了上班族的國會議事堂站旁的小巷格外冷清,我感覺從束縛自己的某個東西中解脫了。我還記得隨著夏天過去,寒風開始吹起的季節到來,就像滾動的落葉般,以輕盈的步伐經過那裡,但是為了治癒這段短暫而粗暴的暴力時間,我需要比這更長的時間來面對我的傷口。我仔細思索,為什麼自己沒有先離開公司,我好像只是因為不想輸而已,我不想先從對我太過苛刻的老闆那裡逃走,帶著一種「因為你是加害者,我是受害者,所以我不會先躲著你」這樣的自尊心。
我想熙延和秀英的心情應該也和當時的我差不多吧。雖然在公司裡意外地遭受職場上的折磨,但是當我們把自己當成「受害者」的瞬間,似乎就會得到某人的支援,或成為需要擺脫這個狀況的一種被動存在。雖然沒有為了積極解決問題而挺身對抗的勇氣,至少不想要屈服,因此只能選擇盡可能長久地堅持下去。但事實上公司直到熙妍和秀英要求諮詢為止,都沒有主動出面提供幫助。雖然這樣的職場霸凌已經嚴重到可以直接舉報,但實際上,如果公司抱持不合作的態度,受害者很難單打獨鬥並獲得勝利。我到現在還會害怕見到曾經實習過的那間公司的老闆,雖然只是兩個月的實習,但我受到的損失卻非常大。之後我下定決心,再也不會忍受被虐待的情況,雖然這明明是理所當然的,但也許是因為不想忍受想要學習的心受到挫敗的失望,以及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卻先放棄的委屈,所以對這份工作產生了一種執著。
在進行職場霸凌的相關諮詢時,常會聽見這樣的話:「雖然我們可以充分瞭解這是不正當的情況,但若考慮自己的健康,直接離開這樣的公司,調整心態後到新的公司工作也是一種選擇。」擺脫職場霸凌的情況,絕不是「逃跑」,而且最好不要期待公司會給予任何幫助,因為大部分的人不太關心別人的事,雖然職場上司有問題是原因,但是對此置之不理的公司也無異於共犯,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沒有為個人發揮積極作用,反而成為以個人的犧牲作為食物,如寄生般的存在。當想法愈複雜時,只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才能夠做出最明智的選擇。
傾斜的運動場
想必大家並不是在第一次聽到「失敗為成功之母」時,就覺得這句話只是謊言而已。我原本也相信即使摔倒,只要堅強地站起來,總有一天就會克服失敗,順利取得成功。但是在放棄第一份工作後,在不安中掙扎時,我很確定失敗絕對不是成功之母。我想著「如果我做著不怎麼樣的工作,那我就不可能東山再起了,因此這次無論如何,我都要通過勞務士的考試。」這句話像咒語般被我每天默唸著,焦慮成為了鞭子,在我的心上留下深深的自我厭惡。與其說是心病,我所苦惱和期望的只是平凡年輕人面對的現實情況而已。
在韓國社會,一旦失敗了,通常就不會再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為了克服這個危機,解僱了工人,開始濫用非正式員工。他們說如果經濟恢復,勞動市場就會重新回到原位,即使暫時成為非正式員工,也只不過是當上正式員工的過程,就這樣以甜蜜的謊言大量「製造」了這些非正式員工。一旦成為非正式員工,就永遠無法擺脫那個位置。非正式員工沒有機會,且他們的經歷對以後想獲得更好的工作也沒有幫助。看著這樣的現實長大的年輕人已經知道,一次的失敗可能會影響自己的整個人生,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讓我們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就默默地接受像命運般無止境的競爭。
但是,尋找好工作的競爭其實並不平等,畢業於好大學,能夠找到好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擁有穩定的環境,並且來自能夠享受各種機會的富足家庭。電視劇《天空之城》(Sky Castle)即講述為了成為上流階級而執著於子女教育和入學考試的家庭面貌。但即使知道入學考試的重要性,卻不是所有人都執著於此,不,應該說「無法執著」。劇中的主要人物藝瑞在「天空之城」這個富裕的環境中,以家中父母出色的情報力和財力為基礎,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但像藝瑞的父母一樣,擁有良好職業和人脈,能夠接觸到有利於大學入學考試資訊的人很少。因此,像醫生世家通常會不斷讓後代也成為醫生,來強化他們的機會和特權。
《20 vs. 80的社會》(Dream Hoarders:How the American Upper Middle Class Is Leaving Everyone Else in the Dust, Why That Is a Problem, and What to Do About It)這本書的作者理查・里夫斯(Richard Reeves)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機會囤積」(opportunity hoarding),也就是說,發展在勞動市場成功所需的能力,實際上依照不同的成長環境,獲取這些能力的機會並不平等。衡量一個人的社會經濟階級受父母所屬階級影響的概念,在經濟學上被稱為「代際所得彈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IGE),愈難以擺脫父母所屬的階級,彈性就愈高。根據代際所得彈性的概念,父母的社經階級會成為子女的絆腳石,假如階級由高到低劃分為一到十,父母的階級是第九級,那麼即使子女有到第一級的成功能力,由於被父母絆住,只能停留在第四級。相反地,如果父母的階級是第一級,那麼即使子女只有第五級左右的能力,也可以因為父母的幫助爬升到第三級。
依靠父母而改變的能力發展機會是「排除」的另一種說法。從一開始就根本無法接觸到機會的人其實更多,社會階級不能說是單靠個人努力所獲得之能力的結果,依照能力獲得公平機會的錯覺,只是把特權正當化而已。實際上要在這個不公正也不平等的社會裡,想靠自己培養能力並取得成功是很難實現的夢想,而夢想著這種事的我們也健康不起來。
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過於龐大,想要在這樣的結構中成為例外的人展開了激烈的生存鬥爭。若想要在傾斜的運動場上進行勝算極低的戰鬥,就必須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更加狠毒,為了不失去屬於自己的那一份,不斷地與他人比較和競爭。愈是不安,就愈不會對他人有利他之心,只會想著自己要如何生存下去,此時所謂的共同體便不復存在,因為我們將會變得無法體諒隊友的失誤,也不能等待他們適應。在不平等的社會中受到的痛苦會成為傷害彼此的刀刃,而我們也將成為互相折磨的加害者和被害者。
在某個媒體的訪談中,曾經被問到職場霸凌的原因,雖然我沒能夠用整理好的句子流暢地回答,但腦中浮現了平常對不平等社會的苦惱。當然,造成職場霸凌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拚命守護的東西愈來愈多。要竭盡全力守住自己的位置,如果失去這個位置就再也沒有機會的迫切感,藉由對同事的尖銳態度和扭曲的補償心理表現出來,造成彼此的痛苦。大多數出生在普通家庭平凡的我們,為了不失去任何一次機會而一直處於不安之中。
雖然透過懲戒加害者可以讓大家對職場霸凌提高警惕,但在沒有職場霸凌的世界裡,從個人身上尋找職場霸凌的原因是不夠的。若是即使沒遇見富裕的父母,不是畢業於名門大學,不在大企業工作,也能過上不錯的生活,那麼競爭和不安才有可能大幅減少。真正放鬆的態度,只有在所有人都能過上好日子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踏實工作最後卻死了
我負責的第一個職業災害案件,是一位水族館的工作人員因為意外而在水中死亡。
從一開始負責這個職業災害死亡案件後,我想起了實習期間記錄的自殺職業災害案件。在那些全都於紙張上方打洞後用繩子綁起來的紀錄之中,有部分用夾子夾住紙張右側而無法翻頁,因為翻閱紙張的習慣,我不自覺地伸手想拿掉夾子,在那瞬間,文件標題「現場調查報告」卻吸引住我,我的手停了下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不該看的文件,裡面的東西可能會在腦中留下長久都難以忘記的殘影。果然直覺是對的,這份報告書裡完完整整地記錄了死者最初被發現時的現場照片。就像每個人所處的情況都不一樣,死者一定也有不得不選擇死亡的處境。負責這種案件的勞務士,必須重新拼湊該勞工自殺前的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要觀察當事人的精神病歷、心理變化、誘發精神壓力的條件、加重壓力的因素以及其他特殊事項等。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被認定為職業災害也不容易,而近距離觀察某個人的死亡這種事,光是想像就已經讓人心情沉重。
健康又年輕的人在工作時間內發生的事故中喪生,雖然乍聽之下會認為是明確的職業災害案件,但仔細一看,也存在一些模糊的討論空間。
第一個討論焦點是該勞工的死亡時間是他可以自由放鬆的休息時間,還是雖然沒有實際工作,但已經開始準備要投入工作的等待時間。休息時間是勞工可以自由使用的時間,因此事故和業務的關聯性會降低,相反地,如果是待機時間,隨時都要開始工作,因此和業務的關聯性會提高。第二個討論焦點是造成事故原因的行為是私人行為還是和工作業務相關的行動。工作時去上洗手間或吃午餐本身雖然不屬於業務範疇,但因為是在工作時間中理所當然會發生的行為,所以去洗手間或吃午飯時摔倒也被認定為職業災害。此外,在休息時間做伸展運動時發生事故,如果可以被看作是準備工作的行動,那麼就能被認可與工作業務有關聯性。我負責的死亡事件同時具有這兩個爭論點,是休息時間進行私人行為而死亡,還是待機時間進行業務相關行為而死亡,還有待商榷。
一般在進行案件釐清時,如果想要拿到必要的資料或確認事實關係,最快也最準確的方法莫過於詢問當事人,但是職業災害死亡案件的當事人已經不在了,無奈之下,我只能詢問死者家屬。雖然我努力不要在工作上參雜個人情緒,但我實在很難做到親自打電話給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當事人父母,具體詢問事故發生原委。儘管我把這件事擺到待辦事項的最後,先處理其他事情,但也不能繼續猶豫下去,我只能打起精神,按下號碼打了電話。
之後連遺屬撫卹金的申請準備都完成了,只剩等待勞動部的判定出爐,但某天卻突然接到通報說要召開判定委員會。勞動法規規定,如果是在工作過程中發生事故而申請職業災害的話,勞動部會自行判定,相反地,如果在工作中患上疾病,則由業務上的疾病判定委員會審議後進行判定。該事件是因執行業務上的事故而死亡的案件,卻突然說要召開判定委員會。此時的我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太生氣了,因為突發事故而死亡的人連一次喊痛的機會都沒有,如果知道這件事,他該會覺得多委屈啊。
臺灣情況:臺灣對於職業災害的認定可以分為因工作中發生的事故而造成的「職業傷害」,以及長期執行職務所導致的「職業病」。無論是職業傷害或職業病,都需要勞工所進行的勞務活動和損害結果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尤其是職業病,需要請醫生開立職業疾病診斷書,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也制訂了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作為依據。若勞雇雙方對診斷內容有爭執,可先向各縣市政府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申請鑑定,若仍有爭議再向勞動部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申請鑑定。
根據勞動部的立場,認為這起事故是由於心臟麻痺之後因腦部損傷而死亡,因此將心臟麻痺視為業務上的疾病,而召開判定委員會。最後我還是參加了判定委員會,並在現場用激昂的聲音對他們說:「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時候抽筋,但卻不會因此而死。就像抽筋這種情況,身體出現了異常症狀,偏偏當事者是在水中工作的人,所以水中這個工作環境特性才是導致死亡的關鍵,因此該事件不屬於判定委員會的審議對象。」
他們接受了我的意見,隔天勞動部表示決定不在判定委員會進行審議,他們會於內部重新審議後再與我聯絡。一週之後勞動部來電,我看了一下手機上的區域號碼,知道是勞動部,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後接起電話,他們說這個案件被認定為職業災害。我當時覺得真是太好了,本來就應該這樣,只是因為存在爭議部分才不得不擔心。
但我並沒有因此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通常在職業災害案件中,我們稱呼勞工時會使用「死者」或「災害者」的表達方式,但這次我卻使用了「該案件的勞工」,因為我不想直接公然寫出已經受傷而生病的人或者因受傷而死去的人。遺屬們可能會看到我寫的書面資料,每當看到死者一詞時,該會有多傷心呢?父母從子女出生到成長的每個瞬間都曾經感到幸福和喜悅,他們現在應該也還記得那個瞬間吧,所以我不想要像其他資料,留下彷彿認證當事人比父母先成為死者那樣的話語。但是職業災害竟然順利被批准了,我在那個瞬間才真的感受到該送他離開的感覺,此時才是真正的離別。
雖然沒有不令人遺憾的死亡,但是接到被認定為職業災害的通知後,卻讓人感到更加悲傷了,當事人不是因為什麼,只是像平常一樣工作,但是卻死了。他不是為了享受什麼榮華富貴,也不是在悠閒玩樂,他只是認真工作而已。他工作到命都沒有了,卻沒有留下最後一句話,也沒能發出一聲疼痛的喊叫,沒有比瞬間到來的死亡還要更為殘酷的事了。負責勞工案件的時候,我總以為贏了就好,但這件事卻讓我的心情很複雜,當然以對在工作中受傷、生病或死亡的補償來看,職業災害能夠順利得到批准當然是好事,但一方面也讓人惋惜為什麼當事人會在工作中死亡。
我無法理解那種當親近的人死去,或者原本存在的人消失了的情況。雖然不知道死亡是什麼,但是我知道死亡會讓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離別是新的相遇」、「結束是新的開始」這種話在死亡面前行不通,死就是死了。因此我們要盡全力預防死亡,《重大災害企業處罰法》就是對沒有預防職業災害發生的企業追究責任的法律。讓未能預防死亡的罪、逃避死亡責任的罪都能得到嚴正地處理,我衷心希望不要有人在工作中死去。我們是為了吃好住好而工作,因此我希望大家認真工作後都能過上好日子。現在到了真的該送走這位當事人的時候了。
臺灣情況:臺灣與職業災害較相關的法律主要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並於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針對一定規模事業單位、違反法令情節及重複違反情形等提高罰鍰額度,嚴懲未盡預防職災之責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