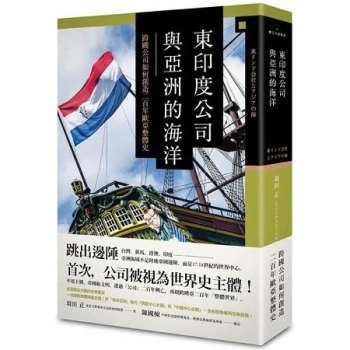前言
四百年前的世界
攤開並且眺望世界地圖,試著想像距今大約四百年前,西元一六〇〇年代初的世界,那是一個與我們目前生活的現代極為不同的世界。接著,再試著想像從美洲大陸往東繞行世界一圈。
今日的美國所在的北美大陸,當時大部分仍然是先住民居住的空間。來自英國的移民開始建設真正的居住地――詹姆斯鎮(Jamestown, Virginia)是在一六〇七年;而清教徒先輩(Pilgrim Fathers)搭乘五月花號(Mayflower)抵達這片大陸也不過是一六二〇年的事情。至於在中、南美洲,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驅使先住民與來自非洲大陸的奴隷挖掘銀礦,並且開始栽種商品作物――甘蔗。當時距離歐洲人「發現」新大陸已經超過一個世紀。阿茲提克和印加等先住民建立的帝國已遭毀滅,當地連一個現代獨立國家的雛形都還沒出現。
接下來看位在歐亞大陸西邊的歐洲。從十六世紀前半開始,歐洲由於基督信仰與儀式的差異,造成政治上持續不斷的對立。新教徒勢力強盛的北部低地諸國與強制實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的獨立戰爭結果大致抵定,最後終於建立尼德蘭七省(荷蘭)共和國。失去手工業與金融中心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Spain)受到嚴重打撃。此時中歐日耳曼諸侯之間的宗教對立正起,三十年戰爭即將爆發,之後就連法國、瑞典等周邊各國也被捲入其中。
另一方面,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頒布統一令,法國的亨利四世(Henri IV)頒布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使得兩國領內的宗教紛爭終於塵埃落定,王權的力量也逐漸強化,絕對王政的體制日益成形。至於主導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各城市的光芒在這個時期已經逐漸黯淡。當時歐洲地區的人口數推估約一億人左右。至於歐洲的東方,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House of Romanov)即將誕生,俄羅斯人的勢力終於開始延伸到烏拉山脈的東側。
接著把目光從歐亞大陸的西南方轉到南方。那裡有數個比鄰的帝國,由西到東分別是鄂圖曼帝國、薩法維帝國(Safavid dynasty)與蒙兀兒帝國。這些帝國的影響力遍及廣大的領域,規模遠遠超越歐洲的各個王國。當時蒙兀兒帝國的人口超過一億人,據說甚至多達將近一億五千萬人。推估當時世界總人口數也不過五億數千萬人,也就是說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蒙兀兒帝國。三個帝國的皇帝或政治強權者雖然都信奉伊斯蘭教,不過帝國領內的人民卻大多數是非伊斯蘭教徒。不過帝國內部宗教、宗派之間的對立與抗爭被強大的王權掩蓋,不像歐洲那樣浮出檯面,所以幾乎沒有成為問題。從現代反觀當時,十七世紀初可以說是這三個帝國的最強盛時期。鄂圖曼帝國與薩法維帝國的國境一帶雖然有激烈的紛爭,不過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這些帝國的統治極為穩定,也因此皇帝的權力與權威也顯得極為強勢。
十七世紀初的世界東南亞與現在則形成極大的對比,當時居住的人數極少,估計人口只有二千三百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五・五人。這個數據僅當時中國或印度的七分之一~六分之一、歐洲的一半而已。不過從兩百年前展開的海上交易活動依然活絡,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都形成了擁有一定規模的政權。比如北蘇門答臘的亞齊(Aceh)、西爪哇的萬丹(Banten)、南蘇拉威西的望加錫(Kota Makassar)等島嶼部的伊斯蘭教徒王國,還有位在大陸部信奉佛教的泰國阿育陀耶王朝、緬甸的東吁王朝(Taungoo Dynasty)等。
從歐亞大陸中部到東北部一帶,是土耳其裔諸語系和蒙古語系民族的世界。不過各民族並沒有統一的政治或軍事政權,對於周邊各地區的影響力也不及三百年前的「蒙古和平」時期。這些人大多是遊牧民族,所以相較於使用火槍、大砲等火器的定居軍隊,漸漸處於劣勢。
歐亞大陸東部則有一個醒目並且已經持續將近兩百五十年的巨大帝國――明帝國。明帝國底下統治的人口約有一億人,幾乎與蒙兀兒帝國相同。然而當時的明帝國正面臨財政危機。因為十六世紀末的日本軍在豐臣秀吉的令下出兵侵略朝鮮半島,明帝國為了救援朝鮮而派遣大軍與日本交戰。前後兩次的戰役對明帝國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支配階層的官僚之間、官僚與宦官之間的對立也日益嚴重,帝國正一步步地走向瓦解。另一方面,取代明帝國繼而建立清帝國的女真(jušen)人指導者努爾哈赤,於現在的中國東北地方建立後金,並逐漸擴大勢力。
最後來關注一下浮現於歐亞大陸東邊的日本列島。日本列島歷經了一百年以上的戰國時代之後,由徳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不過當時在大坂這座巨城裡,豐臣氏的勢力依舊健在,德川政權下的「天下統一」究竟有多穩定,此時還是未知數。當時日本列島的人口約有一千兩百萬到一千六百萬人左右。
除了以上的地區以外,大洋洲和非洲大陸應該也有許多居民各自營生。然而現代的我們對這兩個地區的政治與社會認識極為有限。因為不光是居住在大洋洲和非洲大陸的人沒有保留自己的歷史,也很少有人從外部造訪這些地方並留下記錄。這或許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政權、社會對外部世界的影響不大之故。
四百年的巨大變化
把以上描述的四百年前的世界和現代的世界相比,相信讀者應該會對兩者之間的差異之大感到驚訝吧?當時地球上的總人口數不到現在的十分之一。讀者可以試著想像一下擁有現代知識的我們,如果誕生在當時的世界會有什麼樣的感覺。當時沒有飛機、鐵路、沒有汽車,人口也極為有限,地球給我們的感受,想必遠比現在更廣大。當時地球上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馬。而不要說核能了,甚至連電力或瓦斯也沒有,所以夜晚漆黑一片,冬天也應該相當寒冷。尤其是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的這段時期,南法的隆河從一五九〇年到一六〇三年期間就曾經凍結三次,據說馬賽附近的海域在一五九五年也結冰了。
當時地球上將近六億人的總人口之中,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從事農業。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數帝國、國家,幾乎都仰賴領地內農民生產的農作物維生。營生的方式可以說完全不同於第三級產業(商業及服務業)就業者眾多、逐漸都市化的現今世界。
現在是全世界關注焦點的中東地域,在當時沒有伊拉克、以色列,也沒有巴勒斯坦或是阿富汗;現在的世界超級大國――美國也還沒誕生。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土與現在完全相同。也許會有人說:「才沒這回事呢!『日本』不就是嗎?」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當時德川政權的權力尚不及於北海道與沖繩。沖繩在那時是一個被稱琉球王國的國家。又譬如我們所稱的「英國」,在當時英格蘭、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也還沒統合。地球上許多地區的政治體,在那個年代尚未被視為所謂「國」或「國家」。不只南、北美洲大陸和大部分的非洲大陸是如此,就連北海道愛奴人的社會也是其中一個例子。有些地區即使存在著所謂的「國家」,國界也總是曖昧不明。現代所有的陸地、甚至就連海洋都區劃著清楚的國界線,但當時的地球完全不是如此。不過才短短的四百年,地球和居住其中的人類社會竟然就有如此大的轉變。究竟是為什麼呢?
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的歷史
這是個任何人都會感到疑惑的根本疑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只專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並不充分,還必須要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回顧世界整體的歷史才行。本書所要進行的嘗試,便是專注於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這兩百年間的歷史。因為筆者認為在過去的四百年裡,只要先了解了前半段兩百年的歷史,應該就能掌握明確的線索,思考之後兩百年間產生的變化吧?
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到十七世紀初的世界。乍看之下,會發現這個時期的世界存在著各別的政治權力、國家,以及地區,各自以獨自的節奏刻畫歷史。在歐洲、西亞、東北亞等地區,人們雖然因為移動而產生政治關係、發生軍事衝突,不過就整體而言,每個地區的人依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空間,看似與其他地區的人毫無關聯。政治權力的型態或社會特徴看起來也因地而異。實際上,在當時占地球總人口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部分終其一生只知道自己生長的環境和其周邊地區。當時的世界與現代完全不同,通信、交通沒有那麼發達,人員、物品、資訊也不像現代一樣急速並大量流通,討論當時的世界時,真的能像現代這樣把整個地球視為一個整體嗎?
答案得視回答時站在什麼樣的立場而定。地球上無論哪個地方的人和周遭的生態環境都會相互影響,雖然影響的展現方式會依地區與時代而有所不同。如果把影響的過程視為一個整體,並且試著以這樣的角度去掌握、去描述環境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那麼整個世界就必須當成一個整體來看。而直到近代為止,國家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都只不過是個配角而已吧?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現代,也特別需要這樣的歷史研究方法。筆者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想試著挑戰這種類型的歷史敘述。
至於本書所進行的嘗試則是透過把焦點擺在人員與物品的流通,考察世界的過去。因為至少從人員的移動和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早在十七世紀初,除了南半球部分地區和北極圏以外,大部分的世界確實已經串連在一起。南、北美洲的銀流通到中國、印度,東南亞的香辛料則被運往中國和西亞、歐洲。被當作商品的非洲奴隷也在新大陸勞動。中國的絲綢及陶磁器也從東南亞被運到西亞,甚至被運到歐洲,在歐亞大陸全境都十分受歡迎,印度的棉織品也被運往亞非各地。日本列島和串連世界的商品流通網絡也並非全然無關。當時列島各地產出的大量的銀被運往中國,換成中國的生絲和東南亞的染料、香木再運回日本。無庸贅言,當時商人與船員為了運送這些物品,活動橫跨世界各地。
當然,如果只是關注歐亞大陸,這座大陸的東、西之間早在紀元前就存在著交流活動。十三至十四世紀的蒙古時代,緊密連結歐亞大陸東西兩側的陸上和海上交通也相當地發達。不過直到十六世紀,連同非洲和新大陸在內的全世界,才透過商品流通與人的移動緊密連結,地球像這樣成為一個整體在人類史上還是第一次。當時或許還談不上如此大規模的流通,不過若從現在回顧當時,這個時期的人與物品的流通所促成的地球一體化,正是決定日後世界史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
透過東印度公司所見兩百年的世界史
本書試圖描述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世界史,而在其中擔任世界舞台引導者的正是「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就是在世界海上交通與商品流通一體化的背景下創立。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〇一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則成立於一六〇二年。其他包括法國、丹麥、瑞典、奥地利等西北歐各國,也在不久之後成立了相同性質的公司。就整體來看,這些公司都成立於十七世紀,到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就因為任務結束而解散。東印度公司在世界展開一體化的同時登場,並加速這股潮流,最後隨著在世界一體化的完成也失去存在的意義,因而消失在世界的舞台上。
以《興亡的世界史》為題的系列叢書其他著作,主要講述的是王朝、帝國、文明等的興亡。本書在其中可以說是相當特別的存在,因為本書企圖透過東印度公司的興亡,描述整體世界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的變化。這是一項極為大膽的嘗試,因為日本近一百年來的歷史研究,都以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這三門學科為基本架構,但如果不打散這樣的架構,把整個「世界」視為研究主體,就無法涵蓋本書所欲探究的領域。
過去的相關研究以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為單位進行,或是考察亞洲各國對於東印度公司的因應之策。主要的研究範疇舉例來說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軍印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之間的長崎貿易,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英國經濟產生的影響等等。其中即便只是一個個的小主題,留下的史料與相關研究成果的數量也都十分驚人。如果不把這些研究、史料統合起來,立基於一貫的視角進行考察,將無法描繪這兩百年的世界歷史。
老實說,一個人要挑戰如此巨大的主題可以說是一項無謀之舉。筆者本身在開始寫作後,也因為這項艱困的挑戰感受到數次挫敗。不過總有人得進行這項挑戰,因為目前的歷史研究需要以整體性的概念理解現代世界的建構,而身為一名歷史研究者,應該要正視這個課題。筆者基於這樣的想法,特別要求編集部變更原有的提案,本書也因此誕生。當然在日文的出版品中幾乎沒有同類型的書籍。雖然必須在有限的頁數裡以極為粗略的方式描述,但如果這樣的敘述方式能夠多少帶給讀者新的氣息,將令筆者感到欣慰。
本書所處理的各地區與主題,都必須參照龐雜的相關研究。特別是日本研究者對於日本史及中國史、印度及歐美研究者對印度史的研究成果,數量可說是數也數不清,全部讀完是不可能的。筆者雖然企圖將主要的研究成果全部讀過,不過受限於時間,也不敢說掌握得十分全面,所以想必會有來自各地區的歷史専家對本書的內容提出批評,比如內容不足、論點不是最新、重要論點有所疏漏等等。對於這些批評筆者都將欣然接受。然而除去這些不完美的部分,本書還是有幾分優點,譬如橫向闡述「世界史」的嘗試,以及把「日本」置於這樣的脈絡當中。本書主要針對日本讀者以日文撰寫而成,這樣的優點或許是理所當然。而筆者的嘗試是否成功,端看讀者最直接的感想了,所以希望有機會能夠得到來自讀者的回饋。
亞洲與東印度
東印度公司雖然誕生於歐洲,不過其主要活動的舞台卻是在歐洲以外的地區。本書將東印度公司的活動空間稱為「亞洲海域」。「亞洲海域」以地理位置來說,指的是包含印度洋、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在內的海域(各海域和其沿岸)。印度洋以印度次大陸為界,又可以分為西側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與東側的孟加拉灣,本書中將前者稱為印度洋西海域,後者稱為印度洋東海域。
「亞洲海域」是一個權宜之稱,因為從現在的地理學來看,烏拉山脈以西的歐亞大陸稱為歐洲,以東則稱為亞洲。把歐亞大陸一分為二的稱法,造成了迄今為止的各種誤解、偏見、對立以及反彈,這已經無須多加說明。歐洲中心史觀、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進歩歐洲與停滞亞洲、大亞洲主義等,這些就現在看來有問題的概念,都是源自於歐洲與亞洲對立的世界觀,也因此必須謹慎地使用這兩個詞彙。在本書裡「歐洲」和「亞洲」都屬於中立的地理用語。亞洲境域遠較於歐洲廣闊,因此會適時地在「亞洲」之前加上表示方位的「東」「西」等字眼,如「東亞」「西亞」,並將依敘述的必要性進行區別。此外,為了展現歐洲只是地理上的名稱,當本書欲把東印度公司誕生的英國、荷蘭、法國等諸國當成一個全體指稱時,會使用「西北歐」一詞。各位讀者也許已經對一再重複的說明感到厭煩,還請見諒。不過還是要再一次提醒,毫無批判性地使用同時夾雜概念與地理性意義的「歐洲」一詞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關於這件事情還有一點需要提醒。雖然說歐亞大陸在地理上區分為「歐洲」和「亞洲」兩大部分,不過人們的生活或是其整體的文化都無法明確地劃分為二。比如包含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包含印度在內的「南亞」,以及包含波斯在內的「西亞」,都不可以因為同屬「亞洲」,就認為彼此擁有相近但不同於「歐洲」的文化。所謂的「亞洲」,不過是一個把「歐洲」視為整體空間的人們所使用的語彙,用來統稱文化與自己不同的人所居住的東方空間。
東印度公司活動的十七、十八世紀,來自「歐洲」東印度公司的人在「亞洲」全境進行交易活動。基於這樣的背景,也不是不能將「歐洲」與「亞洲」當成對比性的詞彙使用。本書選用「亞洲海域」一詞,就是這個原因。亞洲在東印度公司的時代,可以說首度成為一個整體。然而,這不過是當時的「歐洲」人與生於後世的我們的看法。對於當時的「亞洲」人而言,並不曾想過大家都是亞洲人,與歐洲人屬於不同的群體。比如江戶時代的長崎人,就不曾認為自己與華人及來自於現在的印尼、侍奉出島荷蘭人的侍僕一樣都是亞洲人,只有荷蘭人是不同於大家的歐洲人。
還有另一個容易產生誤會的名詞必須事先說明,那就是「東印度」。在十七世紀初左右,西北歐的人所認知到的世界中,從歐洲乘船往西遭遇到的島嶼、大陸,直到新大陸南端的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Magellan)為止全都是「西印度」。加勒比海的島嶼群和南北美洲大陸都在這個範圍裡。至於從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沿岸的各地區則全都被視為「東印度」。因此,不光是現在的印度次大陸,包括從阿拉伯半島、波斯,經東南亞到中國的亞洲各地區全都被視為東印度各國,日本當然也包含在東印度裡。對於當時的歐洲人而言,不論是波斯、印度,還是中國、日本,全都屬於東印度的範圍。
所以,「東印度」一詞和「亞洲」一詞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性。不過,「亞洲」的地中海沿岸,也就是現今的土耳其、敘利亞一帶,就絕對沒有被視為東印度。中亞也沒有被歸入東印度的範圍。所謂的東印度,不過是乘船通過好望角往東後抵達的空間而已。日本就這層意義而言,也在企圖透過東印度公司探討世界歷史的本書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世界史與日本史密不可分。另外,本書在描述「東印度」各地之事時,原則上使用現在的地理名稱,所以印度指的就是現在的印度次大陸。
世界中心的亞洲海域
透過人員和物品的流通促成地球一體化的功臣,正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船員。十五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西班牙人開始進軍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並且從墨西哥橫渡太平洋,在一五七一年時抵達菲律賓的馬尼拉,接著在一五八四年,西班牙商船從馬尼拉抵達日本平戶。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通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到達印度後,轉眼間也來到了亞洲各地,並於一五四二年或四三年抵達日本的種子島,之後便以九州各地為主展開貿易活動。這在日本是眾所皆知的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就是因為有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國家,以及其商船與船員,地球上的許多區域才能透過物品的流通合為一體。
另外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亞洲海域在本書中所描述的時代,處於世界商品流通的中心地位。請各位讀者再一次回想十七世紀初世界的商品流通路徑,究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為什麼要特意來到亞洲海域呢?因為亞洲海域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而言就像一座寶山,充滿了香料、棉織品、絲織品、陶磁器等他們想要取得的商品。為了取得這些商品,只依靠歐洲生產的商品和貴金屬是不夠的,因此西班牙人運來新大陸的白銀,葡萄牙人則必須調度日本白銀,他們不是來亞洲海域販售歐洲生產的商品,而是被亞洲的商品吸引過來。正如同現在世界的金融活動以紐約的股匯市為中心一樣,在當時亞洲海域的交易行為,對世界整體的商品流通帶來極大的影響。更極端地說,亞洲海域才是當時世界的中心。
前言說明似乎有點過長了,接下來差不多該為各位讀者介紹亞洲海域。首先登場的是葡萄牙人,為了讓各位讀者能夠清楚了解東印度公司為何會出現、東印度公司進行交易的亞洲海域究竟是一處什麼樣的地方,我們必須再把時間往前回溯一百年,看看葡萄牙人當初出現在亞洲海域時,發生了什麼事情。時序為十五世紀末,地點是亞洲海域的西端,東非沿岸的莫三比克。
第八章_東印度公司的變質 ( 節選 )
法國東印度公司的挑戰
晚一步成立的法國東印度公司
繼英國、荷蘭之後,法國東印度公司也在一六六四年創立。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起步,為什麼會比先創立的那兩國的公司要晚那麼多呢?最大的理由是,法國並未在某個特定的港口城市,累積足以承受長時間往返東印度的商業資本,也沒有像荷蘭那樣,自發性地發展出由幾個城市合資出海的型態。
此外,法國與國土四周都是海的英國、或是北海沿岸有一條長海岸線的荷蘭相比,就如同深澤克己所指出的,地理條件更複雜一點。企圖往內陸發展的勢力,與分別指向大西洋、北海、地中海三個不同海域的勢力互相拉扯,難以整合成一個以東印度為目標的強大力量。筆者也想指出,巴黎在地理條件上與靠近遠洋的倫敦及阿姆斯特丹不同。法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巴黎,雖然透過塞納河與海相連,但大型船隻卻不能沿著塞納河駛入,所以巴黎無法像倫敦與阿姆斯特丹那樣,將政治、經濟中心與港灣機能整合起來。
法國政治家柯爾伯向法王路易十四進言:「王國必須取得與亞洲交易的利益,打破只有英國人與荷蘭人才能使用亞洲資源的現狀。」如果沒有他的強烈意志,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創立應該還會更加推遲吧。英國與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先從民間貿易商人的主導開始,再取得王權與共和國對其行動的認可,但法國的東印度公司卻靠著政權本身的意志成立。當然,由此誕生的公司,也帶有濃厚的公營色彩,幾乎可說是公共行政機關。最初準備的一千兩百萬法鎊以上的鉅額資本,大部分都由國王、皇親國戚、宮廷貴族、大臣及官員籌措。公司的經營也由身為國王下屬官僚的國務顧問負責。政府提供大量資本這點,與先行設立的英國及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同,穩定存在的資本理應使投資更容易進行。
公司每年使用公款營運的體制,一直持續到一六八三年柯爾伯去世為止,也展現出一定的成果。法國取得南印度的本地治里,與孟加拉地方的金德訥格爾(Chandannagar),作為亞洲的東印度貿易據點。就如同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在蘇拉特或阿巴斯設置商館,法國公司的商館也設在類似的港口。公司並且成功地在印度洋南部的波旁島(現在的留尼旺島)、法國島(現在的模里西斯島)設置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航海中繼基地。亞洲海域除了有印度裔、阿拉伯裔、伊朗裔等商人外,葡萄牙人、荷蘭及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已經在此建立基礎,相互之間展開不斷的競爭,後來加入的法國人應該很難打入市場。不過在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平戶商館長的法蘭索瓦‧卡隆(François Caron),與以建設本地治里而聞名的法蘭索瓦.馬丁(François Martin)等人的努力下,公司終於建立起在歐洲與亞洲之間進行定期貿易的基礎。
然而柯爾伯去世後,公司的經營就進入嚴峻的時代。路易十四接連在歐洲諸國發動戰爭,沒有多餘的資金能夠挪用為東印度貿易的公款。公司的活動直到路易十四的統治結束之前暫時停滯,必須等到西印度公司(在西印度與非洲經營貿易)成立、深得路易十五信任的蘇格蘭人約翰.羅(John Law)展開改革,公司才重新建立起新的體制,實現大幅度的發展。
「與政府一體化」的先驅
羅從一七一九年展開的一連串改革,具有三項特徵。第一,他將過去個別與海外進行貿易的東印度公司與西方公司(Compagnie de l’Occident)合併,創立新的法國印度公司。這裡所謂的「印度」包含東印度與西印度,因此在法語中採用複數形。羅並授權這間公司壟斷與歐洲以外各地區,也就是東印度、西印度以及非洲之間的貿易。因此嚴格來說,法國東印度公司自此之後就不復存在。但是難以維持壟斷貿易的與非洲、西印度間的貿易,在一七三一年已自由化。法國印度公司實際壟斷貿易的狀況依然與「東印度公司」類似,因此接下來筆者還是以「法國東印度公司」稱之。
後來的法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特徵,就是試圖將東西印度與非洲的貿易合併經營。在他們的構想當中,這整套貿易包含:使用東印度以棉織品為首的物產交換西非的奴隸,並將奴隸運到西印度,再把西印度砂糖種植園生產的砂糖運到歐洲販賣以取得白銀,以及使用這筆白銀購買東印度的物產。好壞姑且不論,這是個規模極為宏大的構想。如果這個構想運作順利,東印度公司在經過這三次交易後,理應能從整體貿易中獲取鉅額利益。但在大西洋壟斷砂糖與奴隸運送,對東印度公司而言卻是一件難事。畢竟橫渡大西洋的距離短,航行時間不長,因此不需要高額資本,許多創業家都跳進來參與。東印度公司不可能將這些創業家都趕出大西洋。
改革的第二個特徵是大幅增資,羅將東印度公司的半數股票對一般大眾開放,公司的特質也稍微有點接近「合股公司」。但國王是握有大約五分之一股權的大股東,其他股東沒有決議權。公司的董事也不像英國東印度公司那樣透過選舉選出。董事會提名的人選必須通過代表王權的「王權理事」審理,才能在國王的任命下成為董事。除此之外,財務總監也握有監督公司的權限。由此可知,法國東印度公司即使經過羅的改革,依然強烈受王權與政府左右。
改革的第三個特徵是在面對大西洋的布列塔尼地區南部,建設東印度公司專用的港灣都市洛里昂。公司過去都將航行據點設在聖馬洛、盧昂、第厄普等多佛海峽(Strait of Dover)沿岸的小鎮,然而一旦與英國發生戰爭,船隻就極有可能落入英國海軍的掌控。將港口設在大西洋沿岸,就能大幅減少這樣的危險性。公司在一七二〇年到三〇年的十年間,在本來一無所有的地方建築出了廣大的設施與城鎮。他們在深入大西洋的海灣沿岸,建造了造船所、船舶的艤裝基地、販賣東印度物產的年市使用的建築、保管商品的倉庫、事務所等設施,並在其周邊興建可容納四千人以上的住宅,作為公司的宿舍使用。都市的名稱洛里昂(L’Orient 東方)清楚顯示出,這是一座專為東印度貿易打造的城鎮。公司的經營總部位在巴黎,負責會計、人事、與政府之間的交涉等等,但貿易的實務則全部集中在洛里昂,因此能夠實現效率極高的作業。
這一連串的改革,大幅強化了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財政與營運基礎,公司在往後的四十年間,事業扶搖直上。如果只看一七二〇年到六九年的這五十年間,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隻艤裝數為五百二十八艘、英國東印度公司為八百〇五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一千六百五十三艘。由於法國的船隻整體而言噸數多半較大,因此若以噸數進行比較則差距更小。這點從三間東印度公司在歐洲販賣的商品總額表中,應該就能清楚看出。法國公司的交易量雖然遠不及荷蘭公司,但在一七四〇年代或五〇年代初,數字卻直逼英國公司。
法國東印度公司的特徵一言以蔽之就是與政府一體化的先驅。公司擁有政府駐外機構的特質,以政府的意志為背景展開經營。第九章將會提到,這與進入十八世紀後半,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採用的體制相同。就這層意義而言,法國東印度公司可說是時代的先驅。無論如何,由法國這個大國政府主導的法國東印度公司展開的大膽挑戰,對英國與荷蘭的公司而言,已構成嚴重的威脅。
本地治里與布林多內
法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拓展商館的方法,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較為接近。東南印度的本地治里,其定位就相當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公司在這裡設置總督府與高等評議會,負責管理孟加拉地區的金德訥格爾、馬拉巴爾海岸的馬埃州評議會與其他商館(摩卡、巴斯拉、阿巴斯、勃固等)。總督與六至十二名左右的評議員組成的高等評議會,除了統轄東印度的貿易之外,也擁有與當地政權或其他歐洲人交涉、交戰、談和的權限。在本地治里管轄下的都市也握有司法權與東印度公司派駐當地的職員的人事權。
東印度公司的正規職員人數因時期而異,譬如一七二七年為六十八人、四七年為九十四人、五七年為一百〇七人,半數以上在本地治里任職。底下還設有書記、通譯、僕從等為數眾多的當地職員,人數不下於一千人。
此外,由於法國國王只承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便以這樣的方針為後盾來此活動。在他們的運作下,本地治里總督禁止了天主教以外的宗教,甚至因為實際採取高壓手段而數度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東印度的所有神職人員人數,至少不下於一千人。就這點而言,本地治里與荷蘭及英國東印度公司管轄下,對宗教包容的城市大相逕庭。
法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樣,允許職員在亞洲境內進行貿易活動。因此許多職員在阿拉伯半島、波斯灣、中國及東南亞從事私人貿易。接下來便以出生於聖馬洛的艤裝業者之家,後來成為東印度公司航海士的布林多內(一六九九~一七五三)為例,為各位進行介紹。
布林多內身為東印度公司的船副,有權利以個人名義在出發港口購買一定金額的商品,利用公司的船隻免費乘載運輸,並在返回港口後販賣商品為自己牟利。一開始公司允許他攜帶的商品購買額度,大約是一萬八千法鎊。一七二七年,聖馬洛的銀行家與其友人、顧客,願意提供這筆融資給布林多內,條件是三年後還款,利息為百分之三十五。他首先與馬德拉斯的英國貿易商人,以及本地治里的亞美尼亞貿易商人合作,買下四百五十噸的船「本地治里號」。
這艘船最初的航行是往返於孟加拉與金德訥格爾之間,第二次航行則是經果阿前往阿拉伯半島的摩卡,最後再回到本地治里。第二次航行共有十五名投資者,其中九名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其餘的六名則分別是以南印度為據點的商人,包括兩名亞美尼亞人、一名英國人、以及三名泰米爾人。第一次航行的獲利率為百分之十六、第二次航行則為百分之三十。
布林多內隨後找來擅長航海術的弟弟,逐漸擴大事業。他們購買新的船隻,投入馬拉巴爾海岸、阿拉伯半島以及菲律賓馬尼拉等地的貿易。
他在寄給聖馬洛的銀行家的信中寫下這段話:
「買賣的機會在這個國家要多少有多少。最主要的重點是前往印度各地區的艤裝。(中略)航海幾乎沒有損失的風險,遇難的情況也很少見。利潤的幅度大約在百分十五至五十之間。不過無論航海順利與否,一整年的利潤大約都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一七三三年,布林多內從經營六年的亞洲地區貿易收手,回到法國結婚。結婚契約書上記載了他的財產。海上貿易的投資、匯票、鑽石、黃金等所有財產加起來,總額高達三十萬法鎊。我們雖然不知道他原本的財產有多少,但從他必須靠著借來一萬八千法鎊,才能展開亞洲境內的貿易這點來看,他的巨額財產絕對是從貿易事業中取得。布林多內原本考慮在法國展開新事業,卻在不久之後成為公司派駐波旁島及法國島的總督,回到印度洋。其經過留待下節再述。
「國旗」代表的意義
許多來自西北歐的人,靠著在亞洲各地之間的貿易累積龐大的財產,比方說第六章介紹過的耶魯、丹尼爾・夏丹,以及本章介紹的布林多內。當然,不是每個人的事業都獲得成功,最近的研究也認為不應該過度強調歐洲人的這類活動。即使如此,這些對當地狀況不一定稱得上了解、言語及溝通也應該處於劣勢的歐洲人,為什麼能夠看似輕而易舉地就取得大筆財產呢?
亞洲海域的投資與其他地區相比更容易獲利,這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根據淺田實的研究指出,英國境內一般的商業獲利率在十七世紀末是百分之六至十二、大西洋貿易的平均獲利率約為百分之十五。但孟加拉地區的內陸交易獲利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至於孟加拉與波斯之間的海上貿易,獲利率更是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在亞洲海域進行一次交易,就有可能獲得龐大利潤。
法國研究者奧德萊爾(Haudrère)也指出另一個理由,那就是歐洲人的船都升上國旗。升上國旗的船除了宣告擁有強大的槍炮武力之外,也代表如果遭到襲擊,升上相同國旗的僚船將會直接前來復仇。的確,除了歐洲船之外,印度洋海域世界的船不一定屬於某個國家。筆者也數度指出,這片海域的「陸上帝國」對於海上貿易及貿易商人有多麼地漠不關心。所以當地商人的艤裝船不會升上國旗。如果比較兩種船的安全性,就不難理解貿易商人寧願將貨物託付給歐洲商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