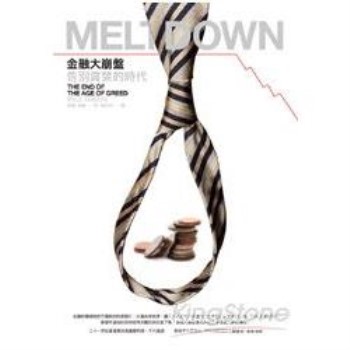前言
我們經歷的這次事件,多數世人原以為永遠不會發生。2008 年10 月,自由市場瀕臨瓦解,政府出手拯救。政府不出手,自由市場就會完蛋。事隔一年,可以清楚看出政府心有餘而力不足。財政和貨幣刺激方案換來18 個月的喘息機會,但已不再管用,這次危機因此進入第三階段,也是最關鍵的時刻。
2010 年春季,先前扳倒銀行的劇毒開始讓政府垮台:債務重整和違約的危險從希臘擴散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了拯救歐元,政府在採行這個世代未曾體驗過的撙節措施。兩年來,各國貨幣競相貶值,還是無法使世界貨幣和貿易恢復平衡;為走出危機所採取的各種不同路線造成嫌隙,侵蝕全球化經濟,只不過這些嫌隙包裹著一層客套的外交辭令。同時,在危機最核心的地方,人們老是愛製造投機性泡沫的傾向,讓造成危機的金融界菁英繼續撈錢。
我在2008 年9 月之後的幾個月完成「金融大崩盤」的第一版, 當時金融體系還處在混亂狀態。我是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垮台那天的午夜動筆,在2009 年2 月完成,那時英國政府第二次對銀行伸出援手,但英美兩國政府尚未採取量化寬鬆措施。
因此,不可避免,第一版只能是個期中報告。以下我列出當時我並不知道的事實,並概要說明這些事實怎樣讓我起初的分析更加完整,或是跟我的分析有矛盾之處。這本更新版沒有更動原本的敘述,也就是一到八章,但在最後加了兩個新的篇章。其中第一部份從2009 年3 月英美政府改採量化寬鬆(QE)措施講起,談到希臘危機、拯救歐元計畫和英國2010年6 月的緊急預算。這14 個月如今看起來像是危機的第二階段,主要特色是振興方案和疲弱的復甦。危機的第三階段可能出現雙底衰退,有些國家面臨通貨緊縮螺旋,而且各國再度競相採取拯救經濟方案,可能導致全球化前功盡棄。
我發現自己正好處在對的位置,可以好好報導2008 年9月的事件,而從那時候開始,我幾乎沒有片刻休息。雷曼兄弟宣布倒閉的那個周末,我在底特律感覺很不真實的裝飾藝術風格廢墟中訪問失業又失去房子的福特汽車廠員工。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在紐約和華盛頓,然後在倫敦白廳(Whitehall,譯註:英國政府部會集中地)地下通道走動,看著英國政府採行第一次紓困計畫,11 月再回到華盛頓採訪20 國集團(G20)的高峰會。
此後我曾在東歐部份地區發生問題時前往觀察;我曾在雅典街頭採訪罷工的工人;我曾到中國,看見他們大刀闊斧,把經濟政策從追求出口轉為推動基礎建設,期間曾碰到一整個火車車廂的民工,他們原本在深圳的工廠上班,如今要到內蒙古開挖鐵路隧道,連回甘肅省老家看孩子的機會都沒有。
我目睹G20 忙著擬訂危機因應措施,我被趕進美國國務院地下室的一個房間,牆上用膠帶貼著一些手寫的標示說,布希總統馬上要把政權轉移給歐巴馬。在倫敦、匹茲堡和多倫多,我看見G20 臨時取代了多項沒有發揮效用的多邊條約。當初訂定這些條約,是要用來治理全球經濟。
我看見知名的經濟研究機構舉雙手投降,學者們不敢相信親眼所見,主張自由市場的右派人士假裝危機並未發生,依照凱因斯理論提出的粗糙解決方案走進死胡同,而凱因斯如果在世,他自己就完全可以預料到這個結果。
在本書第一版的前言中,我寫道:「已開發國家面臨的抉擇是:快速果斷地把銀行收歸國有,同時採行以公共支出和創造就業機會為主的財政刺激方案,不然經濟衰退就會變成長期性的全球大蕭條。」
情況後來有些變化。美國確實推行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中國投入的金額更大,但真正扭轉局勢的是政府改採量化寬鬆政策,也就是巨額貨幣刺激方案,美國的金額達到1.75 兆美元,英國達到2000 億英鎊,在本文截稿前,這些錢還在透過銀行流入整個經濟體系。如果我在本書第一版低估了改採量化寬鬆政策的可能性,那是因為政壇存在不利於採行這項政策的跡象。英國財政大臣達林(Alistair Darling)在2008 年12 月底告訴我,如果英國走上量化寬鬆的道路,會是出於政治考量,但他並無特定立場;如今我們知道,英格蘭銀行那時才開始研究這類技術選項。2009 年1 月中,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 老遠跑到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演說,他要在場的英國重要決策人士別搞量化寬鬆,並說他也不會那麼做。但2009 年3 月,本書第一版付印之後,英美兩國政府都選擇了量化寬鬆。我在新版的第九章討論這項做法的影響和缺失。
英美兩國決策高層砸錢把陷入困境的企業國有化,同時防止經濟倒退,到了2009 年初夏,危機明顯已經遏止。直接將企業收歸國有的例子並不多見。蘇格蘭皇家銀行(RBS)、HBOS、美國國際集團(AIG)、花旗集團(Citigroup)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模式是準國有化,也就是政府在這些機構持有決定性的
我們經歷的這次事件,多數世人原以為永遠不會發生。2008 年10 月,自由市場瀕臨瓦解,政府出手拯救。政府不出手,自由市場就會完蛋。事隔一年,可以清楚看出政府心有餘而力不足。財政和貨幣刺激方案換來18 個月的喘息機會,但已不再管用,這次危機因此進入第三階段,也是最關鍵的時刻。
2010 年春季,先前扳倒銀行的劇毒開始讓政府垮台:債務重整和違約的危險從希臘擴散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了拯救歐元,政府在採行這個世代未曾體驗過的撙節措施。兩年來,各國貨幣競相貶值,還是無法使世界貨幣和貿易恢復平衡;為走出危機所採取的各種不同路線造成嫌隙,侵蝕全球化經濟,只不過這些嫌隙包裹著一層客套的外交辭令。同時,在危機最核心的地方,人們老是愛製造投機性泡沫的傾向,讓造成危機的金融界菁英繼續撈錢。
我在2008 年9 月之後的幾個月完成「金融大崩盤」的第一版, 當時金融體系還處在混亂狀態。我是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垮台那天的午夜動筆,在2009 年2 月完成,那時英國政府第二次對銀行伸出援手,但英美兩國政府尚未採取量化寬鬆措施。
因此,不可避免,第一版只能是個期中報告。以下我列出當時我並不知道的事實,並概要說明這些事實怎樣讓我起初的分析更加完整,或是跟我的分析有矛盾之處。這本更新版沒有更動原本的敘述,也就是一到八章,但在最後加了兩個新的篇章。其中第一部份從2009 年3 月英美政府改採量化寬鬆(QE)措施講起,談到希臘危機、拯救歐元計畫和英國2010年6 月的緊急預算。這14 個月如今看起來像是危機的第二階段,主要特色是振興方案和疲弱的復甦。危機的第三階段可能出現雙底衰退,有些國家面臨通貨緊縮螺旋,而且各國再度競相採取拯救經濟方案,可能導致全球化前功盡棄。
我發現自己正好處在對的位置,可以好好報導2008 年9月的事件,而從那時候開始,我幾乎沒有片刻休息。雷曼兄弟宣布倒閉的那個周末,我在底特律感覺很不真實的裝飾藝術風格廢墟中訪問失業又失去房子的福特汽車廠員工。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在紐約和華盛頓,然後在倫敦白廳(Whitehall,譯註:英國政府部會集中地)地下通道走動,看著英國政府採行第一次紓困計畫,11 月再回到華盛頓採訪20 國集團(G20)的高峰會。
此後我曾在東歐部份地區發生問題時前往觀察;我曾在雅典街頭採訪罷工的工人;我曾到中國,看見他們大刀闊斧,把經濟政策從追求出口轉為推動基礎建設,期間曾碰到一整個火車車廂的民工,他們原本在深圳的工廠上班,如今要到內蒙古開挖鐵路隧道,連回甘肅省老家看孩子的機會都沒有。
我目睹G20 忙著擬訂危機因應措施,我被趕進美國國務院地下室的一個房間,牆上用膠帶貼著一些手寫的標示說,布希總統馬上要把政權轉移給歐巴馬。在倫敦、匹茲堡和多倫多,我看見G20 臨時取代了多項沒有發揮效用的多邊條約。當初訂定這些條約,是要用來治理全球經濟。
我看見知名的經濟研究機構舉雙手投降,學者們不敢相信親眼所見,主張自由市場的右派人士假裝危機並未發生,依照凱因斯理論提出的粗糙解決方案走進死胡同,而凱因斯如果在世,他自己就完全可以預料到這個結果。
在本書第一版的前言中,我寫道:「已開發國家面臨的抉擇是:快速果斷地把銀行收歸國有,同時採行以公共支出和創造就業機會為主的財政刺激方案,不然經濟衰退就會變成長期性的全球大蕭條。」
情況後來有些變化。美國確實推行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中國投入的金額更大,但真正扭轉局勢的是政府改採量化寬鬆政策,也就是巨額貨幣刺激方案,美國的金額達到1.75 兆美元,英國達到2000 億英鎊,在本文截稿前,這些錢還在透過銀行流入整個經濟體系。如果我在本書第一版低估了改採量化寬鬆政策的可能性,那是因為政壇存在不利於採行這項政策的跡象。英國財政大臣達林(Alistair Darling)在2008 年12 月底告訴我,如果英國走上量化寬鬆的道路,會是出於政治考量,但他並無特定立場;如今我們知道,英格蘭銀行那時才開始研究這類技術選項。2009 年1 月中,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 老遠跑到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發表演說,他要在場的英國重要決策人士別搞量化寬鬆,並說他也不會那麼做。但2009 年3 月,本書第一版付印之後,英美兩國政府都選擇了量化寬鬆。我在新版的第九章討論這項做法的影響和缺失。
英美兩國決策高層砸錢把陷入困境的企業國有化,同時防止經濟倒退,到了2009 年初夏,危機明顯已經遏止。直接將企業收歸國有的例子並不多見。蘇格蘭皇家銀行(RBS)、HBOS、美國國際集團(AIG)、花旗集團(Citigroup)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模式是準國有化,也就是政府在這些機構持有決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