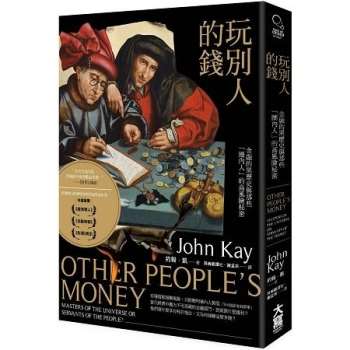第1章 當代金融小史
從危機到危機
我能預測天體的運行,卻料不到群眾的瘋狂。─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在金融史上,投機導致的繁榮與蕭條一直重複出現。
一六三〇年代,荷蘭商人哄抬鬱金香售價,一株上等球莖和一棟房子等價。一個世紀後,英國社會的上流人物瘋南海泡沫。一八四〇年代,鐵路熱潮抓住大眾的想像。一九二〇年代,股票和土地的價格的起落導致華爾街崩盤和經濟大蕭條。崩盤與大蕭條對政治和經濟都帶來立即影響:政治上的極端主義的興起,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戰後在多數已開發國家都確立了受到管制的資本主義。同時,蘇聯帝國在東歐也維持著某種程度的金融穩定。因應華爾街崩盤而推行的管制措施,以及布列敦森林會議所訂下的全球金融架構,沿用了幾十年。那是個繁榮靜好的年代,只是到後期也明顯可見通貨膨脹方興未艾。美國是全球經濟的霸主,但同時德國的復甦也寫下「經濟奇蹟」,日本則是以其他地區都前所未見的經濟成長擠身工業強權之列。法國迎來「黃金三十年」,英國也經歷「狀況從來沒這麼好過」的時期。金融危機並非颶風或地震這類無法避免、人類得學習因應的自然災害。金融危機是人類行為所導致,經濟政策可擴大或降低其頻率與規模,事實也是如此。圖一所顯示的模式十分驚人。十九世紀看得出繁榮與蕭條的模式重複出現。二十世紀初期,危機的振幅加大,最後在華爾街崩盤和經濟大蕭條時達到巔峰。接著出現一段史無前例的穩定局面,之後隨著金融化加快,波動性也穩定增加,一直到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哪裡出了錯?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固定匯率體系已然崩解,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衰退。隨著這些因素一一被檢討,金融體制的保守主義也遭棄守。一九七一年,尼克森總統宣布放棄黃金本位制(四十年來美國財政部一直將黃金價格定在每盎司三十五美元)使得美元兌其他貨幣貶值。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引發的政治危機,導致阿拉伯國家讓石油價格劇烈攀升,也讓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進一步受到挑戰。由於許多產油國無法輕易花掉新增的收入,許多石油消費國也不願減少支出,銀行於是打造出一個看似有利可圖的生意,將石油輸出國賺得的油元回頭借給石油輸入國。花旗公司總裁華特.瑞斯頓(Walter Wriston)曾說過一句名言:國家是不會破產的。嚴格來說,他說的沒錯。但是對銀行體系或全球金融來說,缺乏任何有序的司法或行政程序來處理民族國家的債務違約情事,證明是禍而不是福。很多在這段時期背上債務的國家,償債的能力或意願都微乎其微。非洲國家得再借更多錢才能支付原本的利息,經常動用到援助或開發資金。
因此,這些國家積欠國際機構的款項日益增加。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第三世界債務問題」仍沒完沒了。沒錯,國家是不會破產,但也不一定要還債。
一九八〇年代初,美元利率劇漲,好幾個借貸美元的拉丁美洲國家開始違約。此一危機的解法替未來設下了鮮明前例: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在必要時出手,以保護美國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央行的援助和種種會計方法聯手助攻下,銀行的虧損規模被美化。銀行家、管制機構和政府都希望(通常也都情有可原),受牽連銀行能用交易回復償債能力,最好還能累積點現金。勞氏銀行和花旗公司辦到了。這些半死不活的僵屍銀行又活了過來。然而,這種已無償債能力卻仍持續交易的僵屍銀行,將會是再三發生的金融危機後不斷出現的主題。
股市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穩定上揚。但這集中持股、積極交易的新世界露出新的弱點。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國股市創下單日下跌百分之二十的空前絕後事件。這是如何發生、又為何會發生,迄今仍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釋,不過有些人把矛頭指向「投資組合保險」,透過此一機制,金融機構會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限制跌幅曝險。其他國家股市也出現跌勢,只是幅度較小。不過幾天後,股市回復上漲趨勢。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甚至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美國股市指數在二十分鐘內下跌超過百分之五。有些股票的報價莫名其妙,「埃森哲」(Accenture)是一美分,「蘋果電腦」(Apple)是十五萬美元。在本書原文版送印時,警方衝進倫敦西南豪斯洛市一間不起眼的雙併樓房,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理由逮捕一名男子,指稱是該名男子在自家客廳交易才引發這波股市怪象。但駭人的實情是,在短線交易以電腦演算法進行的情況下,沒有人完全了解到底發生甚麼事。縱然這次事件並未帶來嚴重的後果,但科技失控的景象是令人難安的未來凶兆21。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美國國庫券市場也經歷同樣無從解釋的「閃電崩盤」。
現代第一個龐大的投機泡沫,見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的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在熱潮最盛時,皇居的地價據說高過整個加州。不管是真是假,都無法長久,泡沫後來破滅。日本本國和外國的投資客蒙受巨大損失:今天日本股市指數連全盛期的一半都不到。之前倚靠價格膨脹的資產作為擔保而大肆擴張的日本銀行,陷入名存實亡的破產。這些僵屍銀行讓二十年來的日本經濟陷入惡夢。基金經理人安東.馮.格塔米爾(Antoine van Agtmael)聲稱是他率先喊出「新興市場」一詞22。把新國家納入全球交易體系,是一九八〇年之後的三十年間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最先擁抱變化的是東南亞國家。香港和新加坡成為交易中心。日本戰後的成長有韓國和台灣效法在先,泰國、印尼、菲律賓也接踵其後。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東歐共產政權垮台,其中許多國家都採行了資本主義及其金融制度。中國和印度出現轉型式的經濟變革。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成為商業新天地。甚至有跡象顯示,好些非洲國家也正擺脫淒涼的後殖民經濟傳統。於是「新興市場」成了投資題材。但金融市場的好東西永遠不嫌多。一股腦將資金投在新興市場(尤其是亞洲),讓這些國家的外債來到無法支撐的水位,國內的價格也過高。
一九九七年泰銖崩盤,正是因為外資趁泰銖仍有殘值時搶救他們的部位。效應波及至全亞洲。隔年,俄國也出現債務違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解除了部分新興市場危機,以貸款資助國家,也隱晦地接濟魯莽融資的銀行。該組織對亞洲經濟體施加極為顧人怨的撙節方案。「華盛頓共識」一詞廣泛用來形容,援助交換條件背後的標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私有化和資本市場自由化,都助長國內與國際的金融化。一九九〇年代,受過教育的一般大眾和金融社群開始使用網路。一九九五年是網路熱潮的起點:摩根士丹利的瑪麗.米柯(Mary Meeker,之後人稱網路女王)發表報告點出網路商機,「網景」(Netscape,設計出第一代普及的網路瀏覽器)公開發行上市。到了一九九九年,記者、企業顧問、商業人士都在談「新經濟」。從來沒賺過錢,未來也不會賺到錢的公司,卻以夢幻高價在全球證券交易所掛牌。對新經濟的需求滿溢到,只要推銷人員能找到一丁點和高科技的關聯,就會有人要。
在二〇〇〇年初新經濟泡沫的最末階段,還有美國聯準會為了防杜「千禧蟲」(亦即電腦程式在處理「二〇〇〇」日期時的錯誤)危機,而注入美國經濟的流動資金助陣。二〇〇〇年春,新經濟熱潮來到可預期的終點(大家早已料到)。聯準會於是調降利率,施行更多的刺激金融措施。更大的股票市場一開始固然也和網路股崩盤同步走跌,但在便宜資金的激勵下,股價從二〇〇一年秋天開始回升。
新經濟泡沫事件激起媒體的注意力。不過,下一個,而且仍是最大的一波熱潮興衰,卻沒有被大眾所注意到。儘管對於關心人士而言,有很多徵兆顯示前景不穩,但從網路泡沫破滅到全球金融危機肇興這段時期,世人太過自滿於現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魯卡斯(Robert Lucas)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說:「防堵經濟不景氣時的核心問題,已大致上解決了。」另一位曾被任命為聯準會主席的學院派經濟學者班.柏南克(Ben Bernanke)喊出「大穩健」(the Great Moderation)一語,用以描述應該會出現的的經濟穩定新時代。
回頭來看,此時期的關鍵發展是資產擔保證券的交易日盛,特別是各金融機構之間的房屋抵押貸款擔保證券,以及後續的擔保債權憑證。人們誤以為這樣包裝的證券很有保障,讓這項資產頓時洛陽紙貴。而信用違約交換市場發展似乎更加助長了大眾的信心,因為若是標的證券違約,其衍生的證券將會獲得償付。當時沒有考慮到,萬一訂出這類契約的機構遇上廣泛違約狀況時,能有多大的償付能力。以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該行透過信用違約交換擔保超過五千億美元的證券,因此當於二〇〇八年該行信用評遭調降時,其大眾對債券投資組合安全性的信心等於是崩盤。對資產擔保證券的無盡需求,導致蒐羅的資產品質越來越低。在許多美國城市,房貸業務會鼓吹無實質償債能力的人貸款。但評比機構(和聯準會)依然根據過時的資料庫來推估預期,以為房價仍處於微幅走揚,而貸方個個財務穩健。即便美國房價只是暫時停漲,這棟紙牌屋也會應聲崩跌。二〇〇八年,對銀行帳面證券價值的擔憂,令人進而擔心起銀行自己的負債額度。全球金融體系之所以沒有徹底崩解,全是因為政府大幅介入,規模前所未見。政府基金提供流動資金給銀行體系,直接讓已破產或垂危的機構重整資本結構。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的事件之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或許還排得上是史上第一。
全球金融危機起自美國,隨即波及到大西洋對岸,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於歐洲銀行購買了大量源於美國的問題證券。不過,下一場危機倒是產自歐洲。歐元區原本是要將法國、德國,以及與德國經濟關係緊密國家的貨幣上互相連動,後來卻演變成政治工程,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乃至於希臘都包含在內。
這些國家於一九九九年採行共同貨幣(希臘於二〇〇一年加入),使得歐陸利率一致。交易人不再對不同歐元區政府的歐元債務大小眼,相信往後不只匯率風險,就連以往用來區分治理完善國家與公共財政不穩的國家的信用風險也都就此打消。德國和法國的銀行向北歐國家借貸歐元,再出借給南歐國家。到了二〇〇七年,希臘政府公債的殖利率,只比德國政府同類公債稍微高一些。包括希臘在內的多個國家,也趁機利用這看似取之不竭的低利信貸。
在歐洲銀行窮於應付全球金融危機之際,其資產品質也備受質疑。信用風險的評估變得謹慎許多,歐元區各國的利率差異也再度擴大。隨著利率走揚,以希臘信用進行再融資變得更困難,希臘債券變顯得沒那麼有吸引力。二〇一一年,該國的債務實質上已經違約。但希臘並非歐元區唯一的麻煩。愛爾蘭整個銀行體系於二〇〇八年崩潰。西班牙則是出現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歐元區其餘成員國——葡萄牙、義大利、賽普勒斯——也各有各的經濟與政治難關。所有債務服務都有代價。每有一個小危機,歐洲央行介入的範疇和規模也與之俱增。二〇一二年,歐洲央行新任總裁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保證,會「不計一切」保住歐元區。有鑒於有權發行歐元的歐洲央行手上還有很多資源可用,這個承諾暫時穩住了歐元區危機。
這一連串危機的導火線都極為不同,從新興市場債務問題、新經濟泡沫、資產擔保證券違約,到歐元區政治角力,但這些危機的基本機制卻是一樣的,全來自於經濟環境的真實轉變:像是新興經濟體的興盛、網路的進展、金融工具的創新、歐洲採用共同貨幣。先見之明者荷包滿滿。而交易員的跟風心態讓更多人與錢投入相關資產。越來越多資產被定錯價,但因為價格是往上走,交易人也多半是賺錢的。
儘管這些重新估值都有看似縝密的合理根據,但事實是這些估價都是種情緒化的過程,心理學家大衛.塔克特(David Tuckett)在訪談多數交易員的過程中曾這麼形容。一旦興頭起來後,在信念背後的情緒發展通常會指向單一路徑……驅策人向前的興奮之情,以及往後退時會經歷的痛苦,後者意味著美夢破滅,放棄期待。大家覺得持懷疑論調者是在潑冷水,為了要避開這些挫折感,在這個時段肯定要特別攻擊他們。他們對新故事所提出的疑惑必須予以駁斥,在駁斥的過程中有嘲笑與中傷27。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資產的錯誤定價獲得修正,使投資人與各機構損失慘重。央行與政府出手救援,一來保護金融部門,二來讓非金融類經濟的損害降到最低。這批現金與流動資產於是助長了下一場在不同經濟活動領域的危機。
危機接二連三,程度也越來越嚴重。經濟榮景通常是由金融體系之外的事件所引發。經濟蕭條看起來似乎也源於外部因素:例如俄羅斯違約、美國房價走跌、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但這些都是導火線,而不是解釋。危機機制是現代金融體系的固有環節。現代金融體系不只是很容易變得不穩定,而是少了這個會製造重複危機的機制,這個金融體系就不會是現今的樣貌。這一點會在後文第二章和第四章更清楚地浮現。
從危機到危機
我能預測天體的運行,卻料不到群眾的瘋狂。─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在金融史上,投機導致的繁榮與蕭條一直重複出現。
一六三〇年代,荷蘭商人哄抬鬱金香售價,一株上等球莖和一棟房子等價。一個世紀後,英國社會的上流人物瘋南海泡沫。一八四〇年代,鐵路熱潮抓住大眾的想像。一九二〇年代,股票和土地的價格的起落導致華爾街崩盤和經濟大蕭條。崩盤與大蕭條對政治和經濟都帶來立即影響:政治上的極端主義的興起,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戰後在多數已開發國家都確立了受到管制的資本主義。同時,蘇聯帝國在東歐也維持著某種程度的金融穩定。因應華爾街崩盤而推行的管制措施,以及布列敦森林會議所訂下的全球金融架構,沿用了幾十年。那是個繁榮靜好的年代,只是到後期也明顯可見通貨膨脹方興未艾。美國是全球經濟的霸主,但同時德國的復甦也寫下「經濟奇蹟」,日本則是以其他地區都前所未見的經濟成長擠身工業強權之列。法國迎來「黃金三十年」,英國也經歷「狀況從來沒這麼好過」的時期。金融危機並非颶風或地震這類無法避免、人類得學習因應的自然災害。金融危機是人類行為所導致,經濟政策可擴大或降低其頻率與規模,事實也是如此。圖一所顯示的模式十分驚人。十九世紀看得出繁榮與蕭條的模式重複出現。二十世紀初期,危機的振幅加大,最後在華爾街崩盤和經濟大蕭條時達到巔峰。接著出現一段史無前例的穩定局面,之後隨著金融化加快,波動性也穩定增加,一直到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哪裡出了錯?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固定匯率體系已然崩解,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衰退。隨著這些因素一一被檢討,金融體制的保守主義也遭棄守。一九七一年,尼克森總統宣布放棄黃金本位制(四十年來美國財政部一直將黃金價格定在每盎司三十五美元)使得美元兌其他貨幣貶值。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引發的政治危機,導致阿拉伯國家讓石油價格劇烈攀升,也讓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進一步受到挑戰。由於許多產油國無法輕易花掉新增的收入,許多石油消費國也不願減少支出,銀行於是打造出一個看似有利可圖的生意,將石油輸出國賺得的油元回頭借給石油輸入國。花旗公司總裁華特.瑞斯頓(Walter Wriston)曾說過一句名言:國家是不會破產的。嚴格來說,他說的沒錯。但是對銀行體系或全球金融來說,缺乏任何有序的司法或行政程序來處理民族國家的債務違約情事,證明是禍而不是福。很多在這段時期背上債務的國家,償債的能力或意願都微乎其微。非洲國家得再借更多錢才能支付原本的利息,經常動用到援助或開發資金。
因此,這些國家積欠國際機構的款項日益增加。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第三世界債務問題」仍沒完沒了。沒錯,國家是不會破產,但也不一定要還債。
一九八〇年代初,美元利率劇漲,好幾個借貸美元的拉丁美洲國家開始違約。此一危機的解法替未來設下了鮮明前例: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在必要時出手,以保護美國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央行的援助和種種會計方法聯手助攻下,銀行的虧損規模被美化。銀行家、管制機構和政府都希望(通常也都情有可原),受牽連銀行能用交易回復償債能力,最好還能累積點現金。勞氏銀行和花旗公司辦到了。這些半死不活的僵屍銀行又活了過來。然而,這種已無償債能力卻仍持續交易的僵屍銀行,將會是再三發生的金融危機後不斷出現的主題。
股市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穩定上揚。但這集中持股、積極交易的新世界露出新的弱點。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國股市創下單日下跌百分之二十的空前絕後事件。這是如何發生、又為何會發生,迄今仍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釋,不過有些人把矛頭指向「投資組合保險」,透過此一機制,金融機構會交易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限制跌幅曝險。其他國家股市也出現跌勢,只是幅度較小。不過幾天後,股市回復上漲趨勢。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甚至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美國股市指數在二十分鐘內下跌超過百分之五。有些股票的報價莫名其妙,「埃森哲」(Accenture)是一美分,「蘋果電腦」(Apple)是十五萬美元。在本書原文版送印時,警方衝進倫敦西南豪斯洛市一間不起眼的雙併樓房,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理由逮捕一名男子,指稱是該名男子在自家客廳交易才引發這波股市怪象。但駭人的實情是,在短線交易以電腦演算法進行的情況下,沒有人完全了解到底發生甚麼事。縱然這次事件並未帶來嚴重的後果,但科技失控的景象是令人難安的未來凶兆21。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美國國庫券市場也經歷同樣無從解釋的「閃電崩盤」。
現代第一個龐大的投機泡沫,見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的日本股市和房地產。在熱潮最盛時,皇居的地價據說高過整個加州。不管是真是假,都無法長久,泡沫後來破滅。日本本國和外國的投資客蒙受巨大損失:今天日本股市指數連全盛期的一半都不到。之前倚靠價格膨脹的資產作為擔保而大肆擴張的日本銀行,陷入名存實亡的破產。這些僵屍銀行讓二十年來的日本經濟陷入惡夢。基金經理人安東.馮.格塔米爾(Antoine van Agtmael)聲稱是他率先喊出「新興市場」一詞22。把新國家納入全球交易體系,是一九八〇年之後的三十年間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最先擁抱變化的是東南亞國家。香港和新加坡成為交易中心。日本戰後的成長有韓國和台灣效法在先,泰國、印尼、菲律賓也接踵其後。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東歐共產政權垮台,其中許多國家都採行了資本主義及其金融制度。中國和印度出現轉型式的經濟變革。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成為商業新天地。甚至有跡象顯示,好些非洲國家也正擺脫淒涼的後殖民經濟傳統。於是「新興市場」成了投資題材。但金融市場的好東西永遠不嫌多。一股腦將資金投在新興市場(尤其是亞洲),讓這些國家的外債來到無法支撐的水位,國內的價格也過高。
一九九七年泰銖崩盤,正是因為外資趁泰銖仍有殘值時搶救他們的部位。效應波及至全亞洲。隔年,俄國也出現債務違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解除了部分新興市場危機,以貸款資助國家,也隱晦地接濟魯莽融資的銀行。該組織對亞洲經濟體施加極為顧人怨的撙節方案。「華盛頓共識」一詞廣泛用來形容,援助交換條件背後的標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私有化和資本市場自由化,都助長國內與國際的金融化。一九九〇年代,受過教育的一般大眾和金融社群開始使用網路。一九九五年是網路熱潮的起點:摩根士丹利的瑪麗.米柯(Mary Meeker,之後人稱網路女王)發表報告點出網路商機,「網景」(Netscape,設計出第一代普及的網路瀏覽器)公開發行上市。到了一九九九年,記者、企業顧問、商業人士都在談「新經濟」。從來沒賺過錢,未來也不會賺到錢的公司,卻以夢幻高價在全球證券交易所掛牌。對新經濟的需求滿溢到,只要推銷人員能找到一丁點和高科技的關聯,就會有人要。
在二〇〇〇年初新經濟泡沫的最末階段,還有美國聯準會為了防杜「千禧蟲」(亦即電腦程式在處理「二〇〇〇」日期時的錯誤)危機,而注入美國經濟的流動資金助陣。二〇〇〇年春,新經濟熱潮來到可預期的終點(大家早已料到)。聯準會於是調降利率,施行更多的刺激金融措施。更大的股票市場一開始固然也和網路股崩盤同步走跌,但在便宜資金的激勵下,股價從二〇〇一年秋天開始回升。
新經濟泡沫事件激起媒體的注意力。不過,下一個,而且仍是最大的一波熱潮興衰,卻沒有被大眾所注意到。儘管對於關心人士而言,有很多徵兆顯示前景不穩,但從網路泡沫破滅到全球金融危機肇興這段時期,世人太過自滿於現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魯卡斯(Robert Lucas)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說:「防堵經濟不景氣時的核心問題,已大致上解決了。」另一位曾被任命為聯準會主席的學院派經濟學者班.柏南克(Ben Bernanke)喊出「大穩健」(the Great Moderation)一語,用以描述應該會出現的的經濟穩定新時代。
回頭來看,此時期的關鍵發展是資產擔保證券的交易日盛,特別是各金融機構之間的房屋抵押貸款擔保證券,以及後續的擔保債權憑證。人們誤以為這樣包裝的證券很有保障,讓這項資產頓時洛陽紙貴。而信用違約交換市場發展似乎更加助長了大眾的信心,因為若是標的證券違約,其衍生的證券將會獲得償付。當時沒有考慮到,萬一訂出這類契約的機構遇上廣泛違約狀況時,能有多大的償付能力。以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該行透過信用違約交換擔保超過五千億美元的證券,因此當於二〇〇八年該行信用評遭調降時,其大眾對債券投資組合安全性的信心等於是崩盤。對資產擔保證券的無盡需求,導致蒐羅的資產品質越來越低。在許多美國城市,房貸業務會鼓吹無實質償債能力的人貸款。但評比機構(和聯準會)依然根據過時的資料庫來推估預期,以為房價仍處於微幅走揚,而貸方個個財務穩健。即便美國房價只是暫時停漲,這棟紙牌屋也會應聲崩跌。二〇〇八年,對銀行帳面證券價值的擔憂,令人進而擔心起銀行自己的負債額度。全球金融體系之所以沒有徹底崩解,全是因為政府大幅介入,規模前所未見。政府基金提供流動資金給銀行體系,直接讓已破產或垂危的機構重整資本結構。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的事件之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或許還排得上是史上第一。
全球金融危機起自美國,隨即波及到大西洋對岸,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於歐洲銀行購買了大量源於美國的問題證券。不過,下一場危機倒是產自歐洲。歐元區原本是要將法國、德國,以及與德國經濟關係緊密國家的貨幣上互相連動,後來卻演變成政治工程,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乃至於希臘都包含在內。
這些國家於一九九九年採行共同貨幣(希臘於二〇〇一年加入),使得歐陸利率一致。交易人不再對不同歐元區政府的歐元債務大小眼,相信往後不只匯率風險,就連以往用來區分治理完善國家與公共財政不穩的國家的信用風險也都就此打消。德國和法國的銀行向北歐國家借貸歐元,再出借給南歐國家。到了二〇〇七年,希臘政府公債的殖利率,只比德國政府同類公債稍微高一些。包括希臘在內的多個國家,也趁機利用這看似取之不竭的低利信貸。
在歐洲銀行窮於應付全球金融危機之際,其資產品質也備受質疑。信用風險的評估變得謹慎許多,歐元區各國的利率差異也再度擴大。隨著利率走揚,以希臘信用進行再融資變得更困難,希臘債券變顯得沒那麼有吸引力。二〇一一年,該國的債務實質上已經違約。但希臘並非歐元區唯一的麻煩。愛爾蘭整個銀行體系於二〇〇八年崩潰。西班牙則是出現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歐元區其餘成員國——葡萄牙、義大利、賽普勒斯——也各有各的經濟與政治難關。所有債務服務都有代價。每有一個小危機,歐洲央行介入的範疇和規模也與之俱增。二〇一二年,歐洲央行新任總裁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保證,會「不計一切」保住歐元區。有鑒於有權發行歐元的歐洲央行手上還有很多資源可用,這個承諾暫時穩住了歐元區危機。
這一連串危機的導火線都極為不同,從新興市場債務問題、新經濟泡沫、資產擔保證券違約,到歐元區政治角力,但這些危機的基本機制卻是一樣的,全來自於經濟環境的真實轉變:像是新興經濟體的興盛、網路的進展、金融工具的創新、歐洲採用共同貨幣。先見之明者荷包滿滿。而交易員的跟風心態讓更多人與錢投入相關資產。越來越多資產被定錯價,但因為價格是往上走,交易人也多半是賺錢的。
儘管這些重新估值都有看似縝密的合理根據,但事實是這些估價都是種情緒化的過程,心理學家大衛.塔克特(David Tuckett)在訪談多數交易員的過程中曾這麼形容。一旦興頭起來後,在信念背後的情緒發展通常會指向單一路徑……驅策人向前的興奮之情,以及往後退時會經歷的痛苦,後者意味著美夢破滅,放棄期待。大家覺得持懷疑論調者是在潑冷水,為了要避開這些挫折感,在這個時段肯定要特別攻擊他們。他們對新故事所提出的疑惑必須予以駁斥,在駁斥的過程中有嘲笑與中傷27。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資產的錯誤定價獲得修正,使投資人與各機構損失慘重。央行與政府出手救援,一來保護金融部門,二來讓非金融類經濟的損害降到最低。這批現金與流動資產於是助長了下一場在不同經濟活動領域的危機。
危機接二連三,程度也越來越嚴重。經濟榮景通常是由金融體系之外的事件所引發。經濟蕭條看起來似乎也源於外部因素:例如俄羅斯違約、美國房價走跌、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但這些都是導火線,而不是解釋。危機機制是現代金融體系的固有環節。現代金融體系不只是很容易變得不穩定,而是少了這個會製造重複危機的機制,這個金融體系就不會是現今的樣貌。這一點會在後文第二章和第四章更清楚地浮現。